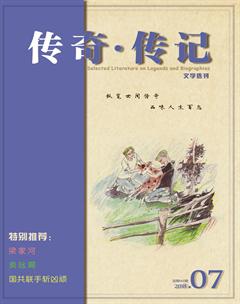“紅色女特工”的燃情歲月
胡遵遠
文媛經常以親身經歷告訴他人:沒有偉大的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沒有千千萬萬革命戰士的浴血犧牲,就不會有今天的幸福生活。
少年走上革命路
1911年,安徽省霍山縣一個禮教森嚴的趙氏門宅里(當時屬霍山縣,現劃歸金寨縣)添了一個女娃娃,這個女娃娃就是文媛。文媛的母親生了四個孩子,其中三個都夭折了。當時,文媛的祖父雖然在霍山縣衙門供職,但家里早已是入不敷出,瀕臨破產。在文媛還不會叫爸爸的時候,父親就因病離開了人世。她六七歲時,祖父請了一個私塾先生到家里教文媛識字。在那個重男輕女的時代,女孩子是不準到外面上學的,只能在家塾里識幾個字。
就在那個時候,文媛家里發生了意外,這使得文媛對舊的禮教產生了懷疑和動搖。她有一個尚未出嫁的姑姑,未婚夫因病死去。為了守節,姑姑竟然吞服黃金和鴉片膏自殺身亡,而家里人還為此大辦喪事,宣揚這位可憐的“烈女”。這個悲劇使文媛內心受到很大震動。
祖父去世后,趙氏家族的根基開始動搖。文媛和堂姐妹慧媛、信媛以及侄女國璧沖破舊禮教的樊籬,離開家庭,來到霍山縣城唯一的一所女子高小求學。從此,文媛在婦女解放的道路上不斷尋求,逐步成為這個封建家族的叛逆者。
文媛最初并不懂得什么是革命,也不知道如何去革命。當時,霍山女子高小有一位從安慶來的語文老師,名叫郭誠淑,為人正派,和藹可親。文媛她們都喜歡同她接近,直到參加革命后,文媛才知道她和她的愛人曹逸新都是中共地下黨員,并與從事兵運工作的劉淠西同志保持單線聯系。劉淠西的家鄉在霍山桃源河。大革命失敗后,組織上派他從武漢回到霍山工作,不久打進了諸佛庵民團,擔任團總。他按照黨的指示,積蓄革命武裝,準備暴動。
在郭老師的教育下,文媛的堂妹慧媛加入了青年團。在這段時間里,文媛的見識比在家鄉時多了許多,還知道了有一個“打富濟貧”的共產黨。當時,郭老師和其他地下黨員經常給文媛她們講革命道理、講封建制度下低人一等的婦女地位、講包辦婚姻帶來的悲劇,等等。這些都激發了文媛她們對舊社會的不滿,她們懂得了只有起來鬧革命,消滅封建剝削制度,婦女才能徹底解放。從此,這些不曾引人注目的黃毛丫頭,如文媛、吳兆瑾、汪寶華、孫光璧、慧媛、信媛、國璧等人,開始在縣城里鬧起革命來,弄得當地地主豪紳寢食難安。縣里有個洪科長,依仗權勢欺壓窮人,她們便點名道姓地反對他。洪科長一下子慌了手腳,便下帖子請她們到陳家花園吃飯,企圖拉攏她們。文媛嚴詞拒絕,弄得他十分難堪。
與此同時,劉淠西也常來給她們講一些革命道理,講掌握革命武裝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有一次,他對她們說:“鬧革命,光搞鼓動和宣傳還不行,還要有自己的軍隊。”經過劉淠西的教育,文媛等人的思想覺悟提高了,在他的介紹下,文媛和信媛都加入了青年團。劉淠西成了文媛她們參加革命的引路人。
1929年11月,六霍起義爆發后,劉淠西的身份暴露了,國民黨下了通緝令。他被迫轉移到安慶,不久郭誠淑也去了安慶。
革命熔爐初煉身
劉淠西走了以后,文媛等人就與組織失去了聯系,好像大海里的幾葉小舟,不知飄向何方。為了盡快同組織取得聯系,文媛和吳兆瑾商量后于1929年下半年也到了安慶。
到達安慶后,文媛設法找到了郭誠淑。按照她的安排,文媛上了安慶女子職業學校,住在附近的宜城旅社,靠地下黨組織解決食宿問題。文媛名義上是學生,實際上并沒有去上過課。她和吳家藏、劉樂英一起,常常到外面散發傳單,張貼《告士兵書》等。
不久,由于壞人告密,劉淠西、郭誠淑被捕了,文媛和吳兆瑾也被捕了。被捕的前一天,文媛還在散發傳單,身上留了一份《告士兵書》,想晚上看看。被捕時,這份《告士兵書》就綁在自己的腿上。文媛借故上廁所,想偷偷銷毀這份傳單,但有軍警跟隨監視,一直下不了手。被抓到公安局后,眼看就要受審,這時,她看見劉淠西被軍警押著先去過堂。他用手提著腳鐐,態度從容。當他走到文媛的面前時,壓低嗓門偷偷地說:“你們是學生,是來考學的,不要亂說。”文媛是第一次被捕,加上身上揣了一份傳單,心里不免有些緊張,正不知怎么辦好,經劉淠西指點,心里一下子亮堂起來了。
敵人審問劉淠西時,他大義凜然,痛罵國民黨反動派禍國殃民,說完,隨手抓起一個電燈泡,向公安局長狠狠地砸去。頓時,堂上大亂,好幾個殺氣騰騰的軍警撲上去,把他按倒在地,拳棒相加,還給他換上了八斤重的大腳鐐和手銬。劉淠西的手腫得像饅頭似的,鮮血浸透了衣裳。文媛見了劉淠西受傷的身體,心里一陣難過,情不自禁地哭了起來。
輪到文媛被提審時,公安局長問:“你是不是共產黨?”文媛裝作聽不懂,反問他:“什么是共產黨?”他又問:“你是不是國民黨?”文媛又反問:“什么是國民黨呀?”文媛當時年齡不大,又是個女學生,敵人并沒有把她放在眼里,便把她和其他人一起關在公安局的看守所里。
一次,一個軍警點名點到文媛時,把文媛念成文暖,文媛有意不回答。他便沖她吼道:“為什么不答話?”文媛說:“我不叫文暖,我叫文媛啊。”還故意把“文暖”兩字念得重一點。那個軍警知道念錯了字,臉漲得通紅。
在看守所里,文媛和一些鴉片販子關在一起,看守是個老婆子。那時,文媛身上的那份《告士兵書》還沒有處理掉,她便把這件事偷偷地告訴了吳兆瑾。吳兆瑾聽后責怪她:“死丫頭,你還不趕快處理掉!”文媛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怎么辦呢?她只好晚上在被子里,把《告士兵書》一頁頁地搓爛,然后丟進馬桶里。誰知紙團在水面漂浮起來。第二天一早,她對看守婆子說:“我去倒馬桶。”看守婆子不準。文媛只好把馬桶拎出來,一直盯著值日的軍警把馬桶倒掉,一顆懸著的心才落下來。
敵人雖然多次提審,卻從她嘴里掏不出半點東西來。他們沒辦法,又把文媛轉到法院的一個大牢里。在那里,文媛認識了剛從蘇聯回國被捕的袁溥之、王惠芬等共產黨人。到法院以后,她們幾個人把字條夾在生活用品里,互相傳遞,相互鼓勵,同時把里面的情況轉告給黨組織。黨組織則為她們四處奔波,托人說情作保,請律師。法官先后兩次審問文媛,她一口咬定自己只是學生,是來安慶考學,是被無緣無故抓來的。當局抓不到把柄,最后只好把文媛和另外幾個人放了出來。
寶劍鋒從磨礪出
文媛又回到宜城旅社住下。很快,組織上派人同她取得了聯系,并指示她繼續留在安慶,建立一個秘密聯絡點。工作不到兩個月,情況突然發生了變化,從霍山來了一批土豪劣紳,說文媛她們都是共產黨,要求國民黨省黨部把她們捉拿歸案。文媛無法在安慶容身了,組織上決定讓她立即轉移到上海,并派了一個姓張的交通員護送她。離開安慶那天,正好下著雨,交通員為文媛雇了一輛黃包車。他們順利到了碼頭,上了船,順流東下。這時已經是1930年的七八月間了。
船行了三天,抵達上海。文媛拿著介紹信,找到王日叟同志,接上了頭。組織上安排文媛住在愛文義路中央軍委機關,同她一起的還有徐子勝的愛人譚冠軍。大約一個月后,文媛就到了江蘇團省委,擔任文件保管工作。1931年底,文媛又轉到江蘇省委,擔任內部交通工作。在這里,文媛成了一名光榮的中國共產黨黨員。
在那些白色恐怖的日子里,從事黨的地下工作是要冒很大的風險的,但是為了勞苦大眾翻身得解放,文媛她們早已把個人的生死置之度外。為了打掩護,文媛的穿著打扮完全是學生模樣,上身穿白洋布褂,下面穿一條黑裙子,這是當時女學生的流行裝扮。
有一次,文媛在送文件的途中突然遇到緊急情況:警笛狂吹,租界的外國巡捕拿著警棍,瘋狂地驅趕著馬路上的行人。文媛被隔在馬路一邊,但要把文件送出去,必須穿過這條馬路。怎么辦?文媛強作鎮定提著小皮箱,壯著膽子走到一個“紅頭阿三”(指印度巡捕)面前,鎮定地說:“啥事情?能走嗎?”“紅頭阿三”上下一瞄,就用警棍把文媛扒向馬路的另一邊。她趕緊穿過人群,順利地把文件送到目的地。
還有一次,文媛送文件時在電車上遇到了停車搜查。文件裝在小皮箱里,銷毀已經來不及了,又下不了車,情況十分危急。文媛想,只有沉著冷靜,才不會惹人注意。她裝著看熱鬧的樣子,主動靠近上車搜查的警察。警察見她是個學生,便不把她放在眼里,還把她趕下車。一下車,她便立即鉆進人流中去。
文媛還干過“交通報警”的活兒,哪里出了問題,就馬上發出報警通知。有一次,為了安全起見,組織上通知文媛她們馬上轉移,并派一個小報童,趁著給文媛她們送報紙時,把寫著“家父病重,快回南京”的紙條夾在里面。文媛一看,知道情況危急。這時,組織上又派了一位女交通員到另一個接頭點,與她們聯絡。上級要文媛她們搬到儉德公寓,等候安排。為了不引起鄰居的懷疑,文媛告訴二房東,說外出走親戚,過幾天就回來。到儉德公寓安頓下來后,有一部分同志,如文媛的愛人陳一新(安徽金寨人)被派到江西蘇區去工作。文媛因為懷孕,行動不便,便留在上海,在潘漢年的領導下繼續從事地下工作。
有一次,潘漢年為了刺探敵人的重要情報,需要出席一個有頭面人物參加的宴會。為了配合行動,組織上要文媛以其女友的身份陪同潘漢年。事前,潘漢年要文媛化一下妝,打扮成上層婦女的模樣,還告訴文媛,在宴會上要注意聽,別亂說,要說也只能說些應酬的話。在宴會上潘漢年談吐風雅,應對從容。三杯酒下肚,這些人的話就多了起來。潘漢年善于引話,不知不覺間就將需要了解的情報從他們的嘴里套了出來。事后,潘漢年表揚文媛任務完成得很好。
革命征途逢偉人
1932年下半年,文媛離開上海,去了江西蘇區。直到長征開始后,文媛才從江西回到上海,在上海她又見到了潘漢年。潘漢年見到文媛和陳一新夫婦,第一句話就說:“你們辛苦了。”接著便問寒問暖,還問到他們上山同敵人打游擊的情況。文媛就把離開蘇區以后的情況說了一遍,一直談到太陽落山。潘漢年聽后,動情地說:“你們總算活著回來了,又可以為黨工作了。我先為你們洗塵,招待你們夫妻下館子。”隨后,潘漢年陪著他們到落腳地點——博實小學坐了一會兒。臨走時,他還一再叮嚀,要他們安心等待,他將設法送文媛和陳一新到蘇聯去學習。后來,潘漢年雖然被安排去西安工作,但他還給文媛他們來信說正在辦護照,準備送他們和王稼祥一起去蘇聯。再后來,由于多種原因,去蘇聯的事落空了。這樣,文媛他們又在上海做起了地下工作。
文媛住在上海機關時,恰逢陳賡被營救出獄,組織上決定讓陳賡暫時同文媛他們住在一起,等待安排。
陳賡是我軍卓越的高級將領。他從小就在父親那里學得一身好武功,十四歲投軍,是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生。他到蘇聯學習過軍事,參加過八一南昌起義。在起義部隊向潮汕進軍途中,不幸左腿負重傷,最后輾轉到上海。那時,他和一批經過考驗的同志從事黨的政治保衛工作,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同敵人進行了許多次驚心動魄的斗爭。1930年后,他到鄂豫皖蘇區任紅軍師長,在一次戰斗中又負了傷。他就是在上海養傷期間被捕的。因為他性格開朗,談吐幽默,再加上他那傳奇般的經歷,所以文媛喜歡同他在一起聊天。有一次,文媛好奇地問他:“你怎么把大獨裁者蔣介石從死人堆里救出來了?”陳賡風趣地說:“那時陳炯明是反革命,我以為蔣介石是跟孫中山一起鬧革命的,誰知道我背的是一條狐貍呢?”
原來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蔣介石擔任過黃埔軍校校長,他和陳賡有過“師生之誼”。蔣介石對陳賡的才能十分賞識,在黃埔學生東征討伐軍閥陳炯明的戰斗中,由于蔣介石指揮失誤,被打得潰不成軍,虧得陳賡冒著槍林彈雨背著他沖出重圍,救了蔣介石一命。為此,蔣介石曾許諾要重用陳賡。“四一二”政變,蔣介石暴露了反革命的嘴臉,陳賡與他分道揚鑣,蔣介石成了陳賡的階級敵人。在這次被捕期間,不管反動派施美人計,還是用“南京衛戍司令”的高官厚祿來引誘;也不管宋美齡屈尊感化,還是校長親自出馬勸降,陳賡都是大義凜然,不為功名利祿、酒色財氣所動,保持了一名共產黨人的崇高氣節。
聽了陳賡的話,文媛哈哈大笑,更加深了對他的敬意。
秘密戰線創佳績
1932年下半年,組織上派文媛到江西蘇區工作。這次去江西,要從廣東、福建繞道,組織上安排了一位廣東籍的交通員護送她。他們在吳淞口坐上了一艘外國商船,在海上航行了幾天后到達廣東汕頭,再到大浦、潮州。他們白天不敢行動,怕被敵人發覺,全靠晚上摸黑走小路,一走就是一百多里。沿途翻山越嶺、風餐露宿,有時還要冒險穿過敵人埋下的鐵蒺藜。最后,終于從廣東到了福建,又從福建來到江西。到江西后,與當地黨組織取得了聯系,他們另派了一位交通員,護送文媛到瑞金沙洲壩。
沙洲壩離瑞金城很近,是中共中央機關的所在地。當時,鄧穎超任中央秘書長,文媛的丈夫陳一新任中央機要科長。文媛來了以后,就在鄧穎超的領導下任機要員,負責譯電,與在白區工作的同志進行電訊聯系。當時,鄧穎超兼任機關的黨支部書記,她對文媛這樣的青年要求很嚴格,每周都要召開一次黨小組會,加強思想教育。那時,根據地正處在國民黨幾十萬大軍的包圍之中,蔣介石不斷發動“圍剿”,在敵人的封鎖下,給養運不進來,生活條件可想而知。沒有鹽,沒有糧食,大家只好吃硝鹽,吃死馬、死驢的肉,很多人全身都浮腫起來。可能是擔心文媛不能適應根據地艱苦斗爭的環境,文媛剛到瑞金不久,鄧穎超就找她談心。先問了一些工作情況,接著又關心地詢問生活上適應不適應。文媛一一做了回答。鄧穎超關切地對文媛說:“這里工作、生活條件雖然與上海不一樣,但時間一長就會習慣的。”她還告訴文媛要注意克服困難、增強信心。鄧穎超的心很細,在以后的日子里,在可能的情況下,盡量改善文媛她們的工作和生活條件。
當時,中央蘇區在敵人的重重包圍中,對外聯絡十分困難,因此無線電就成了中央蘇區同上海黨組織及其他根據地進行聯系的唯一通訊工具,而密碼則成了核心機密。靠著它,黨中央才能及時了解敵人的動態,黨中央的聲音才能及時傳到各個紅色根據地,領導各地的反“圍剿”斗爭。可以說,電臺和密碼已成了中央根據地的生命線。正因為如此,敵人也在千方百計地破壞我們的通訊設備。那時敵人經常派飛機來轟炸瑞金,其中一個重要目標就是我們的電臺,他們妄圖截斷我們的紅色電波。鄧穎超非常重視電臺和機要科的工作,經常同文媛他們談通訊工作的意義,要求他們以黨的利益為重,時刻做好通訊聯系工作。為了防止敵人的飛機轟炸,文媛他們常常帶上密碼本和紙筆躲到山上辦公。到隱蔽的地點,得爬山越嶺,還要穿過荊棘樹林,衣服常常被刮爛,腿腳被劃傷,弄得全身血跡斑斑,但不管多么困難,哪怕是犧牲生命,也要絕對保證電碼本的安全。因為它是黨中央的耳朵和眼睛!每次出發前,鄧穎超總要反復叮囑文媛他們,要膽大心細,一定要把密電碼保護好,千萬不能遺失。有時還親自動手,幫助他們檢查著裝。有一次,文媛已經藏好了密碼本,正準備上山,鄧穎超走過來關切地問,密電碼放好了沒有?會不會掉下來?文媛把放密電碼的地方指給她看,她認真地察看了一番,覺得沒問題,這才放下心來。鄧穎超工作認真,要求嚴格,在她嚴謹細致的作風影響下,雖然環境異常艱苦,但是文媛他們總能順利地完成任務。
虎口脫險得安寧
長征開始時,文媛因為懷孕,不能跟隨大部隊行動。組織上指示她和其他四位女同志(陳潭秋的夫人朱月清,潘漢年的夫人徐幼文,夏曦的夫人趙英和黃秀珍)回到上海繼續搞地下工作。她們只好同留下來打游擊的小部隊一起與敵人周旋,一直隨軍打到了贛東。這時,軍隊傷亡很大,張鼎丞指示她們原地隱蔽。部隊負責人還告訴她們,如果被捕,就說是福建人民政府派她們到江西來參觀的。
文媛等五位女同志離開部隊輾轉到了會昌,躲在山上,沒有吃的,就到附近的地里挖紅薯來充饑;沒有房子住,就住在露天野地。一次,她們找了半天才找到一個野豬窩,里面堆著厚厚的枯枝殘葉,躺上去倒很軟和。晚上,野豬回來了,嗅到了生人氣味,在附近繞來轉去。幾個人被嚇醒了,有的拿棍子,有的摸石頭,壯著膽子拿著手電筒亂晃來嚇野豬。雖然野豬被趕跑了,可她們身上早已浸出了一身冷汗。害怕山上的野獸再來,她們只好輪流睡覺。
這時,國民黨部隊在會昌有一個“鏟共團”,和當地民團一起,常常搜山。一天,“鏟共團”來到這座山,文媛她們雖然四下藏匿,最后還是被發現了,并被帶到會昌縣城,關在牢里。在此之前,被捕的還有一個在蘇區辦報的編輯,叫謝然之。敵人審問文媛等五人時,她們異口同聲地說是福建人民政府參觀團的。敵人不信,就把謝然之拉出來指供。他只認識文媛,說文媛是中央譯電員。敵人便進一步逼問文媛的身份,文媛回答:“家庭婦女,沒有翻過電報。”敵人又說:“你是陳紹禹的弟媳吧?”
文媛回答:“婚姻是父母包辦的,當然嫁夫隨夫走。”敵人看問不出什么名堂,又去問其他幾人。她們也一口咬定文媛是家庭婦女。就這樣,敵人一無所獲,對她們也不再追問了。
后來,敵人把其她四位女同志押到南昌,關進了國民黨的感化院。文媛因為臨近產期,被押到了寧都,轉交紅十字會,并同意可以出保釋放,否則就遣送回安徽原籍。文媛想,如果回安徽就是重犯了,只好說家里人已不在安徽,在上海。當時,文媛也確有一個伯父在上海光華火油公司任職,她就給伯父寫了一封信。不久,伯父來了信,還寄來了錢,文媛才被放了出來。在寧都紅十字會醫務所時,有一個安徽籍醫生,為人忠厚,他聽說文媛被保釋,便告訴她去上海的路徑。這時,文媛的孩子剛滿月,她只好一手提著籃子、一手抱著孩子,只身到南昌,又轉九江,乘船到上海。
奔赴圣地重啟程
上海,是文媛曾經戰斗過的地方。現在,文媛只身回到這塊被殖民化了的土地上,心里有一種說不出的滋味。
按照組織的指示,文媛在上海找到了內山書店。這是魯迅先生的日本朋友內山完造先生在上海辦的一個進步書店。文媛又和潘漢年接上了頭,也見到了馮雪峰等人。在敵人統治的白區,見到了黨的同志,真有說不出的高興。這時,陳一新也到了上海,黨組織要把他們一起送到蘇聯去學習。在等候辦出國護照期間,西安事變爆發了,文媛和陳一新都很興奮,他們想到新形勢下的抗日斗爭一定需要很多的干部,覺得還是去延安的好。正好這時,周恩來因為國共談判的事到了上海,住在東方飯店。文媛和陳一新去看望他。周恩來雖然工作很忙,還是熱情地接待了他們,問長問短,還問到了他們脫險的經過。談話結束的時候,周恩來問他們還有什么要求,他們便提出想去延安工作。周恩來考慮了一下,便同意了,并立刻給李克農寫了一封信,要他負責安排文媛他們去延安,并提供三百元錢路費。李克農接到周恩來的指示,立即作了安排,介紹他們到武漢八路軍辦事處,要辦事處設法送他們去延安。
就這樣,文媛他們于1937年離開上海,逆江而上,到了武漢。在武漢八路軍辦事處工作了一段時間,文媛參加了辦事處領導的一個訓練班,參加學習的還有一部分是要求到延安去的進步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董必武、周恩來和郭沫若等人先后在訓練班給他們上課。1938年5月,文媛他們來到了日夜思念的延安,先進陜北公學學習,然后進入中央黨校學習。此后,文媛和陳一新一起跟隨部隊轉戰東北、南下中南,為建設新中國而努力工作。
文媛曾經動情地說,我們這一代人,雖然在戰斗中度過了自己的大半生,為黨和人民作過一點貢獻,但同偉大的革命事業相比,畢竟是滄海一粟。成千上萬的先烈,為著人民的利益,在我們的前頭英勇地犧牲了,我們只是幸存者之一。我們要用先烈的革命精神自勉,勇往直前,為實現他們的遺愿去努力工作、拼搏奮進。
(本文參考了劉業礎、王文豪和臺益燕采訪并整理的有關文字資料)
〔責任編輯 袁小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