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論儒家的“以人為本,道行天下”
湯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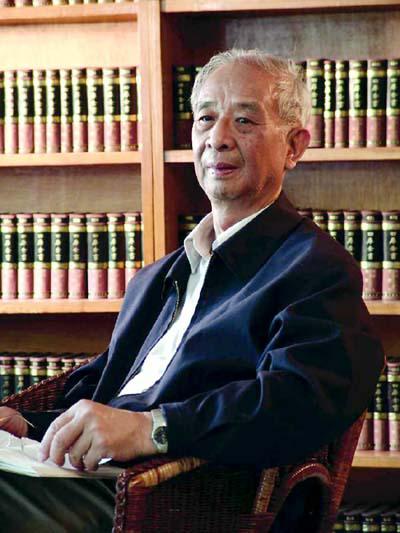
儒家認為“人”之所以為“人”者,在于具有異于禽獸的“人性”。人之異于禽獸的“人性”,它體現在孔子所說的:“仁者,人也……”“仁愛”是人所具有的本質。孔子的《論語》中討論“人性”的地方不多,但他所關注的最重要的問題就是“性與天道”的問題,“人性”之實現即為“人道”,“人道”體現“天道”,這個問題太大,所以他和他的學生很少討論,但它實為中國哲學之根本問題。另有“性相近,習相遠”一說,此說確立了人之為人者其性大體相同,開創了“人性”之共同性、普遍性之先河。自孔子以后到孟子時代,儒家討論“人性”的問題多起來,至少有五派(據王充《論衡》),孟子說:“惻隱之心人皆有之”,這就把“人性”規定為“性本善”。所以孟子說:“人之異于禽獸者幾希”,人與禽獸之不同就在于人有“惻隱之心”那點上,“惻隱之心”的發揮(實現)就是“善”。據此,儒家展開了他們的“以人為本”的“道德倫理”“政治倫理”“經濟倫理”“社會倫理”“天人倫理”等諸多方面關于“人”的學說。
一、儒家的道德理想倫理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中庸》引孔子的話說:“仁者,人也,親親為大。”“仁愛”是“人”本身所具有,愛自己的親人是“仁愛”的基礎。但此種“仁愛”必須推己及人,所以儒家為中國設計了一套道德理想社會的藍圖,這就是它的“天下為公”的“大同”思想。從儒家的“大同”論述可以看出,它是基于“仁者,愛人”而推廣于天下,所以孟子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這種“天下為公”的“大同”道德理想信念,自然就是“以人為本”。基于此而展開的儒家學說都沒有離開“以人為本”這一基本理念。我們可以把這種信念稱作“道德理想倫理”。然而“道德理想倫理”要落實,需要有儒家的“政治倫理”(政治)、“經濟倫理”(經濟)、“社會倫理”(人與人的關系)、“天下倫理”(天道與人道的關系)相配合來擴展而實現。
二、儒家的政治倫理
《大學》中說:“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這就是說,沒有“以人為本”的“道德理想倫理”,“政治倫理”是無從談起的。
如何“修身”?孔子提出要“修德”“講學”“徙義”“改過”,這樣才能“下學上達”,成為君子,才能使自己有個“安身立命”處。
如何“齊家”?儒家把“孝”作為家庭倫理的基本。《論語·學而》:“孝悌也者,其為人之本與?”王弼注謂:“自然親愛為孝,推己及物為仁。”“孝”是出于“自然親愛”。《孝經注疏》中說:“父子之道,自然慈孝,本乎天性,則生敬愛之心,是常道也。”又說:“孝是真性,故先愛后敬也”“愛之與敬,俱出于心”。“愛”與“敬”發乎于人之本性,非外力所加,自然如此。費孝通先生對此有一新的解釋:家庭倫理中“孝”的意義在今天主要應體現在“尊敬祖先和培養優秀的后代”。這就是說,對祖先要尊敬,對后代要精心培養,這樣就做到“齊家”了。
如何“治國”?在中國,如果說“家庭”是個小社會,“國”則是一個大社會。一般認為,中國前現代是一專制的“人治”國家,而西方近代則是“民主”的“法治”國家。我認為,這種說法并不全面,應該說在前現代儒家的理想應是以“禮法合治”治國。我們從《二十四史》的“志”中常常看到有“禮樂”和“刑法”兩志,這說明儒家不僅注重把國家建成禮樂之邦,同時也對“刑法”的建立頗為重視。
《禮記·坊記》:“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意為“禮”是君子所設立為防止超越道德的界限;如果用“禮”不能防止道德敗壞,那么就要用“刑”來制止為非作歹,禍亂社會;如果“刑”還有不足之處,則可以用“法令”來補充,以防止社會貪欲橫流。可見,“禮”“刑”“令”三者功能不同,但都帶有制度性的意義。

《論語·為政》:“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這里不僅說明“禮”和“刑”的功能不同,而且說明二者的效果不同。因為用“政令”和“刑法”雖然民可以暫時避免犯罪,但不是自覺地遵守社會規范,因此對犯罪并無羞恥之心;如果用“道德”“禮教”來治理國家,那么人們就會自覺地走正道。賈誼《陳政事疏》中說:“然禮者禁于將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生難知也。”這是說:“禮”的作用要在人們犯錯之前就加以防范;而“法”是在人們犯錯之后加以懲治。“刑法”的作用易見成效,而“禮”的作用難以立竿見影。這說明,“禮”要靠道德教化長期養成(修身),“法”是一種外力所加的不得不備之舉,不遵守“禮”的要求,這叫“出禮”(或“越禮”),“出禮”就會“入刑”。所以在中國儒家認為“禮”和“法”有著表里相依的關系,不應忽視。
《漢書·禮樂志》中說:“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政刑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禮”的作用是調節民心之所求,“樂”的作用是表達人民追求和諧相處的要求,“政”是要求處理“政務”,要順民情而能行通,“刑”是為了防止人民“出禮”而“入刑”所設立。我認為,這也許是儒家“以人為本”的政治倫理所求。
如何“平天下”?此句應理解為“如何使天下平”。此“平”或有三義:“平”可作“和平”解,如堯對舜說“協和萬邦”,各邦國和平相處;“平”也可作“平等”解,如孔子說“四海之內皆兄弟”;亦可作“平安”解,如“仁者安仁”“老者安之”“修己以安人”。“天下平”,包括國與國、民族與民族之間的“和平”;還包括“人”與“人”之間的“平等”關系;又包括每個人身心內外的“平安”“安寧”,這樣就真正“天下太平”了。
三、儒家的經濟倫理
《論語·子路》:“子適衛,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孔子看到,衛國的人口眾多,這和孔子的“來遠人”思想有關,因為眾多的老百姓都愿意安家落戶于此地,說明在此處生活能安頓下來,可以建立家業。
有家有業之后,國家就應使人民富裕起來。為什么能生活聚集在一起,《周易·系辭》中說:“何以聚人,曰財。”要想把人民聚集在一起,很重要的是要靠經濟的力量。所以孔子并不反對“富與貴”。《論語·里仁》:“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人追求富貴并非不應當,但取得富貴要有正當性,“取之有道”。而如何使“取之有道”具有正當性,這就要靠教化之功能。由此可見,儒家認為經濟活動必須是合乎道義的。《二十四史》多有“食貨志”,可見當時治國者對農商工的各種政策和制度多以關注人民之經濟生活為目的。
四、儒家之社會倫理
《禮記·禮運》:“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修十義,講信修睦,尚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這是說“人”與“人”之間的道義關系。日常生活中,人與人必然發生各種各樣的關系。相互發生關系的雙方即有應有之權利(如“君”要求“臣忠”),但雙方也應有承擔之相應的責任或義務(如要求“臣忠”時,也就要求“君仁”),這樣相互對應關系的合理建立,社會才會“講信修睦”“尚辭讓”“去爭奪”,這是“禮”所要求建立的雙向權利和義務之關系,這樣社會才能真正安穩,而人人安居樂業,生活在“以人為本”的社會中。“人”不能離開他人而單獨存在,在“人”與“人”之間總是存在著相互依存的關系,只是在“人”與“人”相對應的較為合理的關系得以建立的情況下,社會倫理才可以達到相對的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和安寧。
五、天人關系倫理
朱熹說:“天即人,人即天。天即生此人,則天又在人矣。”天人不相離(天人相即不離),既然“天”產生了“人”,“天道”將由“人道”來彰顯,也就是說“天理”(天道)將由“人”(“人道”)來實現。為什么“天道”能由“人道”來彰顯?因為人具有與“天”相關聯的“人性”。朱熹說:“仁者”“在天地則坱然生物之心,在人則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所以“天道”與“人道”是相通的。朱熹說:“惟仁,然后與天地萬物為一體。”《郭店楚簡》中說:“易,所以會天道人道也。”這一思想又和后現代主義所主張的“人與自然是共一生命同體”有某些相合之處。處理好“天人關系”(即人與整個宇宙的關系),人們才能真正幸福、社會才能真正安寧、國家才可以真正富庶、老百姓才可以真正富足,此乃“以人為本”所追求。
以上,所討論的儒家“以人為本”的“人性”問題,以及由此展開的儒家“道德理想倫理”“政治倫理”“經濟倫理”“社會倫理”“天人倫理”,都是說明儒家“以人為本”所蘊含的內在精神。我用“道德理想倫理”,而未用“體系”“主義”,等等,蓋因“倫”者“常”也,“倫理”者“常理”也。對儒學“常理”的傳承并給以合乎時代的詮釋,也許其“以人為本”之真義可見。但我們必須看到,“理想”往往終歸是“理想”,它并不必然會成為“現實”。儒家的“理想”是否一定圓滿,是否能見之于現實,這也是一問題。
從歷史上看,儒家為中華民族所設定的理想社會的諸多方面,在歷史的實際中并未實現,至少是并未能全都實現,這是由于歷史發展的各種主、客觀條件的限制,但作為對自己民族以及人類社會抱有責任的真正儒家必須有其理想,此理想是真正儒者身心性命的命脈,是儒家為人處事“良知”的體現。孔子在春秋時,由于“天下無道”,而卻一心一意地努力為把“天下無道”改變成“天下有道”,其實孔子也明白這不過是“知其不可而為之”。對于“理想”我們也許常常抱著“雖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的態度。我想,張載的《西銘》頭兩句“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說得對,人必須有理想,把“人”看作“人”,“以人為本”這是真正儒者可貴的精神;《西銘》最后兩句“存,吾順世;沒,吾寧也”,說得也很對。人的一生必須對社會盡倫盡職,追求“道行天下”,在他離開人世的時候才可以問心無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