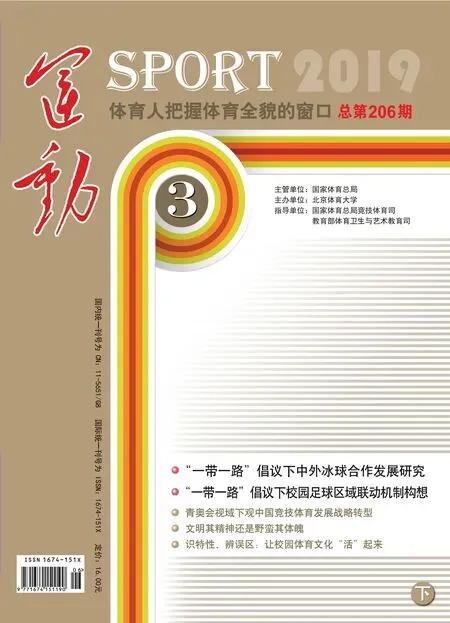古滇國青銅器文物中的體育文化分析
汪 雄,陳玉林,周山彥,白麗佳
(1.玉溪師范學院體育學院,云南 玉溪 653100;2.文山學院體育學院,云南 文山 663099)
神秘的古滇國潛藏著多年的文物及其文化信息,為世人揭開了一個沉睡了兩千多年的古代王朝的真實面紗。1955—1996年間5次發掘了的晉寧石寨山墓地,是中華民族重要的考古界杰出著作之一,墓地中出土的“滇王之印”金印,江川李家山墓地、昆明官渡羊甫頭遺址,都是中華民族考古界的重要發現,證明了古滇王國的在歷史上的真實存在。古滇國地區青銅文化,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晉寧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墓地。在古滇國遺址中還出土了許多與體育有關的器物,如兵器、鋤具,有裝飾的銅鼓、扣飾、馬具、陶瓷、銅牛等。這些文物說明古滇國人民當時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特征,其古滇國體育表現形式多樣及其文化內涵豐富多彩,對其研究具有重要的歷史文化價值。
1 古滇國的歷史溯源
追溯歷史可知,司馬遷的《史記》里記載著,在古代滇池附近生活著一個神奇的民族。大約在公元前339年,楚國不想被秦國吞并,于是派莊蹻來完成開闊疆土,試圖將勢力范圍向西南方向拓展。莊蹻進入滇不久后楚國就滅亡,便失去了與故國的聯系,順勢誠服于古滇王國,換上戎裝成為古滇國國民。史書中明確記載的一代滇王,在莊蹻進入古滇國之前,古滇國的青銅文化已經達到登峰造極的程度。大約公元前1世紀一位霸占一方水土的滇王帶領著自己的文明走向了衰亡。西漢年間,漢武帝帶兵吞并滇國,滇王舉國投降并誠服于漢朝。于是漢武帝賜給滇王金印,命令他掌管這里的人民(這枚純金制造的金印在兩千年后出土于晉寧縣的石寨山)。那么,古滇國的疆域范圍是什么樣的?在司馬遷《史記.西南夷列傳》中有相關記載,西至安寧、祿豐一帶,南至新平元江至個舊一帶,東至石林、瀘西一帶 ,北至曲靖、東川以北的會澤、昭通一帶。這段歷史記載對古滇國疆域的界定最完善,也能夠說明古滇國的具體疆域和它與周邊部落的關系。
2 古滇國體育文化形成的社會成因
2.1 原始的自然崇拜
古滇民族信奉的是原始宗教,他們對大自然所發生的一切尚未形成科學的見解。諸如山川、河流、森林、雷電、毒蛇、猛獸、巖石、日、月、風、火、水、霜以及仙逝的祖先,他們認為都無不具有潛在的無法抗拒的力量。這些神靈可直接或間接地降下吉兇禍福給他們,隨時都在危及人們的生活和生存。為了生存、生活和獲得豐收,消除災難,人們逐漸形成了祈求神靈給以恩賜和保護的原始崇拜情結。在這最樸素的原始自然崇拜情結里蘊含著積極參與祭祀活動、利用不同的肢體語言來表達自己的虔誠,以取悅神靈的樸素的體育思想。可以這樣說,是原始的自然崇拜情結促進了古滇國民族體育思想的萌芽與形成。
2.2 統治階層的休閑娛樂
在古滇國時期由于權力和金錢的過度集中,統治者或奴隸主為了豐富自己的空閑時間,在自己的直轄地域內舉行具有觀賞性和娛樂性的體育活動,如斗牛、狩獵、縛牛等活動。由于長時間或頻繁地舉行這種活動,在人們的思想中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種習慣或定式。這種習慣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相應的體育活動在貴族間廣泛流傳,從而促進了體育活動及其文化的進一步呈現并逐漸流傳開來。
3 古滇國青銅器文物中的體育表現形式
3.1 競 渡
歷史資料已經證明銅鼓是古滇國祭祀崇拜的主要對象之一,而競渡圖紋出現在銅鼓上,可以看出競渡是古滇人民的一項神圣活動,且用于祭祀河神、水神或者祭天。競渡圖紋(圖1): 船上共有15個人,穿著羽毛做成的帶有尾巴的服飾。船頭一人持小旗立于船頭作指揮,其余14人分為7小組,每2人1組肩并肩而坐,每個人手中持一槳在水中做滑動狀,他們皆頭微仰,口微張,動作整齊規范,定是在指揮者揮動小旗和統一口號聲中的統一行動。最前面的一個人在舉著旗子指揮著,行使著教練員的權利。2人1組表明當時滇族已明自在競渡過程中分工合作的重要性.兩人肩并肩而立比兩人一前一后或其他組合方式更有利于船只在水面上劃行,有利于集中力量提高滑行速度。從劃船者頭微仰,口略張可以看出,劃船者抬頭有利于看清指揮者的手勢或者劃船者要抬頭看神靈所在的方向,且口中要不停地喊口號或念祭詞。從動作整齊統一可以看出,滇國舉行的競渡活動事先是經過專門訓練的,其中蘊含了祭祀活動背后的訓練內容,由此可見古滇體育操演已經開始萌芽。

圖1 競渡圖紋
3.2 磨秋(秋千)
在江川李家山出土的銅鼓圖紋中,銅鼓側面記錄了當時磨秋的情節(圖2),圖中央立一柱,頂端有一固定橫軸,軸上有可轉動的圓盤或滑輪,盤周系4條繩索,每條繩之端另系一個圓環。4個人都穿戴羽毛做成的衣服,最下面有一人在揮動著2面小旗子,可以看作是教練員,說明當時體育教練員和體育專項訓練已見萌芽。其余4人每個人各持1環,做跳躍旋轉狀并且蕩到了秋千的最高點,或者是古滇國的秋千是從最高出向下跳的運動,說明蕩秋千的技術很嫻熟。從圖中可以看出古滇國的秋千與現在的秋千有所不同,古滇國的秋千實在繩子末端有一橫木秋千,運動員是用雙手挽住橫木,而現在的秋千則是用腳踩或用臀部坐在橫木上。他們每個人都穿著羽毛狀的服飾,說明古滇國的磨秋是在重大節日舉行的體育活動項目。

圖2 磨秋或秋千
3.3 鏢 牛
玉溪市江川縣李家山25號墓出土的一件銅扣飾,反映了滇國祭祀過程中鏢牛的場景(圖3左側圖片顯示)。牛的正面圖像的右側有一木樁,木樁上粗下細,最上面有一平臺。一頭牛被拴在木樁上,牛角上倒懸一幼童,可能是和牛一起作為祭祀用品的活人祭祀品。圖像中有一人被牛撂倒在地靠在木樁上作呻吟狀,其余3人捆縛此牛。其中一人緊拉而栓住牛頸與前腿的繩索并繞于柱上,一人拉住系牛頸的繩索,另一人雙手緊挽牛尾,控制牛不要亂動。從上述場面中可以看出,參與鏢牛活動的人必須體格強壯,體格稍弱就會被牛撂倒。經過嘗試或者經驗的總結,古滇國人已總結出了一套比較成熟的縛牛方法。

圖3 左“鏢牛”、右“斗牛”
3.4 斗 牛
晉寧石寨山出土的一件斗牛銅扣飾形象地表現了當時古滇斗牛活動的盛況。該扣飾分為3層, 最高一層:在木制的3層看臺上,最上層坐著10人,正中間的那個人顯然是奴隸主或統治者,兩側8人可能是貴賓或侍從。為顯示主人的威嚴貴賓侍從們都自覺地與中間2人保持一定的距離;中間一層有9座成一排人,門頭上蹲據的人手握從門上伸出的民棍,作用力開門狀,兩側分別跪著4人,右邊的4人因受奔牛沖出的誘惑,姿態略有改變,靠里的一人更是引頸而望;最下層左邊5人又不4人共有9人,收到驚嚇而做回避狀,有的人尖叫,有的人歡呼也有人不動聲色。圖中所表述的是1頭牛與2只豹子在爭斗,一只爬在牛背上拼命的狂抓,另一只則咬住牛的腿企圖將牛絆倒,經過激烈的斗爭牛角已經斷了一只,但是它仍然在奮力拼搏,體現了牛的堅強和寧死不屈的精神。在江川李家山出土的扣飾文物中有牛與其他動物在爭斗的場面,既然古滇人民把它記錄下來,就說明當時這種牛與其他動物爭斗的場面是人們經常可以看到的,也可也說是牛與其他動物在爭斗。如圖3中右側描述的是晉寧石寨山出土的3人縛牛扣飾,它記錄的是3人在與牛爭斗的場面,其中2人在后面控制住牛的尾部,一人在前面用繩子拴住牛的頸部和前腿然后試圖把牛腳絆倒,看他們的表情并不是那么的吃力,說明在當時對于縛牛活動來說他們的縛牛技術已經到了一定的高度,還能說明縛牛活動在古滇國很流行或者它產生的年代久,否則古滇國的人民不會擁有這么高超的縛牛技術。
3.5 軍事體育活動元素
“滇王”和“族長”是其政治身份的階級代表。統治階層為了捍衛白己的部落,以及權力不斷擴張土地而使得戰爭頻繁,促使部落士卒掌握一些戰爭需掌握的技術,生產技能也被應用于軍事技能培養。于是,武器的制作、使用和作戰訓練成了古滇體育文化不可缺少的內容。體育與人類的生產、生活、實踐、戰爭需要密切相關。那是一個封建專制思想橫生、權利極度膨脹的社會。在石寨山、李家山等古滇遺址出土了很多的兵器,如青銅劍、青銅戈、青銅矛、銅斧與械、弩機與傲,其他如戈蹲、矛及防護性的兵器盾、胸甲等。滇王或者部落首領為了維護自己的政權或者為了抵御外來民族或部落的侵略,必須要使自己的軍事力量強大起來,開始發展自己的軍隊、戰術和武器。由此,在操練士兵的過程中便出現了體育元素,在戰場上也出隨之出現,即士兵熟練的掌握了自己的武器和使用方法后,將其應用于戰場。
[1]云南省博物館.石南青銅文化論集[C].昆明:石南人民出版社,1991:85.
[2]晉寧縣文物體育局.古滇工都巡禮—石南晉寧石寨山出上文物精髓[M].昆明:石南民族出版社,2006:102
[3]江川縣文化局.玉溪市文物.管理所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川李家山第一次發掘報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67.
[4]楊學政.原始宗教論[M].昆明:石南人民出版社,2000:235.
[5]云南省博物館.云南青銅文化論集[C].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31.
[6]晉寧縣文物體育局.古滇王都巡禮—云南晉寧石寨山出土文物精髓[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125,230.
[7]江川縣文化局,玉溪市文物管理所,云南省文物考古研所.江川李家山第二次發掘報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27,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