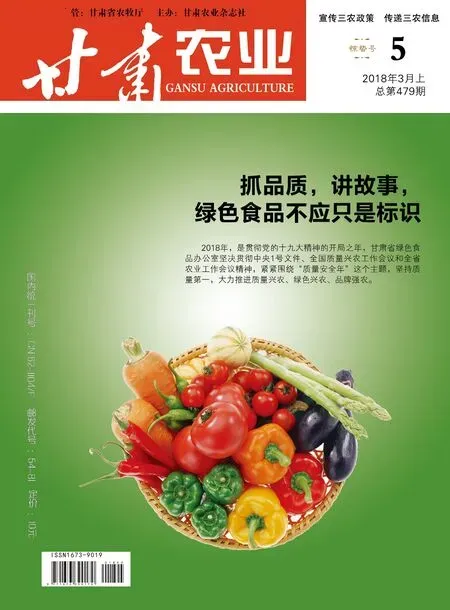一個村莊的眼淚
走在果灣梁上,你就能明顯感到這里與我們慣常意識中的關山風光并不一樣,沒有潺潺流水,沒有綠肥紅瘦,沒有馬匹羊群,甚至連低空飛翔的烏鴉也難得一見,越過一個山頭,便是另一個山頭,一條小路到了盡頭,跨過一段小小的溝渠,斜溢出去,便又能尋見另一條隱隱約約的小路——人們總是有辦法,從這個山頭,到那個山頭去。
這時候,你肯定會想,在果灣梁上做一頭黃牛,也是糟糕的。雖然有吃不完的青草,有耕不完的山地,也有拉不完的車子,高興的時候,可以沖天嚎叫,不高興的時候,可以漫山瘋跑,只要還能動,就不會擔心被人宰了賣肉。對山里人而言,牛總是有用的,總比一頭犟脾氣的驢要受人喜歡。按理來說,牛會受到優(yōu)待,如果不偷懶,不像驢一樣與人對著干,那一輩子下來,注定會過著貴賓一樣的悠閑日子,做該做的事,一聲不吭,才好。但很快你會發(fā)現(xiàn),物質上的優(yōu)待,并不能解決精神上的空茫。沉默是牛的本領,而這空蕩蕩的果灣梁,卻比牛更沉默,你縱使沖它吼上一萬遍,它也不發(fā)一言,到處都是你一個的聲音,四周靜得可怕,你只不過是與自己置氣,根本不會有人理你,活一日,就要憤怒一日,終有一天,你會像瘋狗一樣把自己氣死。

那么,做一條上躥下跳的狗會怎么樣呢?當然,不是說做一條瘋狗,就是那種矯健的猛物,逮著人就咬,那樣的話,你注定會像牛一樣,因為找不到發(fā)力的對象而抑郁致死。我說的是有靈性的狗,可以看家的狗——整天由著性子,一會兒到這個山頭,一會兒又到那個溝壑,不用做事,只是盡情地奔跑,尋找獵物,發(fā)情嬉戲,暴露在山頭的十個堡子,任你酣睡,對,就是那十個相傳用來躲避土匪的堡子,雖然只有殘垣斷壁,但對一條狗來說,擋擋風雨已經(jīng)足夠了,多好。但很快你也會發(fā)現(xiàn),縱使你馳騁十里,除了見過幾個主人搬到新疆后殘留的破舊莊院,你幾乎嗅不到人的氣息,雞鴨的氣息,甚至連那種曾經(jīng)躲在糧倉下吃得肥肥胖胖的家鼠的氣息也嗅不到。找不到同仇敵愾的同類,找不到與你分外眼紅的異類,僅僅是一條狗孤獨的奔跑,又有什么意思呢?
然而,你再往前走,往山的深處走,走到山的最高處,再俯沖下去,卻能見到人,見到這個稱作果灣的村子。你肯定會悲喜交加,就像經(jīng)過漫長的黑夜,見到了早晨的第一縷陽光。誰說不是呢?這里居然住著人,真的有牛,還有狗,牛不止一頭,是四頭,而狗呢,據(jù)說是跑出去半個月了,沒有回來,大約是再也不回來了,正如他們說的,要回來早就回來了。他們是那樣肯定,那條黑色的狼狗的確不會再回來了,就像那些陸續(xù)搬去了新疆的人家,決然地斬斷了他們與村莊的聯(lián)系,從來沒有回來過一樣。狗有大用處,甚至比牛用處更大,在這空蕩蕩的梁上,它能看家,能嗅到生人的氣味。但家并沒有什么可看的,十二戶人家,剩下了三戶,老老小小加起來,才八人。院墻倒塌了,也懶得修葺,如果不是怕半夜有狼竄將進來,不然,晚上睡覺,門都不用關的,家徒四壁,三家人,相依為命,又有什么可防的呢?但狗丟了,是自己跑出去的,大約真是待不住了,要不然,我們?nèi)r,狗就能報信,能給我們領路。他們說,兩個月了,我們是唯一的生人。
準確地說,其實是兩戶人家,一家是兩個七十多歲的殘疾老人,主人姓趙,年輕的時候,農(nóng)業(yè)社用大炮打天上的黑云,不小心走火,炸掉了左手。他用一只手拉扯了兩個兒子,山里人家,仿佛對孝道并沒有概念,也許是村里的傳承所致,也許是缺少教育所致,但在我目力所及的地方,越是窮困,便越是人與人水火不容,就像人與山里的黃土那樣敵對,也許這并不是人的錯,是這非人的環(huán)境對人之惡的本性激發(fā)所致,每一種憎恨都有其自身的因由,外人不可妄加評說。所以,兩個兒子自然而然地都很早分出去單過,九年前,強壯的二兒子與那些有本事的人一樣,舉家去了新疆,他沒有揮手,沒有回頭,也沒有抬眼看天上的云彩,他走了,杳無音訊,老人只知道去了新疆,到底是哪兒,日子怎么過,他一概不知。大兒子也走了,沒有走遠,卻再也見不到了,四年前,他開著拖拉機下山,天黑路滑,從溝里翻了下去,等到發(fā)現(xiàn)時,已經(jīng)過了一天一夜。大兒媳原本是要改嫁的,卻舍不下孩子,他們唯一的兒子,在不滿一歲的時候,得了腦膜炎,成了癡呆人,從此再也沒有站起來,癱瘓整整十八年。十八年前,他們一貧如洗,孩子得病的那個冬天,大雪封山,從果灣梁走出山去,需要一個上午的時間,再去縣城,又要一個下午的時間,一個孩子美好的未來就那樣斷送了。好在,前年孩子也走了,大家都不受罪了,他們空洞的眼睛里,沒有悲喜,太多的苦難,讓他們連一滴眼淚都流不下來,他們習慣性地望望遠方,望望藍得深邃的天空,只丟下一聲嘆息,便不再說話。他們無話可說,一步之遙里,我們什么都感知不到,一如云淡風輕,一如蒼白遼遠。半身不遂的老太太,從剛剛搭建的平板房里慢騰騰地扔出來一句話:“什么都不想了,再等兩年,我們也就走了,兩眼一閉,就什么都不記了。”她的聲音很輕,一股風吹來,就遠遠地飄走了,但這句話,卻讓旁邊他們住了幾十年岌岌可危的羊圈,抖了三抖,年前加固在房脊上的白楊木,一如常年吃野菜而身體透明的人無可包庇的五根骨頭,白森森蜇人,一層厚土沙啦啦地掉下來,仿佛掙脫了枷鎖,看清了自己。
大兒媳四十多歲,不能生養(yǎng)了,前年入贅來的關山深處的男人去了縣城打零工,兩三個月回來一趟。她已經(jīng)像一個年過六旬的老人,揉揉眼睛,攔過垂下來的一縷頭發(fā),望著村口的那個拐角,像一只溫順的老鳥,一臉空洞。

另一戶真的姓果,果灣的果。在二十米開外,略低一階。天氣不好,冷風吹著,早幾年從梁上引過來的自來水絲線一樣掙扎著慢慢地淌,多半桶水是這一天的收成。男人年輕的時候,在蘭州的建筑工地從腳手架上跌了下來,摔壞了腰,不能拿重物,只能干一些輕省的活,天麻麻亮步行出山,去縣城打零工,晚上抹黑回來,他放心不下妻兒,要不然也就不用這么辛苦地來回跑了。女人亦是四十好幾,看起來,年齡要更大一些,她正與大兒子給牛鍘草。大兒子十九了,以穆斯林的鄉(xiāng)俗,早到了娶媳婦的年紀,但他從十五歲起就去山外給人裝卸水泥,個頭被上百斤的重物壓下去了,反而顯得比實際年齡小一些,我們進去看他們房子的時候,他蹲在水池旁,摳著指甲,低頭不語,倒像是久經(jīng)年月的中年人,他的母親說:“我們這樣的地方,誰會嫁過來呢?”話還未說完,她就哭了起來,她說,那些早年間經(jīng)過的苦,并不算苦,耽擱了孩子的前程,她就成了罪人。她把我當做能為他們辦大事的大人物,一再地講著日子的艱難,說著“如果”一類的假設,是啊,何嘗不是如果呢?
她在為她的苦爭取一點同情和希望,我們也在為我們的苦使盡渾身解數(shù)。這時候,你才能真正體會到無能為力的酸楚,雖然曾經(jīng)常常無能為力,但這一瞬間,卻是那樣令人難過
果家人有三個孩子,老二是女兒,上五年級,放學后被老師留著寫作業(yè),還沒有回來。老三是兒子,十二了,才上三年級,他一直坐在鍘刀旁,把自己陷進了松軟的麥草,怕人似的勾著頭。路不好走,他只能長到九歲才上學,我問他時,好久他才抬起頭來,卻是滿眼淚花,他將眼淚憋著,緊閉著嘴,我知道,只要他一松口,定會放聲大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