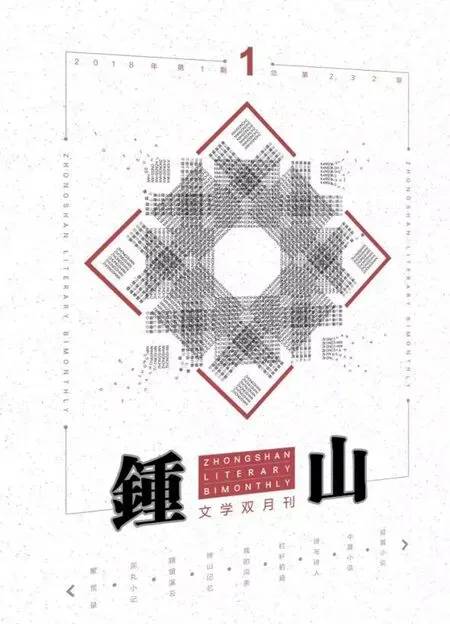場(chǎng)景:紹興和平湖
李潔非
覽太平天國(guó)事,宜注意其中的一類史料。
這段歷史留下的文檔種類繁多,粗歸納蓋有九大類。一曰檔案,清、天雙方的文告、諭旨、大臣奏稿、鞠訊記錄或供狀,西方外交官提交本國(guó)政府的正式報(bào)告等,可歸此類。一曰情報(bào),此系為搜集敵方信息而形成的材料,《賊情匯纂》乃其著名代表,余如《虜在目中》《張繼庚遺稿》也具這種性質(zhì)。一曰日記,不少身逢其世者通過(guò)私人日記逐日留下大量相關(guān)記述,如《荊花堂日記》《能靜居日記》《己酉被水紀(jì)聞》《戴經(jīng)堂日鈔》《史密斯日記》《吳清卿太史日記》等。一曰方志,中國(guó)獨(dú)有發(fā)達(dá)的地方志系統(tǒng),于太平天國(guó)起義、所經(jīng)之地及統(tǒng)治區(qū)域,均保存了不少信息和線索。一曰綜述,太平天國(guó)戡定之后,陸續(xù)有一批梳理和統(tǒng)敘其經(jīng)過(guò)的書籍編刻出版,如官方之《欽定剿平粵匪方略》,或私家所撰 《中興別記》《平定粵寇紀(jì)略》《粵氛紀(jì)事》《金陵兵事匯略》等。一曰報(bào)道,這一類材料為近代新聞產(chǎn)物,多由在華洋人撰寫,發(fā)表于上海和香港兩地報(bào)刊,尤以英商所辦上海《北華捷報(bào)》登載為多,如《裨治文關(guān)于東王北王內(nèi)訌的通訊報(bào)導(dǎo)》《小刀會(huì)占據(jù)上海目擊記》《外國(guó)傳教士訪問(wèn)蘇州太平軍》等。一曰尺牘,一些重要的歷史當(dāng)事人為處理公務(wù)的書信往還,像《曾文正公全集》中之書札三十三卷、李鴻章之《朋僚函稿》,以及《吳煦檔案選編》等,太平天國(guó)將領(lǐng)之間也留有不少書信。一曰傳記,麥沾恩的《中華最早的布道者梁發(fā)》、羅孝全揭秘洪秀全的 《洪秀全革命之真相》《太平天國(guó)起義記》、蘭杜爾的《“常勝軍”建立者與首任領(lǐng)隊(duì)華爾傳》、亞朋德的《華爾傳:有神自西方來(lái)》、安德魯·威爾遜的《“常勝軍”:戈登在華戰(zhàn)績(jī)和鎮(zhèn)壓太平天國(guó)叛亂史》,包括《清史稿》各本傳、《清史列傳》有關(guān)篇什,均在此列。一曰親歷錄,多取自撰者本人的直接目擊,其中又分兩種,一種屬于泛記,將一段時(shí)間某地社會(huì)見(jiàn)聞攬于筆下,如陳徽言《武昌紀(jì)事》、張汝南《金陵省難紀(jì)略》、謝介鶴《金陵癸甲紀(jì)事略》、滌浮道人《金陵雜記附續(xù)記》等,另一種則就個(gè)人一段險(xiǎn)情或奇遇,專事專述,道其原委,如周邦福《蒙難述鈔》、刀口余生《被擄紀(jì)略》、顧深《虎穴生還記》、魯叔容《虎口日記》等。
豐富多樣的史料,各有價(jià)值和意義,但從特定角度,我們更傾心于其中一種,亦即親歷錄里后一種的專事專述文字。這類材料,幾乎不含議說(shuō)和意見(jiàn),全是場(chǎng)景,全是畫面,全是“鏡頭”,讀之恍若置身現(xiàn)場(chǎng)或仿佛在觀看一部記錄影片、一次視頻直播。相較乎某些史料,比如含官方視角與立場(chǎng)的史撰,抑或政客們自其角色出發(fā),于公文、信函、日記里所載述之情形,這些內(nèi)容,固然都不失研究的價(jià)值,然而究竟預(yù)存了一定傾向性,其中失真或不客觀處,蓋亦難免。專事專述的親歷錄一般無(wú)此瑕玷,更接近如今嚴(yán)格意義上的紀(jì)實(shí)之作。許多寫者當(dāng)時(shí)形諸紙墨,根本并不為著發(fā)表,而僅出于難以忘懷、刻骨銘心,欲向親友訴說(shuō),于是留下一份實(shí)錄,以共唏噓與牢記。因此,對(duì)相隔一百六十年而又想不受打擾,冷眼鑒察那段歷史原始面目的我們來(lái)說(shuō),這將是無(wú)可替代的依傍。在茲,就中分別擇出浙江紹興、平湖兩位平民,就個(gè)人親身經(jīng)歷,所作帶有歷險(xiǎn)色彩的記敘,藉之以窺太平天國(guó)期間普通民眾既無(wú)所諱亦無(wú)所飾的遭際景狀。
紹興
魯迅姓周,但他給自己起的筆名,卻以魯為姓。那是他母親的姓氏。似乎紹興這個(gè)地方,魯姓很常見(jiàn)。我們現(xiàn)在講的主人公,也是紹興人,他就姓魯名叔容,魯迅先生的老同鄉(xiāng)。魯迅誕于1881年,其時(shí)魯叔容或許還活著,寫過(guò)一篇對(duì)于紹興數(shù)千年歷史獨(dú)一無(wú)二的東西。
《虎口日記》經(jīng)歷和角度殊奇。為它作序的陳元瑜說(shuō):“余訝其升屋而避,入篁而伏,匿大樹之下,藏古墻之陰,急迫在中,既恨翳形之無(wú)草矣,而又見(jiàn)虜者再,欲殺者三,餓且病者屢,昕暮奔竄,辛苦萬(wàn)狀,乃復(fù)從容握管,絕日成書,八旬之間,積為一帙。”從開(kāi)始陷城中不得脫,到后來(lái)經(jīng)人搭救出城,經(jīng)歷了漫長(zhǎng)的七十九天;日復(fù)一日,不論風(fēng)霜雨雪,魯氏大多數(shù)時(shí)間都是爬上屋頂,藏身于瓦檐犄角躲避搜捕,且從這樣的位置聽(tīng)察太平軍占駐紹興的諸般情形和動(dòng)靜。所有這些,被他逐日書于紙上,而留下這部特殊的“野史”。
故事開(kāi)頭與周邦福在廬州有些相似。咸豐十一年(1861年)九月底,紹興風(fēng)聲吃緊,二十九日一大早,魯叔容派仆人出城買舟,打算逃到鄉(xiāng)下老母親家中;正在這時(shí),太平軍“奪西門入”,魯氏倉(cāng)猝不能去,只身陷城中。較之廬州,紹興少了一個(gè)圍城階段,太平軍突如其來(lái),來(lái)即得手。

至此,魯叔容兩次被捉,兩次脫身,且平生頭一回殺人。
時(shí)已拂曉,他奔至一戶種菜人家,求棲身而不見(jiàn)容,“不得已奔后衙橋南岸人家后樓窗外暫避”。雨下了一整天,他廁身窗下,借著伸展到窗前的柚樹的枝葉蔽身,雨勢(shì)如傾,渾身濕透,餓焰于腹內(nèi)熊熊燃燒,但分毫不敢動(dòng)彈,整整一天僅靠就近摘得的一枚柚子療饑,視線所及“四處火光相映如霞電”,耳內(nèi)則“煏爆之聲轟耳不絕,愴呼亂起,哀鳴動(dòng)地”,的確是太平軍大隊(duì)人馬撲至的架勢(shì)。挨至黃昏,魯叔容這才放膽溜至街上,見(jiàn)一店門窗緊閉,縫中燈光隱約,上前輕呼,幸而啟之,“主人惠冷酒一瓢,爛豆盈握”,并讓他留宿一夜。
翌日黎明回自家。家中已非先前模樣,“什物星散滿地”。他找到幾件舊衣?lián)Q上,然后去敲隔壁友人王子堅(jiān)家門,“其妻饗余麥飯”,兩天來(lái)第一次吃飽。轉(zhuǎn)回家來(lái),起初藏于床頂,“苦床頂?shù)蜕酰ノ萃邇H尺許,跼蹐不能轉(zhuǎn)側(cè),乃避于承塵上”。(按:明清多為架子床,四角立柱,上安頂架,頂架也叫“承塵”。但“承塵”往往又指室內(nèi)天花板,如《聊齋》有句:“殿承塵上,藏大蛇如盆。”)從魯叔容所講看,他先是藏在床頂上,但床頂緊挨天花板,過(guò)于逼仄,于是爬到天花板上面,那兒和屋脊之間構(gòu)成稍大空間,“架朽欲傾,中積殘破木器,蛛網(wǎng)塵封”,類似一間小閣樓。
幸虧藏在那里,倘是床頂,或早就被發(fā)現(xiàn)。他伏在上面,借縫隙下望,闖入屋內(nèi)的太平軍也注意過(guò)天花板,但大多抬眼打量而已。也有人用長(zhǎng)矛捅,甚至爬上屋頂掀瓦下窺,老天保佑,都沒(méi)有敗露。有一次,長(zhǎng)矛戳在離身體很近的地方,“幾為所覺(jué)”,令人“心悸肌慄”。
薄暮,藏了一天的魯叔容,耐不住口渴,外出找水喝,“倏遇三賊走入,坌息急奔始得免”。太平軍“連日窮搜,亂草叢棘中亦用矛數(shù)搠乃已”,主要是索取錢財(cái),如愿乃已,并不殺人;但可怕的是,“遇他賊亦脅取如前,所獻(xiàn)不多,輒砍一二刀,物盡則殺。故僵仆路旁者傷痕遍體,此屢砍使然,非一賊所致也。”
種種跡象說(shuō)明,紹興這支太平軍手段兇狠,并且遲遲沒(méi)有“安民”意愿。魯叔容感到絕望,十月初五日晚上,他從承塵下來(lái),找筆硯想寫遺囑,以防意外隨時(shí)發(fā)生。翻檢時(shí),發(fā)現(xiàn)一本日歷,心中一動(dòng),打算從此開(kāi)始寫日記;由是,吾等后人方能讀到《虎口日記》這樣一篇奇文。
從初三日起,魯叔容在承塵上已經(jīng)藏了五天。初八日,又闖進(jìn)幾名太平軍,“在下窮搜細(xì)掠,半日始去”。魯叔容屏息斂體,既嚇得夠嗆,也認(rèn)識(shí)到承塵非久留之地。前兩天,他曾偶然爬上房頂,發(fā)現(xiàn)那兒頗為隱蔽,至此乃決意改“匿承塵上”為“升屋”。“升屋”后,他的日記內(nèi)容變豐富了,因?yàn)槲萃庖曇皵U(kuò)大,聞見(jiàn)更廣,例如“賊擄船入城,載婦女輜重泊門外”,或者“賊于前街焚化積尸,煙結(jié)如霧,腥風(fēng)刺鼻,胃欲翻嘔”,諸如此類的記述,先前都沒(méi)有出現(xiàn)在他筆下。另外他該慶幸變換匿身處的想法及時(shí),十四日,“賊擄掠愈甚,結(jié)隊(duì)窮搜,承塵亦被毀”,若非先期轉(zhuǎn)移,后果堪憂。
一番勘察,他發(fā)現(xiàn)自家“壽萱堂屋上天溝西南倚高墻,東北連屋脊,中凹可容三四人”,心想與人結(jié)伴藏身,可以彼此照應(yīng),遂與鄰居磨剪匠王三、張姓少年商定每天結(jié)伴升屋,“黎明倚梯以登,令藏梯于墻外”,天黑后下來(lái),各自回屋睡覺(jué)。
二十一日,有屠城傳聞,“升屋同避,托比鄰歐叟藏梯”。有些居民,或老或病,也就聽(tīng)天由命,并不躲避,例如這位歐姓老頭。為何屠城?據(jù)說(shuō)是太平軍“有去志”,后證明并非如此,太平軍沒(méi)有離去,反而“新到賊愈多”。但屠殺確實(shí)降臨了:“四處火起,光如電灼,聲若山崩,風(fēng)勢(shì)怒號(hào),日色慘淡”,“日中比鄰殺人,乞命者遍遠(yuǎn)近,刀聲 然,悚耳惕心”。魯叔容等躲在屋脊凹處,沒(méi)有看到屠殺過(guò)程,卻仍然通過(guò)傳來(lái)的聲響感受到它的可怖。尤其是,這天直到夜半人靜,仍無(wú)人前來(lái)搭梯。魯叔容和王三將張姓少年從屋頂縋下取梯,三人走到街上一看,“尸橫滿地”而“歐叟死焉”,難怪“援梯不來(lái)”。魯叔容感慨:“此老患難相恤,藏梯執(zhí)炊,關(guān)切獨(dú)厚,倏喪賊手,為之悽然。”連這樣一位風(fēng)燭殘年的老者也命赴黃泉,說(shuō)明殺戮是不分青紅皂白的。以往太平軍嗜殺多見(jiàn)于城池初下時(shí),眼下占領(lǐng)紹興將近一月,仍發(fā)生這樣的慘案,實(shí)屬少見(jiàn)。二十七日晚間,魯叔容溜下辦事,經(jīng)過(guò)馬梧橋,見(jiàn)太平軍告示,才知道慘案起因是“義民屢殺賊”以及“陷城中者遍貼檄文,列款罵賊”,“賊怒甚,故欲屠城”。報(bào)復(fù)近乎瘋狂,“男婦老幼死于賊者不可紀(jì)極”,魯叔容路遇一老嫗,“血濺雙耳,問(wèn)之,因念阿彌陀佛,被賊割去”。
以前白天躲避,夜晚回屋,如今再也不敢如此。三人搬衾被于屋頂,“以防夜驚也”,晝夜露宿瓦棱之間。二十三日,至?xí)裕皳眙浪耐酄a猶炎炎作勢(shì)”,午時(shí)“搜物賊來(lái)……他賊又續(xù)至,鎮(zhèn)日沸騰”。安全起見(jiàn),他們把梯子也吊上屋頂,消抹蹤跡。翼日,又找來(lái)棕棚墊在瓦上,“臥始安帖”,這是欲作長(zhǎng)久之計(jì)。所有需要辦的事情,都只有天黑以后趁著夜色去做。二十五日夜,他們下來(lái)找到歐叟尸體,用布衾包裹好,將老人葬在唐家巷那處墳地。
露宿的日子極難熬,時(shí)漸入冬,霜降滿地,“衾寒似鐵,僵臥不成寐”,趕上雨天還會(huì)“衣衾透濕”。苦到這種地步,卻無(wú)人動(dòng)過(guò)回屋之念,乃至十一月初二日黃昏,“下屋即到妙佳橋買谷藏衣篋中,置屋上,足一月糧”,益發(fā)咬牙鐵心,就這樣熬下去。一邊是頑強(qiáng)的求生本能,一邊是生不如死的滋味,三個(gè)紹興人在二者夾擊下,掙扎著,堅(jiān)持著。“初三日丁亥,霜重,天愈寒”,魯叔容凄苦中“續(xù)寫遺囑,述未了事”,寫著寫著,“墨痕淚痕,模糊滿紙”。
至此,昕暮奔竄、避伏匿藏的生活已整整一個(gè)月,前景依舊茫然,不知何時(shí)是了,每天相伴的,只有突如其來(lái)的驚嚇。那天,天氣晴好,“未聞槍炮聲,遂擁衾坐以濁醪澆塊壘,日昳閱殘書數(shù)帙,正凝思間,忽有數(shù)賊立南首王姓樓窗外,舉手遙指,似為所睹者,余與王三、張七魄飛氣索,偃臥不敢動(dòng),惴惴者半日”。其實(shí)對(duì)方并未注意到他們,他們卻如驚弓之鳥,以為大難臨頭。又一日午后,魯叔容正打著瞌睡,忽聞?dòng)腥藛酒涿艁y中辨出是某“友人婦”,“繞室迭呼”不已,“細(xì)聽(tīng)雜男子聲,皆非鄉(xiāng)語(yǔ),不敢應(yīng)”,晚上下屋至友人家一問(wèn),方知“其夫被虜擄,賊尚需善書者,故招余耳”,魯叔容嘆曰:“婦人之居心行事,有出乎情理外者,可畏可笑。”
不是所有人都躲了起來(lái),有些仍住家中,安危則看各自運(yùn)氣。紹興太平軍讓人摸不準(zhǔn),說(shuō)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安民告示已下,卻是一紙空文:“賊目有偽示不準(zhǔn)搜虜擄,不意更甚于前,甚至拆墻掘地,無(wú)物不毀。”魯叔容晚間潛出,過(guò)一處,“見(jiàn)貼有門牌,禁止滋擾。詢之,蓋從賊目偽朝將周文嘉處購(gòu)買者。”看來(lái),安民告示純屬擺設(shè),欲保平安,須另外掏錢換取專門的護(hù)身符。魯叔容日記里所曾提及的呆在家中、沒(méi)有躲避的街坊和友人,差不多都死、傷或被擄——除先前歐叟橫尸街頭,鄰居王離堂“罵賊死,妾與孫亦被戕,其孫才八九齡耳”;鄰居余南渠“死于賊,夜助其家殮尸,草草蓋棺,得免暴露”;友人王秬香“傷重死矣,延喘兩月,仍不免尸骸暴露,無(wú)力為之揜埋,徒呼負(fù)負(fù)”;親戚李內(nèi)嫂“母子均受重傷,其母年七十余矣”;友人余晉軒 “手足受重傷”,“不良于行”,嗣后還是被抓走,不數(shù)日妻亦“為賊拉去縫紉,遺二子在家,憫茲煢獨(dú)”……這些都是普通老百姓,并不在“妖”之行列,而紛紛遭難。
十二月初一日,日記寫道:“屈計(jì)城陷兩閱月矣,虎口余生,差幸無(wú)恙,惟苦出城無(wú)期,仍命懸賊手,殊惴惴耳,張望白云,思親落淚,兀坐者終日。”過(guò)了十來(lái)天,看到了一線生機(jī),聽(tīng)說(shuō)紹興一帶太平軍“設(shè)鄉(xiāng)官兩百余處,司辦糧餉等事”,這意味著局勢(shì)趨于安定。魯叔容開(kāi)始試著輾轉(zhuǎn)與城外親人聯(lián)系。十二月十九日,“舊仆任阿發(fā)持賊令旗”,以鄉(xiāng)官的名義前來(lái),“呼余下屋,遂袖日記同行”,至太平軍某部,領(lǐng)取出城憑據(jù)。穿過(guò)昌安門,魯叔容終于走出在無(wú)望中久困將近八十天的紹興城,“如魚脫網(wǎng),如鳥離籠,悲喜交并,心不自主”。那一刻,他想到杜甫的詩(shī)句:“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
太平軍咸豐十一年九月末占領(lǐng)紹興,同治二年正月退出,前后五百多天,魯叔容大概經(jīng)歷了其中六分之一。關(guān)于紹興在這五百多天中的損失,《越州紀(jì)略》云:
吾越比年來(lái),人情如日,相競(jìng)鮮美,有過(guò)蘇杭。今已自陷而復(fù),民死于賊者,可十萬(wàn)人,死于貧病、毀于火者,亦萬(wàn)家;所喪衣飾,合三邑計(jì),以白金五千萬(wàn)猶未止,可謂大亂矣。
稱之前紹興發(fā)展勢(shì)頭極好,甚而在蘇杭之上,而這一年多以來(lái),民眾遇害約十萬(wàn),被貧病和戰(zhàn)火毀滅的家庭上萬(wàn),經(jīng)濟(jì)方面則僅浮財(cái)之中某一部分,損失就達(dá)白銀五千萬(wàn)兩以上。這是一座中等城市一年多時(shí)間的損失,而太平天國(guó)之亂,自金田起義至天京為曾國(guó)荃攻陷,首尾十四年,波及十八省,大小城池?cái)?shù)以百計(jì)。其中人口損失知其大概,較亂前約減少四分之一,財(cái)產(chǎn)損失難覓核計(jì)之?dāng)?shù),若據(jù)紹興一地以窺,殊為驚人。中國(guó)近代國(guó)運(yùn)之衰,以往關(guān)注點(diǎn)集中在外侮所致巨額賠款、關(guān)稅流失,而太平天國(guó)十四年內(nèi)亂的經(jīng)濟(jì)代價(jià),至今不曾水落石出。庚子賠款總額四億五千萬(wàn)兩白銀,紹興一郡則未足兩年僅“所喪衣飾”便“白金五千萬(wàn)猶未止”,亦即九個(gè)這樣的紹興相加,損失便能趕上庚子賠款,惟不知《越州紀(jì)略》所言是否可信也。
平湖
《 虎穴生還記》一卷,題“金山顧深撰”。 閱至卷末,有民國(guó)二十四年同閭姚光所寫跋文,曰:“吾鄉(xiāng)顧漱泉氏,名深,篤行君子也。居于邑之錢圩,為樸學(xué)大師尚之先生觀光之子。”原來(lái)作者是清末大學(xué)問(wèn)家顧觀光之公子。顧觀光,字賓王,號(hào)尚之,別號(hào)武陵山人,《清史稿》說(shuō)他“博通經(jīng)、傳、史、子百家,尤究極天文歷算”,撰有《古韻》《國(guó)策編年考》《七國(guó)地理考》等,校勘《華陽(yáng)國(guó)志》《吳越春秋》等,同時(shí)還是一位神醫(yī),“往往用一味藥就能奏效,有‘一味靈’之稱”,所輯《神農(nóng)本草經(jīng)》被列為“中醫(yī)十大經(jīng)典”。尚之先生膝下三子,長(zhǎng)子深,次子 ,季子源。其歿于同治元年(1862年),亦即顧深被擄后次年。不過(guò),結(jié)合《虎穴生還記》的敘述,我們能夠指出今人所撰顧觀光傳,有些地方是不確的,例如:“咸豐十一年(1861年)太平軍占領(lǐng)金山縣,避亂東赴奉賢、南匯,但其次子顧 則隨太平軍而去,下落不明……”而顧深則記述繼他本人于同治元年二月初脫身后,十九日,離散的顧 也逃回父親身邊;可見(jiàn)顧觀光去世前并非不知次子下落。
以上乃枝節(jié)。回到本事:咸豐十一年十月十四日,也即紹興魯叔容伏匿屋頂之時(shí),顧深與仲弟顧沄從逃亡地“金家棋桿”(疑是“金家旗桿”之誤)動(dòng)身回其本村錢家圩。顧家是七十天前的八月初四日,因太平軍攻至金山而逃離的。為何冒險(xiǎn)回村呢?“因念家中有稻二十余畝,已經(jīng)成熟,共議歸刈,作避難費(fèi)。”由這個(gè)細(xì)節(jié),我們發(fā)現(xiàn)顧家雖詩(shī)書傳家且累世行醫(yī),卻難稱富奢,否則不至于為二十來(lái)畝稻子去闖“虎穴”。當(dāng)然還有一點(diǎn),就是他們聽(tīng)說(shuō)十月初的時(shí)候,太平軍已從金山撤走,那一帶既無(wú)官軍扼守,太平軍則 “時(shí)來(lái)時(shí)去,并未設(shè)卡把守”,有點(diǎn)半真空狀態(tài),乃決定趁此縫隙搶收那些稻子。
“金家棋桿”距錢家圩約百里,翌日午后,兄弟二人抵家,“見(jiàn)門窗毀壞,闃其無(wú)人,遍訪鄰人,盡皆逃散”,找了半天,總算找到一位親戚,正詢問(wèn)間,就聽(tīng)西南方槍炮聲響起,于是拔腿便跑,途中遙見(jiàn)前面過(guò)來(lái)數(shù)十人,以為一定也是逃難者,“可以問(wèn)賊蹤跡”,迎上前去,“未見(jiàn)漸近,見(jiàn)各穿紅衣,黑布裹頭”,情知不妙,掉頭而逃,對(duì)方卻已看見(jiàn),緊追不舍。跑到一座橋上,顧深回頭看時(shí),一名太平軍執(zhí)槍作瞄準(zhǔn)狀,另有兩名太平軍提刀追來(lái);乃止步,不敢再逃。
兄弟二人被抓,搜去隨身所有金錢,押著往西南而行。行至河邊,有船數(shù)十,插著各種旗幟,押送者指著其中一船,命令顧深:“下去。”顧深回頭朝弟弟望去,見(jiàn)他被帶著繼續(xù)南行,兄弟從此分開(kāi)。
第二天晚上,顧深所在船隊(duì)駛?cè)胝憬胶h城水西門。平湖,今為嘉興市所轄縣級(jí)市,其東北緊鄰上海市金山區(qū)。鎮(zhèn)守平湖的將領(lǐng)是庥天安陳玉書。“安”乃爵名,前綴二字以封功臣,羅爾綱《太平天國(guó)史》云:“天京事變后,天王初不欲再封異姓為王,故在侯爵之上,設(shè)義、安、福、燕、豫五爵,共成六等之封”,亦即爵名高于侯爵,例如陳玉成曾封成天義、李秀成曾封合天義;不過(guò),后來(lái)恢復(fù)王爵且愈益濫封,“六等爵”隨之貶值,“幾乎到了‘舉朝內(nèi)外皆義皆安’的地步”。
與廬州周邦福、紹興魯叔容不同,顧深被擄后直到逃離期間,在平湖沒(méi)有受任何罪。其原因,我們通過(guò)他的敘述了解到有以下四點(diǎn):第一,平湖一帶太平軍形成了較穩(wěn)固的統(tǒng)治,秩序已經(jīng)建立起來(lái),滋擾較少,殺戮更無(wú)必要,“當(dāng)是時(shí)平湖地界,已立鄉(xiāng)官,出示安民,各村莊進(jìn)貢,給一小令旗,扯于樹梢,名曰‘安民旗’,又曰‘進(jìn)貢旗’,從此不許薙頭,納賦完糧,各安生業(yè),賊過(guò)時(shí)亦不許擄掠,所以衙前鎮(zhèn)生意依舊”。第二,顧深運(yùn)氣不錯(cuò),遇上了一支心態(tài)較為平和的太平軍,從被捉之初,里面的人待他很和氣,不打不罵,好言相慰,勸之“先生毋恐,不要緊的,做長(zhǎng)毛很有好處,不必想家”,且“出熟蠶豆與余食”,其中一人更對(duì)他講:“汝來(lái)此館,即是祖宗積德,自己修行。余在此已及一載,從未見(jiàn)有刺字割耳殘忍之事,頭子以忠厚待人,甚屬安閑,何必急于思?xì)w?”第三,顧深自身態(tài)度亦較得當(dāng),被擄后,抱著“死生有命,憂亦無(wú)益”的認(rèn)識(shí),安然以對(duì),這反而令眾人對(duì)他感到親近。第一次開(kāi)飯,一名小太平軍將飯菜端來(lái),說(shuō):“先生心緒不快,必食不下咽矣。”沒(méi)想到顧深“放膽連食兩碗”,少年不覺(jué)驚呼:“先生好大膽!”口氣頗為稱贊。時(shí)間久了,顧深始知“館中不忌歡鬧,大忌憂愁”。后來(lái)又新?lián)飦?lái)一名道士,亭林人,“滿面愁容,為人呆笨,命伊做事,俱言不會(huì)”,表現(xiàn)很抗拒,結(jié)果“殺之,懸其頭于門前,棄其尸于長(zhǎng)平倉(cāng)中”。第四,太平軍面貌在變,鐵血?dú)赓|(zhì)褪去,早先一派肅殺的氛圍漸漸被一種慵懶散漫情狀所取代,表現(xiàn)于日常,即是少了些殺氣,而多了些松懈,甚至是“寬容”。這種變化,看得見(jiàn)的原因是太平軍兵卒來(lái)源幾乎完全“本地化”,不要說(shuō)出身兩粵的“老弟兄”,即便籍貫湖廣的次生代,亦難覓其一,顧深被抓后曾一一交待他所見(jiàn)到的每位太平軍戰(zhàn)士的來(lái)歷,有嘉興人、乍浦人、無(wú)錫人、丹陽(yáng)人等,最遠(yuǎn)亦為“江北人”,他描述道:“見(jiàn)司廚者、司茶者、燒火者、擔(dān)水者、洗盞者,紛紛擾攘,雜沓喧嘩,俱是本地口音。”部隊(duì)成員構(gòu)成的“本地化”,顯而易見(jiàn)無(wú)形中悄悄改變著太平軍與環(huán)境、人、物、生活和風(fēng)俗等之間的關(guān)系,弱化著敵對(duì)的意識(shí),銷熔著仇視的心理。不過(guò)除此之外,其實(shí)還有更深層的原因——在基本信念及意識(shí)形態(tài)奉持方面,太平軍從上到下有瓦解的趨勢(shì)。
基督教史上,由早期圣徒開(kāi)創(chuàng)了餐前禱告、感恩于主的傳統(tǒng),《哥林多前書》11中,保羅云:
23我從主那里領(lǐng)受,又傳給你們的,就是主耶穌被人出賣的那個(gè)晚上,他拿起餅來(lái),
24感謝了,掰開(kāi),說(shuō):“這指的是我的身體,是為你們舍的。你們要不斷這樣做來(lái)記念我。”
25晚餐過(guò)后,他又同樣拿起杯來(lái),說(shuō):“這個(gè)杯指的是憑我血所立的新約。你們每次喝這個(gè)杯,都要這樣做來(lái)記念我。”
26你們每次吃這個(gè)餅,喝這個(gè)杯,都是顯揚(yáng)主的死,直到他來(lái)。
27所以,誰(shuí)妄拿這個(gè)餅吃,妄拿主的杯喝,就是冒犯了主的身體和主的血。28人應(yīng)該先省察自己,認(rèn)明自己合適,然后才吃這個(gè)餅,喝這個(gè)杯。
在太平天國(guó),餐前贊美也是日常最基本的儀式,從武昌到南京以及廬州,所有對(duì)太平天國(guó)生活起居的描述,都提到這種儀式被嚴(yán)格執(zhí)行,“早晚吃飯鳴鑼集眾,率眾念贊美”,“館內(nèi)有多少人都站在二面,高聲念所謂‘贊美經(jīng)’一遍,念畢,一齊跪下,真長(zhǎng)毛口中默誦所謂‘悔過(guò)奏章’”。但是《虎穴生還記》寫到的所有進(jìn)餐經(jīng)過(guò),沒(méi)有一次舉行餐前贊美,如:
第二埭正廳為天福堂,乃新兄弟吃飯之所……劉賊余共食,劉南向,何西向,余東向。細(xì)杯象箸,魚肉滿前。有俊童四五人,頗伶俐,皆衣紅站立旁邊,酌酒添飯。余放膽大嚼,兩賊相語(yǔ)曰:“這先生好大膽。”又曰:“大的好。”
原附著餐飲行為之上的虔敬色彩消失,回歸于地道的中國(guó)世俗享樂(lè)意味,乃至流諸奢靡。其中我們還注意到赫然寫著“酌酒添飯”四個(gè)字,太平天國(guó)明令禁酒,“不得吹煙、飲酒”,雖然此一禁令不可能真正遵行,尤其特權(quán)階層在私生活中根本置之不顧,然而像眼前這樣,普通軍卒一日三餐的場(chǎng)合也公然違背,則實(shí)在宜以視之蔑如形容了。
重要的禮拜日活動(dòng),亦即《天條書》規(guī)定的“每七日要分外虔敬禮拜,頌贊皇上帝恩德”,以前各地目擊者也都觀察到太平軍 “每閱七日為一贊期”,“夜半烹茶誦贊美一遍”;眼下在平湖,則似乎縮水為每月兩次,即月初及月中的所謂“敬天福”:
賊每逢朔望,必燃燭焚香,陳設(shè)酒肉,名曰“敬天福”,頭子南向坐,余人侍坐,先來(lái)者上坐,后來(lái)者下坐,不得紊亂。坐定誦贊美一章。
不光次數(shù)縮水,內(nèi)容形式更是甚有悖謬之處——上載“焚香”“酒肉”,均犯大忌諱。“焚香”為中國(guó)土生迷信的舊事物,與拜上帝教掊擊的“偶像崇拜”有千絲萬(wàn)縷聯(lián)系,所以過(guò)去會(huì)中堅(jiān)決擯斥,用燭不用香,燭為上帝之物、香則邪教之屬,“點(diǎn)燭而無(wú)香”是很明確的規(guī)范。至于酒,日常尚且厲禁,更不應(yīng)該出現(xiàn)于嚴(yán)肅的宗教活動(dòng),凡涉祭告,《天條書》限定一律用“茶飯”,如“俱用牲饌茶飯祭告皇上帝”、“虔具牲饌茶飯, 敬奉天父皇上帝”、“但用牲饌茶飯祭告皇上帝”,張汝南關(guān)于早期天京則具體記為“茶三盞,飯三碗”。可到平湖這兒,卻公然成為“無(wú)酒肉不成敬”了。
更嚴(yán)重的墮落是吸食鴉片,不但嘗此禁臠,且不避人前、無(wú)所忌憚。顧深甫被帶至船上,即見(jiàn)到如下情形:
余下船,見(jiàn)一賊衣服華麗,藍(lán)緞裹頭,橫臥吸雅片,見(jiàn)余點(diǎn)頭作招呼狀,余亦拱手問(wèn)姓,賊言姓吳,嘉興人。
翼日清晨,轉(zhuǎn)至另一條船,“有兩老賊在焉,年各望七,對(duì)臥吸雅片”,有人告知:“此皆老大人,一姓劉,一姓何”,亦即這支太平軍的兩名頭目,他們也大搖大擺吸食鴉片,還逢人即問(wèn)有無(wú)同好:
劉賊問(wèn)余吸雅片否?余曰:“不會(huì)。”問(wèn)飲酒否?余又對(duì)以“不會(huì)”。又問(wèn)喜食何物?余曰:“好食肉,喜吸水煙黃煙。”賊遂以一短竹煙管授余,視之乃黑煙也,連吸兩筒。劉曰:“汝好食肉,我館中盡有,到彼任汝大啗。”余唯唯。
之前《蘇臺(tái)麋鹿記》記蘇州太平軍“鴉片之禁尤酷,而搜奪煙膏及老槍等具,喜形于色”,說(shuō)明這種嗜好養(yǎng)成日久。太平天國(guó)禁煙依據(jù),出自《太平天日》所載洪秀全游天時(shí)耶和華的一句話:“見(jiàn)凡人食煙,天父上主皇上帝怒曰:‘爾看凡人這樣變怪,其口出煙! ’”后來(lái)還寫過(guò)《戒鴉片詩(shī)》:“煙槍即銃槍,自打自受傷。多少英雄漢,彈死在高床。”多次下詔戒鴉片:“吹來(lái)吹去吹不飽,如何咁蠢變生妖!”太平天國(guó)的禁煙,不特以其為磨損生命之劣習(xí),也似乎嫌厭噴云吐霧形象有失人形、狀似“魔鬼”,所以它將煙土與煙草等量齊觀煙草有害健康,二十世紀(jì)六十年代以后始成共識(shí),十九世紀(jì)不要說(shuō)中國(guó)即在西方也無(wú)從談起,凡“其口出煙”,一概目為邪惡,嚴(yán)予禁止。然而到了蘇浙階段,天王眾所周知的憎惡已無(wú)人理會(huì),“其口出煙”模樣在太平軍中隨處可見(jiàn)。
另一項(xiàng)大罪奸淫,亦被置若罔聞。不得奸淫,列第七天條。一涉此罪,視為“變妖”。《天條書》說(shuō):“天下多女子,盡皆姊妹之群”,“凡男人女人奸淫者名為變妖”,并附詩(shī)詮釋:“邪淫最是惡之魁,變怪成妖甚可哀。欲享天堂真實(shí)福,須從克己苦修來(lái)。”以上每個(gè)字,眼下皆被拋置腦后,因?yàn)楝F(xiàn)實(shí)顯而易見(jiàn),“天堂真實(shí)福”愈益遙不可及,縱然“克己苦修”也根本無(wú)望,所以“天下多女子,盡皆姊妹之群”這樣的嘉言懿德,只能流于說(shuō)教,無(wú)法讓人心悅誠(chéng)服,兩性關(guān)系視角難以扼制地回到生物本質(zhì)的雌雄之義。顧深于平湖街頭,見(jiàn)“婦女遂隊(duì)閑行,皆涂脂抹粉,衣服鮮華,或揚(yáng)揚(yáng)得意,或郁郁含愁”,于是問(wèn)同行一太平軍少年,后者告知“此長(zhǎng)毛妻也,或系擄來(lái),或系娶來(lái)。”
余曰:“長(zhǎng)毛皆得娶妻乎?”童子曰:“自丞相以上,始得有妻,然亦必須稟明庥天安,其下則不能也。”余曰:“此婦女中年長(zhǎng)者是長(zhǎng)毛之妻,其垂髫者其即長(zhǎng)毛之女乎?”童子曰:“不然,年輕者亦是妻。”余曰:“如此輕年(應(yīng)系“年輕”之誤),豈可為妻乎?”童子曰:“我們長(zhǎng)毛中都是毛毛呼呼的,見(jiàn)了婦女,總要打水泡,那管他死活,即死了,棄諸曠野,或埋諸土中,投諸流水,誰(shuí)為伸冤?”打水泡者,猶言奸淫也。
“丞相”官職,前期地位很高,“居于極品”,通常由封侯爵者任之。眼下到后期,爵職之濫已致“丞相”地位低微,“在二千六百二十五人的一個(gè)營(yíng)里面就設(shè)有十個(gè)丞相,丞相已淪為軍營(yíng)里面的一個(gè)小小官佐”,估測(cè)之,約略相當(dāng)于如今軍制中的團(tuán)級(jí)干部。早期,惟王爵方許有家室,連封侯之人與妻幽會(huì)亦視為茍合。楊秀清頒給配令后此禁松馳,從少年所說(shuō)來(lái)看,后期解禁范圍以“丞相”級(jí)別為限,以上者經(jīng)批準(zhǔn)可婚配并隨軍攜眷,所以駐地才有“婦女遂隊(duì)閑行”的景象,其中有的明媒正娶,有的卻是擄奪所致,例如那些“垂髫者”,顯系幼女,不大可能明媒正娶,其自擄奪無(wú)疑。但這種擄奪行為,還勉強(qiáng)屬于“合法”范圍,是“丞相”以上級(jí)別可以享受的權(quán)益。其下官兵則如何?從待遇、紀(jì)律和道德而言,他們性的需求沒(méi)有合法渠道解決,但也絕不甘于現(xiàn)狀。那便如少年所說(shuō),隨時(shí)隨地用暴力方式了卻,“見(jiàn)了婦女,總要打水泡”,先奸后殺。此本屬重罪,被嚴(yán)申是“惡之魁”,是“邪淫變妖”,然而誰(shuí)也不在乎。
劫掠,一直是太平軍的基本生存方式。此時(shí),平湖一帶為太平軍所控制,官軍匿跡,無(wú)仗可打。于是,在所駐之地,太平軍主要工作更集中到一件事上:外出搶劫。如前所述,左近地區(qū)業(yè)已“安民”,太平軍與居民訂有協(xié)約,后者依約“進(jìn)貢”,前者不加滋擾。所以搶劫活動(dòng)本著“兔子不吃窩邊草”的精神,在周邊稍遠(yuǎn)的灰色地帶展開(kāi)。例如,顧深被擄時(shí)所在的金山錢家圩,距平湖數(shù)十里,就是這樣一種尚未形成“安民”格局的灰色地帶,凡此都是搶劫對(duì)象。當(dāng)然,太平軍自己不會(huì)稱之“搶劫”,而代以“打先鋒”的名詞:
打先鋒者,即擄掠也。黃昏有令,則五更造飯,雞鳴出城。賊舟通以百計(jì),出去或五六日,或八九日,必滿載而歸。
以前,“打先鋒”是工作和任務(wù),眼下也是人人爭(zhēng)先、趨之若鶩的事情。區(qū)別在于過(guò)去成果一律歸公,現(xiàn)在卻可以中飽私囊:“得谷米牛羊豬雞等,則館中公用;銀錢衣服,則各自收藏”,大宗物資歸公,細(xì)軟歸己。“每次歸來(lái),余必問(wèn)此回在何處發(fā)財(cái),賊亦直言不諱。”因?yàn)槭前l(fā)財(cái)機(jī)會(huì),大家也就像對(duì)待嘴中之肉,當(dāng)仁不讓,誰(shuí)都要咬一口。顧深得知:“長(zhǎng)毛規(guī)矩,以大壓小。如庥天安所安之民,倘狼天義過(guò)境,則仍欲擄掠;狼天義所安之民,倘將王等過(guò)境,則亦欲擄掠;倘爵位相埒者,則或然或否,無(wú)一定之理;惟位卑者則不敢也。”義爵在安爵之上,天將、王爵又在義爵之上,所有高級(jí)別軍官對(duì)于位卑者的轄地,毫不客氣,都視為自己地盤,盡管手下業(yè)已“安民”,仍然照擄不顧。爵位相當(dāng)者之間,對(duì)他人地盤擄或不擄,亦視各人心緒而定。因此所謂“安民”,只是相對(duì)平安罷了。在弱肉強(qiáng)食的法則下,老百姓日子很難真正靖寧,李秀成后來(lái)指責(zé)陳坤書“亂蘇州百姓”,大概包括“打先鋒”過(guò)程中的各種亂象。然而問(wèn)題究竟出在陳坤書那里,還是太平軍整體素質(zhì)江河日下所致,其實(shí)容易判斷。
顧深發(fā)現(xiàn),此時(shí)太平軍營(yíng)中竟彌漫著一種樂(lè)以忘憂的氣氛。許多人和顧深一樣,俱系擄來(lái),但呆了一段時(shí)間,反而喜歡上這里。某金姓之人,他本有辦法逃走,聽(tīng)說(shuō)顧深想逃,拍胸脯說(shuō)只要拿二十兩銀子來(lái),保證幫他脫身。顧深問(wèn)他為何自己不逃,他徑直言道:“我不愿逃,且家破人亡,出去恐難活。”一副來(lái)去自由然而卻心甘情愿留下來(lái)的口吻。還有個(gè)叫丁必通的,顧深告以“欲逃”,卻遭反問(wèn):“汝在此亦甚安逸,何必急于思?xì)w?”對(duì)于原因,金姓者稱:“老劉在長(zhǎng)毛中已十一年矣,官居文軍政司之職,汝在手下,他人不敢欺侮,倘得其歡心,半年之后,亦得封官作事。”老劉,便是那位見(jiàn)面即問(wèn)顧深“吸雅片否”的館中頭目,他馭下頗寬,不加約束,手下皆感自在。老劉與人為善是一方面,但眼下太平軍士兵有利可圖、有“福”可享,大概才是人們不思逃走更主要的原因。每次“打先鋒”都是“發(fā)財(cái)”機(jī)會(huì),平時(shí)吃穿無(wú)憂、酒肉管夠,還可以吸鴉片、隨意“打水泡”,上哪兒找這樣快活的去處?反觀外面世道,到處兵荒馬亂、餓殍遍野,的確“出去恐難活”。對(duì)比如此鮮明,難怪逃跑意愿不高。
當(dāng)然,想逃之人仍有。有人就對(duì)顧深說(shuō):“擄來(lái)之人,誰(shuí)不思逃?實(shí)不能逃也。”逃的沖動(dòng),主要是想家或“恐父母懸望”。另一個(gè)家在杭州的人也說(shuō):“我到此四百余里,日后尚想回家,先生去家只四五十里,歸亦易易耳。”但逃跑有難度,冒險(xiǎn),萬(wàn)一不成功下場(chǎng)可怕。“日前殺逃犯數(shù)人,煮其肉,逼與新弟兄食之,號(hào)令其頭,鳴鑼示眾。”然而談?wù)撎优芎孟褚呀?jīng)半公開(kāi)化,不擔(dān)心被告發(fā),顧深便至少與五六個(gè)人交換過(guò)看法,大家態(tài)度都很從容,或坦言不想逃,或表示暫作觀望,沒(méi)有人大驚小怪。所以顧深想逃已不是秘密,但仍然安全地呆到成功脫身那一天。
轉(zhuǎn)眼是年底,平湖洋溢著迎新氣氛。太平軍過(guò)年風(fēng)俗極盛,曾有文章概括道:“太平天國(guó)領(lǐng)袖極其重視春節(jié),在春節(jié)前后,他們醉心于度歲大事,從不主動(dòng)出擊敵人,而在那時(shí)劍拔弩張、無(wú)日不戰(zhàn)的烽火時(shí)代,就常常坐失良機(jī)。”還列舉了幾個(gè)事例,其中有“1862年1月,太平軍分五路攻打上海,但主帥李秀成卻中途到蘇州度春節(jié)去了,前線因缺乏統(tǒng)一指揮官,步調(diào)就不一致,影響了對(duì)上海的東西合圍”。巧的是,顧深在平湖所迎乃同一個(gè)新年:
除夕,各人贈(zèng)錢一百文,這是庥天安所給新弟兄壓歲錢。晚飯每桌八簋,殊豐盛,旨酒佳肴,彩杯象箸。
入夜,“金鼓喧天,通宵爆竹”。翼日,“各各雞鳴而起,盥漱畢,即到天福堂上,整備敬天福禮,燃大燭如臂,豬頭三牲,大菜八簋,四海味,糖食八碟,威儀更加整肅。”正午時(shí)分,“外面鑼聲喧天,槍聲震地”,盛大游行,庥天安親自出游,“頭載黃緞繡龍兜,束以金抹額,上綴紅絨球,身穿黃緞繡龍褂,黃縐馬衣,足躡五色繡花鞋,錦鞍銀鐙,按轡徐行”。游行后,各館頭目相互拜年,館中之徒則“群聚賭博,敲鑼打鼓,吸煙閑談”。一連三天如此。
壬戌新年使李秀成撂下戰(zhàn)事,回蘇州度歲,上海因而躲過(guò)一劫。對(duì)顧深來(lái)說(shuō),同一時(shí)刻則將平湖闔城帶入慵懶松弛節(jié)奏,給他極佳的逃跑契機(jī)。
節(jié)間,北門吊橋放下來(lái),白天城門打開(kāi),以方便“新年弟兄們欲往福真寺游玩”。顧深與人謀畫,想乘吊橋放下的機(jī)會(huì),在夜間值更時(shí)縋城逃離。但是,城墻與吊橋之間還隔有一道木柵欄,到了晚上會(huì)關(guān)閉,過(guò)不去。正在發(fā)愁,他們觀察到木柵欄“斷去一根,可以側(cè)身而過(guò)”,大喜。之后開(kāi)始窺伺機(jī)會(huì),但“屢次蹉跎,正月已盡”,一直到二月初二日夜間終于等到穩(wěn)妥時(shí)機(jī),顧深遂與同伙三人付諸行動(dòng):
三人相繼而下,同循城而東,過(guò)木柵,至北門,渡吊橋,舍命北行。是夜雖明星有爛,而田岸崎嶇,跌仆數(shù)次,約行二三里,雞已鳴矣。
自去年十月中旬至此,顧深被擄將近四月,最后毛發(fā)無(wú)傷地出現(xiàn)在老父面前。抵家后他得知,其間弟弟顧沄曾兩次與家中通過(guò)音訊,反倒是他“獨(dú)無(wú)信,或言殺于金山衛(wèi)西門外,鑿鑿有據(jù),合家痛哭”。半個(gè)月后,顧沄也安然回到家中,尚之老先生幸運(yùn)地在去世前看見(jiàn)兒子們都還平安。
注釋:
(1)見(jiàn)《中國(guó)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guó)(六)》第789-804頁(yè),下引是書皆出此不贅。
(2)陳元瑜《虎口日記序》,《中國(guó)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guó)(六)》,頁(yè)787。
(3)隱名氏《越州紀(jì)略》,《中國(guó)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guó)(六)》,頁(yè) 773。
(4)羅爾綱《太平天國(guó)史》卷一,頁(yè)79。
(5)葛劍雄稱:“1851年至1865年這14年間總?cè)丝跍p少了1.12億,下降了26.05%,平均每年下降21.8%。”《中國(guó)人口發(fā)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頁(yè) 253。
(6)顧深《虎穴生還記》,《中國(guó)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guó)(六)》,頁(yè)731-745,下引是書皆出此不贅。
(7)姚光《虎穴生還記跋》,同上書,頁(yè) 746。
(8)《清史稿》卷五百七,列傳二百九十四,頁(yè)13999。
(9)《顧觀光》,金山文化信息資源共享網(wǎng),http://jswhgx.jinshan.gov.cn/html/whmr/57.html。
(10)顧觀光輯、楊鵬舉校注《神農(nóng)本草經(jīng)》,學(xué)苑出版社,頁(yè)200。
(11)《顧觀光》,金山文化信息資源共享網(wǎng),http://jswhgx.jinshan.gov.cn/html/whmr/57.html。
(12)羅爾綱《太平天國(guó)史》卷十,頁(yè)397。
(13)同上。
(14)《圣經(jīng)新世界譯本》漢語(yǔ)版,2007,日本印,頁(yè) 1434。
(15)《太平條規(guī)·定營(yíng)規(guī)條十要》,《中國(guó)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guó)(一)》,頁(yè)155。
(16)《天條書》,同上書,頁(yè) 78。
(17)張汝南《金陵省難紀(jì)略》,《中國(guó)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guó)(四)》,頁(yè)696。
(18)《天條書》,《中國(guó)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guó)(一)》,頁(yè) 76。
(19)同上。
(20)同上,頁(yè) 77。
(21)張汝南《金陵省難紀(jì)略》,《中國(guó)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guó)(四)》,頁(yè)696。
(22)潘鐘瑞《蘇臺(tái)麋鹿記》,《中國(guó)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guó)(五)》,頁(yè) 284。
(23)《太平天日》,《中國(guó)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guó)(二)》,頁(yè) 639。
(24)《洪秀全集》,頁(yè) 30。
(25)同上,頁(yè) 187。
(26)《天條書》,《中國(guó)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guó)(一)》,頁(yè) 79。
(27)羅爾綱《太平天國(guó)史》卷二十八,頁(yè)1046。
(28)盛巽昌《太平天國(guó)春節(jié)》,《新民晚報(bào)》1990年2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