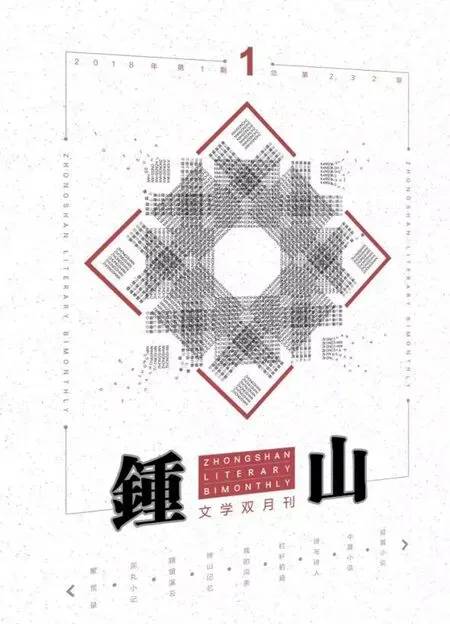“我們世界的根須靜臥在他心里”
———拉貝對希特勒的想象
王彬彬
一據(jù)黃慧英《南京大屠殺見證人拉貝傳》,約翰·拉貝1882年11月23日出生于德國漢堡。1909年,27歲的拉貝來到中國北京以商務(wù)謀生。1911年,拉貝進入德國西門子駐北京分公司,擔(dān)任會計工作。不久,拉貝就被任命為西門子北京分公司經(jīng)理。1911年,拉貝任職的公司建立了中國的第一個電訊臺。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結(jié)束,德國作為戰(zhàn)敗國必須接受協(xié)約國的懲處。新生的魏瑪政府與協(xié)約國簽訂了“喪權(quán)辱國”的《凡爾賽和約》,德國方面割地賠款,事情才算了結(jié)。中國也曾對德宣戰(zhàn),也算戰(zhàn)勝國之一。戰(zhàn)爭結(jié)束后,在華德國人,除身患重病不能行動者和在華從事教師職業(yè)者,都必須離開中國。1919年春,已在中國生活了十年的拉貝,拖家?guī)Э诨氐降聡?zhàn)爭結(jié)束后,德國經(jīng)濟舉步維艱。中國的廣闊市場本來就對德國經(jīng)濟發(fā)展有并非可有可無的意義。于是,魏瑪政府積極謀求恢復(fù)與中國的商貿(mào)關(guān)系。1921年7月,中德在北京簽訂了 《中德協(xié)約》,中德關(guān)系宣告恢復(fù)。這意味著西門子公司在中國的業(yè)務(wù)可重啟,而拉貝也可回到他深愛的中國。于是拉貝立即回到北京。業(yè)務(wù)不但迅速恢復(fù)并且蓬勃發(fā)展。1925年,西門子公司在天津建立了自動電話局,需要大批職員,西門子在中國的總部也因此從北京遷往天津。拉貝也到天津任公司經(jīng)理。西門子天津公司設(shè)在英租界廣東路,是一座三層樓房,內(nèi)設(shè)洋商行和工程部兩個機構(gòu)。拉貝主管洋商行。1930年11月,拉貝被西門子上海總部任命為南京分公司經(jīng)理。南京是中華民國的都城,“公司因拉貝出色的工作能力而將他放到中國首都來開辟業(yè)務(wù)”。
1937年11月,侵華日軍攻占南京前夕,在南京工作的外國人組成了一個國際委員會,成員主要是鼓樓醫(yī)院的美國醫(yī)生和在金陵大學(xué)任教的傳教士,拉貝也受邀加入了這個委員會。據(jù)《拉貝日記》,國際委員會試圖建立一個難民區(qū),也就是在城內(nèi)或城外設(shè)立一個中立區(qū),一旦日軍占領(lǐng)南京,非戰(zhàn)斗人員可以進入中立區(qū)避難。11月22日,國際委員會開會,正式?jīng)Q定成立南京平民中立區(qū),拉貝被推舉為中立區(qū)主席。在此后的幾月間,拉貝利用歐洲人并且是德國人的身份,為救助中國民眾竭盡所能,從日軍的屠刀下?lián)尵攘嗽S多中國人的生命。拉貝在南京的所作所為,自然令日本方面不快,日本方面也會把對拉貝的不滿傳達給德國政府。而希特勒政府正謀求與日本結(jié)盟,于是通過西門子總部勒令拉貝回到德國。1938年3月14日,拉貝攜家人,永遠(yuǎn)地離開了他生活了三十年的中國。
1941年,拉貝在柏林的家中開始整理在南京寫下的戰(zhàn)時日記。拉貝用一年多的時間,重抄了從1937年9月至1938年2月在南京的日記,厚達2100頁,其中日軍在南京大屠殺的實例就有五百多個。這部戰(zhàn)時日記,最初被命名為《敵機飛臨南京》,整理后定名為《轟炸南京》。日記后面附有相關(guān)文件、報刊文章、信件和照片。黃慧英認(rèn)為,拉貝在納粹鼎盛時期閉門整理謄抄南京戰(zhàn)時日記,與他對納粹認(rèn)識的轉(zhuǎn)變和對世界局勢的看法有關(guān)。拉貝沒有在回到德國后的1938年立即整理這些日記,也不是在戰(zhàn)爭結(jié)束后的1945年整理這些日記,這意味著世界局勢發(fā)展到1941年時,拉貝已深刻認(rèn)識到自己在南京記下的日記將成為重要的歷史見證,“此舉表明他不僅徹底看清了納粹黨的本質(zhì),而且對納粹已十分厭惡。”
在1941年開始整理南京戰(zhàn)時日記是否就意味著拉貝徹底看清了納粹的本質(zhì)并對之十分厭惡,是可以疑慮的問題。拉貝的這部戰(zhàn)時日記,長期隱秘不彰,直到1996年才為人所知。1997年8月,中文譯本由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
《拉貝日記》的史料價值和人文內(nèi)涵,無論怎樣估價都不會過分,這主要的方面,用不著我多說。我想說的是,如果拉貝在整理、謄寫這些日記時已經(jīng)認(rèn)清納粹的本質(zhì),如果拉貝在重新面對、審讀這些日記時已經(jīng)對希特勒厭恨、憎惡,那拉貝就是一個極其誠實的人。因為在日記中,時時出現(xiàn)對希特勒的信賴、謳歌,時時可見對希特勒的贊美、崇拜。當(dāng)拉貝已經(jīng)徹底改變對納粹和希特勒本人的看法后,仍然保留當(dāng)初對納粹和希特勒的歌頌、尊崇,這使得這部日記不僅對研究日軍侵華史有史料意義,也對研究德國納粹運動的過程有著史料意義。《拉貝日記》記下的是一個普通的德國人對納粹的信賴和對希特勒的崇拜。這個普通的德國人是本性善良的,是具有強烈的人道主義精神的。當(dāng)日軍殘酷地屠殺中國平民時,這個普通的德國人卻以全部的力量救助這些中國人,而這些被他救助的中國人其實是與他沒有什么關(guān)系的。但就是這樣一個好人,卻曾經(jīng)對納粹無限信賴,卻曾經(jīng)對希特勒無限崇拜。這提供了一個觀察、思考納粹運動興起的角度,也讓我們更好地理解了希特勒從一個街頭小混混成為萬眾景仰的元首的原因。
二據(jù)黃慧英所著《拉貝傳》,拉貝于1934年3月1日在中國加入了希特勒的納粹黨(即“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簡稱“國社黨”)。黃慧英強調(diào),拉貝的入黨動機是極其簡單和純樸的。當(dāng)時在南京的德國人,大多是德國公司的雇員,其中許多人就供職于西門子公司。這些人長期在中國生活,當(dāng)然要生兒育女。這些孩子到了入學(xué)年齡后,上學(xué)就成了嚴(yán)峻的問題。南京沒有德語學(xué)校。這些德國孩子要就學(xué)就只有回到德國。拉貝的獨生子奧托,就被拉貝送回德國南部上了一所寄宿學(xué)校。拉貝決心在南京創(chuàng)辦一所德語學(xué)校,解決德國孩子的就學(xué)困難。要辦學(xué),最大的難題當(dāng)然是經(jīng)費。拉貝向德國駐華使館提交了申請經(jīng)費的報告,其中說明了辦學(xué)理由、規(guī)模和教學(xué)計劃等問題,要求德國政府從教育經(jīng)費中撥款支持,并說明,學(xué)校成立董事會,拉貝任董事長。德國駐華使館的答復(fù)說,拉貝作為董事長,必須加入黨組織,這樣元首才能為在中國辦學(xué)撥發(fā)經(jīng)費。而“拉貝未多加考慮就同意了”。
希特勒于1933年1月坐上德國總理的寶座。1934年8月才把總統(tǒng)與總理辦公室合并,成為把黨政軍都捏在手里的元首。當(dāng)希特勒還并沒有在大眾面前充分暴露其真實面目時,拉貝加入納粹黨,確實不算稀奇。
或許有人對拉貝身在中國卻能加入德國的納粹黨感到不解,其實,從1933年開始,納粹黨便開始在中國進行有組織的活動,他們以上海為中心,從事為納粹德國服務(wù)的勾當(dāng)。后來在整個二戰(zhàn)期間,上海灘上都隱現(xiàn)著納粹的魔影。據(jù)美國學(xué)者華百納(Bemard Wasserstein)所著的《上海秘密戰(zhàn)——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的諜戰(zhàn)、陰謀與背叛》,1933年以后,希特勒的納粹黨就在上海的德僑社區(qū)積極開展工作,到大戰(zhàn)爆發(fā)前夕,上海的納粹黨組織已經(jīng)成功地爭取了大多數(shù)非納粹德僑力量對納粹的支持,至少持中立態(tài)度。當(dāng)然,這不包括德籍猶太人,因為納粹根本無意于獲得猶太人的支持。不僅是上海。在天津、北平和其他一些城市,也有納粹黨的支部。納粹還在中國建立了各種黨的外圍組織,例如,“希特勒青年”就是一個納粹文化和醫(yī)療方面的組織。納粹甚至在上海組建了“黨衛(wèi)軍”,成員有100人左右,著統(tǒng)一制服,其任務(wù)是保衛(wèi)德國電臺等機構(gòu),并對非納粹的德國人進行威嚇。
在上海的非納粹德國人,受到嚴(yán)重威脅。例如“信義會”中一個叫麥斯的人因為替“非雅利安”德國流亡者主持圣禮而被解職。“伴隨著歐洲大戰(zhàn)的爆發(fā),本來對納粹主義不感興趣的上海絕大部分德國商人發(fā)現(xiàn)黨員身份是取得德國政府訂單的前提條件。1939年以后,上海的德國商行與英國商行一樣,政府訂單數(shù)量一下子激增,一時生意興隆。在納粹的壓力下,矮克發(fā)(Agfa)、億利登(I.G.Farben)等洋行都辭退了其上海辦事處的猶太雇員,調(diào)整其政策以迎合所謂國家利益,也就是納粹的利益。”
納粹在中國的領(lǐng)導(dǎo)人叫拉爾曼(Siegfried Lahrman),原來是一名商行職員,1931年加入納粹黨。他在中國公開的身份是“德國國家鐵路公司中國分部董事”。此人身材十分魁梧,紅光滿面,大腹便便。一個德國外交官后來回憶說他看上去 “有些兇殘”。作為納粹在中國的最高領(lǐng)導(dǎo),拉爾曼對一切非納粹的德國外交官嚴(yán)密監(jiān)督,例如指控德國總領(lǐng)事費師爾(Martin Fischer)缺乏“希特勒精神”。
拉貝與這個拉爾曼打過交道,這下面要說。現(xiàn)在想說點題外話。希特勒對德國猶太人大規(guī)模迫害、屠殺前,有為數(shù)不少的猶太人逃離德國,到了中國。他們一開始居住在上海。我原來以為,逃到中國的猶太人雖然也會面臨生存的困難,但總算徹底擺脫了納粹的魔掌。德國離中國那么遠(yuǎn),納粹不會對遠(yuǎn)在中國的猶太人構(gòu)成傷害。待到讀了美國學(xué)者寫的這本《上海秘密戰(zhàn)》,才知道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對于逃到上海的猶太人來說,納粹并沒有遠(yuǎn)在天邊,而是就在眼前。上海納粹組織的使命之一,是對流亡到上海的猶太人進行監(jiān)視。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后,上海全面淪入日軍之手,而在上海的美、英、法等國僑民也就成了日軍的“敵國僑民”,日軍建立了集中營,囚禁這些敵國僑民。在上海的德國人,本是日軍的友邦僑民,理當(dāng)受到禮遇。但從德國逃到上海的猶太人,則也被日軍作為“敵人”看待,也須進入集中營。“關(guān)押在上海集中營內(nèi)的最大外國族群并非同盟國公民,而是沒有國籍的猶太人,他們大多數(shù)以前是德國公民。1933年至1941年間,大約有兩萬名猶太難民逃離納粹歐洲來到上海。”當(dāng)然,逃到中國的猶太人還不至于被公然屠戮。
當(dāng)拉貝向德國政府申請辦學(xué)經(jīng)費時,納粹已經(jīng)在中國開始了有組織的活動。把在中國的非納粹德國雅利安人納粹化,是納粹組織的重要使命。像拉貝這樣的人,本來就是納粹組織要轉(zhuǎn)化的對象。現(xiàn)在,拉貝申請政府資金,等于找上門來,把拉貝加入納粹黨作為提供資金的前提條件,也就是納粹政府自然的做法了。
三加入希特勒的納粹黨,對于其時的拉貝,也并非不得已的勉強之舉,毋寧說是心甘情愿甚至引以為榮的。
自1933年開始,神化希特勒的運動就在德國如火如荼,德國民眾普遍有著對希特勒狂熱的崇拜。到拉貝就任南京難民區(qū)主席時,德國社會對希特勒的個人崇拜已經(jīng)登峰造極。對希特勒的個人崇拜不僅在德國本土洶涌澎湃,在德國以外的地方也同樣存在。在中國的德國僑民,也普遍視希特勒為曠古未有之英雄,為人類的大救星。華百納在《上海秘密戰(zhàn)》中說:“在戰(zhàn)爭期間,凡有大事,德僑(雅利安人)社區(qū)都會聚集在德國花園總會。例如1943年4月,納粹沖鋒隊運動部、希特勒青年團和德國少女聯(lián)盟以演說和游行為希特勒慶祝生日。納粹黨支部頭目休瑟(K.Huether)帶領(lǐng)社區(qū)‘向元首三敬禮’,然后全體人員高唱德國國歌和霍斯特·威塞爾之歌。”所謂霍斯特·威塞爾之歌,就是納粹黨歌。
日軍在侵占南京的數(shù)月前,就開始對南京進行轟炸。1937年10月1日,德國使館通知所有在南京的德國公民,使館方面已經(jīng)包租了印度支那輪船航運公司(怡和洋行)的“庫特沃”號輪船,作為德國公民的避難所。輪船停泊在下關(guān)上游約兩英里處,所有在南京的德國人隨時可避居船上,從而避免遭日軍空襲。這不僅因為輪船離南京市區(qū)有一定距離,更因為一旦有必要,輪船可遠(yuǎn)遠(yuǎn)駛離南京。10月4日,全體德國人在船上慶祝收獲感恩節(jié),拉貝執(zhí)筆為《遠(yuǎn)東新聞報》和《中德新聞》撰寫了長篇報道。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也在船上。拉貝寫道:“陶德曼博士先生用令人感動的話語講到了為什么要舉行慶祝會的緣由……他特別感謝我們祖國的政府,我們尊敬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他沒有忘記生活在危險關(guān)頭的我們,他使我們在這艘船上有一個避難所。在這艘船上,我們可以安全而平靜地迎接未來可能發(fā)生的一切事件。令人難忘的慶祝會結(jié)束時,大家三呼元首和德國萬歲,唱了《國旗之歌》。此情此景我們這些與會者可能誰都不能忘記。”
既然幾乎所有在德國和不在德國的德國人 (當(dāng)然一般不包括猶太人)都崇拜著希特勒,拉貝內(nèi)心也自然充滿了對希特勒的熱愛、崇拜,也對希特勒有著無限的信賴。拉貝總認(rèn)為,如果偉大的元首知悉日軍在中國的作為,一定會義憤填膺,一定會拍案而起,因為元首是那樣仁慈,那樣熱愛人類,那樣熱愛和平。
國際委員會要在南京成立中立性的難民區(qū),需要得到日本方面的認(rèn)可。如果日軍根本不拿你那“中立”當(dāng)回事,當(dāng)然也就起不到保護平民的作用。拉貝在1937年11月25日的日記中寫道:“電臺還報道說,日本人對于建立中立區(qū)一事至今還沒有給予‘最終答復(fù)’。我決定通過上海德國總領(lǐng)事館和上海國社黨中國分部負(fù)責(zé)人拉曼給希特勒和克里伯爾發(fā)電報。”這個拉曼,就是前面說到的拉爾曼。當(dāng)設(shè)立平民中立區(qū)的計劃受到日本方面的無視、冷落時,拉貝第一時間想到的是向希特勒求助。當(dāng)天拉貝發(fā)了“致元首”的電報,其中說:“國社黨南京地區(qū)小組組長、本市國際委員會主席請求元首閣下勸說日本政府同意為平民設(shè)立一個中立區(qū),否則即將爆發(fā)的南京爭奪戰(zhàn)會危及20多萬人的生命。”電報是否送到希特勒手里,不得而知。電報即便送到了希特勒手里,希特勒也不會理睬。拉貝心中偉大而仁慈的元首,正在思考著怎樣制度化地迫害猶太人并最終徹底消滅猶太人,怎么會為遠(yuǎn)東一個城市的些許平民操心。但拉貝卻對希特勒滿懷希望。在當(dāng)天的日記里,寫道:“我多么希望(上帝作證)希特勒會幫助我們,讓我們終于能夠建立起中立區(qū)”。
在以后的日子里,拉貝經(jīng)常在日記里表達對希特勒的期待、信任和崇拜。例如,在1937年12月1日的日記里,拉貝寫道:“羅森博士從美國人那里得到消息說,國社黨中國分部負(fù)責(zé)人拉曼把我給希特勒和克里伯爾的電報轉(zhuǎn)交上去了。謝天謝地,現(xiàn)在我敢肯定,我們有救了。元首不會丟下我不管的!”拉貝堅信,元首一旦得知自己在南京的困難,就會立即伸出偉大的援助之手的。這么偉大的人!這么仁慈的人!這么熱愛人類的人!怎么會置地球上任何一個地方平民的苦難、傷亡于不顧呢?!
拉貝日記中關(guān)于希特勒的文字,最讓人難忘的出現(xiàn)在1937年11月29日。這天日記中寫道:“整理房間的時候,一張元首的相片偶然落入我手中,上面寫著巴爾杜爾·馮·席拉赫的一首詩。”希特勒照片上的詩寫道:
這正是他最偉大之處:
他不僅是我們的元首,是民眾的英雄,
而且他為人正直、樸實而堅定;
我們世界的根須靜臥在他心里,
他的精神輕撫著群星,
而他始終是和你我一樣的普通人。
拉貝接著說:“這再次給了我勇氣。我仍然希望希特勒幫助我們。一個和你我一樣的普通而樸實的人想必不僅對自己民族的災(zāi)難,而且對中國的災(zāi)難也有著最深的同情。我們當(dāng)中(德國人或外國人)沒有一個人不堅信,希特勒的一句話(也只是他的話)會對日本當(dāng)局產(chǎn)生最大的影響,有利于我們建議的中立區(qū),而且,這句話他一定會說的!! ”
“我們世界的根須靜臥在他的心里”,這是我見過的最漂亮的頌圣詩。這首詩表達的是德國一般民眾對希特勒的感受和想象,自然也是拉貝對希特勒的感受和想象。既然“我們世界的根須靜臥在他的心里”,那中國的根須、南京的根須自然也靜臥在他心里;既然中國的根須、南京的根須也靜臥在他心里,他又怎會對中國的災(zāi)難、南京的災(zāi)難視而不見呢?他一定會管的!他一定會發(fā)出他的綸音佛語的!拉貝用兩個驚嘆號表達他對希特勒的信賴。
四那些年,不僅是德國人崇拜希特勒,其他國家也不乏希特勒的崇拜者。中國當(dāng)然也會有。后來成為大名人的儲安平,當(dāng)時就十分崇拜希特勒。
儲安平于1933年7月進入《中央日報》任職,主持副刊。幾年間,也算干得轟轟烈烈,事業(yè)蓬蓬勃勃。但儲安平一直有著留學(xué)夢,心儀的國家是英國。1936年,儲安平?jīng)Q定中止國內(nèi)的事業(yè),赴英國求學(xué)。是年,第十一屆奧林匹克運動會在德國柏林舉行。中國此前也曾兩次派員參加奧運會。1928年的阿姆斯特丹奧運會,中國只派出了觀察員,沒有派出運動員。1932年洛杉磯奧運會,中國只派了劉長春一個運動員,當(dāng)然不可能取得任何名次。1936年的柏林奧運會,由于希特勒熱情邀請中國派團參加,中國便分外重視,組建了堪稱龐大的代表團,其中男女選手七十人,職員二十多人,國術(shù)表演隊九人,體育考察員三十多人,總數(shù)達一百四十余人。代表團出發(fā)前,蔣介石親自宴請隊員并親手授予旗幟。國民政府撥專款十七萬元用于此事。并派考試院院長戴季陶作為政府代表隨團赴德。《中央日報》必須派記者隨團采訪。儲安平既然要到歐洲去,那就讓他先到柏林,作為報社記者報道完奧運會再去英國。報社毋須另行選派記者,而儲安平也可公款赴歐,還可以好好看看奧運會。 儲安平當(dāng)然很樂意。

有許多相關(guān)著作都說明了納粹的興起和希特勒受到狂熱崇拜的原因。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中成為戰(zhàn)敗國、被迫與協(xié)約國簽訂《凡爾賽和約》,這使得德國出現(xiàn)了國民經(jīng)濟和國民精神的雙重崩潰。這個時候,整個社會心理渴望有一個強有力的人物和強有力的政府登上歷史舞臺。這個政府和這個人物能夠迅猛地重振國民經(jīng)濟,讓人民吃飽穿曖,同時還能重振國民精神,把墮落、潰散的國民精神調(diào)動和激發(fā)起來,凝聚到一個神圣宏偉的目標(biāo)上。在這種情況下,納粹黨和希特勒應(yīng)運而生。納粹黨和希特勒迅速做到了民眾渴盼他們做到的事情,盡管是以飲鴆止渴和對大眾欺騙愚弄的方式做到這些的。納粹使德國的國民經(jīng)濟短期內(nèi)復(fù)蘇,物質(zhì)的極度匱乏很快扭轉(zhuǎn),而國民精神(除了猶太人)也死灰復(fù)燃,并且烈焰沖天。在這種情況下,希特勒和納粹黨受到擁護和崇拜也就很自然了。
黃慧英在《拉貝傳》中解釋了拉貝作為一個普通的德國人信賴、崇拜納粹和希特勒的原因。1919年,拉貝回到德國,看到的是政治的動蕩、治安的惡化,看到的是民眾的萬念俱灰和饑寒交迫。通貨膨脹到了人們工資的購買力等于零的程度。大筆銀行存款還買不到一把胡蘿卜。女大學(xué)生在饑餓驅(qū)使下淪為娼妓,歌劇演唱家為了幾片面包任人包唱。幾乎所有物品都要憑票供應(yīng)。拉貝作為德國人中的一員,當(dāng)然也經(jīng)受著生活的艱難。有一次,拉貝得知城里有個地方可以買到稍為廉價的豆類。他趕快過去,買了兩大紙袋豌豆便往回趕。但歸途中下起了雨,又沒有公交車可乘,他在雨中抱緊紙袋,但紙袋被雨打濕,豆子不停地流落下來。到家后,兩袋豆子只剩下一半。黃慧英指出:“戰(zhàn)敗后的德國,經(jīng)濟已到了崩潰的狀態(tài),悲觀失望和困惑,生與死的危機感,在各處蔓延開來。人心思變,人們迫切希望一強有力的政府來收拾動蕩的局面,領(lǐng)導(dǎo)德國擺脫危機,重入正軌。”而拉貝的心態(tài)也不例外。
五茨威格在 《昨日的世界——一個歐洲人的回憶》中,也從物質(zhì)和精神兩方面說明了希特勒崛起的原因。茨威格說,希特勒崛起前,德國的經(jīng)濟崩潰到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先例的程度。一戰(zhàn)后,奧地利的通貨膨脹比例曾達到一比一萬五千,人們已經(jīng)認(rèn)為不可思議。而這與后來德國的通貨膨脹比,簡直是不值一提的兒戲。茨威格說,如果把德國其時的通貨膨脹具體情形和典型事例說明白,需要寫一本書,而且在后來的人們看來,這本書簡直是童話。茨威格說,他親歷過這樣的日子:早晨用五萬馬克買一張報紙,晚上就得用十萬馬克;想要兌換外幣的人不得不按鐘點分多次兌換,因為四點鐘的兌換比價可能要比三點鐘翻幾番,而五點鐘的比價又可能比六十分鐘前多好幾倍。茨威格給出版商寄出一部寫了一年的書稿,為求保險,要求立刻支付一萬冊的稿酬。稿件寄出一星期后,一萬冊稿酬的支票來了,可面值還抵不上一星期前寄稿件的郵資。電車票是用百萬計算的。從帝國銀行(央行)往各銀行運紙幣,運載工具是卡車。茨威格曾在一處排水溝里見到面值十萬的馬克紙幣,那是一個乞丐看不上眼而扔掉的。一根鞋帶先是比先前的一只鞋還要貴,后來則比先前擁有兩千雙鞋子的一家豪華商店還要貴。一扇窗戶玻璃被打碎了,修一下花的錢以前可以買下整幢房子。買一本書花的錢以前可以買下?lián)碛袔装倥_機器的印刷廠。如果有人肯出一百美元,就可以把庫爾菲斯滕達姆林蔭道上的一排六層大樓買到手。以前可以買下幾家工廠的錢,現(xiàn)在只能買一輛手推車。一個剛成年的小伙子在港口撿到一箱肥皂,每天賣出一塊就可生活得像貴族一樣……
茨威格說:“我自信對歷史比較熟悉,但據(jù)我所知,歷史上從未出現(xiàn)過與此類似的瘋狂時代。”不僅是有神話般的通貨膨脹,一切方面都變了,“國家的法令規(guī)定遭到嘲笑;沒有一種道德規(guī)范受到尊重,柏林成了世界的罪惡淵藪……”對于這個戰(zhàn)敗后誕生的魏瑪共和國,全國人民都感到無法忍受,“被戰(zhàn)爭弄得滿目瘡痍的整個國家,實際上都在渴望秩序、平靜、安寧和法紀(jì)。而且整個民族都在暗中憎恨這個共和國。這倒不是因為共和國壓制了那種放縱的自由,而是恰恰相反,共和國把自由放得太寬了。”廣大民眾的意志化作兩只臂膊,把希特勒和納粹黨高高舉起,一只胳膊是對自由的厭惡,一只胳膊是對秩序的向往,而希特勒和納粹黨確實能夠消滅他們厭惡的東西和給予他們向往的東西。
德裔美籍學(xué)者克勞斯·P.費舍爾在《強迫癥的歷史:德國人的猶太恐懼癥與大屠殺》一書中對導(dǎo)致納粹勃興的德國社會普遍的精神狀態(tài)有更詳細(xì)的揭示。費舍爾指出,希特勒和納粹崛起之日,正是德國社會的價值觀念、道德規(guī)范處于被撕裂的狀態(tài)之時。犯罪活動急劇增長、道德標(biāo)準(zhǔn)則快速滑坡,整個社會都有一種“詐騙心態(tài)”。毒品販子、賣淫者、殺人狂、江洋大盜,是有關(guān)20世紀(jì)20年代柏林故事中頻頻出現(xiàn)的角色。費舍爾引用德特勒夫·波伊克特的一番話:“柏林處于國內(nèi)戰(zhàn)爭的狀態(tài)。沒有任何警告,仇恨突然在任何地方和時間爆發(fā):在街頭,在餐館,在電影院,在舞廳,在游泳池;在午夜,在早餐時,在下午三四點鐘。刀子會突然拔出,帶刺的指環(huán)、啤酒杯、椅腿或者鉛棒都成了斗毆的工具;子彈擦過海報柱上的廣告,從廁所的鐵皮屋頂上反彈出來;在擁擠的大街上,一個年輕人受到了沖擊,衣服被扒光,遭到毒打后,流著血被丟在人行道上。十五分鐘后,一切都過去了,攻擊者消失得無影無蹤。”費舍爾強調(diào),知道并理解德國人生活中這些黑暗角落,對于認(rèn)識希特勒和納粹的崛起是很重要的。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和國內(nèi)動蕩的五年,使得殘暴成為德國人日常的生活方式,人們對血淋淋的行為習(xí)焉不察、見怪不怪,人的生命變得十分低廉。希特勒和納粹正是充分利用了德國社會現(xiàn)實中的黑暗和德國民眾內(nèi)心的黑暗,以達到攫取一切權(quán)力、實現(xiàn)自己意圖的目的。換句話說,希特勒正是在德國現(xiàn)實的黑暗和德國人內(nèi)心的黑暗中看清了自己通往權(quán)力頂峰的道路。這時期,小說家托馬斯·曼的兒子克勞斯·曼在慕尼黑卡爾頓酒店的茶室里看見過希特勒,他正坐在另一張桌子邊,一口氣吃了三個草莓餡餅。克勞斯·曼后來回憶說,這個納粹領(lǐng)導(dǎo)人的面孔使他想起新近在報紙上看到的某個人:
除了幽暗的玫瑰色的燈光、輕柔的音樂和一堆曲奇,這里什么也沒有;在甜蜜的田園詩般的氣氛中,一個留小胡子的男人,他眼神迷離,有著一個固執(zhí)的前額……我招呼了一位女招待員結(jié)了咖啡單,這時突然想到希特勒先生像一個人。他是漢諾威的性謀殺者,他的案子是醒目的新聞頭條……他的名字叫哈爾曼……他和希特勒的相似是令人震驚的:迷離的眼神、小胡子、殘暴的神經(jīng)質(zhì)的嘴,甚至難以言表的粗俗的肉鼻子:這確實是太相似的外貌了。
希特勒正是其時德國的黑暗中最黑的那一塊。他之所以能在德國的黑暗中敏銳地發(fā)現(xiàn)自己的機會,就因為他比其他一切黑暗更黑更暗。
拉貝這樣的普通德國人在那些年間對希特勒有著堅定的信仰和熱烈的崇拜,是能夠得到解釋的。黃慧英在《拉貝傳》中說:“1933年1月,希特勒上臺后,在短短的4年內(nèi)奇跡般地解決了國內(nèi)600萬人的失業(yè)問題;6年內(nèi),德國經(jīng)濟在沒有通貨膨脹和完全穩(wěn)定工資和物價的情況下,從蕭條過渡到繁榮,并向戰(zhàn)時經(jīng)濟過渡,希特勒統(tǒng)治下德國的經(jīng)濟發(fā)展速度之快,為英、法、美所望塵莫及。然而,這一切都是在極端手段下強制執(zhí)行的戰(zhàn)爭經(jīng)濟,是為他稱霸世界的狂妄野心服務(wù)的。”千千萬萬個德國人于是信仰和崇拜希特勒,拉貝是其中之一。而一個人,一旦確立了這樣的信仰和崇拜,要發(fā)生動搖、要徹底崩潰,是很不容易的事。必須有連續(xù)性的且性質(zhì)嚴(yán)重的鐵一般的反面事實,才可能讓這樣的信仰動搖和崩潰。而有的人,一旦在內(nèi)心建立起了這樣的信仰和崇拜,便是再多再嚴(yán)重的反面事實,也無法讓其信仰和崇拜動搖和崩潰,即便這事實鋼一般堅固,也絲毫不起作用。懷疑心中的信仰和崇拜,等于否定過去的自己,而有的人,一旦否定了過去的自己,就什么也沒有了,他就歸零了,因為他只有過去而沒有未來。
盡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把拉貝在納粹勢力如日中天時整理南京戰(zhàn)時日記看作是對納粹厭惡的表現(xiàn),但拉貝并沒有留下任何表達對納粹反思和批判的文字。實際上,我們并不能確切地知道拉貝最終是否懷疑并否定了對希特勒的信仰與崇拜。如果希特勒屠殺了六百萬猶太人還不足以令拉貝對希特勒的信仰和崇拜動搖與崩潰,那只能說,有一種信仰和崇拜是無論怎樣的力量都不能摧毀的。
六現(xiàn)實也直接把鐵掌抽在了拉貝的臉上,而且是一個又一個。拉貝希望并相信希特勒和德國政府會同情并支持他在南京的救助活動,但情形卻完全相反。其時,希特勒正想著與日本攜手,而拉貝在南京的作為,可能影響德日關(guān)系,于是納粹政府通過西門子上海總部勒令拉貝離開南京,并且不得回來。盡管拉貝十分放不下南京那些急需救助的人,但也不得不服從命令。拉貝在日記里記下了他的痛苦。1938年2月22日,拉貝在家“打包”。晚上,收音機里傳過來德國承認(rèn)“滿洲國”的消息,拉貝在日記里記述了此事:“晚上10時收音機里傳過來新聞,德國承認(rèn)了滿洲國。據(jù)收音機里說,正逗留在漢口的我國大使陶德曼博士先生在中國政府面前陷入了尷尬的境地。我們擔(dān)心他可能會辭職,盡管報道絲毫沒有提及。從這里我很難看清國內(nèi)的局勢。可是,是對還是錯?它畢竟是我的國家!”日軍在中國的暴行令拉貝對日本沒有好感,而現(xiàn)在,德國竟然承認(rèn)日本扶持的“滿洲國”,這令拉貝困惑。但拉貝沒有讓困惑變成深層的思考,因為“它畢竟是我的國家”,國家主義,或者說國家至上的觀念,阻礙了拉貝把困惑變成求索、反思和深刻的追問。
1938年4月,拉貝回到柏林。西門子總部任命他為遠(yuǎn)東人事部部長。五月上中旬,拉貝在不同的地點做了多場介紹日軍在中國暴行的報告,報告中拉貝放映了相關(guān)影片,更展示了大量圖片。拉貝仍然希望廣大民眾知曉了日軍在中國的行為后,會敦促政府出面阻止盟友日本的暴行。拉貝十分希望當(dāng)面向希特勒匯報在中國的見聞。他仍然相信,如果希特勒親耳聽到了他的訴說,一定會有所作為。他在日記里寫道:“我內(nèi)心期盼大區(qū)領(lǐng)導(dǎo)人伯勒能帶我去見元首,但這個希望沒有實現(xiàn),我便不假思索地在6月8日將我的報告寄給了元首。”拉貝六月八日給希特勒寄出的關(guān)于日軍在南京暴行的報告長達259頁,當(dāng)然還寫了一封致希特勒的信。
報告寄出后,拉貝等待著回音。回音來了。幾天后,兩名納粹黨衛(wèi)軍來到拉貝家中,查收了拉貝的日記和有關(guān)日軍的照片。拉貝本人則連大衣都來不及穿、帽子來不及戴,就被帶出家門、押上了警車。“拉貝被帶到位于阿爾布雷希特街的警察總局,被秘密審訊了好幾個小時。他們讓他坐在白墻前,經(jīng)受各種折磨,被迫回答各種莫名其妙的問題。”讀了拉貝報告的元首,顯然認(rèn)為拉貝的所作所為損害了德國的“國家利益”。由于拉貝為西門子公司立下了汗馬功勞,公司總裁出面保釋,拉貝才得以回到家中,但被釋放前得到這樣的警告:不得再做關(guān)于日軍在中國行為的報告,不準(zhǔn)出版相關(guān)書籍,特別是不準(zhǔn)再放映關(guān)于日軍在南京暴行的影片,甚至不準(zhǔn)寫信和打電話……
至于也熱情謳歌過希特勒的中國人儲安平,大家知道,后來失蹤了,至今活不見人、死不見尸,而仍以活不見人死不見尸之身,頂著一頂大帽子。
2017年11月8日夜
注釋:
(1)(4)(5)(16)(17)(21)(23)(24)(25)(26)黃慧英:《南京大屠殺見證人拉貝傳》,百家出版社2002年12月版,第84頁,第310頁,第103—104頁,第71—73頁,第77頁,第305頁,第297頁,第300頁,第297頁,第301—302頁。
(2)(3)(9)(10)(11)(12)(22)[德]約翰·拉貝:《拉貝日記》,江蘇人民出版社、江蘇教育出版社2009年4月版,第69頁,第73頁,第23頁,第80—81頁,第94頁,第89頁,第572頁。
(6)(7)(8)[美]華百納:《上海秘密戰(zhàn)——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的諜戰(zhàn)、陰謀與背叛》,上海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2015年8月版,周書垚譯,第57頁,第153頁,第144頁。
(13)(14)(15)韓戍:《儲安平傳》,牛津大學(xué)出版社2015版,第133—134頁,第137—138頁,第142頁。
(18)[奧]斯蒂芬·茨威格:《昨日的世界》,三聯(lián)書店1991年3月版,舒昌善等譯,第347—348頁。
(19)(20)[美]克勞斯·P.費舍爾:《強迫癥的歷史:德國人的猶太恐懼癥與大屠殺》,譯林出版社2017年1月版,佘江濤譯,第168頁,第17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