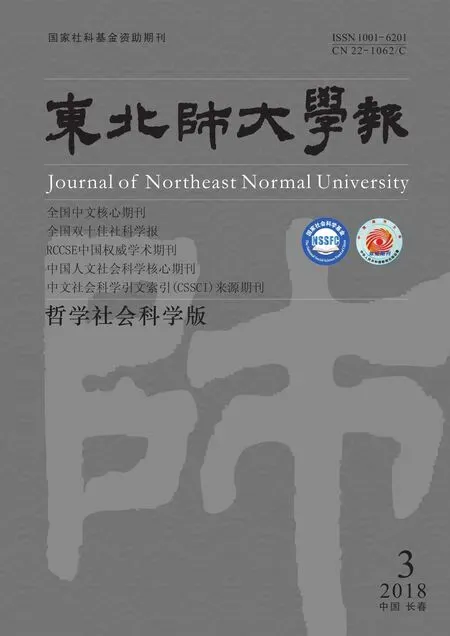人文科學與公共領域:語用學視角
耶夫·維索爾倫 著,仇云龍 譯
(1.安特衛普大學 人文學院,比利時 安特衛普 2000; 2.東北師范大學 外國語學院,吉林 長春 130024)
一、引 言*2013年10月21日至22日,芬蘭科學與文學學會人文科學分會建會175周年研討會在赫爾辛基舉行,筆者在會上發表演講。隨后,該演講的主要內容又在其他場合發布。本文是基于演講內容整理而成的,但根據觀眾反饋及Pragmatics and Society雜志匿名審稿人的建議進行了大幅修改。英文版原文曾刊載于Pragmatics and Society 雜志2016年第1期上,頁碼為第141到161頁。
在《媒體與現代性》一書中,約翰·湯普森呼吁“公共性的再造”。“協商民主”認為:“一切個體都能吸納信息和不同觀念,進而成為具有理性判斷力的自主個體。而且‘協商民主’整合多種機制,將個體判斷納入集體決策的進程中。”[1]255顯而易見,公共性不可或缺。但是為什么呼吁“公共性的再造”呢?
首先,回溯到20世紀60年代早期[2],哈貝馬斯概念下的公共性聚焦的語境是:公民在討論和確立自己的立場時,可以置身國家權力之外并常以批判的眼光檢視國家權力。當下,公共性所關涉的領域勢必超出政治范疇。其中的部分領域并不直接被國家政權管控,部分領域具有跨國特征,這些是目前多數交流形式和經濟活動所具有的特征。在變化日新月異的今天,結構邊界的存在已無必要。國家政權、語言、國民經濟、紙質媒介、廣播、公共話語之間的邊界已經模糊。公共領域的范圍已向全球擴展,這使意義制造的過程空前復雜。
其次,公共與私人的邊界愈加模糊。與前一點統合考慮,用皮特·瓦格納的話說,在本土可見的一個重要的全球化現象或許是“意義來源語境的式微”[3]168。這源于邊界或解釋框架的模糊,事實上成為“流動的現代性”[4]。
再次,再造公共性是因為公共性不再需要可視和共現。這是因為通訊媒介的大規模發展產生了“中介化的公共性”。這在湯普森1995年呼吁“公共性的再造”時已是事實。在通信技術飛速發展的今天,更是不言而喻。因而,在全球化語境下,一種新興的公共領域正在形成,它不把公共交流領域局限于某一特定場所,也不把其局限于單一的言語社區。
這一視角暗含著一種多元的公共領域觀。我避免使用復數形式來表示公共領域,以免人們誤以為公共領域是可被切分的分散單元。意義生成的過程是動態的,其關涉的個體不會是固定不變的或邊界明晰的。數字媒體的發展更印證了這一點[5]*這種視角與當下社會邏輯學有關現代性的認識是一致的,即認同多種現代性的存在[6][7],但不認同其根植于特定的文明或文化經驗之上。相反,這種多樣性源自以交際為基礎的或分或合的體驗和闡釋[3]。考慮到當今的交際實踐,瓦格納呼喚“世界現代性社會學”的出現;湯普森也闡述了類似的觀點[1]。。
同時,以上論述暗示:公共領域是一個可以公共獲取意義的空間。意義生成具有交際性、交互性和主體間性。這是公共領域的本質所在。因此,當我們對公共領域中的交際感興趣時[8],我們應把公共領域本身視作語境中的交際集合。語境包括共享媒體、網絡、組織、機構、國家以及類似于國家的組織。
另外,公共領域可被視作意義博弈不休的舞臺。意義博弈受制于結構語境;而人也總是起作用,因而交際非常必要。對于語境意義的解讀及其可能產生的后果,評價不盡一致。人的決定和行動正是建立在這些不同評價之上的。在民主社會的公共領域里,人們言論自由,解釋和決定需要通過爭論得出,行動需要后續合法化予以確認。沒有一件事情是永遠不變的。此種意義博弈會產生社會、經濟和政治影響,因而它們值得密切關注。
我們說“公共領域是意義博弈的舞臺”也暗示著一些潛在的問題。其根本問題在于意識形態成為“為權力服務的意義”[9]7。公共領域里的社會關系和人際之間的公共定位普遍以支配關系為特征。它們的建立和維系有賴于公共話語或交際中潛存的意識形態。此處,意識形態并不等同于那些被視為現代歷史發展動力的政治流派或“主義”。它是一類更為寬泛的現象,包含關涉社會現實的多種意義形式和解釋框架。意識形態信念常被視為“常識”(或者說它們被籠統地看作“常規”),進而不受質疑地浸入交際之中[10]。人們的行動將被不知不覺地引導。與意識形態有關的交際失衡已是當今權力機制運行的特征,我們應對其進行監控。這對于那些以其民主根基為榮的社會尤為重要,因為將自己劃入“民主”行列是規避民主相關討論最有效的捷徑。
二、人文科學
現在來談談人文科學。從目前的發展潮流來看,社會科學更多地聚焦于宏大的結構而非微小的機構,這有其合理之處。與之相對的研究情況是(這是有據可查的,甚至在Gripsrud[11]等2011年在其四卷本《公共領域》中提出該術語之前的舊材料中都可以查得到),更多的研究集中在政治、傳媒和機構等與上層建筑有關的分析上,而不是觀點的創造性(特別是與話語有關的)產出以及基于這些觀點的批判性行動。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大眾傳媒(數碼的、視聽的和印刷的)與社會經濟、政治結構及進程之間的結構性依賴被廣泛研究,有時是從歷史維度進行的[12],但通常還是從歷時維度進行的[13][14][15]。研究焦點是,媒體作為公共觀點的塑造者和承載者如何對公民身份、國家身份和民主產生作用。跨國界過程研究成為新寵。與歐盟那樣具有政治抱負的機構相關的話題則更受關注。人們從中可以發現創立一個跨國公共領域的嘗試甚至見證一個跨國公共領域的出現*學者們圍繞歐洲公共領域、跨國歐洲身份和公民身份、政治參與和民主新樣態的出現展開了討論,詳情可見 Giorgi 等[16],Koopmans & Statham[17],Triandafyllidou等[18]。。
以上有關微小機構的論述并非哈貝馬斯[2]所想。在哈貝馬斯看來,資本主義公共領域是從事公共活動的個體舞臺,它獨立于國家政權之外。而個體定位和理性辯論是其觀點的核心所在。他將公共性的裂變歸因于公民社會與政權的逐步交織(前者呈現公共權力,后者浸入私人空間),歸因于特殊利益集團(包括政黨)代替了依靠推理、論證基本工具所追求的共同利益,歸因于信息生產者和消費者的進一步分離。但對于哈貝馬斯來說,公共領域的基本要素,無論是原始形式還是后期變體(有些理想化),都是交際;而交際則是人類都能參與的活動。這一核心分析原則可以解釋哈貝馬斯的悲觀情緒是如何被其秉持的積極觀念所中和的[19]。其悲觀情緒源于官僚化和市場化所產生的抑制作用;其積極觀念源于他相信現代性仍是個未盡的任務。哈貝馬斯堅信,通過交際行為公眾會對社會和政治進程產生持續的潛在影響[20][21]。
如果我們將意識形態過程視為由話語生成和支撐的,滲透于公共領域的思維慣習,則由人文學科具體領域所提供的對意義制造過程的細致觀察便會對我們所說的公共領域“生態”做出有益的貢獻。我對公共領域“生態”的使用基于兩點考慮。一是它強調了這樣一個事實,即全球公共領域作為一個意義疆域不可能是單向的、自成一體的。相反,它是復雜的,其復雜性體現在它是一個由多種語言和交際風格所承載的,動態、多向的意義制造連續統。它在廣泛的網絡和機構中通過多種公共媒介(印刷的、廣播的、數碼的)運行。二是這種綜合性的、通過交際形成的動態公共領域缺乏透明度且容易被操控。圍繞意義的博弈會維系或建立支配形式。此種博弈必然為個體或集體意向所驅使,但又會被視作公眾性和全球性意義生態的一部分,因而受到生態制約。任何可持續的平衡或均勢都依靠對這些過程的清晰認識,意義生態因此可被視為將人文科學融入公共領域相關分析的、首要的理論和實踐關切;盡管公共領域分析在傳統上被社會科學和政治科學所支配。
自不必說,與早先出現的人類生態、社會生態、文化生態、城市生態、公共生態等術語類似,此處的“生態”一詞也經歷了詞義拓展,超出了常規意義。顧名思義,這些領域聚焦人類在社會語境中的位置和角色,而社會語境又無一例外地與自然環境相關。Hawley(1950)提出的“人類生態”[22]從整體上關涉人類社會同生態之間的關系。Bookchin(1980)提出的“社會生態”[23]首先是一個生態惡化理論,該理論將生態惡化現象與社會基本問題相鏈接。《生態與社會》(EcologyandSociety)這樣的刊物主要關注自然科學各方面服務于可持續發展這類重要社會目標的方式。類似地,Steward(1972)提出的“文化生態”[24]旨在描述人類與多元化的物理環境相順應的方式,而Bateson(1972)提出的“心智生態”[25]則強調心智與自然的一體(更加全面的論述詳見于后續發表的《心智與自然》一書[26])。Finke(2005)或許是偏離自然范式最遠的論著,該書引入“知識生態”的概念來描述現代科學的發展,其中也兼顧了相對獨立的文化過程[27]。同時,“知識生態”也成為一場運動的代名詞,該運動與現今經濟學中的知識管理問題相關。
在語言學領域,“語言生態”也傾向于包含語言 “自然生命”的意蘊,這表現為語言與語言之間的互動(存在于多語使用者或雙語使用者的腦海里)或語言與其發揮作用的社會之間的互動。如Haugen(1972)所言,“長久以來,語言生態在認知語言學、民族語言學、語言人類學、社會語言學和語言社會學的范疇內進行研究”,“語言學家在語言演化和變異、語言接觸和雙語主義以及語言標準化等方面對其進行了涉獵。”[28]327從這個意義上說,語言生態在Enninger 和 Haynes(1984)[29],Mühlh?usler(1996)[30],Mufwene(2001)[31],Calvet(2006)[32]及Bastardas-Boada(2012)[33]的論著中被使用,使用疆域基本處于“語言化”的社會和空間維度(“語言化”一詞有據可查,可能有些著述并未使用這一時髦的術語,但說的就是這種現象,如Schneider 和 Barron 2008年的作品[34]及 Auer 和 Schmidt 2010年的作品[35])。
我對語言生態的認識與前人不同,我將焦點放在意義上,放在生成意義的方式上,放在由意義產生的彼此相連的公共領域所構成的世界上(公共領域此處用了復數,其處理需格外小心,以免造成錯誤的暗示,即存在界限明晰的若干領域)。
圍繞上述焦點,與人文學科相關的研究可從兩個層面進行。為方便起見,我將其稱之為“自上而下的視角”和“自下而上的視角”。“自上而下的視角”是對現存交際樣式的宏觀審視。從該視角出發,我們可以進行一些有趣的觀察,觀察交際系統如何協同決定我們看待世界的方式。例如,當我們觀察市場化背景下的媒體話語和政治話語時,可以發現一些有趣的話語樣式(已有大量文獻對這一現象進行評論)。我們可以舉出許多有趣的例子,但這并非本文探究的重點。
“自下而上的視角”主要是對情境中的具體語言使用過程進行小規模的微觀分析。事實上,該視角須先于“自上而下視角”,“自上而下視角”本身必須建立在具體話語分析的基礎上。此處,我想從人文學科的一個角度出發進行闡發,這一角度便是語用學。
三、語用學
上文我將公共領域定義為 “意義空間”。為何如此界定此處勿須贅言,我只想說明,從意義的角度定義人類環境并非新事。Winch的論斷[36]是這種定義方式的源頭,但社會科學界并未對其給予足夠重視。Winch(1958)指出,任何形式的社會行動都是“有意義的”[36]。因為它是被參與其中的行動者所解釋的,所以只有了解了行動者的解釋才能理解社會行動。同樣,也早有論斷指出,沒有話語或交際(即沒有口頭或符號形式的意義交換),也就沒有社會行動。因而,我冒著贅述的風險再次重申,公共領域應從意義的角度進行研究。
在先前的論述中,我強調了公共領域的意義博弈及其與意識形態之間的必然聯系。意識形態在本文中是指趨向于常識的解釋模式。與所言相對的,浸入語言使用的意義無疑是隱性意義。在公共領域或其他地方的意義制造總是隱性意義與顯性意義互動的結果。尤其是從意義博弈的視角出發,對公共領域中互動過程的仔細分析具有重要作用。對意義制造過程中的隱性意義及其作用發揮需要借助工具進行語言差異分析和風格差異分析,而語用學為此類分析提供了工具(?stman于1986年將語用學定義為“隱性語言學”[37])。
語言學家(比如 Chilton 2004,Scollon 2008,Wodak &Meyer 2009 等)[38][39][40]已為公共話語研究提供了有效的工具,其研究對象與我從生態角度探究的話題相似。盡管我的主張建立在系統的語用學理論體系之上,但我早期的工作是站在特定的批評立場上,使用有限的分析工具,開展有關政治現實的研究。這種方式在研究某些類別的批評話語時存在局限[41]59-81。對于這種方法上的局限,Verschueren提出了較為有效的解決方案[10]。在該書中,我運用語用學理論框架系統設計了用于公共領域意義分析的步驟。該書的焦點也是由隱性意義和顯性意義互動而成的意識形態意義。
從廣義上講,語用學是關于語言使用的具有跨學科屬性的(認知的、文化的、社會的)科學[42]。其起點在于語言使用的心智活動從根本上說是生成意義[43]。它存在于連續不斷的選擇之中,選擇不只發生在語言結構的不同層面之上,也包含交際策略,甚至語境的不同層面。做出選擇是語言產出和語言解釋的共有特征。做出選擇可以是具有不同意識突顯度的過程或活動。并非所有的選擇都是等同的,一些可能比另一些更具標記性。它們總是觸發其他待選項或構成對比集。但做出選擇是不可避免的,它由居于社會文化之中且具有生物學基礎的人類認知體制協調,與元語用自返性相關,并產生監控效應。
變異性、協商性和順應性這三個屬性使語言選擇成為可能。變異性限定了做出選擇的可能范圍。范圍本身并不穩定,它會隨語境和時間發生變化,也可被語言使用者主動改變。協商性意味著語言選擇不是機械的。選擇并不遵循嚴格的規則,形式與功能之間的關系也不是一成不變的。相反,選擇遵循靈活的原則和策略進行。這一屬性可以解釋意義的不確定性,也可以解釋為什么有限(盡管總是可以擴充的)語言形式具備巨大的意義潛勢。最后,順應性使人們從若干可能中做出協商性選擇,以此到達符合交際需要的滿意點位。
意義生產在社會—文化語境中發生,順應性被認為是意義生產過程中形式與功能之間動態、可協商的相互順應。這一概念本身并不是一個操作性概念,它將我們引向語用學研究的四個角度,在分析語料時,這四個角度都是相關項。
(1)順應性的語境相關成分 — 順應性選擇如何與復雜的事件狀態(被語言外事實和既成的語言使用模式所塑造)相關?
(2)順應性的結構對象 — 選擇發生在語言結構的哪些層面上?
(3)順應性的動態過程 — 形式不決定功能但卻有效影響功能,我們如何解釋這種關系?
(4)順應性的意識突顯度 — 高度動態的意義生成過程與居于社會文化之中且具有生物學基礎的人類認知機制之間有何關系?
總而言之,語境和結構構成了探述語言使用過程的所在位置[44]14-24。但語用學者的終極關懷在于意義生成的動態過程,即與社會心智相關的語言形式如何有意義地發揮作用。
順應性(Verschueren 和Brisard 2002進行了綜述)將語用學理論與上述公共領域概念及意義生態直接相連[45]。從進化的視角看,基本的人類順應是高度發展的順應于社會—文化語境的能力。語言使用是社交世界的重要組成部分,而社交世界是人類“自然”環境的一部分。甚至人類心智在根本上都是“社會的”[46]。或者,使用Enfield(2010)的術語,由一系列社會導向的認知能力所組成的人類“社會性”是語言的核心[47]。語言是社會行動的主要工具,進而也是生成公共領域的工具。因此,如果我們想要理解公共領域,探究相關生態要素,對語言使用的實證研究則是重要的。
現在的問題是,我們如何將這項工作付諸行動?
四、挑 戰
就隱性和顯性的關系而言,語言有兩個本質特征。第一,所有的語言(或許所有的言語)使用的都是由隱義和顯義共同構成的復合體。第二,所有的語言都有結構手段對隱性意義進行“標記”(或編碼)。隱性意義的“標記語”或“載體”從對象待定的指示成分(如人稱代詞或時間副詞,其指示內容隨語境而變化),到語義內容不完整的詞語表達(比如“高”這樣的形容詞會引發有關評判標準的問題),再到大量負載預設的詞和結構(比如因某事而抱怨某人預設了被抱怨內容事實上存在且說話人對該事件的評價是消極的)甚至地名(預設了這些地點的存在)和互動生成的會話含義(比如“約翰有三個孩子”的常規解釋是約翰正好有三個孩子,盡管從邏輯上講,即使約翰有四個孩子,該話語仍然成立)。
在某種程度上,看似出現了一個語用矛盾。有標記符號標識的(或編碼的)隱性意義還是隱性的嗎?如果僅有那些無標記符號標識的(或編碼的)的隱性意義是真正的隱性意義,它還能從語言學的角度進行研究嗎?這一“問題”捕捉到了語言使用中隱性意義的本質,以及語用學應該如何對其進行闡發的問題。對于聽者而言,隱性意義必須是可推斷的。這就要求有觸發物或可追溯的痕跡,而這些可被研究者識別和分析。這就是Levinson(2000)提出用語用策略來描述推理和解釋的原因[48]。語用學若想保持其實證性學術領域的地位,它所探述的只能是以下表征隱性意義的形式:(1)有清晰可辨的語言痕跡或觸發物;或(2) 沒有“可見”觸發物,其功能亦能呈現。在第 (1) 種情況下,我們可以處理那些與話語類型相關的常規意義或者處理那些由話語類型承載的偏離常規的意義。在第 (2) 種情況下,我們必須依靠這種形式,即一個話語片段明確地建立在前一個語言選擇的具體解釋之上,即使該選擇是隱晦的或潛存著歧義。
總體而言,這是一個重要的方法論問題。但是就本文所探討的問題即公共領域的意義生成而言,我們所面臨的具體挑戰是什么呢?
公共領域是意義博弈的領地,其復雜性源自顯性意義和隱性意義的非透明(或者說基于習慣的)交織。這與上文提到的語言的第一條本質特征一致。基于以上描述,可判斷此問題在語言使用中普遍存在。
一個更加具體的挑戰在于以下兩者的疊加:(1)公共領域被重新定義為具有擴散性、調節性和流動性的新興的全球性現象。(2)上文提到的語言的第二條本質特征。換言之,其復雜性亦源于這樣的事實,即意義的顯性—隱性級別差異性地附著在不同的語言和交際風格之中。具體地說,這就意味著,即便在不同語言和社區中表達同一事件或狀態,即便說者并非故意講述不同的故事,不同的意義景觀也會出現。
我將試圖使用一個描述性的、可被用作討論隱性意義的三維模型來厘清這一點*有關這一視角相關理念的更直接闡述,詳見Verschueren(2013)[49]1-9。。盡管此處不能詳述此模型(或我下文呈現的用于可視分析的表格)的具體特征,但我還是需要簡短地指出隱含其中的假設。第一,隱性—顯性的區分不是二元的而是層級的。并不是所有的隱性意義在隱性程度上都是相同的。因而,存在一個“突顯度”的問題,其程度由可及性決定,也由與隱性意義具體載體相關的處理消耗決定。第二,這種層級性并不是單維度的,即語言現象不被置于單一的顯性—隱性軸上。因為在隱性意義載體與其語言環境和非語言語境之間還存在著局部的策略性互動。這就意味著,“結構”和“語境”兩個維度亦應被考慮在內,進而衍生出圖1所示的三維模型。

圖1 隱性意義的三維模型
原則上說,這三個維度(對應語言順應論四個研究角度中的三個)應該可以使我們描繪意義的景觀(呈現第四個,也是最中心的角度,動態性)。實際操作中其實更難。毫不隱晦地說,目前我只能靠直覺操作。無疑,“意識突顯度”在一定程度上可測;例如,實驗語用學的巨大進展可以幫助我們從處理時間和付出努力的維度來區分不同種類的一般會話含義[50]124-154,但此類工作僅限于相當有限的現象。也許“結構”是最容易操作的維度,因為意義觸發物的結構位置可以被成型的語言類別所描述。“語境”稍顯復雜,因為相關要素是在具體情境中由視野線或話語使用者的取向所決定的。
現在讓我嘗試性地對該模型進行說明。我使用的語料同時也用于說明意義景觀中互文性差異的生成以及它們如何幫助我們理解新興的國際化公共領域。
我使用的語料來自2004年歐洲大會討論歐盟憲法[51]時使用的,寫于2003年的協議草案*我使用此例之靈感源于從Stella Ghervas[52][53]處得到一份兩頁長的與此話題相關的諷刺短文。在此,特對其為本文做出的貢獻表示感謝,但本人對文中得出的結論負責。。2004年歐盟進行了擴員,協議草案所使用的語言是擴員前歐盟國家使用的11門官方語言,它們分別是:丹麥語、荷蘭語、英語、芬蘭語、法語、德語、希臘語、意大利語、葡萄牙語、西班牙語和瑞典語。我將集中于其中的部分版本加以評論。樣本選用的標準是,在國際層面,它是一個在不同語言中意義潛勢相當(就整體而言)的獨特文本。我的問題是,這些不同的版本呈現的意義景觀相同嗎?
不同版本之間的確具有高度相似性。但區別在標題中已有顯現,其中至少可以發現三種細微的意義差別。英語、法語和意大利語版本的標題中,動詞形式暗示所描述的行為是結果性事實。荷蘭語版本的側重有些許不同。協議草案與憲法之間也是因果關系,這與上述三個版本相同。但此處使用的是由動詞派生而來的名詞外加一個方向性的介詞,而不是直接使用動詞形式,表達的便不是結果性事實而是結果性目標。西班牙語版本雖表面上看似差異明顯,但其基本含義相同。使用因果狀語外加反身被動式(reflexive passive)的表達方式也是設定了目標,目標源于由任意或模糊施動者參與的過程。在德語版本中,條約與憲法之間并無施事性關聯。二者只有相關性,預設憲法的事實性存在。
用我們的三維模型來描述這些區別,對結構層面的判斷并不難。在結構層面,我們不難發現前文提及的意義差別的觸發物。盡管形式不同(動詞、由動詞派生的名詞、介詞、結果狀語),但其發揮的作用相似。因為沒有找到更合適的術語,我們姑且將其稱為“關系標識語”,簡稱為“X-關系-Y”。
上面提及的隱含義都與特定的語境要素相連:事實性意味著在“世界”中存在,“世界”可以是先在的或結果性的;而目標則與交際過程中人們的參與有關。
對隱性意義的意識突顯度的評價更難些,且目前只能依靠直覺判斷。但德語版本的事實性表述無須耗費太多精力進行處理。其結果性事實和結果性目標離所言距離遠些,一旦說話人意向被否,它們更易受到影響。因而,如果用直覺來區分意識突顯度的兩個層面,我們會將德語版本置于較上層面(距離表面最近),而將其他版本置于其下面的水平線上。
為了使三維模型更加可視,我們可將其轉化為二維模式進行表征,上部為序列結構,下部是語境索引,中間是不同程度的意識突顯度。于是,就條約草案而言,可見如下意義景觀:
表1標題中的意義差別

現在我們將注意力由標題轉向序言部分。序言結尾處融合了兩個有趣的轉折。
[…]inthehopethatit [this text] will constitute the foundation of a future Treaty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Constitution.
[…]ensouhaitantqu’il constitue le fondement d’un futur Traité établissantlaConstitution européenne.
[…]auspicandocheesso costituisca il fondamento di un futuro trattato che istituisce la Costituzione europea.
[…]inderHoffnung[…]dasserdas Fundament eines künftigen Vertrags über die Europ?ische Verfassung darstellen wird.
[…]daarbijdewensuitsprekenddathij als grondslag dient voor een toekomstig verdrag tot vaststelling van de Europese grondwet.
[…]coneldeseodeque constituya el fundamento de un futuro TratadoporelqueseinstituyelaConstitución Europea.
首先,引文中語境化的從句以顯性的方式引入了一個新要素,即愿望。對其解釋只需依字面意義而行,無需付出更多努力加以處理。其次,德語版本中仍有類似于標題部分的事實性轉向,其實現方式是將與“憲法”配合使用的不定冠詞變為定冠詞。該意義要素是否會被輕易捕捉仍不確定,因為 “the European Constitution” 和 “a future Treaty” 并行使用。因而需要一定的精力進行處理。但在2004年,在爭議聲中,確定的條約文本得以通過時,定冠詞又一次被不定冠詞取代,這種確定性/事實性變得更加清楚了。所以,不同的形式在此處似無區別。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條約草案的引言部分,它以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的格言開篇(II,37):

在其不同版本中,除了在英語、法語、意大利語、西班牙語版本中選用名詞 “民主”(“democracy”)而非荷蘭語版本中使用的形容詞“民主的”(“democratic”)以外,多數表述都很類似。民主被社會掌權者所定義,公民則被定義為積極的參與者。德語版本中的表述則有明顯不同:
Die Verfassung,die wir haben … heisstDemokratie,weilderStaatnichtaufwenige Bürger,sondernaufdie Mehrheitausgerichtetist.
此處,權力(“Macht”)一詞未被選用,轉而以國家這一掌權機構代之。另外,人民也并未積極參與,他們被國家機器所引導。這個區別不小。我們只能推測形成這種差異的原因。德語中未使用“權力”一詞或許是為了規避其極權主義內涵。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德語中代替“權力”的機構本身是個施動者,它選擇性地導向多數。而其他版本的表述中并未指出多數人掌權,而是不加選擇地導向社會中的每一個個體。
不同版本間的區別體現在詞匯和短語的選擇上。在“人民手中的權力”(下文表2中簡稱“權力/人民”)和“國家手中的人民”(或“人民/國家”)中,對應的語境含義與意識形態差別相連。就信息處理而言,前者與所言層更接近(表2中的頂層),后者依賴于更多背景信息,包含可能引起爭議的重要元素(因此置于三層以下)。
引言進一步細化了一些假定的歐洲特征,并將其作為解讀憲法草案的背景。其中之一表述如下:
[…] while remaining proud oftheirownnationalidentitiesandhistory,the people of Europe are determined to transcend their ancient divisions and,united ever more closely,toforgeacommondestiny
[…] que les peuples de l’Europe,tout en restant fiers deleuridentitéetdeleurhistoirenationale,sont résolus à dépasser leurs anciennes divisions et,unis d’une manière sans cesse plus étroite,àforgerleurdestincommun
[…] che i popoli dell’ Europa,pur restando fieri dellaloroidentitàedellalorostorianazionale,sono decisi a superare le antiche divisioni e,uniti in modo sempre più stretto,aforgiareillorocommunedestino
[…] que los pueblos de Europa,sin dejar de sentirse orgullosos desuidentidadydesuhistorianacional,están resueltos de superar sus antiguas divisiones y,cada vez más estrechamente unidos,aforjarundestinocomún
[…] dat de volkeren van Europa,ook al zijn zij trots ophunidentiteitenhunnationalegeschiedenis,vastbesloten zijn hun oude tegenstellingen te overwinnen,en,steeds hechter verenigd,vormtegevenaanhungemeenschappelijkelotsbestemming
[…] das die V?lker Europas,wiewohl stolz aufihrenationaleIdentit?tundGeschichte,entschlossen sind,die alten Trennungen zu überwinden und immer enger vereintihrSchicksalgemeinsamzugestalten
我不想在國家身份和歷史的可能含義中停留。人們可以問為什么英語版本是僅有的將身份一詞用作“復數”(identities)的版本,荷蘭語版本為什么把形容詞“國家的”置于“歷史”之前,而德語版本又為什么把“國家的”置于“身份”之前(或者更傾向于置于“身份和歷史”之前,這也是多數其他版本的傾向性解讀)。這些區分可能是僅由語言的不同特點所致,也可能由干擾所致(例如,荷蘭語版本可能源于法語版本,因而導致其解讀是將“國家的”置于“歷史”之前;盡管另一種解讀方式,即將“國家的”置于“身份”和“歷史”之前也看似有理)。
更加有趣的是最后引用的段落,此處描述的是追尋共同命運的方式。有三種不同的版本:
英語和西班牙語使用的是奔向“一個”(不定冠詞“a”)共同的命運,清晰地表明共同的命運仍不是事實而是努力的目標。
法語、意大利語和荷蘭語積極奔向“他們的”共同命運,鮮明預設其先在性(盡管仍需進一步塑造);法語“destin-commun”語力很強。
德語版本傾向于共同塑造“他們”的命運,因而聚焦于過程,隱含地否定了共同命運的先在性。
意義的細微差別由修飾詞和(如德語)形容詞向副詞的轉換所觸發。英語和西班牙語的隱性意義很淺(下面第二層),德語略深(下面第三層),或許法語、意大利語和荷蘭語最深(下面第四層)。
上面提及的現象,如果孤立地看,差異不大。然而,若將其統合在一起,六種語言形成的意義景觀差異巨大。上文僅呈現了部分片段。表2從標題、序言、格言和引言的維度對六種語言生成的意義景觀進行了描述,使與其對應的評論更加可視。
表2差異化的意義推進過程

不難想象,倘若我們將不同版本的條約草案全文進行比較,會看到怎樣的意義景觀。更難判定的是這些差別所能達成的最終效果。在此階段,我不想暗示,西班牙語版本的可能屬性導致西班牙選民在憲法投票中樂于投贊成票,而法語、荷蘭語版本的可能屬性導致其公民在公投中投反對票。但不可否認的是,圍繞重要公共事件出現的差異化的意義景觀產生了重要的效果。
五、前 景
同一事件的不同版本之間尚存如此差異,不同事件之間的差異之大自然可以想見。這就意味著,盡管在世界范圍內,交流日趨便利,信息更為可及,但是解讀信息、形成觀點和做出決定所立足的論述和敘述卻差異甚大。于是,平行的領域被建立起來,而且人們仍然抱有一種錯覺,即這些領域彼此連通、可及而且透明。我們很容易相信今天的通信技術會抹平邊界。如在本文引言中所說的那樣,被可控的公共媒介支撐的熟悉的結構邊界(國家之間、語言之間和國家經濟體之間)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消蝕。但這并不是說結構不重要。相反,多數人使用工具需要界定其交際領域(通過有意地包含或排除彼此的聯系),以及其他人使用工具使信息“個性化”或過濾信息(無論是出于政治目的還是商業目的)的方式。這使結構更加碎片化,并造成這樣的印象:一個人可知的領域無限,一個人可以采取的視角無限。
身居全球化公共領域中的人們對社會、政治事實的解讀必然存在差異。未來我們必須找到理解這些差異的方式。與以往相比,我們今天更須找到教育人們注重相關過程的方式。日趨成熟的有關語言使用的科學可以詳細描述人與人之間、文化與文化之間、國與國之間的差異性,它將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為我們的上述努力助力。在此進程中,人文科學必須與社會科學合力,或許還會有人補充,也需與認知科學合流。如果我們使用一個宏觀概念來指代構成公共領域內核的意義景觀的話,這個詞便是意識形態。畢竟,意識形態是一個社會性嵌入的認知現象(或者說是一個認知性附著的社會現象)。
我嘗試性地在日趨成熟的有關語言使用的科學疆域中尋求一條進路,以期為再造的公共領域提供一種理解方式。之所以是“嘗試性地”,是因為這個依托翻譯語料所進行的分析是靠直覺判斷的。語用學研究仍需取得積極進展,無論是人種學方面的、計算機方面的,抑或實驗方面的,并以此超越直覺判斷層次。
[參 考 文 獻]
[1] Thompson,J.B.TheMediaandModernity:ASocialTheoryoftheMedia[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2] Habermas,J.TheStructuralTransformationofthePublicSphere[M].Cambridge,MA: MIT Press,1989.[Original German version,Strukturwandelder?ffentlichkeit,1962.]
[3] Wagner,P.Modernity:UnderstandingthePresent[M].Cambridge: Polity Press,2012.
[4] Bauman,Z.LiquidModernity[M]. Cambridge: Polity Press,2000.
[5] Gripsrud,J.& H.Moe.(eds).TheDigitalPublicSphere:ChallengesforMediaPolicy[M].G?teborg: Nordicom,2010.
[6] Eisenstadt,S.N.MultipleModernities[M].Piscataway,NJ: Transaction,2002.
[7] Eisenstadt,S.N.ComparativeCivilizationsandMultipleModernities[M].Leiden: Brill,2003.
[8] Wodak,R.& V.Koller(eds.).HandbookofCommunicationinthePublicSphere[M].Berlin: Mouton de Gruyter,2008.
[9] Thompson,J.B.IdeologyandModernCulture:CriticalSocialTheoryintheEraofMassCommunication[M]. Cambridge: Polity Press,1990.
[10] Verschueren,J.IdeologyinLanguageUse:PragmaticGuidelinesforEmpiricalResearch[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
[11] Gripsrud,J.,Moe,H.,Molander,A.& G.Murdock(eds.).ThePublicSphere(vols.I-IV) [M].London: Sage,2011.
[12] Barker,H.&S.Burrows.Press,PoliticsandthePublicSphereinEuropeandNorthAmerica,1760—1820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
[13] Dahlgren,P.TelevisionandthePublicSphere:Citizenship,DemocracyandtheMedia[M]. London: Sage,1995.
[14] McNair,B.JournalismandDemocracy:AnEvaluationofthePoliticalPublicSphere[M].London: Routledge,2000.
[15] Price,M.E.Television,thePublicSphere,andNationalIdentity[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16] Giorgi,L.,Ingmar von H.&W.Parsons(eds.).DemocracyintheEuropeanUnion:TowardstheEmergenceofaPublicSphere[M].London: Routledge,2006.
[17] Koopmans,R.& P.Statham(eds.).TheMakingofaEuropeanPublicSphere:MediaDiscourseandPoliticalContention[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

[19] Habermas,J.Modernity - An incomplete project [A].Foster,H.PostmodernCulture[C].Port Townsend,WA: Bay Press,1983.
[20] Habermas,J.CommunicationandtheEvolutionofSociety[M].Boston,MA: Beacon Press,1979.
[21] Habermas,J.TheTheoryofCommunicativeAction[M].Cambridge: Polity Press,1984.
[22] Hawley,A.H.HumanEcology:ATheoryofCommunityStructure[M].New York: The Ronald Press Co,1950.
[23] Bookchin,M.TowardandEcologicalSociety[M].Montreal: Black Rose Books,1980.
[24] Steward,J.H.TheoryofCultureChange:TheMethodologyofMultilinearEvolution[M].Champaign,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72.
[25] Bateson,G.StepstoanEcologyofMind:CollectedEssaysinAnthropology,Psychiatry,Evolution,andEpistemology[M].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1972.
[26] Bateson,G.MindandNature:ANecessaryUnity[M].New York: E.P.Dutton,1979.
[27] Finke,P.Die?kologiedesWissens[M].Freiburg: Alber,2005.
[28] Haugen,E.TheEcologyofLanguage[M].Stanford,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
[29] Enninger,W.& L.M.Haynes(eds.).StudiesinLanguageEcology.(=Zeitschrift für Dialektologie und Linguistik,Beihefte,Heft 45) [C].Wiesbaden: Franz Steiner Verlag,1984.
[30] Mühlh?usler,P.LinguisticEcology:LanguageChangeandLinguisticImperialisminthePacificRim[M]. London: Routledge,1996.
[31] Mufwene,S.S.TheEcologyofLanguageEvolution[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
[32] Calvet,L.J.TowardsanEcologyofWorldLanguages[M]. Cambridge: Polity Press,2006.
[33] Bastardas-Boada,A.Sociolinguistics:TowardsaComplexEcologicalView[M].Berlin: Springer,2012.
[34] Schneider,K.P.& A.Barron(eds.).VariationalPragmatics:AFocusonRegionalVarietiesinPluricentricLanguages[M].Amsterdam: John Benjamins,2008.
[35] Auer,P.&J.E.Schmidt(eds).LanguageandSpace:AnInternationalHandbookofLinguisticVariation[M].Berlin: de Gruyter Mouton,2010.
[36] Winch,P.TheIdeaofaSocialScienceanditsRelationtoPhilosophy[M].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1958.
[37] ?stman,J.O.PragmaticsasImplicitness:AnAnalysisofQuestionParticlesinSolfSwedish,withImplicationsforthestudyofPassiveClausesandtheLanguageofPersuasion[M]. Ann Arbor: University Microfilms,1986.
[38] Chilton,P.AnalysingPoliticalDiscourse:TheoryandPractice[M].London: Routledge,2004.
[39] Scollon,R.AnalyzingPublicDiscourse:DiscourseAnalysisintheMakingofPublicPolicy[M].London: Routledge,2008.
[40] Wodak,R.&M.Meyer(eds.).MethodsofCriticalDiscourseAnalysis[M].London: Sage,2009.
[41] Verschueren,J.Predicaments of criticism [J].CritiqueofAnthropology,2001(21).
[42] Verschueren,J.UnderstandingPragmatics[M].London: Edward Arnold/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Now freely downloadable at.https://www.uantwerpen.be/en/rg/ipra/research/publications/books/),1999.
[43] Bergen,B.K.LouderthanWords:TheNewScienceofhowtheMindMakesMeaning[M].New York: Basic Books,2012.
[44] Verschueren,J.Context and structure in a theory of pragmatics [J].StudiesinPragmatics, 2008(10).
[45] Verschueren,J.& F.Brisard.Adaptability [A].?stman,J.& J.Verschueren.HandbookofPragmatics(8th annual installment) [C].Amsterdam: John Benjamins,2002.
[46] Vygotsky,L.S.MindinSociety:TheDevelopmentofHigherPsychologicalProcesses[M].Cambridge,MA: MIT Press,1978.
[47] Enfield,N.HumanSocialityattheHeartofLanguage[M].Nijmegen: Radboud Universiteit,2010.
[48] Levinson,S.C.PresumptiveMeanings[M].Cambridge,MA: The MIT Press,2000.
[49] Verschueren,J.Markers of implicit meaning: A pragmatic paradox? [J].ForeignLanguageEducationandResearch,2013(1).
[50] Doran,R.,Ward,G.,Larson,M.,McNabb,Y.,R.Baker.A novel experimental paradigm for distinguishing between what is said and what is implicated [J].Language,2012,88(1).
[51] European Convention [Z/OL].[texts of the Draft Treaty establishing a Constitution for Europe].http://european-convention.eu.int/EN/DraftTreaty/DraftTreaty2352.html?lang=EN(October 2013),2003.
[52] Ghervas,S.A propos des traductions du projet de Constitution européenne [M].Geneva,unpublished ms,2004.
[53] Ghervas,S.Les valeurs de l’Europe: entre l’idéal,le discours et la réalité [A].InRethinkingDemocracy,Kiev[C/OL].http://rethinkingdemocracy.org.ua/themes/Ghervas_fr.html,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