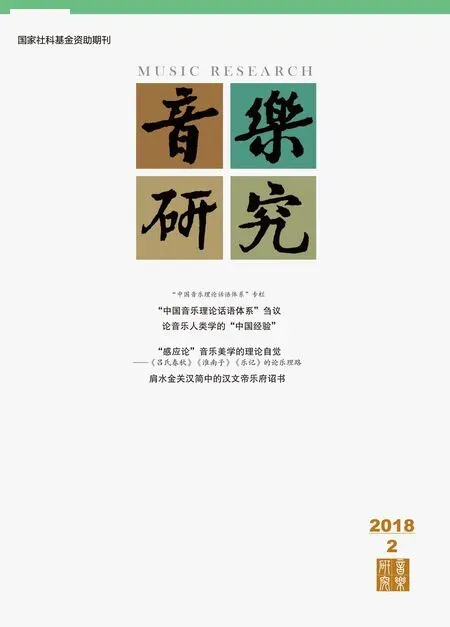傅能仁簡譜研究
文◎徐天祥
一、引 言
“傅能仁簡譜”(以下簡稱“傅譜”)是20世紀上半葉老傈僳文的創制者、英籍中華內地會宣教士傅能仁(James Outram Fraser)在通用簡譜基礎上創制的改良簡譜,學界亦有“富能仁簡譜”“傅氏簡譜”“傈僳簡譜”“傈僳族簡譜”“傈僳文記譜法”“傈僳文譜”“改良簡譜”“‘瓦祜木刮’記譜法”等寫法或稱謂。這種譜式最初為傈僳人使用,后傳播至瀾滄江—湄公河次區域的其他民族/支系,影響深遠。
從目前所見資料來看,楊民康最早對傅譜做過開拓性的研究,其對中國傈僳、拉祜和佤族等基督教音樂及贊美詩進行了系統調查,率先將傅譜介紹到學界。楊先生分析了傅譜的特點,如高低八度符號、節奏拉長、變音標記等,并指出傅譜節奏拉長可能沿用了中世紀格里高利圣詠的做法。①楊民康《云南怒江傈僳族地區的基督教音樂文化》,《中央音樂學院學報》1991年第4期;楊民康《云南少數民族基督教贊美詩的五線譜和簡譜記譜法研究》,《中國音樂》2006年第1期;楊民康《本土化與現代性:云南少數民族基督教儀式音樂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此后楊元吉等多位學者亦對其進行過探討②段玉明《中國寺廟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12頁;楊元吉《傈僳族基督教音樂》,載張興榮主編《中國少數民族宗教音樂研究(云南卷)》,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第276—289頁;趙蕾《從宗教信仰談滇西北少數民族的基督教音樂——對怒江流域貢山縣傈僳族的田野考察》,《民族音樂》2010年第5期;李娜娜《20世紀瀘水傈僳族基督教音樂舞蹈及其功能變遷研究》,云南大學2013年碩士論文,第39頁;石瑩《怒江瀘水六庫鎮傈僳族基督教儀式音樂實地調查研究》,云南藝術學院2014年碩士論文,第9—10頁;孫晨薈《傈僳族與大花苗四聲部合唱音樂的比較研究》,《黃河之聲》2014年第21期;孫晨薈《谷中百合——傈僳族與大花苗基督教音樂文化研究》,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5年版,第183—192頁。,關注到了傅譜的傈僳唱名,推進了學界的相關研究。傅譜是一種在多個國家分布的譜式,對于該譜仍需進行大量的實地考察與細致的譜式分析,才能全面準確地把握其規律與來龍去脈。筆者于2014—2016年赴中國云南省與緬甸克欽邦進行了調查,搜集到中、緬、泰、印等國印制,涉及傈僳、日汪(獨龍)、載瓦、峨昌、怒蘇、拉祜、佤、緬等民族支系十余個教派的二十種傅譜贊美詩集。
1.傈僳文,單聲部。傅能仁編寫的這本《傈僳語言手冊》包含了15首贊美詩,是歷史上所有傈僳文詩集的雛形。
2.傈僳文,四聲部。這是第一部獨立出版的傈僳文贊美詩集,曾是傈僳內地會的核心詩集,共收錄233首贊美詩,由傅能仁在中國編輯,1930年前在印度印制。③信息報告人為克欽邦傈僳基督教會負責人大衛·費仕(David Fish)。
3.傈僳文,四聲部。與前著重名,為緬甸神召會編印的傈僳核心詩集,共收錄230首贊美詩。
4.傈僳文,四聲部。與前著重名,為中國怒江州基督教兩會編印的詩集,共收錄270首贊美詩。
5.傈僳文,四聲部。與前著重名,為緬甸2006年印制的詩集,共收錄106首贊美詩。
6.傈僳文,四聲部。這是目前各國傈僳人通用、影響最大的詩集,共收錄319首贊美詩(以下簡稱《319首詩集》),20世紀上半葉由內地會的楊思惠(Allyn B.Cooke)、摩西和尤比編輯。④據大衛·費仕所述,全書第140首由摩西作詞,楊思惠譜曲;第290首由尤比作詞,楊思惠譜曲;其他作品譯自西方贊美詩。怒江州有會眾認為前290首由楊思惠等編輯,后29首為20世紀80年代增補,但大衛·費仕認為楊思惠等當時即編成了319首。他們在內地會成立150周年出版的紀念本中,特意將增加的25首新編詩歌附在后面,以保留前319首的歷史完整性。
7.;Bl..LE M JU- BILI PAI CI.M DU》,傈僳文,四聲部。這是2015年克欽邦傈僳基督教會為慶祝內地會成立150周年出版的《319首詩集》紀念本,其在319首后面增補了25首新詩,共344首。
8.《DO MU MU GW》,傈僳文,四聲部。這是緬甸傈僳浸信會的核心詩集, 2012年印制的第5版收錄474首贊美詩。
9.傈僳文,四聲部。這是1995年由David L.M.編、在泰國印制的詩集,共收錄665首贊美詩。
10.傈僳文,四聲部。該詩集2001年在泰國編印,共收錄133首贊美詩。
11.《DO MU, DO MU GW》,傈僳文、緬文,四聲部。這是緬甸神召會密支那妙梯支(Myotitkyi)學校使用的詩集,共收錄183首雙語贊美詩。
12.赤恒底農民合唱團樂譜,傈僳文、漢文,四聲部。這是云南怒江州赤恒底村農民合唱團使用的樂譜,未匯編成冊,但分篇樂譜保存在村民手中,常用曲目有《友誼地久天長》《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愛我中華》等。
13.《Shvring Zaywa》,日汪文,四聲部。這是緬甸基督會最新的日汪文核心詩集,共收錄490首贊美詩。
14.日汪文,四聲部。這是緬甸神召會最新的日汪文核心詩集,2011年第3版共收錄304首贊美詩。
15.《Gvmeu Kvseq Mvkon》,獨龍文,四聲部。這是云南怒江州貢山縣獨龍族使用的核心詩集,共收錄214首贊美詩。
16.《Zoppaip Chungh Thwe》,峨昌文,四聲部。這是緬甸峨昌人各派信徒共用的核心詩集,共收錄463首贊美詩。
17.緬甸怒蘇詩本,四聲部。這是緬甸怒蘇人正在編纂翻譯的詩本。
18.拉祜文,四聲部。這是中國拉祜族使用的核心詩集,共收錄585首贊美詩。
19.《Lai Ra Praok》,佤文,四聲部。這是中國佤族使用的核心詩集,此前版本收錄了253首贊美詩。⑤參見楊民康《本土化與現代性:云南少數民族基督教儀式音樂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第151頁;歐陽園香《佤族基督教音樂》,載張興榮主編《中國少數民族宗教音樂研究(云南卷)》,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第318—331頁。
傅譜的符號體系頗為豐富,以往研究未涉及全部符號。筆者的研究思路為:首先采用已有解釋方式,可以大致閱讀上述傅譜,但在節奏時值規律等方面存在疑問。其次,就相關問題請教當地會眾及教會的音樂教師,他們解答了部分問題,但對于某些不常用的符號則語焉不詳。再次,在前二者基礎上逐一瀏覽/分析二十部詩集中的每首樂曲,將所有疑問及符號標出。這些傅譜贊美詩多數譯自西方五線譜/簡譜,經與五線譜/簡譜原詩對照,即可發現傅譜如何在原譜基礎上記寫變化,幾乎所有符號的涵義也自然水落石出。
本文的主要發現在于:其一,總結出傅譜節奏拉長規律的解讀方法,認為它并未將時值全部拉長一倍,也未取消十六分音符。其二,全面闡述傅譜的記譜法則與符號體系。其三,結合田野調查,探討傅譜的創制者、產生時間、設計原理、分布與變化、對音樂實踐的影響等議題。以下分別進行論述。
二、創制者與產生時間
(一)關于創制者
關于傅譜的創制者,有兩說:一說為傅能仁。例如傅能仁的女兒艾琳·克蕾斯曼曾認為“富能仁自己發明了一種簡易識譜法。”⑥〔英〕艾琳·克蕾斯曼著,阿信、阿萍譯《山雨:富能仁傳》,團結出版社2014年版,第170頁。

圖1 傅能仁
另一說為內地會宣教士楊思惠。克蕾斯曼指出:楊思惠“把西方很和諧的四部合唱圣詩翻譯成傈僳語詞譜,并把五線譜創造性地改寫成傈僳簡譜。”⑦同注⑥,第243頁。中國傈僳學者史富相認為,楊思惠“把西歐國家很和諧的四部合唱歌曲翻譯成傈僳文詞譜,并把五線譜創造性地改寫成傈僳簡譜,這個譜子的節拍縱線,完全與漢文簡譜相同,但音符節奏的快慢,聲音的強弱以及休止符的表示,完全和漢文簡譜不同”⑧史富相《傅能仁、巴東和楊思慧夫婦》,載《史富相文集》,怒新出(2006)準印字16號,第197頁(內部資料)。。楊元吉也認為,楊思惠“在音樂方面很有造詣,他把圣經的四聲部歌曲《贊美詩》……翻譯成傈僳文詞和很特殊的曲譜,這個曲譜與現在通用的記譜法不一樣,但演唱效果完全與簡譜相同,目前這種記譜法還沒有一個準確的名字,傈僳語把用這種記譜法演唱的贊美詩叫‘瓦祜木刮’(War Ku Mo Gw)”。⑨楊元吉《傈僳族基督教音樂》,載張興榮主編《中國少數民族宗教音樂研究(云南卷)》,第276—289頁。
筆者在田野中尋訪到的兩則材料,認為該譜由傅能仁創制。
其一,為克欽邦傈僳基督教會總部的說法。傅能仁、楊思惠為原中國內地會云南傈僳地區的主要負責人;傈僳內地會遷入緬甸后,更名為傈僳基督教會(LCC)⑩LCC目前有兩個,一個為緬甸撣邦臘戍的緬甸傈僳基督教會(Lisu Christian Church of Myanmar);另一個為緬甸克欽邦密支那的克欽邦傈僳基督教會(Kachin State Lisu Christian Church)。,其總部位于緬甸克欽邦密支那的雷貢,并設有傅能仁紀念館。筆者數次在傅能仁紀念館采訪LCC負責人大衛·費仕(David Fish)?據筆者2016年1月對大衛·費仕的采訪。,據其所述,傅能仁創制了改良簡譜,楊思惠等用這種改良簡譜編譯了通用的《319首詩集》。筆者反復詢問是否楊思惠創制了改良簡譜,老人明確表明,改良簡譜的創制者就是傅能仁,LCC已正式將這種樂譜與傅能仁的名字聯系起來,他為我親筆寫下了名稱“A-YI-S XY T M MU”(圖2)。A-YI-S(阿益三)在傈僳語中指“三哥”,為傈僳人對傅能仁的尊稱(傅能仁在家中排行第三);XY T M為“創造的”;為“樂譜”,三詞合起來為“傅能仁創制的樂譜”之意。

圖2 傅譜的傈僳名稱
LCC總部紀念碑上,用傈僳文、英文兩種文字刻著為傈僳教會、文化和教育做出突出貢獻的人物介紹。其中,楊思惠條目說到他“和克雷恩將贊美詩翻譯為傈僳文”,傅能仁的條目則明確說明傅“是第一位傈僳傳教士,他發明了花傈僳文。1915年,巴托與侯麥協助他一起創制了傈僳文。傅能仁還創制了傈僳簡譜” 。?英文原文為:“Dr.James Outram Fraser(26.8.1886-25.9.1938)is the first Lisu missionary and the founder of flower Lisu writing. Thra Ba Thaw and HO-ME assistant coworker in founding the Lisu writing in 1915. He also designed a written musical notation in Lisu.”
其二,為前述傈僳詩集的說法,其前言對傈僳簡譜的由來做了介紹:“傅能仁對音樂很有興趣,……傈僳族是愛唱歌的民族,所以他創制了易學易懂的(123)記譜法。……他創制的這種記譜法,迄今為止其他民族也在學用。因為經過使用之后發現,它特別適宜于人聲合唱,可以演唱三四個聲部,使用方便,易學、易寫、易打譜。……五線譜的優點是適于樂器奏,而(123)簡譜則易于演唱。”?該段傈僳文由中國云南怒江州六庫的余永光與福貢縣老姆登村的蘭寶為筆者翻譯。此外,西人德愛莫(Bernard R. DeRemer)也認為傅能仁發明過一種樂譜。?原文為“He also designed a written musical notation for transcribing the Lisu's oral history songs.”參見Bernard R. DeRemer. “James O. Fraser: Pioneer to the Lisu”,網址http://www.disciplemagazine.com/www/articles/180.897.
(二)產生時間
傅譜的產生時間未見史冊記載。據筆者了解,其最遲1922年已與首部老傈僳文著作同時公開出版。
傅能仁1886年生于英國,1908年來到中國,后被內地會派往云南,接觸傈僳人后嘗試創制傈僳文字。1922年7月15日,他在緬甸仰光出版了傈僳文書籍《M I MI?另有一說為1919年出版,克倫人巴托寫作。但筆者所見LCC重印本,封面標明原版作者傅能仁,時間為1922年7月15日。這部小書后半部分收錄了15首用傅譜記錄的贊美詩。?史富相在《傅能仁、巴東和楊思慧夫婦》(《史富相文集》,第183頁)中提到,“巴東翻譯的五十首歌曲也選登了部分歌曲”,或為這些歌曲。它是最早出版的老傈僳文書籍,因此傅譜的產生時間,最遲應不晚于1922年。從譜例1可以看出,傅譜在該著中已具備基本樣態,只是符號體系沒有后來豐富而已。傈僳人以四部合唱聞名,但最早的這本傈僳文贊美詩只記錄高聲部。此后傈僳人出版了多部詩集,在這些詩本中傅譜漸趨完善。
譜例1

三、傅譜的記譜法則與符號體系
傅譜以通用簡譜為基礎,對音高與唱名、時值與節拍等進行了本土化改造。下以《319首詩集》為例,對其記譜法則與符號體系進行闡述。
(一)音高與唱名
音高上,傅譜與通用簡譜一樣均采用首調記譜,以阿拉伯數字1 2 3 4 5 6 7代表七個基本音級,但進行了兩點改良。
一是高低八度符號不在數字上下方加點,而是高八度在數字右上標記逗號“’”,低八度在數字右下標記逗號“,”。例如簡譜中的“”記為“’”,“”記為“,”。傅譜專為演唱贊美詩(四部合唱)設計,贊美詩音域基本在三個八度內(c-b2),因而不存在升高降低兩個八度的情況。其將高低八度的點改為逗號后,視覺上更加清晰明了:①逗號比點明顯。②逗號位置與數字略微錯開,看起來更清楚。③傈僳文有“.”的符號,傅譜的附點也用“.”,音高上改用逗號可以避免三種“.”相互混淆。
二是以五個傈僳文元音字母A、E、O、代表五個變化音級:在通用簡譜中代表空拍,在傅譜中代表#4/b5音級。從應用效果看,傈僳文字母代表變化音級,增加了傈僳人對簡譜的親近感。在通用簡譜與五線譜中,某變化音級是升還是降(例如#4/b5)需根據前后音符關系確定,傅譜則不作區分,這也降低了民眾掌握變化音級的難度。

圖3 傅譜的音級排列
唱名上,傅譜不用do re mi fa sol la ti(si),而改用傈僳語數字的讀音為唱名。傈僳文的寫法及讀音(國際音標)為:

圖4 傈僳數字(唱名)寫法與讀音
五個變化音級的唱名也與傈僳字母發音一致:A[a]、 E[e]、 O[o]、 U[u]、[?]。對于傈僳人來說,傅譜意味著不用學習陌生的西洋唱名,只需將本民族語言中的數字讀音用音高唱出即可,民眾更易接受。客觀上看,唱名需要單音節讀音,傈僳語以單音節為主,符合這一要求;主觀上講,單音節語言很多,例如漢語也以單音節為主,但并未使用數字讀音作為簡譜唱名,也未借用傳統“上尺工凡六五一”或“宮商角徵羽”的讀音,而是原樣學用外來唱名,未像傅譜那樣進行本土化的調整。
(二)時值與節拍
時值上,傅譜對通用簡譜的記法進行了重大改變,將音符時值做了拉長。例如,將通用簡譜中的記為等。?傅譜無“X”的標記,因而本文暫以“1”代表“X”。有文章曾對比過二者的時值記法。

圖5 ?楊元吉《傈僳族基督教音樂》,載張興榮主編《中國少數民族宗教音樂研究(云南卷)》,第276—289頁。
這一示例大致接近傅譜的實際用法,不過:1.“”代表四個四分音符,而非一個全音符,全音符應記為“”;同理,二分音符應記為“”。2.十六分音符并未被取消(見下文詳述)。緬甸日汪人2013年版的緬文贊美詩集,即標明了傅譜全音符、二分音符、四分音符、八分音符、十六分音符的寫法及與五線譜的對應情況(圖6)。

圖6
為全面說明傅譜的時值變化,本文將通用簡譜與傅譜的時值對應如下:

類別音符時值通用簡譜記法傅譜記法傅譜說明全音符1二分音符1基本音符數字代表音高,一個中橫杠代表一個四分音符時長。1四分音符長橫杠與中橫杠含義一致。八分音符(單下劃線)或無附加節奏信息的數字或短橫杠,代表八分音符。十六分音符(雙下劃線) ' 右上斜線(不是逗號)代表十六分音符。附點二分音符附點音符數字代表音高,一個中橫杠代表一個四分音符時長。附點四分音符11..或附點八分音符.或.雙附點四分音符1...此處的短橫杠等同于附點;傅譜與通用簡譜附點用法相似,為前面時長的一半。
(續表)

表1 通用簡譜與傅譜的時值對應
傅譜時值記法需要注意的地方有:1.橫杠共有短、中、長三種,短橫杠“”代表八分音符或附點;中橫杠“”代表四分音符;長橫杠“”與中橫杠含義相同,只是當對應的其他聲部音符較多時,本聲部需要將中橫杠拉為長橫杠以保持清晰。2.附點可以打破音值組合的整拍原則,如通用簡譜、的兩拍半不能以附點、而必須用兩拍 + 半拍連線的形式表示,傅譜卻可以直接記為附點3.整小節長音可以打破音值組合的整拍原則,如整小節的長音不必體現為3+3相連可直接用2 + 2 + 2的形式“”。4.對完全小節的要求不嚴格,可以在小節中甚至半拍、附點處斷行。
傅譜拍號均以斜線分隔左右書寫(例如標為2/4),其節拍總體上分為三類:二分拍(、等)、四分拍(、、、、等)與八分拍(、等),其時值換算原理與通用簡譜相仿。如傅譜的四分音符()在二分拍中代表半拍,在四分拍中代表一拍,在八分拍中代表兩拍。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四分拍最多見,人們口語中常把單個四分音符稱為“一拍”,前人研究傅譜的成果也多沿用此種習慣,論文中提到的幾“拍”即指幾個通用簡譜的四分音符。

表2 傅譜的分拍對應
與通用簡譜比,傅譜節拍信息比較豐富。如譜例1左上角除寫明節拍外,新增了起唱節拍的序次,如代表,第3拍起唱。若寫為則代表從第2拍的后半拍起唱。右上角以傈僳文加括號形式,標明樂曲節拍及起唱位置。NYI為數字2(二拍子),S為數字3的首個字母(三拍子),LI為數字4(四拍子),為數字6(六拍子);為前面的意思,dY 為中,為后:

表3 傈僳文起拍表
通過該表可以看出:第一,傈僳文標記突出每小節含幾拍(分子),而不強調幾分音符為一拍(分母)。、均用NYI表示,、均用表示。第二,9在傈僳文中應寫作“KU.”,但該譜以代表3的“S”標示,說明創制者將9拍子作為3大拍(三個3拍)看待。傅譜將第7拍起的也用后拍而非中拍Y表示,原理相同。第三,Y意為中間起拍,至于從第幾拍起則比較靈活。若從后半拍起唱,不用在樂譜前標出半拍休止符。
關于傅譜的時值,筆者的主要發現為:
其一,傅譜并未將通用簡譜的時值全部拉長一倍。
一般認為,傅譜將時值整體拉長一倍。筆者起初也帶著這一觀念進入田野,但在閱讀多數曲目時存在問題。例如譜例2為采用《友誼地久天長》曲調的第79首贊美詩《圣靈,幸福的使者》?《友誼地久天長》是一首西方曲調,常用于各民族贊美詩中。傈僳人至少有兩個歌詞版本:其一為傈僳部分節奏比對,原曲為。第一行為通用簡譜記法,第二行為時值整體拉長一倍的樣式,第三行為《319首詩集》中傅譜的實際寫法。第一、二、三小節的時值均拉長了一倍,但第四小節卻未拉長一倍,這是何故?
譜例2

筆者在研究中發現,傅譜時值實際上存在三種變化情況:
一是整首樂曲的時值均拉長一倍,這在八分拍中較為常見。例如,譜例3《平安夜》原為,時值拉長一倍后,用通用簡譜觀念審視接近。
譜例3

二是整首樂曲的時值均未拉長一倍,這在二分拍中較為多見,長音符較多的四分拍也有此種用法。例如,譜例4原為,若整體拉長一倍后應為通用簡譜的。而該譜第1、3、5小節為通用簡譜的十拍,第2小節為十一拍,第4小節為九拍。全曲時值拉長呈現為三種拍數,但均沒有拉長一倍者。贊美詩中的《圣靈,幸福的使者》,英文名為Holy Spirit,Bringer of Happiness,這是一首贊頌圣靈的教會歌曲。其二為近年隨著紅歌、旅游、展演等活動出現的用傈僳語演唱《友誼地久天長》民歌原詞。傈僳人主要演唱前者(對內),后者多在官方組織的展演等活動中使用(對外)。中國的拉祜族、獨龍族教會,以及緬甸的峨昌浸信會、浪峨浸信會、浪峨神召會、日汪浸信會、日汪神召會、日汪基督會等詩本中均有這首贊美詩,只是譯為不同文字,使用不同譜式。景頗人對這首贊美詩曲調進行了重新填詞,改名為《全體景頗同胞》。使用該曲調的漢文贊美詩有基督教的《圣潔入天》《天父,我向你舉起手》、天主教的《再會吧弟兄姊妹》等。
譜例4

三是樂曲中有的小節時值拉長一倍,有的小節未拉長一倍,這在四分拍中較為多見。譜例2即為如此;譜例8原為,時值若整體拉長一倍后,用通用簡譜觀念審視應接近,而該譜第1、2、3、5、6、7小節為通用簡譜的六拍,第4、8、9、10、11小節為五拍,并未將所有時值拉長一倍。
以上情況是否為特例?筆者進行了核查:(1)通讀中國傈僳族的《319首詩集》。(2)通讀緬甸傈僳人使用的《319首詩集》。(3)查閱尋訪到的十余種傈僳詩集。(4)查閱日汪(獨龍)、載瓦、峨昌、拉祜、佤、緬等民族/支系的傅譜詩集。(5)查閱筆者搜集的部分采用傅譜節奏的字母譜詩集(上述二十部傅譜詩集之外),發現它們全部貫穿這一原則。這表明傅譜未將通用簡譜時值全部拉長一倍,不是流傳中發生的變異,而是該譜式的基本特點。
那么,傅譜時值拉長的規律是什么?筆者認為應是以四分音符(含附點四分音符)為中心,根據音符時值的長短作變化。
凡短于(等于)四分音符者,時值拉長一倍。例如,四分音符通用簡譜記為“1”,傅譜記為“”;八分音符通用簡譜記為傅譜記為“”。附點四分音符、雙附點四分音符、附點八分音符等,時值均拉長一倍。傅譜十六分音符記法較為特殊,屬于另創符號,不過其右上角短斜線是單線而非雙線,與通用簡譜八分音符的下劃線同為單數,因而大體上也可視為拉長一倍。
凡長于(等于)四分音符者,時值未拉長一倍,其音高數字無時值含義,后面幾個中橫杠“”代表幾個四分音符時值。其關鍵有兩點:一是通用簡譜數字本身代表一個四分音符的時值,而傅譜長音符的數字不具有任何節奏含義。二是“”符號在傅譜和通用簡譜中相同,均代表一個四分音符(四分拍的一拍),并未拉長。以四分拍為例,二者組合后,“”代表唱名為(do)的一拍,“”代表兩拍,“”代表三拍,“”代表四拍。
轉換的中介是四分音符,它既可視為原有時值拉長一倍,也能用音高與節奏分離的模式作解釋。仍以四分拍為例,其規律可呈現為下圖:

圖7 傅譜時值拉長規律
這一變化原則,可以在所有傅譜樂曲中得到驗證。
其二,傅譜最小的時值單位不是四分音符,也未取消十六分音符。
多數學者認為傅譜時值拉長后,最小的單位是四分音符,取消了十六分音符。實際上,探討傅譜時值的一個前提,是應明確所指為何種意義上的“四分音符”。從客觀事實看,傅譜與通用簡譜一樣,仍由四分音符、八分音符等構成,只是用后者二分音符、四分音符的寫法標記而已。一個最直接的證據是,傅譜時值雖拉長,節拍并未改變,仍為2/4,仍為3/4,并非變 4/4 或 2/2,變6/4或3/2。因此,“”應被視為傅譜的四分音符而非二分音符,“”應被視為傅譜的八分 音符而非四分音符。從主觀用法看,前人使用“四分音符”等概念時,有的指傅譜的四分音符();有的指通用簡譜的四分音符();有的提到的傅譜“四分音符”,甚至是通用簡譜四分音符的表層寫法()、傅譜八分音符的實際時值。因此,傅譜中雖未見通用簡譜的八分音符寫法(),但八分音符在傅譜中大量存在()。
傅譜也并未取消十六分音符,只是改變記譜方式而已。其記法不是通用簡譜的雙下劃線(),而是在音符右上角標短斜線“′”(例如譜例3的第2個音)。該符號與高八度的右上逗號“’”容易混淆,不過一個是短斜線,一個是逗號,寫法不同。如遇到高八度的十六分音符時,則音高記號在前、時值記號在后,即“’′”的組合方式。實際上,贊美詩常用八分附點 + 十六分音符的節奏型,即便拉長一倍后,最短的通用簡譜時值寫法也應不止于四分音符。筆者在傅譜詩集中未見過三十二分音符,這與贊美詩的音樂特點有關,其一般不采用帶有三十二分音符的節奏型。
(三)輔助符號
除音高、時值的特殊標記外,傅譜的輔助符號非常豐富,主要有:
1.樂譜以四聲部為一行,左側用大括號括出,行與行之間以長實線分隔,視覺效果更清晰,不易串行。
2.與五線譜曲譜在上、歌詞在下的安排不同,傅譜是女高、女低聲部在上,歌詞居中,男高、男低聲部在下。若歌詞節數太多,樂譜只保留若干段歌詞,剩余歌詞附于樂譜后。
3.若各聲部歌詞不同,歌詞差異較小時,二者歌詞仍標于中間(例如第39首贊美詩);歌詞差異較大時,女高、女低與男高、男低下方各帶一行歌詞(例如第64首贊美詩的第二個版本)。若四聲部歌詞均不同,則用虛線分開(例如第193首贊美詩),代表一聲部(女高),代表二聲部(女低),代表三聲部(男高),代表四聲部(男低)。
4.長虛線的另一種用法是分隔臨時聲部,新增臨時聲部時,用虛線將原有四聲部隔開。
5.每節歌詞前以序號(1)(2)(3)(4)等標注段落,副歌以大括號相括并標以豎排斜體的傈僳文“DU- TI- LE=”。據當地人說,該詞在傈僳語中是“來來回回”之意,以此代表副歌。
6.與一般簡譜不同,傅譜每兩個聲部共用一個小節線,結束時四聲部共用一個終止雙豎線。反復記號以單豎線加點的形式()標記;該符號若位于某小節中間,表示從此處反復,并不代表小節線;反復記號若位于終止位置,則與雙豎線分開同時標記
7.“一房子、二房子”反復記號,《319首詩集》用帶圈數字標出,并以高于小節線的長豎線標明起止位置(如)。該長豎線不是小節線,不具有劃分小節的意義。有的傅譜詩本則大致保留了通用簡譜“一房子、二房子”的原有記法。
8. 延長記號標在時值記號后面(如),而非數字上方。
四、傅譜的設計原理與關系探討
(一)設計原理
傅譜的設計原理是什么?這一點可以從傅能仁改良簡譜的動因探尋答案。傅能仁音樂素養較高,早年曾在英國開過鋼琴獨奏會。不過他首先是位傳教士,不遠萬里從英倫三島來至傈僳人中,做的所有工作都圍繞傳教這一目的展開。因需要讓傈僳人讀圣經,所以創制了傈僳文;因需要讓傈僳民眾盡快學會贊美詩,所以創制了改良簡譜,這些是傅譜產生的根本原因。以贊美詩為代表的西方音樂與傈僳傳統音樂屬于兩個不同的體系,傅能仁推廣西方簡譜所面臨的困難主要有兩點:一是該譜對普通傈僳民眾來說較難;二是通用簡譜采用西方的符號體系,缺少傈僳文化信息。為解決這兩個問題,傅譜的改良秉承了兩項原則:
其一,簡單易學、靈活變通。從邏輯上說,傅能仁完全可以教傈僳人通用簡譜,之所以改良簡譜,就是要讓這種樂譜比通用簡譜更簡單,使普通民眾一學就會。從簡單易學的原則出發,傅譜進行了“改”和“增”:一是改變通用簡譜的符號,能變簡單的就變簡單,能省略的就省略。高低八度的上下點不夠清晰,就改為在右上、右下加逗號;變化音級太復雜,就將升降號合并,不再區分升降;音值組合的整拍原則不必遵守;不完整小節可以斷行。二是增加若干新符號。四聲部用括號括出,行與行之間以長實線分隔,每節歌詞前以序號標注,副歌前提示“DU- TI- LE=”,節拍號后增加起拍數字,這些措施都是為了讓樂譜更清晰明了,方便會眾掌握。
傅譜的時值設計更是秉承了簡單易學、靈活變通的原則,為此不惜將兩種看似矛盾的方案同時安排于時值拉長的過程中:短音符拉長一倍是為了減少通用簡譜中細碎的時值記號,使短音符更易辨認;長音符未拉長一倍是二分音符、全音符若拉長一倍,時值符號過于繁瑣,而幾個“”代表幾拍(幾個四分音符)則容易很多。這樣的設計安排實際上具有一定合理性,筆者童年初學通用簡譜時即感到奇怪:既然數字代表音高,“”代表節奏,為何“”沒有橫杠,卻仍被視為一拍(一個四分音符)?為何不能按照音高、節奏組合的邏輯,將“”作為一拍,“”作為兩拍?傅譜雖然單個數字(1)也代表八分音符時值,但長音符將數字時值內涵剔除,只用“”代表拍數,符合音高、時值分離組合的簡潔思維。
其二,親近傈僳文化。簡譜改良后仍是西方樂譜,只有增加傈僳語言文字信息,才能更易為傈僳人接受。傅譜棄西式唱名、改用傈僳數字讀音,棄西式升降號、改用傈僳字母與讀音代替,增加傈僳文的起拍標記等做法,拉近了傈僳人與西方樂譜之間的心理距離,使得該譜迅速為傈僳人掌握并接受。傅能仁借用傈僳數字讀音,主觀上雖是想讓傈僳人盡快接受贊美詩,客觀上卻促成了簡譜的全民普及。創制者不是居高臨下地推行西方音樂文化,而在一定程度上尊重了本民族的語言傳統,根據使用者特點進行了靈活調整。
改良簡譜與老傈僳文同為傅能仁創制,二者在簡單易學、靈活變通的原理上相通。老傈僳文最大的優點是簡潔,傅譜同樣體現了這一原則。傅能仁并非專業音樂家,其改良簡譜是為了方便傳教,而非站在音樂立場考慮問題。因此傅譜創制者受到的束縛小,只要能讓異文化的傈僳民眾接受,所有的規則都可以打破,重要的是讓“白丁”覺得簡單、易學。近代以來基督教向各地傳播的過程中,有的恪守西式樂譜原貌進行教習,有的則站在接受者的立場,對原有樂譜做改變。傅能仁的改良簡譜、柏格理的苗文譜、李提摩太夫婦的《小詩譜》、杜嘉德的階梯譜?參見宮宏宇《杜嘉德的樂理書系列與西洋樂理之東傳》,《音樂研究》2009年第1期,第24—38頁。、采用形狀符號的艾金記譜法等都是這方面的實例,這也顯示出創制者的良苦用心。
由此來看,傅譜是通用簡譜進入傈僳后本土化的結果。它是改良簡譜,但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本土化,屬于本土化類型的樂譜。
(二)關系探討
傅譜在通用簡譜的基礎上改良而成,其改良方式的創意源于何處未見明確記載。該譜產生之前其他樂譜的相似做法,可供我們參考。它們或許僅是原理相通,傅能仁主觀上未受之影響;也可能從中受到部分啟發。這里提供兩則事例:
其一,湯加譜。該譜是南太平洋島國湯加使用的樂譜,19世紀60年代由英國衛斯理公會的莫爾頓創制,約早傅譜半個世紀產生。?本文涉及湯加譜的資料源于劉穎《湯加記譜法研究》,載《音樂學中國新生代:中央音樂學院王森基金獲獎論文選2007—2011(本科組)》,中央音樂學院出版社2014年版,第471—510頁。湯加王國與傈僳人所在地相隔萬里,但兩種樂譜有相同之處:(1)二者同為改良簡譜。(2)湯加譜唱名不用do re mi fa sol la ti,而用湯加數字讀音(簡寫)to fani o tu va hi;變化音不用西式唱名,而用湯加數字讀音簡寫中省略的音節演唱(十二個音分別唱為:to lu fa ma ni o no tu fi va a hi)。(3)四部為一行,每行之間以長橫線分隔。(4)創制者莫爾頓與傅能仁同為英國人,同屬一個教派。譜例5為西方贊美詩O God, Our Help in Ages Past,后譯為湯加文、湯加譜;緬甸基督會日汪詩集的第94首(譜例6)為同首作品,采用傅譜、日汪文記錄。
譜例5

譜例6


其二,字母譜。字母譜是19世紀中葉英人約翰·柯文(John Curwen)與約翰·斯賓塞·柯文(John Spencer Curwen)在薩拉·安娜·葛洛薇(Sarah Anna Glover)發明樂譜基礎上創制的一種被稱為Tonic Solfa的首調記譜法。?參見牛津音樂在線(http://www.oxfordmusiconline.com)中的“Tonic Sol-fa”辭條,其資源源于格羅夫音樂在線(Grove Music Online)。柯文與傅能仁同為英國人,傅能仁所屬的中華內地會也曾推廣字母譜,因此傅譜的創制可能受到字母譜的啟發。例如,字母譜取消兩個八分音符節奏型的下劃線,用“.”將兩個四分音符分開,代表兩個八分音符時值,而傅譜的記法也為通用簡譜的兩個四分音符;字母譜的短橫杠“-”代表延長半拍,傅譜用“-”代表八分音符或附點;字母譜用右下逗號“,”代表十六分音符,傅譜用右上短斜線“′”表示等。一般認為,傅譜繼承了字母譜高低八度的符號標記,但據筆者在中緬兩國尋訪到的材料:(1)雖然當地部分字母譜與傅譜一樣高低八度以逗號表示,不過英人柯文的字母譜原著、《新格羅夫音樂與音樂家辭典》的“Tonic Sol-fa”辭條,以及波拉德苗文譜(變體字母譜)、中國內地一些早期的字母譜,均用小豎線“”而非逗號代表高低八度。(2)部分字母譜詩本未用常見的字母譜節奏符號,而是采用傅譜的節奏符號體系(例如,字母譜的譜例7與傅譜的譜例8、9、11、12的節奏相同)。因此,這些特點究竟是字母譜影響了傅譜,還是傅譜對字母譜也有反哺,尚待進一步研究。
譜例7 緬甸浪峨人的字母譜贊美詩

此外,李提摩太夫婦于1883年編印的《小詩譜》,用西方字母譜符號對中國傳統工尺譜進行了改良。其與傅譜相通之處為:用不同于基本音級譜字的本民族文字符號(大、夾、勾等?轉引自劉奇《李提摩太夫婦與〈小詩譜〉》,《音樂研究》1988年第1期,第22—27頁。)表示五個變化音級,不再區分變化音級的升降。
五、傅譜的分布與變化
傅譜最初為傈僳人使用,后流傳至周邊。僅筆者所見,即有日汪、載瓦、峨昌、怒蘇、拉祜、佤、緬等民族/支系使用,其在保持傅譜基本原則的前提下也有若干變化。
(一)傈僳
1.據大衛·費仕介紹,他的表兄弟、緬甸傈僳浸信會的臘吾(Dr.La Wu)認為,A、E、O、U、 的變音記法不妥,1989年對原方案進行了調整,將A改為 ,E改為。目前傈僳浸信會的傅譜詩集改用了這一標記。

圖8 傈僳浸信會詩集音階圖
2.近年,部分傈僳及其他民族支系的人士用字母Y代替與 相比,Y為各民族通用字母,傳播、打字更加方便。不過無論變音記號怎樣調整,對音樂的實際影響并不大。據筆者考察中緬傈僳、日汪、怒等民族的音樂活動,會眾的四部合唱較為出色,但較難掌握好變化音,比較常見的處理方式是將其修正到最近的基本音級(如直接將O[升fa]演唱為5[sol])。
3.前述詩集對贊美詩的記錄格式進行了豐富。其樂譜說明以《接近他》(Close To Thee)為例,歸納了18項信息。
譜例8


上例符號意為:該曲在本詩集中的編號。該曲在來源英文詩本中的編號。該曲與《319首詩集》詩歌的對應情況。應用場合或所屬分類。傈僳曲名。英文原名。調性。節拍與起拍。整拍標記,即幾分音符為一拍或一大拍,(-)代表四分拍,(- -)代表二分拍,(-.)代表八分拍。包含三個信息:第一個(3)代表每小節三拍,第二個(3)代表第三拍起唱,(1)代表正拍(非后半拍)起唱。傈僳文節拍與起拍信息。音域(高聲部的最高音與最低音)。反復時的起唱位置。反復時的結束位置。反復記號。對應的經文章節。原詞作者。原曲作者。這一方案匯集信息較多,但多數傈僳詩集未采用此種格式,《319首詩集》即無項信息。該著還將傅譜的附點八分音符記號改為“·′”,而“·”代表八分音符,“′”代表十六分音符,二者相加即為附點八分音符時值。
此外,部分傈僳詩集也有取消左側大括號,將分隔行與行的長實線改為長虛線,略去右上角的傈僳文起拍標記,或恢復“一房子、二房子”的橫括線者。這表明,部分人士在實踐中對傅譜的某些符號進行了調整和變化。
(二)日汪(獨龍)
日汪與景頗、載瓦、浪峨、勒期、傈僳同為緬甸克欽族支系。日汪包含瑪汪、則汪、當薩、丁塞四個分支,則汪與中國獨龍族同源。?據筆者2016年1月對緬甸日汪學會密支那分會負責人藏朋(Zame Hpung)的采訪。緬甸日汪基督會(譜例9)、日汪神召會及中國獨龍族詩集均有傅譜記錄的《接近他》。
譜例9

日汪(獨龍)教會多源于莫爾斯家族的滇藏基督教會。莫爾斯曾在日汪、傈僳人中傳教,日汪人與傈僳人相鄰而居,因而也采用了傈僳人的傅譜,其變音記號也為A、E、O、U、Y。日汪詩集的樂譜說明雖用字母譜唱名解釋傅譜的譜字(圖表12),但據筆者對緬甸密支那日汪教會的采訪,緬甸日汪人最初使用傈僳唱名,后來仿照傈僳唱名原理,將日汪語(瑪旺方言)數字讀音作為基本音級唱名:1= [thi55]:2= [?31?ji51];3= [?31?um51];4= [a31pji51];5= [phu?55?ua51];6= [a31?huq55];7= [???31??t31],顯示出傈僳本土化唱名對日汪人的啟發。由于日汪數字有雙音節詞匯,演唱起來并不方便,因此中老年日汪人仍多使用傈僳唱名。青年人受當代學校教育影響,開始學習“do、re、mi”的西式唱名。

圖9 緬甸日汪詩集的音階唱名圖
(三)載瓦
載瓦支在中國屬景頗族,在緬甸屬克欽族。20世紀30年代,西方宣教士威廉姆(Dr. Fezt william)曾用傈僳字母創制過載瓦文字。他用該文字編寫的《載瓦問答書》(ATSI MI TU MAU SAU)收錄了15首贊美詩,應為較早的載瓦贊美詩。根據LCC提供的《載瓦問答書》重印本,其所用樂譜為傅譜。
譜例10

(四)峨昌
緬甸峨昌人與中國片馬茶山人為同源族群,其并非獨立支系,而被劃入緬甸克欽族的勒期支。緬甸峨昌人的核心詩集采用傅譜,變音記號也用“Y”,使用字母譜唱名。在譜例11的《接近他》中,峨昌人將傅譜的附點八分音符記為“·”,而非“·′”。
譜例11

(五)怒蘇
緬甸怒蘇是克欽族中未獲得獨立支系身份的族群,與中國怒族的怒蘇支系同源。他們受傈僳影響較深,普遍使用傈僳文贊美詩。目前,緬甸怒蘇人創制了拼音文字,正在翻譯贊美詩。根據緬甸怒蘇學會為筆者提供的手稿,其翻譯的底本為傈僳《319首詩集》,因此未來的怒蘇文詩集同樣采用傅譜。
(六)拉祜
拉祜族也使用傅譜,其核心詩集同樣標A、E、O、U、Y的傈僳變音記號,樂譜說明用字母譜唱名解釋。該詩本也收錄有《接近他》(譜例12)。拉祜教會大多源于20世紀初美國傳入的浸信會,浸信會多使用五線譜譜本,為何拉祜族使用傅譜?據記載:(1)傅能仁、楊思惠曾在臨滄市耿馬縣一帶傳教,1937年楊思惠帶人去臨滄“糯福拉祜族浸禮會,一面主持教會工作,一面組織他們進行《圣經》傈僳文草稿的審閱、修改工作”。1951年,楊思惠“在泰國北部的某一個傈僳人和拉祜族居住的地方傳教”。?史富相《傅能仁、巴東和楊思慧夫婦》,載《史富相文集》,第196、200頁。(2)1924年內地會的Crance(Khaw Ma Pha)在緬甸撣邦拉祜人中傳教。?LCC提供數據,轉引自何林《民族的渴望:緬北“怒人”的族群重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90頁。拉祜族傅譜的傳入或與此相關。拉祜族核心詩集部分曲目標有與傈僳詩本的對應情況(來源),進一步證明傅譜由傈僳傳入。?中國拉祜文贊美詩共585首,前403首與緬甸日汪基督會的贊美詩(共490首)一致,只是譯為不同文字。二者究竟誰影響了誰,尚待進一步研究。
譜例12

(七)佤
佤與拉祜相鄰而居,二者均使用傅譜。1870年庫森(Josian H. Cushing)夫婦沿薩爾溫江(怒江)旅行至緬甸景棟時見過拉祜人和佤人?Burma Baptists Chronicle. Ranggoon: The University Press, 1963, p.208.;1901年,永偉里(W.M.Young)父子在中緬邊境先后為拉祜族、佤族傳教;1917年教會剛傳入佤族人口較為集中的滄源縣時,“就已有拉祜文的《圣經》和《贊美詩》了”;1931年,滄源縣首次打印出佤文的《圣經》和《贊美詩》。?歐陽園香《佤族基督教音樂》,載張興榮主編《中國少數民族宗教音樂研究(云南卷)》,第320—321頁。可見,佤族贊美詩應在拉祜贊美詩的影響下產生。
(八)緬
緬語為緬甸官方用語,因此緬語詩集的樂譜種類較多。緬甸日汪基督會因需要向克倫、撣、若開、欽、那伽等民族傳教,因而將原日汪文詩本譯為緬文,樂譜仍為傅譜,變音記號也為A、E、O、U、Y。在緬甸基督教會(BCC)2003年印制的緬文詩集中,傅譜變音記號直接在音符右上角標升降號“#與b”(譜例13),唱名也采用字母譜唱名。簡譜原本來自西方,經過傈僳等民族的改造成為本土化的傅譜;而現在本土化的傅譜反過來又受到西方五線譜、通用簡譜的二次影響,將某些符號吸收使用。這種現象在部分拉祜人中也存在,2016年8月云南省瀾滄縣那步村的《新米節獻詩集》?該譜本由中國音樂學院韓冰提供。即在傅譜中使用了西式升降號。
譜例13

六、傅譜對音樂實踐的影響
傅譜對傈僳等族群的音樂實踐產生了深刻影響。筆者在調查緬甸克欽族各支系音樂時發現一個有趣現象:緬甸克欽族會眾最多的支系是景頗和傈僳,傈僳會眾拿著傅譜的四聲部詩本,普遍能夠演唱四部合唱;而景頗詩班雖能唱四聲部,但普通會眾拿著五線譜的四部詩本,一般只唱高聲部,即便上萬人的集體唱詩也聽不出四部效果。這并非局部現象,中緬各地景頗、傈僳的情況均如此,當地其他民族也如此——使用傅譜的各民族/支系多數能唱四部合唱,使用五線譜的各民族/支系多數看著四聲部唱單聲部(如緬族、克倫族、克欽族浪峨支等)。那么,景頗、傈僳等為何有如此反差?是音樂天賦有別,還是后天因素使然?
應當說,傈僳四部合唱的普及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如審美喜好的不同,傈僳教會更重視音樂與合唱,投入時間更多,會眾唱詩有指揮帶領等,1974年梯詹福爾特(Herman G. Tegenfeldt)甚至認為:“音樂就被證明更能吸引傈僳人而非景頗人”。?Herman G. Tegenfeldt. A Century of Growth: The Kachin Baptist Church of Burma. Calif:The William Carey Library, 1974, p.283-284.不過筆者認為還有一個關鍵因素——使用不同樂譜導致的識譜率差異。西式四部贊美詩不同于東方民族的傳統多聲部民歌,其建立在大小調和聲功能基礎上,每個聲部有嚴格進行。會眾如果不識譜,或只認識一點而不熟練掌握的話,四部合唱是無法進行的。
景頗等使用的五線譜,對于初學者而言難度較大。五線譜由符頭、符桿、符尾組成,其外觀大體相同,僅根據位置的高低判斷音高。五線譜屬于固定調記譜法,音高隨譜號、調號變化而變化。贊美詩多數為帶調號的作品,三升(A大調)、四升(E大調)、四降(bA大調)、五降(bD大調)歌曲時常可見。普通會眾很難全部掌握,即便在高等專業音樂院校,這也是部分系部學生視唱練耳修畢才能達到的程度。筆者在田野中專門調查過景頗會眾的識譜率,受訪對象為中國德宏州隴川、盈江、瑞麗三縣市,緬甸密支那的基督教及部分天主教人員與音樂教師,結果為:緬甸大約只有5—10%的景頗人精通五線譜,10—30%的人可以看新譜視唱,多數人雖略識五線譜,但不能熟練掌握;中國景頗族的識譜比例較這一數據更低。五線譜的書寫需要專門的印刷紙,使用起來也不方便。因此各地景頗人學唱新歌(贊美詩)時,教歌者幾乎只發放歌詞,用“有詞、無譜、滾學、跟唱”的方式,一句句帶領民眾背誦演唱。由于只有歌詞,學唱的新歌絕大多數也為單聲部作品。實際上,西南一帶使用線譜的民族普遍識譜率不高。據筆者調查,云南怒江丙中洛的藏族天主教會仍在使用西方古老的四線譜,使用者看詩本演唱,但同樣不識譜。他們與景頗人一樣,絕大多數只能看譜本中的歌詞,聽記背唱。普通會眾掌握不好五線譜,也就不可能唱好合唱,這是景頗等會眾普遍手持四部贊美詩卻只唱單聲部的重要原因;景頗合唱詩班成員的音樂素養較高,基本都識五線譜,其排演合唱以識譜為前提。
傈僳等使用的傅譜,對于初學者而言簡單易懂。它采用首調記譜,不存在調號變化問題,降低了應用難度;樂譜數字容易辨認和書寫,也不需要專門的譜紙;數字和傈僳字母在生活中經常出現,使用者比較熟悉;傅譜進行了本土化的改造,更易為當地人接受;當前學校音樂課也教習通用簡譜,使得民眾對簡譜更加熟悉。因此,傈僳人認識傅譜的比例明顯比景頗人認識五線譜高。筆者曾在云南怒江州碧江、福貢、貢山三縣,緬甸密支那調查過傈僳會眾的識譜率,多數受訪者估計半數以上的傈僳人能看懂傅譜,有的給出數據的比例達70%以上。據筆者觀察,這一估計大致符合實際狀況。傈僳會眾學唱的新歌多為四聲部,即便手抄的臨時新編作品也如此,半數會眾拿到樂譜后可以直接視唱。傈僳人中也有不熟悉傅譜、跟隨大家一起背唱的會眾,但這一比例遠比景頗低。由于地域差別、對識譜的衡量標準不同,相關人士的估算數據有所差異,但使用傅譜人群的識譜率明顯高出許多是事實。緬甸傈僳浸信會曾將傅譜詩本改為國際上更“通行”的五線譜,但當地使用者普遍不接受,最后不得不重新改用傅譜詩集。五線譜與傅譜各有所長,但傅譜是一種特別適合四部贊美詩的樂譜。贊美詩節奏比較舒緩,較少出現過密的音符,音域一般在兩個八度內,很少做調性轉換,傅譜的拉長節奏、覆蓋三個八度內的音高標記、首調記譜等,正好對應了這一特點。而快速變化、轉換頻繁的器樂作品,則不太適合傅譜記錄,這也是為何傅譜主要用于四部贊美詩的原因。
當然,樂譜并非是決定會眾能否演唱四聲部的唯一因素。同樣使用簡譜,漢族會眾很少唱合唱;同樣使用五線譜,西方國家會眾演唱合唱的比例更高。但樂譜卻實實在在成為影響會眾是否使用四聲部的關鍵因素。多數人如果不識譜,尚可以在經年累月的齊唱中將旋律聲部記在心里,卻很難演唱旋律性不強、起和聲支持作用的中低音聲部。傅能仁起初創制改良簡譜,是為了使傈僳人盡快識譜,學會合唱。當傈僳人習慣使用傅譜后,這種樂譜在一定程度上又塑造了傈僳人的音樂樣態。它牢牢地將傈僳音樂與四部合唱聯系在一起,形成了幾乎全民而非詩班或音樂家才演唱四部合唱的現狀,強化了無伴奏合唱的體裁與傈僳人的多聲部和聲思維。傳統傈僳音樂以單聲部為主,而四部合唱的學習、傅譜的使用,使西方多聲部和聲思維融入了傈僳人的審美習慣中,當前傈僳人創作的包括流行音樂在內的多聲部作品明顯比其他民族/支系多。四部合唱建立在大小調功能體系上、頻繁使用下屬音(fa)和導音(si),使得傈僳人部分接受了西方的七聲音階與音樂思維,客觀上使得傈僳傳統音樂的五聲性思維有所弱化,出現了兩種音樂風格融合的作品,這些都值得研究者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