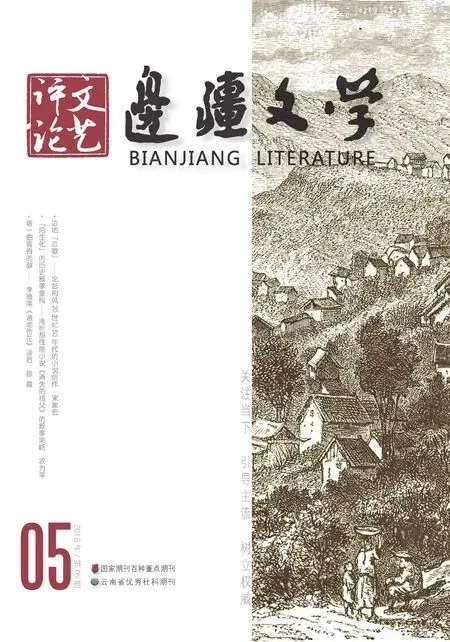現實困惑與期望喪失的非虛構表達
——讀呂翼長篇小說《寒門》
師立新
長篇小說《寒門》,是我的同族,作家呂翼先生的近作。
一座叫碓房村的村莊,馮家有馮維聰、馮天俊、馮天香、馮春雨,兩男兩女四個孩子;趙家有趙得位;萬家有萬勇。這群孩子在供奉著孔子牌位,奉行“唯有讀書高”傳統理念的村寨,被從小寄托了每個家庭的希望。然而,父輩迸盡力氣追求的愿望并沒有在下一代身上得到實現。小說以現實的殘酷把每位孩子的人生賦予了戲劇化,人性的復雜與命運的曲折,在一至四十二個章節中,次第打開。
全身心夢想通過高考跳離農村的馮維聰瘋了,從此永遠留在了村莊;馮天俊從少年考到中年,最終仍然夢斷清華北大,只考上省內師范大學;馮天香因家境緣故少年起無奈放棄學業,靠出賣身體換來后續的富足生活;最為順意的是馮春雨,真的通過高考離開農村并出了國,但她本來就不是碓房村的原住民,只是馮家收留的外來孩子;而趙家的趙得位成了小生意人,萬家的萬勇流落為飄游浪蕩的無業游民,打著考上復旦大學的虛無幌子,在外消耗著父親打工掙來的血汗錢。
這部小說描繪的寒涼人生,讓我心緒久久難平,以致讀完作品多時才斷續動筆評寫。
小說是生活場景與自然場景的提煉和加工,要彰顯和表達人物、情節和環境三大要素,它的架構要求必須嚴謹。好的小說,可以用虛構寫出非虛構的在場感,寫出人物所處歷史階段的核心物質,其更多的成分,是詮釋社會單元中個體生命里的自然生存和精神生活。如同詩人具有詩觀一樣,好的小說作家也有自己的小說觀。而且,我自以為,小說觀幾乎等于作家本人的價值觀和世界觀。它在小說的虛擬構建里,以所塑造的人物將作家的這些觀點表達或昭告讀者。呂翼,就是這樣一位具有小說觀的作家。
自幼聽過一句老話,是:付出就有回報。好像,這話在我長大成人的道路上也總被身邊的長輩引用,并對我加以教導。但呂翼先生卻沒有在《寒門》里給我這個圓滿,他毫無溫情撕碎現實面紗告訴我,生活就是活生生地存在著,卻沒有一定或者必須可言的規律能遵循。可以說,這部小說已不自覺地成為了一個時代的記錄和見證,這也是作者拷問生命及個體精神傳輸的層面升騰。它不可重復,也不受束縛,自然地還原了某一段時間的過痕。
于是,在《寒門》中,我從小說的歷史性、小說的情節設計、小說的鄉土語言,看到了現實困惑與期望喪失的非虛構表達。
《寒門》的開篇入題很好,以碓房村馮家四個孩子的一場嬉戲,一路鋪展開。進而,從少年講到中年,隨著他們年齡的增長,碓房村的歷史、人文,波瀾不驚的層層展現,人性的溫情或者貪婪轉換出不同的故事場景。英國戲劇理論家威廉·阿契爾認為:小說是漸變的藝術。而漸變,是一個過程的慢速運動。這個慢速中可以體現和容納的信息量由作家控制,因此,小說的歷史性有足夠的空間來拓張。
最近幾年,我陸續讀到了呂翼的幾部小說,有《風過楊樹莊》《村莊的喊叫》《疼痛的龍頭山》《土脈》等,這些作品的書寫,每一次的風格都在推陳出新力求不同,唯一不變的是,這些小說總體的在場都是鄉村。每個作家都會恪守自己的價值體系,小說是呂翼在文學世界里存在的方式 。他把生命賦予每一部作品的人物和故事,而鄉村是他和所有作品的原鄉,他將對生命的所感所想毫無保留地安置在這片大地上。呂翼在原鄉的曠野找尋每個人物與所處年代的背景契合度,這種表達,在行文中就水到渠成地構筑出小說的文學歷史性。
我國在1996年實行了大學的教育制度改革,不再對畢業大學生進行工作分配,且國家不再承擔大學生學費。從此結束了自1977年高考恢復后,近二十年的大學生包分配工作等制度。《寒門》橫跨這么一段不長的歷史,以平穩的虛構描寫把一撥人因高考傾注的個人和家庭乃至家族的付出推入讀者眼前,在歷史與現實交織的時間維度下,強調了文化的社會烙痕。小說中以馮天俊為代表人物的個人高考史,是一部鄉村底層民眾的精神追求史;擴大了說,也是一部基層某一面的眾生生存相,囊括了這個層面涉及到的與高考有關的眾多事與物,提供了其范圍內的生動細節和形象化的歷史材料。這種對歷史過程的展現,不同于文字概念里對歷史觀的解釋,但卻能極為客觀地反映出歷史觀里的社會存在。社會基本矛盾,本來就是歷史進程中社會發展的動力和最初源泉。在《寒門》里,我不妨將作家的這種充盈歷史性的敘事處理理解為他的創作技巧,他通過高考的歷史延續性,表述對當下許多農村家庭期望依靠高考來改變命運,及因讀書出現的返貧狀況而深陷的焦慮。另一個層面上,也凸顯出作家的社會責任意識。
胡塞爾曾在現象學的基本精神概括中言:回到事情本身。回到的方式是本質直觀,也就是直擊實事,說到底,事情的本身就是歷史性。這部小說極認真地告誡人們,歷史是用來尊重和如實記錄的,不容戲說。
《寒門》的情節設計我很欣賞。我相信,呂翼創作時真的具有了納博科夫式的靈感,這也是一部最貼近作家曾經生活場景的小說,他有完全來自鄉村的底層生活體驗,但情節描寫的語句沒有落入一般鄉村小說里就村莊風習及愚昧,進行批判或譏諷的老套設計。《寒門》跳離了喜劇與悲劇相交融的鄉村小說美學風格,沒有一味抑郁的抒情調子,這是作家本部小說在情節處理上的成功之處。
現實狀態與傳統經驗的割離,讓作家擔當責任的同時,心里也在產生茫然,本小說的情節設計從中體現了這份沒有答案的無助。明線上,全書是以馮維聰為主的故事,從躊躇滿志到考后發瘋再到專項潛能的異峰突起,最終得到來自清華大學相關研究方的賞識與認可;但書中另一條線,則是以馮天俊為輔的情節線,一個人十五次的高考路,以夢斷名牌大學做了收尾,轉而以教書育人的特長回饋碓房村。全書所派生出各章節舒枝散葉的開端、發展、高潮、結局,均附和著這兩條情節線的最終趨向。復線型結構的小說情節設計,能夠較詳細地敘述所構建的故事,人物形象從中得到豐滿的塑造和雕琢。這種不同于意識流小說板塊式結構的處理,讓我的閱讀得到了習慣性審美的流暢。
優秀小說的情節設計,有著共生的特點,那就是:波瀾起伏、跌宕婉轉和緊扣主題。《寒門》具備著這些特點,并且伏筆與照應,細節上的游離與依附等相互交融,讓作品里的人物和走向各具風采,情節設計的不斷變化,夯實了主題意義的升華。
本書將完結時,小說的情節設計是:“馮天俊在眾多記者圍追采訪時,心生煩躁,抓了抓零亂的頭發,悲傷地說:我這半生不算長,也不算短,可我和我們家遇上了兩大悲劇,一是教育,二是醫療……說著說著,淚露水就流下來。”本書主旨在此得到再次強化。事實如此,現當下廣大農村還面臨著教育和醫療兩大難題,《寒門》的故事情節設計把這兩大問題提出,而這些問題的社會意義及解決方式,我在全書的結尾處看到了積極向上的光亮。
《寒門》的作品主題是在故事人物產生之前就確定的,所以,它有自帶的社會疼痛,更有橫跨疼痛的各種努力。全書復線型結構的情節設計,使讀者清晰解讀出文字的更深層次內涵,那應是隨著時間流逝,正常的成年人能得到的最好收獲是逐步穩定的思想和感受,還有,必須直面現實的一切。
通讀《寒門》,發現作家在創作中加入了大量鄉土語言及鄉村民俗的白描。理論上,中國現代小說創作流派之一的鄉村小說,追溯到早期是以魯迅為核心發起的,其中鄉土語言的作用和意義,構成了這類小說恢宏的文化張力,內涵指向的是現代文化定位、文化漂泊和文化歸屬的范疇。這些理論觀點,貫穿了《寒門》全書文學深度寫作的要義。
好的小說就是一個好故事,好故事就必須有適合的語言來建筑組合。現代化進程的大環境下,以城市為主導的語言環境主宰了文字的話語導向,盡管鄉土語言是漢語表達的一部分,但并不能占據寫作主流。作家呂翼卻以自己的個體文學學養和鄉土文化素養,賦予了本部作品獨特的地域特質,全書四十二個章節中鄉土語言的運用,較好地描摹了各人物間的愛恨糾結,如同賈平凹先生在小說中使用他熟悉的秦腔一樣,呂翼先生使用的也是他本人生活的滇東北地區的鄉土方言。這樣的行文方式滿足了鄉土小說極貼地氣的處理要求,成為了本書較為出彩的又一亮點。語言的縝密,輕易就透入小說細節,貫通上下文的邏輯連接,積累出作品的真實感。《寒門》里,鄉土語言的添加將幾個家庭面對現實困惑與期望喪失的無奈,安靜而安然地加以敘述,作家剝去游歷的淺淡,直抵作品人物個性之外,眾生共性的在命運中的掙扎起伏,虛構的場景就表達出了非虛構的思索。
如:馮嬸說:“悖秋時了!悖秋時了!”“恥死了”“砍竹子遇到了節子”;萬禮智說:“手閑干瘡癢”;趙得貴說:“你沒有做高腳騾子生意吧”;馮天俊說:“你這樣的麻筋,煩不煩!”“萬禮智是小量蝦子無血”;馮天香說:“原來是爛桿水回來了”“二謊謊”;萬嬸罵:“花雞公!”等等,一群人各自使用的鄉土語言,飽含語言的鄉土自覺性,生動自然地將作品里各人物的性格特點揮灑而出,一輻幅鄉村生活的畫面,淋漓盡致地涂染在不同的時段和生活場景間 。
鄉土語言是鄉村小說中人物、動作的重要塑造手段,對故事的蔓延有著單純文字無法達及的高遠,可以提升作品的文學意象,讓小說的漸變藝術避免了枯燥和乏味。《寒門》的創作元素中,很好地掌控了鄉土語言的分量,并使之優勢最大化,暢達嵌入生活內里,不加任何評說就體現了其所具有的風土風俗意味。
對民俗,本書內也有眾多細致的描寫,如趙嬸給馮維聰叫魂作法的過程,馮嬸咒罵時邊唱邊砍木頭的全套動作。這些民俗單元的提取、加入,為鮮活人物的性格,起到的作用可謂四兩撥千斤。
文字是觸摸靈魂最便捷的途徑。在本書的字里行間,作家已安放了自己的文化根脈,無論世界怎樣變幻他依然固守生命的原鄉,明確自己的價值立場,在傳統文學認知方向上,形成了自己的文本風格。呂翼先生的文學態度,讓我心生敬佩和感動。
小說《芳華》里有言:一個始終不被善待的人,最能識得善良,也最能珍視善良。本部長篇小說沒有原諒、沒有和解,甚至,沒有很樂觀的結局,但善良的人們仍然在創造希望。
讀罷《寒門》時,引發了我長久的思考和疑慮,這應該算是我所讀過的呂翼先生作品中最為傷感的一部小說,也曾就此感覺向呂翼先生對文本的結局提出異議,可最終他的觀點說服了我。毋庸置疑,現實困惑與期望喪失是真實的,不可回避。盡管小說拋出的現實問題,難于在最短的時間得到解決及緩和,盡管作家從虛構中讓我看到了非虛構的病癥一樣的疼痛,但是,能大膽地把這些擺出來,何嘗不是一位作家的文學良心?
生活要繼續,小說或現實里的所有的人,還需要在向前行的過程中披荊斬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