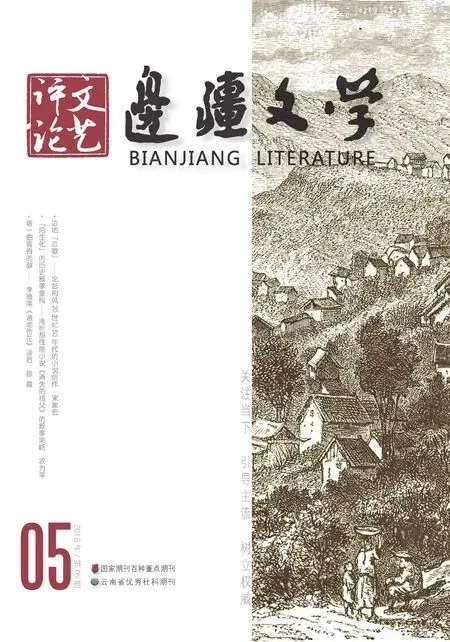神秘文化與邊疆歷史尋蹤的心靈追述
——讀西木長篇小說《金沙江之西》
王人天
去年,在昆明參加《邊疆文學文藝評論》筆會學習的時候,就聽楚雄女作家西木說她在創作一部關于畢摩的長篇小說,當時大家都對這個題材表示濃厚興趣,認為非常具有價值和意義。畢摩文化是彝族文化的代表。畢摩在彝族文化中扮演著傳承者和演習者的重要角色,可以說要研究和探討彝族文化是一個繞不開的主題。寫作畢摩小說具有相當高的難度,因為畢摩文化實在是太專業了,神秘空間很廣闊,令人真正動筆的時候卻又無所適從,因此全國以畢摩為題材的小說創作幾乎是空白。要創作這部小說,要了解的東西太多了,畢摩文化現在是非物質文化遺產,遺失嚴重,更何況一般作家是很難了解的,為此,她的創作令我吃驚。我說,畢摩題材非常有意思,但是畢摩很難了解全面,單靠抓得一鱗半爪是很難寫好的。沒曾想,時隔半年多,這部小說以《金沙江之西》為名發表在了《陜西文學》2017年6期上。我接到她寄來的專輯后,認真拜讀,受益頗多,在此淺談閱讀《金沙江之西》的感受和思考。
一、對人文歷史神秘性題材的選題與挑戰
創作小說,選題是成功的關鍵。題材老舊,一般不容易出新意,但是題材新,往往都面臨各種各樣的難度,需要作者雄厚的筆力駕馭和廣博的知識見聞。一部小說的涵蓋容量絕不是散文和詩歌可以比擬的。從寫作技法上說,小說包含了其他體裁的所有技法,無論是散文、詩歌、報告文學、論文等,都包含在里面,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面目呈現;從內容上說,既可以宏大敘事,也可以纖毫畢現從細微處著眼。曾有人說:“小說就是細細地說。”也就是說小說要展現細節,把每一個細節都活靈活現地描寫出來,帶著讀者去進入微妙的世界。但是,除了小小說、短篇小說等較短的小說外,中篇小說或長篇小說往往要承載一個更大的文化氛圍,一個時代或是一個環境下的文化,以這種文化氛圍成為小說生存的背景,作家敘寫的時候把人物和環境置身于文化氛圍下考慮,言行舉止、反映內容均需對應,由此,作家的選題就更加重要起來。
西木的《金沙江之西》從題材的選題上說是一個較新的選題,充滿魅力,令人叫好,但是這也是一個特難寫的選題。正如張慶國在《〈金沙江之西〉的寫作之難》中說的“這是一次寫作冒險”,她“狂妄地選擇了一個男性題材……還是一次寫作的開創性嘗試,西木所寫的畢摩,大大超出了男性題材范圍,涉及到了人類的鬼神文化”。也就是說西木所選的題材是建立在神秘文化之上的。在云南,由于民族眾多,又地處邊疆,在古代的時候常因遠離中原,管理上多實行羈縻政策,一度出現多個小國或部落,文化的傳承形成了與中原不同的多元文化,后因戰爭及一些部落的消失而產生文化的更多神秘性,至今讓史學家和人類文化學者們孜孜不倦深掘,妄圖解開許多有影無形謎團。譬如南詔、大理國、自杞國、勞浸國(部落)、靡莫國(部落)、青銅文化、巫鬼文化、爨文化等云南古文化,這一切人文歷史文化形成了太多的神秘性,讓人追蹤、探索。由此,也就產生許多小說作家追蹤選題,意圖在心靈的秘史上進行挖掘,書寫人類發展的軌跡,愛松的《異夢錄》《金縷曲》、郝正治的《充軍云南》都屬于這類選題。《異夢錄》和《金縷曲》都是置身于古滇青銅文化背景下的敘述,探索人類精神與靈魂的苦苦追索,毫無疑問古滇國與青銅文化的神秘是令人猜測和揣摩的,具有著一種心靈上的探訪性;《充軍云南》也是一個大題材,雖然史料中或多或少記錄了許多有關充軍的資料,實質上要探訪充軍人的心理結構和那些文化背景下的足跡,依然是一次邊疆題材的神秘之旅,有影無形的文化結構非常難以駕馭,由此而增高小說的敘述難度。也就是說這類選題具有高難度的專業化知識,需要深入研究,超脫小說的人物、環境、心理、情節描寫,除了掌握小說的幾大要素寫作外,還得具有人文社科知識的深度,并把握遠古文化背景下的歷史,以掌握的資料揭示人類的秘密和探索人類的精神與靈魂,心靈的追述與需要是讀者和作者所共有的空間,幻象而真實。
因其神秘而具有挑戰,因其神秘而有閱讀的欲望;同樣因其神秘而難以敘述,因其神秘而困難重重。在寫《金沙江之西》中,不知西木是否考慮過,畢摩題材小說《金沙江之西》為何成為張慶國先生在《〈金沙江之西〉的寫作之難》中說的“是中國小說寫作中的首創”?“首創就有無法預料的難度,眾多作家回避此類鬼神文化題材,一定有其原因……小說的敘事并非論文的理性闡述,看起來誘人和想起來豐富,真正落實到筆下,就有可能阻塞,困難重重。”換句話說,也就是不可控的寫作難度隨時有可能提高,隨時有可能讓創作者推翻重來,選題已經鑄就了寫作難度,不能不讓創作者將神經緊繃,每一時刻都要考慮文化與歷史的挑戰,分寸拿捏成了這部小說的最高難度和挑戰。西木也在她的創作談《月亮升起來》中說:“我為寫作這部長篇小說,準備了10年,吃盡苦頭。”當然,不能吃苦,就沒有成功,她創作成功了,令人欣喜。
二、對神秘文化的闡述與記錄
在《金沙江之西》中,關于神秘文化的闡述和記錄連篇累牘,可以說去除神秘文化,這部小說也就不存在了,因為整部小說是以文化作為骨架支撐著情節和故事發展,大理國德江城的四大家族無一不在文化中進行,他們的言談舉止和所作出的決策均是圍繞著文化而進行的。退隱的相國高量成雖不在其位,但是仍以國家和百姓的利益為重,努力維護國家統一和社會和平;莫什土司卻在家族的利益中爭斗,以此提高身份和地位;阿蘇幫主則在商業中穿行于豪門強權之間,不畏懼,也不妥協,自有其生存之道;最后要說的是大畢摩,他是整部小說的關鍵人物,以人神所賦予的超能力及責任維護著正義、善良與和平,換句話說,是他利用自身所擁有的文化推動人類向前發展。四大家族的交錯從不同角度闡述和記錄著神秘的古代大理文化、地域文化、彝族民俗風情及瑰麗多姿的畢摩文化,讓我們深刻地體會這些文化的難得及生生不息的文化傳承力量,僅從記錄上說就是一份莫大的貢獻。
首先說畢摩文化。從文中,我們可以看出西木十年的準備工作沒有白費,她將彝族文化探討了個徹底,特別是畢摩文化。“彝族民間常說:頭人的知識上百,茲莫的知識上千,畢摩的知識無數。彝族民眾認為,畢摩是智者和知識豐富的人。在彝人眼里,學識淵博,精通眾藝,出類拔萃者的畢摩,才能被尊稱為大畢摩。”“畢摩是人與神、人與鬼、人與祖先的調解人。保護畢摩的神靈,有畢摩神、護法神、法具和經書。畢摩神是祖先神和行業神……后來,畢摩才有了經書和法具。”《金沙江之西》不但對畢摩文化進行記錄和闡釋,還寫入了大量的彝族古籍畢摩經書,“從材質上分,有竹經、獸骨經、羊骨經、皮經、紙卷等種類,從書寫上分,有人血經、獸血經、牛血經、豬血經、雞血經、木炭經、墨汁經等種類。從內容上分,有祭祖經、詛咒經、通神經、生育經、畢摩史經……治怪病經等。畢摩經書不但能與鬼神溝通,與靈界對話,還有治病救人和呼風喚雨的神力。”例子很多,不一一抄錄,這些神秘的畢摩文化,令人耳目一新,單從分類看就不可謂不全面,有治病救人的,有生育兒女的等等,乃是彝族先祖長期的文化總結,是中華文化大家庭的一個分支,凝聚了一個民族——彝族的智慧結晶。小說中大量的記錄和闡釋具有著文化傳承和保護的功用。換句話說,西木的《金沙江之西》超出了小說文本具有的情節娛樂賞美而擔負起了非物質文化與原生態文化傳承的功用。
接下來再談談西木在《金沙江之西》對民俗風情和地域文化的描摹。滇西是一個神秘的地方,滇西是一個多姿多彩的地方,西木對這里的民俗風情和民間文化進行了大量的記述。譬如彝家生生不息的火塘、精巧絕倫的銀器制作、銅鼓作坊、彝族刺繡手工坊,“在茶花酒館里開設彝族刺繡手工坊,讓茶花招收了十幾位擅長女紅的姑娘,制作繡品,賣給大理國王室。還安排茶花手下的店小二,去山里的村寨中收購零星繡品。彝繡遠銷外地,生意越做越大。”這些是地方上的土特產品,也是傳統文化。關于銀器的制作,她寫道:“他們做銀器很有經驗。選料、溶解、敲片、拉絲、制模、成型、畫樣、簪花、焊接、組裝、打磨、清洗、拋光,無不精通。做出大批好銀器,是大買賣!大家日子過得好,百姓也就安心了。”走在滇西的集鎮或城市,我們隨處可見銀器手工作坊,他們制作銀器精細美觀,給每一個到過滇西的人都留下了好印象,作家西木自然也就寫進了作品中。還有大理刀、三月馬市都屬于這一類。寫到音樂、舞蹈和迎賓禮,她又寫道:“大道左側站著一排端著羊角酒杯的彝家少年,右側站著一排彈著三弦跳著三跺腳的彝家少女。”想必去過彝寨旅游的人都會記得那種迎賓儀式,回味而難以忘記。婚嫁禮俗,彝族人唱哭嫁歌,“盛裝的女伴登場,她們圍著茶花,唱祝福歌和跳舞。領唱者、代唱者和隨唱而歌的女伴們,開始一輪又一輪,一唱一和,把彝族男女歌場定情、夜會相戀的風俗,以及成年時從母親處繼承首飾的習俗,統統唱了一遍。”這些讓我們更多地了解彝族習俗和盛大的儀式,喇叭吹《擺碗調》《上菜調》等曲子,坐在青松毛上喝米酒,吃羊肉,圍著篝火跳舞,生動地記錄著民俗風情,不斷推進了小說情節的發展,同時也為推出地域文化和旅游文化做出了相應的貢獻。小說的價值不是單一的,有著復式、重疊和跨界的價值體現,一個好的小說往往是有著文本外和文本內的雙重性價比,既有娛樂賞美,也有社會功用。
三、對邊疆歷史的尋蹤
寫畢摩,其實就是寫彝族文化。眾所周知,彝族是云南最古老的土著民族,過去曾被稱為叟族、爨族、夷族等,有著極其深厚的歷史根基和厚重的文化淵源。作家西木把它重點放在滇西這塊土地上來寫作,而且歷史背景是放在具有著重大歷史意義的宋朝時期的大理政權階段,由此涉及的歷史就更加厚重起來,作家需要了解的東西也更加廣闊和豐富。正如張慶國在《〈金沙江之西〉的寫作之難》中說的“她早在十年之前,就開始了這部《金沙江之西》寫作的認真準備和艱苦思索,既收集畢摩文化資料,也研究云南地方文史資料,研究云南西部的古代史,云南早期人類活動中的部落戰爭史與文化融合史,研究彝族歷史和種種古代神秘文化。”丁永杰碩士也在《彝族先知的秘密生活,驚心動魄的歷史追述》中說:“《金沙江之西》中還給我們呈現了大量關于彝族少數民族的政治斗爭、農業生產活動、商業活動、巫術醫術、經書神話……比較完整全面地概括了德江彝族的社會風貌,帶領讀者重溫當年愁云慘淡的生活。”厚重的歷史增加了寫作的難度,也迫使西木苦苦追尋和研究歷史,迫使她像學者一樣埋在書本的海洋,研究與彝族有關的人文社科知識。歷史已不再僅僅是滇西的歷史,而是整個云南,甚至四川、越南也都涉及了進去,當年的馬幫走南闖北,與大宋朝在廣西開設馬市交易等等,都是有據可查的歷史。
在大理國時期,政治權力的中心主要以段氏和高氏為主,段氏王族和高氏相族君臣相處百年,其中高升泰曾一度掌握政權,后還政于段氏,段氏與高氏在大理政權中的地位、權力及治國理政思想交融、傳承都有著極為重要的文化關系。西木需要理清那一時期的政治權力關系,由此才能部署設置《金沙江之西》的人物。大理的政治經濟文化繁榮在云南來說,不是最早的,云南大的政治經濟文化繁榮是在滇東北地區,那時候有兩個較大的部落(或者說小國家)勞浸、靡摩,被漢武帝開南夷道時擊滅,人員相繼趕往滇中、滇西地區,滇中文化才以滇池為中心建立起來,后來南詔、大理政權建立以后,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才又從滇中移位大理。雖然如此,滇東北的爨文化仍然很發展,在漢晉時期形成以南中(今曲靖)為中心的爨文化。其實爨文化也是彝族文化的一個分支。宋朝時期,也就是大理政權時候,出現了三十七部,現《三十七部會盟碑》保存于曲靖市第一中學內。
說起三十七部,便牽涉到了當時的土司制度。三十七部是當時分封的大大小小的土司部落,各管一片,養有兵馬。我曾一度追尋地方文化根源,研究了許多典籍,追蹤三十七部歷史,但沒能將三十七部盡數找出,許多書中都只列了部分,而西木卻在《金沙江之西》中將它們全部說了出來:“普摩部、磨彌部、納垢部、羅鳩部、夜苴部、磨彌殿部、落溫部、落蒙部、師宗部、仁德部、閟畔部、嵩盟部、際鹿部、維摩部、彌勒部、陽城堡部、強宗部、步雄部、羅加部、寧部、休臘部、因遠部、羅婺部、華竹部、羅部、屈中司部、納樓部、教合部、矣尼迦部、王弄山部、烏蒙部、乃娘部、芒布部、烏撒部、于矢部、休制部、嶍峨部號稱三十七部”,可見西木對少數民族的歷史尋蹤之深。在這部小說中,她多次寫到部落之間的戰爭以及方位,甚至還談到一些部落的實力和物產情況。這時候的戰爭多為部落之間的戰爭,《三十七部會盟碑》就是大理段氏政權聯合三十七部攻伐東方部落而立的會盟碑,不過,大理段氏政權和這些部落間時戰時盟,其間有多次攻伐征討和會盟,土司職位也存在世襲和分封兩種,不過權力卻不一樣,小土司管的地盤小,大土司則管的大,有的小土司受大土司制約而成為其屬下。部落酋長、卡、目都是當時土司的職位。
再一個,小說中寫的主要活動地點德江城也是有著歷史關系的,切不可當作隨意安的地名,更不可當作貴州的德江縣名。“德江”,貴州有個德江縣,位處貴州高原東北部的銅仁市,西木所寫的“德江城”是指滇西楚雄的一個古城名,是高泰明于宋徽宗崇寧元年(公元1102年)所建楚雄城而筑的外城,距威楚(楚雄)西北二公里,是高氏族人的居所和統治署衙,曾一度成為后大理國的政治中心,由于戰亂和自然災害等原因幾近消失,現處于彝人古鎮位置。作家西木比較細心,對于這些古城,她也進行了一番研究和考證,是真實存在的。
總之,西木為了寫好《金沙江之西》,我從文本中看出她對云南邊疆歷史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以她的話說就是:“這部小說牽涉到的各方面知識范圍廣,容量大。小說里涉及到的彝族文化、歷史事件、情感糾葛等,相互糾纏,非常復雜。”
四、尋蹤里的心靈糾纏及追述
對于西木的長篇小說《金沙江之西》,我認為這是一部文化尋蹤小說。里面充斥著以彝族畢摩文化為代表的邊疆文化尋蹤,譬如以高量成為代表的治國輔政思想文化,以莫什土司為代表的土司文化,以阿蘇幫主為代表的商賈文化、馬幫文化,以大畢摩為代表的畢摩文化,這一切構成了《金沙江之西》的文化大舞臺,任其在舞臺上盡情表演,或哭或笑,或鬧或跳,以小說的形式表達著作者的認知和心靈的探求。當探尋的文化越豐富的時候,小說的深度就越高,同時表現的難度也在增加,主題相對顯得模糊。此時,作家必須要入乎其內,方能掌握小說那根動人的弦,推動小說發展,讓人物性情顯露,另外又必須要求作家能夠出乎其外,清醒地認識到文化的復雜性,保持清醒的頭腦來把文化在情節線上串連。何況除了這四大人物為代表的文化外,又不勝其煩地寫了許多滇西的民俗風情、民歌民謠、旅游景點、土特產品等民間文化。西木在《月亮升起來——〈金沙江之西〉創作談》中說:“我進行了很多實地考察尋訪,結識了眾多畢摩傳人,閱讀了大量民族學、歷史學、地方史、民歌民謠和民間傳說等等資料。”這一切說明她對文化的尋蹤是深入的,真實的,刻苦的。“我在無數個日日夜夜里,畫下了很多圖譜,一次次修改寫作提高,一次次調整創作思想,一次次修改寫下的文字。推翻重來,再推翻重來。”這是文化尋蹤的心靈煉獄,龐大的文化集團構成了文化尋蹤心靈的糾纏,要蛻化在小說的情節里是非常難的,當發現得越多,“推翻重來”的可能性就越大,認知與心靈及小說的表達構成了多重糾結,換句話說就是文化的復雜性在左右著小說的推進、人物性格的表達,寫作的時候,有時到底是該將重點放在文化的表達上,還是放在人物性格的描寫上都有可能會成為她潛意識里心靈上的一種矛盾。倘若文化與人物的發展關系沒考慮清楚,就必須“推翻重來”了。
其實,該小說情節的推進就是作者心靈對文化的探求和認知。無論是古老的巫術卜卦,還是神奇的醫術,再或者黑、白畢摩的斗法,都是西木對文化尋蹤的心靈糾纏,糾纏得越緊,寫出的小說越精彩,最終大畢摩張古力(白畢摩)以善良和堅韌打敗了兇殘成性的黑畢摩瓦苦多。但是因為畢摩文化的神奇,古老的彝族祭師畢摩一方面是人類早期的精神生活領袖,精通彝族醫藥等文化之外,還承擔著彝族社會活動中的卜卦等巫祝行為,溝通天地人神,這就導致作家在寫作中必須睜著一只眼睛,時時刻刻醒著,注意行文拿捏分寸,這恐怕也是西木在寫作中心靈最為糾結之處。張慶國老師說:“當作家真正開始鬼神小說的敘述之路,文字就會慌張和無所適從,故事就會猶豫不決和左右為難,寫起來就會很痛苦。”當我讀完《金沙江之西》,我認為張慶國老師說得很對。此時,文化已經左右了故事的發展,但是作家卻在文化的認知中提升著心靈境界,更深入地探討生命的復雜性。也由于文化的復雜性,導致這部小說必須是全知性的寫作,即醒著的“完整的敘事”。
文化的多元構成了邊疆的歷史,在《金沙江之西》中,我認為西木的敘述有兩個巧勁:一是加入了神話和武俠的敘述技巧,二是多種聲音共同發聲的交織敘述方式。神話敘事是《金沙江之西》的一個鮮亮特色,神話緩釋了“鬼神文化”拿捏分寸的難度,讓她更好地從容地進行故事的編織和敘述。武俠小說敘事則有可能受到金庸《天龍八部》的影響,因《天龍八部》寫大理政權的情節很多,至今許多故事情節和滇西豐富多彩的多元文化仍讓許多人回味,《金沙江之西》中武俠小說敘事也從某種角度更好地詮釋和緩釋了神秘文化,并推動小說情節的發展,換句話說就是武俠小說的神秘與神秘文化的神秘融合起來了,從而在文中更好地詮釋了作家心中對多元文化的尋蹤。另外,《金沙江之西》前半部多為第三人稱敘述,后來卻發展成了多種聲音共同發聲的交織敘述,出現了一些第一人稱和第二人稱的穿插,或許這是文化的復雜性讓西木發現僅僅第三人稱已經難以滿足多元文化尋蹤里的表達,特別是畢摩神秘文化的通靈,于是她就采用加入了第一人稱和第二人稱的敘述方式,以更好地體現她心靈里對文化的尋蹤與糾纏,也就是說境界的提升需要一種更好的表達方式,促成故事情節的驚心動魄,始發性心跡坦露,吸引讀者在認知中前進。最終,她以這種敘述方式完成了小說的全知性敘述,塑造了一組豐滿的人物形象,特別是德江城的守護神大畢摩,正義、堅忍不拔、吃苦耐勞的形象呼之而出,小說變得完美,情節復雜而生動,故事曲折飽滿,也就是說在這次文化的多元尋蹤里,她的心靈追述得到了完美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