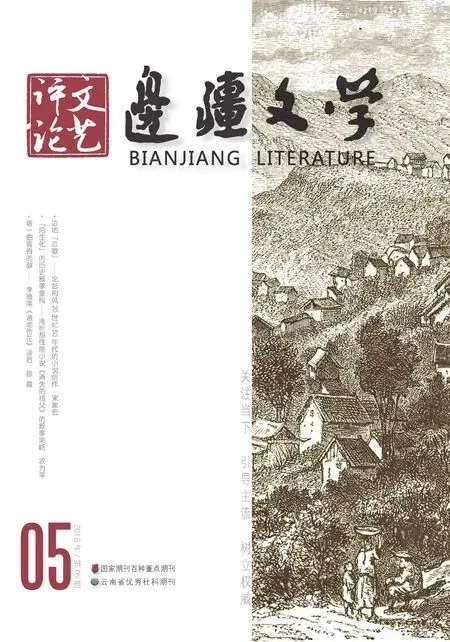“陌生化”的歷史敘事重構
——淺析胡性能小說《消失的祖父》的敘事策略
農為平
按照新歷史主義的觀點,文學與歷史之間存在著互文互現的對應關系,一定的文學文本總是映照著相應的歷史闡釋,而且任何歷史建構都不可避免地摻雜著敘述者的個人色彩。從這個意義上說,胡性能的小說《消失的祖父》正是從一種個人化的視角呈現了一段既波瀾壯闊又詭譎沉重的歷史風云,從其裂縫中書寫小人物隨時代跌宕起伏的傳奇人生和悲劇命運,折射大時代對普通人命運的裹挾與掌控。尤為引人注目的是,小說并沒有采用常規的直面歷史的敘事方式,而是巧妙借助一種新穎別致的“陌生化”手法,將一段原本已為人所熟知的歷史以另一副“新奇”面貌呈現,既使故事產生引人入勝、曲折生動的藝術感染力,也潛在地達到了借助小說載體回顧并反思歷史的深層訴求。
“陌生化”是20世紀初興起的俄國形式主義詩學理論中的一個核心概念。它認為對于習以為常的存在,人們總是以一種不經意的、機械的甚至是麻木的方式去把握,而陌生化則是對日常話語以及前在的文學語言的背離,它會不斷破壞人們的習慣性反應,使人們從遲鈍麻木中驚醒過來,重新調整心理定式,以一種新奇的眼光,去感受對象的生動性和豐富性,而藝術的根本任務就是使事物“陌生化”,正如俄國形式主義的代表人物什克洛夫斯基說,“作家或藝術家全部工作的意義,就在于使作品成為具有豐富可感性內容的物質實體,使所描寫的事物以迥異于通常我們接受它們的形態出現于作品中,借以吸引讀者的注意力,延長和增強感受到時值和難度。”在《消失的祖父》一文中,正是由于極為出色的“陌生化”策略和手法的運用,從而使小說在故事講述、歷史構建、文本形態等多方面對讀者產生強烈的吸引力和審美感受。
一、人物傳奇的陌生化處理
語言學家熱奈特將文學敘事具體分為三個層次:故事、敘述話語和敘述行為。而故事是其中的基礎、出發點,是敘述的目的所在,在小說中尤為重要。《消失的祖父》首先吸引人的一點是講述了一個曲折而耐人尋味的故事,這個故事實際上就是主人公聶保修充滿傳奇色彩的人生經歷。眾所周知,對人物傳奇的摹寫是小說中的一種重要模式,尤其在中國傳統小說中極為普遍常見,因而如何跳出窠臼,寫出新意和特色,自然是這類小說成功與否的關鍵所在。在《消失的祖父》中,作者有意設置了一種遠距離、散點式的觀察人物的敘述方式,使一個原本尋常的戰爭年代的人物傳奇故事,變得撲朔迷離、懸念頻頻,從而大大增強了故事的可讀性和吸引力,顯示了“陌生化”效果的獨特魅力。
先看看主人公聶保修的人生經歷,主要分為三個階段:一、青年時代留洋日本,后從昆明陸軍講武堂畢業,之后投身行伍,隨遠征軍赴緬甸抗擊日軍,經歷了九死一生的野人山大撤退,負傷回國;二、傷好后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在國共戰爭期間受命潛伏進國軍第六十軍作特工,在云南和平解放前夕隨國軍殘部撤入緬甸,與組織失去聯系;三、在緬甸漂泊十余年后冒險越境回國,因無法證明自己地下黨身份而鋃鐺入獄,被關押十多年后釋放,在申訴無望及親人的誤解、冷漠中離家出走,從此杳無蹤跡。這樣跌宕起伏的人生經歷本身就具有很強的故事性,如果按傳統的敘述方式來進行講述,也足以吸引人,但作者大膽擯棄了常規的手法,另辟蹊徑,用一種陌生化的手法予以講述,為讀者呈現一種新奇獨特的閱讀體驗。
首先,對主人公一生的敘述并不是從他自己的角度或是由熟悉他事跡的人來講述的,而是由一個對他知之甚少的他者——主人公的孫子來承擔的。在敘述語境中,主人公是缺席的,他只是一個被人追述、回憶的不在場當事人。而且不同于一般的祖孫關系,聶保修和孫子之間是隔膜的,他在孫子成長歷程中長期缺席,雖然出獄后回到老家與孫子有過極短暫的相處,但孫子對他顯然是不了解,二者間也甚少感情。一直到聶保修失蹤多年后,已步入中年的孫子出于本能的親情,才開始了對祖父人生的探尋。因而,不論是在時間還是空間上,講述者與被講述者之間都是疏離的,他們已無法實現真正的溝通和交流,講述者只能依借自己并不可靠的記憶和祖父殘留下來的各種支離破碎的蛛絲馬跡,透過重重迷霧去追蹤祖父的人生軌跡。這種敘事者的不可靠及敘事本身具有的可疑性,顯然使得整個故事在敘述視角上充滿了陌生化的特質。
其次,與傳統的人物傳奇故事有頭有尾、環環相扣,并試圖全景式呈現人物事跡經歷的敘事方式不同,《消失的祖父》采取了散點式的取舍策略,這與敘述者受限制的觀察視角正構成邏輯對應關系。祖父戎馬半生,漂泊、入獄半生,既享榮耀,又飽嘗艱辛恥辱,一生的經歷可謂紛繁復雜,若要全部展開敘述,足可敷衍成一部洋洋長篇。但在這篇小說中,作者僅有選擇性地選取一些重要的事件作為敘述對象,并且有意打亂前后時間順序,以跳躍式的思維來勾勒祖父的人生軌跡。這從揭示內容主旨的各部分的小標題即可反映出來:
二○一五年:照片;
一九八一年:丹城;
一九八二年:申訴;
一九九九年:尋找;
一九八三年:重逢;
一九五○年:逃離;
一九六六年,回國;
二○一五年:補記。
這種跳躍式、碎片化的敘事方式,必然對讀者慣有的漸進式線性閱讀思維構成阻礙和挑戰,造成閱讀上的新鮮體驗。這就好比玩一個拼圖游戲,作者不再按順序把圖片一一呈現出來,而是有意打亂順序,讀者要把錯亂的圖片按其內在邏輯關系重新進行組合,最終才能獲得對圖畫的完整印象。更何況,作者并沒有把所有的圖片都顯露出來,而是有所取舍,并且有意設置一些懸疑、空白,從而使讀者自然而然地滋生對人物對情節的好奇心和新奇感,大大增強了小說的陌生化效果。
最后,與上一點相適應,小說既有選擇性的以一些主要事跡為重點,以點帶面鋪陳人物的人生軌跡,同時又有意略去一些關鍵點,以造成懸疑,使通向真相的路途困難重重,使主人公原本就復雜朦朧的人生再生疑團,從而為聶保修的人生傳奇更添神秘色彩。在閱讀文本的過程中,讀者不僅需理順前后關系,通過邏輯推理來推測缺失的情節,而且也在無形中被作者所導引,跟隨敘事者一起去深入探尋主人公充滿謎團的一生。這時,讀者實際上已不再是單純意義上被動的接受者,而是參與者、探訪者,與對祖父并不了解多少的敘事主人公一樣根據不斷顯露出來的各種信息去判斷、推理、思考,無意識地共同參與到主人公命運的構建上。其中,最大的一個敘事空缺就是祖父當年是否是打入國軍隊伍里的地下黨。對于整篇小說來說,這顯然是一個邏輯關鍵點;對祖父一生來說,這更是最為至關緊要的事件,因為這決定了他的入獄從政治層面來說是否是冤屈,甚而決定了他后半生所有行為的價值走向。然而對于這樣一個重要的細節,小說中卻沒有正面提及,僅僅是從側面提供一些相關事件、情節,讓讀者自行去拼接、推斷。其中包括祖父多年后分別向安青、父親的口頭陳述,他身上攜帶的當年的上線黃敏文給他寫的證明材料,他一次次給有關部門寫材料申訴,等等。但另一些材料也不免令人產生疑惑,比如他當年是如何從一名國民黨軍官轉變為中共地下黨?其上線黃敏文是個什么樣的人?他潛伏進國民黨六十軍的任務是什么?云南解放時他為何不選擇留下來,而是要隨國軍撤入緬甸?……再加上作者有意在文中設置一些“迷魂陣”,比如聶保修的孫子在這件事上模棱兩可的態度,“直到今天,我仍然懷疑祖父如他所說的是潛伏在國軍里的地下黨。是,或者不是,也許都不太重要了。”通過這些敘事上的“障眼法”,祖父的一生行跡雖然基本上被勾勒出來,但一些關鍵的局部依然懸而未決,讀者最終無法如愿以償獲得全部真相,文本留下了豐富而意味深長的想象空間。
二、敘述視角的陌生化設置
受俄國形式主義影響,德國戲劇家布萊希特從戲劇理論角度提出了“間離效果”說:“把一個事件或者一個人物性格陌生化,首先意味著簡單地剝去這一事件或人物性格中的理所當然的、眾所周知的和顯而易見的東西,從而制造出對它的驚愕和新奇感。”在《消失的祖父》中,對主人公傳奇人生的追懷,對過往歷史的再現,不是采取全知全能的視角,而是運用了第一人稱這一限制性人稱,——而且是他者第一人稱,即由恰恰是對聶保修知之甚少的孫輩“我”來進行講述。講述者與被講述者之間,當下與特定歷史年代之間的隔膜,消解了人物、歷史事件的“前在性”,從而成功設置了人物之間遠距離的對話模式,達到了以一種新奇視角進行歷史掃描的藝術效果。這種巧妙的敘事人稱設置無疑是文本取得的陌生化效果的一個重要因素。
本來,在文學作品中,第一人稱的使用往往能使敘述事件顯得真實具體而具有較強的現場感和藝術感染力,而在本篇小說中,這種敘事人稱不僅喪失了其固有優勢,而且更加深了的故事的陌生感。對“我”而言,從小未曾謀面的祖父僅僅是一個能指符號,既是從大姑媽嘴里聽說的那個“聰明、帥氣,風度翩翩”的青年才俊、抗日英雄,也是被父親埋怨害了一家人的“反動舊軍官”,所以“我”對祖父的認知是遙遠、模糊、碎片的;當1981年祖父從監獄被釋放回家,第一次見到祖父的“我”,看到的是一個令人失望的蒼老憔悴的白發老頭,和他之間也始終保持著一種疏遠關系。主人公跌宕起伏且充滿謎團的人生,由對他知之甚少的孫輩來講述,本身就充滿了難以跨越的隔膜。而且,這一敘述行為是從聶保修失蹤23年后才開始,也就是說敘述者完全失去了與主人公交流的機會,因而只能依借記憶、相關人員的陳述、一些殘留資料,通過這些支離破碎的間接來拼接出聶保修的人生鏡像。
在這種不確定敘事中,作者還常常有意加入主觀臆測、判斷甚至是自相矛盾的看法,不僅使事件更顯撲朔迷離,也進一步加大了讀者與人物之間的距離。比如在上文提及的祖父是否是被安插進國軍隊伍中的地下黨這一核心事件上,祖父自己的陳述,安青的尋訪,黃敏文的證明等等,本來已使事件真相趨于明朗,而就在讀者以為真相大白之時,敘事者又冷不防地跳出來說:“有跡象表明,祖父當年參加國民黨中央軍,之后的行伍經歷遠不像他檔案里記錄的那樣簡單,就在祖父失蹤后不久,有人曾給家里送來過一筆錢。”還有在去緬甸這件事上,“祖父當年選擇離開昆明,跟隨國民黨殘部南逃緬甸時,究竟有多少是組織的安排,又有多少是自己的個人選擇,已經不得而知。”這就使得聶保修的行為變得曖昧不明而又無跡可尋。另外,小說利用第一人稱的特性,在一些細部將現實與想象、真實與幻覺雜糅起來,營造出一種虛虛實實、似幻似真的氛圍,與主人公充滿神秘傳奇的人生相得益彰。云南宣布和平解放后,由于祖父及時提供情報,解放軍將撤退的國民黨部隊阻擊于云南元江一代,雙方在此地展開了中國人民解放軍與國民黨在大陸的最后一戰,多年后,當“我”來到當年的戰場,“身穿國軍上校軍服的祖父在我的大腦里清晰起來,我甚至覺得自己,看見了半個世紀前,他穿越這條河谷之后遠去的情景。”就在當晚,我睡下后不久,“我看見祖父從窗子外面進來,穿著照片中的那套國民黨上校軍服,面目慈祥,與我現在的年齡相仿,那情景更像是我鏡中的自己,穿了戎裝。我仰躺在床上,望著浮在空中的祖父,他在一點點變小,又一點點靠近。當他縮小到只有兩寸照片大小的時候,我感到他像雪花一樣,漸漸融入我的身體。”“那一瞬間,我仿佛成了祖父,親歷了1950年跑到緬甸,以及十多年后,從緬甸潛逃回國的情景。”這原本不無夢魘色彩的場景,卻因接下來的一句話變得虛實難辨、神秘莫測:“這種靈魂附體的事情,在我的人生中曾數次發生。”
對于聶保修的人生經歷來說,“我”不僅是一個不可靠的敘事者,而且“我”所獲得的信息又主要是通過其他人而得到的,這更進一步加深了小說的“陌生化”距離。并且,幾個方面匯總起來的與祖父相關的信息是不同甚至互為矛盾的,這些不同的人的敘事既起到互補作用,也使得祖父的形象更為撲朔迷離。“我”的大姑媽是提供祖父正面形象的一個重要人物,她是祖父幾個孩子中唯一對祖父有印象并且在情感上與祖父親近的人,她話語中的祖父是俊朗的青年才俊、受人景仰的抗日英雄,她以這樣的父親為榮,并樂此不疲地對“我”講述祖父的輝煌事跡,幸運的是,大姑媽在祖父出事前就病逝了,她得以永遠保留對自己父親的崇敬之情。而“我”父親對祖父則是另一種態度,他尚未出生祖父就離開家鄉上戰場了,他從來沒有感受過具體的父愛,相反,在他成長的歲月里,祖父的存在像一塊頑石,一次次阻擋他的前途和人生:考上大學卻因為政審不過關而被卡,工作后積極進步,每年都工工整整地遞交入黨申請書,但由于祖父的影響而發展緩慢,一直到三十八歲才被提拔為文化館館長,入黨問題,則拖到四十歲才解決,因而不難理解他對自己的父親更多的是埋怨甚至是怨恨的情緒,他與祖父一直處于一種尷尬的對立狀態,這也是導致祖父晚年出走的重要原因。安青則是所有敘事者中最重要的一個,她17歲時在戰地服務團與祖父相識,愛上了這個右手負傷的帥氣的戰斗英雄,祖父曾與她在昆明置屋同居了多年,直到被迫撤離。“我”手中保留的祖父唯一的一張照片,祖父生前的諸多秘密,如他中共地下黨的身份,他當年如何撤離昆明,他在緬甸九死一生的漂泊經歷,他所寫的申訴材料內容……這些關系到聶保修命運的重要信息,“我”都是通過安青獲得的。應該說,安青的存在,更增添了聶保修人生的傳奇色彩,同時,從敘事立場來說,這個人物為“我”的限制性視角開辟了一道通向聶保修人生秘密的便捷途徑。
總之,小說既設置了主觀性強的第一人稱視角,但又通過“我”來回溯、展開另一個他者——聶保修迷霧重重的一生,使得第一人稱喪失了自身的優勢,“我”和讀者一樣,對祖父所知甚少,只能借助其他人、其他途徑來找尋關于祖父的種種蛛絲馬跡,在判斷、猜測、臆想中拼接起祖父的人生軌跡。在這個過程中,讀者本能地產生了似幻似真的參與感,在文字的導引下,仿佛隨著“我”一起去探尋一個被歷史煙塵所遮蔽的神秘人物的人生歷程,好奇心、新奇感自然而然被激發出來,進入了一種“陌生化”的境界。不用說,這種“間離”的手法將敘述者、讀者皆排斥在主人公的世界之外,他們只能隔著一道道藩籬窺見、猜測聶保修的遭際經歷,卻無法順利走進他的人生和內心世界,無法抵達一般文學作品慣常會提供的“真相大白”境界,從而保證了新奇感、陌生感的始終存在。
三、歷史敘事的陌生化構建
為更好地達到陌生化的審美效果,形式主義倡導者們主張在文學創作中盡量取消文本經驗的前在性,“瓦解‘常備的反應’,創造一種升華了的意識”,“最終設計出一種新的現實以代替我們已經繼承的而且習慣了的(并非是虛構)現實。”《消逝的祖父》雖以人物敘事為中心,但文本同時呈現出一種厚重的歷史質感,或者說聶保修復雜跌宕的傳奇人生正是依托于紛繁動蕩的特定時代才得以發生。小說將人物命運置放到波瀾詭譎的宏大歷史場景中去展開,既彰顯時代洪流裹卷下小人物的身不由己,又從一種私人化的視角建構了獨特的解讀歷史的視角,使一段早已被意識形態所定性的歷史呈現出某種引人沉思的詭吊色彩。
從時間維度上看,《消失的祖父》選擇了中國現當代最動蕩復雜的一段歷史作為敘事對象:從1937年抗日戰爭橫貫至敘事當下(2015年),時間跨度前后綿延近80年——這樣巨大的時間容量也充分顯示了作者展現并審視歷史的視野及訴求野心。小說中具體指涉的歷史事件主要有:抗日戰爭,具體寫到滇西抗戰,緬北野人山大撤退;國共內戰,包括云南和平解放,國民黨殘部撤入緬甸;1949年共和國建立后的諸多政治運動。在一部中篇的篇幅內容納了如此繁復的歷史信息量,這是使小說血肉豐滿、豐贍充實的一個重要因素,也使小說在某種程度上負載了闡釋歷史的重任。當然,由于涉及政治、時代等特殊語境,這并非是一件輕而易舉之事。對于以上在史書、史料中均有大量詳細記載而且廣為人知的歷史,作者刻意避開與歷史的正面遭遇,別出心裁地轉換視角,選擇從主人公聶保修充滿神秘、傳奇色彩的人生際遇來作側面呈現,同時也放棄家族敘事、性格敘事等傳統敘事立場,一意從宏觀的歷史視野來建構、觀察,從而將人物命運與歷史風云緊密勾連起來,盡寫處于歷史激流中小人物身不由己的沉浮和跌宕,使人物命運盡悉統攝于歷史不可捉摸的戲劇性變遷之中。可以說,小說中聶保修及其家人、相關之人的遭際無不是時代使然,他們自身無法掙脫的人生、命運不過是歷史的一個小小注腳而已。借助這樣的視角與手法,小說在主題命意上達到了個人命運與時代歷史的高度融合,寫人即是敘史,二者渾然一體,水乳交融,給予讀者一種新奇、陌生的歷史體驗感,完成了“一種新的現實”的“設計”。
小說以倒敘手法,在開篇首先營造了一種充滿神秘懸疑色彩的氛圍:作為小說敘述者的“我”——主人公聶保修的孫子,在一個即將辭舊迎新的歲末寒夜中追想已失蹤32年、生死未卜的祖父。在故事尚未正式展開的狹小敘事空間里,作者倒豆子般將一堆陌生信息向讀者傾瀉而下:失蹤,身著國軍上校軍服的老照片,上線黃敏文,喜歡黃色“懶梳妝”菊花的安青的墳墓,愧疚的父親,印有上海外灘圖像的手提包……對于一無所知的讀者而言,這些信息的所指是不明確的,充滿著疑問,而它們綜合疊加起來明顯帶有濃厚的舊時代氣息,小說的敘事時間指向隱隱閃現。在一堆充滿懸疑色彩的疑團面前,讀者的好奇心自然而然被調動起來,產生了欲從文本中追尋答案的興趣。這樣,一條進入主人公身世、進入歷史的敘事途徑就成功地搭建了起來。
在接下來的敘事中,小說以幾個時間、地點、事件上的節點作為線索來串聯起祖父時而明朗、時而模糊的一生,而且在排列順序上并非線性行進,而是打亂的,一會兒是“1981年:丹城”,一會兒是“1999年:尋找”,下一節則“1950年:逃離”,在這種時而當下,時而回憶的混雜敘事中,祖父撲朔迷離的一生通過一些并不連貫的時間和事件片段得以部分呈現。只不過這個呈現的過程始終籠罩著一層面紗,讀者只能窺見部分細部,更多的部分則像歷史真相一樣永遠逝去,留下的只有不無沉重的思索和遺憾。而重要的是,祖父人生中的每一個重要事件和轉折,無不與當時的時代緊密勾連,甚至可以說,他所邁出的每一步關鍵步伐,都是為時代大潮所驅動:在清末民初的留學大潮中赴日學習,在軍閥混戰的亂世進入陸軍講武堂學習軍事,因抗戰爆發而奔赴戰場,在國共紛爭時作為地下黨打入敵軍內部,反右運動中因身份不明入獄……祖父波瀾起伏的一生實則正是那段紛繁動蕩歷史的真實寫照,作者欲借人物傳奇來重構歷史的意圖也就昭然若揭。
縱觀聶保修的一生,體現的是中國傳統的精忠報國的人生追求。他前半生戎馬沙場、舍家為國的富于傳奇色彩的人生履歷,不論是從價值評判還是道德評判的角度,都可稱得上是一個大義凜然的時代英雄。然而,歷史卻與他開了一個荒誕的玩笑。寧聶保修九死一生、忍辱負重,最終贏得的不是鮮花、掌聲、功勛、獎章,而是異國漂泊、鋃鐺入獄,后半生一直頂著“國民黨反動軍官”的罪名,在古稀之年凄涼地離家出走,不知所終;家人也因為他的歷史問題飽受牽連:母親、妻子先后自殺,兒子因他而在上大學、提拔、入黨等人生大事上受阻,不僅將他視為路人,還從心里怨恨他,不正常的家庭氛圍又造成孫子人生、心理上的失格……亞里士多德以藝術是對人生的模仿的觀念入手,第一個提出了悲劇的定義,認為“悲劇是對于一個嚴肅、完整、有一定長度的行動的模仿”。車爾尼雪夫斯基稱“悲劇是人生中的可怕事物”。在乖戾無常的時代面前,聶保修及其家人的命運注定了是一出他們無法選擇也無法掙脫的時代悲劇,而同時,他們的人生遭際也像一面鏡子,反射出時代的凜冽寒光。
有幾個細節尤其耐人尋味。1966年,聶保修在大批國民黨殘部撤回臺灣之際,冒著生命危險偷偷穿過國境線回國,四處尋找當年介紹他入黨的上線黃敏文——黃是唯一能證明他地下黨身份的人。但當時國內正開展轟轟烈烈的政治批判運動,諷刺的是,黃敏文早已被劃為右派而在農場接受勞動改造。當聶保修費盡周折終于找到他時,在這個決定他命運的關鍵時刻,卻出現了戲劇性的一幕。“終于與自己的上線再次見面了,祖父拉著黃敏文的手,激動得想哭,可黃敏文卻用警惕的目光打量祖父。得到消息的農場場長趕了過來,用鷹一樣的眼光審視著祖父和黃敏文。場長問黃敏文:‘你認識他?’黃敏文盯住祖父望了又望,搖搖頭說:‘不認識!’”于是,聶保修就成了一個國民黨的反動軍官被投入監獄。多年后,黃敏文的右派帽子被摘除,釋放之日前去探望聶保修,“面對祖父的質問,黃敏文沉默長久之后,承認自己認識祖父”,他后來還專門寫了證明聶保修身份的材料交給組織,聶保修也以此為據一次次寫申訴材料,但都如石沉大海。“那一段時期,全國都在落實政策,那些此前幾十年走背運的人迎來了一個人生的小陽春。只有祖父例外。”平反的無望,親人的冷漠,最終,無路可走的聶保修只能離家出走——這樣的選擇顯然與他早年熱血慷慨的形象更相符。葉歌苓在《陸犯焉識》中也設置了一個類似的結尾,但陸焉識的去向是明確的,而且他身邊還有篤愛他的馮婉如相伴,多少有一抹暖色調,而祖父是真正的孑然一身,不知所蹤。這個不無殘酷的結局將聶保修的人生悲劇推向了極致,作者對歷史的反思也升華到了一個令人沉重的高度。
與聶保修的悲劇命運相映照,小說中還安插了一個似乎與故事關聯不大的情節:身為歷史教師的“我”曾去采訪一個叫李茂的抗戰老兵,但老人三緘其口,當“我”為了消除他的顧慮說“您是打小日本的,是抗日英雄”時,95歲高齡的老兵放聲嚎啕大哭,“‘我不該參加國軍抗日!’老人說,他的眼淚順著滿是溝壑的臉慢慢地往下流淌。”后來“我”才知道,抗戰勝利以后,李茂,這個曾經的中國遠征軍戰士,因為歷史原因三次被判刑,一共在獄中度過了二十六個春夏秋冬。是什么令歷史蒙塵?是什么讓聶保修、李茂這些曾為民族命運而以命相搏的人遭受命運屈辱的戲弄?行筆至此,小說的用意已經不僅是要探尋某一個人飄忽的蹤跡,講述一個傳奇故事,而是努力從歷史的塵埃中打撈一個已經遠去的特殊群體的過往——哪怕只是支離破碎、只言片語的殘留,哪怕只是一些模糊的身影——透過他們盡可能地接近歷史真相。這潛埋于文字下的深沉訴求,使小說文本具有了厚重的歷史質地,充分顯示了作家鮮明的歷史責任感和難能可貴的歷史求索意識。
“祖父顛沛流離,輾轉一生,最后概括為短短的幾行履歷,就像一根吃剩的齒刺不全的魚骨頭。僅憑這個殘損的魚骨,我們無法想象這條魚活著的時候,它身體的流線、完整而閃耀著光澤的鱗片,更何談它曾游過的江河、寄身的水草、經歷過的熾熱或寒冷的歲月。”作者在結尾處不無感慨地如此寫道。聶保修們殘破不全的人生,充滿了歷史不可捉摸的戲劇性和時代荒誕色彩。需要指出的是,俄國形式主義主張陌生化,是為了將讀者的注意力引至文本即“文學性”本身,而《消失的祖父》中陌生化手法的運用卻是反其途而行之,很顯然,它欲令讀者關注的是一段歷史而不僅僅是一個小人物的故事。

陳玲潔 冬至 布面丙烯 2015年
【注釋】
[1] 登載于《人民文學》2016年第4期。本文所引例文,均出于此處。
[2] 轉引自張冰《陌生化詩學》,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78頁。
[3] 張黎編,《布萊希特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第204頁。
[4] 霍克斯,《結構主義與符號學》,翟鐵鵬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97年版,61~62頁。
[5] 亞里士多德,《詩學》,陳中梅譯,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68頁。
[6] 車爾尼雪夫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論文學》中卷,辛未艾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88頁。
【參考文獻】
〔1〕 張冰:《陌生化詩學》,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2〕 趙一凡等編,《西方文論關鍵詞》,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
〔3〕 方珊編:《俄國形式主義文論選》,三聯書店,1989年版。
〔4〕 什克洛夫斯基,《散文理論》,劉宗次譯,百花文藝出版社,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