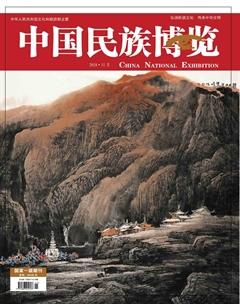唐代的私兵武裝與部曲
郭紹華
【摘要】中國中古時期存在著一個系統、嚴格、成熟的身份制度——良賤制度,賤民內部又分為雜戶、官戶、部曲、奴婢等多種不同的階層和等級。唐朝時部曲身份發生了重要變化,《唐律疏議》中對部曲有著詳細嚴密的規定,士族豪強占有一定數量的部曲,其由部曲所組成的私兵武裝成為一股潛在的社會勢力,士族豪強的演變與部曲的演變有著密切的聯系。唐中后期均田制、租庸調制和府兵制趨于瓦解,部曲逐漸轉化和減少,安史之亂和之后的藩鎮林立則與部曲的再一次武裝化有著重要的關系,也體現了唐中后期部曲變化的一種特殊形式。
【關鍵詞】唐代部曲;士族豪強;私屬武裝;藩鎮私兵
【中圖分類號】K24 【文獻標識碼】A
漢代的部曲,起初是一種軍事編制,漢末以后專指豪強地主的私人武裝。到南北朝時期,部曲同時成為一種賤民的法定稱呼。但關于唐代部曲的身份,史學界卻頗有爭議。或者認為唐代是部曲佃客生產制,部曲佃客是典型的農奴;或者認為唐代的部曲是法定的賤口;或者認為其是軍隊部屬;也有認為部曲只見于唐律,而為史書所沒有,特別是中唐后,部曲在現實生活中已基本消失。
一、唐代部曲概況
關于部曲的研究,學者們大多認為其興盛是在魏晉南北朝時期,隋唐以后走向衰落,但是對于部曲消亡的具體時間問題,亦存在一些分歧。
一種觀點認為,到唐代,尤其是唐中葉以后,社會上已經幾乎不存在部曲了。唐長孺在《唐西州諸鄉戶口帳試釋》中就認為:“唐律中明確規定其‘賤口身份和法律地位的部曲,幾乎在史籍中一無所見……具有強烈人身依附關系的部曲制在中原地區是過了時的”。他還分析了吐魯番文書中出現的部曲,認為“西州之有部曲,顯然是從內地引進的。基本上在全國過了時的殘遺同樣在西州也沒有獲得發展”[1]。李伯重的《唐代部曲奴婢等級的變化及原因》一文認為,到了唐代中后期,不僅庶族地主擁有部曲的例子不多見,就是官僚士族地主擁有部曲的記載也很少了。武宗會昌滅佛只是釋放奴婢而不見部曲,唐代中后期因罪沒官者,只見資財及奴婢,也不見部曲。這說明到唐代中后期,私人占有部曲的現象幾乎消失了[2]。
另一種觀點認為,唐代社會依然存在一定數量的部曲,部曲的消亡應當是在宋以后。韓國磐在《隋唐五代時的階級分析》中認為,隋唐五代史書中記載的部曲客女不多的原因,是因為“唐朝史書多言家僮、僮仆或仆隸,而少言部曲,因為‘部曲奴婢,是為家仆,部曲既是家仆,故徑言家僮或仆隸”,實際上隋唐五代時期擁有大量家僮仆隸的官僚豪強還有很多[3]。張澤咸在《唐代的部曲》一文中認為,唐律有關部曲的規定更重要的是為了適應唐代社會現實的政治需要,史書和出土文書所留下的有關部曲的記載,就是很好的證明。中晚唐時期部曲客女在社會上仍有一定數量,那種認為中唐以后部曲在現實生活中消亡的結論未必妥當,部曲在歷史上的完全消亡,大概是在元、明之際,但同時他也認為宋朝時殘存的部曲已不像唐代那樣具有普遍的社會意義[4]。
唐代部曲的身份,即他們的法律地位,在唐代法典《唐律疏議》中有詳盡而嚴密的規定。《唐律疏議》卷六《名例》規定:“部曲,謂私家所有”,“諸官戶、部曲、官私奴婢有犯,本條無正文者,各準良人”,“其部曲、奴婢應征贓贖者,皆征部曲及奴婢,不合征主”[5];卷一二《戶婚》又規定:“依戶令,放奴婢為良及曲客女者并聽之,皆由家長給手書,長子以下連署,仍經本屬,申碟除附”,“放奴婢為部曲、客女,而壓為賤者,又各減一等,合徒一年。仍并改正,從其本色”[6];卷一七《賊盜》規定:“諸部曲、奴婢謀殺主者,皆斬。謀殺主之期親及外祖父母者,絞;已傷者,皆斬”[7];卷二十二《斗訟》規定:“諸部曲毆傷良人者,官戶與部曲同。加凡人一等。加者,加入于死。奴婢,又加一等”,“諸奴婢有罪,其主不請官司而殺者,杖一百。無罪而殺者,徒一年”,“諸主毆部曲至死者,徒一年。故殺者,加一等。其有衍犯,決罰致死及過失殺者,各勿論” [8];卷二十五《詐偽》規定:“諸妄認良人為奴婢、部曲、妻妾、子孫者,以略人倫減一等。妄認部曲者,又減一等。妄認奴婢及財物者,準盜論減一等”[9]。除此之外,《雜律》等皆有關于部曲的記載。但唐代部曲的法律地位往往因事而異,不能一概而論。唐代的部曲一部分是由奴婢放免而來的,奴婢的放免有兩種情況,一是逕直放免為良人;二是雖然免除奴婢身份,但未離主家且仍供主人使役,后者即所謂“部曲”。因此,唐代法律中部曲和奴婢、客女[10]往往是在一起規定的,唐代的部曲既不受田又不納課,只是合法的依附者。
根據唐代部曲身份屬性的變化,將唐代部曲大致分為兩類,一類為用于家庭生產的賤口部曲,一類為用于作戰和扈從的武裝部曲。
韓國磐在《隋唐五代時的階級分析》一文中就曾認識到“自唐朝安史亂后,武人多擁兵自重,所部兵士差不多成為私人的武裝力量,故亦通稱為部曲。這種部曲,和魏晉以來稱私人武裝或泛稱所部兵為部曲者情況相同,而和《唐律》所言部曲卻不盡相同”[11]。
李伯重認為,“唐初承南北朝余緒,以部曲進行生產的事理當有之。但安史之亂后,這種部曲則根本見不到了。這時的部曲,其工作主要是作戰或做將帥的武裝扈從,與社會生產己經完全沒有聯系了”[12]。即認為唐中期以后賤民部曲不復存在了,存在的部曲都是些武裝部曲。
李靖莉的《從吐魯番出土文書看唐代西州部曲》《再談唐代的部曲》《唐代中原地區賤口部曲趨于絕跡的原因》《唐代中原與邊地部曲比較研究》等一系列文章認為,唐代同時存在著兩種類型的部曲,即賤口部曲與武裝部曲。賤口部曲主要分布在西州、渤海國等社會發展相對滯后的緣邊地區,這一類部曲較多的應用于家內生產和役使,更符合《唐律疏議》中規定的部曲的性質,其擁有者分布于社會的各個層面,并且存在一定的比例。而中原地區則分布著具有良人身份的武裝部曲,主要用于征戰和武裝扈從,并主要隸屬于官僚階層,并認為唐代內地的賤口部曲己經很少,趨于絕跡[13]。
二、地方私兵武裝與部曲
從南北朝至隋唐,社會上存在著一股潛在的武裝力量,他們以士族或地方豪強、富室為領袖,以私兵、部曲和一些地方豪俠武士為骨干,組成了一股介于政治力量和社會力量之間的不容忽視的力量[14]。士族、豪強和富室以他們占有的土地為經濟基礎,吸收那些因種種原因游離于社會正常生產之外的個體,組成自己的私兵部曲,以此作為他們在地方實力的基礎,而將這股勢力納入政治體制中也成為統治階級的一項重要任務,西魏北周直至唐前期的府兵制便與此有著重要的聯系,這部分武裝力量的擁有者和領導者,即士族豪強們便可依據這一力量進入官僚集團。相比之下,士族更多的是憑借自己的家學和門蔭入仕,豪強富室無論是接受教育的機會還是教育內容上都較弱于士家大族,他們的入仕更多的是憑借自己掌握的部曲特別是武裝部曲而所擁有的武力和一定的地方社會的影響力。毛漢光的《中國中古社會史論》中將此一階段的豪強描述為地域性的武質集團,充分說明了其所顯示的武力性[15]。
李勣“家多僮仆,積粟數千鐘,與其父蓋皆好惠施,拯濟貧乏,不問親疏”[16],儼然為一地方豪強富室,程知節“大業末,聚徒數百,共保鄉里,以備他盜”[17],盧祖尚“累葉豪富,傾財散施,甚得人心。大業末,召募壯士,逐捕群盜,時年甚少,而武力過人,又御眾嚴整,所向有功,群盜畏憚,不敢入境”[18],皆以自己的私兵武裝起家,以致之后入唐為官。
除了地方豪強之外,一些大姓士族同樣也吸收一些流亡人口作為其私屬武裝,以應對時局變化,如李唐王朝之平陽公主。公主乃歸鄠縣莊所,遂散家資,招引山中亡命,得數百人,起兵以應高祖。時有胡賊何潘仁聚眾于司竹園,自稱總管,未有所屬。公主遣家僮馬三寶說以利害,潘仁攻鄠縣,陷之。三寶又說群盜李仲文、向善志、丘師利等,各率眾數千人來會……公主掠地至盩厔、武功、始平,皆下之。每申明法令,禁兵士無得侵掠,故遠近奔赴者甚眾,得兵七萬人……時公主引精兵萬余與太宗軍會于渭北,與紹各置幕府,俱圍京城,營中號曰‘娘子軍。[19]
由此可見,平陽公主在李淵初起兵時“散家資,招引山中亡命”組成自己的私兵武裝,這種潛在的武裝勢力在戰亂時更容易得到發展,它的歸附或對立對于新政權完成統一具有強有力的影響。同時,也可以發現這類私兵中也有因軍功當官入仕之人,如馬三寶。馬三寶為“家僮”,其性質相當于部曲,但以軍功入仕,“初以平京城功拜太子監門率”,后“又從平薛仁杲,遷左驍衛將軍”,再從柴紹“擊吐谷渾于岷州”,累封新興縣公、左驍衛大將軍。[20]
在戰亂時期,特別是隋末唐初之際,豪強富室依靠自己的部曲拒捕盜賊、保衛鄉里,在地方的控制力和影響力上占有較大的比重,是一股強有力的社會勢力。在國家社會逐步穩定統一之后,這股勢力便站在了統一的中央政府的對立面,勢必要為統治階層所吸收同化或打擊消滅。同時,豪強階層在戰亂時憑借自己的社會勢力崛起,大多因軍功入仕,其所擁有的部曲特別是武裝部曲被納入正式的制度之中,其數量逐步減少,武裝性逐步減弱,統治階層通過《唐律疏議》等法律形式將部曲奴婢等人的社會性質與地位進行了界定,確保其能夠處于正常的控制之下。
毛漢光在論述地方豪族向士族的轉化過程時,認為豪強在這一過程中體現了由武質團體而兼具文章世家,由地方性人物而成為中央性人物,由社會性而兼具政治性,經濟性的形而上等趨向[21]。由此可見,地方豪強逐步向官僚士族轉變的過程中,逐漸放棄了其在地方上和軍事武裝上的獨特地位,由武轉文并向中央靠攏,與地方的聯系逐漸減少。在這一點上,豪強與士族極其相似,與本地域的聯系更多地體現為經濟即占有土地上的聯系,這一聯系所反映的部曲更多地應用于生產上,其武裝性逐漸減退,正如《唐律疏議》所規定的部曲性質那樣。
在士族郡姓大規模向兩京地區遷徙后,其與本地望的聯系也在日趨減弱,除了大姓遷出本望造成的小姓快速發展以頂替空出的地位和勢力真空之外,原大士族所占有的家族田產以及擁有的部曲奴婢數量都在減少。即便之后文官武將來往轉任于京師與地方,其所擁有的部曲數量也會出現不同程度的變化,如“初,子儀自相州罷歸京師,部曲離散”[22]。這種種變化導致了唐中后期部曲,尤其是中原地區用于家內役使和從事生產的部曲奴婢數量的減少,而這些脫離原主人的部曲奴婢有的落藉為民,有的則被地方節度使吸收,成為自己的牙兵或親軍,又重新成為節度使的私人武裝。
三、藩鎮私兵與部曲
唐朝中后期,均田制、租庸調制和府兵制趨于瓦解,以此為基礎的人身依附關系減弱,租佃關系和雇傭關系的發展為部曲、奴婢等私屬脫離主人提供了更多的選擇,同樣替代府兵制的募兵制也需要大量的兵源。安史之亂的沖擊更加速了這些轉變,促使社會進一步變革。
面對這一變革,部曲脫賤為良的出路更為廣闊,通過就地轉化和逃亡,或轉化為佃客農民,或因雇傭關系在外地落籍為良,或進入募兵行列等,部曲一旦掙脫主人,就有更多的機會找到糊口生路。
部曲的再一次武裝化與安史之亂和之后的藩鎮林立有重要關系。安史之亂中安祿山的主力部隊即為被稱之為“曳落河”[23]的由雜胡組成的親軍,直屬于安祿山本人,一定意義上是其私屬,這可以看作武裝部曲的一種形式。在安史之亂之中和之后,依然有部曲存在。如“安慶緒之北走也,其平原太守王暕、清河太守宇文寬皆殺其使者來降;慶緒使其將蔡希德、安太清攻拔之,生擒以歸,于鄴市。凡有謀歸者,誅及種族,乃至部曲。州縣官署,連坐死者甚眾”[24],“子儀自相州不利,李光弼代掌兵柄,及征還朝廷,部曲散去”[25],“承恩多以私財募部曲”[26],“洛苑使姚文壽縱部曲奪民田,匿于軍,吏不敢捕。府大集,部曲輒與文壽偕來,宿掩取榜殺之”[27],“(元和十四年)冬十月丙午朔。壬戌,安南軍亂,殺都護李象古,并家屬、部曲千余人皆遇害”[28],“(乾寧二年)十一月癸未朔。壬寅,王行瑜與其妻子部曲五百余人潰圍出奔,至慶州”[29]等等。雖然并不完全確定這時的部曲屬于武裝部曲還是賤口部曲,但可以確定的是部曲在這時并未完全消失。
承續安史之亂的影響,各地藩鎮逐漸增多,藩鎮林立已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張國剛將唐中后期的藩鎮分為四種類型:河朔割據型、中原防遏型、邊疆御邊型以及東南財源型。割據的藩鎮主要為河朔型,其中又以河朔三鎮(魏博、成德、盧龍)為主,中原、邊疆、東南型的藩鎮雖不割據,但它們以本身各自不同的地理特點及其與唐王朝的政治、財政、軍事關系,影響著整個藩鎮割據形勢的發展[30]。
由于府兵制的瓦解及其向募兵制的轉化,唐中后期的軍隊大多為雇傭兵,其中不乏掙脫主人逃亡后成為雇傭兵者。尤其在割據藩鎮,節度使往往倚武力與中央對抗,因此需要更多的軍隊以自保,但雇傭兵與純粹的部曲家兵又有區別,其軍費開支由藩鎮財政支付,而且由于種種復雜的關系,藩鎮的士兵嘩變也常常發生,因此,節度使便需要一支私屬性更強的部隊來保護自己的安全。
牙兵便是節度使穩定對內統治的支柱,“士卒驕不能御,則置腹心之士,幕于公庭廡下,挾弓執劍以須。日出而入,前者去;日入而出,后者至。寒暑時至,則加勞賜酒肉”[31]。牙兵由藩鎮主帥直屬的番號軍中擔任宿衛的那一部分親軍組成,又稱作衙軍,主要分布在藩鎮的牙城內外、羅城內外,使府治所境內、管下各州縣和險要之地皆有牙兵鎮守。主帥與牙兵之間的關系亦不穩定,常有主帥虐殺牙兵或牙兵殺逐節帥的事件發生,于是主帥又另置親兵(又稱后院兵、后樓兵)以制衡牙兵,《資治通鑒》載:“魏博節度使樂彥禎,驕泰不法,發六州民筑羅城,方八十里,人苦其役。其子從訓,尤兇險,既殺王鐸,魏人皆惡之。從訓聚亡命五百馀人為親兵,謂之子將。牙兵疑之,籍籍不安”[32]。相比于牙兵,親兵的私人屬性更強,貼身親隨,出入臥內,“(樂從訓)又聚亡命五百人,號‘子將,出入臥內”[33],以保護主帥安全為主。但牙兵和親軍與主帥的契約性和利益性更強,他們與主帥的關系并不比普通兵士與主帥的關系親密多少,與主帥的矛盾沖突也時常爆發。他們的產生既是藩鎮內部動亂頻發的產物,同時也加劇了藩鎮內部的紛爭和不穩定性。張國剛認為,大部分的藩鎮內部動亂基本上是反暴性和嗜利性相結合的產物。[34]
雖然牙兵和親兵的成分復雜,其與主帥的關系也不穩定,但其最初都是由主帥自己招募,以維護自身利益為目的所組成的軍隊,與部曲最初的軍事職能存在相似之處,是部曲重新發揮軍事職能的反映,是武裝部曲的一種演變形式。同時,牙兵和親兵與主帥之間關系的變化也反映了部曲特別是武裝部曲身份的變化,其私屬性質在逐漸減少,對其之后退出歷史舞臺也有重要影響。
藩鎮軍隊與傳統的武裝部曲之間也存在明顯的差別,一般意義上的部曲家兵亦耕亦戰,大多數擁有農業生產和武裝扈從的雙重屬性。而安史之亂后的藩鎮軍隊則大部分為雇傭職業兵,其成分來源復雜,且以當兵為其職業,將此與其生存和利益連接在一起,一旦其生命或利益受損,便會激起強烈的反抗。因此,這一時期的藩鎮軍隊相比于之前傳統的武裝部曲擁有較少的對其主的服從性和依附性,較多的利益性、斗爭性和對抗性。
四、小結
漢代的部曲是一種軍事編制,漢末以后專指豪強地主的私人武裝,到南北朝時期,部曲同時成為一種賤民的法定稱呼,唐朝時部曲身份發生了重要變化。《唐律疏議》中對部曲、奴婢、客女等有著詳細嚴密的規定,部曲是為合法的依附者。
地方豪強與中央政治力的聯系遠不如士族緊密,他們所擁有的地方社會勢力和影響力在安定時期,特別是在強有力的中央政府控制之下產生的作用有限。但在戰亂時期,這一平常潛在的社會勢力便會迅速崛起,以他們所吸收的私人武裝組成的部曲家兵為骨干,利用自己的社會控制力和影響力對中央政治力的重新統一造成影響,并有可能以軍功入仕。士族與豪族的遷徙變化對部曲的演變產生著重要的影響,其中所體現的武質性也逐漸減少。
唐朝中后期,均田制、租庸調制和府兵制趨于瓦解,以此為基礎的人身依附關系減弱,由于生產力和商品經濟的發展,租佃制和雇傭制發展起來,促進了部曲等賤民身份的轉化。安史之亂對社會形成了巨大的沖擊,之后的藩鎮林立更是對武裝部曲的演變產生了重大影響,在促使部曲再一次武裝化的同時,也使得其性質和屬性發生了變化。藩鎮主帥私募部曲為軍隊,以財物授私恩于部曲,部曲承恩而為主帥效命,主帥同時又以牙兵和親兵為倚助維護其利益,但又與他們之間形成了復雜且不穩定的關系,相互之間的利益性和對抗性要遠大于傳統意義上的服從性和依附性。武裝部曲的這一變化亦是整個部曲階層的演變的一個反應。
唐代部曲的武質性經歷了一個由多到少又再次增加的變化過程,但他們與其擁有者之間的依附性卻逐漸減少,同時利益性卻在逐級增加。
參考文獻:
[1]唐長孺.唐西州諸鄉戶口帳試釋[A]//敦煌吐魯番文書初探[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83:202-203.
[2]李伯重.唐代部曲奴婢等級的變化及原因[J].廈門大學學報,1985(1):103-110.
[3]韓國磐.隋唐五代時的階級分析[A]//隋唐五代史論集[M].北京:三聯書店,1979:72.
[4]張澤咸.唐代的部曲[J].社會科學戰線,1985(4):264-271.
[5]唐律疏議(卷6)//名例[M].北京:中華書局,1983:131-132.
[6]唐律疏議(卷12)//戶婚[M].北京:中華書局,1983:239.
[7]唐律疏議(卷17)//賊盜[M].北京:中華書局,1983:328.
[8]唐律疏議(卷22)//斗訟[M].北京:中華書局,1983:404-406.
[9]唐律疏議(卷25)//詐偽[M].北京:中華書局,1983:466-467.
[10]唐律疏議(卷13)//戶婚,載:“客女,謂部曲之女,或有于他處轉得,或放婢為之”,第256頁.
[11]韓國磐.隋唐五代史論集[M].北京:三聯書店,1979:73.
[12]李伯重.唐代部曲奴碑等級的變化及其原因[J].廈門大學學報,1985(1):106.
[13]李靖莉:《從吐魯番出土文書看唐代西州部曲》,《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7年第1期,第10-17頁。《再談唐代的部曲》,《濱州教育學院學報》,1999年12月,第5卷,第4期,第20-23頁。《唐代中原地區賤口部曲趨于絕跡的原因》,《史學月刊》,2002年第5期,第120-122頁。《唐代中原與邊地部曲比較研究》,《山東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50卷第6期,第106-109頁.
[14]毛漢光.中古統治階層之社會基礎[A]// 中國中古社會史論(第一章)[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3-32.
[15]毛漢光.中古士族性質之演變[A]//中國中古社會史論(第四章)[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70-105.
[16]舊唐書(卷67)//李勣傳,第2483頁.
[17]舊唐書(卷68)//程知節傳,第2503頁.
[18]舊唐書(卷69)//盧祖尚傳,第2521頁.
[19]舊唐書(卷58)//平陽公主傳,第2315-2316頁.
[20]舊唐書(卷58)//馬三寶傳,第2316頁.
[21]毛漢光.中古士族性質之演變[A]// 中國中古社會史論(第四章)[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86.
[22]新唐書(卷137)//郭子儀傳[M].北京:中華書局,1975:4603.
[23]新唐書(卷217下)//回鶻下,載:“安祿山反,劫其兵用之,號「曳落河」者也。曳落河,猶言健兒云”,第6141頁.
[24]資治通鑒(卷220)//肅宗乾元元年[M].北京:中華書局,2011:7171.
[25]舊唐書(卷120)//郭子儀傳,第3456頁.
[26]資治通鑒(卷220)//肅宗乾元元年[M].北京:中華書局, 2011:7175.
[27]新唐書(卷177)//馮宿傳,第5278頁.
[28]舊唐書(卷15)//憲宗下[M].北京:中華書局,1975:470.
[29]舊唐書(卷20)//(上)昭宗,第757頁.
[30]張國剛.唐代藩鎮的類型分析[A]//唐代藩鎮研究(增訂版)第四章[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42-59.
[31]韓昌黎全集(卷37)//贈太傅董公行狀[M].馬其昶,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582.
[32]資治通鑒(卷257)//僖宗文德元年,胡三省注云:“魏博牙兵始于田承嗣,廢置主帥率由之。今樂從訓復置親兵,牙兵疑其見圖,故不安。”第8494-8495頁.
[33]新唐書(卷210)//樂彥禎傳,第5939頁.
[34]張國剛.唐代藩鎮的動亂特點[A]//唐代藩鎮研究(增訂版)》第五章[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6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