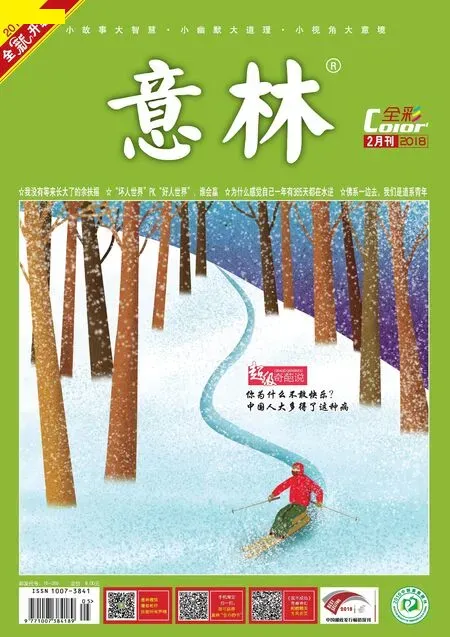送兒子去哈佛留學的前一夜
□ 何 江
2009年,我大學畢業,并拿到了學校本科生最高的榮譽——郭沫若獎學金。同時,我也收到了哈佛大學生物系的錄取通知書。不出意外,我成了村里知識水平最高的,也是第一個出國留學的小孩。
鄉下人對國外的印象并不明晰,哈佛是所什么學校也不一定弄得清楚。不過,大家聽到何家有小孩要出國留學后,都感到特別新奇。出國前的那一夜,父親邀請了村里的皮影戲藝人又演了一出《楊家將》,那是我印象中我們何家又一個熱鬧的夜晚。
母親顯得非常興奮,她的大兒子要去美國留學了,是村里第一個走出國門留學的人,她覺得臉上很有光彩,想讓兒子快去美國,好告訴她,那個陌生的國度究竟是什么模樣。她對美國了解得不多,只知道美國在地球的另一頭,美國人講一口她聽不懂的洋文。
她覺得知道這些已經足夠了,此刻,她在幫著兒子檢查行李箱,保證兒子帶齊了所有該帶的物件。
“兒子,你帶針和線了嗎?我在你包里沒看到啊?”
“沒有,媽,帶針線干嗎?”
“你衣服要是在那邊壞了,好自己補一補嘛。這么重要的東西怎么能夠不帶過去呢?”
“我不會自己補衣服,要是同學知道了,那多沒面子。”
“面子面子,你就知道這些虛東西!要是衣服掉扣子了,隨手補補又不花時間,哪會有人笑話你?帶著吧,肯定用得上。”
“好吧,你塞進去,但你放了也沒用,我不會用的。”
母親從衣櫥里拿出了幾團棉線,有黑色的、綠色的、紅色的、白色的……她每團棉線上都別上一根細針,然后打包好放進了我的行李箱。
“兒子,你行李箱里的布鞋呢?昨晚我給你檢查箱子的時候還在,怎么現在不在了?”

“我早上拿出來了。我的行李箱已經裝滿東西了,再裝就會超重。”我把布鞋從床底翻出來,不耐煩地解釋著。行李箱中其實還能裝不少東西,只是我不想要這幾雙土氣的布鞋。
“一雙鞋能添多少重量?兒子,把鞋放進去,都放進去。鞋是我今年春天的時候新做的,棉花也是新采的,肯定保暖,你帶過去穿著一定舒服。”
“那就放一雙吧,我到美國不會穿布鞋。”
“還有,你要不要帶點吃的?你常抱怨大學食堂的菜不好吃,沒家里做的味道正宗。是不是該帶點?我特地到田里捕了不少黃鱔、泥鰍,用陳年的木頭鋸出的木屑熏好了。你聞聞,有一股很香的木材味道。要不要放些進去?哦,對了,家里的剁辣椒你最愛吃,在美國不一定有,也帶幾瓶吧。”
“媽,我不是跟你說了嗎?飛機上不允許帶吃的,尤其是肉,過海關的時候查得嚴。”
“那些烘干的長豆角、黃瓜皮、白辣椒和蕨菜總沒問題吧?你都塞點,免得沒帶過去你又后悔。”
去美國那天,一大早我們一家人吃完早餐,圍坐在一起聊家常,可是話剛起了個頭,卻又撂了下來。一家人沉默地坐著,等待從村里進城的汽車。母親似乎有什么話想和我說,但欲言又止。
她再次拉開我行李箱的拉鏈,簡單地查看了一下,又合上了,然后走進廚房,倒了一杯溫水,遞給我。我搖了搖頭,告訴她我已經喝飽了水。“你就不用瞎忙活了,干嗎不坐著?”我的語氣中帶著幾絲不耐煩。于是,母親把水放下,望著窗外晨光照耀下的村落。
汽車站很簡單,就是在路邊上立了一塊牌子,牌子旁邊是一條很深的水渠,初秋時候,由于上一季水田的泥巴滲入,水渠現在已經灌滿了泥土。菱角在這個季節剛好成熟,深綠的菱角葉上沾著露水,在清晨的微弱光線下,看起來十分漂亮。
一家人在家里等得不耐煩了,便提著行李來到汽車站旁。幾個鄉鄰背著鋤頭在田埂上除草,看著我們一家人都提著行李,就問誰要遠行。
“我的大兒子。”母親的口吻里充滿了自豪,她告訴他們,她的兒子要去美國,那個只在電視新聞里聽說過的國家。“兒子,我當年織漁網的時候,看著你和你弟在漁網里打滾,以為你們以后會以打魚為生。可我沒想到,你讀書讀得走出了國門。”
很快,一輛汽車拖著揚起的灰塵,駛入村中的公路。我朝汽車看了看,而母親在此刻卻將視線移到了我的身上。她想笑,畢竟這次遠行能夠給我一個更好的未來,作為母親,她應該為兒子的未來祝福。
可是,母親又意識到這駛來的汽車將把她兒子送到一個她不熟悉的地方,在未來的很長一段時間里,她都見不到兒子,這讓她有點傷感。
母親并不知道該說什么,那些動情的離別贈言,她只在電視劇里看過,在現實中她什么也說不出來。
她笨拙地握住我的手,盡管這個動作在她看來顯得那么不自然。我顯然也感受到了這份不自然,故意說要去提包,順手甩開了她的手。母親大概明白我的意思,于是,她也彎腰去幫我提包。
母親和我就這樣提著本可以放在地上的包,靜靜地等著汽車到站。
“兒子,你還記得菱角是什么味道嗎?現在正是采菱角的時候。”母親指著水渠邊的菱角問。
“當然記得呀。這是小時候我們經常吃的零食,怎么會忘了呢?”我笑了笑,“我上次吃菱角還在上大學之前,一轉眼已經過去四年多了。”
“你想不想吃幾個菱角?美國吃不到。”
我點了點頭,但感覺來不及了。
“你等等我,我這就去弄幾個來。”話音還沒有落,母親放下包,朝水渠邊跑去。她趴到地上,想用手抓住靠近岸邊的菱角葉,可她的手不夠長,怎么也夠不著。我看了便阻止道:“我下次回來再吃吧。”
母親根本聽不進我的話。
乘客已經陸續上了到站的汽車,我一個人站在車門邊,看著母親正努力拔菱角的背影。
“媽,算了吧,我上車了。”我喊著。
母親急了,她站了起來,脫掉鞋子,抓住水渠旁邊的草,一點點滑進了水渠。
“嘩啦!”母親踩進了水渠的深泥巴里。我聽到響聲,驚訝地回頭,只見母親在齊胸的泥巴水里走著,碰到水渠里長熟了的菱角便抓進手里,扯掉菱角葉,在水渠里洗了洗,便朝著岸上扔了過來。
“兒子,快撿幾個大的趕緊上車去。這司機也真是性急,又在按喇叭了。別看我,朝我看干啥?我待會兒回家換身衣服就好了,你快點撿幾個菱角上車去!”
我滿眼淚水地站在車旁,看著還在水渠中笑著的母親。
我想告訴母親自己有多么愛她,可是,鄉里孩子很少會用“愛”這個字,即便是母子之間。我不知該和母親說些什么,撿起菱角,在褲腳擦掉了沾在菱角上的泥巴,用牙齒咬掉了硬殼,把菱角掰成兩半,跑到母親身邊,遞了一半給她。母親站在水里接過去咬了一口,我站在岸上咬著帶汁的另一半菱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