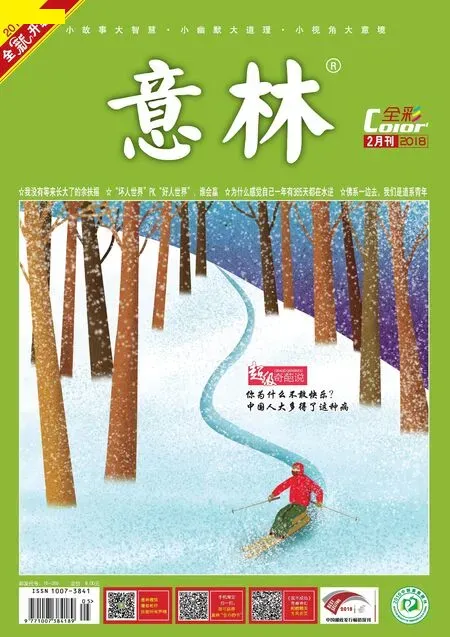微小的圓滿
□ 陳思呈
大概一個月前,茶館里來了一個朋友,說幫忙修建籬笆。我們的茶館里,很多東西是自己修建的,比如有兩個茶臺:一個是砌好水泥臺往上鋪紅磚,一個是將枯萎的玉蘭樹鋸成幾截,最粗一截作為茶臺,另幾截作為凳子。
另外還有很多花盆花架都是DIY的,今天輪到籬笆了。
這位虎虎生風的朋友,在角落里掏出一大捆竹子,又從自己的牛仔褲兜里掏出一把鉗子,又像變魔法一樣變出一小堆鋼絲來。他的褲兜就是他的工具箱。
他用鉗子把竹竿三下兩下全裁成一米長短,這長度其實就是籬笆的高度。
直到籬笆做好我也沒覺得這活兒有什么難度,但我突然意識到籬笆是一種很美的事物。它有疏有密,起到一種間斷,但不完全隔絕的作用。
做完籬笆后,我們開始在空中和墻上做另一攀架,可以讓藤蔓類植物攀緣生長。花木正漸漸蔥蘢,這個過程,我總是想到杜甫的草堂。
杜甫的草堂,也是有籬笆的。在成都的郊區,這個籬笆對鄰居的意義,不像墻那樣生硬而隔絕,而有一種便于溝通和邀請的意味。所以杜甫寫:肯與鄰翁相對飲,隔籬呼取盡余杯。他和鄰居,在那個籬笆那里交換酒杯。這樣的細節,對于漂泊一生的杜甫來說,很是溫暖。

上元元年(公元760年)初,杜甫來到成都,當時他五十多歲,古人壽命短,這已算是中年接近晚年的歲數。他在成都一待就是幾年,中間也去梓州、漢州等其他地方避亂,但總的來說,相比他之前和之后顛沛流離的人生,在成都這幾年算是其安逸時光。
到成都后的杜甫首先建了個草堂,由他表弟王司馬贈資。這草堂非常出名,它不豪華,連結實都談不上,所以后來被秋風一吹,就透風漏雨了。但這個草堂的意義很大,安慰了詩人在祖國大地上漂泊大半生的疲勞身心。
在那段時間,他像記裝修日記一樣寫詩。寫他如何去跟綿竹縣令討竹子,如何跟另一位縣尉要榿木苗,又去跟誰要瓷碗,東家要一點,西家要一點,這行徑雖然有點饑貧寒感,卻更有生機勃勃的建設之趣。
最有趣的是,建成之后他還在草堂前劃了一塊地,專種草藥。他也未必是堅實的中藥愛好者,種草藥的目的之一是做回禮用,常有朋友接濟他糧食,他沒有其他可以回贈的物品,只好用自己種的藥草。
然后他就開始了他在這個草堂的幸福生活。我們看到他在這草堂里設置家宴:請他吃自己常吃的糙米飯,看到他家的娛樂,老妻稚子都在干啥,還認識了他的左鄰右舍,知道他和誰相談甚歡。
這段時間的杜甫,詩歌里出現了與他之前沉郁風格很不同的活潑輕盈,比如:“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朵萬朵壓枝低。流連戲蝶時時舞,自在嬌鶯恰恰啼。”音樂感仍然存在,是很流暢的音樂感,“千朵萬朵壓枝低”還有天真。這詩里的情景也很天真,慣以沉郁形象出現在中國文學里的杜甫,此時站在“黃四娘”家的門口,也不進去喝茶,看樣子也不像是特意來拜訪,更像是無意路過。
這時的杜甫,與拾橡子充饑、在羌村秉燭飲泣的杜甫是何等不同,這是一個從博愛回到差等之愛的杜甫,而這暫時的圓滿,很可能得益于這座簡陋草堂。
不管是杜甫還是我,在我們的一生中,在我們微小的空間建設我們的家,也算是我們微小的圓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