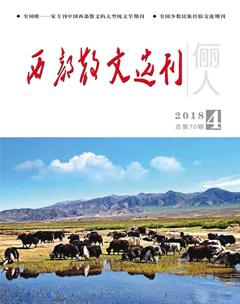塞外白楊
王建忠
故鄉,已是漸行漸遠,離別二十年了。可故鄉的那些人那些事,總在我的心田縈繞,總是叫我不能忘懷。特別是我家老屋院子里的那棵白楊樹,每當我回鄉探親、祭祖時,遠在十幾里路的地方就能看到,它像一面迎風飄揚的旗幟巍然挺拔在廣袤的賽外荒原,招示著我,指給我回鄉的路。
記得那是一九六二年,父親為我們蓋起了新房。一排三間的大正房,和東鄰趙二仁、趙保兒、王七十六,四家人家墻屋相連,形成了很長的一排,在當時的環境下,確實顯得氣派。我們幾家也是村子里最重要的戶子,一色的貧農人家,父親是多年的生產隊長,趙二仁是多年的大隊書記,趙保兒是二仁的哥哥,是村子里最富有的,王七十六是我本家的一位長輩,又是貧協主任。大家相處的和睦親切,在我的記憶中一直也沒有過矛盾。
一九六三年,父母在院子里種下了這棵楊樹。那時,村子里一棵樹也沒有,因為那里的自然條件差,不僅風沙大,而且干旱無雨,更沒有地下水,人們吃水都困難,要專人趕著畜力車到十幾里遠的地方去拉,樹木的成活率幾乎為零。父親不知從哪里得來的這棵樹苗,種下了也就不管了,是母親看著心急,便把洗臉水、洗碗水積攢起來澆到樹坑里,有時也把水甕底積垢了的水從甕底淘洗出來澆灌,因為當時要是浪費了人畜還能飲用的水是會受人們批評的。可就這樣,那棵樹在母親的照料下,竟存活下來,長成了后來的參天大樹,那粗壯的樹桿現在已是倆個人合起來才能圍回來。看到母親種活了樹,相鄰的幾家也在院子里各種了一棵,村子里也有人種了些,可成活的很少,有些成活了也都沒有趕上這棵樹高。
那時的我年齡還很小,我們國家又實行了人民公社,集體所有制,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所有的土地、耕畜、農具,都收歸集體所有,大家都集中在一起生產勞動。秋天下來,農作物都拉到隊里的場面里,打下糧食來,要先保證送交一部分公糧,然后留足了飼料、籽種,剩下的才能分給社員口糧。最好的年頭每人也只能分三百六十斤粗糧,節余還是要上交。可在我的記憶中,從來沒有分過那么多,而且是山藥、菜類都折算在了口糧里邊。要是遭遇災荒,就全靠國家給撥供應糧來維持。
父母生了我們六個孩子,其中只有我一個是兒子,排行老四,其她都是女兒。那時大姐年齡最大,多年前已聘給了離家很遠的杭錦旗一家貧苦人家,日子過得也很苦。我和二姐、三姐、四妹、五妹和父母一起過日子。那時父親在農民中還是算最有見識的農民,父親經常說的一句話:家有黃金用斗量,不如送子上學堂。就是在那最為困難的時期,還是送我和倆個姐姐去上學。那時的上學條件也很差,最近的大隊學校離我們也有六七里地。給我們教書的老師只有小學二三年級文化水平。就這樣的學校也沒有條件能立得住,還是被撤點并校,二姐、三姐因家庭困難最后還是失學了,我轉移了三個學校才讀完小學。以后五妹到了上學年齡,家里生活條件也稍好了點,父母讓她也上了學,只苦了四妹,一天學校也沒進。
那時家里很窮,很少能吃到肉。記得有一次,父親拿回了一條羊腿,放在盆子里,這可是全家最高興的事了。大人們去勞動了,我們姐妹幾個坐在一起,大家都想吃。那時只有三姐最聰明,她不知從哪里取來一個刀,在羊腿上割了幾塊肉,又不知在哪兒找來一點蕎面和起來,把肉包在面里,每人一塊,放在柴火爐灰里為我們燒著吃。當時給我的一塊是最大的,不過也沒有一個餃子那么大。吃完了也沒吃出個味道來,還想吃。可二姐早就把肉藏起來了,說沒了,不能吃了,再吃就吃完了,還有爸媽一口也沒吃呢。我們都提著一顆心,不知父母回來會怎樣說,大家都覺得我們犯了錯誤。中午了,父親還沒回來,母親回來了,因為她要提前做飯。一進門大家都沒有一個敢作聲。母親還沒進門就在院子里抱上了柴,回來首先生上火,口里對我們說,我走了你們幾個沒害人吧,怎一個說話的也沒有?又看到盆子里的肉不見了,問放到哪兒了,中午要給大伙兒燉著吃。二姐大些,一邊叫三姐去取肉,一邊對媽媽說,弟妹們都愛得不行,燒得吃了點。其實這肉二姐是一點也沒吃的,當時她說自己不想吃。這時三姐取回了肉,她把割過的地方迎下,沒割過的地方迎上讓母親看,母親笑道,怎不見有割過的痕跡?翻過來看,才看到并沒割了許多,笑道,“這一定是你出的鬼點子。”說著還在三姐的頭上輕輕地拍了拍。三姐便指著我,“是他要吃的,這不怨我。”大家都知道,做為母親唯一的兒子,母親是不會怨我的。其實那肉根本不是我提議吃的,我也不推托不揭穿,只是默默地看著母親。母親沒有罵我們,只摸著我的頭對大家說,等咱過上了好日子,媽天天給你們弄著吃。就這樣,我們的童年在不知不覺中就度過了。童年給人的記憶總是美好的,幸福的。
后來,我真的參加了工作,成了國家的人,當上了人民教師,成為村里最受羨幕的人。那時,全大隊只有我和五妹是國家人員,父母也常把我們當成了一種驕傲,逢人都在夸我們。我和妹妹也不負眾望,嚴于律已,努力工作,總是學校里的先進教師。
隨著時間的流淌,院子里的那棵白楊樹也長高了。由于當時種下樹苗時,樹苗是一個多枝的,當時又沒舍得砍去些枝杈,因此那樹到長大的時候,樹頭變成了一個圓形的類似于雨傘的形狀,遠遠望去,是一棵既雄偉又漂亮的參天大樹。可隨著時光的流逝,父母的年齡也越來越大,父母的臉上皺紋越來越深,手上的老繭也越來越厚了。等到改革開放的時候,父親已是六十多歲的老人,可就那樣,父親還是堅持在地里勞動,春種夏鋤秋收冬儲,一年之內也沒個閑的時候。在父親的努力下,家里過上了豐衣足食的好日子。我在工作之余也經常利用星期天和假期回家幫父親干活兒,因此也成了農業上的好手,耕種鋤摟割樣樣都會。
一九八七年,我和五妹回家和父母過年。那時父親都已七十多歲,在大家的勸說下,父母終于同意搬到我工作的地方居住。我決心讓父母擺脫繁重的體力勞動,讓他們過兩天輕閑舒服的日子。父母不忍心丟下那居住多年的老屋不管,更不想讓自己的那份承包地荒廢,母親心里也放不下院子里的那棵白楊樹。為了讓父母安心,更是生活的需要,我又承擔起了家庭農業地上的全部勞動,星期天便成了我最忙最累的勞動日。為了不讓老屋荒廢,我便讓同村的二姐家搬過來居住,她們家的房子沒有我們家的大些,這樣既解決了她們的住房需要,又解決了照看我家房子的事情。那時二姐已是四個孩子的母親,由于操勞過度,身上染上了重病,就在那一年含淚而去了。二姐去的時候,只有大女兒一人成家,其他兄弟三人還都未成年,最小的只有幾歲,她給孩子和我們所有親人留下的是深深的痛。
父母到了學校所在地和我一起住了,我們一家七口擁擠在一個只有四十多平米的小屋二百多平米的院子里,可我們都感到幸福。我和妻子每天忙于學校里的工作,孩子們都去上學,家里只留下了父母。父親很快適應了當時的環境,和附近年齡相當的人們聊得很好。可母親卻沒有多少認識的人,總感到孤獨,后來變得精神壓抑,說話不多。就是在這里,父母度過了他們幸福的晚年。
一九九三年,父母都去世了。我因工作上的調動,全家搬到了鎮里去住。走時,我把全部的房產都給了外甥,就是二姐的大兒子。可院子里的那棵白楊樹沒給,我對外甥說,你要好好地為我照看好這棵樹。我覺得那棵樹有我童年的記憶,有家庭和社會變遷的痕跡,更有父母留給我的思念。每年清明我都要回去上墳,順便看看老屋,看看那棵白楊樹。老屋幾經滄桑已是破舊不堪,院子里也積滿了沙土。院鄰們和父母年齡仿佛的人,大部分去世了,他們的后代有的搬走了,有的蓋起了新房,他們的孫子輩見了都不認識了,村子里已是面目全非了。只有那棵白楊樹卻雖經歷了近半個世紀的風雨,可還是那樣的英姿挺拔,枝繁葉茂,令人神往。
——選自《長河》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