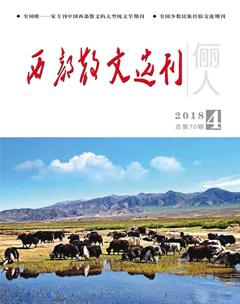電影情結
陳俊杰
情結對于每個人都是至關重要的,它可能深深地扎根在你的心底,也可能改變你一生的命運,甚至與你的生命息息相關,情結沒有了,可能就會失去生存的意義。這絕對不是危言聳聽,也不是夸大其詞,情結就像人類的靈魂,失去靈魂的人如同行尸走肉,可以形象地說,情結是人類靈魂的主板。
我的情結與別人好像不同,甚至有些另類。在文化單一枯燥的歲月里,尤為突出。七十年代后期,全國文化市場上,除了八大樣板戲之外,一些走俏的電影都是比較經典的老片子,十五六歲的我,對電影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特別是對家鄉小鎮的電影院有了情結。
我出生在北方偏僻的小山村,名叫小荒頂子,這里是山區,參天的大樹看不見太陽,踩一腳枯葉子,就能陷到膝蓋。怎么起了個這樣的地名?我也不知道。我家兄弟三個,我排行老大,手下跟班的只有倆個弟弟,二弟小我兩歲,三弟小我五歲,媽媽是大城市的姑娘,聽父輩人講,爸爸是把媽媽拐到了這個小山村成親的,至于父親用了什么手段,我聽的是支離破碎,沒有完整的故事。我九歲那年,父親犯了錯誤,被判刑入獄,媽媽帶著我們兄弟三個改嫁,來到了我家鄉的小鎮。
小鎮電影院坐落在鎮子中心的繁華地段,三層樓高的馬尾式建筑,水刷石掛面,兩側是售票口,中間是入場大廳。一毛錢一張的兒童票,讓我望怯生畏,看到巨幅電影海報,怎么也挪不動步了,腳底下像釘了釘子一樣,為了能混進入場大廳,真是煞費苦心。為了能弄明白電影票是什么樣子,窺視了很多孩子手里的電影票,一張十公分寬的白紙上,印制著鮮紅的圖案,“兒童票”三個字格外醒目,油印版印刷而成。電影已經上映許久了,我仍然徘徊在電影院門前。收票員出來倒廢票屑,這個機會絕不能放過,我一路跟到了垃圾堆附近,等收票員離開后,我迫不及待地把一些廢票屑摟了起來,裝進了兜里,頭也不回地回家了。
功夫不負有心人,經過小半天的拼湊,一張完整的兒童電影票終于拼湊成功了。開始照貓畫虎了,紅色油墨只能用紅鋼筆水代替,此時的我,完全一副認真鉆研的狀態,比寫作業的態度端正多了。經過數小時的反復勾畫和修改,一張以假亂真的兒童電影票終于面世了,我興奮不已,接下來就是實地體驗了。我的倆個跟班弟弟都自告奮勇,誰都抵御不了電影的誘惑。二弟手里拿著我畫的電影票走向收票大廳,我躲在遠處窺視,心里“噗通噗通”地亂跳,好像有人知道我造假似的,一旦有人沖過來,我肯定會丟下跟班的弟弟逃跑的。事情并沒有像我想的那么糟,二弟已經安全通過收票員的審驗,順利進入了放映大廳。高興之余,又多了一絲惋惜,為什么自己不敢去試試呢?
畫電影票成為了這段時間的主攻方向,剛剛上二年級的我,因為母親又填了個小弟弟而輟學,帶小弟弟玩兒成為了我的主業。小弟弟睡覺了,我就畫電影票,終于如愿以償地看上了電影,我清晰地記得,當時看的是彩色故事片《平原游擊隊》,電影院每天放映七場,我一口氣地看了七場,忘記了吃飯,忘記了帶小弟弟,結果被繼父修理了一頓……可是,在我的內心世界里,這次電影院之旅卻終身難忘。電影一詞已經深深地烙印在腦海之中,生活當中,許多經典的電影臺詞成為了我的口頭禪,電影改變了我的生活方式,改變了我的生活邏輯,改變了我的思維……
歲月在時光中蕩漾,高中畢業后,我又回到了闊別已久的小荒頂子,命中注定要在這里度過自己的青春了。離開小鎮的時候,我小學還沒有畢業,親生父親提前釋放出獄了。母親帶著我那倆個跟班弟弟回到了親生父親身邊,我自己躲出去十幾天,不想回親生父親身邊,我驀然意識到,雖然父親比繼父年輕許多,但在我的心目中,他還是那么陌生。我舍不得離開自己帶大的小弟弟,繼父又沒有明確態度收留我,無奈,我孑然一身踏上了二十多公里的山路,懷著忐忑的心情去面對自己親生父親。
二十多公里的山路,大約走了半天的光景,一邊走腦海里涌現出許多的電影臺詞,在很多英雄人物的激勵下,我的膽子漸漸地壯了起來。傍晚的時候,我回到了他們的身邊,一種時刻準備獻身的意識驅使著我,所以沒有害怕父親打我。父親破天荒地沒有打我,而且把我摟進了被窩里,雖然很疲憊,但是我還是警惕著父親,從他那狡黠的眼神中,我意識到了潛在的危機感……渾渾噩噩的夢幻伴隨到天亮,我已經可以去上中學讀書了,讀書是一種解脫,可以擺脫邪惡的父親,盡管回到了親生父親身邊,可我從來就沒有認可過他,直到結婚的那天,我才怯生生地喊了一聲“爸”。這種作秀的感覺,我自己都感覺惡心,明顯是給媳婦做樣子嘛!
因為經常去探望繼父和小弟弟,常常成為父親發泄的對象,他狠狠地打我,我從來也不屈服,人不可能沒有感情,我認為自己沒有錯!沒有錯為什么會經常挨打?自己也解釋不通,后來,小弟弟不幸患病夭折了,我的心情如同斷線的風箏,搖搖欲墜。從那一刻起,我變了!變得沉默寡言,變得內向了,過早地開始思考問題了。
自以為才華橫溢的我不甘心在農村生活一輩子,雖然這里也有電影放映,但露天電影和電影院有了天壤之別,我要走出農村!這是我心底中的吶喊!
八十年代的農村,生活條件還是比較艱苦,全家人睡在一鋪炕上,勞作一天的全家人吃完晚飯,就躺在炕上睡覺,如果睡不著,可以偷偷摸摸地聊一會兒,前提是不能點燈,高額的電費必須每個人帶頭節省。晚飯后,我自己早就準備就緒,自制稿紙和手電筒已經帶入被窩中,把被子蓋到頭上,遮個嚴嚴實實,打開手電筒開始寫作。所有的小說、詩歌、散文還有電影劇本,都是在被窩里誕生的,直到第一篇小說在省報上發表,全家人才對我另眼相待,破例讓我多用電一個小時。發表的這篇小說幫了我的大忙,父親終于能正視我的存在了,不再罵我是叛徒了,有時候,也在人前賣弄一下我的文采,直到我真正走出了家鄉,來到鄉政府上班了,我變成了全家人驕傲的資本。
當初,對電影的情結也許是抽象的,雖然非常酷愛電影,但是對電影了解甚少,懂一點也是一知半解,這個情結改變了我的人生軌跡,也幫了不少倒忙!尤其是在戀愛和婚姻中突出。鄰居曉琴是我非常鐘愛的姑娘,有一次,我鼓足了勇氣向姑娘家求愛,也許是怕姑娘曉琴拒絕,竟破天荒地跟曉琴說:“等我電影劇本拍攝了,我們就成親?”曉琴竟然同意了。我興奮的不知所措,拼命地創作電影劇本。幾年過去了,我的電影劇本還是石沉大海,曉琴也變成了別人的新娘,我也有了心愛的女兒。
進入九十年代后,在當地我已經是小有名氣了,已經發表了許多文學作品,可是對電影的情結越來越濃郁了,而且有增無減。我熱愛白山黑水的長白山家鄉,更熱愛養育我成長的這片沃土,無論在任何工作崗位上,創作電影劇本成為了我的第二職業。這時候,我已經完全弄明白了,拍攝電影是我們國家的壟斷行業,半輩子弄明白的事情,成了霧里看花。
二十一世紀以后,隨著電影市場的改革開放,壟斷資源變成了全民行業,所有人都可以實現自己的電影夢想了,我當然也沒有例外。我的第一部電視連續劇在省臺播出的時候,我已經年過半百,而且在異地他鄉。為了孩子的生活,我放棄了白山黑水像吐谷渾一樣,從遼東牽棲到大西北的青藏高原青海,偶然的一次機會,為別人創作了一部電視連續劇,也完成了自己的夢想和情結。這一次的偶然,讓我完全了解了影視,也走進了影視,我再一次地放棄了所有的文學創作,專心致志地攻克電影。經過不懈的努力,現在真正成為了電影人,也創作了許多電影劇本,拍攝了八九部電影作品。情結找到了歸宿,跨越半個世紀的電影情結終于釋懷了。
第二家鄉青海與東北家鄉截然不同,青海如同高大的巨人一樣,頂天立地,有著博大的胸懷,連血管都赫赫有名,什么瀾滄江、長江、母親河都叫得那么親切,她昂首挺胸走出藍天。
電影情結定位了我的人生軌跡,雖然有些艱辛,但還是如愿以償了。回眸反思的剎那,讓我浮想聯翩……現在的情結是什么?我曾無數次地反問自己。現在的情結是責任,對自己的情結負責任才是最根本的理由。
——選自2018年第1期《荒原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