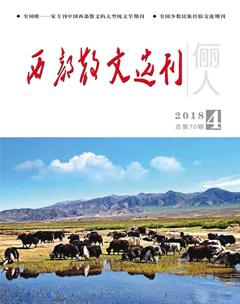小石橋
何剛
叫小石橋的地方早已經(jīng)沒有了橋。
那時候,我考進(jìn)紅專中學(xué)(現(xiàn)在的一中)讀初中。剛好是星期六晚上,就在北街花五分錢看了電影《畫皮》,回宿舍后,不知是興奮還是害怕,我沒有能夠睡踏實;剛好,離著我們在城河邊的宿舍一百米開外連夜建蓋商場,攪拌機(jī)咣當(dāng)咣當(dāng)?shù)穆曇簦秃碗娪暗目植酪魳芬黄鹪趬衾镆嗷靡嗾娴捻懼?/p>
好像也就是那個時候,城里的不知武裝部抑或哪個單位撘建的簡易石橋就被取締,總之,水泥就把這一段城河覆蓋,發(fā)展成一條數(shù)十米的小街。小石橋就成了街名。
十多年前的一個夜晚,我們在小石橋燒烤串喝啤酒,聽見旁邊的人爭論:小石橋?橋在哪里?
前邊呀。
哈哈,那叫東門城河橋。
又怎么能叫街呢,這么短。
那十字街不叫街嗎。
那倒也是,東西南北四條街交匯,那里就叫十字街。
現(xiàn)在回想,首先擺上小石橋街頭的是看書攤,成排擺放數(shù)十上百冊黑白版連環(huán)畫,四周放置條凳,兩分錢看一本。然后是修鞋匠、配鑰匙,不知哪一天,有了一個米線攤。
出學(xué)校大門,左轉(zhuǎn)前行一百米,走上小街,花七分錢吃一碗涼米線;或者穿過小街,再左轉(zhuǎn),就進(jìn)了東街,走幾十米就有食館,兩角錢可以吃一碗小鍋米線,一開初,只能在每個月發(fā)放兩塊錢的助學(xué)金時吃一次,在讀書的六年時間里,條件逐年好轉(zhuǎn),后來,一星期吃三五次也是有的(當(dāng)然,價錢也在不斷上漲,漲到現(xiàn)在是五塊);或者直接穿街而過,走上城河埂,用不了幾分鐘就走到北街,那里吸引我們的是大禮堂,禮堂兼做了影院,似乎有三十排,每排三十個座位。在初中三年,最記得的是電影《少林寺》和《白蛇傳》,《少林寺》看了六七場,看到完整記住臺詞,放映《白蛇傳》時,母親安排我?guī)痛謇锶伺抨犢I票。在我的記憶里,縣城自此外沒有再出現(xiàn)這樣的看電影盛況。
那時候的電影院管理算不上嚴(yán),偶爾我們也能蹭電影看。但很害怕一個叫做老青苔的來查。老青苔身材高大,一只眼睛像覆著一層白膜(雪盲癥),看著令人心慌,手里還捏著一只超長的亮閃閃的鐵皮手電,似乎一手電就可以把我們拍翻在地。一直到最近幾年才知道,老青苔是那個時代的官二代,他到電影院純粹是出義工,不領(lǐng)一分錢工資。斯人已經(jīng)過世數(shù)年,只是感喟現(xiàn)在還能找!
小街在歲月中繁華。那些攤點搭起五色布的棚子,有鍋有灶,涮菜、烤羊肉串,還有專門賣豬下水的,也有豆花、紅糖稀飯,賣紅糖稀飯的是個老頭,啞著聲音口頭廣告——糖稀飯啰,趁熱乎!讀高中時,在這些攤點上留下無數(shù)記憶。最近兩年,在三月會會場上,幾個朋友都愿意在街邊的棚子里吃一碗羊湯鍋,喝一杯酒。是否這樣的情結(jié),年少時就已經(jīng)埋下。
到我外出讀書回來,九十年代的這一條小街已經(jīng)無比熱鬧。商場拆了院墻,蓋了店鋪出租,一溜小食館,夾雜音響店,最當(dāng)頭是一家衣鋪,賣襪子賣短褲,店主明明是一個女子,不知如何的就得了個老公鴨的綽號,名號很響,大人孩子都這樣叫她,我們叫一聲,她也回聲“噯”,不見惱。
小街開始蕭條,大約在七八年前,吃的攤點入了門店,只剩下修鞋和配鑰匙的,數(shù)年前,一棵樹下又增加了一個經(jīng)營銅錢和老舊玉石一類的攤點。
現(xiàn)在棚改,一個占地六百畝的袖珍老城消失,小街也即將壽終正寢,那些食館,包括老公鴨的店鋪已經(jīng)和四條老街一起拆成廢墟。那天我去看,街口樹下有個婦女支著一個煤爐,溫著一鍋茶葉蛋,沒有一個顧客。
我在廢墟上轉(zhuǎn)了一圈,依稀還能辨出東街和西街我吃了無數(shù)年的兩家米線館。紙板頂棚上浸潤油煙,點點斑駁一片黑烏,地面潮濕,滿屋煙火味的米線店消失了。因為曾經(jīng)常到位于西街的文聯(lián)去,這幾年就成了西街米線館的熟客,他家搬到寬敞的繁華街道繼續(xù)開店,我去吃了一次,但已經(jīng)沒有了過去的味道。
吸納數(shù)百年人間煙火的老地方,已然仙風(fēng)仙骨,豈是青蔥事物能比!
懷舊一條小街,懷念那些朝暮四季的人間煙火。
——選自作者網(wǎng)易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