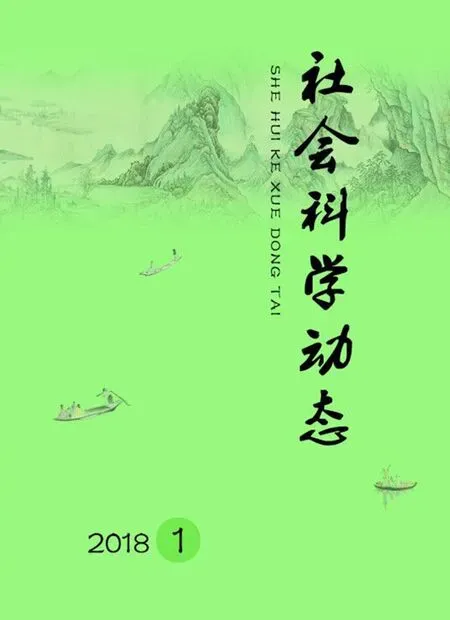以理性探尋純凈的詩意
——羅振亞詩歌批評與創作探微
王巨川
在中國新詩研究領域,在以孫玉石等先生為代表的前輩學者開辟的新詩研究之外,作為第三代詩歌研究者的羅振亞先生,其詩學理論的影響及他對當代詩潮、詩人的批評無疑是一座重鎮。振亞先生多年在詩歌研究領域的浸染,再加上他作為詩人所特有的敏感與敏銳,使他對中國現代詩歌的發展脈絡及其思潮、詩派、詩人了然于胸,因此他的詩歌理論研究范式及評判風格對許多同仁與后輩都有著積極的影響,同時對當代詩歌批評的健康成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早在北方文藝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 《中國現代主義詩歌流派史》書序中,呂家鄉先生就以 “理性的閃光,感情的激蕩”①來贊譽振亞先生在詩歌研究領域的獨特風格。他還認為羅振亞 “帶領讀者進入現代派詩歌的本體世界去作精神遨游,再加上他的意興酣暢、文采斐然的表述,使他的論著氤氳著沁人心脾的詩意”。②筆者以為,以振亞先生為代表的這一代詩歌研究者,大都有著自己較為獨特的治學理念和研究風格, “感悟理性”與 “純凈”的精神旨歸無疑是羅振亞在治學與創作中較為重要的風格特征。
一、以“感悟理性”為基石的詩學理論批評
振亞先生30年前少年出道,便在詩歌創作與研究中成為令學界矚目的雙棲型學者。不張狂的性情與耐得住冷板凳的沉穩,使他在30余年的詩學探索之路中著述頗豐。比如 《中國現代主義詩歌流派史》(1993年)、 《中國三十年代現代派詩歌研究》(1997年)、 《中國現代主義詩歌史論》(2002年)、 《中國新詩的文化與歷史透視》(2002年)、《朦朧詩后先鋒詩歌研究》(2005年)等,每一部著作出版后都能在學界引起強烈反響,成為引領當代學界研究新詩的重要標度和基石。在這些著述中,我們看到蘊含其中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他對于 “感悟理性”的思考與運用。
應該說,理性是每一個從事學術研究者的基本素養,但對于詩歌的研究與創作而言,真正的 “絕對理性” (Absolute Reason)似乎并不適用。我們知道,感悟思維歷來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最為重要的特征之一,而作為中國的詩歌來說最不可能的就是以 “理性”的思維來創作 (雖然有哲理詩,但詩歌的生成依然存在于感悟思維之中),特別是中國傳統詩學的生成更是以特有的感悟思維作為存在基石。雖然現代詩歌是在西方詩學觀照下成長起來的,但其在中國固有的語言形態、思維模式影響下,依然無法完全摒棄感悟思維的傳統。同時,如果從詩歌研究角度來看,完全承襲和運用感悟思維進行學術研究,似乎又無法完成現代學術的轉換。這里似乎產生了一個矛盾現象:研究者既不能以感悟的思維去研究現代詩歌的思潮、流派,又無法完全以理性思維觀照、闡釋詩歌文本中鮮活的、敏感的生命形態。
從振亞先生的多部著述中,我們看到他對于這個矛盾有了很好的調和,那就是 “知覺通感理性”的運用。詩學的研究必然要與其他文體研究采取不同的研究范式,要想在浩瀚歷史長河中辨析斑駁交雜的詩歌思潮流派、審美特征及詩人風格,則要求研究者既具有理論視野高度、理性知識體系,更應具備知覺通感的思維深度與體悟。也就是說,作為主體生命存在的研究者,首先應該是有感知的直覺存在,才能讓身為個體感悟的自己直面現實。莫里斯·梅洛—龐蒂曾說:“處境從不對我隱瞞,它不是作為一種外在的必然性在我的周圍,事實上,我不是像盒子里的一個物體那樣被關在處境中。我的自由,我作為我的所有體驗的主體具有的基本能力,就正是我在世界中的介入。”③他認為,正是因為生命存在的 “我”本身無需反思追問,而是要直接面對世間的通感,并投射于現實世界之中。同時,有物質生命的 “我”在面對詩性的文本時,才能更有效地去理解其呈現出來的意義,歸根結底“我”并不是這個世界理性的客觀觀察者,而是前反思地鏈接于現實世界的實存的生命體。基于這樣的理解,我們看到了振亞先生的詩學研究在這方面所做出的努力,他把詩歌研究的學術理性提升到了“介于感性與理性之間,是感性與理性的中介,同時是二者的混合體,是橋梁”的感悟理性層面。楊義先生曾對知覺感悟有過精辟的闡釋,同時他也一針見血地指出東西方學術溝通的路徑:“走向現代形態的感悟汲取了新的時代智慧,在縱橫的時空坐標上疏通古今脈絡,溝通中西學術。它似乎不再到處賣弄自己的招牌,而是潛入歷史的深層,埋頭苦干,不動聲色而又無處不在地醇化著和升華著新的審美創造和知識體系。它大體舒展著兩條基本思路,一是對傳統的詩學經驗、術語、文獻資源和學理構成,進行現代性的反思、闡釋、轉化和重構;二是對外來的詩性智慧和學術觀念,進行中國化接納、理解、揚棄和融合。”④這段論述的關節點似乎也是對中國傳統詩學的凝練與西方詩學的融合,對于當代學者更多的是深層感悟傳統詩學的精髓與體悟西方詩學的智慧。而知覺通感與理性并不是絕對對立的,因為一切具有理性的意識都會是早于其個體本身親臨感知的知覺世界,知覺本身就構成了理性思維的背景基石。
談到振亞先生的理性,呂聚周的評述可以說十分到位:“羅振亞具有詩人的氣質和學者的風范,這對其詩歌研究具有重要的意義。作為詩人,他對詩歌創作本身有著深切的體會,詩人的敏感與激情使其研究充滿了詩情詩意;作為博士、教授,他接受了正統的學術訓練,學者的冷靜與理性使其研究具有理性的穿透力。感性體驗與理性評判的合一,形成了其鮮明的研究風格。”⑤這是鮮明地帶有生命意識的知覺通感。因此,從這個角度去理解振亞先生的詩歌理論研究,就會發現他具有溫潤而綿長的生命力與創造力,不論對20世紀90年代先鋒詩歌的理性判斷,還是對現代詩派詩學思想的審視與重構,振亞先生的詩學研究都深深地植根于 “泥土里”,具有鮮活的生命存在意識和感悟體驗。
二、以“感悟理性”為目標的詩歌批評范式
對于詩歌研究來說,完全以科學理性所建構的方法論來解讀詩學世界,很容易被事先預設的理想秩序所規約,進而導致 “祛魅”與非神秘化。這樣一來,詩學系統也必然喪失其本真的生命價值與絢麗的豐富性, “正是因為知覺在其生命含義中和在一切理論思維之前,表現為一個存在的知覺,所以反省以為不需要研究存在的系譜,只局限于研究使存在成為可能的條件”⑥。在這個基礎上理解振亞先生的詩學研究范式,無疑契合了 “知覺通感理性”的所有要素。同時,他的 “知覺通感理性”也暗合著楊義先生所討論的——中國傳統的“感悟”與外來的詩性智慧相結合的這一思路前行,并通過對現代詩歌歷史流脈的切實把握與感悟,經過大量歷史文獻資料的驗證和理論推衍,在條理清楚地分析中逐漸形成自己創造性的理性與感性合二為一的知覺批評體系。
振亞先生對詩歌理論體系建構的知覺活動,是一種實存的主體生命存在活動,同時他把作為鮮活的自我主體意識感悟轉變為心靈感知的行為,因而當他直面詩歌現場時便會迸發出激昂的情感體悟。
這里我們僅以羅振亞早期 《中國現代主義詩歌流派史》為例。該書的出版為中國現代主義詩歌研究范式提供了一個新的視野。在這本內容貫穿半個多世紀的歷史著述中,我們看到了理論的深度和視野的廣度,雖歷經20余年仍是學者們研究中國現代主義詩歌流派不可繞過的重要參照著作。 《中國現代主義詩歌流派史》在豐厚翔實的歷史資料支撐下結合他的 “審美感悟與理論標注的準確性”,使之成為振亞先生在詩歌研究領域地位奠基的重要著述之一。 “從20年代李金發為代表的 ‘象征派’的初創,到30年代 ‘現代派’的成熟與分化,再到40年代 ‘九葉詩派’的進一步深化與發展,再到五六十年代旁枝逸出、異彩競現的臺灣現代詩,再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國大陸的 ‘朦朧詩’,80年代后期 ‘新生代’的相繼崛起, 《流派史》完整而全面地勾畫出了中國現代主義詩歌發展流變的全過程,展示出中國新詩發展的一個歷史性走向。”⑦這本著作對于現代詩歌研究而言,其意義并不僅僅是一部明確現代詩歌解讀方法與闡釋路徑的研究著作,同時也是以 “現代主義”為核心符碼、以知覺通感為學理基石來完成中國現代詩歌的完整敘事解碼活動,使當代學人能夠更為清晰直觀地面對中國現代主義詩潮的發生、發展。吳井泉曾較為全面和客觀地對 《中國現代主義詩歌流派史》作出評價:“羅振亞善于用在不同的文化環境和政治背景下所產生的審美心態和創作態度互異的詩歌流派和詩人群落來梳理中國現代主義詩歌流派發展的歷史軌跡,將色彩紛呈的詩歌現象和個性復雜的詩歌作品置于廣泛的文化場中作深度透視和歷史考察。”⑧
關于振亞先生的批評范式與風格,當代許多學者都對此進行過嚴謹的分析與判斷。比如徐志偉認為:“羅振亞的詩歌批評總體看來是一種 ‘歷史—美學’批評,注重從詩歌創作生成歷史的基點上去認識詩人、文本,不是簡單地把詩歌創作現象看作是歷史運動和文化傳統及其流變在人們心理世界的投照,而是將其納入到詩人內心的審美結構與社會歷史結構的互動中加以認識。”⑨確實,振亞先生的詩歌批評是在秉承中國傳統意象 (感悟)的同時,與西方理性分析相融合,這種詩學研究理念使他形成了自己獨有的、且是開創性的詩歌批評范式,我將其稱之為 “知覺通感的理性與感性相融合的批評范式”。作為一種高度凝練的文學體式,詩歌對它的評判主要體現在語言內涵的理解與體悟,正如語言學家奧斯汀等人所說: “什么時候我們會說什么,在什么情況下我們會用什么詞,需要考察的不僅僅是詞,而且還有在現實中我們使用這些語詞所談論的東西:我們是通過正在使用的對語詞的敏銳意識來使我們有關現象的知覺更加敏銳。”⑩對詩歌研究和批評亦或如此,我們不應只是理性地考察詩歌的詞匯,而是應該將更多的精神觀照投入到詩歌本身,從而捕捉到蘊藏在詩歌之中反映現實世界的潛在的思想表述。語言的作用不僅僅是描述和評定現實世界,也不是運用技巧賣弄詞藻,而是參與和建構人們生活世界的情感表征。在這方面,振亞先生也同樣給我們做了很好的表率,就像劉波在其文章中說過他的詩歌批評是 “‘對話與溝通’的 ‘文學創造’,其批評有強烈的抒情氣質與理性精神,他常常能以樸實的短章,充分捕捉到詩歌本身所潛藏的內蘊與獨特的藝術價值”?。這些判斷基本指出了振亞先生詩歌研究與批評范式的感悟理性特征,他的詩歌批評更加觀照與挖掘那些體現民族語言感悟的群體與時代特質。因為每一個民族的語言都是世代凝結的結果,會呈現出自身獨有的特性,作為有著千年歷史的漢語言發展至今,更體現出世代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民眾智慧的結晶, “我們所擁有共同的語詞集中體現了許多世代的生存中人們所發現的值得劃分的一切區別以及值得標示的聯系,他們是人類在許多年的生活中積累起來的,要比你我坐在安樂椅上冥思苦想出來的東西要更加的微妙、正確,因為它經受了人類世代生存的檢驗”?。振亞先生在詩歌研究中的語言表述,更多地著眼于對漢語言的體悟與歷史文脈的探究,宋寶偉這樣評述說:“羅振亞先生多年致力于中國現代主義詩歌的研究與批評,對西方現代主義詩學理論有著深刻的領悟,但在他的詩歌批評中,卻看不到西方理論的枯燥乏味的引用、論述,而是始終把西學理論的‘中國化’、 ‘本土化’放在首位。”?可以說,他充分以感悟的方式探尋歷史脈絡中的紛繁現象,進而在感悟、體驗的基礎上建構了自己的理性批評范式。
三、以“純凈”為精神核心的詩歌創作內質
如果說知覺通感理性建構了振亞先生詩學研究的重要知識體系,那么在這一體系的內核中, “純凈”則是必不可少的精神指向。
眾所周知,中國現代詩歌發展路途并非一帆風順,詩壇的江湖紛爭與詩歌的研究亂象,一直都是一些理性學者所憂慮的問題。然而,不論是詩歌遇冷年代還是喧囂時代,振亞先生面對詩歌時都有著一顆虔誠之心和敬畏態度,表現在詩學研究中便是一種 “純凈”的本真,包括熔鑄的情感、書寫的語言等,也可以說他是在感悟的理性知識體系中用誠懇而踏實的語言文字探尋純凈的詩意,就像張學昕所說: “他始終在詩歌的森林里追逐、觸摸和闡發詩學的意義和價值,本質地去發現和拓展詩歌感受和藝術思維的可能性領域。在這個過程中,他謙虛、 謹慎,不貌似 ‘深邃’,卻保持著特有的冷靜和內斂的激情。他在詩歌固有的內在張力中,捕捉語言所建立起來的詩意空間。”?這樣的精神內核使振亞先生的詩歌研究與批評自然而然地產生出一股強大的道德力量,誠如他自己剖析的那樣:“與詩結緣,是我的痛苦也是我的幸運。她讓我不諳世故,難以企及八面玲瓏的成熟,更讓我的心靈單純年輕,不被塵俗的喧囂所擾;她教我學會了感謝,感謝上蒼,感謝生活,感謝那片生我養我的土地。未來的歲月雖然還十分漫長,但有繆斯在前方不停地呼喚,我會走得淡泊自然,走得快樂永遠。”?面對詩歌能有如此淡泊而自然的純凈態度已是難能可貴,更為可貴的是他能夠把這種態度置于喧囂嘈雜的情境中進行打磨,最終能夠不被各路神怪所裹挾而堅持一路走下來。
在我看來,振亞先生的生命已與詩歌融為一體,其生命存在基于對詩歌的熱愛與執著,進而形成了一種在現實中純凈的存在狀態。我們知道,一個人要想得到真正的本真存在,并不是說要脫離現實的生活,而是應該更深刻地感悟人世間生存的真理和真諦,即人的生存感知既要能夠融入紛繁忙碌的現實世界之中,同時又能有別于常人而清醒地認知這個現實世界,從沉淪與迷茫的狀態中走出來,再以本真的、純粹的方式守候詩與詩意的存在,任憑心底自然的呼喚, “為自己的存在操心、思慮、奔忙,對自己的存在有所領悟、有所作為”?。可以看到,在振亞先生的詩學研究中處處都有著純凈的、本真的痕印,比如他對朦朧詩人的深度理解、對先鋒詩歌的準確定位等等,都顯示出他在歷史的、現場的體驗感悟之后由心而生的理性判斷。再比如,振亞先生認為90年代先鋒詩歌應該 “是那些具有超前意識和革新精神的實驗性探索性詩歌的統稱,它至少具備反叛性、實驗性和邊緣性三點特征”?,充分顯現出作為詩歌研究者 “以詩為本”的純凈態度。
值得一提的是,振亞先生的純凈精神內核除了在現代詩學研究中獨樹一幟外,在他的詩歌創作中也同樣保持著,這也使得他的詩歌在立意與抒情、語言與意象上都流淌著醇厚的親情、鄉情與真情,能讓我們感受到一個個生命律動的躍動。在詩學研究及其詩歌創作中,振亞先生能夠觀照到不易被察覺的那種內心切己的渴望,即人的本真的存在,能真實自然地熱愛現實的生活,這也是純凈靈魂的感知基礎。詹姆斯·尼古拉斯曾說:“對于我們的福祉而言,最重要的東西是我們的靈魂的健康,否則,一切外在的東西都是玷污人的,都是沒有價值的。”?在那本 《揮手浪漫》中,振亞先生以詩人的敏感和學者的理性,把那些生命過程中流光碎影的感動化為一首首詩歌,帶著我們走進過往生命的風景之中。他的 《父親的季節》、 《鄉路》、 《山中札記》、 《讀恩師呂家鄉來信》等詩作,詩中升騰著的醇厚親情、鄉情和不斷跳躍而出的哲理性語言,都在讀者心中自然散發出純凈而自然的真情真意,讓人久久不能忘懷。
比如寫鄉村:“像炫耀秋天似的/家家屋檐下/都掛起串串燃燒的紅辣椒//一陣輕風吹來/于是,山村/開始又酥又香了”; “一條七色的彩虹/從山村里飄出/伸向綠瑩瑩的憧憬”; “山谷傳送清幽的雞鳴/偷懶的太陽還沒睡醒…… 一縷呼喚的炊煙/牽出了秋意濃濃的黎明”。這些熟悉的鄉村景致,在作者看似不經意的語言描述中境界全開,顯露出一股質樸的真情與純凈的詩意。再如寫自己的父親: “煙鍋一閃一閃/幾十年的歲月被依次照亮/傾聽玉米拔節的夢/一任金黃色的風/醉醺醺地漫向遠方”,形象而生動地把 “父親”這一平常形象刻畫出來,并且在充滿詩意的情境中展開歲月的追溯。對自然與親情的意境有深情感悟之外,更深層地感悟到振亞先生寫 “父親”形象的擔當與責任的體悟:“父親”更多的是肩上既要扛自己的生存責任,又要清醒地引領下一代走向明晰的遠方;當“父親”把遮蔽著光明的烏云撥開之時,后人能更加明確路徑的選擇,也就會更好地生存與通達在真實之中。
振亞先生正是在他的研究與創作中保持了 “純凈”的精神,才使得研究與創作能夠在和諧中交相呼應,并同時與他的感悟理性形成具有特質的詩學思維和語言風格。對振亞先生30余年的詩學研究與詩歌創作,我們現在并不能夠一錘定音地予以總結,因為他的學術之路還有漫長時日,他一定還會創造更多的學術高峰等待我們去探究。但有一點是顯而易見的,那就是 “理性”與 “純凈”早已蘊含在他對現象的準確把握、對詩意真切的抒情之中,他的 “理性內涵是被一種不經意而為之的抒情之水溶解的,似有若無,沒有生硬的表達 ‘思想’之感”。?我們相信,未來他仍然會在感悟理性的思辨中、在本真純凈的存在中做 “一位執著的繆斯追求者”!
注釋:
① 呂家鄉:《中國現代主義詩歌流派史·序》,北方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第1頁。
② 呂家鄉:《進入現代派詩歌的本體世界——讀〈中國30年代現代派詩歌研究〉》, 《詩探索》1998年第3期。
③⑥ Merleau-Ponty,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Routleau,2002,p.419,p.63.
④ 楊義:《現代中國學術方法通論》,山東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97頁。
⑤ 呂聚周:《感性體驗與理性評判的合一——談羅振亞的詩歌研究》, 《渤海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6期。
⑦ 華清:《“理性的閃光,感情的激蕩”——評羅振亞著 〈中國現代主義詩歌流派史〉》, 《山東師范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1995年第4期。
⑧ 吳井泉:《理性與情感交織的藝術世界——評羅振亞著 〈中國現代主義詩歌流派史〉》, 《佳木斯師專學報》1996年第2期。
⑨ 徐志偉:《在史實與體驗之間——評羅振亞的現代主義詩歌研究》, 《詩探索》2004年春夏版。
⑩? J.O.Urmson and G.J.Waronck:Philosophical Papers,Third Edi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9,p.182,pp.181-182.
? 劉波:《新詩研究及其批評的倫理——論羅振亞新詩批評與研究》, 《詩探索》2013年第4輯。
? 宋寶偉:《孤寂堅守中的思想探險——評羅振亞的 〈與先鋒對話〉》, 《詩探索》2010年第1輯。
? 張學昕:《虔誠地站在詩意這邊——關于羅振亞及其詩學理論與批評》, 《渤海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2期。
? 羅振亞:《中國現代主義詩歌史論·后記》,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441頁。
? 劉小楓:《詩化哲學》,華東師范大學出版2007年版,第289頁。
? 羅振亞:《1990年代新潮詩研究》,河北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1頁。
? 詹姆斯·尼古拉斯:《伊壁鳩魯主義的政治哲學》,溥林譯,華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頁。
? 邢海珍:《歲月深處的詩情——讀羅振亞的詩》,《文藝評論》200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