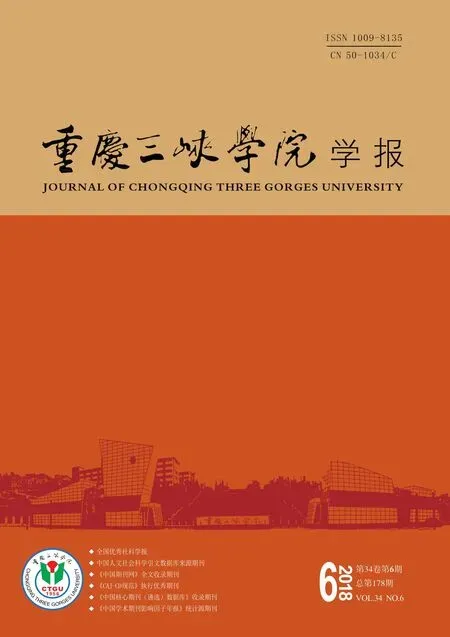《誰家有女初長成》中殺人行為分析
鄭宗榮
?
《誰家有女初長成》中殺人行為分析
鄭宗榮
(重慶三峽學院學報編輯部,重慶 404020)
嚴歌苓小說《誰家有女初長成》中講述少女潘巧巧被人販子拐賣,嫁給大18歲的養路工郭大宏,遭到郭大宏的傻子弟弟性侵,殺死郭大宏兩兄弟的故事。潘巧巧殺人的直接原因是二宏的性侵和郭大宏的不作為,深層原因是以暴制暴的本能、自我意識的覺醒、追求生存價值、缺乏安全感等。現代社會,可以通過提高女性受教育的程度、進行道德法制教育、實行替代性攻擊等方式疏導女性不良情緒,減少殺人行為的發生。
《誰家有女初長成》;殺人;自我意識;情緒宣泄
社會在發展,人類在進步,可暴力從未退出歷史舞臺,“殺人”甚至成為某些現代人發泄憤怒、表達不滿、解決問題的簡單粗暴方式。以前人們更多關注男性殺人,悄然間,女性殺人也成為不容忽視的社會現象。文學是對社會生活的反映,文學作品中,以臺灣作家李昂的《殺夫》為代表,許多作家描述了女性殺人的種種悲劇。嚴歌苓的小說《誰家有女初長成》中寫了川西偏僻黃桷坪的女孩潘巧巧被人販子拐騙,賣到更偏僻落后的甘肅農村,本來已經接受被拐賣的命運,安于生活,受到丈夫郭大宏傻子弟弟的性侵,郭大宏不理解潘巧巧的痛苦,對弟弟袒護包容,一氣之下,潘巧巧揮舞菜刀,干凈利落地殺害了郭大宏和他的弟弟。一切發生得那么突然,大錯釀成,潘巧巧被判處死刑。受害者如何變成了施暴者?探究其中原因,探討如何疏導不良情緒,可以減少殺人和故意傷害等暴力行為的發生。
一、殺人行為及原因
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雖然只讀到小學五年級,但“殺人償命”的道理潘巧巧還是懂的。即便如此,“她把提刀的手背在身后,邁著如往常的輕快步伐走進廚房。……她背后的菜刀從一側切入她自己的視野,隨后她整個視野成了一片紅色的混沌。……他感到冷颼颼一片東西截斷了他的歡樂。他轉過正汩汩流血的脖子,看著這個給了他三個月美妙溫暖的女子”[1]42-43。潘巧巧揮刀相向的背后,包含著深層的社會、經濟、文化、心理等原因。本文擬從女人的自然存在、精神存在、社會存在三個方面分析潘巧巧的殺人行為。
(一) 自然存在:以暴制暴
人屬于自然的存在,遇到刺激會做出本能的生理反應。生活是理性與非理性的平衡。人之需求的復雜性和生存環境的不確定性,使非理性世界充滿了自我矛盾和非連續的跳躍,這些矛盾和跳躍既可以通向創造和發現,也可以導致無謂的消耗甚至破壞[2]161。作為一個健全獨立的人,遭到外界侵犯時本能地會抵抗。但因為人的社會屬性,人的理性會克制本能的沖動。人的需要不論為何,只有得到滿足時,他的內心才會得到安寧。當人產生不良情緒時,有多種釋放方式。比如用暴力,比如用語言表達和傾訴自己的情緒。語言使人的生命體驗明確化,使人明確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要逃避什么,從而知道自己實踐活動的方向和目標[2]177。語言就是自我意識的自我確證[2]195。
巧巧確證自己被賣給大齡的郭大宏之后,“她惡毒污穢的咒罵是指名道姓的”[1]21,“郭大宏承受著巧巧對他祖宗八輩的毒咒”[1]21,“于是嘴里更是千刀萬剮的兇狠”[1]21罵完了,也就默默接受了自己被賣的事實。用語言發泄憤怒,需要被罵的人能夠理解語言中蘊含的不滿及委屈。當潘巧巧遇到傻子二宏時,二宏不能理解語言的意義,語言就沒有了殺傷力,巧巧選擇以暴力進行直接反擊。
以暴制暴是指用暴力手段抵制暴力,針鋒相對地進行回擊。“以暴制暴”比的是力量,是一種原始同態復仇意識的殘留。“以暴制暴”也是日常生活中人們最本能最直接的一種反抗方式。暴力的形式充滿激情,源自人內心渴望的力量巨大,深入人心。
巧巧第一次和大宏發生關系,二宏就在外面聽房,“巧巧突然竄起,抓起床邊大宏的翻毛皮鞋,對著門砍過去”[1]26,一個“砍”字,將巧巧的厭惡和憤怒表現得淋漓盡致。“本來鬧得差不多了,聽傻子二宏這一叫,她把腳盆連水帶盆朝栓緊的門甩過去。”[1]31每一次巧巧厭惡二宏,都以暴力宣泄情緒。“情緒自覺不自覺的忽然宣泄作為表現方式,相當于心靈在特定時間范圍內的活動。”[3]257巧巧習慣了這種簡單快捷的解決方法,為后來被強奸之后直接提刀殺人埋下伏筆,也是她欠缺思考,行事魯莽的直接結果。波伏娃說:“暴力是每個人忠實于自己,忠實于他的熱情和自己的意愿的真憑實據。”[4]
巧巧雖然接受了和大宏的婚姻,但不意味著她能夠容忍傻子二宏對她的性侵,尤其是她認為兄弟倆合伙分享她的肉體。人類之所以有今天,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是由于能夠對性交關系進行限制和選擇。人類社會的婚姻制度的發展歷史,本質上就是人類對待性關系進行適當控制的發展歷史。不受限制的性交,與其說是人的性交,倒不如說是動物的性交。從動物的性交發展為人的性交,實際是人類從動物世界走出的一個根本標志。人對性關系的正確處理,是人性的重要方面,也體現著人性的光輝[5]177-179。即便被拐賣,巧巧也有選擇自己性交對象的權利。巧巧明白自己受到性侵犯時,提著刀追了二宏幾圈,沒找到人后冷靜下來,本想著和大宏好好溝通,希望自己被侵犯被侮辱的屈辱感能夠得到大宏的認同,自己的憤怒和不滿可以通過語言得到發泄。可是大宏沒有設身處地地理解巧巧的憤怒,反而袒護二宏,寧愿自己去坐牢,也不能懲罰二宏。大宏對二宏的袒護激發了巧巧本能中非理性的一面。
非理性是人的本能,是生命的自我確證,非理性沖動常常沒有客觀原因,更加說明這種沖動來自人的生命本身。由于非理性感受的切己性和低成本性,由于語言符號中介的不在場,生命能量直接作用于感受本身,可以使感受表現得相當活躍和不穩定,其利在于有時可以憑直覺降低決策成本,其弊在于過強的主觀任意性使其容易在現實中碰壁[5]161。如法國珍妮薇·傅雷絲在《兩性的沖突》中所說:“家庭不單純是角色分配和任務分攤的場所。……家庭是一個政治場所,因為這是一個辯論與權力分配的場所。這里所謂政治場所并不是指通過公共領域在私生活范圍的延伸使得私生活變成政治。這是一個政治領域,因為有些決定要采取,有些權力要實施。”[6]262
巧巧嫁給郭大宏以后,一直被郭大宏寵著,處于家庭中的強勢地位,擁有較大的主宰權利,而在被二宏凌辱這等重大權力被侵犯,需要進一步強化其主體價值時,居然一拳打出去完全落空,遭到大宏的漠視,于是“為了讓某個原則被接受,我們會去戰斗……然而,兩個性別既相似又相異,甚至為此原因,不平等和平等在自由的剝奪與贏得上面糾纏一起,把一切都攪渾了”[6]263。
暴力和攻擊在社會生活中普遍存在。攻擊是對他人的傷害行為。提供強化或弱化攻擊行為的原因的時機也很重要。如果人們在受攻擊之前就已經了解對方這樣做的理由,那么他們就不大可能發怒或者變得有攻擊性[7]533。從過去20年的心理科學研究中得出的一個一般原則是,當意識沒有推翻直覺反應的傾向或沒有能力推翻直覺反應時,直覺反應會指導行為[8]95。有相當高比率的男人(79%)和女人(58%)承認有過殺人幻想。這個比率看上去已經很高了,但我猜想有過殺人幻想的正常人的數量應該比這個還要多[9]。
出于“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的本能,巧巧在小月子中受到二宏性侵時,“她直接沖到廚房,抓起菜刀回到二宏屋里”[1]39,“傻畜牲對她如此畜牲了一番,她感到手里的菜刀如同她的牙齒和指甲,痙攣地發著狠勁,成了她軀體、肢體的延伸”[1]40。巧巧第一次出于本能提刀殺人沒有成功而向大宏表達憤怒時,如果大宏能夠傾聽巧巧的憤怒,理解、道歉并且給予安撫,讓巧巧的不良情緒得以疏導,悲劇可能不會發生。家庭暴力通常是缺乏溝通,不了解對方行為動機,爭論逐漸升級后發生的。同時道歉可以避免一些攻擊行為。一般而言,如果人們為了本來可能會導致攻擊的行為道歉,感覺受到傷害的一方容易原諒對方。可大宏缺乏與巧巧的良好溝通,導致巧巧沉陷在自己的世界中,認為“他不是為他自己娶的她,他實際上是買了她來,是省了一部分的她給他兄弟的”[1]40,“巧巧推理完成了,一套丑惡罪過的邏輯完整了”,導致她以暴制暴,用殺人的負面方式作為更高生命意義的實現方式。
(二) 精神存在:自我意識的覺醒
“以暴制暴”是出于本能的直接反應,驅使巧巧受到強奸后作出猛烈反擊的深層動因,應該是巧巧內心里自我意識的覺醒。自我意識覺醒強大的爆發力與巧巧身體內部某種極端化情緒相扭結,導致巧巧瞬間情緒失控并歇斯底里。因為意識與存在的矛盾就是意識的自我矛盾,所以可以避開物質現實對它的種種限制。一旦意識突破種種現實原則或道德原則對它的束縛,就會追求一種絕對的自由。人不僅具有社會現實性,而且具有類的潛能,使自己的潛能自由而全面地實現的人才是自由的人[2]174。中國以前的文學作品中女性多是忍辱負重,處于被統治、被奴役的地位,遭到凌辱只能忍氣吞聲或者自殺,巧巧將復仇的心理付諸行動,反映出她自我意識的覺醒。
人之所以作為人的需要,可以分為客觀需要和主觀需要。所謂客觀需要,是指由人的生存發展所產生的需要,它包括人作為生物體的需要和因社會制度要求所產生的需要。……主觀需要可分為兩種:一種是對客觀需要的準確反映,它也就與客觀需要等同。另一種是社會賦予人的主觀需要,是人的主觀能動性所產生的需要[5]63-64。
美國·大衛德斯迪諾認為:“保持情侶關系良性發展的關鍵是,一方提供的好處恰好是另一方很重視的那個領域即可。只要獲得的收益與實際的成本本質上大致相等,兩人的關系就會繼續平穩緩慢地向前發展。”[8]83巧巧“明白了,他牲口是牲口,畢竟掙國家的錢,占著個城市人口的名分”,“哦,一個月一百出頭呢。很快算了一下:一年能存出一千塊呢。她又想,這個人看上去倒憨厚,恐怕還有點?,潘富強老婆要敢這么無法無天地鬧,十頓揍恐怕都挨了”。郭大宏有城市戶口、工資收入不低、脾氣好,巧巧接受了他。郭大宏不強行與她同房,巧巧甚至心疼大宏為了買她花了一萬塊錢。巧巧在大宏的信任與照顧之下,獲得了溫飽等基本需要,擁有了一定的自由,發現了自己生命的意義和價值。
巧巧有被尊重、性自由等更重要的主觀需要。固然,由于肉體生存的緊迫性,它往往會壓倒精神發展需求,但肉體需求得到滿足后,就不能完全忍受被踐踏的尊嚴,而渴望得到理解與尊重。女性獨立意識越強、思考越深刻,遭受精神痛苦的程度越深。人雖然向往著圓滿,向往著所有需求的滿足,但是生命的有限、能力的有限、資源的有限使人只能實現極其有限的目標,因而各種價值需求的沖突勢不可免[2]158。遇到沖突時,自我意識覺醒,為了維護自己遵從的原則,自然會對違背自己意愿的言論或行為做出反擊。二宏對巧巧的性侵突破了她的底線,內在的自我必然做出反擊。
一般而言,人的行為具有以下特點:第一,人的行為在動力上具有復合性。人的行為固然有單獨由欲求推動或決定的時候,但大多都是欲求、價值觀、欲求實現可能等整合后形成的動力推動的結果,是一種自覺的行為。第二,人的行為在過程上具有可變性和可控性。人的行為在方向上、程度上都具有可變性。人改變行為固然可以是因為客觀環境發生變化,但也可以是意志作用的結果。人的行為能夠因意志作用而導致方向、力度等變化,表明人對自己的行為具有一定的控制能力。第三,人的行為在結果上具有可預見性和可評判性。人在行為之前就對行為結果有所預見,這種預見可以說是構成人之行為動機的一個因素。人在行為之后,一定還要對行為結果進行預見,這是人在行為過程中決定是否繼續行為的重要因素。……對行為結果進行評判,以及對行為過程進行回顧反思,是人的一個重要特點。這個特點使人的行為得到自我糾正。第四,人對自己為滿足欲求而實施的行為可做善惡評判[5]95-96。
巧巧遭到二宏性侵后找大宏傾訴,大宏不但沒有站在巧巧的立場理解巧巧心中的痛苦和憤怒,讓她發泄壓抑的不滿,而是說巧巧“你又不是沒給人禍害過”[1]40,揭開巧巧過去的傷疤,對巧巧猶如火上澆油。如果大宏能夠合理地向巧巧表達自己心中的愧疚,在購買昂貴的彩電之前告訴巧巧他準備用物質彌補,也許巧巧物質的一面會占上風,“我的軀體屬于我”的自我意識不會那么強烈,不再受這種超越她、使她順從的自然力的控制。婦女過去是、現在仍然是交換品,更有甚者,她們是所有社會中一枚交換的硬幣[6]247。當人們脫離了發生在過去和展望未來的方向感時,他們就扭曲了他們的現實,采取了施特勞斯所稱的“現時生存”,即只為暫時而生活[10]200。巧巧被壓抑的自我在所有現實合理的權力遭到否定和侵犯時被激活了。薩特描述了兩種存在模式,即自身存在和為自身存在。自身存在就是確切的自身本來面目;相反,為自身存在是指一個人如何對外部世界做出反應[10]204。
一次又一次的傷害累積起來,被拐賣、誘奸、強奸的巨大傷害撕扯,吞噬了巧巧的靈魂,原本潛藏著的自我因正好摸到那把帶著體溫的刀而瞬間爆發,由本能驅使對遭受的種種損害進行了徹底反抗。巧巧不僅是對生存狀態的反抗,更是對悲慘命運的反抗,是自我意識的覺醒,用行動突顯自己的價值。
(三) 社會存在:經濟文化因素
潘巧巧殺人,除了她自身的原因,與社會環境也緊密相關。從現象上看似乎是發生在巧巧身上的偶然事件,其實是改革開放初期,新的生活方式對舊理念的挑戰,女性自主意識的崛起,是不同社會力量之間的沖突與交鋒。如果她不是生活在偏僻的川北農村,沒有對現代化城市深圳的向往,如果不被人販子拐賣,對這個世界沒有那么多失望,她怎么也不會舉起屠刀,成為殺人兇手,而像小說下篇展示的那樣,一個乖巧能干招人喜歡的小女人。
偏僻鄉村殘存著以男性為中心的思想,男人絕對的主導地位及這地位賦予男人任意宰割他者的權力。在男權秩序的控制之下,金錢與男權社會合謀,女性只是男性的附屬品。女人及女人的本能、尊嚴全部被消解。看似郭大宏順從巧巧的意志,可當巧巧被他的兄弟傷害時,他有的只是蔑視,拿脊梁對著巧巧,讓她要咋說就咋說,“他連看都沒看巧巧一眼,拾起地上的膠皮雨衣就走了出去”[1]41。
在巨大的男權陰影中,女性沒有獨立的話語權、身體權,只能用身體供男性消費換來生活的平安、富足。當人被禁錮在生存的直接現實性和具體性之中時,也就意味著自由的匱乏[2]268。“爹疼媽愛的巧巧,最初也只不過是這些人手里的一塊糕餅,大口吞小口啃,巧巧給他們咀嚼、咂巴著滋味,消化。巧巧感到自己此時是一堆穢物,消化后的排泄。”[1]41女性在婚姻關系中普遍處于弱勢地位,有時飽受情感虐待、家庭暴力,但求助無門。
巧巧被拐賣之后,家鄉黃桷坪也回不去了。家鄉人對那些混得不好的女孩的態度是,寧愿像從來沒有生過這些女孩一樣,也不能讓她們回來丟人現眼。在這些認為女性低賤的人看來,女性天生就應溫順、臣服,對此不必有半分質疑[3]117。人類文明的整體歷史表明,女性一直承受著社會給予她們的太過沉重的壓力,不堪忍受,所以才會選擇抗拒。巧巧獨自在甘肅偏僻的小地方,沒有父母可以依靠,嫁的男人也不與她同心,得不到他的幫助,信賴缺失,難以坦誠相待。孤獨無助、沒有安全感、對生活絕望了的巧巧容易走向極端。家庭作為構成社會的最小單元,家庭成員之間都沒有了信任和依托,整個社會呈現出物質至上的病態。
在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物質利益原則既是社會制度的基石,也是個人行動的動力和調整行為的準則。物質利益原則在需要它的社會歷史階段,使人們必講利害,必講利益得失。兩利相權取其大,兩害相權取其輕,也就成為人們選擇行為的準則[5]73。巧巧在陌生的甘肅接受了被拐賣的命運,渴望的深圳就像一個遙遠的夢,像母親和外婆一樣認命——生活在郭大宏狹窄的院子里,操持家務,像模像樣地過起了小日子。即便如此,命運沒有對巧巧開恩,讓她在這偏僻的角落好好活下去,而是用二宏再給她重重一擊。
物質利益決定人的生存權利和生存過程物質生活的水準,道義則決定人的生存價值。當人只為生存而活時,則物質利益最重要,物質利益大于天;當人為生存價值而活時,物質利益就只是人生的手段。每個人的生活原則都是有底線的,為了活下去,巧巧已經接受了嫁給大宏的事實,但是她不能淪為兄弟倆發泄性欲的工具,她有自己的生存價值。所謂人性,本質上就是人類學會依靠自己的力量和智慧從自然界獲取物質生活資料以解決自己的生存和發展問題,進而將自己與動物區別開來的東西[5]89。她必須維護自己作為人的尊嚴。人的生命以及生命價值的顯現對物質資料的依賴本是有限的,這不僅表現為人的物欲在生理上有限,而且表現為人的物欲在心理上也存在邊界。她不會為了茍活而什么都接受。人的物質欲望是隨著物質財富增加而遞減的。巧巧借殺死侵犯她的男人實現對以男權為中心的社會的反抗與報復。巧巧的悲劇,是個人的性格和命運造成的,也是不公平的社會環境造成的。
二、 極端情緒宣泄策略
要減少或消除《誰家有女初長成》中這樣的殺人悲劇,必須提高女性社會地位,真正實現男女平等,尊重女性。當男性與女性發生沖突時,如何讓女性不再陷入狹隘的個人情感糾葛之中?如何控制自己的思想和行為?如何宣泄情緒、控制情緒呢?
第一,提高女性受教育的程度,鼓勵婦女廣泛地參與社會生活,走出個人狹窄的恩怨情仇,放大自己的格局,培養女性的獨立意識。有研究者對監獄里女性殺人者進行調查①,受教育程度越低,發生暴力事件的比例越高。如果女性社會參與程度高,分散注意力的東西越多,累積的負面情緒相對少一些,可以更好地控制自己。
第二,進行道德法制教育。攻擊表達焦慮,需要抑制攻擊焦慮。當個體想要采取攻擊行為時會感到焦慮,講道理可能產生更多的對攻擊性的內在抑制,這比畏懼懲罰更有效。當然,對懲罰和報復的害怕也可以明顯減少攻擊行為。適當的法制宣傳,可以期望人們對自己的攻擊行為后果進行想象并且因為要被懲罰而避免暴力。
第三,替代性攻擊。向一個替代對象釋放攻擊性,指向更弱小和沒風險的對象。受挫和襲擊是憤怒的主要來源。憤怒被釋放以后,進一步攻擊的可能性會降低。現代社會提供了很多發泄憤怒的合法途徑,可以釋放極端情緒。
《誰家有女初長成》中的殺人行為不是個案,而是社會惡性暴力事件的一個縮影,是社會生活側面在文學作品中的表現。提高婦女的社會地位,真正實現男女平等,疏導人在憤怒時的極端情緒,可以減少類似悲劇的發生。
[1]嚴歌苓.誰家有女初長成[M].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3.
[2] 張立達.對象化和人的生存矛盾[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1.
[3] 阿爾弗雷德·阿德勒.洞察人性[M].張曉晨,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6.
[4] 波伏娃.第二性[M].陶鐵柱,譯.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8:381.
[5] 張寬政.論人性:善惡并存,以善為主[M].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17.
[6] 珍妮薇·傅雷絲.兩性的沖突[M].鄧麗丹,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7] S.E.Taylor L.A.Peplau D.O.Sears.社會心理學[M].謝曉非,謝冬梅,張怡玲,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8] 大衛德斯迪諾.信任的假象:隱藏在人性中的背叛真相[M].趙曉瑞,譯.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14.
[9] 道格拉斯·肯里克.性、謀殺及生命的意義[M].朱邦芊,譯.北京:中信出版集團股份有限公司,2013.
[10] WILLIAM Blair Gould.弗蘭克爾:意義與人生[M].常曉玲,翟鳳臣,肖曉月,譯.北京:中國輕工業出版社,2000.
① 具體研究情況請參見邢紅枚.受虐婦女殺夫的原因——對四川省某女子監獄的調查報告[J].四川警察學院學報,2010(4):65-70.
An Analysis of the Murder Behavior in
ZHENG Zongrong
Geling Yan’s novelis mainly about Pan Qiaoqiao, the girl who was trafficked to be the wife of Guo Dahong, murdered both Guo and his silly brother who has raped her. The direct reason for the murder is the silly brother’s sexual invasion and her husband’s tacit permission. However, the further reason for the murder is out of the instinct of fighting back, self-awareness, the pursuit of life values and insecurity. There are good ways to release female’s frustration and sadness by improving education degree of female, inculcating moral and legal concepts in females and making substitutive attack, etc. so that to reduce murder behaviors.
; murder; self-consciousness; emotional catharsis
鄭宗榮(1975—),女,重慶萬州人,重慶三峽學院學報編輯,副教授,主要研究文藝學。
I206.7
A
1009-8135(2018)06-0059-06
(責任編輯:張新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