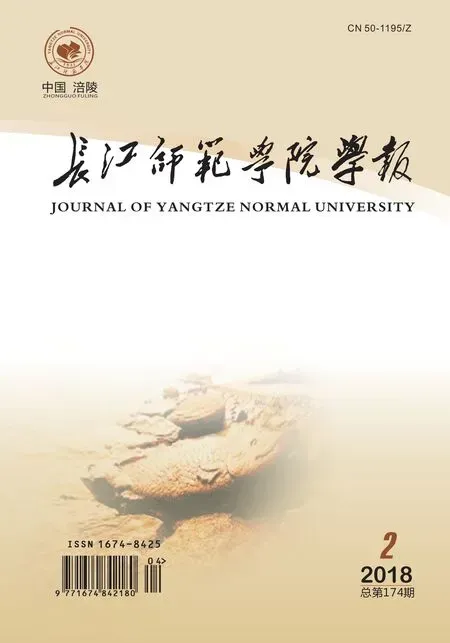以事實作為論據
——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論證方式分析
韓佳蔚
(長江師范學院 傳媒學院,重慶 408100)
2014年10月15日,習近平同志主持召開文藝工作座談會,并發表重要講話。習近平同志的《講話》全文凡14 000余字,內容博大精深,結構宏偉縝密,是新時期文藝工作的綱領性文獻,體現了黨和國家對文藝工作的高度重視和宏觀指導。《講話》文本是議論性文體,必然包含有議論文創作的3大要素,即論點、論據和論證。論據作為支撐論點的材料,是作者闡述思想、論證觀點的依據,自然十分重要。議論文中的論據通常有“事實性論據”“比喻性論據”“引言論據”等類型[1]。《講話》運用了多種類型的論據,其中使用最多、頻率最高、占據篇幅最大的是“事實性論據”。詳讀《講話》全文,便會觀察到其敘事的顯著特點之一,即是以事實作為論據。“事實勝于雄辯”,數量眾多,并與論題高度契合、邏輯關系嚴密的“事實性論據”不僅極大地增強了《講話》的說服力和感染力,而且賦予文本深厚的文化底蘊和強大的思想張力。因此要全面地研究《講話》這一新時期的重要歷史文獻,便不能忽略文本所采用的論證方法及其以事實作為論據的寫作特點。
一、事實性論據的充分性——博引古今中外事實加強論證力量
《講話》作為議論性文體,旨在發表議論,闡明論點,實現以理服人、以情動人之創作目的。在其行文中常提出具有“分論點”性質的觀點,并援引大量事實對觀點進行充分論證和深入闡發。作者所選用的“事實性論據”,既有人們普遍知曉的本民族古往今來的典型事實,也有大家耳熟能詳的域外古今經典案例。《講話》特別擅長在列舉和分析大量古今中外“事實性論據”的基礎上,對所提出的觀點進行邏輯嚴密、水到渠成的推論和確認。
《講話》指出:“歷史和現實都表明,人類文明是由世界各國各民族共同創造的。”[2]這是一句論斷性話語,也是人們普遍認同的觀點。為了充分證實這一觀點,作者運用了事實論據法,旁征博引,以大量古今中外各國各民族創造文明成果的歷史事實來論證自己的論點。習近平同志先用自己出國訪問時“最陶醉的是各國各民族人民創造的文明成果”[2]打開以事實進行論證的通路,并以自己在國外所親見并“陶醉”于其中的親身經歷來凸顯事實的真實性、可靠性。在“比比皆是”的“世界文明瑰寶”中他首先列舉了“對人類文明影響深遠的”古希臘神話、寓言、雕塑、建筑藝術及古希臘的著名戲劇作家;其次列舉了俄羅斯、法國、英國、美國等國家的數十位藝術大師;接著以自己近期訪問印度為例,對印度公元前1000年前后的4種文獻本集詳細列舉其名,并指出在我國高僧法顯、玄奘取經時,“印度的詩歌、舞蹈、繪畫、宗教建筑和雕塑就達到了很高的水平”[2]。他還提到了印度近代具有“世界性的影響”的文豪泰戈爾。在如此廣泛地列舉域外文明成果的基礎上,他又以“我國就更多了”作為過渡句,進入博引我國古今文學藝術成就的事實性論證。他首先列舉了我國先秦諸子、屈原、王羲之、《詩經》、楚辭、漢賦、唐宋詩詞、元曲、明清小說等古代名家名作,接著引述了現當代藝術大師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聶耳、冼星海、梅蘭芳、齊白石、徐悲鴻等,并且提到我國少數民族史詩《格薩爾王傳》《瑪納斯》《江格爾》。《講話》由國外到國內、由古代及現代,選擇“事實性論據”的視野極為廣闊,以彪炳史冊、人盡皆知、舉世敬仰的古今中外各國各民族創造的文明成果作為“事實性論據”,從而使“人類文明是由世界各國各民族共同創造的”這一觀點得到充分而完滿的論證,而且論證過程縱橫開闔、文氣充沛、一氣呵成,如行云流水,富有感染力和說服力。
《講話》指出:“文藝是時代前進的號角,最能代表一個時代的風貌,最能引領一個時代的風氣。”[2]習近平同志的這一論斷旨在強調文藝與時代及社會現實的密切關系,進而勉勵文藝工作者關注現實、服務人民、推動和引領社會前進。為了闡明這一觀點,他先以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為例,列舉了“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達·芬奇、拉斐爾、米開朗琪羅、蒙田、塞萬提斯、莎士比亞等文藝巨人”,指出正是他們“發出了新時代的啼聲,開啟了人們的心靈”[2],啟動了偉大的文藝復興運動。《講話》接著將話鋒轉向對我國歷史事實的引述分析,強調“包括文藝在內的文化發展同樣與中華民族發展緊緊聯系在一起”。他先后列舉了先秦諸子開創“百家爭鳴”局面、迎來我國古代文化“鼎盛期”的典型史實,特別指出“五四”時期“發端于文藝領域的創新風潮”對當時中國社會變革產生了“重大影響”,因而成為民族“思想解放運動的重要引擎”[2]。《講話》以人們熟知、確信無疑、已有定論的中外、古今的歷史事實作為論據,再加上對“事實性論據”的精辟分析和深入闡發,充分論述了“文藝是時代前進的號角”和文藝能夠“引領一個時代的風氣”的思想觀點。
議論文寫作運用“事實性論據”容易出現的失誤主要有如下情況:“事例敘述太過詳盡,近似記敘文”,因而“造成文體不清”;引述的事實材料未能“緊扣論點”,對論點的證明“如隔靴搔癢”;對事實論據缺乏“說理分析”,以致事實論據與所要論證的觀點“分崩離析”[3]。習近平同志的《講話》則避免了這種情況,雖然通篇頻繁地援引“事實性論據”來闡述觀點,所列舉的“事實性論據”不僅數量大,而且縱橫“域內”與“域外”、跨越“古代”與“現實”,但如此紛紜駁雜的“事實性論據”并非毫無邏輯關系的“雜陳”與“堆砌”,亦非與論點相“偏離”、相“疏離”,甚至離題萬里;在《講話》中每一個“事實性論據”都被作者精心剪裁,都與論題保持著密切的相關性和內在的邏輯聯系,這些“事實性論據”在作者“緊扣論點”展開的“分析說理”中充分而有效地力證觀點,揭示全文的主旨。
二、論據的相關性——事實性論據充分闡明論點
在議論文寫作中,“如果論據對論題沒有相關性或相關性很小,則論據就發揮不了論證作用從而失去論據資格”,因此與論題的“相關性”便成為“事實性論據”最基本的屬性;與論題的“無相關性”或“虛相關性”與“弱相關性”,都是“事實性論據”運用中最常見的“邏輯錯誤”[4]。《講話》運用“事實性論據”的最大特點,則是“事實性論據”與論題保持了高度的邏輯“相關性”。實際上,作者選擇“事實性論據”的觀察視線觸及到了古今中外廣闊無垠的歷史生活和社會現實,可供選擇的歷史或者現實的“事實”應當是難以窮盡的,但作者做到了在相關事實中精準而貼切地選取那些與論點最具有“相關性”的典型案例,并通過透徹分析和哲理性聯系將其“打造”成為立論觀點的“事實性論據”。
《講話》在論證文藝與生活的關系及文藝對人類思想感情的潛移默化作用時指出:“文藝深深融入人民生活,事業和生活、順境和逆境、夢想和期望、愛和恨、存在和死亡,人類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可以在文藝作品中找到啟迪。”[2]為了闡明這一觀點,習近平同志以自己的閱讀經歷作為“事實性論據”,他說自己青年時期熱愛閱讀,對優秀文學作品的“許多精彩章節、雋永文字至今記憶猶新”。為了論證“文藝也是不同國家和民族相互了解和溝通的最好方式”,他列舉了自己2013年出訪俄羅斯、2014年出訪法國的感觸,強調俄羅斯、法國文學對自己的深刻影響,甚至詳述自己在陜北插隊時為借閱德國文學家歌德的詩劇《浮士德》而徒步30里路、知青伙伴為取回《浮士德》也徒步30里路的難忘經歷。因為這些“事實性論據”是他本人所親歷并有著深刻的感觸,所以貼切、充分而令人信服地實證了文藝與生活的緊密關系,以及文藝所特有的情感教育功能。由此可見,《講話》對“事實性論據”的選擇已經達到“指向明確、語意集中”的藝術佳境[5],因此其論證必然具有很強的說服力和感染力。
《講話》提出“人民的需要是文藝存在的根本價值所在”的觀點,并以國內外文藝創作的事實加以論證。習近平同志首先指出:“我國久傳不息的名篇佳作都充滿著對人民命運的悲憫、對人民悲歡的關切,以精湛的藝術彰顯了深厚的人民情懷”[2]。為了闡發這一觀點,《講話》列舉了我國傳自遠古的狩獵歌《彈歌》,我國最早的詩歌總集、產生于周代的《詩經》中的《七月》《采薇》《關雎》等反映勞動人民生產生活和感情心聲的詩歌,并且列舉了戰國時期偉大詩人屈原探索宇宙奧秘的《天問》,以及南北朝時期歌詠北方游牧民族生活的《敕勒歌》、體現古代女性英姿的《木蘭詩》等,還引述了屈原、杜甫、李紳等詩人的傳世名句。這些深刻反映社會現實與人民疾苦心聲的佳作名篇凸顯了文藝與社會現實、人民生活的密切關系,《講話》以它們作為“事實性論據”來論證觀點,論據選擇做到了既自然得當又準確貼切。事實上,我國文學史上的優秀作家燦若繁星,文學經典浩若煙海,那些具有憂國憂民情懷的文學家及其佳作名句都可以作為論證文藝與人民關系的“事實性論據”。但《講話》所引述的上述文學創作事實,在中國文學史上都被公認為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都是深刻反映社會現實與人民生活、具有人民性和批判精神的藝術珍品,所以這些“事實性論據”必然與“人民的需要是文藝存在的根本價值所在”這一論點之間具有顯而易見的“相關性”與嚴密緊湊的邏輯關聯。
三、論據的典型性——事實選擇與素材剪裁的藝術效應
議論文體中的“事實性論據”還必須具有“正確性、典型性和代表性”[6],才能夠喚起人們的普遍認同、深刻反思和思想共鳴,進而產生震撼心靈、令人心悅誠服的表達效應。
《講話》在論證“精品之所以‘精’,就在于其思想精深、藝術精湛、制作精良”[2]時,也采用了事實論證法。習近平同志列舉了法國著名作家福樓拜創作《包法利夫人》時“有一頁就寫了5天”“客店這一節也許得寫3個月”,以及我國偉大的現實主義作家曹雪芹創作《紅樓夢》時“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的事例,從而有力地闡述了“孜孜以求、精益求精”是打造出精品佳作的關鍵。古今中外的文學家在創作中精益求精的“事實”和“案例”必然很多,顯然作者對相關素材進行了富有創意的取舍和剪裁。無論是福樓拜寫作《包法利夫人》的精雕細琢,還是曹雪芹創作《紅樓夢》的嘔心瀝血,都是中外文學史上被一致認同,特別具有代表性、典型性的事實案例,所以作者以此作為“事實性論據”,當然很具有說服力。
《講話》指出:“中國精神是社會主義文藝的靈魂”,而“中國精神”的核心是愛國思想,所以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最深層、最根本、最永恒的是愛國主義”[2]。為論證這一觀點,作者列舉了大量古典詩文中表現愛國主義精神的名作佳句,例如北宋著名政治家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南宋杰出愛國詩人陸游的“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南宋愛國名臣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清代愛國政治家林則徐的“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南宋民族英雄岳飛的名作《滿江紅》,以及現代愛國志士、共產黨人方志敏的《可愛的中國》等,以這些舉世皆知、人皆認同,具有正確性、代表性、典型性的“事實性論據”,充分地論證了愛國主義精神自古及今都是中國文藝“常寫常新的主題”,也應該成為當代文藝創作必須唱響的主旋律。所以當代的文藝工作者必須肩負起歷史使命,有責任創作出更多宣揚愛國主義精神的優秀作品,“引導人民樹立和堅持正確的歷史觀、民族觀、國家觀、文化觀,增強做中國人的骨氣和底氣”[2]。
《講話》還指出:“追求真善美是文藝的永恒價值。藝術的最高境界就是讓人動心,讓人們的靈魂經受洗禮,讓人們發現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靈的美。”[2]文藝創作追求真善美,是《講話》提出的重要觀點之一。為了闡發這一觀點,習近平同志列舉了家喻戶曉、感人肺腑的優美短詩《游子吟》,他說:“一首短短的《游子吟》之所以流傳千年,就在于它生動謳歌了偉大的母愛”,宣揚了人類最真摯樸素的美好情感。習近平同志接著列舉了宋代文豪蘇東坡稱贊韓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的名句,并進而論斷從漢代到中唐文風經歷了“八代之衰”后韓愈之所以能夠崛起于文壇,就在于他大力倡導“文以載道”,并以自己的詩文創作承載了“道”、宣揚了“真善美”。習近平同志列舉從古至今人們普遍認同、也最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唐代孟郊的《游子吟》,以及在文學史上人們津津樂道的蘇軾論韓愈的著名案例,以事實作為論據,充分地闡發了文藝應該承載和宣揚真善美,激勵和引導人民群眾“向往和追求講道德、遵道德、守道德的生活”[2]。
自古以來中國文人寫作特別講究要有“文氣”,主張以充沛的“文氣”來增強文章的論辯力量,加強文章的感染力和說服力。鐘嶸《詩品·序》云:“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7]這是說文藝作品應該蘊藉著豐富深刻的哲理和撼人心魄的情思,并通過“感人”和“搖蕩”人之性情來實現其創作目的。事實上,文學作品對人類思想情感的“遷移”和“搖蕩”,都離不開潛藏于作品之中的“文氣”。歷史上無論是莊子的“汪洋恣肆”,還是韓愈的“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都源自作者在論說中灌注了浩然“文氣”[8]。《講話》可謂是立意高遠、“文氣”充沛的藝術佳作,其文本所蘊藉的“文氣”不僅源自蕩滌于作者胸襟的真知灼見,還來自作者的真情實感,當然也包括文本創作中選擇事實性論據時對于各種“事實”的理性判斷和運用“事實性論據”的情感滲透。
《講話》文本中組織了豐富多彩、貼近論點并力證論點的“事實性論據”,而且作者在論證中圍繞論點對“事實性論據”進行了鞭辟入里、透徹中肯的分析闡發,所以《講話》是一篇充滿了論證力量和說服力的議論文佳作。《講話》正是通過大量列舉與論點“相關性”強烈、“邏輯關系”緊密,并經過精選與剪裁而具有正確性、典型性、代表性的“事實性論據”,從而成功地構組了話語文本。事實勝于雄辯,“事實性論據”的成功運用賦予《講話》強大的論證力量和感人的藝術魅力,也使文本的字里行間激蕩著說服人、感染人、震撼人的浩然氣勢。
《講話》已經引起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學術界對《講話》的思想理論深度、對當前文藝創作的宏觀性指導和深刻社會影響力,以及文本創作的各種精彩點皆有論述。但從其文本作為議論文體對于論證方法的選擇運用及其取得藝術成就的視角,尚未有充分關注。故這里選取“以事實作為論據”的視角考察習近平同志《講話》在文本創作方面的論證方法和藝術特點,以期引起學界關注,并為全面細致地研究《講話》起到添磚加瓦的作用。
參考文獻:
[1]王鳳英.論說語篇的布局與論證方法[J].外語學刊,2005(5):63-67.
[2]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N].光明日報(電子版),2015-10-15(1).
[3]陳朵.議論文事實論據之選擇與加工[J].貴州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4):191-193.
[4]李卒.略論論據與論題間的相關性[J].廣州市公安管理干部學院學報,1999(2):28-30.
[5] 陳亞敏.論證有力量,要用好論據[J].寫作,2011(22):17-18.
[6]王林琳.議論文事例及道理論據的處理[J].西北成人教育學報,2002(2):78-79.
[7]鐘嶸.詩品全譯[M].徐達,譯注.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0:1.
[8]王寶大.議論文寫作技巧[M].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0:2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