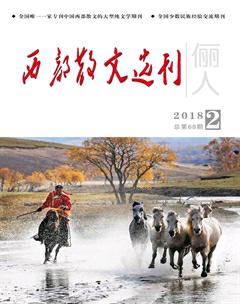祭母文
徐培春
一
曾經好多次爬過這條“之”字形的山路:陡峭、狹窄、潔凈。偶爾有個小石頭作為臺面,更多用來穩住腳步的,是一個個小土坑,小得像兒童玩具,便能判斷,從這里上下的,都是些年長的、體力不濟的人群。唯有路兩邊菜地里鋪開的大小長短不一的翠綠,跳躍著強烈的生命氣息。
今天也如此:陡峭、狹窄、潔凈。所不同的是,原來爬這個坡,是為了看望短時間住在半山中央教堂里的娘,今天卻是替娘來看望兩個曾經給她許多溫暖的羅長老和商姊妹。娘是個你敬我一尺,我要敬你一丈的人,她會很贊同我這樣做的,其實,她早希望我這樣做了。
我左右手分別提著一盒老年人營養牛奶,腳步艱難,心情忐忑。跨在左邊肩膀上的包,不時地滑落下來,歇下右手拉了幾次后,便隨它跟著我的腳步,啪、啪、啪,一下又一下地敲打著我的腿,后來,干脆放下兩個盒子,一屁股坐在小土坑上,俯下臉,輕輕地感受,感受媽媽留在這一個個山坡小坑里的溫度。
院子依然平靜和干凈——這是上帝居住的地方,干凈和平靜是上帝的本性。那只慵懶肥胖的大黃狗,慢騰騰地朝我走來,像迎接家人樣,蹭了蹭我的腿后,揚起臉來,好像在問:干嘛那么久才來?
三月,正是各色花開的好季節,院子里哨極了:三角梅、火焰木、辣子花,還有匍匐在地表上的藍色小花朵……這一切,都在告訴我,告訴到這里來的每一個人:生活就像這花兒一樣,經歷寒冬后,終究會在春天里綻放的。可是上帝啊,我的娘凋謝了,凋謝得徹底、干脆和無影無蹤!
以前每一次來,只要我的頭從土坎上冒出來,準能看見我風燭殘年的娘眨巴著混沌的雙眼頹廢地坐在教會門口脫了漆的長凳子上,每天下午,她都坐在這里。因為她知道,如果沒有特殊情況,她的女兒會踏著夕陽來看她。
我又來了,媽媽,你一定要坐在那條破舊的長凳子上啊……
聽到狗叫聲,老尚叔從廚房里出來,張開嘴,僅剩下的兩顆門牙便暴露出來。這個不足1.5米的老人,隨時一副好笑臉,以致他的一雙眼瞇成一條縫,他也是上帝虔誠的兒女。他說羅長老和商姊妹一起到外地傳教了,就他一個人在家。
我便給羅長老打電話,只簡單兩句,她就聽出了我的聲音,說話就沒有了生分:郭(媽媽姓郭,大名桂芳)大姐的姑娘呀?徐姊妹改?莫,郭大姐過世你們也不通知我們一聲,我們沒能去看她最后一眼,我們做的不夠,做的不好啊……
我涌到嘴里的感謝話,一下子打住,鼻子發起酸來。
最后一次送媽媽進醫院時,她提出這樣個要求:要教會里的姊妹去陪她幾天,我們付護理費用。當時我想的是,媽媽病得不輕,讓別人招呼不放心,再說,她生養了七個孩子,病入膏肓時刻卻請別人護理,于情于理都說不過去,于是,我沒有滿足她的要求,我們姊妹幾個,還有她的孫輩,一天24小時輪換著陪護她,直到歸西而去,都沒有通知教會里的姊妹。都是上了年紀的老者,怎忍心讓他們顛簸跋涉跑到我老家,讓他們經受失去姊妹的傷感?
我一直沒能理解教會在媽媽心目中干嗎如此重要。最長的一次,媽媽在這里居住了三個月,這里成為一個暮年老人最大的心理安慰,成為她心靈歸宿、港灣,從這點上說,我們非常感謝教會,感謝長老和許多的姊妹,是他們讓內心孤獨而復雜的母親擁有了一些平靜和短暫的快樂時光。
二
很多子女對過世父母抱有遺憾的原因是,“子欲孝來親不在”。我們則不,爹媽在世的時候,我們能夠而且堅決地守候在他們身邊,雖然普通平淡,但吃穿沒問題,疼病可以上醫院,可我們也有遺憾,而且是非常的遺憾,尤其是對我媽媽。
母親生于1925年農歷1月19日,這一天是太陽的生日,這成為她最值得驕傲的資本,仿佛出生在這樣一個與太陽有關的日子,一輩子都會被太陽的光環所照耀,陽光燦爛,順暢無比。事實卻是相反,媽媽的心情,始終是郁悶而暗淡的,她甚至都不愿意將大門向我們敞開過。媽媽走的那天是2015年農歷10月21日早晨,再熬28天,她就跨進九十一歲的門檻了,最終,媽媽沒有挺住,嚴重的心衰、心律不齊、心臟肥大和嚴重的胃病讓這個孤獨、堅強而固執無比的老人經歷幾天幾夜疼痛的折磨后,在那個濕漉漉的清晨,不顧我們的不舍和呼喚,義無反顧地回到上帝那兒去了。
90年,那是數不勝數的細碎腳步、數不勝數的竹編背籮、數不勝數的披星戴月堆砌起來的歲月啊,可真要說點什么,我竟然無從說起……
媽媽是個暗淡而孤獨女人。在暗淡的歲月里過暗淡的日子,跨進陽光燦爛的時光里,卻因為她已經習慣了那種暗淡的方式,也始終走不出,也不愿意走出她自己設想的悲苦,雖然她養大一男六女七個孩子,老年的時候子孫滿堂,個個對她孝敬有加,但歲月在她的心坎上刻下無法抹去的對家人子女深刻的懷疑和猜忌,她想依靠、她必須依靠,卻又不敢、不愿意、不甘心完全依靠,這讓她的內心更加痛苦和煎熬。
媽媽把壞日子過好了,卻把好日子過壞了。
三歲的時候,媽媽的父親病世,六歲那年,她的親娘改嫁,把她和唯一的哥哥放在老家,隨年邁的奶奶及態度不太友好的嬸嬸生活。哥哥是草根媽媽的靠山和燈塔,可這個小男子漢也狠心,早早就撇開他妹妹自個兒離世,媽媽在寒冷、饑餓、孤獨和無限的超出年齡局限的勞作中度過了她的童年、少年和青年:饑了野果裹肚;冷了拖床蓑衣到火塘邊過夜;想娘了,跑山背后哭一場……媽媽像一棵生命力極強的小草,挺過了無數的磨難,麻木不仁地迎接著每一個據說生命中就屬于她的太陽,可是,意外的驚喜從未降臨到她的頭上,歲月到把她雕琢成一個高挑、清秀、皮膚細膩白凈的大姑娘,只是,她從沒認真穿過一件衣裳。
媽媽把過上好日子的希望寄托在婚姻上。
我爹是搞生產的能手,但絕不是知冷知熱的丈夫和父親。他的規定動作簡單、粗糙卻堅持不懈:天亮出去做活計,天黑回來吃飯睡覺,家里長短很不上心。六七時年代的農村,那是天地都在鬧饑荒餓肚子,加上我們一大家子八口人呢,媽媽的心,簡直是操碎無數次!她除了要和我爹一樣,為我們姊妹幾個不至于餓死而付出所有的體力和智慧外,還要打理我們成長過程中所有的瑣碎……媽媽走路永遠是碎步小跑,直到她再也不會站立在大地上行走;媽媽吃飯必須有湯,她把湯泡在飯里,稀里嘩啦就倒進肚里了,她說,只有懶人和憨人才會在吃飯這樣的小事情上耽誤時間。如果不是長年累月不科學的飲食習慣讓她的胃變成一張爛網,也許,現在她還能和我一起坐在沙發上看電視。媽媽這輩子最喜歡做的事情是養豬,這也讓她獲得無數稱贊和羨慕,成為寨子里最賢惠最能干的媳婦。不養不行啊,不養好更不行,吃賣各半的年代,她就憑半丫豬肉(那個年代,一頭豬自己只能留下一半,另外一半必須上交給國家)囫圇她的一窩兒;媽媽睡眠方式與我們正常人相反,她晚上睡不著,白天卻能呼嚕嚕,這也是年輕時養成的習慣。晚上切豬食、烀豬食——豬養的多,吃的待遇也不同:年豬吃的比較精細,粗食里加大瓢糠或者小碗紅薯;生兒的母豬,媽媽侍候得就更上心,攪半盆稀包谷面摻在芭蕉里;架子豬,就純粹是粗糙食,媽媽一晚上差不多要切好、煮好三鍋豬食,只能拄著火鉗在鍋洞門口沖瞌睡,歪過來,扭過去的,豬食弄好了,天也差不多亮了,揩把臉,媽媽就出山做活計了。endprint
貧賤夫妻百事哀。爹媽經常吵架,任何事情都可以成為導火索。媽語言豐富,動作也靈巧,我爹絕不是對手,他就采取家庭暴力,開初幾次得逞,后來,媽就鬼了,吵到眼冒火星,看行頭不同,她撒腿便跑,我爹只能捏著棍子干瞪眼。媽媽過上好日子的希望,在她看來,是徹底落空了!從此,她堅信,這個世界沒任何人可以相信,除了自己;沒任何人可以依靠,除了自己!這個想法左右了她一生,也為她的晚年生活留下深刻的陰影。
媽媽對爹的仇恨,是堅決的、徹底的,始終沒有原諒的,可是選擇墓地的時候,媽媽選擇了雙墓,爹才走了半年,媽媽也跟著走了。每次走到他們倆的墳前,我都會這樣想:媽也是牽掛我爹的,是固執而要強的性格讓她做了在陽間不愿意妥協,那就在陰間長久地廝守的選擇。我們給父母修了漂亮的大房子,燒了很多的紙錢,他們可以衣食無憂地過二人世界,補償在人世間沒有相親相愛地過好日子的遺憾。
媽媽恨我們為什么爭先恐后地擠進她的世界,讓她的身子、思想和日子都沒有輕松清閑的時候。在懷孩子、生孩子、奶孩子、前后背著孩子干活計的勞累中度一天天,一年年,苦的像頭牛,更主要的是,一個個張開的嘴巴,所等待的不是喝開水啊,一天兩頓飯,再如何忽悠,也是得弄出來的,何況,除了最大的是兒子,其他的一扒拉都是丫頭,是臉朝外的,幫別人養的——這樣的老觀念,在媽媽腦海里牢固的很,對這一窩兒,她不打則罵,基本沒有什么好臉色,一路怠慢到什么程度,就連一個正規的名子都不愿意給,除了給哥取名為“昌”;給大姐取名為“環”之外,其他的,就是老二,老三、老四、老五、老六地叫喚——這就是媽媽給我們的一輩子的記號了。我們的學名,都是進學校后老師給取的。
媽媽信奉棍棒底下出人才。除了她追求完美之外,是她沒有時間精力,也沒有能力教育這大窩兒的。也是,一個山溝溝里沒有父母呵護撫養的文盲,能夠懂多少教育孩子的道理呀。放豬的,沒有全部趕回或者吃了莊家要用棍子收拾;安排澆菜水的,任務完成不認真要被收拾;安排煮飯的,因為貪玩天黑也還沒煮好飯,要被打屁股;要是在學校犯了點小錯誤,被長嘴的告狀到媽媽那兒,天差不多就要戳通了。
媽媽始終是比別人聰明的,除了大姐實在沒有能力供之外,其他的,統統趕進村辦小學,把我們交給從昆明下放來的周老師。
再艱難的歲月,童年都是愉快和幸福的。每天放學回來,用最快的速度完成自己的任務后,我們就奔到公路上,一大群衣角破爛飄飛的孩子,玩各種各樣的游戲,笑聲塞滿小寨的每一個角落。
每天重復勞身、勞心和勞神的生活,媽媽時不時表露出對生存的無奈和絕望,讓我們有了她想推卸責任和義務自己解脫的擔憂。如此艱難的生活,選擇拋棄或者死亡是完全有可能的啊!于是,深刻的恐懼攫住我們流水樣的心:無論到哪山哪凹,無論暴雨烈日,我們姊妹必須有一個人跟著她,其實,就是跟蹤了。晚上媽媽煮豬食的時候,我就拖床蓑衣睡在她腳跟前。有天晚上,娘看著雙手夾在腿間,灰老鼠樣卷縮著熟睡在蓑衣的我,輕聲叨念到:黃毛丫頭、黃毛丫頭!眼淚掉在我的額頭上,高度緊張的我“霍”地跳起來抓住媽媽的手,她一把摟我進懷里,把她的臉貼在我的臉上……
三
再如何的抗拒,我們終歸是娘身上掉下來的肉,她粗糙而暴戾的母愛,經常在棍棒底下閃現出來,娘最怕的,是我們生病。生病了沒錢請醫生,生病了得耽擱活計。
我們家下面有一條清澈見底的河,距離我們家只是幾步遠,進入夏天,這河就是小屁娃娃的樂園:光著身子,泥鰍樣在水里鉆出鉆進。我們姊妹幾個是不能去的,媽說過,會被冷著,會生病,不能去。我三姐比較叛逆,經常干“你說你的,我做我的”這樣的事情。有次,我媽就捏著細棍子蹲在水潭邊,等我三姐摔著頭鉆出水面,本來就青的臉,見到娘就成紫的了。娘扭著三姐的耳朵,一路用細棍子抽著三姐稚嫩的小屁股,一邊抽一邊問:你還敢來洗澡?你還敢來玩水?三姐被抽得一驚一跳,屁股上留下紅紫相間的痕條,殺豬樣哭嚎著拖回家。我們圍過來幸災樂禍地問她:細棍子抄牛肉給好吃?細棍子抄牛肉給好吃?“呸!”三姐朝我們臉上吐了口吐沫,倔強地一轉身,跑開了。我們的聲音追著她的身影繼續幸災樂禍地狂叫著:細棍子抄牛肉給好吃?細棍子抄牛肉給好吃?幾次下來,我們誰都不敢再到河里悶澡了,即使是去放豬,也就在沙壩上翻石頭,捉小石花魚。所以,我們姊妹七個都是旱鴨子,這在寨子里,在小伙伴面前,是非常沒有面子的。
媽媽怕我們生病還表現在對我們月經期間的特殊照顧。這個時候媽媽稱之為:“身子不方便的時候”。媽媽說,身子不方便的時候注意不好,會落下很嚴重的病,這樣的病很難治好。這個時候,是不用出山去干重活,也不用到水里栽秧的,只要在家里做飯、喂豬就行。當然,冷水和冷的東西是不能吃的,如果媽媽心順了,還會給“身子不方便”的姑娘煮碗雞蛋湯,因為六個姑娘嘛,個個發育都還比較順溜,一個月下來,家里差不多都會有“身子不方便”的姑娘在做家務,可吃雞蛋湯之類的待遇,除了大姐之外,是少之又少的。大姐因為要供自己的哥哥和妹妹讀書而沒能上學,對她,媽媽一直是愧疚的,直到最后咽氣,她最心疼的,還是大姐。她幾次對大姐說:“環,我買了很多衣服褲子,全部給你,不要都燒給我,那是人做給人瞧的,沒意思”。加上大姐有痛經的毛病,每次身子不方便的時候她都可以名正言順地吃上雞蛋湯。
其實,我們生病了,媽媽會心疼的,而且是很疼。這點,我到十二歲那年才領會到。
那次,小伙伴們一起跳玩的時候我的左手腕折了,骨頭差不多要戳破皮膚,樣子很可怕。出現這樣的意外,媽媽是不會心疼的,她甩給我們兩巴掌,還咒罵說:跳嘛,再跳嘛,這回給是跳得吃了?給是跳好在了?大山養育的孩子,生命力特別強的,斷個骨,流點血之類的,那簡直不當回事的,這方面的民間醫生到處有。附近村寨骨傷的,基本上去找一個姓郭的永遠佩戴一頂變色氈帽的小個子老頭,包幾次臭烘烘的草藥,個把月后,基本恢復。治療費用也就是一只雞,幾個蛋,最高級的,就是幾把掛面(面條)了。endprint
媽媽把我送到郭醫生那,每次換藥包扎,媽媽用雙腿夾住我的下身,雙手箍死我的身子和右手,郭醫生把我稚嫩的左手當一只沒有生命的蓮藕,捏了又捏,搓了又搓,之后用針戳……我都疼得死去活來,衣服全被汗水浸濕,嗓子叫啞哭破。三個月后,我受傷的左手腕依然伸不直,并且,與右手相比,明顯地細了,我整個人,也像被螞蟻吃了心的芭蕉,焉焉的。娘焦心了,跟我爹商量:小五的手怕不能這樣拖著了,他們說,大毛木樹有個草醫,醫骨頭斷裂厲害,包幾副藥就好,怕得領去瞧瞧?爹自然不管這樣的小事。
天還沒亮,媽媽把我從床上拖起來,朝那個叫大毛木樹的地方奔去。媽媽一直拉著我的手小步地跑。她說,她還要趕回來,陌生的夜路她不敢走。我實在跑不動了,媽媽就背我一小段。
一路上,媽媽喘著粗氣,斷斷續續地交代我:路程遠,你就在醫生家住幾日,扎扎實實地包藥,我回來做幾天活計就來接你。住在別人家,要勤腳快手地做事,肚子吃個半飽就得,下次來,我會把米背來,按一天一碗米的標準給醫生家。你不能像在家里樣瘋瘋癲癲的,還說,小姑娘家,要是左手伸不直,要是左手跟右手不一樣粗,就是殘疾,殘疾就做不得活計吃,嫁男人也難……她就重重復復地說這些話,說要是她不把我的手治好,長大了,我會怪罪她這個娘的。
這雞腸子樣的山路,可真是遙遠啊!翻過一座山,又是一個凹,娘總說,要到了,要到了,卻總是不到。我的腳起泡了,泡又被磨破了,手上、腳上都鉆心地疼,我沒敢哭,怕媽媽罵,怕媽媽傷心——我們姊妹幾個從小都養成這樣的習慣,自己的事情自己扛,不給父母增加壓力。
等媽媽把我交給那個慈眉善眼的老奶奶轉身回走時,我用健康的右手撕著她的衣角不放,她一巴掌打開我的小手,跑了。她在前面跑,我在后面追,一邊追,一邊哇啦哇啦大哭……
兩個山凹后,看不見娘的身影了,我站著哭嚎了一會,抽抽搭搭地往回走。走過一棵大麻櫟樹腳時,聽到斷斷續續的抽泣聲,那是我娘的聲音!那是娘在心疼我!
這個發現,很讓我釋然。反正得留在這里,反正得把這手給治好,反正不能跟媽媽回去,反正……這樣想,就裝作沒發現樣子,慢騰騰往醫生家方向走。在拐角處,我一閃,鉆進一篷長勢繁茂的茅草叢中。媽媽果真從麻櫟樹后面梭下來,朝我這邊方向深深地望,停留幾分鐘后,她的抽泣變成了哭啼,無可奈何罵著:黃毛丫頭,我不有辦法呀,黃毛丫頭,你要聽話點噶……我把右手拳頭咬在嘴巴里,幸福極了。
四
還以為,把媽媽從老家接出來,和我們一起住在小城的小樓里,過一種純粹的城里人的生活:吃菜、吃糧出錢買,煮飯不燒柴,喝一口水,上個公廁也要掏錢——這是做子女的對她最好的回報,也是媽媽晚年生活的最好安排。殊不知,習慣赤腳踩在泥土上的老人,一下子移居到喧鬧小城,一整天在一百來平米的空間打轉轉,是何等殘酷!
媽媽也出去找伙伴,但小區里老人很少,能夠與我娘有相同話題聊的,就更少了。在街上轉幾圈,她便找不到回家的路。因為聽不懂普通話,看不懂電視劇故事情節,她也只能看“動物世界”這個欄目,看她所熟悉的豬、牛、羊…….很多時候,她就只能坐在沙發上打發時光了。下班回家,打開家門,媽媽幾乎都坐在沙發上等,無論中午還是下午。直到現在,每次回家我都很急切,總有這樣的幻覺:媽媽就坐在沙發上等我,等她的女兒回家……
不知道媽媽是何時找到她的庇護神——耶穌的。可走進基督教教堂,走進她眾姐妹中間,確實是她最后時光里的美好享受,她覺得,這才是她自己的家,是她靈魂歸宿地。在那里,她不用懷疑,不用防備,不用擔心。
一個小縣城里的基督教堂是否能把基督教核心傳播的準確、真實,我沒認真去了解過。其實,這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基督教堂讓我媽媽和像媽媽那樣暮年的老年人堅定了自己的信仰:人類是有罪的,上帝是仁愛的,所以派自己的兒子耶穌來拯救人類贖罪靈魂。這個場所讓煩躁不安的媽媽平靜了下來。每個周末早上準時梳洗干凈后到教堂去做禮拜,平時早晚必須禱告,從沒進過課堂的人,硬是叫我女兒教她讀圣經,教她唱圣經歌曲。有段時間,媽媽干脆跑到教堂和羅長老,尚姊妹一起吃住,最長一次是住了三個月,我和姐姐除了準時給她送伙食費、打針吃藥錢之外,周末我們要抽時間煮點好吃的送上去,讓媽媽和她的姊妹們分享。這個小小的不值得一提的行為,贏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在媽媽眾多姊妹中,我們穿上了“孝順”的外衣,媽媽為此也吃得踏實、住的安心,甚至是理直氣壯。的確,那些子女不管或者管得很少的老人很羨慕媽媽,其實,內心深處,我多少有點推卸責任的,媽媽住在那里,她開心愉快,有熱飯吃,疼病有人招呼吃藥,我自己也輕松多了。媽媽,這是多么大的罪惡啊!
近三四年來,媽媽精神方面的疾病表現越來越突出,身體稍有不適,就懷疑自己的娃娃在飯菜里下毒藥了,她要趕緊跑醫院打解毒的針水,當然,醫生不會給她打,或者跑到農貿市場買個黃瓜生啃吃,她說,生黃瓜解毒。平時,媽媽是不吃涼東西的,哪怕水果也很少吃。
有個晚上,十二點多了,住在同一個小城的姐姐打電話給我,她哭得委屈傷心,要我火速趕過去,送小住在她家的娘上醫院。不用說,我就明白是咋回事情。在姐姐家,娘像只被人追殺的蒼老無助、無處可逃的貓,躲在昏暗的廚房角落啃生黃瓜。她有氣無力地說:這個背濕姑娘,她在三七燉肉里下毒藥,她要毒死我……媽媽分別在她的七個孩子的家里呆過,高高興興地去,罵咧咧地回到我這兒,促使她離開的內容只有一個:她的娃娃在她的飯菜里下毒藥。一個風燭殘年的老人,一個只能飯來張口衣來伸手的老人,她活在這個世界上最親的、最可以依靠的就是她一手拉扯大的孩子們,可在媽媽的心目中,我們是她的敵人,是隨時在窺視她捏在手里、其實也是我們給她的幾張紙幣,隨時要她老命的敵人,這在媽媽心里,是何等痛苦的事情!對于我們來說,更是無法釋懷!
要是給媽媽做個小灶,燉點補藥什么的,嫌疑就更大了,她認為,里面一定是下了毒藥的,即使我們故意在她面前吃給她看,也是沒用的。有一段時間,她甚至自己買了個小茶缸,吃飯時間就抬著茶缸搖搖晃晃地走到農貿市場快餐店,打一塊錢的飯吃,遇到好心的店主,會給她舀一點點菜,一般人,把她當混吃的,隨便打發她半小勺米飯,加一勺免費的米湯或者討口開水泡飯。遠遠地看著媽媽,像棵枯老不堪的樹樁蹲在墻角,稀里嘩啦地扒口缸里的飯,我泣不成聲,心堵得只想把胸口破開!萬能的耶穌啊,請你告訴我,我們該怎么做,才能解開媽媽的疙瘩?endprint
媽媽身上沒缺過錢,但她舍不得用,她總擔心在需要錢的時候,她的子女會不管她,故而拼命攢。開始給她錢,還比較拘束,后來是直接開口跟我們要,理由只有一個:看病。媽媽過世后,我們姊妹幾個給她凈身、穿衣服,收拾床鋪,在她墊的棉絮里、枕頭殼、衣服口袋、背的包,還有抽屜里,到處別著錢,面值大小不一,小幣居多,這是因為在銀行工作的姐姐比較細心,給媽媽的錢基本都要求我們都兌換成十塊、二十塊或者五十塊的紙幣,方便媽媽使用,她卻都積攢了起來,足有三萬多……
醫生說,媽媽這叫妄想癥,是一種很頑固的精神疾病,導致此病的原因很多,癥狀就是想當然,懷疑一切,越是與她親近的人,她越懷疑是要加害她的人,嚴重的會導致自殘,年近90的老人,醫生建議不用藥物治療,說是副作用特別大。“避免她傷心生氣,盡量讓她開心高興”,醫生建議說。可是,對于媽媽來說,她最不相信的人,就是她的七個孩子了,無論我們再怎么做,無論她教堂里的姊妹、親戚還有寨子里的鄰居如何跟她做工作、講道理,她都認為,世界上最壞的人,就是她生養的這七個,為此,她無數次地沉浸在這種親人變成壞人的悲痛中,從而處處防備,事事小心,因為健忘,她經常找不到自己放的東西,都怪罪是我們給偷了,我們變得越來越壞,壞得她無法容忍。
不得不承認這個事實的時候,我們姊妹七個面面相覷!
好吧,我們不改變您的觀點和看法了媽媽,只要您覺得這樣想、這樣做是愉快的,你就按照你的方式繼續吧,我們愿意做你的“敵人”,做您永久不變的“敵人”,我們需要的,我們盼望的,就是能夠天天守候在您身旁,與您為“敵”,我們愿意以這樣的方式與您一起生活。
特地回老家來照顧媽的哥哥,只好一天三頓地把飯菜做好了從廚房的墻洞里遞出去,堂里的嬸嬸在外面接了后送我媽媽,媽媽一直以為是嬸嬸做的飯菜,還夸獎她手藝好,伺候老人有耐心,都是她喜歡吃的。
進入2015年春天,媽媽的狀況更差了,我只好再次把她送進醫院,姐妹們輪流24小時照顧,最大的難題,還是吃的問題,身體不好,媽媽的疑心更重。下了班,匆匆忙忙做好送過去,她說,不餓,其實,是不敢吃。只好費盡心思找借口或者托別人,告訴她是快餐店買的。第二次住院時候,我們遇到秀英娘,這是個善良的老人,照顧生病的弟弟,與我們的媽媽住在一個房間,了解媽媽情況后,她主動提出幫助我們,每天,我們把飯送到走廊上,秀英娘就故意問她:大姐,我要打飯吃了,幫你買回來,你姑娘給我錢了,你想吃點什么?秀英娘出去走廊轉轉,抬著我們送的飯進病房,還會一口一口喂給媽媽吃,邊吃邊聊,媽媽很開心,甚至發出暢快的笑聲。媽媽病重送回老家后,秀英娘還特地跑去看她,走的時候,媽媽拉著秀英娘的手說:相親相愛的人,是裝在心里的。
好人一生平安,秀英娘,我們深懷感激。
五
媽媽最后一次住院是2015年11月18日,這是她在這一年的第五次住院。心臟肥大等一系列嚴重的器官衰竭讓媽媽疼得日夜不眠,她已經沒有力氣猜疑我給她吃的藥是否有毒了,只要給她吃藥,她心理就有安慰,就有盼頭,就有活下去的希望。其實,媽媽多希望能夠繼續活下去。她經常自我安慰說,教會里的姊妹們很羨慕她,說郭大姐臉色紅潤,頭腦清晰,活到一百歲一點問題都沒有。實事是,藥物對媽媽的作用已經不大了,一輛歷盡歲月磨礪的破舊不堪的老水車,再也無法修補好了。在醫院里,媽媽徹夜不睡地說混話,更多的,是叫那些已經作古的親人們的名子,叫得親切,叫得心碎,叫得最多的,是她的哥哥:哥,哥,來領我,來領我……實在太累了,她瞇瞇眼,睡那么一會,又開始叫喚。我們像抱一個小孩子樣,輪流著把媽媽輕輕抱在懷里,一刻也不敢放開。
無論活的多長或者多短,人最終的結局是相同的——死亡。看著自己最親的人,從健康走向衰弱,然后,生命慢慢地遠離,而自己卻束手無策的過程,這是何等的殘酷!我的親娘,我留得住太陽,留得住青山,卻拉不住您逐漸遠離的步伐啊!
爹在十多年前就患上老年癡呆癥,痛苦和快樂不表現出來,他是在姐姐喂他吃稀飯的時候閉上眼睛的,走得安詳、平靜。媽媽生命的過程,讓我,讓我們姊妹的內心受盡了折磨和煎熬。
看著鏡子里媽媽樣式的臉盤、鼻子、眼睛和嘴巴,我就堅信,其實,父母從未遠離,他們就存在于我們的體內,血液里。
——選自作者新浪博客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