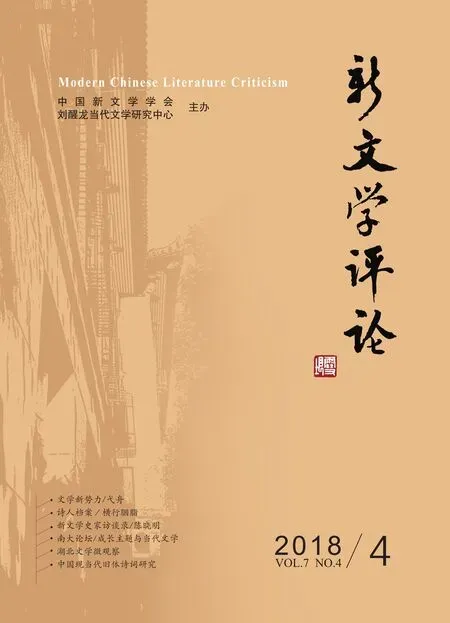暗夜劃過詩意的光
———弋舟小說讀記
◆ 宋 嵩
底層境遇的關切與命運抗爭的吶喊
作為一個對社會底層困頓境遇格外敏感與關注的作家,弋舟在自己的作品里塑造了這個時代被侮辱與被損害者的群像,其中又尤以少年和女性居多。他向社會最脆弱和最軟弱的一部分投去了最為關切的目光,用心感受著他們的悲歡離合。而對于作為社會中堅力量的中年人群,他則極力彰顯他們在命運泥淖中的徒勞掙扎,以及對天涯淪落人之間相濡以沫的渴望。
《蒂森克虜伯之夜》寫一個長相英俊似“快男”陳楚生的顢頇少年是如何在對未來的懵懂憧憬中逐漸被金錢的勢力所戕害的。“蒂森克虜伯”這個全球性的鋼鐵和機械制造業巨頭,在小說中化身為“另一個世界”的代名詞。它和它所生產的“電梯”這一現代社會中司空見慣的事物,每每賦予來自偏僻小鎮的夜總會“少爺”包小強一種迥異于故鄉生活的戲劇性和儀式感,成為少年心目中臆造出的說不清道不明的“最高象征”。十幾年淳樸曠達民風的熏陶,終究敵不過幾個月來“夢幻一般的場所”里紙醉金迷的耳濡目染,少年幾乎就要淪落為被富婆包養的面首。但事態就在富婆一句不容置疑的“跟我走”之后急轉直下,包小強“蒂森克虜伯”式的夢態之旅被血淋淋的事實所驚醒:先是被富婆拋棄在荒郊野外漫天飛舞的鈔票里,繼而又在撿拾泥濘中的鈔票時被富婆的轎車碾斷了左腳。至此,曾經被女同學兼同事的高麗揭示過的世界真相原原本本地在包小強面前展開:那個由“蒂森克虜伯”所代表的“最高象征”,其實完全不屬于包小強這樣的窮人,他們都是被這個世界消費的“消費品”,有錢人可以在對這個世界的惡意消費中獲得縱情的歡笑和快感;若要擺脫這種被消費的處境,只有像高麗那樣,認清鈔票的霸道,摸清釣大魚的所有規矩和門道,讓自己成為合格的誘餌,甚至不惜欺騙和犧牲自己周圍同樣汲汲于生存的螻蟻們。小說中最令人觸目驚心的一幕是,即使自己的左腳被車輪碾斷,包小強的手里依然還攥著一把濕漉漉的臟票子——富人可以用金錢來輕描淡寫地抹去自己的罪惡,這是物欲橫流的時代里的基本邏輯,它同樣深刻地體現在《夏蜂》(又名《禮拜二午睡時刻》)中。在這個向馬爾克斯致敬的短篇里,弋舟將自己營構環境氣氛并以此來引領人物心理波動的本領發揮得淋漓盡致。整篇小說被籠罩在夏日午后燠熱、沉悶而慵懶的氛圍里,交織其中的是嘔吐物的餿臭和墮胎的血腥味。這一切都與主人公母子二人此番進城的目的地——有大塊草坪、爬滿藤蔓的鐵柵欄、噴泉和穿制服的保安的小區格格不入;屬于這里的,應該是也只能是丁先生家里咖啡的焦香。男孩此前只在電視里見過的“喝杯咖啡吧”“加點兒糖吧”,和他手中盛著自家用芹菜葉漚的漿水的可樂瓶一起,構成了世界的兩級。正如從來都不曾真正存在平等的雇傭關系一樣,咖啡所代表的一極天然地對漿水所代表的一極具有壓倒性的優勢:進城打工的“保姆母親”在雇主丁先生的引誘(或者是脅迫?小說中并未明說)下懷孕,丁先生面對找上門來的受害者卻表現出“愛莫能助”“置身事外”的姿態,最終用一只裝著錢的牛皮紙信封將事態化解,只留下小診所門外雞下水堆里“一桶血糊糊的垃圾”(墮下的胎兒)。在不可一世的驕陽下,“母親整個人光芒閃耀披著金色的紗巾,宛如站在未來的世界里”,這顯然是一個圣母般的形象,她用自己被侮辱的尊嚴與被損害的身體,換來了那個信封,以及男孩從未曾得到過的百元大鈔。就像抽象而縹緲的“蒂森克虜伯”之于包小強一樣,在男孩心目中,其實并沒有真正嘗到的咖啡的滋味成為另一種生活、另一個世界的象征,并被自己有限的經驗想象為“油脂與蜜的混合物”。當母親的掌心向他傳遞出“暗自生長”的希望,裝著鈔票的牛皮紙信封似乎昭示著由生活的一極向另一極啟程的可能性時,他“故作輕松地用普通話鄭重其事地說:‘喝杯咖啡吧,加點兒糖吧’”。但隨之而來的便是勢不可擋的嘔吐——這意味著男孩在一瞬間洞悉了世間的本質,紛繁的景象、混雜的氣味和殘酷的事實,使他的心智有了成熟的可能。
《蒂森克虜伯之夜》和《夏蜂》為我們呈現的成長歷程,或酷烈或含蓄,都是借少年的懵懂眼光去認識世界、感受苦難。而《鴿子》所表現的,則正是一個少年對自我認定的苦難根源所做出的決絕報復。與《夏蜂》類似,《鴿子》中少年的母親也承受了侮辱和損害,但卻是為了一個攤位而與廣場管理處的人所做出的交易。這個令人羞恥的隱秘,和為了抑制廣場鴿繁殖而強制摻雜在鴿食里的避孕藥一起,成為少年仇視這個世界的誘因。在他眼中,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事物,包括面容姣好、青春靚麗的打工少女楊如意,都難逃被那些腹部隆起、頭發稀少、終日悠閑得令人發指的中年男人所戕害的命運。他們就像那些大腹便便的雄鴿一樣擠占生存空間并毫無節制地繁殖,世界因他們的存在而變得骯臟不堪。最終,他以少女的監護者自居,以為少女也為自己向這個世界復仇的名義,殺死了原本無辜的、被中年危機困擾著的失業編輯祝況。作者將一樁兇殺案的始末完整地呈現在讀者面前,敘述腔調隱忍、克制,近乎冷酷,彰顯出持久的苦難對人們心靈的扭曲與荼毒。
《鴿子》對少年一家的生活窘境著墨并不多,卻通過少年對人間歡樂的冷峻審視,傳達出鮮明的壓抑感。更令人值得深思的是,少年身上長期以來郁積的暴戾之氣,除了來自日常生活中承擔的與年齡不符的艱辛(“一個本應坐在學校里讀書的人都要辛勞地操持小買賣”),更是現代社會人與人之間冷漠關系的直接產物。這一主題同樣突出地反映在中篇《天上的眼睛》中。作者以第一人稱沉痛而壓抑地陳述了充斥在一個中年男人生活中的苦難:下崗失業、妻子外遇、女兒叛逆、壞人橫行、奸夫霸道……但相較于竊賊捅來的刀子和奸夫幫兇抽打在自己臉上的拖鞋,更令人難以忍受的是周圍的人(包括親人)眾口一詞的指責:一切苦難的根源,都被他們歸納為“我”不懂得及時閉上眼睛、不懂得裝作看不見、不懂得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在他們那里,生活的真諦被歸納為一句話:人窮就要志短,就要能吞得下事情。而在《雪人為什么融化》中,“我”因一場網戀招惹了黑社會老大李老板的“妹妹”,從此給自己帶來無盡的麻煩,甚至連自己親妹妹的安全都受到了威脅。在種種努力都徒勞無功之后,“我”只能突破尊嚴的底線,以自殘的方式去跟李老板謀求和解。“我”的朋友包爾剛之流平日里掛在嘴上的“長了腦袋,就要敢于迎著南墻撞上去”的豪言壯語,在強大的邪惡勢力面前不堪一擊,為求自保謀劃出諸多荒唐又空洞的解決方案,卻比不上“我”和平日里倍受單位同仁歧視嘲諷的女會計楊玉寧之間的同病相憐。最終,“我”鼓起了“捍衛所有的妹妹”的勇氣,向著惡勢力做出了自己微弱卻又悲壯的抗爭。
“捍衛所有的妹妹”幾乎可以視為弋舟早期創作反復書寫的主題之一。他的小說中屢屢出現被囚禁在生活的煉獄中,等待捍衛和拯救的女性形象。她們或者是被歲月的風沙打磨得蒼白憔悴,無從把握自身的命運而最終淪落為時代的犧牲品(如《我主持圓通寺一個下午》里的徐未);或者是被家庭、親人和陳腐的倫理觀念所傷害,在生活的浪潮里隨波逐流,用肉體換取心靈的安慰(如《黃金》里的毛萍);或者是默默啜飲親人離去的苦酒,孤獨承受著人世間的悲涼(如《空調上的嬰兒》里的母親);更多的女性則因無力抵抗彳亍于世的孤獨和窘迫的物質生活,將心靈出賣給金錢與欲望(如《凡心已熾》里的阿莫、《金枝夫人》里的金枝、《跛足之年》里的羅小鴿)。在這些女性身邊晃動的,大多數是卑微甚至猥瑣的男性形象,非但無力用自己的肩膀扛起捍衛她們的重擔,在堅硬冰冷的現實面前常常不擊自潰、落荒而逃。長篇小說《戰事》所集中反映的,就是一個少女在成長過程中尋找屬于自己的英雄、謀求巨大的粗魯的溫存的主題。因為父親的猥瑣和在母親外遇事件中表現出的齷齪,少女叢好體會到“凌厲的屈辱感”,因此,她將敢于對美國霸權說“不”的薩達姆作為心目中的偶像。她先后經歷了與張樹、小丁、潘向宇三位丈夫(男友)的感情生活,他們或粗獷野蠻,或陰柔文靜,或舉手投足間都透著主人的氣勢,卻始終都無法讓叢好安心地托付終身,難免換回“為什么到處都是低三下四的男人”的感慨,甚至為此落得傷痕累累,身心俱損。而薩達姆被俘后爆出的真相——“他一直試圖為自己樹立‘硬漢’的形象,但事實證明他是一個懦弱的膽小鬼”——也使叢好泯滅了心中對這個世界的最后一絲幻想。在小說的結尾,她“在一種戰后一般的寧靜中,終于和自己和解”,也為“捍衛所有的妹妹”做了最好的注腳:女性的命運,終究還是要由女性自己做主;而男性倘若想擔負起社會和家庭賦予性別的責任,首先要戰勝自己身上猥瑣齷齪的劣根性。
詩人氣質與理想主義情懷的抒發
弋舟是公認的具有詩人氣質的小說家。這種氣質最為直接的表現,就在于他的小說中詩歌、詩句的出現頻率極高。《我主持圓通寺一個下午》的寫作由詩人獨化的同題詩歌誘發,“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的漢樂府詩則敷衍出長篇《我們的踟躕》。詩句在《賦格》《被遠方退回的一封信》《嫌疑人》等篇目中承擔起篇首題辭的作用;而在《所有的故事》和《戰事》里,“即使明天早上/槍口和血淋淋的太陽/讓我交出青春、自由和筆/我也決不會交出這個夜晚/我決不會交出你”(北島《雨夜》)的詩句反復出現,成為結構全篇的關鍵,其中所詠嘆的“堅貞與背叛”的主題,甚至成為弋舟小說創作的母題之一。
在弋舟筆下,詩人、詩歌總是與一個早已遠去的時代存在著密切的聯系,或者說,詩人、詩歌就是那個時代的象征。在短篇《嫌疑人》中,詩人直接登場,詩人、詩歌與時代、現實、生活的關系,成為作者思考和喟嘆的核心。曾經的詩人格桑,“如今已經成為一個標準的中年男人,有了醫療保險和住房公積金,有了亞健康和一個女兒”,成了“一條生活在盆地里的魚”。通過小說字里行間透露出的信息,我們大概可以總結出導致格桑現狀的原因:曾經和妻子(那時候“也是一位將世界簡單化的詩人”)一起在西藏不羈地流浪的格桑,因為經受不起艱苦的考驗(“睡在羊圈里”)而與現實妥協,最后難免回歸盆地里日復一日的平庸生活。現如今,格桑的妹妹投入了一個瘸腿詩人唐克的懷抱,義無反顧地盜竊了金庫里的巨額現金潛逃;格桑面臨著抉擇:是以一個世俗之人的身份去“捍衛”自己的妹妹、干涉她與詩人的愛情,還是忠誠于一個詩人的初心、冒著包庇貪污犯的風險、以詩歌的名義去成全這場畸戀。作者將主人公格桑、唐婉,以及讀者推向了一個兩難的境地,倫理、法律、理想之間相互拮抗,形成了巨大的張力。通過《嫌疑人》這個題目,弋舟似乎是想告訴讀者:“詩人”們就是當下這個一切從實際利益出發、輕視理想的社會和時代里的“嫌疑人”,他們的所作所為,常常會有挑戰、背叛這個社會和時代里約定成俗的規則的嫌疑,他們必須具備敢于承擔質疑甚至審判的勇氣。

回望歷史與觀照現實
在探尋解讀弋舟小說的關鍵詞的過程中,“歷史意識”是一個繞不開的重要節點。他曾坦言,“‘歷史意識’在我們的寫作中從來都應當是重要的,我們必須知道我們是誰,我們從哪里來,由此,去揣度我們將向何處去”。盡管他像大多數“70后”小說家一樣,是通過對日常生活的關注和描摹開始自己的敘事實踐的,歷史意識的養成需要有一個隨著年齡增長和閱歷積累而漸進的過程,但當他真正將關注的目光投向這一領域,便展現出超越同代人的真誠與深刻。
《跛足之年》是弋舟最早的作品。在千禧年來臨之際,主人公馬領的腳意外骨折,這一年也因此被他稱作“跛足之年”。小說寫的是世紀之交普遍的浮躁心態,以及社會上光怪陸離的亂象,因而有了為時代立傳的意味,“歷史意識”由此得以不自覺地呈現。但在之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弋舟要么是直接書寫當下,要么是隨著主人公的成長歷程一路寫來。雖然他在《蝌蚪》中寫出了十里店這個地方隨著市場的開放和煤販子的到來而發生的巨變,在《戰事》中跨越了前后兩次海灣戰爭之間十幾年的歲月,卻很難讓人體會出鮮明的歷史感,似乎小說中人物對歷史的淡漠態度也影響了讀者。唯有《我主持圓通寺一個下午》是個例外,作者將故事發生的時間明確地規定在1983年,因為這一年在全國范圍內掀起了“嚴打”運動,而主人公徐未的遭遇只有在這個特殊的時代背景下才有發生的可能。但作者創作這篇小說的動機,大概只是由一首詩誘發的虛構實驗,還算不上真正具有“歷史意識”的寫作。
盡管如前文所言,弋舟習慣于將詩人、詩歌與一個早已遠去的時代聯系在一起,在《所有的故事》里還特意設置了一群大學生在畢業前夕的篝火晚會上集體背誦詩歌的情節,但就像人們已經習慣于將“八十年代”與“詩歌”之間畫上等號,這仍然只是一個泛指。直到2013年、2014年,以“劉曉東”為共同主人公營構的三個中篇小說(《等深》《而黑夜已至》《所有路的盡頭》)集中問世,弋舟的歷史意識才被驟然放大,好像黑夜中的一顆照明彈,幾乎所有人的目光都被聚焦在那個導致三篇小說主人公命運劇變的轉捩點上。一個以吶喊為己任的人,在畢業前不期而至的疾風驟雨里被推向風口浪尖,隨后被打入文史館的故紙堆里(《等深》里的周又堅);與之相反,一個與生俱來的溫和者、從小就對自己的膽小怕事而感到羞恥的“弱陽性”男人,卻因為身上根深蒂固的性格缺陷而免于卷入時代的颶風中,進而從中獲利成為“新階層”的一員,其代價則是曾經的偶像與禁忌都隨著時代的變遷而坍塌(《所有路的盡頭》里的邢志平、尹彧)。而那個用十幾年時間改造了城市面貌的人,雖然作者不曾明說他與那個時代轉捩點的關系,但他顯然就是那次轉捩的受益者,一個試圖用金錢換取心安的抑郁癥患者(《而黑夜已至》里的宋朗)。關于小說中那些時代親歷者的反省抑或“自罪”,現有的評論已經說得夠多了。既不將責任全部推脫給歷史,將自己的罪責撇清,也不諱言面對當下時的迷茫,并盡力避免時代的悲劇在下一代身上重演,而不是單純嗟嘆“我們這代人挺不容易的……”,才是“這代人”“歷史意識”的題中應有之義。在《等深》中,當“我”覺察出少年周翔準備報復褻瀆了母親的郭總的真相時,“我覺得此刻我面對著的,就是一個時代對另一個時代的虧欠。我們這一代人潰敗了,才有這個孩子懷抱短刃上路的今天”。那么,這種“時代的虧欠”究竟應該怎樣去償還?其實早在將近一百年前,魯迅在《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里就給出了答案:“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顯然,周翔式的“懷抱短刃上路”,以及徐果對心有愧疚的富翁梁山好漢“劫富濟貧”式的敲詐,盡管都顯得頗有“古風”,都能在歷史的長廊里聽到回聲,卻終究算不得“幸福的度日”,更不是“合理的做人”。也許,為了下一代,“挺不容易的”的“這一代人”需要做的還有很多。
創作于“劉曉東”系列之后的《平行》和《隨園》同樣滿溢著弋舟對歷史的審查與反思。與“劉曉東”系列不同,這兩個短篇將歷史標本的取樣點前移近二十年,時間線索則埋伏得更為隱秘。《平行》以對“‘老去’的含義及其本質性的突變”的形而上思考切入歷史與現實。老人從老同事、前妻等人那里得到了不同的回答,卻仍舊無法解釋心中的疑問;直到他完成了“飛越老人院”這一令人匪夷所思的舉動,才在無意中給出了屬于自己的答案:“老去”就是一點一點變得輕盈,變成一只候鳥與大地平行。這種對“輕盈”和“平行”的渴望,源自他力圖與大地站成一個標準的直角的一生——為此,他曾被“下放”而蒙受困厄,從此對那種粗暴殘酷、整齊劃一、四列縱隊式的集體生活方式懷上了深深的恐懼。而在《隨園》里,戈壁灘上隨處可見的累累白骨、薛子儀對尸骨主人“不過是幾十年前的男女”的確認、“他們是那個時代的文藝青年”的暗示,還有那本扔在《子不語》下的《夾邊溝記事》,無一不指向反右派斗爭中著名的“夾邊溝事件”。這些右派們身上的理想主義氣質曾經對“我”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以至于崇尚自由的“我”屢屢被學校和工作單位勸退。時隔多年后,罹患乳腺癌的“我”和曾經的流浪詩人、如今的養鴨小老板老王一起回到戈壁灘,發現當年的古代文學老師薛子儀已搖身變為地區首富,卻并未建起曾經承諾過的墓園,只是在一座極盡奢華之能事的仿古建筑“隨園”里等待死亡的降臨。小說中另一個暗藏的時間線索與“我”念念不忘的那句“執黑五目半勝”有關——1990年7月1日,錢宇平在第五屆中日圍棋擂臺賽的最后一局對決中“執黑五目半勝”日本棋手武宮正樹。聯系到“劉曉東”系列里主人公們的經歷,當年薛子儀天天打坐的舉動、麻木而垂頭喪氣的樣子、帶給旁人“像是置身在一個沒有余地的失敗當中”的感覺,以及隨后靠興辦制藥企業而成為首富的發家史,無一不與這個時間點緊緊聯系在一起。所謂的“用隨園戲仿墓園”,其實反諷了薛子儀對當初理想與信念的背叛。由是觀之,《隨園》可以被視為“劉曉東”系列的“別冊”,縈繞全篇的是一種悲涼頹敗之感,其心理抑郁和精神委頓的氛圍不亞于《而黑夜已至》。
恐懼的美學與光明的憧憬
在一篇評論中,張莉曾將弋舟小說的顯著特點概括為:“他尤其擅長提取具有精神性意義的語詞,比如羞恥、罪惡、孤獨、痛苦出現頻率極高。這些詞語有精神性色彩。”其實這樣的詞語還能列舉出很多,例如“恐懼”和“光明”。尤其是前者,相較于“羞恥”“罪惡”“孤獨”來說更具代表性。可以說,弋舟在自己的小說世界里建構起了一種“恐懼的美學”。在某些篇目里,作者直接書寫“恐懼”,以及這些“恐懼”給人心靈帶來的煎熬。例如《時代醫生》中,兩位眼科醫生被人類“心中那種與生俱來的莫須有的恐懼”所折磨,在潛意識里隨時做著逃跑的準備;《誰是拉飛馳》里,街頭少年“恐懼”的是那種似是而非的邏輯和決定自己命運的莫須有的事物,無法忍受這個世界的虛無;而在《我們的踟躕》中,在李選和曾鋮你一言我一語的分析下,人性中與生俱來的種種恐懼在強大的外部力量和世界的幽微面前逐漸現形,它所呈現的行為便是“踟躕”;在更多的篇什里,少年們因恐懼變得肥胖、骯臟、油膩而拒絕被中年人的世界招安,進而以極端的姿態與之對抗……總之,弋舟為讀者建構了一個充滿恐懼的小說世界,在他的筆下,“恐懼”已成為時代精神病癥最為顯眼的表征。
值得慶幸的是,盡管這個世界被太多的“恐懼”所充斥,但弋舟卻總是在茫茫的灰暗中留給我們一線光明的憧憬。他的筆下幾乎看不到絕望,像《天上的眼睛》那般困窘逼仄到極點,仍然會安排一家三口人的和解;《凡心已熾》里阿莫因挪用公款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即使找不到曾經的那片向日葵叢,卻還可以在路邊發現如“被無限縮小了的向日葵”的野花在這世界“動人的冷漠”里開放。而像《光明面》那樣,寫一個男人在萬念俱灰的關頭受到打工女昂揚活力的鼓舞重燃生活熱情的作品,在弋舟的作品序列里原本堪稱異數,但收入《丙申故事集》里的五個短篇,除了《隨園》的結尾略顯硬氣,其余的四篇,都不乏憂傷中的溫婉,仿佛命運之神有不忍之心。正如《出警》結尾寫道的,“人活著已經是在苦熬”,那么,就給這困頓的生活一個喘息的機會,讓這暗夜里劃過一道詩意的微光吧。

注釋
:①弋舟、李德南:《我只承認文學的一個底色,那就是它的莊嚴與矜重》,《青年文學》2015年第7期。
②魯迅:《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魯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35頁。
③張莉:《以寫作成全——讀弋舟》,《西湖》201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