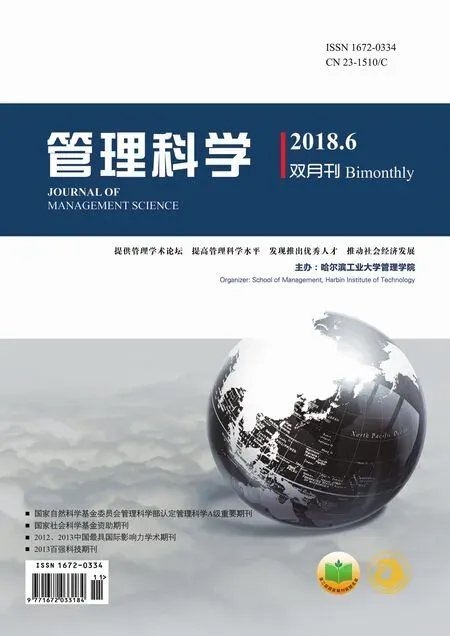離職傾向與行為表現的關系:自我效能感和主動性人格的調節作用
張凱麗,唐寧玉,尹 奎
1 華東理工大學 商學院,上海 200032 2 上海交通大學 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上海 200030 3 北京科技大學 東凌經濟管理學院,北京 100083
引言
員工離職一直是學術界和實踐界關注的重要話題[1]。已有關于離職的研究從離職傾向和離職行為兩個方面進行探究,并認為離職傾向會導致員工的實際離職行為[2-3],即員工想要離開組織的心理傾向會導致員工結束與組織關系的實際行為。雖然離職傾向與離職行為的具體表現不同,但都會帶來消極影響[4],如員工離職行為會降低組織績效[4]、造成人力資本投入的浪費[5]、增加組織內其他員工的離職行為[6],離職傾向則會導致個體增加反生產行為等[1]。有關員工離職前因的研究為管理實踐提供了眾多啟示,但離職傾向和離職行為依然普遍存在于組織中,員工離職率在近年依然居高不下[4],新員工在2011年一年的離職率高達30.600%[5],而關于新員工報道最多的便是離職[7]。
計劃行為理論下個體的內在傾向促進個體采取相應的行為[8],但是這種傾向與行為間的關系受到個體特征的影響[2,9],如個體感知到對行為的控制度影響個體是否按照內在傾向采取行動。雖然離職行為更加外顯,給組織帶來的損失具體且可衡量[10],但如果員工僅有離職傾向而沒有實際離職行為,是否會給組織帶來一定的消極影響還需進一步探究。員工績效行為包括角色內行為和角色外行為,任務績效體現了員工角色內行為,而組織公民行為和反生產行為則是員工自發的、沒有被組織正式制度界定的行為,是角色外行為,組織公民行為體現了積極的角色外行為,反生產行為體現了消極的角色外行為。本研究結合計劃行為理論,探討員工離職傾向是否對員工的績效行為產生影響,以員工的績效行為作為重要的結果變量,選擇自我效能感和主動性人格作為調節變量,構建離職傾向對員工績效行為影響的雙變量調節模型。
1相關研究評述和研究假設
1.1計劃行為理論
計劃行為理論(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TPB)是對理性行為理論(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TRA)的發展和延伸,認為個體的內在傾向作為內在動機,對于引導個體對應行為的發生有重要作用[8-9]。個體內在傾向的產生受個體對此行為的態度、個體感受到的主觀環境以及個體感知到對行為的控制度共同影響[8-9,11],個體感知到對行為的控制度同樣會作為調節因素影響個體傾向與行為的關系。當個體感知到有較高的控制度時,會按照內在傾向采取相應的行為;反之,則會削弱內在傾向與行為的關系[11-12]。計劃行為理論提出后,AJZEN[12]對計劃行為理論進行了進一步的豐富,并主要關注影響傾向與行為關系的多種邊界條件,如個體感知到行為的風險性、個體以往的行為表現、個體的個性特征(大五人格和主動性)、對自我的認知、自我監控、內外控等[13-14]。因此,雖整體而言個體的傾向會導致其相應行為的發生,但這種傾向與行為間的關系存在個體間差異,即不同的個體會因個性特征、認知水平等的不同使內在傾向與行為間的關系加強或削弱[2,8-9,12-14]。
在影響個體內在傾向與行為關系的調節變量中,個體感知到對行為的控制度發揮重要作用[12]。個體對行為的控制度體現了個體感知到的采取某種行為可能遇到的困難和阻礙,以及個體可以控制的程度。在影響個體對行為的控制度感知中,個體對自我能力的信心以及個體可以按照內在想法實施行動的特質發揮重要作用[11-12,14]。基于此,本研究選取自我效能感和主動性人格作為影響內在傾向與行為關系的調節變量。
1.2離職傾向和員工行為表現
有關離職傾向與員工行為表現關系的研究中,已有研究多關注離職傾向對員工離職行為的影響[2]。離職傾向體現了員工想要離開組織或工作崗位的心理傾向,是一種員工的意愿和想法;離職行為是員工采取的、決定離開組織的實際行為[1]。前者體現了員工的傾向性,后者則體現了實際表現,是雇傭關系的最終結束[10]。離職傾向是離職行為的開始階段,對實際離職行為有較高的解釋度[1-2],這也是對計劃行為理論[8]的具體體現,即行為傾向影響實際行為表現。
雖然離職傾向對離職行為有直接影響,但離職行為常常是員工綜合考量后做出的選擇,因此也有研究提到離職傾向到具體離職行為的關系是復雜的、受多種因素共同影響的,是利弊考量的結果[2],因此員工即使存在離職傾向,也不一定選擇離職行為。基于此,本研究選擇員工的日常工作行為作為結果變量,探究離職傾向對員工日常工作行為表現的影響。工作中員工日常行為包含多種類型,如任務績效行為、角色外行為、主動性行為、反生產行為、團隊績效行為等。本研究關注3種類型的員工行為表現,①員工任務績效行為,即與工作任務直接相關的、屬于正式績效考核的行為;②員工角色外行為,即不被組織正式的規章制度所規定的、屬于員工角色外行為;③員工反生產行為,即員工不遵守或違背組織正常規則制度或價值觀的行為。一方面,這3種行為被學者廣泛研究,也常作為員工態度和傾向等的重要結果變量;另一方面,這3種行為體現了不同的維度,如任務績效行為體現員工遵從規則下的行為,反生產行為體現員工不遵從規則下的行為,而對角色外行為的進一步研究可以充分了解員工對組織的投入。將這3種行為表現作為結果,本研究可深入了解員工離職傾向對行為表現的不同影響。
對于組織中的個體來說,努力工作常常是為了獲得組織的回報,如獲得組織支持、提高薪酬或促進職位晉升。當員工認為努力工作會獲得組織未來的回饋時,員工會有展現積極行為的動機;當員工與組織的交換關系不夠強時,這種表現積極行為的動機會降低[15-16]。具體到員工離職傾向,具有高離職傾向的員工認為自己不久將會離開組織,不會將自我的職業發展寄托于組織,因此缺少提高工作投入和工作績效的動機[17-18]。同時,基于計劃行為理論,具有離職傾向的員工可能會減少對組織有利的行為,增加對組織不利的行為。因此,員工在較高離職傾向下會降低任務績效和角色外行為,并可能增加反生產行為。綜上,離職傾向與員工的任務績效可能存在負向關系,即高離職傾向的員工會降低與工作相關的并影響組織績效的行為[19]。高離職傾向還可能與員工的角色外行為存在負向關系,本研究選擇員工角色外行為中的幫助行為[20-22]。幫助行為體現了個體在組織中提供幫助的人際互動行為[23-24],包括幫助同事完成工作任務、幫助新員工適應工作等。具有離職傾向的員工認為自己即將離開組織,對工作的投入性和參與性也會降低。此外,高離職傾向還可能與員工反生產行為正相關,因為具有離職傾向的員工可能需要花時間尋找其他工作,會在工作時間內拿出更多的時間關注求職信息、接聽求職電話等,與反生產行為中的描述具有一致性[25-26]。因此,離職傾向高的員工會降低任務績效,減少幫助行為,并增加反生產行為。
1.3自我效能感的調節作用
自我效能感體現了個體對自我能力的整體認知,是對自我能夠應對并且成功處理問題的能力認知[27]。高自我效能感的個體對自我有積極的認知,表現為對自我有較高的信心,認為自己可以成功處理困難和問題,并會主動采取行為解決困難[28]。從已有研究發現,自我效能感對個體積極行為會產生重要影響,高自我效能感的個體會更加持續的投入到工作中,對任務績效產生積極作用;自我效能感對要求主動性、具有風險性的行為也有積極作用,高自我效能感的個體更會采取創新性行為[29]。同時,自我效能感還對個體的決策行為產生積極影響,高自我效能感的個體對自我有較高的信心,并能充分掌握和利用信息,從而實現理性判斷,做出理性行為[28,30]。關于自我效能感對于行為的影響存在不同的解釋機制,GIST[28]認為自我效能感與個體的內控傾向、內在動機、自我管理、目標設定和個體期望等有正向關系,從而對個體的行為有積極的引導作用。
事實上,已有研究也發現自我效能感能夠充分解釋個體內在傾向與行為之間的權變關系,AJZEN[12]認為,自我效能感與感知到的行為控制有一定的相同點,二者都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個體感知到的對行為的控制。高自我效能感的個體有積極的自我認知和自信心,因此認為自我能夠對行為進行控制,從而按照個體內在傾向執行相應行為。有研究認為自我效能感會調節員工傾向與行為之間的關系[9-12],具體來說,高自我效能感的員工對自己能力有更高的信任,認為自己可以實現自己的目標,更會按照內在傾向采取行為[27-28]。因此,本研究認為自我效能感會強化員工離職傾向與具體工作行為表現間的關系,表現為強化離職傾向與任務績效和幫助行為的負向關系,強化離職傾向與反生產行為的正向關系。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設。
H1自我效能感強化離職傾向與任務績效的負向關系,使該負向關系在高自我效能感的員工身上表現更明顯。
H2自我效能感強化離職傾向與幫助行為的負向關系,使該負向關系在高自我效能感的員工身上表現更明顯。
H3自我效能感強化離職傾向與反生產行為的正向關系,使該正向關系在高自我效能感的員工身上表現更明顯。
1.4主動性人格的調節作用
主動性人格體現了個體希望改變外部環境的行為傾向。BATEMAN et al.[31]認為具有主動性人格的個體不會受到外部環境的約束,并會通過一系列行為改變外部環境,如尋求機會,通過持續改變外部環境實現自己的目標。主動性人格體現了個體追求某個目標的意愿和決心[32],并積極采取相應行為。PARKER et al.[33]認為主動性人格具有未來導向性,關注個體未來目標的實現。高主動性人格的個體更喜歡做出改變,改變環境,關注問題和努力解決問題,并圍繞自己的興趣點做出個人的調整;而低主動性人格的個體則不喜歡改變,消極應對問題,并希望讓事情本身發生改變而不是自己主動采取行為[32]。
當員工有離職傾向時,具有高主動性人格的員工更會進行行為的調整以實現其內在傾向。①高主動性人格的員工會采取一些能夠實現他們個人想法和目標的行為,即使這些行為與他人的意見相反,高主動性人格的員工更會將離職傾向轉化為實際行為,降低積極行為,增加消極行為。謝俊等[34]認為主動性人格會強化職場排斥與反生產行為的正向關系。②高主動性人格的員工可能會基于自己的利益和目標而積極采取行為[35]。在具有離職傾向時,高主動性人格的員工更容易認清自己的內在目標,并會按照自己這種傾向采取行為,從而會降低利組織行為,并可能提高反生產行為。CHAN[36]認為高主動性人格的個體在消極情景中可能采取一些反生產行為,以改變當前的環境或者改變當前自己的地位。③高主動性人格的員工具有較高的核心自我評價,有較高的自信心,認為自己對外部有較高的控制度,從而會按照自己的內在想法采取行為。綜上,高主動性人格的員工會更考慮自己的利益,并會積極采取措施實現自己的內在想法,且這種傾向不會因外在的阻礙而暫停[33]。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設。
H4主動性人格強化離職傾向與任務績效的負向關系,使該負向關系在高主動性人格的員工身上表現更明顯。
H5主動性人格強化離職傾向與幫助行為的負向關系,使該負向關系在高主動性人格的員工身上表現更明顯。
H6主動性人格強化離職傾向與反生產行為的正向關系,使該正向關系在高主動性人格的員工身上表現更明顯。
本研究的理論模型見圖1。

圖1理論模型Figure 1Theoretical Model
2研究方法
2.1樣本和程序
本研究樣本是一家大型外資企業,其在全國各地均有分公司。為保證研究質量,采用多時間點、多數據來源方法。研究人員首先聯系公司總部的人力資源總監,由人力資源總監通知各個分公司人力資源經理,并由分公司人力資源經理具體協助3名博士生完成數據收集。第1期調研時間為2015年12月,收集員工自我效能感、主動性人格和人口統計學數據;第2期調研時間為2016年2月,收集員工離職傾向和工作滿意度數據,以及直接上級對員工任務績效、幫助行為和反生產行為的評估。參與第1期調研的員工有923人,剔除缺失值較多和回答重復的問卷,篩選出參與第2期調研的員工,共897人。在第2期調研中,由直接上級評價員工工作表現,然后將評價結果直接交給人力資源經理。總體而言,在剔除無效和不匹配問卷后,兩次調研后得到886位員工的有效問卷和231位配對上級的有效問卷,員工問卷有效回收率為95.991%,上級平均評價人數為3.835。
由于行業限制,員工樣本中均為男性;年齡最大的為57歲,最小的為19歲,均值為28.462歲;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學歷占4.063%,高中或相當學歷占20.993%,中專、高職、技校或相當學歷占35.779%,大學專科或相當學歷占34.312%,大學本科占4.853%;工作年限最長的為14年,最短的為0.250年,平均工作年限為2.072年。
2.2變量測量
本研究中所有測量量表均為國外研究中的成熟量表,并且在中國的研究中得到大量使用,量表具有本土化的適用性。為了保證量表的準確性,根據國外量表的原始翻譯,同時結合中國發表文章的翻譯進行個別語句的修正。測量題項均采用Likert 7點評分法,1為非常不同意,7為非常同意。
(1)離職傾向。采用WAYNE et al.[37]的量表測量離職傾向,包括4個題項,具體為“我在積極的尋找另一份工作”“我很認真的在考慮離開這個組織”“我時常會想要離開這個組織”“如果我能找到一份好的工作,我就會立即離開這個組織”。在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sα值為0.942。
(2)自我效能感。采用JONES[38]的量表測量自我效能感,包括8個題項,其中一題為反向題項,考慮到反向題項常常會導致信度系數降低,本研究刪除反向題項,最終采用7個題項進行測量。具體為“我的能力可以完全勝任這份工作,工作內容在我的能力范圍內”“我在適應這份工作上不存在什么問題”“我覺得我的能力是高于工作要求的”“我具備從事這項工作的技術性知識,現在需要的是實踐經驗”“我對我的能力有信心,相信我的能力不比同事差”“我過去的經驗和成就使我相信能夠在本公司做的很好”“我能夠勝任一個比現在更具有挑戰性的工作”。在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sα值為0.873。
(3)主動性人格。采用SEIBERT et al.[39]的量表測量主動性人格,包括10個題項,具體為“我會經常留心能夠改善自己生活的新方式”“無論在哪里,我都是推動建設性發展的力量”“沒有什么能比看到自己想法變成現實更令人激動的事情”“如果我看到我不喜歡的事情,我就會改變它”“不管成功的幾率有多大,只要我相信,我就會去做”“我會堅持捍衛我的觀點,即便有人反對”“我善于識別新的機會”“我總會尋找更好的方法處理事情”“如果我堅信某個想法,任何困難都不能阻止我去實現它”“我能比別人更早的發現機會”。在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sα值為0.881。
(4)任務績效。采用EISENBERGER et al.[19]的量表測量任務績效,包括4個題項,具體為“該員工能夠充分完成布置的任務”“該員工能夠完成對他期望的工作任務要求”“該員工能夠履行其工作描述中規定的職責”“該員工能夠完成該工作正式規定的要求”。在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sα值為0.921。
(5)幫助行為。借鑒VAN DYNE et al.[22]的量表測量幫助行為,包括5個題項,具體為“該員工會幫助工作量大的員工完成工作”“該員工會幫助在工作上有問題的員工”“該員工會幫助缺席的員工”“該員工會主動為新員工提供指導”“該員工會向周圍需要幫助的員工伸出援助之手”。在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sα值為0.905。
(6)反生產行為。借鑒ROBINSON et al.[25]和YANG et al.[26]的量表測量反生產行為,包括7個題目,具體為“工作時處理私人問題”“工作中上網,瀏覽與工作無關的網頁等”“故意忽略上級的工作要求”“能夠快速工作時故意放慢工作速度”“掩蓋工作上的錯誤”“工作上不及時回復工作電話、工作郵件”“對于一些重要的工作信息不及時傳達”。在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sα值為0.915。
(7)控制變量。由于年齡和工作年限等人口統計學變量會影響員工的工作態度和行為,因此控制員工的年齡、教育水平和工作年限。由于該企業一線員工均為男性,沒有將性別作為控制變量進行分析。年齡為員工的實際年齡,教育水平分為初中及以下學歷等5個等級,工作年限為員工的實際工作年限。同時,考慮到員工的工作滿意度會影響員工的離職傾向和工作表現[1],本研究對員工的工作滿意度也進行控制。工作滿意度的量表來自HACKMAN et al.[40]的研究,包括3個題項,具體為“總體而言,我對自己的工作感到滿意”“我大體滿意從這個工作中得到的成就感”“我大體滿意在這個崗位從事的工作內容”。在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sα值為0.895。
2.3數據分析方法
由于研究中個體績效行為由上級進行評價,一個領導常常需要對3名~5名員工進行評價,員工嵌套于上級之中。由于不同上級存在不同的評分傾向,上級本身會影響對下屬的績效評價。因此,為了避免上級因素的作用,本研究采用三明治分析方法[41]進行假設驗證,該方法的優點在于能夠控制同一上級評價所導致的評價效應偏差。在具體分析中,在模型的第2層加入隨機效應,以控制上級評價多人帶來的嵌套問題。
3數據分析和結果
3.1信效度分析
本研究針對所有變量進行驗證性因子分析,以檢驗變量之間的區分效度,基準模型為7因子模型。通過分析,7因子模型的擬合指數為χ2=2 180.880,df=719,RMSEA=0.048,CFI=0.924,TLI=0.928。同時,由于個體的自我效能感和主動性人格在同一階段獲得,本研究還進行了6因子模型驗證,結果表明,6因子的擬合指數為χ2=3 246.573,df=725,RMSEA=0.063,CFI=0.886,TLI=0.877,顯著差于7因子模型,Δχ2=1 065.693,Δdf=6。由于上級評價員工的3種績效行為,進一步進行5因子模型的驗證,將上級評價員工的任務績效、幫助行為、反生產行為進行合并,結果表明5因子模型擬合指數為χ2=4 886.832,df=730,RMSEA=0.080,CFI=0.811,TLI=0.798,顯著差于7因子模型,Δχ2=2 705.952,Δdf=11。因此,說明本研究中7因子模型具有良好的擬合效果。涉及變量的題項因子載荷在0.552~0.949之間,大于0.500的要求;組合信度系數均高于0.900,大于0.700的要求;平均方差抽取量均大于0.600,大于0.500的要求[42]。此外,調研采用多時間點、多數據來源的方式,員工自我效能感和主動性人格數據在第1階段調研時收集,員工離職傾向和工作滿意度數據在第2階段調研時收集,員工的績效評價由領導在第2階段進行評價。因此,通過此方法有效的避免了同源方差問題。
3.2描述統計分析
采用Spss 21.0對數據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變量的均值、標準差和變量間相關系數見表1。由表1可知,離職傾向與任務績效在0.010水平上顯著負相關,相關系數為-0.100;離職傾向與幫助行為在0.050水平上顯著負相關,相關系數為-0.074;離職傾向與反生產行為在0.010水平上顯著正相關,相關系數為0.188。上述結果為假設檢驗提供了初步支持。
3.3假設檢驗
在離職傾向對員工行為的直接效應檢驗中,為避免上級個人因素的影響,本研究借鑒LIU et al.[41]的分析方法,采用三明治分析,在第2層控制上級評價的嵌套問題,檢驗結果見表2。模型1、模型4和模型7分別檢驗人口統計學變量和工作滿意度對任務績效、幫助行為和反生產行為的影響,結果表明,工作滿意度與任務績效在0.010水平上顯著正相關,β任務績效=0.145;工作滿意度與幫助行為在0.010水平上顯著正相關,β幫助行為=0.104。模型2、模型5和模型8檢驗引入控制變量、自變量和調節變量的主效應,模型3、模型6和模型9給出引入調節效應后的作用值。從R2變化上可知,模型存在調節效應,模型3的ΔR2=0.007,在0.050水平上顯著;模型6的ΔR2=0.008,在0.050水平上顯著;模型9的ΔR2=0.012,在0.010水平上顯著。由模型3可知,自我效能感不存在對離職傾向與任務績效關系的調節作用,β=-0.016, n.s.;由模型6可知,自我效能感不存在對離職傾向與幫助行為關系的調節作用,β=-0.022,n.s.。H1和H2沒有得到驗證。由模型9可知,自我效能感正向調節離職傾向與反生產行為的關系,β=0.084,在0.100水平上顯著。本研究中同時使用兩種人格特質作為調節變量,因此此處放寬了顯著性水平[41]。H3得到驗證。

表1均值、標準差和相關系數Table 1Means, Standard Deviations an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注:**為在0.010水平(雙尾)上顯著相關,*為在0.050水平(雙尾)上顯著相關,樣本數為886,下同。

表2假設檢驗結果匯總(三明治分析方法)Table 2Results for the Hypothesized Test(Sandwiches Estimator)
注:表中數據為標準化系數值,?為在0.100水平(雙尾)上顯著相關。
同理,由模型3可知,主動性人格負向調節離職傾向與任務績效的關系,β=-0.076,在0.100水平上顯著;由模型6可知,主動性人格負向調節離職傾向與幫助行為的關系,β=-0.078,在0.100水平上顯著。H4和H5得到驗證。由模型9可知,主動性人格正向調節離職傾向與反生產行為的關系,β=0.143,在0.010水平上顯著,H6得到驗證。
為了更好地理解自我效能感和主動性人格的調節作用,本研究進行簡單斜率檢測,并繪制調節效應圖[43]。圖2給出自我效能感對離職傾向與反生產行為關系的調節作用,與低自我效能感(-sd)的員工相比,高自我效能感(+sd)的員工在具有離職傾向時,其反生產行為提高得更快。高自我效能感B=0.149,在0.001水平上顯著;低自我效能感B=0.055, n.s.。表明高自我效能感的員工在較高離職傾向時,更會提高其反生產行為。圖3給出主動性人格對離職傾向與任務績效關系的調節作用,與低主動性人格(-sd)相比,高主動性人格(+sd)的員工在具有離職傾向時,其任務績效降低得更快。高主動性人格B=-0.061,在0.050水平上顯著;低主動性人格B=0.012, n.s.。表明高主動性人格的員工在較高離職傾向時,更會降低其任務績效。圖4給出主動性人格對于離職傾向與幫助行為關系的調節作用,與低主動性人格相比,高主動性人格的員工在具有離職傾向時,其幫助行為降低得更快。高主動性人格B=-0.063,在0.050水平上顯著;低主動性人格B=0.017, n.s.。表明高主動性人格的員工在高離職傾向時,更會降低其幫助行為。圖5給出主動性人格對離職傾向與反生產行為關系的調節作用,與低主動性人格相比,高主動性人格的員工在具有離職傾向時,其反生產行為提高得更快。高主動性人格B=0.183,在0.001水平上顯著;低主動性人格B= 0.022, n.s.。表明高主動性人格的員工在較高離職傾向時,更會提高其反生產行為。

圖2自我效能感對離職傾向與反生產行為關系的調節作用Figure 2Moderating Effect of Self-efficacy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urnoverIntention and Counterproductive Behavior

圖4主動性人格對離職傾向與幫助行為關系的調節作用Figure 4Moderating Effect of ProactivePersonalit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Turnover Intention and Helping Behavior

圖3主動性人格對離職傾向與任務績效關系的調節作用Figure 3Moderating Effect of Proactive Personalit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Turnover Intention and Task Performance

圖5主動性人格對離職傾向與反生產行為關系的調節作用Figure 5Moderating Effect of ProactivePersonalit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Turnover Intention and Counterproductive Behavior
4結論
4.1研究結果
本研究基于計劃行為理論,采用來自一家大型外資企業在全國范圍的員工與直接上級配對數據,構建員工離職傾向與其績效行為關系的理論模型,考察員工自我效能感和主動性人格在上述關系中的調節作用,采用886名員工與231名配對直接上級的數據進行分析。研究結果表明,員工離職傾向產生消極后果,并且這種消極作用會在高自我效能感或高主動性人格的員工上表現得更加明顯。首先,自我效能感加強員工離職傾向與反生產行為之間的正向關系。高自我效能感的員工更會按照自己的意愿采取相應的行為,在有離職傾向時提高反生產行為。高自我效能感的員工更會采取反生產行為,說明其對自我的過度關注可能會產生負面作用[30]。其次,主動性人格加強員工離職傾向與員工任務績效、幫助行為的消極關系;同時,主動性人格還加強員工離職傾向對反生產行為的正向影響。因此說明主動性人格的“陰暗面”,即高主動性人格的員工更多關注自我的需求和目標,也因此會按照自己的意愿采取相應的行為[43]。這一研究結果為進一步探究自我效能感和主動性人格的負面作用提供啟示。
本研究雖然沒有發現自我效能感對離職傾向與任務績效、幫助行為關系的調節作用,但是其交互項的作用方向與主動性人格的調節作用方向一致,因此依然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自我效能感可能存在與主動性人格一致的“陰暗面”。同時,相對于自我效能感,主動性人格的調節作用更強,也體現了主動性人格作為一種相對穩定的人格特質,比作為亞特質變量的自我效能感更具穩定性[27-28]。
4.2管理啟示
本研究的相關結論可以為企業管理實踐提供一些有意義的啟示和參考。
(1)管理者可以通過對員工工作行為的表現推測員工的離職傾向。本研究發現不僅員工的實際離職行為給組織帶來負面影響,員工的離職傾向也對員工的績效表現產生消極影響,即具有離職傾向的員工會降低任務績效、組織公民行為,并提高反生產行為。雖然多數組織在關注如何降低員工的離職傾向,但員工的離職傾向并不均是由組織引起,員工因素和員工家庭因素等都會成為前因[2],因此即便優秀的組織依然會存在員工離職傾向。而在產生離職傾向時,多數員工選擇掩蓋,而不會與上級溝通,這也進一步造成了組織不能及時應對員工離職。當員工表現出較高的短期行為導向時,上級可以通過觀察員工的行為表現推斷員工內在動機,并積極采取相應措施。組織也可以鼓勵內部坦誠、公開的交流,以更好地掌握員工工作動態,了解其內在動機和傾向,及時預防有離職傾向的員工降低工作投入。
(2)主動性人格和自我效能感的“陰暗面”需要引起管理者的關注。高主動性人格或高自我效能感并不能一刀切地認為是積極的,高主動性人格或高自我效能感的員工同樣可能存在消極行為,本研究發現兩者均會帶來更多反生產行為。當具有高主動性人格或高自我效能感的員工對組織產生不滿時,這種不滿可能更會導致負面行為。面對具有高主動性人格或高自我效能感的員工,組織需要采取適當的措施支持他們,防止其從反面極端上影響組織績效。
4.3研究局限和未來研究方向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①本研究沒有探究員工離職傾向產生的不同動機對其內在傾向和行為的影響。導致員工產生離職傾向存在不同原因,或是家庭因素,或是工作不滿意因素,或是個體求學等方面因素[1]。在不同的原因下,員工離職傾向與工作行為的關系可能存在差異。因此,未來需要結合員工離職傾向產生的不同原因探究離職傾向與行為表現的關系。②本研究結合計劃行為理論,探討不同的員工個人因素對于員工傾向與行為關系的影響,但研究中僅關注了員工的自我效能感和主動性人格,其他的個體因素(如自我監控、內外控等因素[2])、組織情景(如組織監控)和宏觀情景因素(如找工作的難易程度)等可能也會影響內在傾向與行為的關系。③雖然本研究采用了多時間點、多數據來源的方式收集數據,但是依然不能推斷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即不能說明是任務績效或幫助行為低導致員工產生離職傾向,還是員工離職傾向導致任務績效或幫助行為的降低。未來可以通過長時期追蹤進行探究,控制前1期影響因素來推斷后續的結果。
本研究關注具有離職傾向、高自我效能感或高主動性人格的員工可能更會降低任務績效、幫助行為,并會提高反生產行為。未來研究可以進一步探究員工具有離職傾向、但是同樣具有較高的個人責任心時,可能會降低離職傾向的負面作用。此外,組織因素中的領導也會對員工行為產生重要影響。當領導采取辱虐型領導[44]方式時,員工可能有較高的離職傾向,但是基于領導壓力,員工可能依然會表現出較高的績效行為。
已有研究已經關注到員工主動性人格和自我效能感的消極作用[45],但有關的研究還相對較少。本研究也是對主動性人格和自我效能感“陰暗面”的一種探索和豐富,雖然高主動性人格和高自我效能感的員工也可能會發現組織中的不良現象,并通過積極的改變提升組織績效[43],但是當員工認為的這種負面現象是影響自己的發展和自我利益時,其可能更會采取破壞組織的行為。未來還值得進一步探究員工自我效能感和主動性人格對于組織中員工破壞型行為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