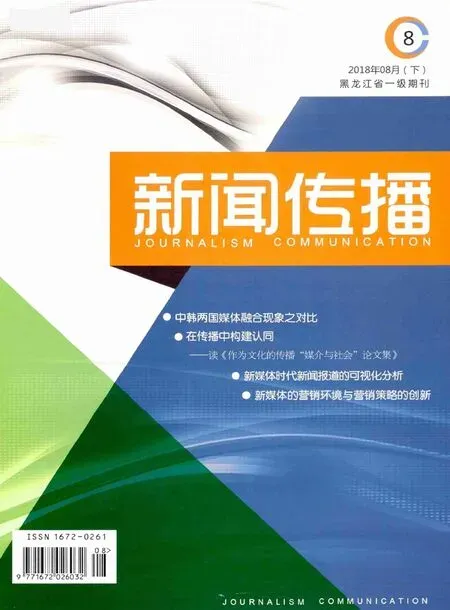新媒體場域下的名譽侵權糾紛
(復旦大學 上海 200438)
一、名譽侵權概述
(一)名譽權的界定
《牛津法律大辭典》對名譽的概念定義為:名譽是對于人的道德品質、能力和其他品質(名聲榮譽、信譽或身份)的一般評價。《布萊克法律辭典》則定義為:名譽是關于一個人特性或者其他品質的共同的或一般的評價。通過以上定義可以看出,名譽的核心意涵在于社會公眾通過主體的行為而對其品質所做出的客觀評價,是主體在社會生活中不斷累積的正向的公眾評價的總稱。可以說名譽是他人賦予主體的重要識別標簽,表征著社會公眾對于主體品格、技能等等重要素質的客觀評價,是主體參與社會互動關系的重要信用標志。
名譽權,就是主體對于名譽所享有的民事權利,即“公民和法人對于自己的觀點、行為、工作表現所形成的有關其素質、才干、品德的社會評價等方面享有的不可侵犯的權利”。[1]學界一般的觀點認為,名譽權具有法定性、專屬性和非財產性。所謂法定性是指,名譽權基于法律的規定而受到保護;所謂專屬性是指,名譽權只能由特定的公民或法人主體享有,是其人格權利與人格尊嚴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得轉讓或繼承;所謂非財產性是指,名譽權不具有財產性的內容,而僅僅是一種社會評價,名譽權遭遇侵害時,首要的救濟方式是恢復名譽并救濟精神損害賠償而非財產性的損害賠償,當然對于法人名譽權的侵害來說,其首先是一種財產性利益的損害。
(二)名譽權的民事法律保護
在民事司法上,我國主要通過侵權責任的追究來保護名譽權。名譽侵權責任的一般構成要件是:1.有侵害他人名譽權的不法行為,主要有侮辱和誹謗兩種行為,所謂侮辱是采取暴力或其他方式使得受害人的人格尊嚴與名譽受到傷害,所謂誹謗是指不法發表或者傳播損害特定主體名譽與社會評價的虛假事實;2.產生了損害后果,即受害人的名譽權受到了現實的損害,主要包括受害人名譽的不當貶損和社會評價的降低、受害人因名譽受損而遭受的精神損害和附帶的財產損失;3.侵權行為與損害后果之間具有因果關系,即受害人名譽的貶損、社會評價的降低是由侵害行為所造成;4.侵權行為人主觀具有過錯,即侵權行為人因為故意或者過失而實施了貶損受害人名譽的行為。
二、新媒體場域下名譽侵權糾紛的主要難題
由于名譽指向的是一種客觀的社會公眾的評價,損害名譽權的行為通常只有通過公開的方式、能夠為社會公眾所普遍知悉的方式才能夠實施,所以“在英美侵權行為法中,公開對于侵害名譽權行為構成是十分重要的要素”[2]。在當代社會,任何信息或言論的公開與傳播都不能不借助新聞媒體這一重要手段與媒介,因此名譽侵權糾紛往往與新聞媒體具有緊密的關聯性。而在互聯網時代,微博、微信、博客、BBS論壇等等新媒體已經滲透到人們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成為人們獲取新聞與信息的重要乃至首要途徑,其自然也成為名譽侵權糾紛的多發場域。
新媒體場域下,信息傳播不再由少數媒體精英審查與控制,新媒體的諸種信息傳播工具是無門檻或低門檻的,任何普通人都可以借之成為信息的發布與傳播者,主體極度開放與多元化。不僅如此,由于新媒體的及時交互性,任何人都可以隨時參與信息傳播之過程,不僅被動地接受信息,而且可以主動地參與信息的進一步形塑與傳播。
由于新媒體的此種特點,就使得名譽侵權糾紛因為新媒體的運用而發生時,其司法審理面臨著某些與傳統名譽侵權糾紛不同的問題需要解決。
(一)受害者的言辭辯論與侵害行為的認定
在傳統媒體下,信息的傳播是單向的,只要侵害行為實施,則作為被動的信息接受者之一的受害者的名譽必然受到損害,因此侵害行為要件是否成立僅僅取決于侵害者的行為方式。但是新媒體具有主體多元化與交互化的特點,受害人在侵害者發布相關貶損其名譽的信息后,往往能夠在同一新媒體場域下對侵害者的行為進行言辭的辯論與抗爭。如果此種言辭辯論和反擊足夠有效,則意味著特定行為雖然具有侵害行為之外觀,卻在客觀上無法實際引起侵害后果,從而侵害行為不能成立。日本法院就曾經在一起新媒體名譽侵權案件中判定,“原告對不適當的網絡言論進行過辯論,所以法院認定侵犯名譽、侮辱名譽的違法行為不成立”[3]。換言之,新媒體場域賦予了侵害人新的抗辯可能。
(二)責任主體認定
在名譽侵權糾紛中,侵害行為的實施往往需要借助一定的傳播媒介。在針對電視、報紙等傳統媒體的名譽侵權責任的認定中,由于編輯在內容撰寫與發布上具有決定性的審查與控制權力,因此十分重視所謂的“編輯責任”或者說新聞單位的責任,新聞作者與新聞的發布單位往往都被認為是侵權責任主體。
但當具體侵害人借助新媒體來實施侵害行為時,責任主體的認定上卻無法沿用針對傳統媒體的立法模式。首先,由于網絡信息總量的急劇膨脹,依靠網絡服務提供商對信息進行猶如傳統媒體之編輯一般的審查與控制是不可能做到的。而新媒體信息創作與發布者的匿名性更增加了審查與控制的難度。
其次,新媒體信息的復制和傳播成本極低,信息一旦發布,很容易迅速蔓延,脫離原始發表者與初始網絡服務提供商的控制范圍,而侵權損害的造成往往是后續的蔓延傳播過程中造成的。若僅對信息初始發布的網絡服務提供商課以責任則可能有失公平,而若將所有涉及信息傳播的網絡服務提供商都課以責任,則明顯范圍過大,無法實際做到。
最后,如果對網絡服務提供商課以較為嚴格的責任,既然其無力實質審查信息之內容,則意味著一旦受害人以相關信息侵害個人名譽為由要求刪除,網絡服務提供商為了避免承擔責任必然積極予以響應,而這有可能對言論自由過分的限制。
(三)責任承擔方式
侵權責任制度以填補損害、恢復原狀為原則,因此在名譽侵權糾紛中,恢復名譽、消除影響是最基本的責任承擔方式。在傳統的司法實踐中,恢復名譽、消除影響通常由法院根據侵害行為所傳播和影響的范圍,要求侵害人在具備相應影響力的新聞報刊上刊登聲明等方式來承擔責任。
此種責任承擔方式在新媒體場域下同樣遭遇困難。
首先,如果仍沿用傳統的責任承擔方式,即在特定報刊上刊登聲明,則由于名譽損害發生于新媒體場域之中,受眾的廣度與受眾的類型皆不相同,難以充分地恢復受害者名譽、消除不良影響。
其次,即使在新媒體上刊登聲明,就填補損害來說也往往是不足的。新媒體場域下,許多損害名譽之信息是侵害人通過其自媒體所發布,按照侵害行為與道歉聲明之影響范圍相等之基本理論,則應當由侵害者在其發布不實信息的自媒體上刊登聲明。比如在我國臺灣地區,法院在審理名譽權糾紛時,就經常判令侵害人在其發布不實信息的個人自媒體上刊登道歉聲明,“在不知不覺中,‘登報道歉’這事已然逐漸絕跡”[4]。但是自媒體的信息傳播受眾往往是侵害人的崇拜者或者其意見的追隨者,此種聲明的刊登往往不僅不能消除影響,反而可能意味著侵害人在其特定追隨者面前再次羞辱受害人。
不僅如此,新媒體場域下,侵害人初始發布信息之媒介對于侵害結果之形成未必具有決定性的影響,信息的迅速復制與快速傳播使得信息迅速地傳遞到網絡世界的各個角落,從而使得不實信息既在物理上不能被徹底消除,其造成的不良影響也往往不能實質性地通過后續民事責任的承擔而充分消除。
三、新媒體場域下名譽權保護的完善
通過前述可以知道,,通過追究民事侵權責任來救濟新媒體場域下的名譽侵權損害,往往面臨著責任認定上的困難以及救濟手段上的不足。一旦損害造成,很可能無法通過民事訴訟的方式充分填補損害。因此,對于新媒體場域下的名譽權保護來說,事先的防免要優越于事后的救濟。
(一)網絡犯罪立法
相較于民事責任追究,刑法上之侮辱、誹謗罪對侵害名譽者的刑事責任的追究更具威懾力,也是名譽權保護中不可或缺的一環。不僅如此,在新媒體語境下,侮辱與誹謗等語言暴力借助互聯網特有的極端化、匿名化特點,往往對受害人造成極其嚴重的后果,追究刑事責任乃是行責相當的基本要求。當前,“我國對于網絡犯罪設定的罪名過少、保護范圍過窄”[5],只有針對新媒體特點更加細化我國現有的侮辱、誹謗罪,才能對名譽權保護提供足夠的制度手段。
(二)行政監管
行政機關的權力具有主動性,相較于被動性的、提供事后救濟的司法權來說,更有利于名譽權的保護。由公安機關計算機及公共信系網絡管理監察部門——“網絡警察”——為主體的互聯網監督系統能夠通過自我審查或者社會公眾的舉報而及時切斷侵害名譽權信息之傳播。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言論自由與名譽權保護之間的利益平衡,行政監管應當盡可能做到事后的理由闡明與信息披露,以提供社會公眾對行政監管行為的必要知悉與監督。
(三)行業自律
以互聯網為載體的新媒體素來有自治之傳統,此種自治本身也是新媒體信息膨脹之下的必然路徑,由于新媒體的多元化,若干政府機關的能力是相當有限的,只有充分發揮各新媒體行業與市場主體自身的積極性,才有可能對海量的互聯網信息進行必要的監督與控制。因此政府機關在加強監管的同時,要積極鼓勵各種新媒體公司探索有效的行業自律手段。政府有權機關的公權力行為應當補充性地發動,而主要依靠各新媒體公司的自律手段來防止侵害名譽權之信息的散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