瑩瑩一點真
米麗宏
人,總是活在社會角色里。在角色里待久了,本來的那個我,往往被忘記了。來處啊,初心啊,原色啊……社會文化的外力,琢磨它,漿染它,就有了一層外衣、一種圓滑。靜下來的時候,我們簡直不認識它了。
當鮮嫩、清新的“真我”閃現而出,真如明珠一般瑩潤可喜;其實大方之家,活得都很自我,很真實。
在我們的印象里,魯迅峻刻、犀利,不妥協、不饒恕,兇巴巴的、一臉愁苦。但,不是這樣的。曾受魯迅啟蒙和幫助的作家唐弢說:魯迅來他家,興致好時,一進門就輕快地在地板上打旋子,一路轉到桌子前,一屁股坐在桌面上,手里拿支煙,嬉笑言談。
這個輕盈自喜的魯迅,真好玩兒,跟激憤、犀利的憤青完全不是一個路子。這真的沒什么好奇怪的。哪個男人心里,沒住著一個小孩?那小孩現身,我們就瞧見了一個人人格的立體和張力。
當代評彈藝術家楊振雄,被評彈界尊稱為楊老爺。為琢磨《長生殿》的劇本,他月余不與人語,完全沉浸在戲里。對藝術的投入度,沒人能比。有一年,他在京城參加文化藝術界匯演,藝驚四座,惹得滿場掌聲雷動。楊振雄回到旅舍房內,還興奮得四方團團踱步,捧著臉,連呼:“開心煞了,開心煞了!”走過門口的年輕后生目睹此景,驚得目瞪口呆。然而老夫子招手叫他進去,道:“開心煞了,來來來,我翻個筋斗給儂看。”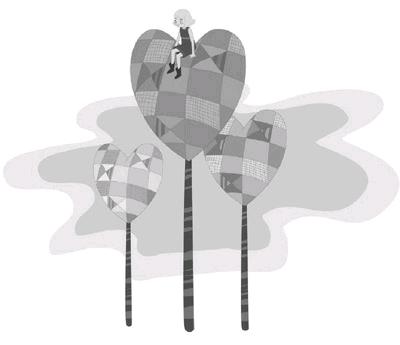
興奮得想翻筋斗,真是率真如小兒。那點真,對藝術家來說,是一種福祉。楊振雄此番,遇知己,趁心愿,靈魂飄舉,那種自得自喜,真算得人生勝境。
早晨行走于超市外頭時,守時的伙計比慵懶的老板早到,臉上顯出比老板更多的一點優越感,那是一種真,生活雖沉重,但靈魂可以輕如云。
“落花深一尺,不用帶蒲團”,古拙率真天然無飾的“禪家本色”,是一種真。一切順其自然,在自然中求頓悟。心中有佛,落花之上便可參禪,何需形式上的東西。蘇曼的癡僧性情,用“真純”二字來形容,再適合不過。
真,也不排除物質要求。畫壇鬼才黃永玉在湖南鳳凰家里的中堂左壁掛了一則啟事:“一、熱烈歡迎各界老少男女光臨舍下訂購字畫,保證舍下老小態度和藹可親,服務周到,庭院陽光充足,空氣新鮮,花木扶疏、環境幽雅,最宜洽談。二、價格合理,老少、城鄉、首長百姓、洋人土人……不欺。無論題材、尺寸、大小均能滿足供應,務必令諸君子開心而來,乘興而返。三、畫、書法一律以現金交易為準,嚴禁攀親套交情陋習,更拒禮品、食物、旅行紀念品作交換。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老夫的眼睛雖有輕微‘老花,但仍然還是雪亮的,鈔票面前,人人平等,不可亂了章法規矩。四、當場按件論價,鐵價不二,一言既出,駟馬難追。糾纏講價,即時照原價加一倍;再講價者放惡狗咬之;惡臉惡言相向,驅逐出院!六、所得款項作修繕鳳凰縣內風景名勝、亭閣樓臺之用,由侄兒黃毅全料理。”
自己的藝術作品,經營起來,有原則,不讓利,不讓步,鐵面無私,但另一方面,他的收入都用于了家鄉公益。這種明朗,折射出的是一個人靈魂的透明和天真。
瑩瑩一點真我,由天而來,隨時生成。遵從真理,也尊重了自己的內心。end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