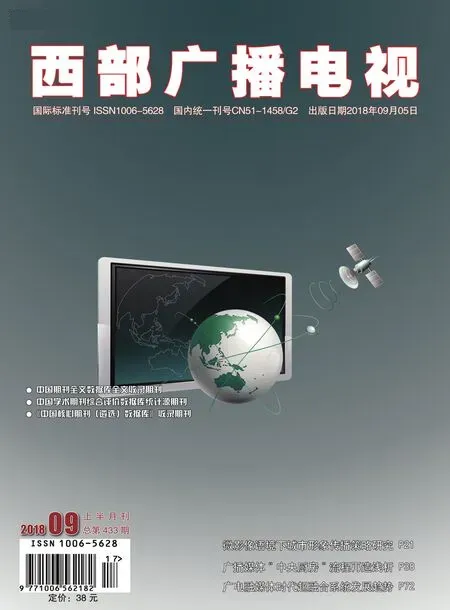精深的思想 精美的藝術(shù)
——電視劇《白鹿原》創(chuàng)作特色解析
李婷婷 藺 飛
(作者單位:1.成都市廣播電視臺(tái);2.自貢市廣播電視臺(tái))
從辛亥革命到1948年這個(gè)特定歷史時(shí)期的中國(guó)社會(huì)文化和人性善惡的深刻反思通過(guò)電視劇《白鹿原》得以形象展示。該劇由獲得中國(guó)長(zhǎng)篇小說(shuō)最高榮譽(yù)——茅盾文學(xué)獎(jiǎng)的著名長(zhǎng)篇小說(shuō)《白鹿原》改編而成,在忠實(shí)于原著前提下將原著精神價(jià)值和電視劇創(chuàng)作特殊規(guī)律有機(jī)結(jié)合,用唯物史觀和當(dāng)代思維統(tǒng)攝全劇,通過(guò)審美化的影視藝術(shù)手段,將近半個(gè)世紀(jì)的中國(guó)社會(huì)生活的巨大變遷濃縮到陜西白鹿原上的白、鹿兩個(gè)家族三代人之間的命運(yùn)、生活道路選擇和人性沉浮當(dāng)中,以豐富的文化含量和開(kāi)闊的審美容量展現(xiàn)了當(dāng)時(shí)整個(gè)中國(guó)社會(huì)、政治、經(jīng)濟(jì)、文化和精神等一系列的沖突和斷裂,把文學(xué)原著中蘊(yùn)含的深刻思想內(nèi)涵和情感內(nèi)涵展現(xiàn)得淋漓盡致。
1 歷史人文思想的精神薈萃
小說(shuō)《白鹿原》用八九十年代傳統(tǒng)文化中的憂患意識(shí)反觀傳統(tǒng)文化,從較為客觀的文化視角抒寫了一段特定歷史時(shí)期中國(guó)農(nóng)民的文化思想歷程,達(dá)到了藝術(shù)性與歷史性的統(tǒng)一,其對(duì)傳統(tǒng)文化中的優(yōu)劣、善惡、正邪所進(jìn)行的現(xiàn)實(shí)主義批判也達(dá)到了文學(xué)性與思想性的相當(dāng)高度,生動(dòng)演繹了中華文化的現(xiàn)代意義。
1.1 影像時(shí)代的歷史觀照
電視劇《白鹿原》之所以被譽(yù)為“現(xiàn)象級(jí)的史詩(shī)大劇”,在于其將近半個(gè)世紀(jì)的時(shí)間跨度中不同生存地位的人物、不同的人生態(tài)度、不同的生存選擇交織在一起,通過(guò)激烈的矛盾沖突向觀眾展示了一幅中國(guó)農(nóng)民斑斕多彩的歷史畫(huà)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