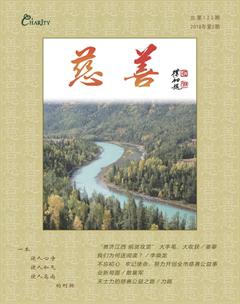彩云香
劉巨真
一朵祥云在藍天上飛,我卻聞到了它的香氣。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有好多天,尤其是春風化雨之后,我常常走出戶外,站在瓷磚砌成的平臺上,看云舒云卷,吟古人之詩:“可憐光彩一片玉,萬里晴空何處來”。這是誰的詩,記不得了,但那個叫云香的人,卻在眼前一天比一天地清晰起來。
她屬大龍,年長我一歲,細高個,圓臉盤,高鼻梁,大耳垂,一雙杏核眼,左眉梢還有一個旋兒,兩片小嘴唇嘟嚕著,似嗔似笑似撒嬌。她是我高中的同班同學。那時候,我所在的普蘭店還沒有高中,只好橫穿九十里,到遼東半島的東海岸的一個叫皮口的小鎮就讀。而她的家就在皮口鎮上。她是走讀生,我是住宿生。時值“大躍進”年代,學校勞動特別多,脫坯、深翻地、大秋收、小秋收,莊稼地里的活兒,幾乎都有學生的身影。那年海潮沖毀了鹽壩,我們又去修鹽灘和鹽壩。俗話說農村的活有“三大累”:砍莊稼、抹墻、脫坯。我們嫩稚的肩膀所承受的又何止這些?我這個住宿生,單靠那點學生的糧食定量就有些不夠吃。我是個大飯量,每次吃完飯,肚子里總是空落落的。有一次,云香背著同學給我飯票,還沒等我緩過神來,塞到我的兜里就跑了。由此,我知道她對我的好。
投我以木瓜,我呢,當然要報之以瓊琚了。我一無所有,沒有什么給她,有的只是力氣,幫她干點雜活。再就是每當想家的時候,寂寞的時候,找她說說話,排解我心中的郁悶。這樣一來二往,我們的關系密切起來了。那時沒有“早戀”這個詞,但在我的心中,確實有一日不見如隔三秋的感覺。其實,我對她早就有好感。不僅因為她長得好看,有一種“清水出芙蓉”的純真的天性,而且人品好,學習好,不是那種冷美人。她還愛好文學,寫得一手好字,這更讓我欽佩和傾慕。每次我們單獨在一起的時候,我都喊她云香姐。那時,在縣醫院工作的有我的一個姑表姐叫玉香,鄰居的一個比我大的女孩叫金香,班里又有一個像姐姐一樣的同學叫云香,而且都姓張。我一下子有了三個“香”姐姐,生活也變得香了。但比較起來,我還是覺得云香姐親近。
可是好景不長。第二學期開學不久,她找到我,對我說:“我要轉學到內蒙古了,我的大哥在那里,跟父母一塊去。”我心里一震,半天說不出話來,少頃,才試探著問:“能不去嗎?”她似乎有許多難言之隱,最后還是很堅決地說:“我家除了三個哥哥,就我一個閨女,怎么能不去呢?”她看我眼淚汪汪的,比真姐姐還親切地安慰我說:“你不要想那么多,我不會丟下你不管的。”俺遼南農村,這個“管”不是管制,而是愛護和牽掛。我心里明白。
第二天,云香就不再上課,回家辦理手續去了。這期間,我每天晚上都把當天的聽課筆記和作業答案重抄一份留下來,在她啟程之前送給她。那是一個星期六的下午,我到了她的家里,見過她的母親,說了一會兒話,天色已暗了下來。伯母拉著我的手,執意留我吃晚飯,我很為難,推辭了半天,老人家才松開手。這時,云香又亮出一條好長好長的白圍巾,對我說:“帶上這個吧!從今以后,咱倆天各一方,你圍上這條圍巾,就能想起我。”接著又告訴我,她的名字已改,叫云翔,不叫云香了。為什么呢?她沒有說,但我猜測其中的緣由,大約是為了紀念我們的離別。云彩要飛走了,不就是翔嗎?
云已翔。空落落的我,常常在手心上寫著她的名字:云香和云翔。對比起來,還是云香寫得多,云翔寫得少。我是多么不愿意她走啊!同學們發現我悶悶不樂,不時地向我發問。我憋不住心里的郁悶,終于道出了白圍巾的由來。同學們聽了,有的奚落我,有的開導我。
“你真是塊榆木疙瘩!”
“大張最喜歡你,誰不知道啊!”
“你倆挺般配的,珍惜吧!”
俗話說,旁觀者清,當局者迷。我體會到了。同學們的點撥,讓我茅塞頓開,心情一下子好起來,想到她太多太多的好,心里美滋滋的。我知道自己該怎么做了。
正在這時,我突然得了一種病,整天腰疼,坐臥不寧,到大連、沈陽都不能確診,后來到了長春,說是腰椎骨結核,無奈之下只好休學了。休學回到家里,一邊用藥,一邊臥床療養,效果甚微。我不知道這種情況什么時候是盡頭。回想到大哥為買雷米封和注射用的進口鏈霉素,花掉了他全部軍轉費,心里更不是滋味。我唯一的希望是給云香(云翔)寫信,盼著她的回音,盼著她的安慰。可拿起筆,又放下了;剛開了個頭,又停下了;寫好了一封,又撕掉了。我跟她說什么呢?我不愿意讓她知道一個她喜歡的活蹦亂跳的人,如今整天地躺在床上。我不愿意讓一個好姑娘嫁給靠背腰支架才能走路的人。索性就不寫,用沉默掩藏我痛苦的心靈。
然而痛苦并不代表頹廢,它還可以產生動力。我喜歡文學,就躺在床上看小說、散文和詩歌。我喜歡音樂,仰在床上吹簫,吹笛子,還報考了青島音樂學院函授班,學習作曲。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會躺在床上度過青春的年華;我不相信,我不相信病魔會永遠賴著不走。華羅庚患了可怕的傷寒,臥床兩年,依然寫出讓清華大學熊慶來教授驚異的數學論文,我為什么不能呢?也許這是異想天開,但正是這異想天開給了我異乎尋常的力量。我除了按時吃藥、注射,每天都像小孩學步似的下床試著走。我要盡快地恢復健壯的軀體,為自己,為云翔(云香)。
兩年過去了。我的病情有了好轉。這時普蘭店的縣二中已增設了高中,我復學就不必再回原校,因此就到二中重讀高一。這是個文科班,正稱了我的心愿。我帶著背腰支架,上完一節課便躺在凳子上休息一會兒。體育課是上不了的,就坐在教室門口看。即使這樣,我的心情是愉快的,因為我又有了新同學。而病情似乎也跟著心情跑,一天比一天好。有一天,上古文課的時候,突然從頭發上落下一只小紅蜘蛛在課桌上慢慢地爬。聽老人說,紅蜘蛛是喜兆。莫非有什么喜事要降臨到我的頭上嗎?果然,吃午飯時我就收到了一封遠方的來信,印證了紅蜘蛛的靈驗。信是來自內蒙古醫學院的。一看那娟秀的筆跡,我就知道它出自云香(云翔)之手。700多天鴻雁斷絕,她是怎么找到我的呢?信沒打開,我已淚如雨下。
她告訴我,她現在就讀于內蒙古醫學院,是大一的學生。還說,自從分別后,就一直牽掛著我這個小弟弟,兩年的音信渺無,使她倍加思念。這些,都是我預料中的,只是信的最后卻出乎我意料。她要改變姐弟之稱,明確戀人關系。這使我茫然無措,頗費躊躇。如果在以前,具體地說在我生病之前,她這樣提出,我不會猶豫,而現在,情況變了,貿然的允諾也許給將來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我的身體將來會怎樣?一旦我考不上大學,將來怎么陪伴她?階級斗爭形勢日緊,我這個出身不好的人,將來會不會影響她的工作和前途?然而我的內心卻又真的喜歡她,確定戀人關系,正是我夢寐以求的。云香啊云香,你叫我怎么辦?云翔啊云翔,你讓我怎么說?在理智和感情之間,我痛苦地進行著抉擇。連著幾天,我寢食難安,神思恍惚。最后,理智還是戰勝了感情。我拒絕了她,同時也拒絕了我自己。我想,她見了我的信也未必是好受的,細心的她一定會發現信紙上的淚痕。
高中畢業時,我的病已痊愈,而原來“腰椎骨結核”的診斷也被證明是錯誤的。我如愿以償考入了遼寧財經學院。這時,有老同學勸我重新與她聯系。我想過,但沒這么做。已是勞燕分飛,何必破鏡重圓?山河異地,風月同天;山與山不見,彩云相連。真心的愛,時空不會有損于它的分毫。情悠悠,兩茫茫。我多么希望,“白云還似望云人”啊!
我站在平臺上看云,不禁哼起了馬玉濤的歌;馬兒啊,你慢些走……哼著哼著,馬兒就變成了云。哎,人已古稀,感情卻常在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