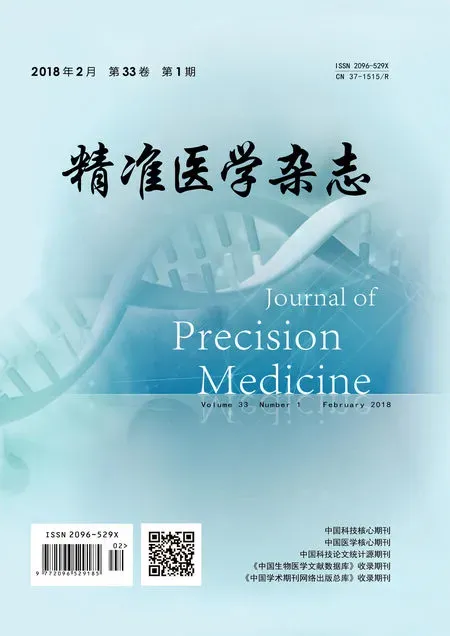第二代測序在腫瘤臨床研究中的應用
(山東大學齊魯醫(yī)院腫瘤內(nèi)科,山東 濟南 250012)
隨著現(xiàn)代醫(yī)學科學技術的飛速發(fā)展,惡性腫瘤的診治已經(jīng)進入了生物信息大數(shù)據(jù)與個體化治療相結(jié)合的精準醫(yī)療時代。在這個發(fā)展過程中,高通量測序又稱下一代測序(the 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NGS)技術以其通量高、信息量大、靈敏度高、耗時短的優(yōu)勢發(fā)揮了關鍵性的作用,逐漸被越來越多的研究者所接受和采用。作為新一代的測序技術,NGS可對數(shù)以百萬計的不同DNA片段混合物進行深度測序,使得短時間內(nèi)獲知個體或疾病的全部基因組信息成為可能。與基因芯片、單核苷酸多態(tài)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NP)分析和傳統(tǒng)的Sanger測序相比,高通量測序可以對從樣本中得到的DNA和RNA進行更大規(guī)模和更高覆蓋度的快速測序,從而得到全景式的分析,并能有效檢測到發(fā)生頻率很低的DNA及RNA變化;有效克服了全基因組關聯(lián)研究(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ies,GWAS) 中假陽性率、假陰性率較高,以及檢測到的SNP很少位于功能區(qū),或?qū)χ虏〉南∮凶儺惡徒Y(jié)構(gòu)變異不敏感等的局限性。NGS主要包括全基因組測序(whole-genome sequencing,WGS)、全外顯子組測序(whole-exome sequencing,WES)以及目標區(qū)域測序(targeted regionsequencing,TRS)等[1]。NGS技術帶來的“革命性”的進步不僅為疾病的基因診斷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利器”[2-3],而且特別適合腫瘤這類同遺傳基因及個體變異雙重相關、具有高度異質(zhì)性的復雜病種[4]。NGS技術的應用使得腫瘤臨床和基礎研究面臨著歷史性的發(fā)展機遇[5]。研究者將NGS技術應用到惡性腫瘤多個領域的基礎和臨床研究中,在腫瘤的發(fā)病機制、分子分型、診治手段及預后分析等方面獲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本文擬結(jié)合一些典型研究對NGS在腫瘤臨床研究中的應用作一綜述。
1 發(fā)掘腫瘤驅(qū)動基因
腫瘤細胞的生成及其惡性生物學表型的維持,有賴于某個或某些癌基因的持續(xù)活化,這些癌基因稱為腫瘤驅(qū)動基因[6]。體細胞基因突變,尤其是驅(qū)動基因突變造成的癌基因激活或者抑癌基因失活,在惡性腫瘤的發(fā)生發(fā)展過程中發(fā)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尋找腫瘤的驅(qū)動基因?qū)﹃U明腫瘤發(fā)生發(fā)展機制以及發(fā)掘可能的藥物作用靶點等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NGS的高通量、高靈敏度為其發(fā)現(xiàn)未知的基因改變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使其成為大規(guī)模發(fā)現(xiàn)腫瘤驅(qū)動基因的“利器”。在美國國立衛(wèi)生研究院發(fā)起的癌癥基因組圖譜項目(The Cancer Genome Atlas,TCGA)中[7],研究者對276例可切除結(jié)腸癌患者的腫瘤樣本進行了全外顯子序列、DNA拷貝數(shù)、啟動子甲基化水平、mRNA和microRNA的表達水平等遺傳學指標的測定,發(fā)現(xiàn)除了已知的APC、TP53、KRAS等常見的突變外,ARID1A、SOX9、FAM123B/WTX等既往報道極少的突變及ERBB2、IGF2等基因的擴增發(fā)生頻率也較高。在乳腺癌[8]、頭頸部鱗癌[9]、惡性膠質(zhì)瘤[10]、卵巢癌[11]等腫瘤當中,TCGA協(xié)作組通過NGS的方法也發(fā)現(xiàn)了一些以前不曾報道過的突變基因。大量新驅(qū)動基因的發(fā)現(xiàn),不僅有助于更好地探究腫瘤發(fā)生發(fā)展的分子機制,也為開發(fā)高效、安全、特異的靶向藥物提供了寶貴的候選靶點。HODIS等[12]利用NGS的方法,對135例黑色素瘤患者的腫瘤標本及其相鄰正常組織進行了全外顯子測序。研究人員總共檢測到了86 813個編碼堿基的突變,平均每百萬個堿基對中就有14.4個編碼堿基的突變,這比其他腫瘤的突變率都要高。而之后,他們還發(fā)現(xiàn)了PPP6C、STK19等6個新的黑色素瘤突變的基因,其中的PPP6C、STK19均可作為藥物研發(fā)的潛在靶點。
2 揭示腫瘤異質(zhì)性
尋找共同的驅(qū)動基因并開發(fā)相應的靶向藥物是使惡性腫瘤的藥物治療獲得重大突破、從而顯著改善患者預后的重要手段。但并不是所有的腫瘤都能找到具有所謂藥靶潛質(zhì)的驅(qū)動基因,也不是所有患者都能從針對主要驅(qū)動基因的治療中獲益。其主要原因就是腫瘤中廣泛存在的異質(zhì)性。這種異質(zhì)性使很多尋找腫瘤“主要”驅(qū)動基因并進行靶向藥物研發(fā)的研究遭遇了滑鐵盧,也導致了很多患者對靶向治療藥物的原發(fā)性耐藥。腫瘤異質(zhì)性可理解為同一種腫瘤表現(xiàn)出不同的遺傳背景、病理類型、分化狀態(tài)、基因變異及蛋白質(zhì)表達特征。腫瘤異質(zhì)性包括空間異質(zhì)性和時間異質(zhì)性,前者包括個體異質(zhì)性、同一個體內(nèi)的瘤間異質(zhì)性和瘤內(nèi)異質(zhì)性;時間異質(zhì)性是指腫瘤發(fā)展的不同階段存在著不同的遺傳學特征。這些差異使腫瘤的生長速度、侵襲能力、對藥物的敏感性、預后等各方面產(chǎn)生不同;更導致腫瘤驅(qū)動基因譜的不同及相應藥靶的選擇障礙。腫瘤異質(zhì)性產(chǎn)生的機制尚不明確,目前認可度較高的學說有:克隆進化學說[13]、腫瘤干細胞學說[14]和腫瘤進化的樹干-樹枝理論[15]。全面揭示腫瘤的異質(zhì)性,就要求研究人員必須多點取樣,即盡量多地獲取某個患者不同部位(通常是原發(fā)灶和轉(zhuǎn)移灶)或者不同時點的標本,從而描繪出這個患者的腫瘤發(fā)病機制及動態(tài)演化的分子圖譜。
GERLINGER等[16]采集了一位腎透明細胞癌患者的9處原發(fā)灶、1處腎周轉(zhuǎn)移灶、2處胸膜轉(zhuǎn)移灶標本,測定了標本全外顯子序列、DNA拷貝數(shù)及mRNA的表達水平等。有研究者推測,BCA52、CCR6、VHL等41個存在于所有腫瘤標本中的基因突變可以被視為腫瘤發(fā)生早期的起源性突變,而SPATA21、ALKBH8、ERCC5等38個轉(zhuǎn)移灶中共有的突變則可能是出現(xiàn)在轉(zhuǎn)移早期,是驅(qū)動轉(zhuǎn)移、定植的關鍵基因。SESN2、CCBL2、CDKN1B等32個原發(fā)灶共有的基因,可能是在腫瘤演化的過程中形成的,可能促進腫瘤適應局部微環(huán)境,也可能是無意義的突變。基于以上分析,靶向藥物的研發(fā)應該針對那些存在于所有癌細胞,即在腫瘤演化早期出現(xiàn)的基因,而不只是那些存在于部分癌細胞的基因。
ELZA等[17]也在非小細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中進行了類似的研究。他們收集了7例NSCLC患者的25份不同部位(原發(fā)灶和肺內(nèi)轉(zhuǎn)移淋巴結(jié))的標本,進行全基因組測序或全外顯子測序。研究者把所有的基因突變或缺失按不同的標本中出現(xiàn)的頻率分為三類:第一類,出現(xiàn)在所有樣本中,包括廣為人知的EGFR、TP53、BRAF、ALK、AKT、PTEN等研究較多的基因;第二類,出現(xiàn)在一處但不是所有的樣本中;第三類,僅出現(xiàn)在一處樣本中。開發(fā)針對第一類基因的靶向藥物有利于更大范圍地殺滅腫瘤細胞亞群,減少腫瘤原發(fā)耐藥。在其中一例患者的標本中,兩處標本的病理類型表現(xiàn)為腺癌,另外兩處標本的類型則趨向于鱗癌。而這兩種不同類型的標本的基因突變圖譜則完全不同。由此可以推測這兩個亞群的癌細胞的腫瘤生物學行為有著極大的差異。因此,針對這例患者單一位點的穿刺活檢極有可能造成誤診,而單一的藥物治療很可能不能覆蓋所有的癌細胞。瘤內(nèi)異質(zhì)性可以導致穿刺活檢的誤診,以及耐藥的發(fā)生。基于瘤內(nèi)異質(zhì)性研究的靶向藥物研發(fā),則有望針對更大范圍的癌細胞亞群,延長耐藥出現(xiàn)的時間甚至避免出現(xiàn)耐藥。
3 揭示腫瘤分子分型
NGS技術的發(fā)展給很多腫瘤的分子病理分型帶來了突破性的進展。以胃癌為例,半個世紀以來,胃癌的病理分型與其發(fā)病機制研究一樣進展緩慢。1965年的Lauren分型[18](腸型、彌漫型)因其簡單、實用仍在臨床沿用,但其不涉及分子機制。2006年有學者發(fā)現(xiàn)不同的Lauren分型對化療的反應不同可能源于不同的病理分子機制,邁出了胃癌分子分型可貴的一步[19]。2011年,新加坡學者基于基因芯片技術,將胃癌按照基因組的特征分為基因組腸型(Genomic intestinal, G-INT)和基因組彌漫型(Genomic diffuse, G-DIF);G-INT患者的預后明顯好于G-DIF的患者;且以5-FU為基礎的輔助化療在G-INT患者中療效更好;提示這種內(nèi)在分型可能是胃癌預后的獨立預測因子[20]。2013年,他們在此基礎上又將胃癌分為了間質(zhì)型(mesenchymal)、增殖型(proliferative)和代謝型(metabolic)。增殖型胃癌細胞存在高度的基因組不穩(wěn)定性、P53突變和DNA低甲基化;代謝型對5-FU敏感,是否接受5-FU輔助治療顯著影響患者生存;而間充質(zhì)型具有腫瘤干細胞的特性,高表達CD44,對PI3K/Akt/mTOR靶點抑制劑敏感[21]。這些研究拓展了胃癌的分子分型及其療效預測的研究空間,為后續(xù)的重要研究奠定了基礎。2014年《Nature》在線發(fā)表的TCGA分型[22]堪稱NGS技術應用于胃癌分子機制研究的里程碑,引起廣泛關注。研究者將胃癌患者組織和血液標本進行了6大分子平臺的測序分析,包括:成組體細胞拷貝數(shù)分析、全外顯子測序、成組DNA甲基化分析、mRNA測序、miRNA測序及成組反相蛋白分析。基于對所得數(shù)據(jù)的分析及整合,提出了一種全新的胃癌分子分型(EB病毒陽性型、微衛(wèi)星不穩(wěn)定型、基因組穩(wěn)定型、染色體不穩(wěn)定型)及其遺傳學特征及干預對策。2015年,亞洲癌癥研究協(xié)作組發(fā)表了基于亞洲患者標本的ACRG的分型,基于多項NGS結(jié)果將患者的遺傳特征進行分類并分析了其與預后的關系[23]。研究者根據(jù)病理標本中微衛(wèi)星不穩(wěn)定性(MSI)、上皮-間質(zhì)轉(zhuǎn)化(EMT)以及TP53突變的情況將胃癌分為微衛(wèi)星穩(wěn)定(MSS)/EMT、MSI、MSS/TP53+和MSS/TP53-四種亞型。研究發(fā)現(xiàn)MSI亞型的預后最好,其主要特點是:高突變(ARIDIA、KRAS、PI3K-PTEN-mTOR、ALK),低復發(fā)率,MLH1缺失,DNA甲基化,多為腸型,復發(fā)率22%;其次是MSS/TP53+,預后較好,EBV的感染較多,高突變(APC、ARID-1A、KRAS、PIK3CA、SMAD4);而MSS/TP53-預后較差,多合并TP53突變;MSS/EMT則多為彌漫型,多為印戒細胞癌,CDH1表達缺失,突變率低,早期發(fā)病,復發(fā)率高,預后最差。此外,MSS/EMT亞型中的腹膜種植率高于其他三種之和。MSI型和MSS/TP53-型的肝轉(zhuǎn)移率均高于MSS/EMT型和MSS/TP53+型。
肺大細胞神經(jīng)內(nèi)分泌癌(Pulmonary large cell neuroendocrine carcinoma,LCNEC)是一種異質(zhì)性很強腫瘤,它和小細胞肺癌(small-cell lung cancer,SCLC)及NSCLC之間的生物學關系仍不明確。而這種不確定性導致臨床上很難給出最佳的治療方案[24]。有學者利用全外顯子測序的方法,分析了45例患者的腫瘤標本及其匹配的正常組織標本,并將LCNEC的基因組改變與其他類型的肺腫瘤進行了對比。研究者發(fā)現(xiàn)根據(jù)基因組的不同改變,可以將患者分為3個亞組:SCLC樣:這組患者均有TP53和RB1的基因突變或缺失,并且有一些其他的常見于SCLC的基因改變,包括MYC擴增等;NSCLC樣:這組患者缺乏TP53和RB1的共同改變,并且存在廣泛的NSCLC樣的基因突變,例如STK11、KRAS、KEAP1突變等;良性腫瘤樣:這組患者有MEN1突變,腫瘤突變負荷較低。SCLC樣亞組和NSCLC樣亞組的許多臨床病理學特征都存在顯著差別,如SCLC樣亞組的腫瘤增殖活性更高(Ki67表達更高),而NSCLC樣亞組表達腺癌分化標志物的水平卻更高。另外,對于以鉑類為基礎的化療,SCLC樣亞組的敏感性明顯高于其他兩個亞組[25]。這項研究為應用NGS手段揭示腫瘤的分子分型并指導臨床治療提供了新的思路。
4 為罕見突變提供治療方案
近年來,晚期惡性腫瘤的靶向治療發(fā)展得如火如荼,尤其是以幾代EGFR的小分子酪氨酸激酶抑制劑(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s,TKI)在EGFR突變晚期NSCLC中的持續(xù)研究和應用為突出的代表。誠然,基于Sanger測序的結(jié)果分析也可以用于指導臨床對于相應患者的選擇。但是NGS技術有著同時檢測多個基因、靈敏度更高、能夠發(fā)現(xiàn)未知或罕見突變等優(yōu)勢,對于發(fā)現(xiàn)罕見突變的患者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以NSCLC的EGFR突變?yōu)槔洳怀R姷耐蛔冾愋桶?9號外顯子插入突變(約占1%),20號外顯子插入突變(約占4%),20號外顯子S768I突變(約占1%),18號外顯子G719X點突變(約占3%)以及21號外顯子L861Q突變(約占2%)等。在HE等[26]的研究中,EGFR 19外顯子插入突變的患者對吉非替尼和阿法替尼敏感。一項回顧性研究發(fā)現(xiàn),阿法替尼對于某些類型的EGFR基因罕見突變療效較好,存在EGFR基因G719X、L861Q和S768I突變的患者獲益較好,但是阿法替尼在其他突變類型中活性均較低[27]。最近報道,臨床醫(yī)生通過NGS技術鑒定了一例NSCLC患者的EGFR的G719C、S7618I罕見突變以及KRAS的E49K突變,并據(jù)此選擇阿法替尼作為治療藥物。后續(xù)隨訪發(fā)現(xiàn)服用阿法替尼11個月后,患者血清CEA明顯降低,胸椎轉(zhuǎn)移灶明顯縮小[28]。除此之外,BRAF基因突變、ALK基因重排、ROS-1基因融合以及其他未知的或者罕見的突變,都可以通過NGS進行鑒定,這對于第一代測序來講,無論是標本量、耗時長度還是發(fā)現(xiàn)未知突變來講,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5 預測療效、跟蹤復發(fā)、判斷預后及分析耐藥機制
SCLC是一種侵襲性很高、易轉(zhuǎn)移的疾病,目前的治療手段仍然是以全身化療為主。很多患者往往是初治敏感,但是不久之后出現(xiàn)耐藥。通常把初治3個月內(nèi)出現(xiàn)的耐藥稱之為原發(fā)耐藥。CARTER等[29]對SCLC患者血標本中的循環(huán)腫瘤細胞(circulating tumor cells,CTC)進行第二代測序,利用拷貝數(shù)變化(Copy-number aberrations,CNA)建立了一個預測化療療效的模型。這個模型預測化療敏感或者耐藥的準確率達到了83.3%,并且根據(jù)模型預測之后,化療敏感組和耐藥組患者的無進展生存期(progression-free survival,PFS),總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均有顯著差異。利用這個模型,只需利用NGS技術檢測病人CTC的CNA,就可以提前判斷患者對化療的敏感性,這是其他技術手段做不到的。
近些年來,對循環(huán)腫瘤DNA(circulating tumor DNA,ctDNA)的研究以及應用的報道越來越多。ctDNA是腫瘤患者血液中腫瘤來源的游離DNA,能全面反映患者體內(nèi)的基因變化情況,具有無創(chuàng)、可重復、患者依從性高的特點,而且能通過多次采樣及時有效地捕捉治療過程中腫瘤基因組變化情況,實現(xiàn)對病情發(fā)展以及治療反應動態(tài)實時監(jiān)測[30-31];而且能部分克服腫瘤異質(zhì)性這個棘手的問題。雖然CTC也具備上述優(yōu)勢,但ctDNA在檢測腫瘤基因組改變等方面有著更高的靈敏度和特異度[32]。
GARCIA-MURILLAS等[33]開展的一項針對早期乳腺癌的臨床研究顯示,相較于現(xiàn)有檢查手段,基于NGS技術的ctDNA的突變監(jiān)測可以將術后復發(fā)的診斷時間平均提前約7.9個月。這有助于及時發(fā)現(xiàn)微小殘留病灶并及時采取相應的輔助治療措施。ctDNA也可以用于反映患者對手術或者化療的響應[34]、檢測靶基因耐藥突變[31]等方面。
EGFR敏感突變的NSCLC患者在臨床使用EGFR-TKI治療9~14個月后會出現(xiàn)耐藥,耐藥機制中最常見的是獲得性T790M突變、MET擴增等一系列的變化。對于耐藥機制的分析也是NGS擅長的領域。同樣,對于T790M突變的特效藥物奧希替尼(Osimertinib)來講,也會面臨繼發(fā)耐藥的問題。有學者利用NGS技術對7例奧西替尼耐藥患者的ctDNA進行高通量測序,發(fā)現(xiàn)了C797S突變;后續(xù)實驗證實C797S突變確實可以導致奧西替尼出現(xiàn)耐藥[35]。 PLANCHARD等[36]利用NGS技術,對2例奧西替尼耐藥患者的活檢標本進行了全外顯子測序,發(fā)現(xiàn)HER2或MET擴增可能是耐藥機制之一。奧西替尼與高選擇性小分子 MET 抑制劑Savolitinib聯(lián)合治療有望延緩甚至克服耐藥的發(fā)生,為這部分患者人群贏得更高的生存獲益。因此,NGS技術為跟蹤分析耐藥機制、發(fā)現(xiàn)新的治療靶點,從而促進惡性疾病向“慢性”疾病轉(zhuǎn)化,以及實現(xiàn)晚期惡性腫瘤患者長期存活的目標提供了有力的技術手段。
6 為免疫治療篩選適合患者
近年來,免疫治療如火如荼,針對PD-1/PD-L1及CTLA4等免疫檢定點的抑制劑在許多腫瘤的治療領域獲得了空前的成功。但是免疫治療尚存在很多爭議,其中之一就是如何篩選獲益的人群。目前通常把PD-L1存在的表達作為生物標志物之一[37]。但這一標志物并不完美,在很多研究中并未能篩選出免疫治療的優(yōu)勢人群[37]。腫瘤突變負荷(Tumor Mutation Burden,TMB)是一項逐漸受到重視的免疫治療預測指標,TMB越多,意味著腫瘤新生抗原越多,就越有利于免疫系統(tǒng)識別腫瘤細胞,進而發(fā)揮殺滅腫瘤的作用[38]。在實際的臨床試驗中,已經(jīng)發(fā)現(xiàn)有著更高的突變負荷的患者在接受治療后有著更高的客觀緩解率(Objective Response Rate,ORR)以及更長的PFS[39]。錯配修復缺陷(deficient Mismatch Repair,dMMR)及高度微衛(wèi)星不穩(wěn)定性(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high, MSI-H)同樣有望作為免疫治療的重要分子標志物之一。dMMR/MSI-H可以導致產(chǎn)生許多體細胞突變,進而產(chǎn)生許多腫瘤新生抗原,誘導腫瘤微環(huán)境局部更多CD8+T細胞的浸潤,進而發(fā)揮更強的殺滅腫瘤細胞的作用。在一項pembrolizumab的Ⅱ期臨床研究中,研究者把患者分為MMR deficient和MMR proficient兩組。前者的ORR(40%)以及無病的生存率(PFS Rate,78%)均明顯高于后者(ORR為0,而PFS Rate為11%)[40]。因此,dMMR/MSI-H也是免疫治療預測療效的分子標志物之一。顯然,不管是TMB,還是MMR,都需要通過NGS(通常是全外顯子測序)的技術來實現(xiàn)。
7 總結(jié)
NGS技術極大地拓展了腫瘤基礎和臨床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在腫瘤學的研究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一方面,NGS將腫瘤發(fā)生、發(fā)展的分子機制的基礎研究推向深入,在發(fā)掘驅(qū)動基因、明確分子分型、揭示腫瘤異質(zhì)性等方面突飛猛進;另一方面,又被越來越廣泛地應用于發(fā)現(xiàn)罕見突變、預測療效、判斷預后、跟蹤復發(fā)、分析耐藥機制及篩選免疫治療的優(yōu)勢人群等臨床治療領域。NGS技術在腫瘤基礎與臨床領域的深入應用和有機結(jié)合,及其衍生出來的“同病異治”(雨傘研究)和“異病同治”(籃子研究)的理論與實踐,突破了傳統(tǒng)研究的范疇,構(gòu)成了轉(zhuǎn)化醫(yī)學研究的經(jīng)典范例,必將極大推動以基因大數(shù)據(jù)與個體化醫(yī)療為特征的現(xiàn)代腫瘤精準醫(yī)學的發(fā)展,為腫瘤患者的生存獲益帶來質(zhì)的飛躍。
[1] 樊綺詩,吳蓓穎. NGS技術在腫瘤診療中的應用及其價值與風險[J]. 檢驗醫(yī)學, 2017,32(4):245-249.
[2] YANG Y, MUZNY D M, REID J G, et al. Clinical whole-exome sequencing for the diagnosis of mendeliandisorders[J]. N Engl J Med, 2013,369(16):1502-1511.
[3] EPI4K CONSORTIUM, EPILEPSY PHENOME/GENOME PROJECT, ALLEN A S, et al. De novo mutations in epileptic encephalopathies[J]. Nature, 2013,501(7466):217-221.
[4] LONGGO D L. Tumor heterogeneity and personalized medicine[J]. New Engl J Med, 2012, 366(10):956-957.
[5] SETHI N, KANG Y. Unravelling the complexity of metastasis-molecular understanding and targeted therapies[J]. Nat Rev Cancer, 2011,11(10):735-748.
[6] WEINSTEIN I B. Addiction to oncogenes—the Achilles heal of cancer[J]. Science, 2002,297(5578):63-64.
[7] CANCER GENOME ATLAS NETWORK. Comprehensive molecular characterization of human colon and rectal cancer[J]. Nature, 2012,487(7407):330-337.
[8] CANCER GENOME ATLAS NETWORK. Comprehensive molecular portraits of human breast tumours[J]. Nature, 2012,490(7418):61-70.
[9] CANCER GENOME ATLAS NETWORK.Comprehensive genomic characterization of head and neck squamous cell carcinomas[J]. Nature, 2015,517(7536):576-582.
[10] CANCER GENOME ATLAS NETWORK. Comprehensive geno-mic characterization defines human glioblastoma genes and core pathways[J]. Nature, 2008,455(7216):1061-1068.
[11] CANCER GENOME ATLAS NETWORK. Integrated geno-mic analyses of ovarian carcinoma[J]. Nature, 2011,474(7353):609-615.
[12] HODIS E, WATSON I R, KRYUKOV G V, et al. A landscape of driver mutations in melanoma[J]. Cell, 2012,150(2):251-263.
[13] DURRETT R, FOO J, LEDER K, et al. Intratumor heterogeneity in evolutionary models of tumor progression[J]. Genetics, 2011,188(2):461-477.
[14] PIETRAS A. Cancer stem cells in tumor heterogeneity[J]. Adv Cancer Res, 2011,112:255-281.
[15] SWANTON C. Intratumor heterogeneity: Evolution through space and time[J]. Cancer Res, 2012,72(19):4875-4882.
[16] GERLINGER M, ROWAN A, HORSWELL S, et al. Intratumor heterogeneity and branched evolution revealed by multiregion sequencing[J]. N Engl J Med, 2012,366(10):883-892.
[17] ELZA C, MCGRANAHAN N, MITTER M, et al. Spatial and temporal diversity in genomic instability processes defines lung cancer evolution[J]. Science, 2014,346(6206):251-256.
[18] LAUREN P. The two histological main types of gastric carcinoma: Diffuse and so-called intestinal type carcinoma, an attempt histo-clinical classification[J]. Acta Pathol Microbiol Scand, 1965,64:31-49.
[19] VAUHKONEN M, VAUHKONEN H, SIPPONEN P. Pathology and molecular biology of gastric cancer[J]. Best Pract Res Clin Gastroenterol, 2006,20(4):651-674.
[20] TAN I B, IVANOVA T, LIM KH, et al. Intrinsic subtypes of gastric cancer, based on gene expression pattern, predict survival and respond differently to chemotherapy[J]. Gastroenterology, 2011,141(2):476-485.
[21] LEI Z, TAN I B, DAS K, et al. Identification of molecular subtypes of gastric cancer with different responses to PI3-kinase inhibitors and 5-fluorouracil[J]. Gastroenterology, 2013,145(3):554-565.
[22] CANCER GENOME ATLAS NETWORK. Comprehensive molecular characterization of gastric adenocarcinoma[J]. Nature, 2014,513(7517):202-209.
[23] CRISTESCU R, LEE J, NEBOZHYN M, et al. Molecular analysis of gastric cancer identifies subtypes associated with distinct clinical outcomes[J]. Nat Med, 2015,21(5):449-456.
[24] VARLOTTO J M, MEDFORD-DAVIS L N, RECHT A, et al. Should large cell neuroendocrine lung carcinoma be classified and treated as a small cell lung cancer or with other large cell carcinomas[J]. J Thorac Oncol, 2011,6(6):1050-1058.
[25] REKHTMAN N, PIETANZA M C, HELLMANN M D, et al.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 of pulmonary large cell neuroendocrine carcinoma reveals small cell carcinoma-like and non-small cell carcinoma-like subsets[J]. Clin Cancer Res, 2016,22(14):3618-3629.
[26] HE M, CAPELLETTI M, NAFA K, et al. EGFR exon 19 insertions: A new family of sensitizing EGFR mutations in lung adenocarcinoma[J]. Clin Cancer Res, 2012,18(6):1790-1797.
[27] YANG J C, SEQUIST L V, GEATER S L, et al. Clinical activity of afatinib in patients with advanced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 harbouring uncommon EGFR mutations: A combined post-hoc analysis of LUX-Lung 2, LUX-Lung 3, and LUX-Lung 6[J]. Lancet Oncol, 2015,16(7):830-838.
[28] TANIZAKI J, BANNO E, TOGASHI Y, et al. Case report: Durable response to afatinib in a patient with lung cancer harboring two uncommon mutations of EGFR and a KRAS mutation[J]. Lung Cancer, 2016,101:11-15.
[29] CARTER L, ROTHWELL D G,
MESQUITA B, et al. Molecular analysis of circulating tumor cells identifies distinct co-py-number profiles in patients with chemosensitive and chemorefractory small-cell lung cancer[J]. Nat Med, 2017,23(1):114-119.
[30] 鄭玲杰,劉舒,王春陽,等. ctDNA在腫瘤診斷和預后應用的研究進展[J]. 中國臨床藥理學與治療學, 2016,21(5):595-560.
[31] DIAZ L A, BARDELLI A. Liquid biopsies: Genotyping circulating tumor DNA[J]. J Clin Oncol, 2014,32(6):579-86.
[32] BETTEGOWDA C, SAUSEN M, LEARY R J, et al. Detection of circulating tumor DNA in early-and late-stage human malignancies[J]. Sci Transl Med, 2014,6(224):224ra24.
[33] GARCIA-MURILLAS I, SCHIAVON G, WEIGELT B, et al. Mutation tracking in circulating tumor DNA predicts relapse in early breast cancer[J]. Sci Transl Med, 2015,7(302):302ra133.
[34] DIEHL F, SCHMIDT K, CHOTI M A, et al. Circulating mutant DNA to assess tumor dynamics[J]. Nat Med, 2008,14(9):985-990.
[35] THRESS K S, PAWELETZ C P, FELIP E, et al. Acquired EGFR C797S mutation mediates resistance to AZD9291 in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harboring EGFR T790M[J]. Nat Med, 2015,21(6):560-562.
[36] PLANCHARD D, LORIOT Y, ANDRE F, et al. EGFR-independent mechanisms of acquired resistance to AZD9291 in EGFR T790M-positive NSCLC patients[J]. Ann Oncol, 2015,26(10):2073-2078.
[37] CARBONE D P, RECK M, PAZ-ARES L, et al. First-line nivolumab in stage Ⅳ or recurrent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J]. N Engl J Med, 2017,376(25):2415-2426.
[38] TOPALIAN S L, TAUBE J M, ANDERS R A, et al. Mechanism-driven biomarkers to guide immune checkpoint blockade in cancer therapy[J]. Nat Rev Cancer, 2016,16(5):275-287.
[39] RIZVI N A, HELLMANN M D, SNYDER A, et al. Mutational landscape determines sensitivity to PD-1 blockade in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J]. Science, 2015,348(6230):124-128.
[40] LE D T, URAM J N, WANG H, et al. PD-1 blockade in tumors with mismatch-repair deficiency[J]. N Engl J Med, 2015,372(26):2509-2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