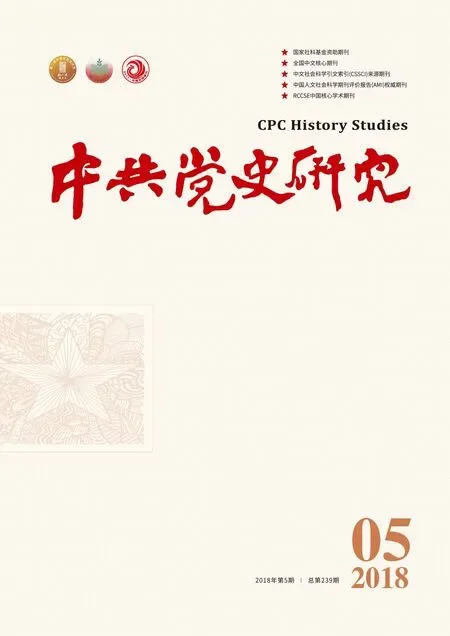“五四”前后陳獨秀對“封建”意涵的探索*
——中共“反封建”話語的初步形成與發展
翁 有 為
與數千年的古代中國相比,近代中國的最明顯變化就是古代中國的影響和活動范圍主要限于東方,而近代則被納入全球化的新的國際范疇。這種變化,一方面表現為中國由以往“天朝上國”的地位而變為強權國際關系中被動乃至較弱勢的一員,處于西方列強壓迫下屈辱、沉淪的“半殖民地”悲慘狀態;另一方面表現為中國在新的國際關系的巨大壓力下由舊而新的自強與革新狀態,是中國在這種國際關系中沖突、抗爭、融合、發展和復興的向上歷史過程。正是在這種沉淪和上升的矛盾斗爭中,中國內部新生的資產階級力量逐步積累和聚變,歷經近代改良、改革而至辛亥革命,一舉結束了“家天下”的千年帝制,建立了新式“共和制”的民國,實現了國家制度的千年“破殼”變局,為未來社會的全面、深刻、徹底的現代化轉型奠定了第一階梯的制度性框架。然而,歷史發展往往并不會一帆風順。民國新制度的建立,并未像革命者所渴望的那樣使中國立即進入國富民強、社會康寧的局面,反而出現了政治倒退、軍人亂政、國家分裂、社會失序的混亂狀態,中國的前途益加危險。在此情勢下,中國必須在辛亥革命的基礎上開拓新的道路。這是一個新的歷史轉變時刻,近代中國社會歷史的發展,已經明確地把對外擺脫列強壓迫、對內消除地方割據分裂局面的嚴峻使命擺到了新開拓者的面前。為完成國家發展和民族生存所賦予的歷史任務,一批懷著拯救和復興民族、改造和建設“新中國”的“新青年”知識分子逐漸積聚到一起,開展“新文化”的啟蒙探索,其中的一部分進而轉變為共產主義者。他們的核心人物是陳獨秀。他站在五千年文明中國與近代西方文明交匯的“五四”潮頭,思慮千載中國歷史理路,洞察萬里國際思潮脈搏,提出了關于近代中國革命和中共革命理論的一系列重大問題,為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和中國革命的發展作出了重大理論貢獻。其中,關于“封建”意涵的探討和“反封建”的思想理論,主要是由他提出并逐步形成初步的理論支點的。這些理論在中共早期的理論發展中具有重要意義和特殊價值,值得系統梳理和認真總結。而“封建”和“反封建”概念不是一個固定的概念,隨著時局和思想的變動,具體所指意涵是不斷擴延的。學界對這一問題的研究還十分薄弱,本文擬就“五四”前后“封建”意涵的演變及“反封建”思想理論的形成和發展作一梳理與分析*相關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馮天瑜:《對五四時期陳獨秀“反封建”說的反思》,《中共黨史研究》2009年第7期;李新宇:《五四“反帝反封建”辨析》,《齊魯學刊》2009年第3期;趙圖雅、斯欽:《五四新文化運動中陳獨秀“反封建”思想評析》,《內蒙古師范大學學報》2008年第3期。上述研究對探討這一問題作了有益探索,不過均將“反封建”視為一個固定概念作為分析的基礎。本文則從“封建”意涵演變的角度,探討中共的“反封建”概念、理論及其思想體系是如何在中國近現代革命的歷史場景和語境中發生、演變的。本文所說的“‘五四’前后”大致起于1915年,止于1926年,橫跨一般所稱的“新文化運動”“五四”“國民革命”等幾個時段。之所以作如此界定,蓋因思想很難用事件的起始標志加以截然分隔,有其獨特的發展脈絡。。
一、所用的中國上古的“封建制度”意涵
陳獨秀在1915年創辦的《青年雜志》上所發表的創刊詞中,就提出了“封建制度”的概念。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此處所說的“封建制度”,細考其“封建”一詞本意,尚非今天通用的“封建”概念,而是指先秦時期所實行的“封建制度”。且看其文道:“舉凡殘民害理之妖言,率能征之故訓,而不可謂誣,謬種流傳,豈自今始!固有之倫理,法律,學術,禮俗,無一非封建制度之遺。”*陳獨秀:《敬告青年》(1915年9月15日),《陳獨秀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91—92頁。可見,陳獨秀認為現在的這些“妖言”“謬種”,不是指現在的“封建制度”,而是以往“封建制度”的遺留。
如果說這里的語意還不夠清晰、明確的話,那么1916年12月陳獨秀在《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一文中的有關表述,則非常清楚地證明了“封建”所指非為“當時”的觀點,正如其文所說:“孔子生長封建時代,所提倡之道德,封建時代之道德也;所垂示之禮教,即生活狀態,封建時代之禮教……封建時代之道德、禮教、生活、政治,所心營目注,其范圍不越少數君主貴族之權利與名譽,與多數國民之幸福無與焉。”可見,“封建”指的是“孔子生長”時代的制度或生活樣式,并非指民國初年的社會與制度,正如他在文中又說:“孔子之經……即在數千年前宗法時代封建時代,亦只行于公卿士大夫之人倫日用,而不行之于庶人,更何能行于數千年后之今日共和時代國家時代乎?”*陳獨秀:《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1916年12月1日),《陳獨秀文章選編》(上),北京三聯書店,1984年,第155頁。此處更明顯、具體地表明“封建時代”是“在數千年前”。這就非常明確地告訴人們,此時所說的“封建制度”或者“封建時代”,都不是指現實的社會制度和時代。也就是說,他這里的“封建”概念,還不是如有學者所說的引自日本或歐洲的概念,而是原原本本的中國固有的“周漢”時代的“封建”概念。其實,在《敬告青年》一文中,他在提到“封建制度之遺”時,就在后面接著說此“遺”之“思想差遲,幾及千載”*陳獨秀:《敬告青年》(1915年9月15日),《陳獨秀文集》第1卷,第92頁。,即表明是很早以前的“制度”。這一認識與一年多以后在《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一文中對“封建”意涵的認定是一致的。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該文中認為當時的社會是“共和時代國家時代”,且提到“今日文明社會”*陳獨秀:《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1916年12月1日),《陳獨秀文章選編》(上),第154—155頁。這一概念,以與“數千年前”的“封建制度”和“封建時代”相區別。
這種語義到1917年在《再答俞頌華》一文中仍是如此:“孔子精華,乃在祖述儒家,組織有系統之倫理學說……其倫理學說,雖不可行之今世,而在宗法社會封建時代,誠屬名產。”*陳獨秀:《再答俞頌華》(1917年5月1日),《陳獨秀文集》第1卷,第239頁。由此可知,在創辦《新青年》的前幾年間,陳獨秀文中所說的“封建”,不是今天所使用的“封建”意涵。盡管當時“封建”的具體意涵指的是幾千年的彼“制度”和“時代”,但陳獨秀是著眼于“今日”而否定以往的彼“封建”的。在這一時期,陳獨秀主要關注的是思想和文化問題,故從中國歷史上的“封建之遺”即上古的“封建制度”探討,從這一思想的淵源和影響脈絡路徑立論,可謂理所當然。但其思想進程在中國整體趨勢向革命發展的情況下,亦必然要向現代革命話語的路徑轉換。就此而言,盡管這一時期中共還未成立,但整體觀之,可視為隨后成立的中共“反封建”思想不可或缺的預備期和醞釀期。
二、由法俄大革命中的“封建”到中國近代“反帝反封”中的“封建”“半封建”
隨著陳獨秀從思想文化領域的啟蒙轉向政治領域的革命建黨,要在中國進行現代革命救國的偉大事業,從中國古代的歷史中尋找不到相應的理論和思想資源,只能到近代西歐資產階級革命和俄國的十月革命中尋找經驗和智慧,其中西歐資產階級革命中的“封建”概念和俄國資產階級革命及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中的“資產階級”“封建”等概念,都是繞不開、避不過的基本性、核心性概念。由于中國革命的后發性,先進知識分子必然要將這些基本的理論和概念,根據中國的革命實際,運用到對中國革命形勢和革命策略的分析與理論思考中來。因此,陳獨秀由論說法國、俄國大革命中與資產階級相對立的“封建”,在認識和分析清末民初辛亥革命尤其是“五四”前后阻礙歷史發展的保守與割據勢力等現象時,必然與法國、俄國大革命時期資產階級對立面的專制君主的“封建”屬性相聯系,而實際上二者在歷史進程中扮演的角色及其屬性也是十分相似的。
“五四”以后,陳獨秀加快了建立中共的步伐,他的思想認識轉到如何從世界革命的角度,認識和分析當時中國的社會階級狀況、時代的歷史性課題和發展方向等重大現實問題上。1920年國慶節之際,陳獨秀在《國慶紀念底價值》一文中,由對“共和”價值的反思分析了歐洲資產階級反“封建”的歷史局限,并繼而用“封建”這一概念分析了民初的社會和政治狀況。這是他認識和運用“封建”概念的一大思想轉折。他寫道:“我們十分承認卻只承認共和政治在人類進化史上有相當的價值,法蘭西大革命以前的歐洲,俄羅斯大革命以前的亞洲,打倒封建主義不能說不是他的功勞。但是封建主義倒了,資本主義代之而興,封建主義時代只最少數人得著幸福,資本主義時代也不過次少數人得著幸福”,“主張實際的多數幸福,只有社會主義”。而在中國,雖然經過辛亥革命,即使“次少數人也沒有像歐美中產階級都得著了幸福,自由權利與幸福還是為最少數人所獨占,直到如今還完全是封建主義恢復了固有的勢力,支配一切。尊祀孔子及武人割據,這兩件事就是封建主義支配一切精神方面及物質方面底明證”。他繼續分析指出:“這封建主義得勢,也不過是一時現象,我以為即在最近的將來,不但封建主義要讓共和,就是共和也要讓社會主義。”*陳獨秀:《國慶紀念底價值》(1920年10月10日),《陳獨秀文章選編》(中),北京三聯書店,1984年,第31—32、32—33頁。在此文中,“封建”的概念一方面指歐洲資產階級革命前的社會狀態,另一方面指當時掌握思想文化權力的尊孔派和掌握軍政大權的軍閥。這就把以往專指西周邦國制度的“封建”轉移到現代歐洲話語意義上的“封建”即指當代權勢階層,并用這一分析框架來分析辛亥革命后的中國權勢狀況。這種話語意涵的轉化是必然的,因為近代革命是中國進入現代國際體系后的必然產物,作為對這一歷史進程狀況的描述和分析,使用現代西方的某些概念不僅是適宜的,而且是必需的。只有這樣,才能更準確地表達最早起源于西方的現代革命運動對中國社會產生的共振和影響,才能真實地表達中國社會轉型的具體歷程。而陳獨秀由使用中國固有意義的“封建”一詞轉為使用引自西方話語的“封建”一詞,恰是一種創造性的使用。中國原有意義上的“封建”雖然與西方話語中的“封建”內涵存在相似之處,但無法與“資產階級”之類概念相連接、相對應,更不宜與現代“民主”“革命”等概念相連接、相對應,而將西語中的“封建”置換過來,雖然詞名相同,但概念的意涵與“資產階級”“無產階級”等現代概念相連接、相對應,語義表達無疑更為清楚、準確,不會產生歧義與意涵混淆的情況,更宜于準確表達現代的社會狀況和政治狀況。轉為現代意義用于指稱現代社會現象,“封建”一詞除具有與歐洲資產階級相對立的“專制”意涵外,當時還具有民初背景下的“割據”“落后”等意涵。因此,陳獨秀在此文中由敘述歐洲資產階級革命對象的“封建”,很自然地過渡到民初仍為資產階級革命對象但因革命不徹底而得以“恢復了固有的勢力,支配一切”的軍閥等“封建主義”勢力。這種置換當然不是隨意的,是陳獨秀從革命理論與斗爭實踐的現實需要出發加以思考和提煉而形成的,也與他接受共產主義理論尤其是共產國際關于“封建”問題的相關理論有很大聯系。不過,他對這一概念的接受,有其對封建問題長期理論思考的基礎和相關的知識積累儲備,并出于分析革命形勢、制定革命政策等現實迫切需要而有意致之。當然,盡管他已對“封建”概念進行了現代性置換,但相關的理論形態還會呈現一時難以穩定的狀況,在一個時期內游離于固有意義上的“封建”與現代意義上的“封建”之間。這也說明,一種思想或概念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陳獨秀對“封建”的認識由指稱中國孔子生活時代到歐洲資產階級革命時代再到民初當代的時空轉變,但落于“當代”之“腳”站立得并不那么踏實。 1920年底,陳獨秀在《民主黨與共產黨》一文中使用“封建”一詞時說:“民主主義是什么?乃是資本階級在從前拿他來打倒封建制度底武器。”*陳獨秀:《民主黨與共產黨》(1920年12月1日),《陳獨秀文章選編》(中),第67頁。顯然,“封建制度”是與民主主義相對立的“專制”。因此從詞義看,這里更突出了“封建”一詞所具有的專制性質,但是在時間上,“封建”一詞主要還是指的“從前”。不過,這個“從前”已不是中國的“周漢”時代,而是歐洲的資產階級革命時代,即此詞的使用是在現代革命話語體系中使用的。不久,他在一次講演中提到“封建”一詞時,其意涵仍是近代資產階級革命的話語分析,他所說的“如今封建時代已經過去,進入資本制度的時代了。又發現兩種階級:代諸侯和地主階級而起,是政府和資本家,從前的農奴,就是今日的勞動者。資本家能壓逼勞動者,勞動者就要受資本家壓逼”*陳獨秀:《如何才是正當的人生——在廣東省立女子師范學校講演會演詞》(1921年1月23日),《陳獨秀文章選編》(中),第102頁。,仍是從世界范圍內來使用“封建”概念的。從其語義看,似乎是屬于“資本制度”體系的,但之前多次強調的“封建主義”與這個體系是何種關系,顯然陳獨秀對這些問題還沒有思考清楚,還處于不自覺的狀態。
隨著中共的建立,作為黨的領袖的陳獨秀必須思考中國革命的一系列重大問題,如在國內問題上,阻礙中國社會發展的主要障礙——軍閥勢力是一種什么樣、什么性質的政治勢力以及對軍閥勢力應持什么樣的政策和態度等,需要新成立的中共及其主要領導者給予準確解答,以確定今后的行動方向。由于軍閥與南方資產階級民主派的對立,陳獨秀明確了軍閥的“封建”屬性,并進一步把軍閥的封建屬性與資產階級的屬性、鄉村地主豪紳的社會屬性放到中國統一體的認識框架內,逐步認識到軍閥的“封建”性、“半封建”性和鄉村地主豪紳的“封建”性、“半封建”性,從而對中國革命的對象、性質等重要理論問題作出了可貴探討。
1922年6月,在中共二大召開前夕,陳獨秀對國際和國內的政治狀況作出分析,認為“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和“國內軍閥的擾亂”為兩大主要問題。也就是說,前者是中國的國家獨立、民族獨立問題,后者是中國的國家統一、民族統一問題。這都是關系到中國生死存亡的重大問題。陳獨秀明確指出:“(一)傾覆軍閥及賣國黨,尤其首先要懲創勾結賣國黨或希圖割據的軍閥,以實現國內和平與本部統一。(二)……反抗國際帝國主義的一切侵略,使中國成為真正獨立的國家。”在國內問題上,陳獨秀進一步分析說:“中國政治糾紛之根源,是因為封建式的大小軍閥各霸一方,把持兵權、財權、政權,法律輿論都歸無效,實業、教育一概停頓。”這一狀況造成國家和民族的空前危機,必須消除。而這種軍閥當政的狀態是一種什么性質的社會狀況呢?陳獨秀分析說:“封建的國家建設在軍閥權力之上……半封建半民主的國家建設在軍閥和人民兩種權力之上。”在陳獨秀看來,中國的社會現狀似乎處于“半封建”的狀態。由西周的“封建”而到歐洲的“封建”,又由歐洲的“封建”到中國民初當下的“封建主義”,再由民初當下的“封建主義”而到“半封建”,其思想認識的演變軌跡隨著革命斗爭的深入以及中共由孕育到誕生再到成長的豐富實踐而逐步深化和明確。他更進一步提煉道:“對內傾覆封建的軍閥,建設民主政治的全國統一政府,對外反抗國際帝國主義,使中國成為真正的獨立國家,這才是目前扶危定亂的唯一方法。”*陳獨秀:《對于現在中國政治問題的我見》(1922年6月),《陳獨秀文章選編》(中),第185—187、188頁。這就是后來稱為中共二大“反帝反封”綱領內核的原創性表述。隨后召開的中共二大通過的《關于“國際帝國主義與中國和中國共產黨”的決議案》指出了“脫離世界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推倒封建制度的軍閥”*《關于“國際帝國主義與中國和中國共產黨”的決議案》(1922年7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冊,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62頁。問題。中共二大通過的《關于“民主的聯合戰線”的議決案》指出,“中國名為共和,實際上仍在封建式的軍閥勢力統治之下,對外則為國際資本帝國主義勢力所支配的半獨立國家”,因此,中共必須聯合“民主派才能夠打倒公共的敵人——本國的封建軍閥及國際帝國主義——之壓迫”*《關于“民主的聯合戰線”的議決案》(1922年7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冊,第65頁。。這就是“反帝反封”的表述。中共二大通過的大會宣言指出:“各種事實證明,加給中國人民(無論是資產階級工人或農人)最大的痛苦的是資本帝國主義和軍閥官僚的封建勢力,因此反對那兩種勢力的民主主義的革命運動是極有意義的:即因民主主義革命成功,便可得到獨立和比較的自由。”其目標是:“(一)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二)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三)統一中國本部(東三省在內)為真正民主共和國。”*《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大會宣言》(1922年7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冊,第114—115頁。這就把“反帝反封”明確地與中華民族的獨立、國家的統一、制度的民主這一歷史任務緊密地結合起來。從歷史的發展來看,中共二大確實確立了“反帝反封”的革命綱領。把陳獨秀在中共二大前的表述通過黨的決議和宣言的形式公之于全黨,為中國革命進程的發展確立了前進的方向。這些思想當然不宜說是陳獨秀一個人的,但以陳獨秀在建黨過程中的地位、威望和思想水平以及他對“反封建”問題的思考來看,這些思想成果無疑主要是他貢獻的。
值得提出的是,陳獨秀在這里把軍閥定為“封建式”“封建”的性質。這一概念的使用使中國革命的事實和實踐上升到革命的理論層面,并進而顯現了中國革命性質及其與世界革命的關系。因為,從事實和實踐層面看,軍閥在中央者干政弄權,在地方者各霸一方,國家陷于紛爭混亂狀態,嚴重阻礙了中國社會的發展,為千夫所指,是必須將其打倒的。但組織人民起來打倒軍閥,與陳炯明率兵攻打孫中山有什么不同,這不僅是“勝王敗寇”的問題,而是因為孫中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派代表著中國救亡統一的方向,而軍閥之所以“禍國殃民”,是因為其代表著“封建”的衰敗、沒落、將要退出歷史舞臺的方向。這就把反對軍閥的斗爭納入到資產階級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序列中來。“反封建”是一個綱領,是一面旗幟,而把軍閥定為“封建”性質,顯然是一個重大的理論突破,為以后的“反封建”向縱深發展選擇了戰略性基點。而當時提出中國的國家和社會為“半封建”,是因為經過辛亥革命民主的洗練,“民主”勢力有了一定力量,和資產階級革命前的“封建時代”不同,和資產階級革命成功后的國家也不同,故稱“半民主”的對立面為“半封建”。這一稱謂此時還主要是從政治視角來立論的,未及考慮社會經濟基礎的因素,表明對“封建”“半封建”的認識,尚處于探索與發展的過程之中。雖然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半封建”的概念早就有表述*列寧指出,應進行“反對各種封建主義現象或封建主義殘余的農民運動”。參見《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17—1925)》,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第142頁。其實,恩格斯早在1851年就使用過“半封建”概念,列寧在1912年就提出中國是一個“落后的、農業的、半封建國家”。參見陳金龍:《“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形成過程考析》,《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4期。,但陳獨秀絕非照搬經典,而是經過長達數年的認識和思考,又經過創辦《新青年》、創建中共、投身反軍閥斗爭等一系列革命斗爭實踐的磨煉,是理論與革命實踐相結合的產物,到中共二大前提出的這一新概念,正是重要的理論創新成果。至此,可以說標志著中共“反封建”話語的初步形成。
三、“封建”“半封建”與從城市軍閥“封建”到鄉村地主“封建”
“封建”既是一個重要的理論問題,也是一個重要的歷史問題,還是一個重大的現實問題。陳獨秀試圖從社會歷史發展階段中探討和解釋社會發展的規律性問題。他在《革命與反革命》一文中,探討“人類社會之歷史,乃經過無數進化階段及多次革命戰爭”,“今日之組織”即是這種進化和革命戰爭的結果。他總結指出,“其組織進化之最大而最顯著者,乃是由部落酋長進化到封建諸侯王,由封建諸侯王進化到資產階級,由資產階級進化到無產階級”,而“在每個進化階段新舊頓變時,都免不了革命戰爭”。他認為,“革命之所以稱為神圣事業”,是因為它“是推進人類社會組織進化之最有力的方法”。*陳獨秀:《革命與反革命》(1923年1月18日),《陳獨秀文章選編》(中),第222頁。在這篇文章中,陳獨秀主要論證革命在“新舊頓變”之際發生的規律性及其“推進”人類歷史進步的重大作用。在這一論證中,陳獨秀筆下的“封建”是簡易版的歷史進化模式中的一個階段,雖然與中國社會歷史發展階段的實際狀況不合,甚至與西歐社會歷史發展階段的實際狀況也不吻合,但畢竟他嘗試從“人類歷史發展”這樣一種宏觀的世界性視野中探討革命的規律性及其歷史意義,而“封建”作為資產階級革命前的一個歷史時代則是毫無疑問的。這樣,根據世界革命運動的歷史規律,當下的中國既然需要繼續進行資產階級的革命,因此而有“封建主義”是合乎這一規律的。而此時,不是資產階級革命尚未發生,而是資產階級革命發生了,但經歷了嚴重挫折,因此此時的“封建主義”是“封建勢力”的“恢復”,而不是完整的“封建勢力”,正如陳獨秀此前所指認的那樣,是個“半封建”。
隨后不久,陳獨秀在《資產階級的革命與革命的資產階級》一文中,沿著“人類社會組織之歷史的進化”之角度,就中國歷史上和現實中的“封建”問題進行了比較系統的理論性探討。他主要從經濟模式和生產力的發展水平,論證中國長期“停頓在家庭農業、手工業自足的經濟制度之下”,“封建軍閥時代遂至久延生命,由秦漢以至今日,社會的政治的現象,都是一方面封建勢力已瀕于覆滅,一方面又回向封建,這種封建勢力垂滅不滅的現象,乃是因為封建宗法社會舊有的家庭農業手工業已充分發展而有更進一步的傾向,但新生的經濟勢力(即資本主義的大工業)過于微弱,還不能取而代之的緣故”。值得注意的是,陳獨秀在這里一是把秦以后的社會稱為“封建軍閥時代”,這與我們后來所說的秦以下的古代史是“封建社會”頗有相近之處,所不同的只是他認為“封建”與“軍閥”是連在一起的;二是他所提出的“封建”“久延生命”長期“垂滅不滅”之問題,在20世紀80年代曾經引起熱烈討論,其實早在五四時期陳獨秀就注意到這一歷史現象;三是陳獨秀試圖解釋中國“封建”之所以“久延生命”,是由于“家庭農業手工業已充分發展而有更進一步的傾向”,這是從經濟基礎這一更深的層面來解釋中國“封建”長期延續的問題。這表明,他對“封建”的認識已從政治層面擴充到經濟層面,顯示了唯物史觀對其思想分析方法論所產生的影響。不僅如此,陳獨秀還用“封建宗法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個概念描述近代西力東侵問題,并說辛亥革命是“中國歷史上封建帝制變化到資本民主之劇烈的開始表現”。在這篇文章中,陳獨秀認為,資產階級在“半殖民地”中國的現實情況下,一部分是具有革命性的,這就是后來所說的“民族資產階級”;另一部分因與封建軍閥和外國勢力有密切聯系,具有反革命的性質,這就是后來所說的“買辦資產階級”或“官僚資產階級”。除此兩派外,陳獨秀認為還有一種是“非革命的資產階級”,他們工商業的“規模極小”,但在中國社會中居于“最大多數”,是反帝反封建軍閥的革命必須爭取的重要力量,這應該就是后來所說的“小資產階級”。歸納其文,在陳獨秀看來,中國的封建社會至“鴉片戰爭”之際“開始大崩潰”,到“甲午、庚子兩次戰爭”是“中國封建宗法的道德思想制度最后的崩潰”,“辛亥革命”本應將封建制度社會轉變為資產階級民主制度社會,但由于資產階級的幼稚與軟弱,“未曾發達到與封建官僚階級截然分化的程度”,遂使政權“完全歸諸帝政余孽北洋軍閥之手”,“所以始終依賴他們的敵人——封建的北洋派”,即使到今天,由于資產階級勢力微弱“尚不足克服封建軍閥”,因此,“革命的資產階級應該和革命的無產階級妥協,打倒共同敵對的軍閥階級”。*陳獨秀:《資產階級的革命與革命的資產階級》(1923年4月25日),《陳獨秀文章選編》(中),第254—258頁。這就從經濟到政治、從古代到近代、從封建軍閥到資產階級再到無產階級等多重角度,系統地論證、闡釋與探討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國國民革命的力量、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合作、革命的對象是“軍閥階級”等重大革命理論問題。
1923年7月,陳獨秀撰寫了《中國農民問題》一文。他指出,在像中國這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中,要進行反對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封建軍閥的斗爭,“不可漠視農民問題”。從人口數量上看,農民占中國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即此人數上看起來,我們應感其重要”。他認為,農民因外受“外貨輸入”影響一般物價增高而農產品價格低落,使中國農民經濟大受打擊;內受“軍閥戰爭及水旱災荒”影響,而使農民困苦失業流為兵匪之困。為解除農民的“此等痛苦”,應該向農民開展以“排斥外力”“打倒軍閥”“限田”“限租”“推翻貪官劣紳”為主要內容的宣傳和動員。進而,更有必要建立“農會”“鄉自治公所”“佃農協會”“雇農協會”等農民群體組織,把廣大農民動員到國民革命的組織系統中來。*陳獨秀:《中國農民問題》(1923年7月1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278—285頁。陳獨秀的這一思想與此前剛剛閉幕的中共三大對農民問題的有關探索是緊密相連的。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共三大在廣州召開。陳獨秀在大會的報告中指出“我們很少注意農民運動和青年運動”*《在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1923年6月),《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冊,第245頁。的工作缺陷,顯示了今后要加強農民運動的動向。因而,中共三大制定的《中國共產黨黨綱草案》明確提到“中國之國民革命及無產階級和農民在此革命中所占的地位”問題,指出:“國民革命,這種革命自屬于資產階級的性質。但是在這個革命中間,無產階級卻是一種現實的最徹底的有力部分”,“至于農民當中國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占非常重要地位,國民革命不得農民參與,也很難成功”*《中國共產黨黨綱草案》(1923年6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冊,第138—139頁。。在這里,會議把農民放到了緊隨無產階級之后的重要力量,顯示了對農民問題的高度重視。中共三大還通過《農民問題決議案》,提出“結合小農佃戶及雇工”以反帝反封建軍閥及“貪官污吏,反抗地痞劣紳”,“以保護農民之利益而促進國民革命運動之必要”*《農民問題決議案》(1923年6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冊,第151頁。。陳獨秀在大會報告中對以往忽視農民問題的反思與大會對農民問題的重視以及關于農民問題決議的制定與通過,說明黨的領袖與黨內高層就重視農民問題已達成高度共識,因此會議結束不久后的次月1日,陳獨秀就發表了關于農民問題的專文,說明中共革命的基礎——農村和農民問題這一重大戰略性問題,已經進入中共的認識視野。1923年12月,陳獨秀在《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一文中指出:“人類經濟政治大改造的革命有二種:一是宗法封建社會崩壞時,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一是資產階級崩壞時,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此外,還有“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國民革命”,“對內”是具有反封建性質的“民主革命”和“對外”的反抗殖民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半殖民地的中國”就是要進行“反封”的“民主革命”和“反帝”的“民族革命”的雙重艱巨任務。為了完成這一艱巨任務,無產階級除須聯合資產階級外,還要聯合廣大的農民。陳獨秀認為:“農民占中國全人口之大多數,自然是國民革命之偉大的勢力,中國之國民革命若不得農民之加入,終不能成功一個大的民眾革命。”*《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1923年12月1日),《陳獨秀文章選編》(中),第362、366—367頁。值得注意的是,在這篇文章中,陳獨秀認識到農民具有“革命之偉大的勢力”,這一認識是對之前農民具有“非常重要地位”認識的深化,也是對他幾個月前在《中國農民問題》一文中所提出的農民為“國民革命之一種偉大的潛勢力”*陳獨秀:《中國農民問題》(1923年7月1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冊,第278頁。認識的進一步發展。應該說,陳獨秀此時認識農民問題,在中共成立不久尚處于“幼年”、力量比較薄弱的情況下,站在聯合勢力較為廣泛的資產階級力量如何打倒強大的“封建”軍閥勢力的角度,對黨的領導力量尚不夠自信應該是個事實。因此,他提出的“國民革命”,大體上仍屬于資產階級領導的革命范疇。正是在這種思想的作用下,他看到了農民有分散和“趨向保守”等缺點(也正因為陳獨秀的這種不自信,在某種意義上影響到他當時及大革命高潮之際對革命領導權的準確判斷),但盡管如此,他對農民這一“偉大”的革命“勢力”的定性,為以后重視農民運動和開展農民組織工作作出了很有意義的探索。
陳獨秀筆下的“封建論”不僅是他分析中國社會進化的重要理論環節,還是他認識中國近代革命運動發生、發展和演變的關鍵性支撐,更是他用以指導革命運動開展、決定革命發展方向、制定和實施革命斗爭政策和策略的思想武器。中共三大通過的文件及其后中共中央第二次對時局的主張,分別以“封建的”和“封建”來確定軍閥性質與資產階級的區別,而把“封建”性質的軍閥作為中國革命的對象*《關于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議決案》(1923年7月)、《中國共產黨對于時局之主張》(1923年8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冊,第146、178頁。。可見,中共三大的這些認識與陳獨秀的思想具有密切聯系。在1924年5月舉行的中共中央擴大會議通過的有關決議指出:“中國享有土地及使用土地的制度在經濟上有一種半封建半宗法的階級關系,而政治上便是一種官僚軍閥任意凌虐農民的景象。”因此,應該宣傳、組織和領導農民進行反對土豪劣紳和軍閥及帝國主義的斗爭。*《農民兵士間的工作問題議決案》(1924年5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冊,第247—249頁。擴大會議關于農村土地制度所反映“封建”“階級關系”的觀點和對農民開展革命宣傳動員的認識成果,與陳獨秀關于農民革命潛力的判斷,以及國共合作后國共兩黨相繼成立相關組織進行農民運動的具體實踐指導和探索,顯然都存在密切聯系,思想認識的發展軌跡非常明顯。中共四大文件指出,中國民族革命的特點之一就是“反對封建的經濟關系,反對封建的軍閥政治(如督軍制,雇傭軍隊制,政權分裂,農民屈伏于官紳,人民無法律的保護)”*《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1925年1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冊,第337頁。。此處的“封建”由以往注重政治與制度層面擴展到經濟層面,而對“封建的軍閥政治”的內涵也有了具體的列舉說明。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四大提出的軍閥政治還包括了“農民屈伏于官紳”,把壓迫鄉村農民的官紳也列入“封建的軍閥政治”的范疇。應該說,這些對“封建社會”“封建軍閥”的分析,雖仍不無粗糙之感,但已具有一定的理論雛形和理論要點。
由于確定了軍閥的“封建”屬性,在陳獨秀看來,“統治中國的當然是封建的軍閥官僚階級”。換言之,統治階級是屬于“封建”性質的。他明確指出,“現在統治中國的封建階級里面,武的既然拿槍搶大錢,文的只得伸手討小錢”,對于“他們這種分贓的怪現象”,“本沒有什么稀奇”。*陳獨秀:《可憐的伸手派》(1923年5月9日),《陳獨秀文章選編》(中),第268頁。他認為:“統治中國的是封建的軍閥階級,他們勾結外國帝國主義者為后援,資產階級、勞動階級都在他們的壓迫之下,所以中國勞動階級和社會主義者的目前工作,首先要做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的國民革命。”*陳獨秀:《關于社會主義問題——在廣東高師的講演》(1923年5月—6月20日),《陳獨秀文章選編》(中),第301頁。
由于軍閥與官僚和買辦資產階級的結合,陳獨秀在對“封建軍閥”認識的基礎上,結合中共關于民族民主革命的歷史范疇,對整個統治階級的“封建階級”的認識,重返1922年6月《對于中國現在政治問題的我見》一文“半封建”的提法上。他在1926年9月《我們現在為什么爭斗?》一文中又使用了“半封建派”提法,認為“半封建派”包括當時的奉直軍閥、官僚、洋行買辦、地主豪紳、交通系、安福系、研究系、聯治派、國家主義派、復辟派及新社會民主黨等當權者及其依附勢力。陳獨秀指出當時正在進行的國民革命的兩個目標,“就是打倒外國帝國主義和國內半封建勢力”即“民族革命”“民主革命”兩個方面。值得注意的是,為了實現打倒半封建勢力派任務,陳獨秀認為:“應該和農民合作,懲治貪官污吏、劣紳、地主、土豪,而不應放任貪官污吏及駐軍勾結劣紳、地主、土豪,蹂躪農民;因為農民是國民革命中主要的廣大民眾,劣紳、地主、土豪乃是半封建勢力之真實基礎。”*陳獨秀:《我們現在為什么爭斗?》(1926年9月25日),《陳獨秀文章選編》(下),北京三聯書店,1984年,第261—262、264—265頁。此處陳獨秀提出的“劣紳、地主、土豪乃是半封建勢力之真實基礎”的認識,是中共黨人反“封建軍閥”思想的邏輯延伸和革命斗爭深入發展的重大標志,無疑是重要的認識成果。
在陳獨秀上述關于農民革命性問題的探索過程中,中共黨內其他領導人也先后由關注工人問題轉向對農民革命問題的思想探索,如李大釗、瞿秋白、毛澤東和鄧中夏等人都公開發表了關于如何從事農民運動問題的理論指導性文章。瞿秋白和毛澤東在這一時期逐漸關注農民運動,他們與陳獨秀的密切關系而受其影響,不能排除是一個因素*在1923年6月中共三大上,毛澤東被選為中央委員會委員,并一度擔任中央執行委員會和委員長陳獨秀的秘書。正是在中共三大上,陳獨秀開始重視農民,隨后發表了一系列關于農民問題的文章。此后,中共中央也起草和通過了關于農民問題的有關決議。作為秘書的毛澤東與委員長的陳獨秀在文件上有共同簽字權,到1924年11月毛澤東仍與陳獨秀共同簽名,說明二人的合作關系。瞿秋白也受到陳獨秀的賞識和重用,留蘇回國后便被陳獨秀提拔到中央機構工作,在1925年1月中共四大上被選為中央委員,并擔任宣傳部委員。這也說明了瞿秋白和陳獨秀的密切關系。同時,瞿秋白和毛澤東都于1924年1月參加了國共合作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二人都擔任了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在大革命失敗之際,盡管瞿秋白和毛澤東反對陳獨秀在國民黨舉起屠刀時的后退政策,但在建黨早期以及國共合作初期,他們深受陳獨秀重用。因而,這一時期陳獨秀關于農民問題的認識對他們的思想影響當是客觀的。當然,后來在大革命面臨失敗之際,陳獨秀的思想趨于停滯、保守而后退,而瞿秋白和毛澤東則隨著時代前進展開了新的斗爭。。瞿秋白在1926年8月的一次演講中認為,到現在“中國的社會依然是封建的形式”,“軍閥是封建社會的余孽,他實是代表地主買辦階級”,“地主與買辦是軍閥的命根,是軍閥的經濟基礎”,因此,“我們要打倒軍閥必須打倒地主”*瞿秋白:《國民革命中之農民問題》(1926年8月),《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80—382頁。。毛澤東于同年9月在《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一文中明確指出:“農民問題乃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經濟落后之半殖民地的農村封建階級,乃其國內統治階級國外帝國主義之唯一堅實的基礎,不動搖這個基礎,便萬萬不能動搖這個基礎的上層建筑物。中國的軍閥只是這些鄉村封建階級的首領”,“地主政權即軍閥政權的真正基礎”*毛澤東:《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農民問題叢刊〉序》(1926年9月1日),《毛澤東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41頁。。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在這篇文章中明確把農民問題提到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之高度加以認識,并把地主這個“農村封建階級”視為內外反革命統治的“唯一堅實的基礎”。在對農村革命極端重要性的問題上,毛澤東的表述最為清晰、完整,是對陳獨秀農民問題之思想探索的發展。在這種探索農民革命問題的氛圍中,從事農民運動的彭湃于1926年9月根據廣東革命形勢發展到農村的實踐情形總結道:“革命的斗爭,由都市而轉入于農村,現在正是農村中革命勢力與反革命勢力不斷的沖突到最利害的時期。”*彭湃:《花縣團匪慘殺農民的經過》(1926年9月),《彭湃文集》,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70頁。瞿秋白尤其是毛澤東和彭湃的這些認識,是他們把陳獨秀和中共中央關于農民革命問題探索的一般理論和政策結合具體從事的農民運動實踐而總結和提煉出來的,是對中共黨人將“反封建”革命推進到農村這一趨勢的新認知和新發展。這一時期,在國共合作“扶助農工”政策的大背景下,國共兩黨各級黨組織成立了指導農民運動的專門機構,在廣東、廣西、湖南、湖北、河南、四川、陜西、江西等地開展了廣泛的“農民運動”。為此,陳獨秀在給中共各級黨部的信中明確提出了“黨到農民中去”的號召*陳獨秀:《陳獨秀給各級黨部的信——對于擴大黨的組織的提議》(1926年10月17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425頁。。這樣,陳獨秀等中共黨人關于中國革命對象的認識,由“封建軍閥”而推進至農村“封建”的劣紳、地主、土豪,成為中國革命由上層推進到社會基層的重大步驟,也是中國由城市革命轉向農村的關鍵邏輯起點*李大釗在1925年底1926年初探討了農民對中國革命的重要性問題。他認為,“在經濟落后淪為半殖民的中國”,農業仍為“國民經濟之基礎。故當估量革命動力時,不能不注意到農民是其重要的成分”。李大釗:《土地與農民》(1925年12月30日——1926年2月3日),《李大釗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98頁。周恩來也認識到農村的重要性,認為應向農村的“半封建”勢力進行斗爭。他說,“各地民團,百分之九十九是在土豪劣紳手中。他們利用此武裝勢力壓迫農民,抽收苛捐雜稅自肥中飽,簡直是鄉村軍閥”,“這些買辦、大地主、逆黨、土豪、民團、土匪、貪官污吏沒有一種不是舊社會遺存的半封建勢力,沒有一種勢力不是與革命為敵的”,我們現在“應加緊而內向半封建勢力爭斗”。周恩來:《現時廣東的政治斗爭》(1926年12月17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3冊,第520—521頁。如前文提到彭湃所考察發現的革命的斗爭“由都市而轉入于農村”現象即為一證。實際上,自國共合作開始逐步發展起來的農民運動,隨著北伐戰爭的推進,在湖南、湖北、江西、河南、福建、陜西等省迅速發展,也是革命開始向農村轉移的重要體現,為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上述諸省農民武裝暴動的發生奠定了不可或缺的群眾性基礎。。
正是在陳獨秀等中共領導人探索的基礎上,中共在1926年7月第三次擴大執行委員會會議通過的中央政治報告中,對軍閥的“封建”屬性問題作出進一步解釋,指出“軍閥買辦官僚新舊士紳之反赤運動”,“這都是中國的半封建勢力,他們都公然站在帝國主義旗幟之下”,而“舊的士紳如城市及鄉村之劣紳地主土豪,專替軍閥官僚剝削農民,他們乃是中國半封建勢力之真正基礎”*《中國共產黨中央擴大執行委員會會議文件》(1926年7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2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第166—167頁。。1926年11月,中共在關于農民運動政綱草案中提出“推翻城市和鄉村中封建官僚(軍閥土豪)的政權”“在平民民主政權上統一全中國”*《中國共產黨關于農民政綱的草案》(1926年11月4日—5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2冊,第434頁。的運動目標。此處“軍閥”和“土豪”顯然是城市和鄉村兩個需要被推翻的封建目標。政綱草案指出:“中國共產黨現在已經應該指導這運動(指農民奪取政權的斗爭——引者注),提出建立鄉村農民政權之任務于農民協會——革命運動先鋒隊面前”,“只有依靠在鄉村的農民政權之上”,領導國民革命的政權“才能鞏固其地位”*《中國共產黨關于農民政綱的草案》(1926年11月4日—5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2冊,第436頁。。到1926年12月,中央特別會議的政治報告明確提出“推翻都市中封建的軍閥政權,推翻鄉村中封建的地主土豪劣紳政權”*《中央特別會議(文件)·政治報告》(1926年12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2冊,第565頁。這一國內政治斗爭的目標。而中央特別會議通過的《關于湘鄂贛三省農運議決案》則指出:“鄉村政權問題即是農民政權代替封建式的土豪劣紳政權問題”,“農協成為統一鄉村運動的唯一中心”,“鄉村中的武裝必須統一在農民手中”*《中央特別會議(文件)·關于湘鄂贛三省農運議決案》(1926年12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2冊,第578—579頁。。這些探索盡管還不免受分裂危機尚未充分暴露的國共合作框架的約束,尚難以完全從中共獨立革命的角度思考問題,理論的局限難以避免,理論的深度難以充分展示,但仍為國共合作破裂后中共轉入農村開展土地革命戰爭積累和準備了極為珍貴的理論資源。此時對“半封建勢力”的涵義及其社會基礎問題所做的事實和理論說明,尤其將“鄉村之劣紳地主土豪”作為封建軍閥社會統治的“真正基礎”,是對“封建”性質的新闡釋,預示了中共將開始進入鄉村的農民革命運動的新階段。至此,從中共二大到大革命失敗前夕,陳獨秀乃至整個中共黨人的“反封建”革命話語有了新的實質性的、標識著中國革命未來新方向的突破性發展,
顯然,以上這種理論發展不是陳獨秀一個人完成的,瞿秋白、毛澤東、彭湃等人在之后反對“封建”地主的問題上有了更新的真知和突破,超越了陳獨秀的認識水平,且后者的思想突破對于革命的發展更帶有根本性意義。不過,應該看到,正是陳獨秀在“封建”意涵、“反封建”話語建構和國民革命運動的農民問題上進行的長期理論探索,對于中共建黨前形成革新和革命思想,建黨后中共二大確定“軍閥”這一封建革命對象,中共三大后制定一系列關于農民運動的方針和政策,引導“新青年群體”反對上古時代“封建制度”的固化(“封建制度之遺”)和脫離現代社會生活的文化,以及建黨后引導全黨重視反“封建”軍閥到重視與農民對立的“封建”地主問題等一系列思想進展,無疑具有開拓和引領之功,其理論價值和歷史性貢獻是不容忽視的。
四、余 論
中共早期革命理論的發展與形成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和時代要求。如果脫離了理論產生的歷史背景和時代要求,很難理解理論形成的歷史真相,也很難理解理論的歷史價值及其現實意義。客觀、全面地探討和認識早期革命家群體關于“革新”、“革命”、反“封建文化”、反“封建軍閥”、反“封建地主”等層層遞進的理論探討和革命實踐,至今仍值得深思、明辨。從“五四”前后十余年間陳獨秀對“封建”意涵的探索和中共“反封建”話語的初步形成與發展的歷史脈絡中,筆者認為可得到以下幾個方面的歷史認識。
第一,從“封建”到“半封建”的思想認識,是陳獨秀等中共黨人長期探索的思想結晶。
中共關于“反封建”理論的建構,雖然早在《新青年》創刊之初就提出反對“封建制度”的口號,但嚴格來說,那時所說的“封建”尚不是現代漢語中的“封建”之意,而是指于今已不合時宜的上古的制度。隨著陳獨秀對中國道路的探索尤其是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理論的探索,把中國納入世界近現代資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歷史視野中,自然對西方革命歷史中與資產階級對立的“封建”問題有了越來越深的了解和把握。而近代中國革命——無論是辛亥革命還是“五四”以后開展的國民革命,都是與近代全球化后國際關系變動以及革命運動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中國的辛亥革命是與鴉片戰爭后中外關系尤其是中日甲午戰爭緊密相連的,甚至可以說是對這些沖擊的“反應”*這里是借用柯文的“沖擊”和“反應”兩對概念。這里的“反應”,不是柯文所指的對“沖擊”的被動“反應”,而是指中華民族在新到來的歷史遭遇下逐步主動性的自救與爭取民族復興的歷史活動。。而五四運動、中共成立及其后的國民革命運動,則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沖擊、巴黎和會對中國思想界的刺激、十月革命對中國的影響等因素密不可分。這表明,自鴉片戰爭到五四時期前夕,中國的思想與國際思潮的變動已處于波濤共流的狀態。在這樣的情況下,自新文化運動后,中國的話語體系越來越融入世界思想的河流之中。這樣,我們就很容易理解陳獨秀把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對立面的“封建”轉化為中國當時資產階級對立面的“封建”話語。而中國資產階級革命的對立面就是軍閥,因此,軍閥自然被定為“封建”性質,而謂之“封建軍閥”也就毫不奇怪。由于資產階級現代工業大生產的生產和經營模式,與之對立的農業經濟和小生產狀態成為“封建經濟”的標志性符號,因此中國古代小農經濟社會狀況也被作為“封建社會”的重要依據。事實也是,中國的“封建軍閥”不可能是天上掉下來的,更不可能是西周封建制度的產物,而只能是清末政治勢力的遺存。追根溯源,以皇帝制度和地主經濟制度為代表的中國古代社會,以全球化的話語邏輯理解,也只能是“封建社會”。因此,在陳獨秀的理解中,中國古代農業自然經濟及與之相適應的宗法社會是屬于封建時代的。
那么,民初的社會性質便成為陳獨秀等革命領袖和思想先驅要致力解決的緊迫重大課題。應該說,當時中國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社會狀況已是輿論的共識。而對內,既然“軍閥”屬于“封建”性質,那么中國社會是一種什么性質的呢?在最初的表述中,有時表述為“現代文明”社會,有時表述為“封建主義”社會。這種表述上的對立,看似矛盾實際上又是統一的:前者主要表述民主與共和的一面;后者主要表述“軍閥統治”或舊思想統治的一面,并逐漸把落后的農業經濟作為后者的一種基本標志。因此,“半封建”的說法由此而起。“半封建”應是“封建”一詞在表述民初中國社會出現困惑的情況下而使用的一個新概念,用來反映民初在政治上既不同于以往“封建帝制”,經濟上也不同于以往的小農業經濟,指政治上有新興資產階級民主力量的成長,經濟上有外國資本沖擊、本國資產階級經濟的發展而使原有小農經濟受到破壞的一種狀況。應該說,這種概念的使用比較符合民初政治經濟的歷史實際。除了用“封建”概念表述軍閥、用“半封建”表述當時的社會進程,使用其他的概念,都難以清晰地表述民初社會的歷史坐標。盡管這種概念是從西方革命話語體系中移植過來的,但在中國固有的話語里,沒有現代資產階級的概念,也就沒有與資產階級相對立的現代意義的“封建”概念;沒有現代社會主義概念,也就沒有與社會主義社會相對立的資本主義社會概念及封建社會概念。任何概念的提出絕不可能是憑空杜撰的,而是對社會現實中逐漸普遍化的一種新社會現象的本質性、符號化、為公眾所能接受的標志性表述,具有很強的客觀性。盡管“封建”“半封建”甚至“半殖民地”諸概念是經典作家如馬克思、列寧等曾先后使用過的,但從上文可以看出,陳獨秀等早期中共黨人使用這些概念,有一個逐步發展的過程,絕非生搬硬套,而是根據中國實際,將西方資產階級革命、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發展過程中的思想成果尤其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成果,逐步運用到中國的革命實踐中的,是革命實踐推動和思想家理論探索的結晶。當然,這種探索還是初步的,如盡管認識到中國社會已經處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狀態,但在中共黨內還未形成完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概念表述*盡管蔡和森于1926年在《中國共產黨史的發展(提綱)》中,就連用“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中國”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家”兩種提法,但黨內尚未形成穩定、通用的概念。參見《蔡和森文集》下冊,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795頁。,認識尚不穩定,甚至還有反復,但整體演進的方向是隨著革命的深入而前進的。
第二,從“封建軍閥”到“封建地主”、從“城市革命”到“農村革命”的初步提出,是革命實踐發展與思想飛躍互動而生的產物。
思想認識的飛躍與歷史發展的推動是互動的,思想指導和引領著時代潮流發展,實踐又推動著思想前行。隨著國共合作的推進、國民革命的深入和北伐戰爭的節節勝利,革命力量所觸及的深度從社會上層已經達到社會底部,中國革命的“偉大”潛力——農民的重要性,被陳獨秀、瞿秋白、毛澤東、彭湃、李大釗等革命家先后認識,中國革命的對象由“封建軍閥”逐步過渡到軍閥統治的基礎——“封建地主”的新階段。這是一個歷史性的轉折。中國歷史上的歷次革命,只是革上層統治者的命,只是改朝換代,從來沒有進行過徹底性、全面性的革命。因此,中國沒有發生質的變化。雖然中國的物質文明和思想文化在向前發展,中國幾千年的小農經濟依然存在,新的生產力(資本主義)沒有形成和發展到質變的空間,舊的制度經過修復式的改革后仍然有很強的生存能力。但是,鴉片戰爭后的近代中西接觸,西方大工業生產模式隨著西方列強的入侵而進入中國,使中國傳統的小農經濟模式失去了長期存在的合理性與可能性。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所遭受的列強的政治壓迫和經濟掠奪,迫使中國必須通過徹底的民族民主革命、從上層到底層的“翻天覆地”的革命巨變,才能求得民族獨立和國家統一。而對于這種變動,鄉村中具有政治權威和經濟實力的地主害怕社會變動損害自己的優勢地位,普遍是社會變革的反對者,是革命的對立面。如何認識地主勢力的性質,是不容回避的問題。在中國的傳統思想資源里,從來沒有這么巨大、深刻、普遍的社會變革,即使王朝末期的農民大起義,也沒有對地主勢力形成摧毀性打擊,地主勢力從來都是統治者治理社會的基本力量,因而不可能提供這方面的經驗與思想來源。故而,當時的革命者只能從世界革命的歷史中尋找理論資源。正如認識軍閥的“封建”屬性一樣,既然地主勢力是“封建”軍閥的擁護者,是軍閥統治的“真實基礎”,那么地主勢力或地主階級無疑也是“封建”性質的。因此,從“打倒封建軍閥”到“打倒封建地主”,可謂中國革命發展的必然邏輯和必經道路,而從“城市革命”轉向“鄉村革命”的認識路徑也初步地展現出來,為土地革命戰爭時期轉移到農村進行廣闊的革命斗爭提供了清晰而堅實的坐標性指向。
第三,如何認識“反封建”話語的內涵及其“概念”的使用問題。
近年來,由于反思近代以來的西方話語對中國本土文化的消解,學界對近代歷史上有關概念的使用開展了新的研究和重新評估。其中,“封建”或“反封建”是引起學界研究較多的概念之一,也出現了不同的認識。根據筆者的梳理和研究,“封建”“半封建”概念是當時陳獨秀等革命先驅和思想家從中國社會發展之歷史與國際革命演變之歷史交匯的角度,從中國革命的現實力量與敵對力量對比的具體實際出發,從革命理論指導革命實踐與革命實踐催生革命理論的互動中,從《新青年》1915年創刊起到大革命失敗前夕的1926年底止,進行了長達十余年的艱辛理論探索。他們的探索對于準確認識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的實際,探索中國革命前進和中華民族復興的道路,作出了重要的理論貢獻。正是在這種探索指導下,五四運動的爆發、中共的成立、國共合作領導的國民大革命的開展、北伐戰爭打倒北洋軍閥的勝利等重大歷史性轉折事件陸續登上近代中國的歷史舞臺,一改辛亥革命以后的軍閥紛爭、民主革命勢力頹廢的狀況,中國革命和中華民族復興呈現歷史性轉折的前景。這表明,包括“反封建”理論在內的中國革命理論符合中國的實際需要,經受住了這一時期的歷史考驗。如果我們運用現代政治理論框架分析,認為孫中山領導的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性質,那么他所對立的軍閥不是“封建”性質的又是什么呢?問題不在于“封建”的稱號,而在于“軍閥”所作所為的基本特征是不是人們所認為的“封建”。當時,軍閥是一種割據性力量,是一種專制勢力。根據當時的界定,割據性是屬于“封建”概念的一個義項,專制也屬于“封建”概念的一個義項。當然,今天有的學者認為西歐“封建”并無“專制”的內容。而揆諸史實,西歐的“封建”也不是一個固定的概念,也隨著歷史的發展發生了演變,前期有割據和分散的特點,后期有專制和集權的特點。因此,將軍閥定性為“封建”既符合事實又符合概念邏輯規范。當時,中共黨人認為軍閥是“封建”性的,孫中山也認為軍閥是“封建”性質的。孫中山曾指出:“中國少部分著名的封建督軍、破產的官僚、投機的政客此三種人形成中國之軍閥政客。”*孫中山:《關于建立反帝聯合戰線宣言》(1924年1月6日),《孫中山全集》第9卷,中華書局,2006年,第23頁。就是說,軍閥的封建性是那個時代的主流意見。事實上,“封建”只是一個語言符號,對其加以評判的主要標尺,是看這個符號所反映的事物是否符合事物的真實和本質*如馬克垚曾指出:“經過長期的研究,在前資本主義時代,大土地所有制和小生產的結合,是各國家、民族的共同經濟特征,應該是沒有問題的。無論你使用封建主義這一名詞與否,但在此共同性下,如何認識各地區、國家、民族的特殊性,并從而對全世界的這一社會有進一步的認識,仍然是一個重大的歷史研究課題。”〔法〕馬克·布洛赫著,張緒山譯:《封建社會》上卷,商務印書館,2004年,“中文序言”第11頁。。應該說,“封建”作為對“軍閥”真實和本質的規定符合歷史事實,是準確的。隨著對軍閥“封建”的定性,對軍閥統治基礎的“地主”之“封建”的定性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地主的“封建”性質一方面是根據作為軍閥的統治基礎而認定的,另一方面是根據其經營的以滿足個人消費為主的傳統農業經濟而認定的。當然,從經濟上看,中國的模式與歐洲的模式存在不同之處,歐洲有領主經濟*歐洲封建社會也并非都存在領主經濟,在某些國家如法國只存在封建社會早期,以后就被地主經濟所代替了。參見王淵明:《法國封建社會農民的生活狀況與社會發展的關系》,《歷史研究》1985年第5期。,而中國則是地主經濟。但無論是歐洲的領主經濟還是中國的地主經濟,如馬克垚所言,“在前資本主義時代”,各國家、各民族的共同經濟特征是“大土地所有制和小生產的結合”。既然主要經濟基礎是相同的,從社會發展的階段來看,或者無以名之,若名之,則以西歐的“封建社會”為參考,名之為“封建”當是適宜的選項。恩格斯指出了歐洲地主(領主經濟)與農民的關系:“在中世紀,封建剝削的根源不是由于人民被剝奪而離開了土地,相反地,是由于他們占有土地而離不開它。農民保有自己的土地,但是他們作為農奴或依附農被束縛在土地上,而且必須給地主服勞役或交納產品。”*恩格斯:《美國工人運動——〈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美國版序言》(1887年1月26日),《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20頁。中國的農民與歐洲的農奴雖有差異,但中國農民因為生活需要也只能被束縛在土地上,通過繳納賦稅或地租向國家或地主“進貢”。
應該說,近代以來,中國的話語系統已發生了很大變化,有些中文固有的本意在現代消失了,轉為引入的現代外來的新意。這是因為社會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語言系統也必須隨之發生相應變化,以反映新的事物或新的認識。這類現象并非“封建”一詞獨然,如中國古義的“經濟”,我們知道是“經世濟民”之意,而與今天指“物質財富”的內涵全然不同;又如“革命”一詞,古義是“根據天命變更而發生的改朝換代、王朝易姓現象”,與現代所指的社會根本變動、制度根本變革的內涵也有著巨大的性質差異,古代認為的改朝換代的“革命”在現代并不認為是“革命”,古代農民造反被稱為“賊寇”,現代則把農民造反名為“革命”;又如“黨”,在古義中指“鄉黨”、“親近”和“偏私”,在政治概念上原為帶有貶義性的詞,現代“黨”的含義與之相比也已發生了性質上的不同;還如“共和”一詞,中國原有的“共和”意涵是指君主世襲制下諸位攝政者代幼主共治之意,而現代的共和則指廢除君主世襲制后,國家權力機關由選舉產生并實行一定任期的政體,體現了人民的主權精神,與原有古義已有了性質上的根本區別。這種古今詞意的變化是歷史演變過程中常有的現象,尤其在近代以來中國進入全球化的國際關系中,文化交流、語言互鑒更是難以避免,是歷史進步、人類文化融合的現象。因此,以現代語義中的“封建”與中國古義的“封建”不符為由,認為不應使用這一概念,理由是不充分的;以中國的“封建”或“半封建”與歐洲不同或與其他國家不同為據,而認為不應使用這一概念或這一概念出了問題,其理由也是難以成立的。從“封建軍閥”到“封建地主”,是中共黨人在早期革命進程中根據波瀾壯闊的豐富革命實際和從歐洲與俄國取得的思想“火種”,“封建”“半封建”概念由此逐漸被廣泛采用,點點滴滴的思想力量匯成“反封建”革命的長河。它是在中國的土地上生長的,是富有中國特色的現代革命思想發展的重要成果。當然,由于它是在戎馬年代淬煉的,不免帶有那個時代的某些痕跡,如學理的論證尚不夠充分、細密、周嚴,陳獨秀等人不可能像皓首窮經的學者那樣為考一字而成鴻篇巨制,他們主要是把這些思想觀念作為革命的火種、斗爭的武器進行社會動員的,是行之有效、有生命力的基礎性思想元素,經受住了嚴峻的時代考驗和歷史驗證。
從《新青年》創刊到大革命失敗前夕的1926年底,以陳獨秀為代表的中共黨人對革命理論的探討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本文所探討的“反封建”思想認識的發展只是其一。這一時期革命領袖和思想先驅對中國革命的認識,為當時中國革命的發展和其后革命的進一步推進作出了不朽的歷史貢獻,在中國革命思想史上占有源頭性、經典性的地位,是中國革命史上極為珍貴的精神寶藏,值得我們認真研究和探索。但是,學界迄今對這一時期的革命理論研究仍嫌薄弱。人們多把研究的視角放到20世紀30年代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發展期和40年代的成熟期,這些研究當然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如果不對中共早期理論進行系統研究,就難以理清這些思想“何以如此”這樣一個“源頭”問題。“何以如此”正是中共早期革命實踐探索和革命理論探索的歷史進程,其在相當程度上影響甚至框定了中共1927年后所要走的道路及其最終的航向*關于“封建”問題的思想和理論探索,對之后民國的學術研究尤其是社會理論,也提供了形成理論輪廓的基本概念及其論說方式,影響到20世紀三四十年代學術界的某些基本術語和基本論證,遠遠超出了革命陣營的范圍,甚至成為當時學界和思想界占據主流的話語言說。。當然,后來的路更艱辛,好在從陳獨秀到瞿秋白到毛澤東,尤其是大革命失敗前夕中共黨人初步認識到由城市“反封建”軍閥到農村“反封建”地主革命的客觀新趨勢。因此,當國民黨“清共”“反共”之時,毛澤東把革命的星星之火帶到了廣闊的農村,帶領共產黨人走上農村武裝革命的道路。動員農民參加革命,武裝農民進行革命戰爭,教育和改造農民建設新社會、新中國。這個更廣大的“反封建”的歷史舞臺,在毛澤東的名篇《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于1927年3月發表幾十天以后血與火的國共分裂中徐徐展開。中國革命終于進入到了“反封建”的底層。此后,中國的新聞媒體、理論界、學術界乃至史學界也越來越關注底層尤其是下層人民的生活問題,發表了越來越多的經濟史、社會史的研究成果,隨著革命的深入,對中國底層人民尤其農村和農民問題的研究越來越多,越來越深入。這就是中共黨人早期“反封建”演變的歷史和邏輯以及對這一歷史和邏輯的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