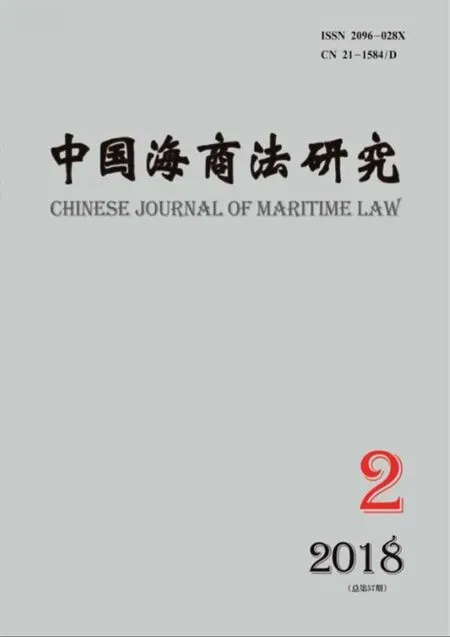提單并入條款的定性與準據法確定
——兼評《鹿特丹規則》第76條
張珠圍
隨著“一帶一路”建設的深入推進,涉“一帶一路”法律糾紛的解決以及良好法治環境的構建,已經成為參與主體的最大利益關切和需求。[1]貿易暢通是“一帶一路”建設的基本目標之一,國際海上貨物運輸合同糾紛的妥善審理是貿易暢通的基礎,也是海事審判服務保障“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切入點。在國際海上貨物運輸實踐中,國際大宗散雜貨貿易通常采用租船合同進行運輸并根據貿易條件簽發相應的租船格式提單。這種運輸方式涉及托運人、船東、承租人、提單持有人等不同國家地區的多方主體,且一個運輸航次可能涉及一系列的“背靠背”的租船合同。船東為了在這種復雜法律關系中較好地維護自己利益,通常要求承租人簽發的提單必須載有并入條款(incorporation clause),將租船合同并入到提單,使自己在面臨提單持有人索賠時也能適用租船合同中的條款約定。但是提單持有人并非與船東簽訂租船合同的當事方,船東能否以提單中的并入條款將租船合同的條款并入到提單進而約束提單持有人,一直是各國海商法領域爭議較大的議題。
一、問題的提出:審查提單并入租船合同法律適用問題
中國學界對提單并入租船合同的研究多集中于租船合同中的仲裁條款效力準據法、并入條件的域外法實踐介紹、仲裁條款效力等問題,[2]卻少有研究關注目前司法實踐所亟需的提單并入租船合同的準據法問題。
在陽光自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與重慶紅蜻蜓油脂有限責任公司海上貨物運輸合同糾紛案(2017鄂民轄終31號)中,[3]提單持有人紅蜻蜓油脂公司因貨損起訴承運人陽光控股公司要求賠償損失,陽光控股公司提出管轄權異議,認為涉案提單已經有效并入租船合同的仲裁條款。根據仲裁條款約定,提單貨物運輸合同下的所有糾紛都應提交倫敦仲裁。一審武漢海事法院認為提單雖載明“與租船合同合并使用”,但提單正面僅載明“運費根據租船合同支付”,并沒有關于并入提單的租船合同的具體記載,且租船合同中未載明船舶的名稱,無法證明該合同與本案運輸的關聯性,因此認定涉案提單并入的租船合同不明確,原、被告之間未有仲裁合意或者其他有關仲裁的約定,裁定駁回管轄權異議。
陽光控股公司提起上訴稱,一審法院適用的準據法錯誤,未先行明確其所應適用的準據法,更未依據應當使用的準據法對仲裁條款的效力進行討論或判定。涉案提單所并入的租船合同中約定有關爭議應當提交倫敦仲裁,應以英國法作為準據法審查涉案仲裁條款效力。根據英國法,涉案提單有效并入租船合同中的倫敦仲裁條款,本案糾紛應在倫敦通過仲裁解決。二審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認為,紅蜻蜓公司提交的民事起訴狀和初步證據顯示,涉案提單雖載明“與租船合同合并使用”,但并沒有關于并入提單的租船合同的具體記載,也沒有注明租約有仲裁條款并入提單,故不能認定陽光控股公司所主張的航次租船合同中的仲裁條款被并入了提單,駁回了陽光控股公司的上訴。
本案是較為典型的因提單并入仲裁條款而引起的管轄權異議案件,體現了并入條款效力問題通常與租船合同中的仲裁條款效力問題并存的特點。這類型案件通常是國內提單持有人因貨損貨差起訴國外承運人要求賠償損失,承運人出于各種原因通常會主張提單并入了租船合同中的仲裁條款。法院以管轄權異議程序審查此類案件,裁判結果通常是否定提單并入租船合同,進而否定仲裁條款約束提單持有人。但是該案例的獨特之處在于承運人對一審法院缺漏了關于法律適用方面的說理論證提出了質疑,認為法院在否定提單并入租船合同的說理認定之前應先行對準據法的確定進行論證說明,本案并入問題適用不同國家法律,得出的結論會存在沖突。筆者認為,這個上訴理由直指中國法院近年來審查提單并入租船合同案件在邏輯論證上的問題:缺乏對于法律選擇結果邏輯推理的說理與闡釋。裁判文書法律適用說理上的缺陷,直接影響了文書對合理性和公正性的宣示,也影響了其權威性。中國法律并未規定審查提單并入租船合同的準據法,理論界對此問題深入研究探討的不多,導致司法實踐對此問題采取忽視回避或模糊化處理的態度。
筆者認為,涉外民商事案件審判中,確定準據法是案件說理論證的起點,法院應先確定審查提單并入租船合同的準據法,再根據所應適用的準據法進行審查認定并入問題。有關提單并入租船合同的審查應適用的準據法的討論,應以這一問題所涉的概念和性質為始。在對相關概念進行定性識別之后,才能援用相應的沖突規范確定準據法。對有關的事實構成的性質做出定性或分類,并將其歸入特定的法律范疇,進而確定應該援用哪一個沖突規范的法律認識過程,理論上稱為識別或定性。[4]定性是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的起點,提單并入租船合同的識別將直接影響其所適用的準據法。提單并入租船合同的性質問題,理論分歧較大,司法實踐也不統一。
二、提單并入租船合同的定性
(一)提單是否并入租船合同的定性問題上存在的理論分歧
一是事實認定性質論,該觀點認為有關租船合同條款以什么樣的方式、是否在事實上被并入到提單,屬于事實認定的問題,應用法院地法來解決。[7]筆者認為該觀點過于片面,沒有認識到提單并入租船合同的問題的核心。提單條款是否有記載并入條款屬于事實認定問題,但是并入條款是否具有將租船合同的條款并入到提單中并進而約束提單持有人是屬于并入條款法律約束力的判斷,所以租船合同條款是否并入并不是純粹的事實判斷問題,而是涉及到提單中的并入條款的法律效力判斷問題。
二是程序性質論,該觀點認為“租船合同仲裁條款并入提單問題是涉及法院地國司法主權的程序性問題,應當適用法院地法”。[6]55筆者認為,雖然提單一旦并入租船合同可能具有排斥法院管轄權的程序效果,目前大部分租船提單格式均約定對仲裁較為寬松、支持的國家或地區如倫敦、紐約或香港作為仲裁地。如果租船合同條款包括仲裁條款被并入提單,根據沖突規范所指引的準據法審查仲裁條款效力時(一般為外國法或香港法)①《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仲裁法〉若干問題的解釋》(2008調整,簡稱《仲裁法解釋》)第16條規定:“對涉外仲裁協議的效力審查,適用當事人約定的法律;當事人沒有約定適用的法律但約定了仲裁地的,適用仲裁地法律;沒有約定適用的法律也沒有約定仲裁地或者仲裁地約定不明的,適用法院地法律。”目前國際通用的租船格式提單通常約定適用外國法及境外仲裁,因外國法對仲裁協議的有效性往往采取鼓勵、支持態度,對仲裁條款多解釋為有效。,就會得出租船合同的仲裁能約束提單持有人的結論,從這個意義上說,提單并入問題具有排斥法院管轄的效果。但是,這種觀點忽視了并入環節的并入條款效力判斷及租船合同中的仲裁條款效力判斷是相互獨立的問題,在邏輯上應先判斷并入條款是否能夠有效并入租船合同,再判斷租船合同中的仲裁條款對于提單持有人是否有拘束力,而不是直接忽略并入環節的判斷而用還未并入的租船合同中的條款來確定并入環節的準據法。
三是仲裁條款性質論,該觀點認為當并入條款涉及的是仲裁條款是否并入租約的問題時,確定仲裁條款并入提單的效力的準據法和確定一般仲裁條款效力的準據法沒有區別,應適用根據沖突規范指引確定的仲裁條款準據法。[7]筆者認為,此種觀點類似程序性質論,也是混淆了租船合同是否并入提單與租船合同中的仲裁條款是否有效力兩個問題,直接以仲裁條款效力的準據法來審查并入問題,該觀點存在邏輯缺陷。
綜上,筆者認為提單并入租船合同的問題兼具程序性與實體性的特點,在邏輯上應正確區分并入問題與租船合同條款效力問題的先后判斷順序。
(二)提單是否并入租船合同的定性問題上進行的實踐考察
當前中國法院審判實踐中,審查提單是否并入租船合同問題主要是以租船合同仲裁條款能否約束提單持有人的管轄權異議糾紛案件的形式體現。在仲裁條款效力審查報核制度下,中國關于提單并入租船合同的觀點也主要體現在最高人民法院歷年來關于提單并入租船合同仲裁條款效力請示的復函中。從這些復函可以看出司法實踐早期適用法院地法直接否定仲裁條款效力,否定其并入提單以及約束提單持有人。[6]53隨著對仲裁司法態度的轉變,特別是《仲裁法解釋》施行以來,法院一般不對仲裁條款本身的效力進行判斷,而在對仲裁條款能否并入提單問題的審查上設置諸多條件,在并入環節加以否定,從而否定仲裁條款約束力。[6]53如《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連云港祥順礦產資源有限公司與尤格蘭航運有限公司海上貨物運輸合同糾紛管轄權異議一案的請示的復函》②參見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四他字第1號。中認為,盡管提單背面約定了提單正面所示租船合同中的仲裁條款并入提單,但提單背面并入條款的約定不產生約束提單持有人的效力,該提單正面并未載明租船合同中的仲裁條款并入提單,不能產生租船合同仲裁條款并入提單、約束提單持有人的法律效果。[8]
司法審查模式由否定仲裁條款效力轉變為否定提單并入租船合同,體現了中國法院對仲裁條款認識的深入和對仲裁態度的轉變,但該模式也產生了如何確定審查提單是否并入的準據法這樣一個新問題。
天津海事法院受理的神華煤炭運銷公司訴馬瑞尼克船務公司確認之訴一案中,神華煤炭運銷公司主張與馬瑞尼克船務公司之間不存在仲裁協議,天津海事法院及天津市高級人民法院認為該案是確定仲裁協議是否有效并入提單,并非確定仲裁條款的效力,故不能適用《仲裁法解釋》第16條的規定。鑒于雙方未能就法律適用達成一致,而涉案運輸的起運港為中國天津,提單也是在天津簽發的,因此中國法律與本案具有最密切聯系,本案應適用中國法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神華煤炭運銷公司與馬瑞尼克船務公司確認之訴仲裁條款問題的請示的復函》③參見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四他字第4號。中認為,涉案提單為與租約合并使用的簡式提單,但提單正面并未明示記載將租約包括仲裁條款并入提單,故租約中的仲裁條款并未有效并入提單,本案并非對租約中仲裁條款效力的審查,天津市高級人民法院認為應當適用中國法律確認雙方當事人之間是否存在仲裁協議正確。[9]
在此案例中,最高人民法院的復函確立了兩個裁判規則:一是確定仲裁協議是否有效并入提單與確定仲裁條款的效力是兩個獨立的問題,不能適用《仲裁法解釋》第16條的規定來確定仲裁協議是否并入提單;二是涉案糾紛是貨物運輸合同糾紛,根據最密切聯系原則確定本案應適用中國法律,提單并入仲裁條款問題也應適用中國法律。一審天津海事法院及二審天津市高級人民法院均在適用中國法的前提下否定了提單并入了租船合同,但是說理論證卻較為模糊,沒有分析論證提單并入租船合同的法律性質及適用運輸合同的準據法判斷并入條款效力的依據。筆者認為,該案的缺陷在于沒有對租船合同是否并入問題進行準確定性,導致準據法確定進路分析論證不明確,削弱了案例指導參考效果,無法有效消弭提單并入租船合同的準據法之爭①在該復函發布之后,仍有多個案件涉及并入問題準據法,如(2015)鄂民四終字第00194號紅蜻蜓油脂公司與白長春花公司管轄權異議糾紛案、(2017)閩72民初21號福建元成豆業有限公司與佛羅萊爾船貿有限公司管轄權異議糾紛。。
(三)提單是否并入租船合同的定性問題上采取的比較法分析
英美法院認為提單是否并入租船合同是提單上的并入條款的效力問題,具體而言是指并入條款是否能夠并入租船合同條款及能在多大范圍內并入租船合同條款并進而約束提單持有人。[10]8關于并入條款效力問題的識別,英國法和美國法均認為并入條款的有效性及該條款可以并入的租約條款的范圍屬于合同條款的解釋范疇,是提單所證明的運輸合同項下的合同性爭議(contractual disputes)。[10]8德國法認為提單是無記名或指示證券,在承運人簽發提單并流轉至第三人的情況下,提單持有人與承運人之間的關系是一種證券關系。提單上記載的請求權是海上貨物運輸合同請求權。[11]提單持有人與承運人之間的無單放貨、貨損貨差等糾紛性質上屬于因無記名或指示證券流轉而產生的債務。英美法與德國法關于提單性質的規定不同,相應地對提單并入租船合同的定性也不相同。筆者認為,英美法將并入問題視為合同性的爭議,對其進行合同法上的考察,更多地體現對合同當事人意思自治的尊重。
中國法律規定及司法實踐與英美法較為相似,均將承運人與提單持有人之間的法律關系定性為提單運輸合同,但是法律并無對提單并入租船合同的性質的明文規定。考察最高人民法院歷年來關于提單并入租船合同仲裁條款的復函,也未發現關于提單并入租船合同問題的定性的說理論證。但是這些復函在審查并入問題時通常以提單正面未明示具體日期的租約并入,未載明仲裁條款并入提單或者提單持有人未明示接受等理由否定提單并入了租船合同,筆者認為這些理由體現了司法實踐中考察提單并入租船合同問題側重實體性問題的特點。中國法院對并入問題的考察主要是對當事人是否就并入問題達成合意進行合同法上的考察,這種審查角度側重關注并入問題對當事人實體權利義務的影響,與英美法定性的合同性爭議的立場較為契合。筆者認為,司法實踐中這種對并入條款進行分析說明,就提單是否并入租船合同達成合意進行分析判斷的做法應認定為是解釋合同內容的過程。[12]
三、并入條款的準據法確定進路域外法實踐考察
(一)合同解釋的法律適用
在將提單并入租船合同定性為并入條款的合同解釋之后,提單并入租船合同的準據法問題就是探討合同解釋的法律適用問題了。中國法律并無關于合同的解釋應適用的準據法的明確規定。
英國法認為合同的準據法適用于合同的解釋,根據英國所適用的《歐洲議會和歐洲聯盟理事會關于合同之債準據法的第593/2008(歐共體)規則》(簡稱《羅馬Ⅰ規則》)第12條規定,合同準據法的適用范圍包括合同的解釋、當事人的權利義務及合同的履行,因此,并入條款效力審查應適用提單運輸合同的準據法。[10]11美國法院認為提單并入租船合同問題是提單所證明的運輸合同項下的合同性爭議(contractual disputes),根據美國《第二次沖突法重述》第186條、第187條規定,與合同相關的爭議應適用合同的準據法。[10]11德國法確定提單的準據法方式較為復雜,提單持有人與承運人之間的糾紛通常被識別為“因提單流通轉讓性而生之義務”,德國聯邦法院及學者通說認為依《德國民法施行法》第37條第1項第1款規定(現為《羅馬Ⅰ規則》第1條D款所替代)排除了合同之債的沖突規范適用于“因提單流通轉讓性而生之義務”,因此收貨人基于提單的債權請求權、物權請求權等法律關系應適用德國長久以來的習慣法“目的港法律”作為準據法。[13]
關于合同準據法的適用范圍,中國學者認為合同準據法適用于合同的實質有效性以及因合同而發生的權利義務關系。[14]筆者認為,合同的解釋針對的是合同的內容,與合同的實體權利義務確定密切相關,所以合同的解釋屬于合同準據法適用范圍。并入條款是提單所證明的海上貨物運輸合同的合同條款之一,對該條款的法律效力的審查屬于合同解釋的范疇,應適用提單運輸合同的準據法。
(二)提單運輸合同準據法的確定
如果提單上有明確的關于法律選擇的條款,英美法均以尊重當事人意思自治的方式確定合同準據法,但是大部分的租船提單為簡式提單,僅在提單上載明“與租船合同合并使用”“租船合同的所有條款、條件、權利和例外規定,包括法律適用條款和仲裁條款并入本提單”,提單上并無關于權利義務的具體約定。此種情況下,英國和美國法院采用了不同的方法確定提單運輸合同準據法。
關于提單運輸合同的準據法確定進路,英國法院判例上采用的是推定存在的合同準據法(putative proper law)的方法,根據英國實施的《羅馬Ⅰ規則》第10條第1款的規定,合同或合同條款的存在和有效性,適用假設該合同或合同條款有效的情形下依本規則所會適用的法律體系。即根據推定存在的準據法,如果合同有效地成立,這個推定的準據法將成為合同準據法的法律。當提單載明的條款沒有約定準據法,而僅是并入條款載明租船合同并入提單時,英國法院也是采用“推定存在的合同準據法”的方式來確定準據法。這種方式先推定租船合同并入提單,再根據租船合同的準據法判斷租船合同能否并入該提單。[10]11
英國判例實踐中,有觀點對這種推定存在的合同準據法是否適用于提單并入租船合同的情形提出了質疑,該觀點援引《羅馬Ⅰ規則》第10條第2款的規定,認為提單持有人幾乎沒有機會或權利能看到租船合同中的法律選擇條款,在此情況下無法推定提單持有人與承運人之間存在明示或推定的法律選擇合意①根據《羅馬Ⅰ規則》第10條第2款的規定,當假定存在合同準據法適用于合同的成立是不合理的,且合同相對方關于合同或合同條款沒有達成合意時,假定存在合同準據法不能適用。。英國法院在The Epsilon Rosa案中否定了這種觀點,該案中Steel法官認為雖然提單持有人沒有機會看到租船合同,但是鑒于仲裁條款在租船合同中廣泛使用,本案適用租船合同的準據法是合理的②參見 The Epsilon Rosa,[2002]2 Lloyd’s Rep 701。。
與英國法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美國法院在審查并入條款效力問題時是先確定提單運輸合同應適用的準據法,再根據運輸合同的準據法判斷租船合同是否被并入。在 Trans-Tec Asia v.M/V Harmony Container案中,法院在審查供油合同是否并入了選擇美國法作為準據法的法律選擇協議的問題時,認為應先行判斷協議是否被并入,該案法官認為如果將協議選擇的美國法適用于判斷并入問題是倒因為果,應在不考慮待并入的法律選擇協議的前提下,先判斷供油合同本身的準據法,再據此準據法判斷合同是否能并入法律選擇協議。所以,在這個案件中法院先根據最密切聯系原則確定了供油協議的準據法為馬來西亞法律,再根據馬來西亞法判斷并入問題③參見 Trans-Tec Asia Harmony Container,583 F 3d 1120(9th Cir 2008)。。[15]
比較上述兩個國家確定并入問題的準據法的進路,可以看出美國法院的法律適用方法更有利于保護提單持有人。筆者認為,中國法院在確定存在并入條款的提單運輸合同的準據法上可以參考美國法院的做法,因為提單持有人很少有機會能看到租船合同中的條款,美國法所采用的方式使提單持有人能夠合理地推斷可適用于提單運輸合同糾紛的準據法,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平衡收貨人和承運人利益保護問題。這種準據法確定進路也更符合“提單中心”的理念,即并入問題的審查應從提單條款出發并回歸于提單條款。[10]11這種以提單為中心的法律適用方法能合理平衡對收貨人和承運人利益保護問題,有效保障提單流通性,夯實國際海上貨物運輸合同的制度基礎。
確定審查提單是否并入租船合同僅是提單并入租船合同案件的中的第一步,根據所應適用的準據法關于并入的形式要件和實質要件的規定審查是否并入還涉及到更為復雜問題:如在提單涉及到多份待并入租船合同情況下如何確定所應并入的合同、租船合同并入情況下承運人的識別、租船合同中措辭(如承租人、出租人)如何與提單運輸合同中的措辭(如提單持有人、承運人)進行協調等。雖然中國司法實踐多在并入環節直接否定了租船合同仲裁條款對提單持有人的效力,但是在并入租船合同其他內容的情形下,法院判例出現了新的動向。在2017年底做出的“山東翔龍實業集團有限公司訴被申請人北方航運有限公司、金源海運有限公司海上貨物運輸合同糾紛”的再審裁定書中,[16]最高人民法院在一系列的事實認定分析的基礎上認為,提單持有人知道也應當知道提單并入的租船合同運費條款,提單持有人接受提單時應當受提單并入該租船合同運費條款的約束。但是在解釋租船合同條款對提單持有人的拘束力的時候,最高人民法院采用了嚴格的語義解釋:盡管提單并入租船合同的運費條款,但在該租船合同下負有支付運費義務的是承租人,該條款并入提單后,該條款的文義并不因并入而改變,該運費條款約定支付運費的義務人也并不由此變更為提單持有人。此案中,在一定條件下允許租船合同并入提單的立場是僅針對個案做出的認定,還是代表法院對并入問題新的認識還有待實踐的進一步檢驗,但是類似案件的審判經驗的積累對中國構建和完善提單并入租船合同的裁判規則是很具有參考意義的。
四、《鹿特丹規則》關于提單并入租船合同仲裁條款的規定
《鹿特丹規則》沒有對提單并入租船合同的條件做出具體規定,而是將該問題的判斷留給各國國內法規定。但是公約在第76條①《鹿特丹規則》第76條規定:“1.非班輪運輸的運輸合同由于下列原因而適用本公約或本公約規定的,本公約的規定概不影響該運輸合同中仲裁協議的可執行性:(a)適用第7條;或者(b)各方當事人自愿在本來不受本公約管轄的運輸合同中納入本公約。2.雖有本條第1款規定,運輸單證或電子運輸記錄由于適用第7條而適用本公約的,其中的仲裁協議仍受本章的管轄,除非此種運輸單證或電子運輸記錄:(a)載明了因適用第6條而被排除在本公約適用范圍之外的租船合同或其他合同的各方當事人和日期;并且(b)以具體提及方式納入了租船合同或其他合同中載有仲裁協議規定的條款。”第2款規定了租船合同中的仲裁條款對提單持有人約束力及仲裁地的問題。仲裁地的規定是《鹿特丹規則》為防止仲裁成為承運人規避公約“訴訟管轄權”規定的創舉,公約規定在提單持有人起訴承運人的情況下,索賠方除可以在協議所約定地點提起仲裁外,還可以在下列任一地點所在國家提起仲裁:承運人的住所地、運輸合同約定的收貨地、運輸合同約定的交貨地、貨物的最初裝船港或者貨物的最終卸船港,學者稱為“法定仲裁地”。[17]在提單并入租船合同仲裁條款的情形下,提單持有人是否仍可以選擇“法定仲裁地”而不是仲裁條款所約定的仲裁地進行仲裁的問題,公約第76條分別規定了兩種情況下租船提單項下的提單持有人與承運人之間的仲裁地受公約限制的不同情形。在雙方是根據明確記載于提單上的仲裁條款進行仲裁的情況下,仲裁地受公約第十五章規定的“法定仲裁地”限制,即提單持有人可以選擇在提單約定的仲裁地仲裁或選擇“法定仲裁地”;在提單是以載明租船合同各方當事人和日期及以具體提及的方式納入租船合同中的仲裁協議的條款的情形下,雙方之間的仲裁地不受“法定仲裁地”限制,應執行租船合同關于仲裁地的約定。
提單并入租船合同仲裁條款問題是《鹿特丹規則》制定過程中各國代表爭議較大的議題,一類代表團主張盡最大限度在公約中適用仲裁自由的原則,另一類代表團認為,盡管當事人可以利用仲裁,但不應將其用于規避公約所列的管轄地。《鹿特丹規則》最終選擇了較為折衷的方案:對于不經常使用仲裁的班輪運輸提供了有限的仲裁,而對主要是以仲裁作為糾紛解決辦法的非班輪運輸業則允許有廣泛的仲裁自由②參見聯合國貿易法律委員會第三工作組提供的第十六屆會議文件《A/CN.9/591——第三工作組(運輸法)第十六屆會議工作報告》,評述意見第96條。。[18]《鹿特丹規則》最終采用的條款是通過區分仲裁條款是直接記載于提單及還是通過并入條款并入的方式,取得在保護提單持有人及仲裁自由上的平衡。筆者認為,對比當前國際通行的租船合同格式提單,可以看出格式提單上的并入條款措辭與《鹿特丹規則》規定的兩項要求的匹配度是較高的,所以在提單并入租船合同的情況下,采用國際通用的格式提單的租船合同中約定的仲裁地具有排他性。
五、結語
涉外民事案件的管轄權和準據法確定規則有三重價值目標:維護國家主權、保護當事人利益、促進和保障國際交往。在中國以往的涉外司法實踐中,存在單純強調維護國家司法主權,對方便當事人訴訟、防范平行訴訟等因素考慮不足的問題,沒有充分意識到一國根據國家利益自愿決定是否限制行使主權,并不是對主權的弱化,而正是行使主權的方式。[19]司法實踐應當確立盡量減少涉外司法管轄權的國際沖突、妥善解決國際間平行訴訟的新型司法理念,[20]注重處理好當事人意思自治和司法主權的關系,尊重有效仲裁協議排除法院管轄原則。并入條款是提單所證明的海上貨物運輸合同的合同條款之一,對該條款的法律效力的審查屬于合同解釋的范疇,應尊重當事人協議選擇適用法律的權利,適用提單運輸合同的準據法判定提單是否并入租船合同,增強此類案件審判中法律適用的統一性、穩定性和可預見性。在提單并入租船合同的案件審理中,找到正確的準據法僅是完成了法律適用的內部證成,同樣的《鹿特丹規則》規定的仲裁制度與中國既有的海事仲裁制度的沖突協調也僅是中國是否該加入該公約的內部證成因素之一,這兩個議題均需要通過進一步衡量法律適用是否與國家的政治經濟大環境相符、法律適用和判決結果是否一致、是否有利于判決的承認與執行、是否符合本國利益等價值選擇予以外部證成。[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