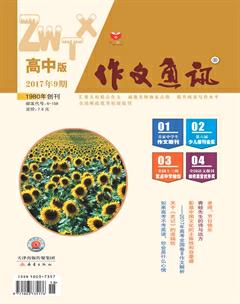木魚餛飩
盧子越
木魚餛飩的聲音整整陪了我十年,但很慚愧,因為種種原因,我從未近距離地見過這位不離不棄的老朋友。它永遠都出現在現實與夢境的交匯點上,“嗒嗒嗒”地響在真實的夜里,亦響在我每晚的夢里。
夢里,我為它配上了圖像。
我站在窗口大喊:“停一下,停一下!”隨后,我拼盡全力跑向它,生怕它等不及就走了。待我跑到它跟前時,鍋里的水已經“咕嚕咕嚕”地沸騰了。微弱的燈光下,老爺爺小心翼翼地將白中透粉的餛飩丟到沸水中,然后蓋上那已被水蒸氣熏成深褐色的木蓋。
其間,我仔細觀察了老爺爺的餛飩擔,基本都是木質的,與餛飩的素凈極為相配。幾分鐘后,老爺爺純熟地把餛飩盛到紙碗里,又撒上點兒榨菜和蔥白作為點綴。至此,一碗餛飩新鮮出爐,而老爺爺又“嗒嗒嗒”地離開了。
這樣的夢出現過很多次,多到仿佛我真的經歷過,多到我真的想要去經歷一次。我不止一次地央求母親讓我晚半個小時睡覺,可左等右等它就是不來。于是和往常一樣,我又只能在夢里吃餛飩了。
這樣的日子不長不短,一共十年。小學四年級的時候,我家從平房林立、街道縱橫的老城區搬到了新城區,新家的周圍樓房很少,出門就是一條國道。夢里再也沒有木魚餛飩的聲音,取而代之的是狂風的哭號和汽車的呼嘯,偶爾響起的喇叭聲會猛地將我驚醒。有時我甚至想回原來那個家,那個房間狹小、樓房密集的地方。那兒的夜再靜再黑,也有柔軟的木魚聲,還伴著餛飩淡淡的香味。那是老城區特有的,氤氳在每一寸土地、每一方空氣中的時光的味道。
又過了兩年,我開始了中學的寄宿生活,兒時魂牽夢縈的木魚餛飩也徹徹底底地消失在了夢里。記得一次語義考試,題目給出了一篇林清玄的散文,要求根據內容為文章擬一個標題:“那木魚敲得十分沉重著力,從滿天的雨絲里穿揚開來,它敲敲停停,忽遠忽近,完全不像是寺廟里讀經時急落的木魚。我追蹤著聲音的軌跡,匆匆地穿過巷子,遠遠的,看到一個披著寬大布衣、戴著氈帽的小老頭兒,他推著一輛老舊的攤車,正搖搖擺擺地從巷子那一頭走來。”
木魚餛飩!就是木魚餛飩!從那之后,我又開始整日整夜地想著木魚餛飩。那次一放假我就住到了老城區的表妹家,按理說我應該感到十分親切,但卻看哪兒都不順眼:道路一點兒也不平整,路邊還亂七八糟地放著自行車和電動車,地上的積水東一攤西一攤,遠不如新家的路好走,而且還沒電梯。
那天晚上,我邊看著最愛的綜藝節目,邊等著木魚餛飩的聲音響起。
“嗒嗒嗒……”十點多的時候,木魚的聲音準時響起,而此時綜藝節目也到了最精彩的部分,讓人移不開眼睛。“嗒嗒嗒……”就在我猶豫不決之際,木魚餛飩的聲音變得越來越輕。我趕忙跑到窗邊試圖大喊“停一下”,但這三個字硬是被卡在了喉嚨里,我只能看著它漸行漸遠,就像好不容易抓到一條大魚卻愣是讓它逃走了。我覺得自己好丟臉,已經沒有了兒時想做就做的勇氣。可如果我知道這將是我和它的訣別,一定會不顧一切地追出去。
最近,街上突然出現了很多名為“高陽餛飩擔”的店鋪,里面的店員都是操著方言的阿公阿婆。一問才知道它本是晚上穿梭在老城區的餛飩擔,但這幾年高樓大廈越來越多,人們似乎更喜歡在店里享受美食,他們的生意也日漸蕭條。無奈之下,擔主們只能湊在一起開起了餛飩店。
坐在裝潢華麗的店里,眼前的那碗餛飩和夢里的很像,卻又不像,而它終究不是!我的木魚餛飩,早已被封在了童年的夢里,被錯過在了少年的猶豫里,被湮沒在了撲面而來的現代文明里。
佳作點評
回憶舊時光的習作讀過很多,無不令人心里一暖,卻難以點下重重一筆。而這篇《木魚餛飩》不太一樣,它是少女對童年的感懷,是大孩子對自己束手束腳的后悔,更是一位中學生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深深擔憂。最后的擔憂無疑是本文的與眾不同之處,讓一篇單純的回憶文變得更有深度與厚重感,不再是一個人回憶,而是一群人的感傷。
(吳敏)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