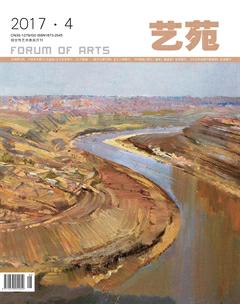《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中的暴力鏡像探究
祁靈怡
【摘要】 臺(tái)灣導(dǎo)演楊德昌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將一樁三十年前的少年殺人案件搬上銀幕,用近四個(gè)小時(shí)的時(shí)長(zhǎng)為觀眾講述了一個(gè)青春殘酷寓言,希望通過(guò)那個(gè)年代的線索讓時(shí)人看清當(dāng)時(shí)的時(shí)代。以往對(duì)于這部影片的解讀大多集中在敘事方面,本文希望打破這一多角度的分析模式,集中于主人公小四的自我構(gòu)建過(guò)程,運(yùn)用鏡像階段理論將人物關(guān)系簡(jiǎn)化為一個(gè)主要人物和多個(gè)鏡像的敘事模式,從而更有重點(diǎn)地解析以小四為代表的外省二代少年在暴力語(yǔ)境下的心理圖式。
【關(guān)鍵詞】 《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暴力鏡像;探究
[中圖分類號(hào)]J90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20世紀(jì)90年代的臺(tái)灣正處于一池“身份認(rèn)同”的渾水前:1987年全面解嚴(yán)后一時(shí)甚囂塵上的民族主義將臺(tái)灣的民族身份問(wèn)題變得白熱化,政經(jīng)各界傳統(tǒng)掌權(quán)者與在野勢(shì)力互相較勁,社會(huì)各界的化學(xué)反應(yīng)都指向一次權(quán)力的重新洗牌。在這樣復(fù)雜詭辯的亂象前,臺(tái)灣外省籍導(dǎo)演楊德昌將一樁三十年前的少年殺人案件搬上銀幕,用近四個(gè)小時(shí)的時(shí)長(zhǎng)為當(dāng)代觀眾講述了一個(gè)青春殘酷寓言,希望通過(guò)那個(gè)年代的線索讓時(shí)人看清當(dāng)前的時(shí)代。以往對(duì)于《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以下簡(jiǎn)稱《牯嶺街》)的解讀大多集中在敘事方面,而其人物形象的龐雜為此類分析增加了不小的難度。本文希望打破這一多角度的分析模式,集中于主人公小四的自我構(gòu)建過(guò)程,運(yùn)用鏡像階段理論將人物關(guān)系簡(jiǎn)化為一個(gè)主要人物和多個(gè)鏡像的敘事模式,從而更有重點(diǎn)地解析以小四為代表的外省二代少年在暴力語(yǔ)境下的心理圖式。
影片《牯嶺街》的開場(chǎng)是一個(gè)極具視覺隱喻性的畫面:在一片黑暗中,一只懸在畫面中央的燈泡被從左下方伸出的手開啟,散發(fā)出昏黃的微光并隨著拉力在空中悠悠晃動(dòng)。隨后,一片鮮紅從背景的紅磚墻中倏然洇出,直至將這個(gè)燈泡的昏暗光芒徹底淹沒浸透。觀眾不難把這個(gè)意象與飄搖處境中的外省兩代人聯(lián)系起來(lái),而當(dāng)小四在教務(wù)處用球棒打碎懸在正中的燈泡時(shí),也可以解讀為他主動(dòng)使用暴力反抗了以校長(zhǎng)為代表的父權(quán)壓制,同時(shí)也強(qiáng)硬地否決了同齡一代人的孱弱寫照。而隨之而來(lái)的,即是子一代的身份認(rèn)同迷思。
在自我構(gòu)建方面,拉康的鏡像階段理論提供了一個(gè)相當(dāng)具有寓意的模型,它描述了處于嬰兒階段的孩子通過(guò)辨識(shí)出鏡子中自己的影像而將自我認(rèn)作他者,并在進(jìn)一步的認(rèn)識(shí)中再重新將他者指認(rèn)為自我的過(guò)程。[1]90值得注意的是,他者的目光即是鏡像。這是一個(gè)象征性模式,主體的首要任務(wù)是在虛構(gòu)的基礎(chǔ)上通過(guò)他者的關(guān)照形成一個(gè)客觀化的“理想我”,然后通過(guò)反思發(fā)現(xiàn)自我在象征性的世界秩序中的位置,用語(yǔ)言重建起在普遍性中的主體功能。戴錦華為這一模型做出了非常形象的比喻:她將弗洛伊德的成長(zhǎng)論述比作一個(gè)有三到四個(gè)角色的多幕劇,而與此相參照,拉康的論述只提供了一部漫長(zhǎng)的獨(dú)幕劇,其中只有一個(gè)人物和一個(gè)道具:主體和鏡子。[2]154全部的劇情就發(fā)生在一人一鏡之間。“在這個(gè)模式中,我突進(jìn)成一種首要的形式。以后,在與他人的認(rèn)同過(guò)程的辯證關(guān)系中,我才客觀化;以后,語(yǔ)言才給我重建起在普遍性中的主體功能。”[1]90小四即是《牯嶺街》中所致力構(gòu)筑的主體,他以純凈無(wú)雜質(zhì)的狀態(tài)進(jìn)入敘事中,如同一個(gè)尚未具有自我意識(shí)的嬰孩,而通過(guò)凝視電影中的他者所反射出的鏡像,小四逐漸將自身從邊界曖昧、缺乏完整性的狀態(tài)中抽離出來(lái),獲得了虛構(gòu)的“理想完形”。《牯嶺街》可以被看作是一個(gè)人(小四)與數(shù)個(gè)鏡像的故事,而從主體與他者的目光互動(dòng)中,我們將注意到暴力在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在此,本文將挑選對(duì)小四的主體構(gòu)建影響最為深遠(yuǎn)的三個(gè)鏡像——父親、Honey和日本女人進(jìn)行簡(jiǎn)要分析。
一、第一個(gè)鏡像:父親
張父最初以一個(gè)壓抑的背面鏡頭出場(chǎng)。在這個(gè)大全景鏡頭中,畫面被分割為室外的墻壁與辦公室兩個(gè)空間,焦點(diǎn)落在左側(cè)的墻壁花紋上。張父微微前傾著坐在景深處的藤椅上試圖為兒子爭(zhēng)取一次到日間部的入學(xué)機(jī)會(huì),對(duì)面相當(dāng)官腔的女聲則被墻壁所遮擋,只露出一只在辦公桌下不耐煩上下打拍的腳。辦公室回聲所形成的自然音效與頂端風(fēng)扇的混響使張父的聲音聽起來(lái)更為空洞乏力,隨后一位女學(xué)生小心翼翼端來(lái)的熱水更是加劇了氛圍的尷尬與悶乏。這個(gè)開場(chǎng)鏡頭非常隱澀而細(xì)膩地將張父的困頓處境呈現(xiàn)出來(lái),而這也不會(huì)是張父唯一一次如此低聲下氣地與校方打交道。鏡頭隨后切換到坐在門口長(zhǎng)椅上的小四,于是開場(chǎng)的鏡頭構(gòu)圖得到了解釋:方才的畫面正是小四觀察父親的主觀視角。兩個(gè)鏡頭空間之間所呈現(xiàn)出的疏離感表現(xiàn)出父子之間微妙的距離張力,而隨之而來(lái)的下一個(gè)長(zhǎng)鏡頭則加深了這種觀感:張家父子從毫無(wú)視覺焦點(diǎn)的街道盡頭一前一后騎車前來(lái),二人姿態(tài)形似速度一致,卻始終保持著夏日午后所特有的充溢著蟬噪聲的沉默。
對(duì)于處于前語(yǔ)言階段的青少年來(lái)說(shuō)(此處的語(yǔ)言意指父系社會(huì)中的話語(yǔ)秩序),父親的形象一方面占據(jù)了他們所能接觸的有限鏡像,同時(shí)其在象征世界的地位又使得他充滿了模仿吸引力。和父親在一起時(shí)的小四通常是沉默寡言而馴服的,他尚未獲得語(yǔ)言的權(quán)力,只停留在影像的模仿層面上。他們是父系社會(huì)中相當(dāng)常見的父子,交流有限,卻也保持著適當(dāng)?shù)南胂缶嚯x,并將最終合二為一。在小四第一次因滑頭舞弊而受處分時(shí),張父對(duì)校長(zhǎng)進(jìn)行了嚴(yán)詞抗?fàn)帲瑘?jiān)持維護(hù)小四的無(wú)辜與正義。其時(shí)他所持有的是社會(huì)責(zé)任與正義感,而在隨后的推車同行中,張父向小四重申了他的價(jià)值觀:“讀那么多書,就是要在其中找出一個(gè)以后做人做事的道理,如果到頭來(lái)還不能很勇敢地相信它的話,那做人還有什么意思啊。”在這里,張父用父親的話語(yǔ)將讀書與做人聯(lián)系起來(lái),向小四做出只要認(rèn)真讀書,好好做人就能在未來(lái)取得社會(huì)地位的承諾。此時(shí)的二人顯得如難兄難弟一般,在形象上幾乎是同步的,小四也對(duì)父親的鏡像產(chǎn)生了象征性認(rèn)同,接受了進(jìn)入以教育制度為標(biāo)志的象征秩序所需要承受的犧牲,即接受符號(hào)“父親”對(duì)他的閹割。也是在這里,小四逐漸將父親所反射出的欲望內(nèi)化為他的理想,即公正地獲取社會(huì)身份。但小四對(duì)父親的認(rèn)同被一個(gè)突發(fā)事件所打斷,這也導(dǎo)致小四最終沒有成為父親的復(fù)刻。這一事件發(fā)生在片中暴力集中涌現(xiàn)的臺(tái)風(fēng)夜:在小四參與血洗217的襲擊活動(dòng)時(shí),張父被警備總部帶走問(wèn)話。endprint
臺(tái)灣白色恐怖時(shí)期長(zhǎng)達(dá)38年,在這期間,幾乎每家每戶都有親人被帶走問(wèn)話的經(jīng)歷,而他們往往在事后都選擇閉口不提。這一記憶禁區(qū)在《牯嶺街》中得到了想象性書寫。警備總部是一個(gè)與牯嶺街完全不同的密閉空間,如果說(shuō)牯嶺街是一個(gè)尚處于合法威權(quán)話語(yǔ)控制下的理性社會(huì),那么警備總部就是一個(gè)威權(quán)政治的暴力集中營(yíng),張父所賴以生存的政治體制將其陰暗面徹底揮發(fā)出來(lái)。影片通過(guò)晃動(dòng)的燈泡、融化的冰塊和充滿禁錮性的框架結(jié)構(gòu),再現(xiàn)了這個(gè)完全為暴力操控的法外空間。道德的界限在此處發(fā)生撕裂,張父以往所參照的國(guó)家鏡像開始為其內(nèi)部的暴力掙裂。在長(zhǎng)時(shí)間的羈押審問(wèn)之后,張父再次以背對(duì)鏡頭的形象出現(xiàn)。他獨(dú)自坐在空曠的房間里,埋頭奮筆交代出所有的秘密,鏡頭由大全景向前快速推動(dòng)變?yōu)橹芯埃缤洗蟾绲目植琅R至。此時(shí)的張父已然如傀儡一般任人擺布,隨著那一聲不耐煩的“好了好了,你可以走了”,張父突然停筆,轉(zhuǎn)身望向大門。鏡頭迅速切換至最初的大全景,只剩下他一人在椅子上不安地左右張望,無(wú)比空闊的審問(wèn)室以蒙灰的透明光感使他處于噩夢(mèng)般的孤零處境,而下一個(gè)對(duì)切鏡頭中,只有一扇打開的門和門外飄落的樹葉,聲音的發(fā)出者卻如同鬼魅一般全無(wú)蹤影。這超現(xiàn)實(shí)的一幕表現(xiàn)出政治權(quán)力最為暴力的一面,即它事實(shí)上是處于權(quán)力語(yǔ)境下的主體的誤認(rèn),是張父的自我想象,但當(dāng)這一鏡像缺失了他者的實(shí)像時(shí),虛無(wú)的恐怖就會(huì)將個(gè)人包裹其中。當(dāng)張父為了維持鏡像中的自我而選擇接受國(guó)家機(jī)器的暴力邏輯,一一交代出自己與他人的秘密時(shí),他本身也已偏離了自我的軌道,于是隨之被剔除出了原先鏡像中的權(quán)力話語(yǔ)秩序。至此,張父所一直誤認(rèn)的理想國(guó)家鏡像成為空無(wú)一片,這是張父的“失父”,也是小四的失父。他無(wú)法再為小四做出任何有關(guān)未來(lái)的承諾了。
影片的開頭曾出現(xiàn)過(guò)這樣的字幕:
民國(guó)三十八年,數(shù)百萬(wàn)的中國(guó)人隨著國(guó)民政府遷居臺(tái)灣。絕大多數(shù)的這些人,只是為了一份安定的工作,為了下一代的一個(gè)安定成長(zhǎng)環(huán)境。然而,在下一代成長(zhǎng)的過(guò)程里,卻發(fā)現(xiàn)父母正生活在對(duì)前途未知與惶恐之中。這些少年,在這種不安的氣氛里,往往以組織幫派,來(lái)壯大自己幼小薄弱的生存意志。
張父因國(guó)家的暴力邏輯而走向衰落,而小四也無(wú)法再?gòu)倪@個(gè)鏡像中得到任何反饋。父親的鏡子被擊碎,變成了一攤碎片。在第二次談話,也就是小四用球棒打碎自己的命運(yùn)寫照后,他利用昔日父親殘留在自己身上的鏡像反射,發(fā)出帶有父權(quán)意味的話語(yǔ):“我一定幫你考上日間部。”小四試圖扮演一位不在場(chǎng)的父親,而當(dāng)他提及張父的舊時(shí)言論時(shí),其實(shí)是在再度提醒父親主體鏡像缺失的恐懼與迷茫。所以張父用取煙的行動(dòng)打斷了小四,轉(zhuǎn)而沉思道:“我如果戒煙,那每個(gè)月省下來(lái)的錢就可以貸款給你買一副眼鏡了。”父親選擇逃避鏡像的碎片,而這一行為同時(shí)也是在暗示小四,他需要看清世界的真相,盡管后者需要的遠(yuǎn)不止是一副眼鏡。
對(duì)于真正的無(wú)神論者來(lái)說(shuō),不是父親死了,這里的“父親”其實(shí)是潛意識(shí)的。雖然我們看到父親的鏡像碎裂了,但其造成的創(chuàng)傷扎在小四的血肉里。當(dāng)小四把刀捅向小明時(shí),他口中所喊的“你不要臉!沒有出息!”正是張父在以為二哥偷了手表而鞭打他時(shí)的憤怒呼號(hào)。這是碎裂父像的最后話語(yǔ)和最后反抗,而符號(hào)“父親”留在其子的記憶中的最后殘像,只有暴力與絕望。
二、第二個(gè)鏡像:Honey
上文提及的片頭字幕除了敘述了父輩的失落,還提及了少年拉幫結(jié)派的原因:為了在父母失去話語(yǔ)權(quán)威之后能夠以團(tuán)體的形式壯大自己的生存意志。《牯嶺街》中的幫派主要分為兩股勢(shì)力:以眷村子弟為主的217和外省本土勢(shì)力混雜的“小公園幫”。前者傳承的是大陸的幫派范式,傾向于組織化和分工化,是結(jié)構(gòu)更為嚴(yán)謹(jǐn)?shù)某墒煨蛶团山M織;后者則更貼近臺(tái)灣本土幫派文化,義字當(dāng)頭,重視哥們兒情分。本省和外省的意識(shí)形態(tài)對(duì)峙由這兩個(gè)幫派的火并爭(zhēng)斗得到了很好的表現(xiàn),同時(shí)這兩個(gè)由二代少年組成的團(tuán)體也成為對(duì)抗父權(quán)統(tǒng)治話語(yǔ)的發(fā)聲筒。
小四在嚴(yán)格意義上并不屬于幫派:他幾乎從未以小公園幫的團(tuán)員身份做過(guò)正式亮相,以至于在殺人之后被帶至警局時(shí),警察竟然驚訝地發(fā)現(xiàn)從沒有見過(guò)這個(gè)“小混混”。小四雖和幫派中的小貓、飛機(jī)交好,但卻始終是個(gè)游離在幫派權(quán)力輻射之外的自由人。因?yàn)樵谀菚r(shí),他還擁有父之名的生存力量,擁有那一席承諾之地。
吸引小四進(jìn)入幫派的并不是團(tuán)體高漲的生存意志,而是Honey。從出場(chǎng)到被山東推到車前橫死街頭,Honey的出場(chǎng)時(shí)間不過(guò)20分鐘,但從他的舉手投足與言行片段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gè)于濁世中散發(fā)理想主義光芒的形象。他雖然是幫派頭目,但卻崇拜個(gè)人英雄主義。Honey是區(qū)別于占據(jù)統(tǒng)治地位的社會(huì)話語(yǔ)體系外的肉體暴力發(fā)言人,他所具有的肉體力量和精神力量,正是遭受以滑頭為代表的暴力侵害的小四所能尋求的最佳庇護(hù)所。
小四與Honey的互相凝視需要以小明作為介質(zhì)。與他人不同,小明的特質(zhì)不是作為鏡像去反射他人形象;相反,她是一個(gè)透明質(zhì),一個(gè)空。正是透過(guò)小明,小四與Honey因同一種以“愛情”為名的注視活動(dòng)獲得聯(lián)系,從而發(fā)現(xiàn)彼此顯得十分對(duì)稱的鏡像,而影片也一早就借小明之口說(shuō)出二人的相似之處:兩人都很固執(zhí),想要改變世界。在Honey與小四單獨(dú)談話的畫面中,二人分坐桌子兩側(cè),中央是懸下的昏黃燈泡,整體構(gòu)圖呈微妙傾斜狀,Honey的臉暴露在燈光下,而小四則背光埋在陰影中。這是一次單向的目光投射,被注視者則沉浸在自我講述中,向?qū)Ψ捷敵鲎晕业膱D像。在Honey敘述往事的過(guò)程中,鏡頭切到了坐在樓梯口的小明。隨著Honey的畫外音,這一折射介質(zhì)進(jìn)入到這一雙鏡像的視線互動(dòng)中,而也正是因?yàn)槎嗔诵∶鬟@一道折射的工序,小四對(duì)這一鏡像產(chǎn)生了誤認(rèn)。
小四對(duì)Honey的注視不僅僅是簡(jiǎn)單的觀看,而且是帶著欲望投射的凝視。凝視的存在意味著欲望的不滿足,其根源就在于小四自我形象的匱乏。凝視路徑的完成需要一個(gè)前提,即對(duì)象的不在場(chǎng)。因此只有當(dāng)Honey死后,小四才終于能夠?qū)⑺硐牖挠尫懦鰜?lái),通過(guò)凝視將自己虛構(gòu)地指認(rèn)為Honey。“鏡子階段是場(chǎng)悲劇,它的內(nèi)在沖勁從不足匱缺向預(yù)見先定。”[1]91自覺匱乏的小四最初接替Honey的形象時(shí)只是對(duì)小明許下他會(huì)來(lái)保護(hù)她的承諾(而這段告白在軍樂(lè)的頓停間被尷尬地暴露在空氣中,欲望的釋放受到阻礙),但在最后,小四的誤認(rèn)變成了一張“偽完形”:“因?yàn)橹挥形抑溃挥形夷軌驇椭悖沂悄悻F(xiàn)在唯一的希望,就像以前Honey一樣。這就是為什么你現(xiàn)在還一直忘不了Honey,因?yàn)椋F(xiàn)在我就是Honey。只有我才能夠幫你,因?yàn)槲揖褪荋oney。”小四完成了自我他化的最后一步,徹底解放地?fù)肀Я死硐胛摇5枰⒁獾氖牵黧w與鏡像永遠(yuǎn)只能漸近而不可抵達(dá),不論作為Honey的幻覺主體有多么真實(shí),都會(huì)隨著主體暴力迫近鏡面的那一瞬間爆裂。“偽完形”狀態(tài)的小四與Honey最大的區(qū)別在于,小四對(duì)世界所投射的目光中包含著侵凌性,他把自己放在了一個(gè)想象的救贖者位置,然而他所要救贖的世界卻將他排斥在話語(yǔ)體系之外;Honey不同,他明白社會(huì)規(guī)則,并且因?yàn)椤案馐∪嘶鞗]有出息”而學(xué)會(huì)了臺(tái)語(yǔ),他理解小明,深諳這個(gè)世界的語(yǔ)法邏輯。他將《戰(zhàn)爭(zhēng)與和平》理解成一部武俠小說(shuō),這種說(shuō)法乍看非常荒謬,但其實(shí)亦可看作世界生存法則的B面。小四只是漸近地貼近Honey的鏡像,他兀自沉浸于自戀模式之中而不知道在這理想化鏡像的背后有著多么巨大的虛無(wú)空間。因此當(dāng)小明擊碎了他想象中的自我鏡像,將其構(gòu)形指認(rèn)為偽時(shí),尖刀才終于滑向了曾經(jīng)折射其目光的另一面空鏡。endprint
Honey是小四開始掌握暴力的契機(jī),他向小四揭開了暴力的恐怖之處與可笑之處,并以其死將小四指定為他的“接班人”。而當(dāng)小四接過(guò)這把暴力鑰匙的時(shí)刻,也正是他主動(dòng)將自己納入暴力邏輯的時(shí)候。
三、第三個(gè)鏡像:日本女人
在以往對(duì)小四主體構(gòu)建的解讀中,日本女人這一形象往往被忽略或輕視。但當(dāng)小四經(jīng)歷了父像的隕落和理想自我的初步成形時(shí),正是日本女人為他的鏡像主體做了加持,并最終將他推向了那個(gè)淌血的夏夜街頭。
日本女人第一次“出現(xiàn)”是在影片的2小時(shí)42分處,她是小貓居住的日式屋宅的舊主,她的照片和一把日式短刀一起被放置在天花板上,后被小貓發(fā)現(xiàn)。日本女人對(duì)小四似乎有著直覺上的吸引力,使他一看照片就著了魔。在她兩次在小貓家的亮相中,克制的中全景機(jī)位沒有給照片任何特寫鏡頭,而即使是第三次她碰巧從小四跌落的日記本中滑落出來(lái),依然被鏡頭當(dāng)作一個(gè)客觀物而以大中景待之,沒有給予絲毫照顧。直到第四次,觀眾才終于看清了這個(gè)女人的容貌:她被掛在小四的床頭,容貌清秀,學(xué)生打扮,是一個(gè)與小四年紀(jì)相仿的女生。其時(shí)三姐跪在柜門外為小四作告解,希望用宗教之情喚回小四的善心。在這個(gè)被提喻為告解室的宗教性空間中,日本女人的照片被置于微小的仰視角度,而借助空間中的宗教氛圍,她的照片似乎具有了某種圣像般的功用。前兩次攝影機(jī)的故意忽略到這里終于發(fā)揮了作用:它們引發(fā)了觀眾的好奇心而誘使觀眾對(duì)照片產(chǎn)生了凝視,而先前圍繞照片中的女人所產(chǎn)生的神秘感則成為了她圣潔地位的佐證。值得注意的是,照片中的女人同樣也在凝視著攝影機(jī)所代表的銀幕外空間,觀眾由是與她產(chǎn)生了互動(dòng)。這種互動(dòng)所產(chǎn)生的心理效果最終會(huì)由觀眾這一旁觀視角自主嫁接到小四的身上。
從小四將她夾在日記本中和掛在床頭的特殊地位我們就可以了解到,在這個(gè)人與鏡像之間必然有著極深的互相凝視關(guān)系。拋離開日本殖民語(yǔ)境不論,日本女人其實(shí)和小四一樣,是一個(gè)孤零的外來(lái)者,而她恰好也是敘事中的一個(gè)缺席者,一個(gè)失根文化的微妙能指,這與小四所背負(fù)的外省移民縮影可以形成一個(gè)鏡像呼應(yīng),凝視正是由此進(jìn)入的,而它也將小四再度帶入鏡像階段。作為主體的欲望對(duì)象,日本女人的靜態(tài)凝視也是小四的欲望抒發(fā),而這將幫助她從根本上擁有小四。在那一場(chǎng)告解中,日本女人的照片成為圣像的現(xiàn)世代表,將小四擁入她純粹而帶有救贖性的凝視中。因此在這個(gè)特寫鏡頭后,小四一反常態(tài)地直接去找小馬攤牌,威脅小馬如果繼續(xù)和小明在一起,他就天天到學(xué)校堵小馬。這個(gè)表面上看起來(lái)相當(dāng)突兀的轉(zhuǎn)變直接導(dǎo)致了最后尖銳時(shí)刻的到來(lái),而如果我們將其置于鏡像理論中考察,這就顯得十分順理成章了:小四認(rèn)同了日本女人的凝視,并將這位象征著純潔貞烈、以死對(duì)抗世界污濁的少女指認(rèn)為自己的精神圖騰,于是他才做出了要維護(hù)小明的純潔的決定。
日本女人的信物是與她一起出現(xiàn)的日式短刀,一個(gè)鮮明的暴力能指。小貓隨口說(shuō)的“我看那把刀八成是她的,說(shuō)不定是用那把小刀殉情自殺的”給了小四一個(gè)完美的想象,其冷銳的刀身也許曾經(jīng)浸噬過(guò)一位從一座小島來(lái)到另一座小島上的女人的忠貞的鮮血,而這種獻(xiàn)祭的可能性和女人的形象一起,構(gòu)成了一個(gè)完整的指向自毀的符號(hào)結(jié)構(gòu),促使小四完成對(duì)她的認(rèn)同。拉康曾指出鏡像的最初沖動(dòng)與自殺傾向的關(guān)系,認(rèn)為它與出生的床上及死亡本能連接在一起,并處于傾向缺失的自戀扭結(jié)中。日本女人的鏡像在小四身上投射出自戀的救贖態(tài),此時(shí),短刀成為了切斷污濁外界與純潔內(nèi)在之間的聯(lián)系的理想工具。在小四最終穿著木屐去堵小馬及至將小明刺死的過(guò)程中,他正處于對(duì)小明所代表的“世界”的狂戀之中,而忘我的他戀恰恰正是狂熱的自戀。最后的殺人時(shí)刻,實(shí)際上是一次雙向的虐殺:小明將小四艱難構(gòu)建起來(lái)的自我形象打破,而小四則在自衛(wèi)與自毀的雙重傾向中將尖刀刺入小明的身體。由此,當(dāng)他望著倒在血泊中的年輕身體,意識(shí)到某一部分已經(jīng)死去。他殺死的當(dāng)然不是小明,也不是他自己,而是他身上所承載的鏡像的重疊;在他面前的不是一具尸體,而是無(wú)數(shù)碎裂的、浸著鮮血的鏡片。
他者的目光即是鏡像,《牯嶺街》中出現(xiàn)的與小四有著目光互動(dòng)的人物都可以作為其自我構(gòu)建過(guò)程中的鏡像,只是其影響程度有別。除了上文所舉的三個(gè)最主要的鏡像,小四的朋友小貓、飛機(jī)、小馬,以及學(xué)校的老師、胖叔乃至家庭中的姐妹兄弟,他們都在一定的時(shí)間內(nèi)反射出了小四的形象,使他見到自我的社會(huì)形態(tài)。但真正使小四產(chǎn)生認(rèn)同并以此來(lái)構(gòu)建自我形象的只有父親、Honey和日本女人。在這三者中,父像受到了政治體制的暴力迫害,中途破裂,而Honey作為暴力控制方成為了小四的理想鏡像,直到暴力的自我施受者日本女人為其鏡像鍍上一層自毀底色,小四的自我構(gòu)建才最終完成,而這一融合了外部暴力和內(nèi)部暴力的“完形”樣式是臺(tái)灣社會(huì)暴力總和的鏡面反像,最后凝固為戰(zhàn)斗態(tài)并指向以自毀來(lái)完成對(duì)自我與他者的救贖終點(diǎn)。
在牯嶺街殺人事件的真實(shí)版本中,殺人的少年茅武在獄中寫了一封信,他這樣說(shuō)道:“我在監(jiān)獄里過(guò)著無(wú)比痛苦的日子,我后悔,我失眠,我深覺我自己已是沒有希望的人,但我卻將希望寄于別人,我希望我的伙伴們以及想混太保的人,以我為一面鏡子。”《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以影像構(gòu)筑了這樣一面鏡子,將整個(gè)臺(tái)灣三十年的歷史映照其中。運(yùn)用鏡像階段理論,我們可以將《牯嶺街》歸納為一個(gè)人與一面鏡子之間的故事,且人與鏡之間的互動(dòng)是在暴力的關(guān)照下進(jìn)行的,最終導(dǎo)致了鏡像的碎裂和人的主體失陷。在外省二代少年的自我建構(gòu)中,來(lái)自政治、教育、文化、家庭等各個(gè)方面的暴力隱患進(jìn)入了他們的鏡像,造成了一代人的自我誤認(rèn)。半個(gè)世紀(jì)后的我們?cè)僦匦逻M(jìn)入那一段歷史未免會(huì)在經(jīng)驗(yàn)上顯得疏離,但隨著楊德昌的鏡頭講述,我們會(huì)從牯嶺街中的角落里發(fā)現(xiàn)能夠串聯(lián)起真實(shí)與影像時(shí)空的線索,而那才是《牯嶺街》所想要表述的那一個(gè)永恒核心。楊德昌及其一代導(dǎo)演在影像中留下了永無(wú)法成人的子一代,這為后世青年在現(xiàn)實(shí)生活中摸索自我身份時(shí)提供了充滿真誠(chéng)與善意的參照坐標(biāo),而這或許也是《牯嶺街》最終想要成為的精神符號(hào)。
參考文獻(xiàn):
[1](法)雅克·拉康.拉康選集[M].諸孝泉,譯.上海:上海三聯(lián)出版社,2001。
[2]戴錦華.電影批評(píng)(第二版)[M].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4.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