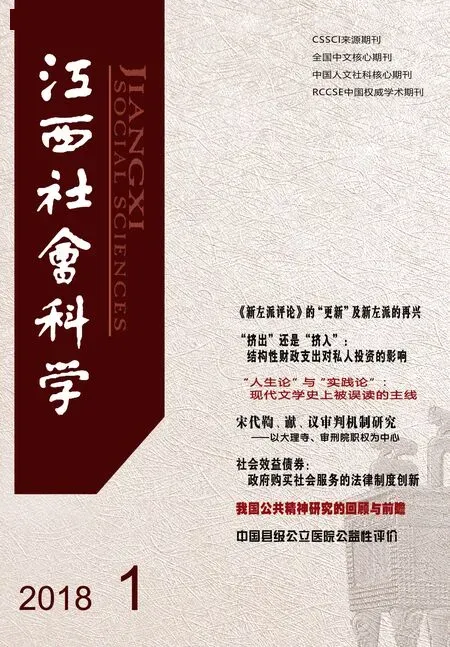受賄罪共犯與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的界限新解
2016年4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發布了《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以解決貪污賄賂犯罪案件辦理過程中存在的法律適用問題。《解釋》既回答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九)》中關于貪污賄賂犯罪定罪量刑標準的明確化問題,又針對司法實踐中長期存在以及新出現的爭議問題進行了回應。其中,針對目前一些案件中國家工作人員本人沒有索取、收受賄賂,索取、收受賄賂的系特定關系人的場合,能否以受賄罪追究國家工作人員的刑事責任的問題,《解釋》第16條第2款規定:“特定關系人索取、收受他人財物,國家工作人員知道后未退還或者上交的,應當認定國家工作人員具有受賄故意。”那么,這是否意味著,只要特定關系人索取、收受了他人財物,國家工作人員知道后未退還或者上交的,就一概認定國家工作人員具有受賄故意,進而在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行賄人謀取利益的場合,認定國家工作人員的行為構成受賄罪?在特定關系人索取、收受他人財物,利用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特定關系人謀取利益,而國家工作人員在此之后才知道特定關系人索取、收受他人財物且未退還或者上交的場合,特定關系人的行為到底構成受賄罪的共犯還是利用影響力受賄罪?基于對上述問題的思考,本文在對199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以下簡稱《刑法》)第388條關于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的規定和《解釋》第16條第2款關于受賄故意的規定進行法理解讀的基礎上,提出應當對《解釋》第16條第2款進行限制解釋的觀點,以厘清受賄罪的共犯與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的界限。
一、《刑法》第388條關于利用影響力受賄罪規定的法理解讀
2009年2月28日,第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七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七)》(以下簡稱《刑法修正案(七)》)第13條在《刑法》第388條受賄罪之后增加了關于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的規定。而在此之前的2008年8月29日,中國人大網公布并向社會公開征集意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七)(草案)》(以下簡稱《草案》)第11條是關于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的規定。關于增設利用影響力受賄罪規定的原因,全國人大常委會在 《關于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七)(草案)〉的說明》中作了如下解釋:有些全國人大代表和有關部門提出,有些國家工作人員的配偶、子女等近親屬,以及其他與該國家工作人員關系密切的人,通過該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或者利用該國家工作人員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自己從中索取或者收受財物。同時,一些已離職的國家工作人員,雖已不具有國家工作人員身份,但利用其在職時形成的影響力,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行為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自己從中索取或者收受財物。這類行為敗壞黨風、政風和社會風氣,對情節較重的,也應作為犯罪追究刑事責任。[1]從條文內容來看,最終通過的《刑法修正案(七)》第13條未對《草案》第11條作出任何修改。換言之,上述解釋可以作為《刑法修正案(七)》增設利用影響力受賄罪規定的立法理由。
通過對這一立法理由的分析可以發現,之所以《刑法修正案(七)》增設利用影響力受賄罪,是因為依據增設之前的規定難以對利用影響力受賄的行為進行刑事處罰。依據《刑法》關于受賄罪和共同犯罪的規定,成立共同犯罪,不僅要求客觀上具有共同的犯罪行為,還要求主觀上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國家工作人員的近親屬或者其他與該國家工作人員關系密切的人利用國家工作人員影響力,為請托人謀取利益,索取、收受財物的行為,如果未與國家工作人員通謀,則無法認定國家工作人員在利用其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時,對其近親屬或者其他與該國家工作人員關系密切的人索取、收受財物的行為知情,進而就不能認定存在共同受賄的故意。那么,在國家工作人員不具備受賄故意,不構成受賄罪的情況下,國家工作人員的近親屬或者其他與該國家工作人員關系密切的人的行為相應地也無法構成受賄罪的共犯。
2003年11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 《全國法院審理經濟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以下簡稱《紀要》)和2007年7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布的《關于辦理受賄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關于受賄罪共犯認定的規定,也是依據上述關于共同犯罪的理論作出的。①依據《紀要》和《意見》的規定,特定關系人或者特定關系人以外的其他人構成受賄罪的共犯,均要求特定關系人或者特定關系人以外的其他人與國家工作人員存在通謀。如果特定關系人或者特定關系人以外的其他人利用國家工作人員的影響力,為請托人謀取利益,索取、收受財物,而未與國家工作人員通謀的,國家工作人員不構成受賄罪;相應地,特定關系人以及特定關系人以外的其他人不構成受賄罪的共犯。
綜上,在法無明文規定的情況下,依照罪刑法定原則,對特定關系人以及特定關系人以外的其他人實施的利用影響力受賄行為不得定罪處罰,這造成了處罰上的漏洞。因此,基于嚴密賄賂犯罪法網、加大對腐敗犯罪懲處的考慮,《刑法修正案(七)》增加了關于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的規定。從法理上說,受賄罪共犯的規定與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的規定之間系一種排斥關系;并且,從法律適用的優先級來看,應當先認定國家工作人員的近親屬或者其他與該國家工作人員關系密切的人、離職的國家工作人員或者其近親屬以及其他與其關系密切的人是否構成受賄罪的共犯,只有在不構成受賄罪共犯的場合,再考慮是否構成利用影響力受賄罪。這是因為,從增設利用影響力受賄罪規定的立法原意來看,是基于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系針對國家工作人員的行為不構成受賄罪,進而國家工作人員的近親屬或者其他與該國家工作人員關系密切的人、離職的國家工作人員或者其近親屬以及其他與其關系密切的人的行為也不構成受賄罪的情形而設立的犯罪。這樣,在國家工作人員的近親屬或者其他與該國家工作人員關系密切的人、離職的國家工作人員或者其近親屬以及其他與其關系密切的人與國家工作人員構成受賄罪共犯的場合,所謂的前者的行為構成利用影響力受賄罪自然就無從談起。
二、受賄罪的共犯與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的應然界限
如果對《解釋》第16條第2款的規定進行平義解釋,那么,只要特定關系人索取、收受了他人財物,國家工作人員知道后未退還或者上交的,就應一概認定國家工作人員具有受賄故意。換言之,依照這種解釋方法,在涉及特定關系人的場合,以下三種情形可以認定國家工作人員具有受賄故意:第一,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行為,或者利用職權、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請托人謀取利益,并授意特定關系人索取、收受請托人財物的;第二,特定關系人收受請托人財物后,將收受財物的情況和請托事項轉達給國家工作人員,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行為,或者利用職權、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請托人謀取利益的;第三,特定關系人索取、收受請托人財物,利用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或者利用國家工作人員職權、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請托人謀取利益,國家工作人員在為請托人謀取利益的行為實施完畢后知道特定關系人索取、收受請托人財物,且未退還或者上交的。
在第一種情形中,國家工作人員與特定關系人之間存在通謀。所謂通謀,是指共同犯罪人之間用語言或者文字互相溝通犯罪意思。[2](P169)如果國家工作人員系在實施索取、收受請托人財物和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或者利用國家工作人員職權、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請托人謀取利益的行為之前,與特定關系人就索取、收受請托人財物進行謀議,授意特定關系人索取、收受他人財物,則屬于典型的事前通謀,即共同犯罪人著手實行犯罪以前形成共同受賄故意。如果國家工作人員系在實施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或者利用國家工作人員職權、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請托人謀取利益行為的過程中與特定關系人就索取、收受請托人財物進行謀議,授意特定關系人索取、收受他人財物,則屬于典型的事中通謀,即共同犯罪人在著手實行犯罪之際或者實行犯罪過程中形成共同受賄故意。在上述事前通謀和事中通謀的場合,認定國家工作人員具有受賄的故意,是不存在障礙的。因此,在這一情形下,國家工作人員與特定關系人構成受賄罪的共犯,不存在特定關系人構成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的可能。
在第二種情形中,雖然特定關系人是在收受請托人財物后,才將收受財物的情況和請托事項轉達給國家工作人員,但此時受賄罪的實行行為還未實行完畢,即還未完成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行為,那么,受賄罪就還處在實施過程中,此時形成的共同故意應當屬于事中通謀的受賄故意。在這一共同受賄故意的支配下,國家工作人員實施了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或者利用國家工作人員職權、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行為,因此,國家工作人員與特定關系人構成受賄罪的共同犯罪。如果特定關系人在收受他人財物之后未將收受財物的情況和請托事項轉達給國家工作人員,而是通過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或者利用該國家工作人員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則特定關系人的行為構成利用影響力受賄罪。
有疑問的是,第三種情形中國家工作人員的受賄故意能否得到認定,特定關系人的行為到底構成受賄罪的共犯還是利用影響力受賄罪?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就《解釋》第16條第2款進行說明時指出:“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便利為他人謀利,‘身邊人’收錢行為的刑事定罪問題。本著主客觀相一致的定罪原則,該行為能否認定國家工作人員構成受賄犯罪,關鍵看其對收錢一事是否知情及知情后的態度”。[3][4]陳興良教授認為,《解釋》第16條第2款對于正確認定國家工作人員的受賄罪以及正確劃分受賄罪共犯與利用影響力受賄罪之間的界限具有重要意義。依據《解釋》的規定,在特定關系人事先并沒有與國家工作人員共謀,其利用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并收受請托人的財物,但在收受財物以后告知國家工作人員,國家工作人員知道以后并沒有退還或者上交的場合,應當認定國家工作人員具有受賄故意。此時,國家工作人員成立受賄罪,特定關系人成立受賄罪的共犯;但如果國家工作人員直至案發并不知情,則國家工作人員沒有受賄故意,不能認定為受賄罪,對于特定關系人應當以利用影響力受賄罪論處。[5](P75)換言之,按照上述說明以及陳興良教授的觀點,在第三種情形下,國家工作人員的受賄故意也是可以得到認定的,國家工作人員與特定關系人之間能夠成立受賄罪的共犯。但是,筆者認為,就第三種情形而言,不能簡單地因為國家工作人員對特定關系人索取、收受財物的行為知情以及知道后未退還或者上交,就認定國家工作人員因具備受賄的故意而構成受賄罪,在這種情形下,只有特定關系人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的行為構成利用影響力受賄罪。
第一,受賄罪共犯的規定與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的規定之間系一種排斥關系,只有不構成受賄罪共犯時,才考慮是否構成利用影響力受賄罪。因而,若認為第三種情形中,國家工作人員與特定關系人具有共同受賄的故意,則特定關系人不可能再構成利用影響力受賄罪。但應當看到的是,對于特定關系人事前未與國家工作人員通謀,而利用國家工作人員的影響力,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索取、收受財物的行為,本不應考慮國家工作人員事后是否知道特定關系人收受財物這一情形,均依照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的規定對特定關系人定罪處罰。而現在如果認定第三種情形存在受賄故意,則明顯不當地縮小了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的成立范圍,使得利用影響力受賄罪只有在特定關系人利用影響力受賄,且事后未讓國家工作人員知道或者國家工作人員知道后退還或者上交的情況下才可能成立。若如此解釋,顯然是通過司法解釋的方式不當地縮小了立法規定成立的范圍,這是修改法律,是不合法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第7條明確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國家機構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第104條規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作出的屬于審判、檢察工作中具體應用法律的解釋,應當主要針對具體的法律條文,并符合立法的目的、原則和原意。因此,司法解釋只能就具體法律應用問題作出解釋,而不能超出立法原意作解釋,改變法律規定的范圍。除此之外,在受賄罪的法定刑比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的法定刑重的情況下,若對特定關系人本應以法定刑較輕的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的規定定罪處罰,卻適用了法定刑較重的受賄罪的規定,則違反了罪責刑相適應原則,也是不合適的。
第二,如果認定這種情形下國家工作人員具有受賄的故意,則意味著對事后通謀的共同犯罪持肯定態度,而這顯然是違背刑法原理的。從字面意義上理解,事后通謀應當是指共同犯罪人在將犯罪實施完畢之后形成共同犯罪的故意。但是,既然犯罪已經實施完畢,又如何還談得上具有犯罪的故意?正是基于此,在共同犯罪理論中,我們只承認事前通謀的共同犯罪和事中通謀的共同犯罪的存在,而不承認事后通謀的共同犯罪的存在。因此,在犯罪已經實施完畢的情況下,僅因為事后知情就認定具備犯罪的故意,有互相溝通的犯罪意思,是經不起推敲的。具體就第三種情形而言,即使國家工作人員實際上利用職務便利,或者利用國家工作人員職權、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他人謀取了利益,但只要國家工作人員在實施上述行為前或者實施上述行為時,不具有索取、收受財物的故意,就不能因國家工作人員在實施上述行為后知道特定關系人收受他人財物,而認定國家工作人員具有受賄的故意。
第三,如果認定國家工作人員在第三種情形下具有受賄故意,則意味著賦予了國家工作人員退還或者上交財物的作為義務,不作為也能構成受賄罪。一方面,這明顯違背對受賄罪客觀方面的認識。在收受財物型受賄罪中,實行行為僅包括兩個行為要素,即收受請托人財物的行為和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的行為,而顯然,這兩個行為都應當表現為作為。另一方面,不作為犯的成立,需要滿足以下條件:首先,行為人負有特定積極作為的義務,包括法律上的明文規定、職務或者業務上的要求、先行行為引起的作為義務以及合同行為、自愿承擔行為等法律行為引起的作為義務;其次,行為人能夠履行特定義務;最后,行為人不履行特定義務,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危害后果。顯而易見,在受賄罪中,很難說國家工作人員負有某種特定積極作為的義務。
具體就第三種情形而言,難以認為國家工作人員在知道特定關系人索取、收受請托人財物的行為之后,負有特定積極作為即退還或者上交財物的義務。其一,國家工作人員對特定關系人利用影響力受賄的行為不具有法律上明文規定的義務。譬如,妻子甲在收受請托人丙的財物后,利用擔任國家工作人員的丈夫乙的職務行為,為丙謀取不正當利益,而乙事后知道甲收受丙的財物,且未要求甲退還或者上交的。雖然甲乙為夫妻,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的規定,夫妻之間具有互相扶養的義務,但是,這并不意味著甲在乙實施了利用影響力受賄的行為后,具備退還或者上交乙收受的財物的義務。這是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還規定,夫妻雙方都有參加生產、工作、學習和社會活動的自由,一方不得對他方加以限制或干涉,如果乙收受的財物并未歸于夫妻共同財產而使用,則很難認定甲具有退還或者上交財物的義務。同時,由于道德義務不具備明確性,將道德義務作為義務來源會破壞罪刑法定原則,因此,也不能在甲不具有法律上的義務的情況下,依據道德上的義務對甲設定義務來源。其二,國家工作人員并非排他性地支配或控制法益侵害結果。雖然特定關系人的行為與國家工作人員存在一定的關聯,但是,存在關聯并不意味著就要國家工作人員履行特定的義務。在對作為義務的來源進行判斷時,只有在行為人排他性地支配或控制法益侵害結果時,才可以認為行為人具有一定的義務。在第三種情形中,國家工作人員雖然在客觀上為請托人謀取了利益,但在為請托人謀取利益時,國家工作人員并不具有受賄的故意,那么,國家工作人員在實施為請托人謀取利益的行為時,也就不可能主動地設定對法益的排他性支配。真正主動地、排他性地支配法益侵害結果發生的是特定關系人,特定關系人的行為決定了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廉潔性會不會被侵犯,如果特定關系人在利用國家工作人員影響力受賄的過程中停止其行為,則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廉潔性就不會被侵犯。其三,如果認為國家工作人員負有退還或者上交財物的義務,則意味著國家工作人員如果退還或者上交財物,就可能避免法益受侵害或者法益受侵害的危險。但由于國家工作人員知道特定關系人索取、收受財物時,特定關系人的行為已經造成國家工作人員職務的廉潔性被侵犯,法益侵害的后果已經造成,因而,即使退還或者上交財物,這種侵害后果也難以被避免。由此可知,在特定關系人索取、收受財物,國家工作人員知道后不退還或者上交財物的場合,不履行特定義務就會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危害后果根本就是無從談起的,國家工作人員不具備退還或者上交財物的義務。其四,退一步講,即使認為具有退還或者不上交財物的義務,這種義務也應當是由特定關系人承擔,而非國家工作人員。如上文所述,國家工作人員不具有法律明文規定的義務,特定關系人排他性地支配或控制法益侵害結果,如果讓國家工作人員承擔退還或者上交財物的義務,就等于讓國家工作人員承擔了本應由特定關系人承擔的義務,而這是明顯違背罪責自負原則的。
還需要指出的是,如果認為《解釋》第16條第2款的規定中不包含第三種情形,而僅包含第一、二種情形,則應依照該規定,結合客觀實際情況,運用邏輯法則和經驗法則,推論受賄故意是否成立。換言之,在上述情形下,《解釋》第16條第2款的規定可以進行推論。所謂推論,是依據客觀實際情況予以推出的結論,該結論應當符合經驗與邏輯,從而具備“合理的可接受性”。推論屬于一種事理判斷或情理判斷的方法,是一種間接證明,不轉移證明責任、降低證明標準。在司法實踐中,由于賄賂犯罪極具隱蔽性,又確實有許多受賄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聲稱是在特定關系人利用其職務上的行為,或者利用其職權、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他人謀取利益并索取、收受了財物后才知情,導致控訴機關難以證明犯罪嫌疑人具有受賄的故意。此時,推論就成為一種有效的證明方式。譬如,在薄熙來案中,薄熙來就明確否認其對薄谷開來、薄瓜瓜收受他人財物的行為知情,并且對證人行為的合情理性進行了較為有力的辯駁,如稱“開來不厭其煩地把這些小事(旅費報銷等)都給我談,試想開來她是不是一個知識女性?她還希望不希望我對她還有感情、還愛她?”[6]在這種情況下,欲直接證明薄熙來具有受賄故意,的確存在困難。但如果公訴方利用事實推斷和經驗法則等間接證明的方式,論證認定受賄故意的推論具有“合理的可接受性”,則可以認為待證事實被證明。當然,推論依據的經驗和邏輯雖然具有一定的蓋然性,但是,這種蓋然性仍應當以一般人的認識為標準,如果一個正常的人按照其生活的經驗,認為該推論不符合常理,則不屬于推論。
顯而易見,對于上述第一、二種情形,如果以一般人的認識為標準,利用事實推斷和經驗法則的方式,能夠推斷出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并授意特定關系人索取、收受請托人財物,或者特定關系人收受請托人財物后,將收受財物的情況和請托事項轉達給國家工作人員,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那么,就可以認為該推論具備“合理的可接受性”,推論成立。至于第三種情形,由于一般人會認為該行為是特定關系人利用國家工作人員的影響力而實施受賄行為,與國家工作人員受賄故意的認定無關,因而即使以一般人的認識為標準,利用事實推斷和經驗法則也無法推論出受賄故意的成立。由此看來,第三種情形無法進行推論。
在第三種情形無法推論的情況下,如果認為第三種情形中的受賄故意仍然可以被認定,則《解釋》第16條第2款的規定屬于法律擬制。所謂法律擬制,是指立法者基于刑事政策上的考慮,為實現一定的目的,將本不具有直接關聯性的基礎事實與法律行為之間建立強制性的關聯,只要能夠證明基礎事實,擬制規定中的法律行為即告成立。法律擬制主要包括兩種情形:其一,將依據基礎事實本不構成法律行為的,擬制規定為成立某一法律行為;其二,將依據基礎事實A本應認定成立法律行為B的,擬制規定為成立法律行為C。就前者而言,《刑法》第66條的規定是其典型的體現。該條規定,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的犯罪分子,在刑罰執行完畢或者赦免以后,在任何時候再犯上述任一類罪的,都以累犯論處。本來,累犯的成立要求被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的犯罪分子,刑罰執行完畢或者赦免以后,在五年以內再犯應當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之罪,但基于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是對國家最危險的罪行,以及當前我國恐怖活動犯罪、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犯罪的現狀及發展態勢,為了加大對上述犯罪的打擊力度,[7](P252)將本不屬于累犯的行為以累犯論處。就后者而言,《刑法》第267條第2款是其典型的體現。該款規定,攜帶兇器搶奪的,依照搶劫罪定罪處罰。本來,攜帶兇器搶奪的行為應當構成搶奪罪,但由于行為人攜帶兇器搶奪的行為表明行為人主觀上具有使用兇器的意識,使用兇器的可能性非常大,因而導致該行為與搶劫行為法益侵害的程度沒有實質區別,最終以搶劫罪定罪處罰。[8](P991)就《解釋》第16條第2款的規定而言,如果認為第三種情形中的受賄故意仍然可以被認定,就是將國家工作人員不退還或者上交財物這一本來不具有法律后果的行為規定了法律后果,即認定存在受賄故意。因此,這屬于法律擬制中的第一種情形,將不具有受賄故意的行為視為具有受賄的故意。
然而,這種通過司法解釋設置法律擬制的做法不具備正當性和合法性。法律擬制應基于應對現實狀況以及彌補法律漏洞的需要,將基礎事實強制升格為法律事實,認為一旦基礎事實能夠得以證明,法律事實也就相應存在。然而,也正是基于這種強制性,一般認為,法律擬制應當由立法者作出規定,而非司法者。畢竟,如上文所述,由于“擬制”才導致基礎事實與法律行為之間產生直接關聯,那么在我國,如果允許司法擬制,則意味著賦予了司法機關類推解釋的權力。這顯然違背罪刑法定原則,不利于人權保障功能的實現。而且,《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第8條也明確規定,犯罪和刑罰、對公民政治權利的剝奪、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等事項只能制定法律。顯而易見,將不應定罪處罰的基礎事實強制升格為法律事實而定罪處罰,涉及犯罪和刑罰,只能通過制定法律來實現。另外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雖然英美法系國家存在司法過程中的法律擬制,但應當注意到,英美法系國家是判例法,其所依賴的就是法官在司法過程中造法。正如卡多佐大法官所言:“司法過程的最高境界并不是發現法律,而是創造法律;所有的懷疑和擔憂,希望和畏懼都是心靈努力的組成部分,是死亡的折磨和誕生的煎熬的組成部分,在這里面,一些曾經為自己時代服務過的原則死亡了,而一些新的原則誕生了。”[9](P101)這種司法過程造法的行為,在某種意義上來說,亦可被視為一種立法擬制。總而言之,在我國,只有通過立法擬制而非司法擬制的方式,才能在最大程度上平衡法益保護與人權保障之間的關系;并且即便如此,對待立法擬制,也應當慎之又慎。
另外需要說明的是,即使認為第三種情形中的受賄故意仍然可以被認定,《解釋》第16條第2款的規定也不屬于推定。所謂推定,是根據案件中已查明的基礎事實,基于一種蓋然性所作的事實“假定”,伴隨證明責任轉移和證明標準降低。[10]推定是可以反駁的,允許被告人對基礎事實或者推定事實提出證據進行反駁,且這種反駁不需要達到“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證明標準,只要能夠使法官對公訴方的主張產生懷疑即可。譬如,《刑法》第395條關于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規定屬于典型的推定。依據這一規定,如果在責令國家工作人員說明其超過合法收入的巨額財產來源時,國家工作人員無法說明來源,則推定超出的差額部分屬于非法所得。如果國家工作人員能夠反駁,說明差額部分的來源,則認定不屬于非法所得。但顯然,《解釋》第16條第2款并未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可以反駁,以證明其不具備受賄故意。根據這一規定,只要國家工作人員知道特定關系人索取、收受財物,且未退還或者上交,國家工作人員就存在受賄故意。換言之,該種情形下認定的受賄故意是不容許反駁的。眾所周知,法律擬制與推定雖然均是將邏輯上存在斷裂和跳躍的兩個問題直接相關聯,即只要能夠證實A,B就存在,無論A與B之間根據經驗法則和邏輯法則是否具有關聯。但是,在推定中,認定B存在之前,允許被告人進行反駁,如果被告人的反駁成立,則B不能成立。而法律擬制則不同,法律擬制不容許反駁,只要A能夠成立,B就相應無條件、強制性的成立。因此,是否容許反駁,是推定與法律擬制之間的最主要區別。《解釋》第16條第2款未規定可以反駁,不屬于推定,而是法律擬制。
此外,推定與法律擬制同樣只能是一項立法技術,而非司法技術。推定是立法者在總結司法經驗的基礎上,基于一定的刑事政策考量和訴訟價值選擇而制定出來的法律規范。推定的設立和適用雖然并不必然導致被告人被定罪處罰,但卻會使被告人陷于這種危險之中,因此,推定應當由法律加以明確規定,司法人員不能根據經驗規則任意創設和使用。[11]如《刑法》第395條的規定,之所以要通過《刑法》作出上述規定,正是因為推定轉移了公訴方應當承擔的證明責任,必須要求國家工作人員說明來源、反駁公訴方的主張,這顯然不利于被告人,因而必須由位階和權威性更高的法律進行規定。因此,即便是關于推定的規定,也只能存在于法律當中,而不能通過司法機關的司法解釋這一形式出現,如果由司法解釋作出關于推定的規定,是對被告人人權的侵犯。
三、結 語
本文的核心觀點與權威人士對《解釋》第16條第2款規定所做的理解是一致的。參與《解釋》制定工作的最高人民法院的有關人士在對《解釋》第16條第2款的規定進行解讀時指出,本規定所涉及的情形以國家工作人員接受特定關系人轉請托為前提,特定關系人未將轉請托事項告知國家工作人員的不適用本規定。[12]從邏輯上說,國家工作人員能夠接受特定關系人的轉請托,一般是以國家工作人員尚未實施轉請托事項所涉及的行為(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行為)為前提的;在國家工作人員已經開始實施涉及他人利益的履職行為的情況下,國家工作人員也存在接受特定關系人轉請托的可能性;而在國家工作人員已經將涉及他人利益的履職行為實施完畢的情況下,則已經不存在國家工作人員接受特定關系人轉請托的可能性,因為既然涉及他人利益的履職行為已經實施完畢,所謂的接受涉及他人利益的轉請托自然就是無從談起的。這樣,此時特定關系人將轉請托事項告知國家工作人員的,當然就不再發生國家工作人員接受轉請托的問題。由此可見,上述對第16條第2款的規定所作的解讀也認為,本規定的適用以國家工作人員尚未將涉及他人利益的履職行為實施完畢為前提。這也就意味著參與《解釋》制定工作的最高人民法院的有關人士對本規定作出了與本文的核心觀點相一致的限制解釋。
注釋:
①《紀要》規定:非國家工作人員與國家工作人員勾結,伙同受賄的,應當以受賄罪的共犯追究刑事責任。非國家工作人員是否構成受賄罪共犯,取決于雙方有無共同受賄的故意和行為。國家工作人員的近親屬向國家工作人員代為轉達請托事項,收受請托人財物并告知該國家工作人員,或者國家工作人員明知其近親屬收受了他人財物,仍按照近親屬的要求利用職權為他人謀取利益的,對該國家工作人員應認定為受賄罪,其近親屬以受賄罪共犯論處。近親屬以外的其他人與國家工作人員通謀,由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收受請托人財物后雙方共同占有的,構成受賄罪共犯。《意見》規定:特定關系人與國家工作人通謀,由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而國家工作人員授意請托人以交易、干股、合作投資、委托理財、賭博、“掛名”領取薪酬等方式,將有關財物給予特定關系人的,對特定關系人以受賄罪的共犯論處;特定關系人以外的其他人與國家工作人員通謀,由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收受請托人財物后雙方共同占有的,以受賄罪的共犯論處。
[1]刑法修正案(七)草案全文及說明[EB/OL].http://www.npc.gov.cn/huiyi/lfzt/xfq/2008-08/29/content_1447399.htm.
[2]高銘暄,馬克昌.刑法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
[3]“兩高”發布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司法解釋[EB/OL].http://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19562.html.
[4]萬春,袎杰,盧宇蓉,楊建軍.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要準確把握法律適用標準(下)[N].檢察日報,2016-05-24(3).
[5]陳興良.貪污賄賂犯罪司法解釋:刑法教義學的闡釋[J].法學,2016,(5).
[6]山東省濟南市中級人民法院新浪官方微博關于薄熙來案件審判的“庭審現場”播報[EB/OL].http://weibo.com/p/1001063708524475/home?profile_ftype=1&is_hot=1#_0.
[7]高銘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孕育誕生和發展完善[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8]張明楷.刑法學(下)[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
[9](美)本杰明·卡多佐.司法過程的性質[M].蘇力,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10]龍宗智.薄熙來案審判中若干證據法問題[J].法學,2013,(10).
[11]史立梅.論貪污賄賂犯罪案件中的推定[J].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8,(6).
[12]裴顯鼎,苗有水,劉為波,王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理解與適用[J].人民司法,2016,(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