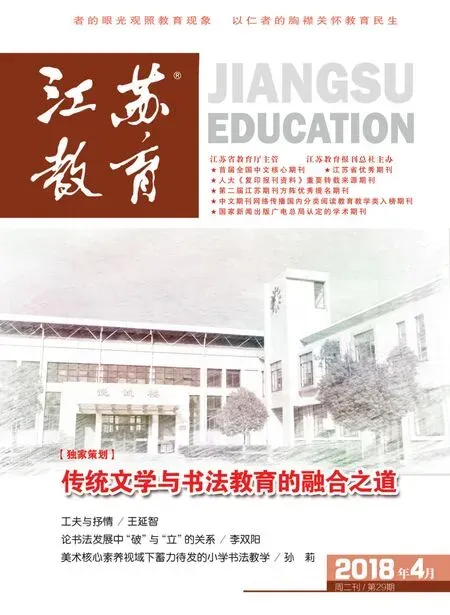論書法發展中“破”與“立”的關系
/李雙陽
我們發現推進當代書法發展的因素,它的價值是多樣,取法是多元的。我更愿意把對當代書法的發展理念,維系在帖學的價值取向上,因為帖學中蘊涵了太多的民族審美的基因,堅守著帖學內部的價值,并用新的精神闡釋著時代和個性風度。我堅信帖學還有很強的吐納能力,當代“新帖學”的出現可以視為一個信號。帖學的精神,是從無法到有法的錘煉,再到隨心所欲的一筆徒手線,我們意念中所表達的一條極為平常的線,從表現升華到自覺,往往是一條生命之線,應該說在這一筆之中,延續著最終達到一種超脫的平靜。近些年來,我主要對魏晉以來“二王”體系書風進行全面的梳理和學習,創作時用唐人書風通過對其筆意、線質、章法的轉換來表現,力求“古為今用、小從大求、大以小滋”的學習創作理念。我們學習書法的手法可以是傳統的,但我們對書法的理解與認識可以是全新的。
一、“破”與“立”的關系
在書法發展的歷程中,“破”與“立”的關系,始終繞不過傳統與當代的問題,也就是說傳統取舍的問題,我們清楚傳統與經典是前人精神創造、技術鍛造的凝聚,是有其空間擴展力與時間穿透力的話語范本。對于后人來說,經典總是先存的,是屬于過去時態的文化遺存物,所以面對經典的咀嚼,實際上就是后人與傳統的一種“體認”,經典的價值與權威性就在這不斷的“體認”中生成或消失、增長或衰減。在這個意義上說,經典的生命力便不僅取決于它切入社會和人生的廣度與深度,同時也取決于體認者有什么樣的審視眼光。如果你是優秀的接受者,有自身時代精神價值、心靈抒發的需要,對經典取舍就成了一種必然。因為不同時代的審美價值觀,一定是在原有的基礎上不斷地偏移。在大的書法發展趨勢上,書法在傳承中不斷地創新,這是一個事實,書法作者的傳統情結再深也不能是純粹的傳統主義,如果一個作者或一個時代都陷于一種與歷史保持不變的傳統中,這個時代的書法不但不能出現新的發展,甚至還會倒退,元代帖學的復古運動和清代帖學走向“館閣體”的結果,都是給我們留下的深刻的教訓。
作為一個書法家,在觀察書法發展“破”與“立”的關系時,目光首先落在技法上,任何一絲變化都是從技法開始,也從技法中傳達。如果理論家說書法史是一部思想發展史,那書法家更愿意說書法史是一部變化的技法史,因為所有的思想落實到作品中,都得有技法作為載體。我們用敏感的創作思路和動態的審美眼光來理解、分析技法,也可以從總體的高度、技法史的高度來觀照當代書法的發展,從技術層面對“破”與“立”的分析是優秀書法家的一種本能。
書法技術的核心是用筆,不同的用筆方法,可以產生不同的結字體勢,從而體現出不同的特征風格,對筆法的追溯與辨析也是書法家慣用的分析手段,應該說在秦漢時期,帖學還沒有出現(書法界一般把王羲之視為帖學的開山鼻祖),秦篆漢隸就有了相對獨立的用筆方法。篆書用筆,圓起圓收中鋒行走,隸書側鋒起筆,方折入紙后擺正筆鋒,也是中鋒行走,篆隸中間的這一段用筆區別不大,只是篆書的線質更為圓實,線形較長,形成了篆隸典型的用筆方式。
王羲之根據魏晉、漢隸筆蹤慢慢演化為行書快速、干凈的行筆過程和一推直進的用筆方式,形成了“一拓直下”的筆法。在他中期的《二謝帖》《得示帖》《喪亂帖》等信札、尺牘中漸漸形成帖學用筆的一大體系。甘中流、宗成振兩位先生編著的《王羲之書派行書翰札導讀》序言中說:“歷史上行書雖然起源較早,但王羲之的創造才真正讓行書有完整的法則。我們從歷代佳作中選出風格大體一致,淵源有緒的作品,裒為此集。我們選擇的這些歷代名家作品從王羲之開始,直到現代的名家沈尹默、吳玉如、白蕉。”可見,王羲之的這一用筆體系的影響是非常大的,但并不是說這一用筆體系沒有出現過變化,其實也是在“破”與“立”的關系中發展的,所以在朱以撒先生的論述中有十分精彩的表述:“王羲之對草書的把握推進了發展,而王獻之的‘破體’又加劇了運動狀態的深入,像王獻之的《中秋帖》《十二月帖》都顯示了與其父所不同的強烈個性。所謂‘破體’當時指的主要是運動的態勢由內斂轉為外拓,體勢由圓美轉為放縱,意態由平和轉為激蕩。”
大家都認為白蕉在現代書家中最得王羲之精髓,然而張旭光先生敏銳地發現白蕉用筆的方法——“白蕉以晉人為宗,同時融合了顏真卿、八大渾圓奇特的營養”。我們把這種破立關系認為是“一拓直下”用筆體系內部的變化,當然像王獻之的部分用筆已躍出了“一拓直下”的用筆體系。
在帖學體系里徹底改變“一拓直下”用筆方式的是張旭。張旭在草書使轉的要求下,不得不改變行書“一拓直下”的方式,創立了一種不同于“一拓直下”的抒情節奏的筆法,形成了相并肩的兩大行草書用筆體系。張旭這種用筆特點,對線條行筆過程的衡定感要求較高,通過不斷的絞轉來保持線條的力度和長線的運動,這種用筆的源頭可追溯到篆、隸書的走筆特征,再到陸機的章草《平復帖》,然后是王獻之的草書,張旭強化線條運行過程的使轉動作,我們統一把它歸為“篆籀絞轉”用筆體系。這是與“一拓直下”最根本的區別。
張旭將這種用筆方法傳授給顏真卿,顏真卿得其精髓,不過顏魯公的行書用筆與張旭的《古詩四帖》和《肚痛帖》比較,有意識地慢化了這種用筆速度和絞轉的跳躍,變得更加的綿實、圓勁。這種用筆方法連綿的長節奏,在表達情感上有先天的優勢,可以呈現出郁郁芊芊的生機,達到生命本質的渾然,與“一拓直下”的一板一眼的節奏感,更顯君子之風。“篆籀絞轉”用筆體系傳到懷素時,懷素更強化了線的特征,更突出了抒情的流暢性。
張旭、顏真卿、懷素用筆體系的破立關系,我們也可視為“篆籀絞轉”體系內部的變化。顏真卿的行書《祭侄文稿》與王羲之的行書《蘭亭集序》并肩為行書兩種審美體系。我們還可以大膽地設想:有沒有在“一拓直下”與“篆籀絞轉”體系的交融中,建立“破”與“立”的關系呢?答案是有的!并有成功的范例給我們提供了巨大的思考空間。八大山人就是其中一例。八大山人早期(1666-1678)學董其昌,并深受董其昌的影響。董其昌的用筆體系無疑是“一拓直下”的“大王”筆法。到后期慢慢從王氏用筆體系轉化為“篆籀絞轉”用筆體系,用筆少提按,圓轉多了起來,線質圓活,但書寫節奏還是用“一拓直下”的節奏感。八大山人草書作品少,不是由于他對草法陌生,而是與他習慣的“一拓直下”的節奏有關,當然這和八大山人對“簡古、簡淡、簡雅”的中國傳統哲學觀念也有關,八大山人在“破”與“立”的關系中,他用概括性和抽象性的線性表達,使他筆下的書法呈現出最簡練的生命軌跡,從而為書法創作增添了新的元素。
我們對技法層面“破”與“立”的思考,旨在開闊我們的視野,梳理我們的用筆方法,以使我們有更多的發現。我們在對“破”與“立”的分析中,還可以做精神層面的思考,目的是推進當代書法發展的進程,我們可以用書法精神,用心靈,用時代的情懷,在“破”與“立”之中創造我們自己的書法時代,傳統和歷史已經存在,而未來的書法存在無限的可能,書法與當下書法家的意義,不僅在于要表達傳統和歷史的厚重,更要努力探求未來書法的發展。
從近幾年帖學的發展來看,一批分散在全國各地的中、青年書法家,以他們敏銳的藝術感受力和時代賦予的進取精神,強化著當代書法的文人意識和精英意識。他們把目光深入到傳統文化體系中,以期在這個參照體系里找到對自己、對當代書法藝術最有影響的諸多因素。而任何一位書家對傳統的解讀和反思,都會給新時代書法發展留下更多的標記。
二、關于“展大書寫”
當代“展大書寫”當然是離不開“展廳效應”,對“展廳效應”認識的逐漸深入,使我們有了一個比較冷靜和客觀的態度。“展廳效應”并不是膚淺的視覺形式的,我們更多的時候應該正視“展廳效應”的作用,把它當作一種文化來認識,“展廳文化”指一件作品在展覽場所中產生的審美效果,由于這種效果的不同,藝術作品的審美也隨之變化,隨著展廳空間的擴大,作品的幅式也越來越大。相對書齋作品閑適的長時間的欣賞,展廳的作品是集中的短時間的觀覽,需要根據展廳大小設計篇幅,審美性要與展覽意識結合才可能產生作用。當然我們可以設計“展廳文化”,有時還可根據不同的作品氣息、意境,來設計展廳的燈光、音響甚至背景和作品裝裱的幅式,能夠讓欣賞者更快、更輕松地體會到作者、作品的表達,從而得到更好的交流。
當然,我們必須讓“展大書寫”定位在帖學內部來完成,保證帖學的美學價值而不是單字獨立展大書寫,因為碑法中大字創作在古人摩崖石刻中就已解決。帖學的展大書寫是在字的連帶運動關系中展開的一種書寫,既能擴大其表現的空間,也能給欣賞者以思維想象的空間,還要有書法文化的那種傳承關系,來維系展大書寫厚重的文化感。由此,我們才有必要將展大書寫提到今天的課題上來。在這個范圍內對于展大書寫的探討,也是書法在當代發展中的“破”與“立”的手段之一。傳統帖學里多以手札、尺牘為表現對象,在尺余大小的空間信手寫來的三五行。到了唐代盡管有了張旭《古詩四帖》與懷素的《自敘帖》,但字徑一般小于二寸見方。一直到了明清八尺、丈二的高堂大軸,字徑突然大了起來,但明清兩代的展大書寫,還有很多沒有解決的問題,留給當代書法家對展大書寫更多的思考空間。我想對展大書寫的有效探討,最終還得落實在技法層面上。
我們先分析明清展大書寫帶給我們的啟示。以王鐸、傅山為代表的明清大草,像王鐸能夠把“二王”尺牘展大,書寫成條幅,在其章法、字勢上增加了自我理解和詮釋的地方,為當今書家展大書寫帶來許多啟示。王鐸在展大書寫時,為了增強作品視覺對比的豐富性與單個字的飽滿度,他一方面有意識地增加筆畫的纏繞,這種纏繞能讓書寫很有流動性和感染力,與性情的揮灑很合拍,往往容易被欣賞者接受;另一方面有時用漲墨增加筆畫的塊面感,增大單字的空間張力。王鐸在用“大王”筆法展大書寫時,還是多用“一拓直下”的筆法,特別是行書大字,筆勢內斂,方折之處太過生硬,所以王鐸用“大王”筆法展大書寫時留下的遺憾也是頗多,展大之后粗糙感也隨之而來,內涵的豐韻也逐漸流失。傅山的大字在體勢上更為流轉,但纏繞過甚,也過于率意,不太耐看。明清朝代展大書寫留下的墨跡,給我們更為深入探討其中的奧秘提供了一定的基礎。
我們首先從筆法角度對展大書寫進行分析。傳統帖學的用筆方法中有兩大體系,一是“篆籀絞轉”法,二是以王羲之為代表的“一拓直下”法。這兩種用筆體系,誰更適合展大書寫?王羲之“一拓直下”的用筆,行筆干凈、爽快,行進中一拓直過,只有在尖鋒入紙后,擺正到轉折處的“切轉”頓挫一個動作,由于用筆快與直,轉角地方的頓挫“切轉”形成體勢內斂、爽朗的風格。這種“一拓直下”的用筆在展大書寫連續不斷的運筆過程中,在使轉方面帶來的困難是明顯的,因為這種用筆方法擺動的弧度小,要求指腕之間的力度在空間增大的范圍內連續運筆,卻難以為繼,只能是間歇性連續而單個成字。大字展寫中使轉、絞動的弧度也隨之增多,要求臂與腕的運動明顯加大。我們能從張旭、懷素長安城粉壁題書的故事中得知,張、懷兩位大師以壁代紙,筆走龍蛇,字肯定是大的,如果他們的題壁還在便更是一目了然。不過我們還是可以從《自敘帖》和《古詩四帖》的書寫風格中,看出兩位大師用的都是“篆籀絞轉”的筆法。這種筆法運筆靈活,線質彈性高,屬于柔性線質,在轉折之處可以遇方化圓。這種筆法對展大書寫的流暢性無疑極有幫助,只是游走時線條粗細把握的難度大。比如過粗的線條給游走帶來不便,因而粗筆畫的地方,用一拓直下的大王筆法作為補充,同時也能增強書寫時跑與走的節奏。
關于展大書寫,我們還可以從結字的體勢角度考慮,應該說不同的結字體勢,需要不同的筆法來完成,體勢與筆法是相生相成的。展大書寫僅僅從筆法上完成是不完整的,雖然筆法在書寫過程中有著主導的力量,不過體勢的開張也是決定展大書寫的一個關鍵。可以想象內斂、緊實的結體,勢的向心力都向內走,氣度就小,連貫的書寫就成了一種困難。體勢的開張、力量的外向、筆畫的舒張與連續就成了一種自然,在這個意義上展大書寫,外拓體勢先天優于內斂體勢,可以說展大書寫僅僅放大王羲之“一拓直下”的筆法與體勢是行不通的。
我們對展大書寫的辨析,是為了更清晰地探討書寫的本身,沒有去褒貶誰高誰低的意圖,只是在展大書寫的思考中,我認為唐代的傳統是在“二王”傳統被充分關注以后,下一個極有價值的目標。“篆籀絞轉”的用筆方式、表達技術所呈現出的迷人藝術魅力,會引發學書者對有唐一代行草熱情的追尋。以我的判斷,有一部分敏感的作者正做著這項工作,并已有初步的成效,在不久的三五年里將會出現唐人行草的復興熱。
三、尋找新的融合
融合也是促進書法發展的一種方法,也是“破”與“立”的一種體現,融合是在原有的基礎上,不斷用新的元素破壞已有的元素構成,然后漸漸成立新的結構秩序。融合在實際的創作中生成。一旦技法和風格趨于成熟與穩定,融合就要困難得多,同時融合的取向也更明確。所以我在《我的草書情結》中提出:“我并沒有過早地,很強烈地去追求所謂的風格,我想一旦形成很強的風格,往往只會去關注與你風格相關的東西,形成排他性,而不能做到兼容并收,融會諸法。學習書法要學會抓住主脈絡,要學會以一碑一帖去打通方法。”
古人常以純粹的一家法示人,其中原因是信息交流的封閉性和教學思想的封建性。學習資料的匱乏,又加上一對一、手把手的傳授方式,形成書寫學習最初的一種模式。這種最初的學書模式也有一定的好處,關鍵是這種模式審美品質的高低,如果是高的則會給他帶來一生的受用。因為創作者在最初的學習中,開始都不會呈主動狀態,他對書法的感覺是遲鈍的、受教的,學習是由教師代為選擇的模式,而積累了一定的經驗之后,審美心理結構也隨之在實踐中不斷建構和完善起來,才有融合和選擇的可能。
在古代只有極少數人擁有這種條件,并身體力行地這樣做,歷代杰出的書法家走的都是一條艱辛融合之路,比如楊凝式學王羲之的《蘭亭集序》而出《韭花帖》,學顏魯公而出《盧鴻草堂十志圖跋》,他是個融合的高手。最有說服力的就是:“昔米元章初學顏書,嫌其寬,乃學柳,結字始緊,知柳出歐,又學歐,久之類印板文字,棄而學褚,而學之最久,又喜李北海書,始能轉折肥美,八面皆圓。再入魏晉之室,而兼乎篆隸。”這段話不管事實真假,但我們從這段文字中,可知一位有成就的書家一定是轉益多師,取我所需。融合從個體方面講,它是個人書藝走向成熟的必然階段,從整個時代來說,也是推進書法發展的一種動力。
其實在風格的融合,也會隨工具的變化而產生一定的變更。我認為林散之先生在融合中做到了了無痕跡。應該說他在氣息上受董其昌影響非常大,然而他改變了董其昌的書寫工具。他用長鋒羊毫與生宣,將羊毫的柔性與黏性,通過裹絞筆法的駕馭以及碑法運筆的澀勁,表達為筆與紙之間相互生發的一種個性化語言。當然還從老師黃賓虹那里吸收了用墨的方法,吸取了董其昌小行草的氣息淡遠,再用小狼毫一類彈性大的精致毛筆,在筆與紙之間產生更為清爽、銳利的筆畫。我還見過董其昌用懷素一類草意書寫的作品,形神都極有分寸,但他那一類勁毫劃過的筆觸稍為緊張。林散之汲取董其昌的神韻,將疏淡、清遠之神化為草書機緣,他的草書猶以氣勝,靜靜地搖曳,行與行之間距離加大,甚至字與字之間都可獨立成單位,但都統一在祥和的化機之中,林散之的大草欲淡方枯,淡中有墨,從而形成了他獨有的面貌。
融合在另一個意義上來說,是作者與表現的融合。一位作者要在書法作品中,體現出真正的自我情懷,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在內涵與形式之中不斷地尋找與磨合,也在感情與理性的交織過程中慢慢自由化。我們對技法與風格的融合的最終目的,就是完成人書一體的大融合。這種融合的難度是我們當代書法家共同的難度,正如邱振中先生所說:“一個民族的文化始終是在變化,但現代社會由于交流傳播的便利,民族文化中增加了許多新鮮的東西,它們不能不影響到人們的精神生活,其中當然有不少浮泛的存在,但也不會不觸及深層的結構。書法中精神內涵與形式的調適本來就需要漫長的時間,現在加上‘日常書寫’的喪失而造成通路的堵塞,更是使新的精神內涵難以與形式發生作用。人們可以努力模仿前人的形式與生活方式,但難以恢復內心生活與技巧形式之間那種活生生的動態聯系。”我之所以大段地引用,是因為他表述準確,分析透徹。在這段文字里我們可以充分感受到人書融合的一種困難,但也是優秀書法家的一種目標。
當代書法在融合的道路上,我認為有三條路是可以走的。一條是邱振中先生自己指出:“現代書法創作的另一途徑,是設法接近現代意義上的藝術:把以人為核心改變為以作品為核心,追求作品形式構成的獨創性,承認評價標準的多元性(不再認為傳統評價標準是唯一的標準),從更廣泛的來源中汲取創作的靈感,(不局限于古典的書法杰作),這樣作品的形式構成處于突出的位置,從而對藝術家的想象力提出很高的要求”。
第二條還是傳統的路子,他們盡量尋找與古人相契合的一面,另一方面又在主體上選擇古人,在今人與古人之間建立一種默契的關系,于相對的時空意識、創作風范、生命情調等方面有了較深的理解,把握住人性中不變的美麗成分,使今日創作綿延并產生不盡淵藪,其實目前大多數作者走的還是這條路子。
但我認為第三條道路可能較為合適,建立新的表達機制,在傳統經典的作用下,培養敏銳的形式感受能力和表達能力,對不同筆法、線質、空間所帶來的一系列審美心理的反應與相對應的表達需要契合起來,讓書法家的創作表達不再是一種被動,可以根據作者的需要、作品的需要調整筆法、線質,甚至改進材料來改變單調的書寫習慣,使整個創作過程盡可能的自由,使作者在整個創作過程中都處于主宰的位置。不論走的哪條道路,書法家之所以是書法家,對表現能力的要求都放在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位置,只是在不同的道路上表現內容、表現方法的錘煉方式不同。
四、結語
我們今天的書法創作要深入挖掘傳統的精華,傳承民族文化基因,在傳承的基礎上寫出自己個人的情懷,這是任何一個有思想和抱負的書法家的追求。對書法在當代如何發展,今天的書法家應該多一種這樣的價值追問,多一些對技法對風格辯證的分析,在創作中多一些對復雜情緒的表達,以求得銳利思想能夠深入我們的精神通道,只有這樣的書寫,才堪稱是值得珍重的書寫。有這樣一句話:“一個人思想有多深,就意味著他最終能夠走多遠。”我深信著,并以此為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