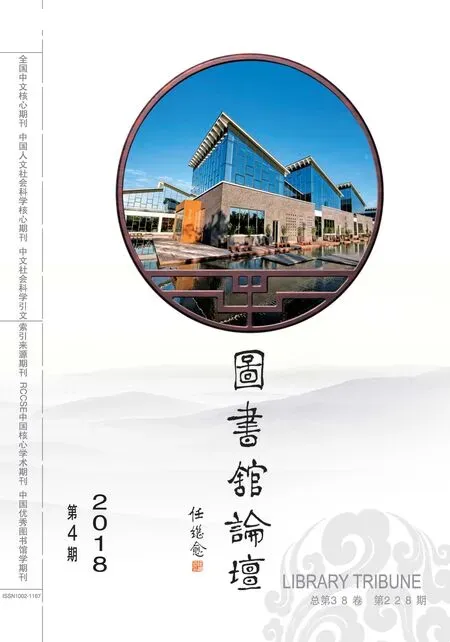圖書館支持數字人文研究進展
肖 奕
0 前言
數字人文與圖書館存在緊密的關聯。圖書館是數字人文項目孵化的場所,也是支持相關工作開展的重要機構,圖書館專業人員在數字人文工作中發揮引導作用,而非僅僅提供支持。隨著數字人文領域的不斷發展,這些專業人員成為與數字人文研究者同樣重要的參與者[1]。圖書館是數字人文學者獲取支持的重要平臺,人文學者需要借助圖書館的特色資源、專業團隊來開展研究,進行學術交流,推廣研究成果。
數字人文的興起給圖書館帶來轉變的機遇,圖書館管理者可利用數字人文的發展契機重新考慮資源建設、人員安排、服務創新等工作。數字人文的“模糊性”使圖書館可利用自身優勢,從研究、教育、館藏等方面對人文學科進行數字化引導,推廣數字人文及其研究成果[2]。反過來,數字人文并非整一規劃的,它不僅僅關乎一個領域、社群和系列的做法,更關乎以理念和技術為指導的多重方法,其下屬的各類項目能夠將圖書館的影響力擴展到新的領域。數字人文研究講求協作,但在工作中難以集中多個機構所需的資源與服務,因此較為可行的方式是利用圖書館的優勢,即提供技術與專業知識支持、提供知識發現的幫助和將學術社群聚集的能力,鼓勵學術社群在數字人文工作中開展合作[3]。
鑒于圖書館與數字人文的緊密關聯,以及圖書館在數字人文研究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有必要認識圖書館在哪些方面、以何種方式為數字人文研究和相關工作提供支持。本文以美國圖書館協會下dh+lib模塊的文獻資料為基礎,并以其他相關著作與資料作為補充,梳理圖書館為數字人文領域提供支持的方式及其成效,為我國研究人員了解該領域的研究現狀、開展相關研究提供幫助。
1 資源建設
為了促進數字人文工作的開展,圖書館需要從人文學者的研究需求出發,整合研究人員常用的資源,這些資源往往與研究團隊項目的主題相關。國外已有多個高校圖書館建設了特色資源,為本校的研究與教學提供支持。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圖書館特色館藏部收錄了大量的手稿、古籍和檔案,這些館藏覆蓋美國文學、書籍史、神學等多個主題[4],涉及特定的作者、種類,對人文學者具有特殊的研究價值。圖書館管理層應當在充分認識人文學科研究范式和方法的變化的基礎上,將數字人文研究者的需求納入特色館藏建設的考量中,更有針對性地建設館藏資源。
聯機計算機圖書館中心(Online Com puter Library Center,OCLC)的調查指出,圖書館可將數字人文研究者所用資源分為主要資源、數字資源和原生數字資源3類,用戶對每種資源的需求以及圖書館相應的建設方式如下[5]:(1)主要資源。研究者希望圖書館集成相關資源,以便從單個入口檢索多個語料庫;多數學者偏向自行獲取資源,包括書目、口述歷史內容、圖片等。管理者應圍繞研究者的需求建設館藏,特別關注他們對檔案和特色館藏的需求;(2)數字資源。人文學者希望大規模深入使用數字資源,管理者應安排研究者參與數字資源內容和格式的設計、館藏數字化和特色館藏甄選等工作;(3)原生數字資源。對于數字人文研究者而言,獲取原生數字手稿和電子文獻的訪問途徑非常重要,因此,圖書館應在采購原生電子文獻的同時注重收集和保存獲取這類文獻的鏈接。
大數據和信息技術的發展使人文科學有了新的研究對象,觸發圖書館將人文學科的數據納入館藏范圍并提供相關服務。北卡羅萊納大學教堂山分校社會科學館員S h a wg o認為,數字人文學者可在圖書館開展的研究包括GIS與數據可視化項目、數字人文數據管理與分析等[6]。人文科學數據的管理與利用成為圖書館與信息科學專業人員開展理論研究和實踐工作的重要領域。學者Padilla等論述了圖書館各類人文數據對數字人文研究的重要性,旨在提升人文數據的利用價值[7];指出這些數據能用于數據挖掘、可視化和生成新的研究對象等多個方面。通過開發相關應用,圖書館鼓勵學者與數據交互、下載數據并使用人文數據館藏;通過提供人文數據利用技能、工具和方法等方面的培訓,向用戶展示圖書館館藏的廣泛性,提升人文數據作為館藏的價值[8]。
項目成果和項目運營期間生成的資源,如數字資料、代碼、算法結構、軟件工具也可成為圖書館館藏。管理者應當對這些資源進行整合,協助研究者妥善保存數字人文研究成果。此外,研究項目團隊希望圖書館增加相應的元數據記錄服務,使項目成果和相關資源能為其他用戶發現、獲取和利用,擴大其項目的影響力。圖書館可向研究者提供基于專業優勢整理的二次文獻,幫助研究者獲取相關資源并推廣項目成果。通過文本挖掘、手稿識別和語義關系提取等方式,圖書館確保了研究者在獲取數字資料方面的權益,提升用戶對館藏的利用程度[9]。
2 教學參與
無論是教學團隊的組建、課程內容的設計,還是閱讀材料與服務的提供、課堂空間的安排,圖書館和館員都在數字人文教學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圖書館中的數字人文:學科館員的挑戰與機遇》(Digital Humanities in the Library: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Subject Specialists)一書介紹了圖書館與教師團隊合作開展數字人文教學的情況[10]。堪薩斯大學圖書館創建了以用戶為中心的服務模型來支持教師的研究與教學工作,為師生提供數字人文有關培訓[11]。在“數字人文導言”這個課程模塊中,3名學科館員與該校法語系教授、研究生主管共同設計有關研究方法的課程。其中,學科館員參與整個學期的教學工作,部分館員講授有關版權、特色館藏利用等方面的知識。除了介紹傳統的研究方法外,課程還關注對學生網頁開發、數字人文項目開展等實用技能的培養。
類似地,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數字人文課程的教學團隊成員包括中東地區研究員、藝術和建筑學專家、數字人文館員、程序員等[12]。在課程開設過程中,圖書館相關工作人員提供技術支持,學科館員成為擴展這一教學協作的關鍵成員。數字人文館員和1名教授共同設計學生的小組任務、課程大綱和課程結構(the logistics of the course,主要指課程開設地點和圖書館的資源類別),擁有藝術與建筑學知識背景的館員負責文獻版權狀態的評估方法、從出版商與作者處獲取版權許可的方法等課程內容。結果表明,不同學科知識背景的館員對教學的參與可幫助學生利用相關資源和方法,提升課程效果。教師們認為,在課程開展過程中,學生表現出樂于參與的意愿,對學術研究和交流有更為深入的認識,科研能力有了極大提升;館員的參與可使學生獲得與出版有關的實踐經驗、掌握相關技術并開展研究工作。教師對圖書館在數字資源整合、促進資源發現以及數字人文項目孵化方面的作用有了新的認識。
數字人文教學實踐的研究者認為,在館內開設數字人文課程對學生和圖書館都有益[13]。就學生而言,這種教學方式使其學會獨立獲取和使用資源的技能,掌握研究方法;主動學習,積極使用各種資源與設備,與專業人士開展協作。這一成效是數字人文專家在傳統課堂單獨授課的模式所無法實現的。圖書館可借助參與數字人文教學工作的契機,向學生展示其服務和資源,同時幫助館員參與數字人文的學術研究。
3 學術研究協作
數字學術與跨學科研究協作的發展、研究資料的數字化、數字工具和方法的應用等構成了圖書館支持數字人文工作的環境。圖書館(人)與人文學者平等地參與數字人文研究,成為重要的研究主體。Rockenbach指出,作為實施跨學科研究活動的場所,圖書館規劃了寬闊的空間用于研究者的協同工作,開發了相關應用和平臺為研究和教學活動提供支持[14]。館員應當掌握項目管理、人文學科環境掃描等技能,評估現有的服務以滿足用戶的需求;掌握支持數字學術研究的相關知識和技能,更好地認識研究者使用的數據資料和新型工具與方法[15]。
數字人文學者以項目為單元開展研究,圖書館和館員加入項目,參與研究工作。項目Webbs on the Web通過整理分析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部分手稿和書籍,研究19至20世紀政治、女性的社會角色及其與家庭的關系等多個問題[16]。該項目總結了圖書館和數字人文兩個領域專業人士共同工作的經驗[17],包括(1)館員和研究人員應當接受更多有關研究協作和跨機構工作的培訓;(2)項目團隊應將合作經驗形成文檔并將其公開,即使項目沒有達到預期效果,也可幫助其他團隊更好地開展研究協作;(3)對協作抱有合理的期望;(4)團隊協作時間跨度較大,團隊成員應抱著適度的耐心和輕松的態度參與研究。
魯汶大學館員兼藝術學院教師Verbeke從事文藝復興方面的研究,在研究中融入了數字人文要素并應用了相關方法。Verbeke與圖書館、檔案館和博物館等機構合作,這些機構通過承擔傳統的文獻保存、策劃、傳播和數字化的方式參與研究;研究者可從這些機構獲取文藝復興時期的資料,包括未被數字化的原始文獻和完全數字化的、可檢索和操作的語料庫[18]。圖書館通過提供研究所需要的資料、方法、工具和圖書情報專業人員協助,參與到數字人文研究工作中,與研究者共同發現和解決研究問題,構思項目創意并將其轉換為研究成果。
4 服務完善與基礎設施建設
在服務方面,圖書館應當關注數字人文學者的需求,在現有服務的基礎上進行創新。Schaffner等指出,研究型圖書館為數字人文提供的服務包括構建學術出版物的機構庫存儲空間、提供面向特色館藏利用的數碼相機、提供數據監管服務、協助制定數據管理協作計劃等,一種可行的方式是將這些服務進行整合并建立虛擬的數字人文中心[19]。Rockenbach介紹了Vinopal和M cCorm ick兩名學者創建的四級(four tier)數字人文服務模型,該模型旨在提供持續的可測量的服務,具有可保存、可測度、標準化等特點。Rockenbach認為該模型擴寬了圖書館服務的范圍,重新定義了館員的職責,要求其掌握新技能。館員角色的演變和服務范圍的擴展對圖書館參與數字人文相關工作的成功與否非常重要[20]。
無論是工具的學習與應用、項目的開展與運營,還是元數據的管理與使用、數字保存的實現,圖書館都應完善現有的信息基礎設施,為研究者利用資源、創建和推廣項目研究成果提供便利[21]。學者Mueller在科學信息研究所2017年信息科學與數字人文關系研討會上指出,手稿轉錄等工作需要專門設施提供支持,數字圖書館基礎設施可幫助研究者獲取文獻,為學術活動提供相關服務,因此,信息基礎設施建設應從數字人文研究工作的角度考量[22]。
圖書館應當完善相關基礎設施,但是否有必要專門設置數字人文中心則需深入考量。為了探究這個問題,彌補圖書館資源與服務和數字人文研究者期望之間的差距,了解圖書館為數字人文提供支持的方式,OCLC研究團隊從數字人文研究者的工作過程和需求出發,了解其工作內容、工作方法和所需幫助[23]。該團隊從多個方面介紹其研究發現。從機構角度來看,學術部門、信息技術部門、圖書館、國家數字基礎設施等組織和機構共同提供數字人文服務,對這一服務支持架構的調整可進一步完善數字人文服務,圖書館管理者可通過協調與信息技術中心的關系來擴大服務空間。OCLC的研究表明,若用戶需求較大,圖書館擁有足夠的資源,則由圖書館管理數字人文中心是最佳的選擇。就中心運營與中心員工構成而言,Rockenbach認為,數字人文中心通常位于圖書館內部或由圖書館運營,中心員工多為人文科學學者、網絡工程師和程序員,館員在大多數情況下僅承擔特定項目咨詢人員的角色而非全職員工[24]。
5 專業人員團隊建設
圖書館對數字人文的支持還應體現在專業人員工作內容創新和職業發展規劃方面。管理層應對館員角色進行重新定位,構建新型專業人員團隊。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圖書館數字人文興趣小組的3名成員對數字人文和數字圖書館領域的相關資料進行收集分析,提出了在數字人文與數字圖書館交互時代下圖書館人所應具備的多層次角色以及數字圖書館的發展方向[25],認為在數字人文項目中,館員扮演多重角色并發揮著不同作用。例如,(1)教育者。館員利用研討室和咨詢臺幫助研究者掌握數字人文工具、方法與技能。(2)協調者與解釋者。館員應掌握人文學科和信息技術的知識,了解相關技術術語。(3)主持者。館員管理著配備有各種設施和工具的物理和虛擬空間,用于數字人文教學研究工作和團隊建設活動。負責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歷史系、非洲研究中心和拉丁美洲研究項目之間聯絡工作的學科館員Vaidyanathan介紹了人文學科館員參與數字人文研究的三個步驟[26]:(1)掌握數字工具、跟蹤數字人文的發展趨勢并不斷提升自身技能;(2)尋求參與、協作和領導的機會;(3)評估當前工作并作出承諾,如花費更多時間學習新技能,為教師和學生提供更好的服務。
數字人文研究及相關工作的開展是協作性的,館員職能的發展還應基于其與數字人文教研團隊之間的關聯。密歇根大學圖書館構建了一種館員和數字人文學者的合作模式[27],其主要特點有:(1)驅動研究和學習的館藏。館藏是創造新知識的基礎,數字人文研究者可利用館員收集整理的不同類型的館藏資源開展研究;(2)驅動知識發現的專長和技術。圖書館提供學術研究所需設備,由館員協助學者將研究資源數字化,并剪輯視頻、開發網站等;數字人文學者關注文化遺產的保存、分析與呈現,在研究過程中可能會遇到研究資料碎片化、使用權利受限等諸多問題,館員應引導研究人員和教學人員使用紙質館藏和技術設施;(3)實驗能力。圖書館擁有用于數字人文項目開發與運營的館藏和技術,研究者可利用這些資源構思項目方案并開展創造性試驗;(4)促進跨學科研究。圖書館可向研究人員提供跨學科協作的機會,由館員培育采納新型應用的學術社群,幫助研究人員獲取跨學科的學術經驗和研究成果。這一模式有利于發展與完善館員和數字人文學者在學術研究與教學方面的協作。
數字人文研究和相關工作的開展通常牽涉到與圖書館和信息科學有關的一系列專業議題,包括數字學術、資源合理利用等,這些議題的詮釋與解讀應當由該領域的專業人員來開展。佛羅里達州立大學圖書館學術交流館員Vandegrift與埃默里大學學者Varner認為,館員對版權、合理使用等問題的清晰認識,對用戶信息組織和利用等問題的敏銳感知,以及其幫助研究者完成項目的職業熱情等是圖書館參與數字人文工作的優勢[28]。在館員的專業素養與能力方面,學者Little,圖書館是幫助項目團隊獲取專業人員支持的理想場所[29],數字人文項目在項目團隊、學科館員與技術專家的共同協作中才能得以良好運行;館員可基于個人需求,利用一定技能參與項目,從事推廣和聯絡工作,參與數字人文項目管理方面的培訓,更好地支持人文學者的研究工作。
6 學術成果的交流與傳播
圖書館為數字人文學者搭建學術討論與交流的平臺,策劃并組織研討會與學術講座,是積極推動數字人文領域研究成果廣泛傳播的重要機構。國內方面,北京大學圖書館在2017年4月13日正式開啟“北京大學數字人文工作坊”系列活動,介紹數字人文的概念、內涵、軟件應用實例等[30];并于2017年5月26日舉辦了第二屆北京大學數字人文論壇——“互動與共生—數字人文與史學研究”,邀請海內外數字人文學者進行理論探討,交流實踐動態,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31]。圖書館(人)是組織并推動數字人文學術成果交流與傳播的重要力量。
7 結語
人文學科教學和研究工作向數字人文的轉變給圖書館帶來了新的挑戰和機遇,使管理者重新省視圖書館(人)的角色與定位。作為孵化數字人文項目、幫助學者探索數字人文研究范式與方法的機構,圖書館應當充分發揮自身的優勢和功能,規劃并完善特色館藏資源,將人文數據、研究中產生的衍生品等納入館藏范圍;幫助館員掌握數字人文方法、技能和工具,安排專業人員加入教學團隊,開展數字人文教學等;履行支持學術研究的職能,作為研究主體之一參與到數字人文研究中;完善服務模式與服務類型,為數字人文研究提供支撐,積極建設基礎設施,參與數字人文中心的設立與運營;充分發揮自身促進學術交流與傳播的功能,擴大數字人文研究成果在社會上的影響力。
[1]IMLS.Libraries and museums advance the digital humanities:new grant opportunity[EB/OL].[2017-05-18].https://www.imls.gov/news-events/upnext-blog/2016/10/libraries-and-museums-advance-digital-humanities-new-grant.
[2]HIGGINS D.Openly uncertain,certainly open[EB/OL].[2017-05-15].http://acrl.ala.org/dh/2013/06/19/openly-uncertain-certainly-open/.
[3][27]ALEXANDER L,Beau Case,Karen Downing,et al.Librarians and scholars:partners in digital humanities[EB/OL].[2017-05-15].http://er.educause.edu/articles/2014/6/librarians-and-scholars-partners-in-digitalhumanities.
[4]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Special collections[EB/OL].[2017-06-26].https://www.library.wisc.edu/specialcollections/collections/.
[5][19][23]SCHAFFNER J,RickyErway.Doeseveryresearch library need a digital humanities[EB/OL].[2017-05-15].http://www.oclc.org/content/dam/research/publications/library/2014/oclcresearch-digitalhumanities-center-2014.pdf.
[6]SHAWGO K.CFP:data driven:digital humanities in thelibrary[EB/OL].[2017-05-15].https://www.hastac.org/opportunities/cfp-data-driven-digital-humanities-library.
[7][8]THOMAS G Padilla,HIGGINS D.Library collections as humanities data:the facet effect[J].Public Services Quarterly,2014,10(4):324-335.
[9]LEONARD P.Digital humanities in and of the library[EB/OL].[2017-05-15].https://liber2016.org/wpcontent/uploads/2015/10/1100-1130_Leonard_Digital_Humanities_In_and_of_the_Library.pdf.
[10][11][12][13]HARTSELL-GUNDYA,BRAUNSTEINL,GOLOMB.Digital humanitiesin the library: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subject specialists[M].Chicago:ACRL,2015.
[14][15][20][24]ROCKENBACH B.Digital humanities in libraries:new model for scholarly engagement[EB/OL].[2017-05-15].https://academiccommons.columbia.edu/catalog/ac:156033.
[16][17]FAY E,NYHAN J.Webbs on the web:libraries,digital humanities and collaboration[J].Library Review,2015,64(1/2):118-134.
[18]VERBEKE D.Renaissance studies,digital humanities and the library[EB/OL].[2017-05-15].http://www.northernrenaissance.org/renaissance-studies-digitalhumanities-and-the-library/.
[21]楊滋榮,熊回香,蔣合領.國外圖書館支持數字人文研究進展[J].圖書情報工作,2016,60(24):122-129.
[22]MUELLER L.Towards information science services: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he digital humanities:ISI 2017 SatelliteWorkshop on theRelationship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he Digital Humanities[C].Berlin:Humboldt-Universit?t zu Berlin,2017.
[25]Zhang Y,Liu S,MATHEWS E.New roles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professionalsin the convergence of digital humanities and digital libraries: An Exploration:7th Shanghai International Library Forum[C].Shanghai: Shanghai International Library Forum,2014.
[26]VAIDYANATHAN C.Three steps for humanities subject librarians interested in[EB/OL].[2017-05-18].http://acrl.ala.org/dh/2013/06/19/three-steps-forhumanities-subject-librarians-interested-in-dh/.
[28]VANDEGRIFT M,VARNER S.Evolvingincommon:creating mutually supportive relationships between libraries and the digital humanities[J].Journal of Library Administration,2013,53(1):67-78.
[29]LITTLE G.We are all digital humanists now[J].The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anship,2011,37(4):352-354.
[30]北京大學新聞中心.圖書館舉辦第一期“北京大學數字人文工作坊”[EB/OL].[2017-08-09].http://pkunews.pku.edu.cn/xwzh/2017-04/18/content_297484.htm.
[31]北京大學圖書館.數字人文論壇通知:互動與共生-數字人文與史學研究[EB/OL].[2017-08-09].http://www.lib.pku.edu.cn/portal/cn/news/00000014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