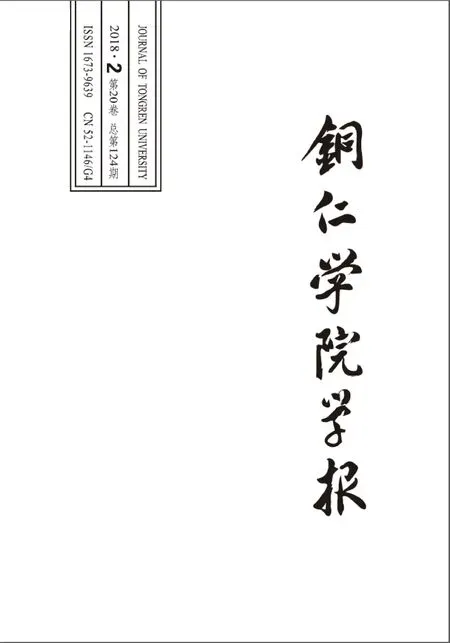經學傳統與回歸經典
范子燁
( 中國社會科學院 文學研究所,北京 100732 )
《詩經》的出現,如同一輪驕陽,照徹了東方詩國的廣宇。大化流衍,江山代謝,世事紛紜,其永恒的經典意義未嘗改變,就像《圣經》對西方一樣。華夏詩史的歷程盡管千變萬化,其根本還是在于《詩經》。故自古至今,《詩經》學也一直蹲踞經學的主流地位。劉毓慶教授在這一研究領域貢獻卓著,世所共知。而本期“梵凈古典學”推出的《〈爾雅〉的出現與〈詩經〉詮釋學的產生》一文,則是他近年來的一篇力作。該文之要旨,在于還原《爾雅》的學術思想體系。文章指出,《爾雅》是詮釋《詩》《書》語匯的先秦古籍,其中釋《詩》猶多,實堪稱《詩經》學史上的第一部詮釋著作。該文將《詩經》的語匯,根據其意義,構建起了以人為中心的世界結構秩序:《釋詁》《釋言》《釋訓》,解釋已內化為人的基本能力的一部分的語言詞匯;《釋親》《釋宮》《釋器》《釋樂》,解釋因人而構成的人際關系與人所創造的日用器具;《釋天》《釋地》《釋丘》《釋山》《釋水》,解釋人類活動的空間舞臺;《釋草》《釋木》《釋蟲》《釋魚》《釋鳥》《釋獸》《釋畜》,解釋人類物質生活需求的資料來源。作者著重指出,這四部分有秩序的結構形式,深刻反映了先秦儒家以人為本的哲學思想,同時也構成了最早的《詩經》詮釋學的主要內容,奠定了《詩經》詮釋學的基礎,明顯存在著將詩學意義上“詩三百”“經學化”的趨向。作者也指出了《爾雅》自身存在的問題,這些問題當然是由其成書過程的“層累性”造成的。平正、大氣、嚴密,富有創見,是該文的突出特征,非常值得青年學者學習。
郭萬金、艾冬景所撰《清季民初經學生態淺議》一文,似乎是以某種方式呼應毓慶教授的研究。在我國盛行兩千余年的經學,在中西文明大撞擊的文化背景和中華民族危機空前的社會背景下,隨著文化生態和社會生態的變化,終于退出了主流地位,失去了往日的宗主身份,成為史學的附庸。本文追尋了這一文化現象發生的始末,揭示了其深層的歷史動因。作者指出,受“存學救國”意識和中華傳統的積極入世觀念的影響,學術“致用”成為清季民初學術研究的主要原動力,在此背景下,傳統經學也嘗試著開始其向現代轉型的艱辛歷程。正如王先明所言,“每一種學術文化思想主潮,通常都規劃和體現一個時代社會歷史運行的歷程與走向。學術文化主潮生命力的長久與短暫,并不僅僅取決于學術文化本身的成熟與完美,而從根本上受到社會生活需求的制約。大體不變的學術文化正是大體停滯著的社會生活的精神世界的模型化。但是,無論一個民族的歷史多么久遠,文化積淀多么厚重,一旦其社會生活本身發生根本性變革,它的學術文化主潮的內容及其走向都將發生前所未有的變遷。”歷史是殘酷無情的,但歷史本身也并不代表著真理。1818年10月22日,黑格爾在就任柏林大學教授的講演中說:“在短期前,一方面由于時代的艱苦,使人對于日常生活的瑣事予以太大的重視,另一方面,現實上最高的興趣,卻在于努力奮斗首先去復興并拯救國家民族生活上政治上的整個局勢。這些工作占據了精神上的一切能力,各階層人民的一切力量,以及外在的手段,致使我們精神上的內心生活不能贏得寧靜。世界精神太忙碌于現實,太馳鶩于外界,而不遑回到內心,轉回自身,以徜徉自怡于自己原有的家園中。現在現實潮流的重負已漸減輕,日爾曼民族已經把他們的國家,一切有生命有意義的生活的根源,拯救過來了,于是時間已經到來,在國家內,除了現實世界的治理之外,思想的自由世界也會獨立繁榮起來。”(《小邏輯》,賀麟譯,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第31頁)我特別欣賞、贊佩“世界的治理”與“思想的自由世界”這樣的說法。也就是說,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發展需要依賴于現實的世界,與此同時,還要保持精神世界的獨立,積極致力于精神領域的建樹。當然,黑格爾無論多么深刻,都料想不到馬克思主義會取代盛行于東方大地兩千余年的經學思想,而卡爾·馬克思乃是他的后學。現實的需要似乎總是高于一切的。這篇論文很值得我們回味。
在《絕代豐華:楊氏豐華堂藏本〈陶淵明集〉三種批語輯考》一文中,劉叔明先生首次披露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圖書館所藏三種特殊的《陶淵明集》:兩種《陶靖節集》,一種為萬歷丙子周敬松刻本,另一種為嘉靖刻、諸福坤手校本;而《陶淵明詩》,則是清仿宋刻本。叔明發現,這些陶集本屬于民國時代豐華堂之舊藏,集中附錄的前人批語對研究陶淵明具有重要意義。同時,這些陶集對研究我國古代書籍文化史和陶淵明傳播史也具有重要意義。而這些陶集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圖書館,與西南聯合大學及其經歷的特殊慘痛事件可能有密切的關系。經歷了戰火硝煙,這些陶集給人帶來的是沉重,而不是輕松。文章指出,一個國家或一個民族在創造輝煌的文化的同時,必須同時注意培養保護這種文化的能力,否則,一切都可能化為劫灰。字里行間飽含作者對歷史的深深憂思。
《文選》是我國中世紀的寶典,《文選》學素來是我國學術界之顯學。在擺脫以清洗“選學妖孽”為旨歸的反選學運動以后,自1980年以來,選學的熱潮日益高漲。選學耆宿和選學新人交相輝映。為扶植選學新秀,我們特別推出在讀博士生馬朝陽的《〈文選〉的編撰意圖》一文。就此選題而言,確能夠深化我們對蕭統的了解以及對《文選》成書、選錄標準等多方面問題的認識。對此,前人多有討論,但本文進行了最為全面的論析。作者認為,《文選》是蕭統主編的體大慮深的泛文學總集,不僅反映了蕭統的思想與文評觀念,也反映了蕭統“化成天下”,鞏固統治,匡正文壇乃至意欲流芳千古的編纂目的。這些觀點都是依據文獻作出的合理推斷。過去的選學研究,很大程度是以相關的版本學研究為核心的,今后的發展方向應該是解讀《文選》收錄的作品。因為在《文選》初成之際,并無所謂《文選》版本學,當時的人所看重的就是書中選錄的作品。隨著各家注本的出現以及宋代的大量刊刻,《文選》版本學才日益凸顯其重要性。因此,我們重視作品,就是對《文選》本旨的回歸。這也是朝陽撰寫此文的一個出發點。就作品而言,選學的空間是無限廣闊的。而根據我的了解和判斷,當代世界的選學家們,根本沒有一個人能夠把《文選》全部講明白。主要原因在于,《文選》選錄作品的標準,除了政治、文學等方面的考量之外,還有一個文化標準。譬如,蕭《選》中有大量作品涉及音樂歌舞,如馬融的《長笛賦》、潘岳的《笙賦》、嵇康的《琴賦》、成公綏的《嘯賦》等等,如果不了解笛、笙、琴、嘯,那么,這些作品根本就是讀不懂的。這也是當今治選學者的最大障礙。
無論如何,追尋經學傳統,回歸傳統經典,在我們時代都具有特殊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