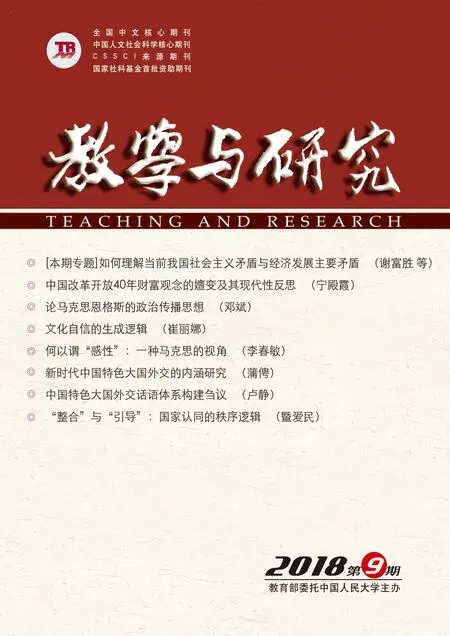從意識形態到知識介入:當代西方學界知識分子研究視域的歷史演變*
,
20世紀以降,知識分子長期是社會學、政治學等學科研究的重要領域,受到曼海姆、布迪厄、鮑曼等諸多學術大家的密切關注。圍繞知識分子的內涵、知識分子的社會政治功能、知識分子與國家及公眾關系等眾多問題,思想界爭鳴不斷,也形成了眾多理論流派與學術主張。細致梳理20世紀以來關于知識分子的理論研究可以發現,人類從工業社會向后工業社會的歷史轉型,成為西方學界知識分子研究的分水嶺,其研究視域及分析視角凸顯出鮮明的古今之別。
一、知識分子內涵的多維解讀
現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intellectuals)最早出現于1898年的法國德雷福斯事件。在該事件中,作家左拉發表了《我控訴》,被反對者斥之為“知識分子”,自此,該術語在歐美社會中得到廣泛使用。[1](P30-32)然而,知識分子的概念缺乏統一連貫性。一方面,雖然它產生于19世紀末,但學者們對這個術語的使用并不局限于現代社會。例如,勒佩尼斯(Lepenies)將文藝復興以來的思想家合稱為知識分子,[2]中國儒家文化中的“士”亦被視為與知識分子有共通特質,甚至被稱為古代知識分子。[3]另一方面,在不同文明和國家中,知識分子的概念所指也存在差異。比如,俄語中與知識分子相近的知識階層(intelligentsia)概念主要指世俗化、受到西式教育的精英并且與當權者存在距離、對時政的批評者。[4](P487-502)而德語中的intelligenz則特指中產階級中受過高等教育的文化人士。[5](P81-82)面對多種語用學意義上的應用,許多研究者試圖剖析出知識分子的本質特征,產生了數十乃至上百種定義。為便于澄清,當下學界對知識分子概念內涵的界定可從職業功能、心理動機、行動場域三個維度展開。
(一)職業功能維度下的知識分子
社會學家希爾斯(Shils)指出,“每個社會都有少數人比他的同胞更為強烈地沉浸在各種象征符號之中……這標志著知識分子的存在”。[6](P4)馬克思(Marx)也表達了類似的功能性觀點:知識分子與其他人的區別在于前者從事的是一種腦力活動而非體力活動。[7](P1-10)史密斯也認為知識分子是創作藝術作品和生產思想的人。[8](P93)李普塞特(Lipset)則按照職業分工的不同,將知識分子用“中心—邊緣”模式予以表述:知識創造者,包括學者、藝術家、哲人、作家,他們構成了知識分子群體的核心;知識傳播者,包括教師和記者等中介群體;知識應用者,包括律師、醫生、工程師等專業人士。[9](P460)可見,社會功能維度下對知識分子的界定重點關注知識分子所屬的社會系統。從該視角出發,社會被區分為政治、經濟、文化等具有不同功能的子系統,知識分子則活躍于文化子系統中,以文化生產和傳承為職業,承擔著塑造社會價值符號的功能。
(二)心理動機維度下的知識分子
以心理動機為出發點界定知識分子的定義具有濃厚的規范主義色彩。該維度認為,知識分子是什么取決于知識分子應當是什么。[10](P187)以此標準考量,在道德層面,知識分子應是善良、公正、同情等倫理價值的捍衛者。正如班達所說,知識分子構成了人類的良心,像蘇格拉底、伏爾泰、斯賓諾莎這樣追求永恒真理與正義的人才可稱為知識分子。[11](P78-144)喬爾(Joll) 也認為知識分子的角色就是承擔蘇格拉底式“牛虻”的作用。[12](P23-31)哈維爾(Havel)則寫下,“知識分子,要不斷見證這個世界的苦難,他們是對權力魔咒的懷疑和批判者”。[13](P16)在行為動機層面,知識分子的首要素質則應是保持冷靜理性的科學價值。如羅素(Russell)認為,知識分子就是以事實為依據提出自己觀點的人。[14](P493-495)康納利(Connolly)也認為知識分子即“獨立思考的人”。[15](P164-165)亦有學者如薩義德(Said)把兩種價值結合起來,認為知識分子是社會流亡者、邊緣人,他們應敢于對權勢說真話。[16](P6)科塞(Coser)也持類似看法,指出知識分子雖自命為捍衛道德的衛士,卻也非狂熱分子而傾向于形成理性批判態度。[17](P3-5)總之,對社會道德總體關懷和求真的科學精神是心理動機維度下知識分子群體的核心特征。
(三)行動場域維度下的知識分子
持此種視角的學者以主體的行動場域與影響對象為標準界定知識分子的內涵,認為知識分子是邁出私域、參與公共政治生活并具有影響力的人。以此觀之,知識分子就等同于公共知識分子。從詞源上看,誕生于德雷福斯事件的知識分子這一概念本身就是在公共領域的語境中被“創造”的。由此,是否在公共領域具有話語權成為知識分子判定的另一準繩。艾爾曼(Eyerman) 把知識分子定義為公共話語中的思想表達者。[18](P455)夏爾(Charle)則認為知識分子是介入到政治事務中的學者或作家,他們聲稱其觀點具有權威性。[19](P209)按照波斯納(Posner)的看法,知識分子是就公共問題面向社會公眾寫作的人,其對象不局限于同行和專業學者。[20](P21-23)在此,行動空間局限于專業圈的學者被排除在知識分子的群體之外。
上述三種維度代表了學術界關于知識分子內涵的基本界定方式。許多研究或采用一種維度,或對多種維度進行綜合以形成復合性的知識分子概念。多維的內涵反映出知識分子概念并不具有先驗的共性特征。這也印證了鮑曼(Bauman)的觀點,即對知識分子的任何定義都是一種自我界定(self-definition),因為它試圖在“我們”(知識分子)和“他們”(非知識分子)之間劃出固定的邊界,未注意到邊界只能是相對的。[21](P117-137)基于知識分子概念的流變性,以研究視域和路徑梳理海外學界關于知識分子的研究歷史可以發現,知識分子研究可以分為工業化背景下的傳統知識分子研究和后工業時代背景下的知識分子研究兩個階段。傳統知識分子研究受到道德動機和公共性維度下知識分子內涵的強烈影響,其研究視域集中在與政治、道德、社會運動等密切相關的意識形態領域;當代知識分子研究受到后工業時代背景的影響,面對知識分子社會角色日趨多元、分化和復雜的社會現實,著重從知識分子的社會功能視角出發,其研究旨趣逐漸從內在性意識形態轉移到行為導向的知識介入。
二、傳統知識分子的研究視域:意識形態及其影響因素
(一)傳統知識分子意識形態研究的緣起
如前文所述,以智識性的文化生產為志業,以道德價值為動機,以影響公共生活為導向構成了知識分子的多維內涵。這意味著知識分子既擔負著認識世界的天職,又有著改變世界的傾向。作為傳統研究的主題,學者們對知識分子意識形態的重視具有深刻的社會歷史原因。一方面,自啟蒙運動與法國大革命以降,文化觀念等象征性符號改變世界的能量大為增強,知識分子作為意識形態的創造者,其社會動員能力迅速提升,積極運用其價值觀念影響和改變社會現實,不再是公共事務的旁觀者。另一方面,20世紀初的歐洲社會深陷現代性矛盾的泥潭,社會意識形態愈發分化,知識精英的觀念上也體現為空前對抗性,不僅存在傳統的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之爭,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種族主義、民族主義,形形色色的左派和右派相繼登上政治舞臺。在這種情況下,知識分子內部互相競爭文化領導權,意識形態的相互斗爭成為此時歐洲文化場域的重要現象,從而為意識形態研究提供了充足且豐富的研究素材。
在上述背景下,傳統研究著眼于描述知識分子意識形態與政治權威的關系,知識分子效忠于誰、[22](P117-137)信奉何種主義、是舊秩序的捍衛者還是革命者等議題成為研究焦點。例如班達發現,法國知識分子的政黨化程度越來越高。出于知識分子應當關懷普世價值的道德初衷,他斥之為“知識分子的背叛”。[11](P78-144)葛蘭西運用“有機知識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s)概念把知識分子視為不同利益集團的代言者。[23](P743-744)科塞則區分了知識分子與權力機構的五種組合關系:掌權的知識分子、掌權者的顧問、權力的合法化者、權力的批判者以及忠誠于外國者,闡釋了他們差異性的政治立場。[17](P147-158)由此可見,由于知識分子紛紛借助意識形態以左右政治,且內部對立嚴重,意識形態逐漸成為理解政權更迭的重要窗口,進而奠定了它在傳統研究領域中的核心地位。
(二)傳統知識分子意識形態研究的兩種分析路徑
以知識分子意識形態光譜的勾勒和描述為基礎,解釋這種差異、分析知識分子意識形態的生成機理與影響因素成為重要議題。在此,古典社會學在結構制約和個體能動性的方法論對立,也反映在了知識分子研究領域。一種是將結構主義應用于社會研究,即分析社會結構。[24]另一種則是從象征符號出發,分析歷史傳統對意識形態的塑造。
1.社會結構分析路徑。
社會結構分析強調宏觀結構對個體意識形態的制約乃至決定作用,其中關注最多的當數馬克思提出的階級結構。依此路徑,學界關于知識分子階級屬性對意識形態的塑造存在如下兩種看法:一是階級依附論(class-bound),二是階級自成論(class-in-itself)。[25](P63-90)階級依附論以馬克思主義者為代表,強調經濟關系、階級屬性對主體意識的約束。其代表人物葛蘭西認為,工業資本主義在創造自身的同時,也生產出了技術人員、政治經濟專家、新文化的組織者等等,這些依附性的知識分子被他稱為“有機知識分子”。[26](P35-48)不過,階級依附論并非完全取消個體能動性。馬克思本人指出:統治階級的小部分人會摒棄落后的意識形態而加入到革命階級。[27](P56-57)因此,依附論并未否定意志自由,但它認為意識形態總歸要附屬于經濟關系,不能超越于階級而存在。
以新階級理論家為代表的階級自成論則認為知識分子本身就是獨立的階級。古德曼(Gouldner)提出,科學專家和技術占有者正在形成一個新階級,試圖以文化資本取代舊資產階級的物質資本,與政治權力合流。[28]然而,新階級內部關于新階級究竟應指哪些知識分子群體并未達成共識。埃倫賴希(Enrenreich)、拉德(Ladd)、古德納、克里斯托(Kristol)對新階級都給出了自己的定義,上述學者在教育程度較低者、人文知識分子、技術專家、職業經理人等群體是否屬于知識分子階級這一問題上爭執不休。[29](P30-71)新階級論在提出后飽受爭議,關于知識分子是否是一個獨立階級這一問題依然懸而未決。
然而,將意識形態與階級綁定的研究忽視了社會環境的復雜性。曼海姆(Mannheim)對此批評道,盡管知識分子天生被嵌入了階級結構,但教育可以使得他們從初始結構中解脫出來,形成公正性的觀點,使之關注社會的整體利益,從而具有“自由浮動”(free-floating)的特質。[30](P91-170)這一論斷也得到了帕森斯(Parsons)的支持,他認為知識分子對文化功能的專注可以使之從其他世俗責任中得以解放。[31](P3-26)在這種批評下,也陸續有學者引入其他結構變量。例如,巴巴咖利(Barbagali)從市場供求的角度指出社會職業的供大于求可能造成知識分子的生產過剩(overproduction),進而形成他們的社會挫折感和激進傾向。[32]以布里姆(Brym)為代表的“社會依附論”,則認為知識分子的政治態度既非自由浮動也非由階級給定,而取決于他們所處的具體情境。除階級外,族裔、宗教、代際結構都應當成為備選要素。[33](P62)雖然同屬外部決定論,但上述研究解釋變量逐漸多元化,揭示了社會結構對知識分子意識形態塑造的多維層次。
2.歷史傳統分析路徑。
歷史傳統分析路徑則更具個人主義方法論色彩。此類研究以知識分子思想生產與創造這一活動為出發和落腳點,考察其意識形態產生、形成、發展的傳統淵源,提倡思想史和觀念史分析、文本分析、譜系學等方法,在分析取向上強調對于話語符號意義的理解。
遵循歷史傳統研究進路的學者認為知識分子的獨特活動就是對以往思想進行系統性學習,其意識形態的生成需要借助已有的價值觀念作為基礎。因此,思維傳統、文化淵源、學術與觀念的交流互通等成為值得關注的變量。希爾斯認為,西方知識分子主要存在五種意識形態傳統:科學主義傳統、浪漫主義傳統、革命傳統、民粹主義傳統和反智主義傳統。[6](P18-26)以賽亞·伯林(Berlin)通過文本分析發現,德國文化特別是浪漫主義對俄國知識分子產生了深刻影響,成為俄國社會批判的思想來源之一。[34](P138-177)李普賽特則通過比較美國和歐洲的文化,指出美國短暫的歷史及開國以來精英的平民主義精神,使得知識分子缺乏在歐洲顯現出的保守主義傳統和社會優越感,進而構成了美國左翼思想的來源。[35](P460-486)雷蒙·阿隆(Aron)則借用“神話”這一概念來解釋“何以馬克思主義在法國這樣一個經濟結構已不符合其預言的國家會重新流行?”發現三種神話起到了催化作用:第一,法國大革命的神話。即理性主義的神話,認為人類的智力能夠建造出理想之國。當代革命的概念表達了一種對大革命的懷舊。第二,無產階級的神話。他們渴望的“理想的解放”根植于基督教的救世理想。第三,歷史偶像崇拜的神話,包括對圣人、歷史決定論和必然性的信仰。[36](P1-199)希爾斯的學生艾森斯塔德(Eisenstadt)則試圖突破對單一意識形態的剖析,指出傳統規范的內在特質——特別是它多大程度允許改變,是對知識分子政治立場產生影響的重要變量。[37](P1-19)
總體來看,歷史傳統路徑關注文化、傳統等抽象符號,引入時間變量,以此分析各種意識形態的承繼、變遷和革新,這種研究視角多用于對不同國家、地區知識分子意識形態的差異分析。同時,它也未忽略個體的能動性,而把意識形態視為原有價值體系和知識分子主體思維互動整合的結果。
三、知識如何介入社會生活:當代知識分子研究的重心
20世紀后期,第三次科技革命的興起標志著人類開始邁入知識社會。隨著實用主義和專業知識逐漸取代了抽象的整體性知識,作為一項社會資源,知識越來越多地被視為一種能力(capacity),而并不必然和社會身份捆綁在一起。隨著知識在社會發展中的意義和地位急劇變革,知識分子的社會功能也發生變化。如果說,知識分子在工業社會還只是由作家和學者組成的小圈子的文化階層,那么它的當代用法無疑涉及更多的群體,包括學者、知識產權的所有者甚至很多網絡媒體人士。 至此,以知識分子群體為出發點的本體性研究的意義和可行性逐漸減弱,知識介入(intellectual intervention)提供了新的研究視域。埃亞勒(Eyal)聲稱,“知識分子社會學應向介入社會學的方向轉移。”[38](P117-137)從對象上看,知識介入和傳統研究的本質區別在于后者的研究對象是意識,而前者是行為。知識介入對知識分子行動的場域、策略、影響效能等議題的關注逐漸成為學界研究的重心,也形成了場域理論、網絡分析、定位理論等方法路徑。
(一)場域理論
場域理論側重從中微觀層面分析知識分子行為的發生環境,在一定意義上是結構路徑的拓展。布迪厄是場域理論的集大成者。在他看來,社會空間中存在著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式各樣的場域。在知識分子問題上,布迪厄既不把知識分子視為一體化的階級,也沒將他們視為 “自由浮動者”,而認為他們具有自利性,相互競爭著可以轉化為其他資本形式的文化資本。以場域作為分析空間,學者們關注不同場域、場域中的不同位置、場域環境的變化對知識介入的影響。納坦森(Natanson)通過對《法國世界報》專欄文章的分析,發現知識分子的公共寫作存在專業結構上的差異,作家和大學教授居多,而歷史學、政治科學家高于心理學家和經濟學家。同時,學術領域和公共領域中象征資本的獲得方式存在矛盾:即學術資本的提升要求專業性寫作,而專欄寫作要求通俗性話語,立基于價值中立(承諾)、內容專業性(大眾化)兩個維度,他區分出了四類知識分子角色。[39](P173-193)賴克曼(Reichmann)則突出了學術場域對行為效果的作用,指出導致哈耶克(Hayek)和拉扎斯菲爾德(Lazarsfeld)公共影響力不同的最重要自變量在于兩人不同的研究領域。[40](P243-261)斯沃茨(Swartz)則以布迪厄本人為對象,發現布迪厄在知識場域中地位的上升,以及舊有領袖福柯的早逝、大眾媒體的興起等知識場域內部的變化共同促使他成為公共抗爭的新一代領導者。[41](P791-823)盡管場域理論對知識分子行為的分析沒有脫離結構的關照,但他們所描繪的場域是一種關系性空間,這一分析路徑更為豐滿而現實,為經驗研究提供了有用的框架。
(二)網絡分析
與場域相關但又存在區別的是網絡分析方法。布迪厄的場域論一方面闡述了行動者在場域空間中的差異性,另一方面也寄希望于知識分子的集體行動以維護其自主性,這也為網絡分析提供了啟示。在這種視角下,知識介入是由知識分子所在的網絡促發的,網絡不僅存在于知識分子群體內部,也高于其所在場域,知識分子僅僅是網絡中的一個要素,其活動需要與外部行動者建立合作性的網絡節點(network nodes)完成。例如,埃亞勒有力說明了諸如GDP等國家經濟指標的設置與出臺,本質上屬于一種知識介入方式,而這依賴于一個由跨學科專家、企業、社會組織、政府組成的制度化交流網絡。[42](P220-253)網絡分析也促成了知識共同體概念(intellectual community)的形成。在知識共同體情境下,知識介入可以以跨領域、跨地域和集體式的方式呈現出來。在此,網絡分析特別適合解釋智庫等新興機構以及新媒體時代的知識介入方式。例如,菲蓋拉斯(Figueiras) 發現互聯網溝通了專家、同行及公眾、形成了智力交流的合作網絡,發揮了類似十八世紀沙龍的作用。[43](P145-160)奧斯登(Oslender)也指出新媒體建構了新的網絡關系,產生了世界社會論壇(world social forum)等組織,意味著知識的集體生產甚至跨國介入成為可能。[44](P508-509)鮑爾(Ball) 則分析了英國政策網絡(policy network)的形成,詳細繪制了智庫之間、智庫與高校、智庫與政府部門之間的網絡關系地圖。[45](P151-169)概言之,網絡分析以平等性否定了中心性,以合作替代競爭,拓撲結構取代線性結構,意味著知識介入并不是由知識分子單獨完成的,而是在各種社會因素的聯系作用下形成的,從而徹底顛覆了知識分子研究的主體性思維。
(三)定位理論
近年來,以劍橋大學巴爾(Baert)教授為代表的定位理論(positioning theory)逐漸興起,成為當代知識分子研究的新領域。奧斯丁(Austin)指出,一類語言,例如承諾、贊美等,它們屬于“述行命令”(performative utterances)的范疇,不是用于描述世界,其本身就在改變世界。[46]依此邏輯,以語言符號為載體的知識并不是對客觀世界的反映,其本身就會產生影響,知識介入的后果就在于必然會產生定位,即將相關特征賦予某個主體或群體。例如,行動者被視為左派還是右派、觀點深刻還是膚淺等。
以定位理論考察知識的生產過程可以發現,平臺、策略、語言修辭甚至個體身份等諸多具有符號象征性的事物都會影響知識介入的狀態和方向,影響公眾對知識的理解和評價。例如,書籍的類別、出版商、作者生平及封面導語都可被視為定位要素,因為它們為讀者提供了額外的符號意義,在閱讀之前就引導著讀者的選擇。在此,定位顯然不是主觀的,也不能完全化約為場域中的競爭文化資本,定位的供給來自于社會通行的價值文化系統,因此,解釋定位要素的社會符號意義就成為理解知識生產與介入模式的關鍵。例如,知識分子通過國家電視節目、官方出版物表達觀點,容易被定位為官方代理人,而選擇非制度化的媒介例如博客則具有更少的權威暗示和更多的平民性和個體性,從而對觀眾產生不同的介入影響。其中,巴爾尤其強調新媒體的作用——它的即時性、互動性極大改變了傳統定位要素的語境和形式。[47](P304-324)
定位理論的獨到之處就是它重視定位要素的選擇,重新復興了符號分析,闡述了知識介入與文化政治情境之間的密切關系。[48](Pvii-xi)它提出:定位既是普遍的又是情境性的,知識介入的模式、知識的接受與擴散并不完全取決于知識的內在價值,也受制于用以定位的話語和情境符號代表的意義,從而在微觀層次深刻探討了知識介入的發生環境。
通過對西方學界知識分子研究歷史的梳理可以發現,百年來,西方學界對于知識分子研究的重心由分析知識分子的意識形態逐漸轉變為知識介入。如表1所示,縱軸代表視域的流變,橫軸代表兩種基本性的分析視角。稍加分析不難發現,古典社會學的基本分析方法:即重視結構的外在性路徑(如涂爾干和帕森斯)以及重視個體能動性的內在性路徑(如韋伯)在知識分子研究中都有所呈現。結構分析和符號分析代表著上述兩種視角,并且隨著知識分子研究的不斷深入,兩種研究方法都得到了極大完善。一方面,傳統結構分析不論是階級決定論抑或多元決定論,關注的是宏觀和靜態性結構,認為知識分子意識由社會和經濟等因素所限定,忽視了日常生活對意識形成的意義。盡管研究對象不同,但當代研究則借助場域和網絡分析,從宏觀結構擴展到中微觀結構,從靜態結構轉移到以關系為基礎的交互性結構,更為完整地揭示了外部環境與知識分子的互動關系。另一方面,傳統符號分析集中于對知識分子書寫文字等話語符號的闡釋,通過話語分析勾勒出思想脈絡。定位理論則擴展了符號的“分析池”,彌補了傳統分析對情境符號的忽視。情境符號和話語符號相結合有助于還原知識分子試圖建構的完整意義圖景。
四、知識分子研究視域變遷的現實背景與文化動因
通過前文可知,傳統知識分子的研究視域主要圍繞觀念層面的意識形態,當代研究不再過多關注知識分子的本質屬性和內在世界,而試圖回答知識分子如何將其智力勞動外在化,采取何種行動影響他者和社會。實際上,知識分子研究視域的轉型內在隱含著不同歷史時期學界對知識分子社會角色與影響力的不同預設。具體來看,在傳統研究中,學界對知識分子的社會角色有著一定共識,對知識分子的動員能力也有著肯定性判斷。而以“知識介入”為核心的當代知識分子行為研究則內在蘊含著如下預設:首先,知識分子的群體邊界并不固定;其次,知識分子的功能角色日益多元;最后,知識分子對公眾的影響力并非一成不變。因此,從社會和文化變遷上看,當代知識分子研究視域及理論預設的演變具有一定必然性。
(一)社會經濟文化的變遷侵蝕了知識分子意識形態生成的基礎
縱觀20世紀歷史,談到知識分子似乎就必須言及他們的意識形態光譜,知識分子是各種“主義”的提出者,可以鞏固也可以顛覆政權。在很多關注結構的學者看來,經濟不平等往往是導致知識分子激進和無產階級化的根源。希爾斯論述道:社會的危機狀態為特定意識形態的上臺提供了條件,它導致公眾對舊有的中心價值系統失去信任,而選擇某種知性建構的理論。[6](P32-38)根據這種觀點,挑戰性的意識形態能否得到認同依賴于社會危機的嚴重性。然而二戰后,西方社會迎來了經濟復蘇的黃金期,福利國家的建立有力緩解了階層矛盾,中產階級數量的上升使社會穩定效應更為顯著。相對和平的社會環境使激進意識形態失去了發展空間,由此知識分子意識形態的動員能力隨之減弱。雅各比(Jacoby)就通過研究揭示,城市化和商業化如何使得傳統鄉村社區衰落,進而導致邊緣知識分子即波希米亞群體的消亡。[49](P18-37)這可謂是環境變遷導致知識分子意識形態功能弱化的證明。此外,隨著經濟環境的變遷,公眾的政治興趣逐漸從烏托邦的憧憬轉移到社會現實問題。按照吉登斯(Giddens)的觀點是發生了從“解放政治”到“生活政治”的轉向,前者旨在徹底消除不平等、改變社會結構,而后者則是關于日常生活的微觀政治。[50](P246-272)醫療、健康、環境等微觀問題逐漸取代了政治哲學、制度建構等抽象問題,成為公眾的關心議題。這種價值觀變遷在很大程度上侵蝕了以階級、革命、權力合法性為核心的意識形態的文化基礎。
(二)知識分子群體的變化豐富了知識分子的社會角色
隨著現代高等教育平民化的推進,知識分子群體數量、結構均發生了重大變化,這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知識分子社會角色的多元化。20世紀50年代之后,西方社會的高等教育飛速發展,僅在美國就先后建立了超過3 000所大學,人均受教育程度空前提高的同時也意味著知識分子傳統的文化精英身份逐漸流失。布蘭德利(Brandury)對此做了系統論述,他把導致英國知識分子“文化領導權”(cultural leadership)的喪失歸結為六個因素,并指出人數增長應負首要責任。[51](P7-9)柯林斯則分析了知識產品數量對質量的影響,通過“知識階層人數增加—競爭加劇—知識產品數量增加(單位投入時間減少)—質量下降”的鏈條,他有力地論證了知識產品的貶值化傾向,指出戰后知識分子的重大危機是其創造力的下降。[52](P73-96)知識分子創立思想體系的闕如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知識解讀、傳播與應用逐漸被人們所關注。邁耶(Meyer)就指出,知識社會促進了全新的知識中介者(knowledge broker)的興起,他們包括科普作家、高校技術轉讓部門等等,在知識管理、溝通行為、知識能力建設三個維度行動。[53](P118-127)奧斯本(Osborne)系統區分了當代社會主要的四種知識分子形態,即立法者、詮釋者、專家以及協調者(mediator),從知識內容、行為目的、行為風格和實施策略等四個維度比較了他們的差異。其中,協調者承擔著社會創新,不斷對知識進行創造性應用和生產。[54](P430-447)學界對知識分子社會角色的歸納充分反映出當前知識分子功能多元化的現實。
(三)知識觀念轉型弱化了知識分子的文化權威與社會影響力
自啟蒙運動以來,理性主義一直是多數意識形態產生的哲學基礎,但二戰之后存在主義和后現代主義的興起對其起到了解構作用,隨之動搖了知識分子的社會影響力。后現代主義者如利奧塔(Lyotard)認為,宏大敘事正為情境(local situation)和語言游戲所解構。[55]鮑曼更指出,后現代社會的知識分子應不再是追求理性的立法者,不能以“導師”的口吻訓誡公眾,而應強調話語意義的相對性和相互理解,成為文本的詮釋者。[56]貝克(Beck)則注意到理性即風險,風險的根源不再是無知而是知識。[57](P432-436)通過對知識尤其是抽象知識的反思,知識分子自己否定了其成為政治權威和人類導師的可欲性。此外,隨著專業的不斷分化,知識分子群體也發生了如福柯(Foucault)所說的從 “普遍知識分子”到“專業知識分子”(specific intellectuals)的轉變,[58](P127-128)而后者實際上降低了知識分子的文化地位,正如富里迪(Furedi)所言:“將知識等同于人們從零星經歷中獲得的洞見,這一傾向使人們無法拿出一個共同標準來衡量是否擁有知識。通過把知識細分為各種知識,知識分子的地位被削弱了”。[59](P56-64)20世紀80年代西方學界開始的關于知識分子公共性的討論,充分體現了知識分子社會影響的衰落。哈斯納指出,“在西方,也同樣在東方,不僅知識分子發現難找到聽眾,也無法確定知識分子確實有東西可說。”[60](P138)由此知識啟蒙變得困難,在一定程度上導致公共領域的民粹化和情緒化傾向不斷加劇。
總之,任何社會科學研究都是時代的反映,知識分子的研究視域、方法的演變既由時代環境所決定,也隨著時代變遷而發展。由此觀之,在信息社會和知識社會勃興的當下,知識介入的研究可謂正當其時。關于知識分子的諸多行為及社會嵌入機制的分析、關于新媒體環境下知識分子與公眾關系的探討、關于后真相時代(post-truth era)下的知識分子如何作為等現實議題都值得學界密切關注和深入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