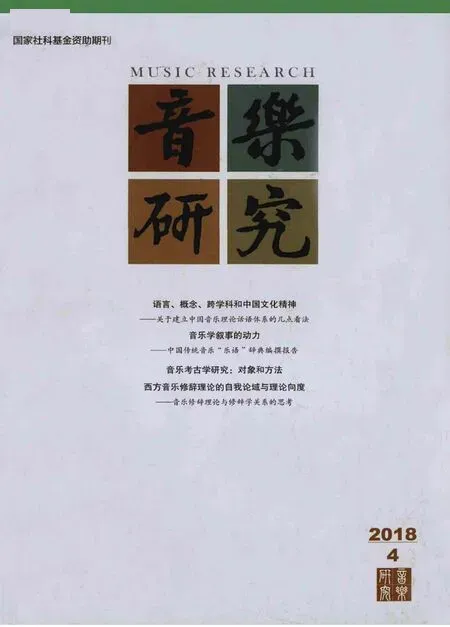音樂考古學研究:對象和方法
文◎方建軍
一
音樂考古學研究的對象是考古發現的音樂文化物質資料,總稱為音樂遺存。音樂遺存分為遺物和遺跡兩類,這里僅就音樂遺物略加論列。音樂遺物主要有四類——樂器、樂譜、音樂文獻、音樂圖像,它們是音樂考古學的主要研究對象,其中又以樂器的研究為大宗。樂譜目前發現較少,出土音樂文獻雖然較為散見,但數量并不算少,二者均具有重要的歷史和學術價值。音樂圖像的數量相對較多,有時能夠提供其他三類音樂遺物所無的內容。
這四類音樂遺物各有自身的特點、優長和局限,它們之間既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又時常相互牽連,相互依傍,具有一定的互補性。
出土樂器大多數是古人使用的實用樂器,具有無可比擬的真實性和具體性。樂器埋葬于特定的出土單位,大多情況下,它都有伴出物,具有一定的考古學環境,而不是孤立的存在。各種隨葬品與樂器的共存關系,使樂器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參照系。在這方面,它比文獻孤立記載一種或一件樂器要全面和豐富得多。
樂器在古代社會的應用處于動態之中,經過埋葬之后便轉入靜態之下,以往使用它的主人已不復存在,如何制造、如何演奏、演奏什么以及當時的具體表演情形等,均難以獲知其詳。并且,出土樂器一般都為古代宮廷和貴族階層所擁有,通過它只能了解這些特定階層的音樂生活和音樂文化,而屬于民間層面的樂器則較少發現,這是出土樂器自身的局限。
古樂譜雖然是彌足珍貴的音樂考古材料,但由于古樂譜在早期(公元前)尚不多見,后來則由于記錄載體難以保存的原因,故目前發現很少,估計其地下潛藏也不會很多。但即使如此,它仍是音樂考古學研究的對象之一,并且還可參考傳世古樂譜對出土樂譜進行研究。不過,傳世古樂譜如同傳世音樂文獻那樣,不應作為音樂考古學研究的對象。黃翔鵬主張將傳世古樂譜的研究稱之為“曲調考證”①參見中國音樂文物大系總編輯部等編《中國音樂文物大系》“前言”部分。,應是比較合適的。
古樂譜是我們了解古代音樂作品具體構成的重要資料,甚至是唯一的資料,這是它自身的優長,但由于古樂譜使用的文字和符號與現今所見傳世樂譜差異較大,加之有的樂器演奏譜存在定弦上的判定問題,所以對它的識讀解譯存在較大困難,研究結果也是仁智互見,甚至是大相徑庭。另一方面,古樂譜記錄的音樂作品缺少精確的節奏、節拍和時值,因此對它的解譯復原就會存在一定的分歧,有時同一首樂曲,不同的研究者所譯,表現在音樂形態上就具有明顯的差異。
音樂圖像出自古代美術家之手,他們對于當時音樂事物的描繪,各有自己的側重,不一定都是從音樂專業的角度來創作。由于創作意圖、圖像主題、畫面布局和藝術手法的不同,以及制作材料、工具和技術的限制,圖像內容會有不同程度的省減,有些只是寫意而非寫實,有些則有所夸張,或具有象征性,甚至想象成分,不可能全部是現實音樂生活的真實寫照。如古代樂隊的組合,樂器的形制、件數和尺寸比例,弦樂器的弦數,吹管樂器的管數或指孔數等,都不是百分之百的準確。
圖像樂器雖然不是實物,但它是實物的形象再現,有的再現可能是比較真實的,有的可能只是輪廓式的,有的則可能是錯誤甚至虛構的,這都需要加以具體的辨析。如在中國出土的漢畫像石和唐代壁畫中,常見有樂人雙手握持一小型樂器置于口邊吹奏的形象,對此有塤、笳、貝等不同說法,但都是從外形所做出的猜測。對于此類不具備觀察條件的輪廓式模糊圖像,應以暫且存疑為是。
失真的音樂圖像,不僅在考古發掘中見到,而且在傳世的古代音樂圖書和考古圖書中,也存在圖像不確甚至圖像有誤的情況。如宋代陳旸《樂書》所繪的塤、于等樂器,即與出土實物的形制不符。又如宋代呂大臨《考古圖》收錄的編鐘,所繪圖像不確且無比例,這些都是應予注意的。
驗證音樂圖像的正確性,需要用一定數量的同類圖像資料加以比較,同時,還需以圖像和實物加以比較,以實物為驗證圖像的標準。當然,有些樂器圖像雖然在出土實物中尚無所見,但恐不能簡單認為即圖像有誤,還應參考古代文獻記載并耐心等待新的音樂考古發現。
音樂圖像資料能夠反映出不同品種的樂器,有些樂器品種迄今并無實物出土,恐怕今后也不會有大量發現。音樂圖像中的器樂表演形象,有的描繪一件樂器,或展示一件樂器的演奏狀態,有的反映出幾件樂器的組合及其演奏情景,有的則是古代樂隊的整體描繪。因此,音樂圖像對于樂器的研究,不僅關注樂器個體,還應包括樂器組合和樂隊構成。
音樂圖像有時反映出一定的樂器組合,有的可能是整體樂隊,有的可能是樂隊的局部,有的甚至是寫意,即所描繪的樂隊只是象征性的幾件樂器,不一定是古代現實生活中的樂隊樂器構成。如中國出土的東周時期青銅禮器,有些上面刻畫有所謂宴樂圖像,但其中只見編鐘、編磬和建鼓等少數幾種樂器,很少看到琴、瑟類彈弦樂器和吹管樂器,但不能據此便認為古代宴樂演奏不使用弦樂器和吹管樂器;而圖像描繪的場面,也不一定必然是宴樂表演。從考古發現看,既有僅隨葬編鐘、編磬的墓葬,也有包含多種樂器隨葬的墓葬,樂器的應用場合則不一定僅限于宴樂。
相對于立體圖像的散置狀態而言,有些平面圖像(如壁畫)反映的樂器組合或樂隊構成則較為可信。但是,墓葬中出土的樂俑,其擺放或出土位置有時具有一定的隨機性,不一定就是古代現實音樂生活中的樂隊排列和組合方式。有時由于樂俑的出土位置被擾亂,發掘者在整理和發表材料或在后期布展時,將樂俑以主觀意圖加以組合,容易給人造成古代樂隊或樂舞排列組合的錯覺,這是需要加以注意的。
與古代文獻對于音樂的描述相比,音樂圖像具有較為直觀的特點,是古代音樂活動和音樂器物的形象化和視覺化。音樂圖像雖然不如出土樂器那樣具有無比的真實性和具體性,但往往能夠提供較為廣闊的音樂表演場景,有時能夠表現出某種音樂活動的整體或局部整體。與出土樂器相比,它有表演者甚至觀賞者,以及表演的場面和環境,有樂器或樂隊的排列組合,表演者(奏、唱、舞)的姿勢、姿態和服飾,反映出樂器的配備、安置和演奏方式,器樂演奏與其他表演的關系,因而具有自身的特點和優長。
出土音樂文獻是古人對當時或之前音樂活動和音樂事物的描述和記錄,具有相當的真實性,體現出重要的史料價值。歷史上由于種種原因,傳世文獻會發生遺失乃至毀滅,如六經之一的《樂經》即已失傳。古代文獻流傳至今,經過多次傳抄、刊印,會發生一定程度的修改或竄亂,從而產生一些訛誤,有時甚至包含有作偽成分。而出土文獻往往能夠提供傳世文獻所無的內容,彌補傳世文獻之缺,有些則可糾正傳世文獻的訛誤。
出土文獻有關音樂的記載,常能提供音樂活動的社會歷史背景,以及與其他事物之間的相互聯系,具有上下文語境和音樂事象的關聯性,而不是孤立地記錄一件樂器或一部音樂作品,這是它明顯的優長。
不過,應該看到,出土文獻猶如傳世文獻那樣,主要記述統治階層的日常生活和行為,其中的音樂事物,自然屬于統治階層所有,而民間音樂則缺乏記載,這方面它與出土樂器具有同樣的局限性。此外,出土文獻里面專門記載音樂內容的書籍或篇章目前發現較少,而有關音樂的記載通常都是較為分散零碎,往往穿插于其他出土文獻之中,需要做專門的梳理和分析。
二
音樂遺存的時間跨度較長,因此集中對某一個或某幾個歷史時期的音樂遺存進行斷代研究,可以形成音樂考古學的分期研究,從而出現石器時代音樂考古、青銅時代音樂考古,或某一國家和地區特定時代的音樂考古等。如中國的商周音樂考古、隋唐音樂考古,歐洲的史前音樂考古、中世紀音樂考古等,就是按照考古資料的時間范圍而形成的分期研究。
音樂遺存分布于較廣的地理范圍之內,都屬于特定的考古學文化。因此,從空間視域看,音樂考古學還能夠從事分區或分域研究。在世界范圍內,音樂考古學有以國家和地區為限的,也有以洲際為限者。如中國音樂考古、希臘音樂考古、埃及音樂考古、美索不達米亞音樂考古、斯堪德納維亞音樂考古、地中海國家音樂考古、東亞音樂考古、歐洲音樂考古和南美洲音樂考古,等等。在同一個國家之內,還可進一步再行分區研究,如中國東周時期的音樂考古學研究,可以從歷史地理學的角度,按當時的國別和族屬分為周音樂考古、楚音樂考古、秦音樂考古、三晉音樂考古、吳越音樂考古和巴蜀音樂考古,等等。
對于上述四類音樂遺物進行專門研究,可以形成音樂考古學的分類研究。②方建軍《音樂史學的一門新興分支學科——音樂考古學》,《黃鐘》1990年第3期。集中研究出土樂器,可以形成古樂器學或樂器考古學;對出土樂譜進行研究,可以形成古樂譜學;對出土音樂圖像進行研究,可以形成“古樂圖像學”;對出土音樂文獻進行研究,能夠形成“古樂銘刻學”③“古樂圖像學”和“古樂銘刻學”的名稱,系李純一先生提出。參見李純一《中國音樂考古學研究的對象和方法》,《中國音樂學》1991年第2期。。其中,有的音樂遺物還可做進一步的分類研究,如目前學術界對編鐘、銅鼓、口弦(jew's harp)、里拉(lyre)等的集中研究,已經形成音樂考古學樂器類研究的分支。
音樂考古學的分期、分區和分類研究,既可以各自獨立開展,成為音樂考古學的分支,也可以同時交叉進行,形成綜合性研究。在從事音樂考古學的分期研究時,可以在同一時期再進行分區和分類研究。例如,要研究中國東周時期的編鐘,似可將其分成春秋和戰國兩期進行研究,每一期再做分區或分域研究,每一區域又可單獨進行編鐘的類型劃分,然后再做進一步的綜合。分區和分類研究,也可大體參照這樣的分期研究模式開展。
三
相對于傳世的音樂歷史文獻,考古發現的音樂遺存,猶如一系列需要讀解的“地下音樂文本”④方建軍《地下音樂文本的讀解》“序”,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2006年版。。音樂考古學的研究資料,本身即具有較強的綜合性,而各種音樂文化物質資料之間,也具有多方面的聯系。不同的音樂文化物質資料,與相關的學科領域發生直接或間接的聯系。因此,認識和解釋音樂考古資料的內涵,就不可能運用單一的理論、技術和方法,而必然要涉及諸多的理論、技術、方法和學科領域,以此來進行綜合性的研究。
綜合運用多學科融合的研究方法,是現代學術的普遍特點。新技術的不斷發展和應用,為音樂考古學研究提供了契機。我們應及時學習和吸納有關的科學技術和方法,只要能夠達到音樂考古學研究的目的,即可法無定法。
由于音樂考古學試圖重建考古實物所反映的某一歷史時期人類音樂行為及其發展規律,所以必然要涉及較多的學科領域,以多學科知識或多學科協作的手段,來達到和實現研究的目標。總體來看,在音樂考古學的研究方法或涉及的學科領域中,考古學和音樂學應是最基本的兩種,二者需要科學有效的結合。音樂考古學所應用的考古學方法,主要是考古類型學,當然也涉及考古地層學、考古學文化、古文字學、古人類學、實驗考古學、民族考古學等;而音樂學方法則主要涉及音樂史學、樂器學、音樂聲學和音樂人類學等,并通過樂器測音、音樂遺存的復原和模擬實驗等特殊方法,來探索古代人類的音樂行為和音樂文化的構成。
鑒于音樂遺存來源的考古學性質,我們不能脫離考古學來孤立地看待和處理音樂考古資料,或者僅從音樂學的角度來審視和研究它,那樣就會使音樂遺存與考古學割裂或隔絕。音樂遺存分為遺跡和遺物兩大類,遺跡通常是遺物的出土和存在單位,二者關系密切,相互依存,不可分割。因此,音樂考古學研究必須掌握與之有關的一切考古資料。諸如音樂遺存出土的地層、年代(時代)、考古學文化、共存物、墓葬情況(墓主、國別、族屬等)、器物組合、人種分析等,都是音樂考古學研究必備的資料,需要與音樂遺存聯系起來加以通盤考慮和分析。
就出土樂器而論,只關注樂器本身,僅掌握單一資料是遠遠不夠的,需要密切追蹤相鄰和相關學科的研究成果,為音樂考古學研究奠定基礎。如對于曾侯乙編鐘的研究,就涉及古文字學、樂律學、音樂聲學、音樂史學、冶鑄學和化學等。因此,單純從某一學科出發,只能認識事物的一個方面或一個側面,而集聚多學科進行綜合研究,則有可能較為全面地認識和分析音樂考古材料。
在關注樂器本體的同時,還應通覽和把握與之共存的其他出土物品。也就是說,在研究過程中,既將音樂考古材料與一般考古材料有所分別,同時又需將音樂考古材料與一般考古材料加以整合。這是因為,出土樂器與一般考古發掘品有所不同,它是音樂制品而非一般生產和生活用品,所以它是一種特殊的考古材料,應該將其抽繹出來予以特別對待。同時,音樂考古材料又與一般考古材料具有相互間的有機聯系,因而不能將其與一般考古材料絕然分離,而應厘清考古發現情況,將其納入考古材料的整體系統之中來關照。
基于這樣的認識,出土樂器的研究方法,似可歸納為由外部形制、內部結構再到音響性能的三層遞進模式:
外部形制——內部結構——音響性能
這種三層遞進模式,也可表述為出土樂器的表層、內層和深層研究方法:
表層研究——內層研究——深層研究
出土樂器的三層遞進研究模式,是由外到內,由視覺觀察到聽覺判斷,由儀器測量到人腦分析的過程。
僅進行表層的樂器外部形制學(包括紋飾)研究,普通考古學即可勝任;樂器的內部結構與音響之間的關系,樂器的材料性質、化學成分和樂器形制的斷層掃描等內層范圍的考察分析,需要由音樂考古學者從事實物觀測,并與有關學科的學者密切合作;聲學特性、音樂性能和音樂分析等,則主要由音樂學術背景的音樂考古學者來完成。因此,音樂考古學研究是案頭工作、田野工作和實驗室工作相互滲透和融合的結果。
在對音樂遺存進行考古學觀察的同時,還要參考傳世古代文獻記載,以考古發現與文獻記載相結合,對音樂考古材料予以闡釋。這就是王國維倡導的古史研究“二重證據法”⑤王國維《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見之學問》,載葛劍雄主編《王國維考古學文輯》,鳳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87頁。。因此,音樂考古學應將歷時研究(diachronic study)與共時研究(synchronic study)結合起來。目前主要還是集中于音樂遺存的歷時性探索,而在共時性研究方面則較為欠缺。音樂文化的存在和發展不是孤立的,而是與社會文化具有多方面的聯系,因此不僅應將音樂考古材料置于歷史的時間維度來考察,而且需要將其納入同時代社會文化的橫向空間維度來審視,這樣才能縱橫交織,從時間和空間維度來進行音樂考古學研究。
考古發掘揭示的音樂遺存,由過去的動態而處于靜態,使用它的原主人業已消逝于歷史之中,我們只能“睹物思人”,并盡可能運用考古學環境并結合文獻記載進行關聯分析。因此,在從事音樂文化物質資料分析時,不能僅限于就物論物,而應聯系到物背后的人。
由于考古發現的音樂遺存屬于特定的時代,所以我們在進行必要的考古學分析之后,還要將其納入音樂歷史發展進程之中來考量。如果游離于音樂歷史之外,不關心音樂考古資料的創造者和使用者,不考慮資料的人文屬性,這些資料就徒成自然形態的物質。從此而看,音樂考古學應由純物質層面的研究,進入到文化的、精神的和人類行為方式的研究。音樂考古學應借鑒文化人類學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體現音樂考古學研究的人文精神和人文關懷。
綜上所論,音樂考古學對出土樂器的研究,實際應主要包括形制、音響、文化三個方面,其中的樂器形制研究,包括三層遞進模式的外部形制(表層)和內部結構(內層)研究。
音樂考古學的研究工作,基本遵循由個體、群體到總體的研究路徑,即由個別到一般、由小的綜合到大的綜合、從微觀到宏觀的研究過程。音樂考古學的個案分析是群體和總體分析的基礎,也是一個必經的研究階段,但僅有個案分析,就會只見樹木而不見森林。因此,在個案分析之后,還應進行群體和總體的綜合分析,以此來考察不同音樂考古學文化的特點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和作用,探索古代音樂文化發生、發展的歷史過程和規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