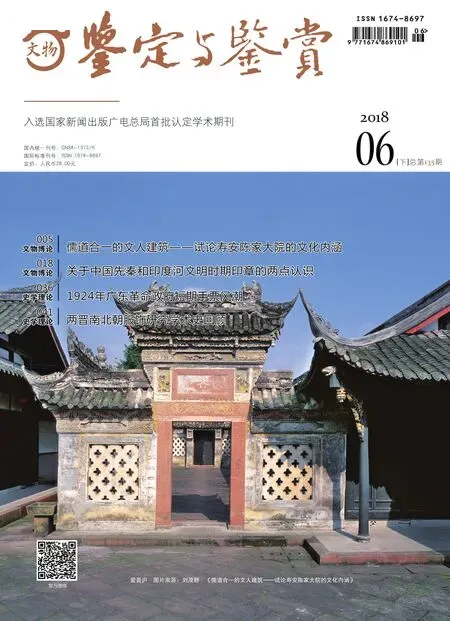“舶來品”與“中原制造”說
——試論漢晉出土的掐絲、金粟帶扣
劉燕
(北京服裝學院,北京 100029)
目前國內外考古發掘出土的漢晉掐絲、金粟帶扣總計5件,分別出土于新疆焉耆的西漢墓[1]、大連營城子的東漢墓[2]、朝鮮平壤石巖里的東漢墓[3]、安徽壽縣東漢劉延墓[4]以及湖南安鄉西晉劉弘墓[5]。這幾件帶扣的裝飾手法和紋飾極其相似,可能是出自同一地、同一批工匠之手。而目前國內學者就出土的這類帶扣的來歷問題主要有兩種傾向,一種是域外“舶來品”,一種是“中原制造”仿制品。一方面這種采用掐絲、金粟工藝制作的帶扣,其形制和工藝都充滿了異域的味道,與中國傳統風格相異。另一方面漢晉時期中外文化交流頻繁,陸上、海上絲綢之路的開通,加之先秦時就已存在的歐亞草原之路,使得民族與民族之間交流的距離縮小,文化上得以相互吸收、融合,這也就使得帶扣的來源變得更加復雜了。
1 “舶來品”之說
漢晉所出的掐絲、金粟帶扣究竟為“中原制造”還是“舶來品”?首先應明確帶扣的來歷。孫機先生認為這種前橢后方類型的帶鐍為匈奴、東胡革帶的扣具,且同類型的帶扣在準格爾旗西溝畔戰國墓、呼倫貝爾盟陳巴爾虎旗完工西漢鮮卑墓以及內蒙古土默特左旗討和氣墓均有出土[6],只是裝飾題材與材質有所區別。另外,有學者認為平壤與營城子出土的帶扣為高規格具有匈奴藝術風格的文物,系烏桓盜掘匈奴大墓之物,后流傳至兩地,而非漢地所有;焉耆所出土的帶扣其制作者為東遷新疆天山的烏禪幕工匠,是他們將中亞的黃金工藝傳入到天山南北的[7]。也就是說這幾例帶扣的形制實質源于匈奴、鮮卑等草原民族,有別于中原革帶使用的帶鉤。而從制作工藝上講,帶扣上所使用的掐絲、金粟工藝最早見于兩河流域烏爾王陵(公元前2600)所出的一件黃金匕首上[8],其后,在北亞的阿爾贊國王谷,以及中亞阿富汗的黃金之丘以及南亞古印度都出土過類似工藝的金飾。在我國最早使用這類工藝的例子是廣州象崗山南越王墓(公元前122)出土的金花泡。而孫機先生認為它們是西方工藝品,極有可能非本土制作[9]。那么,可以試想掐絲、金粟的制作與焊接工藝的技術門檻較高,在漢以前及漢晉時期中原以外的域外地區金屬工藝已相當成熟,故有理由懷疑這幾例帶有匈奴藝術風格的帶扣可能為“舶來品”,并經歐亞草原之路或絲綢之路由北方傳入中原。
2 “中原制造”之說
再回到帶扣的形制問題上,前文提到其形制是具有匈奴藝術風格的,但帶扣上的紋飾尚未論其歸屬,各考古報告都言“龍紋”金帶扣,而有的考古報告描述龍紋上似有翼[10],且細查龍紋還有單角雙角之分,這不得不讓人聯想起流行于漢代的“天祿”“辟邪”兩種神獸。它們一般刻有雙翼,常作為鎮墓獸成對出現,雙角者為天祿,獨角者為辟邪[11]。那么,這幾件帶扣中的龍紋是否與“天祿”“辟邪”存在聯系呢?有學者認為漢代以來的龍與獅首翼獸相互影響,同時改變著它們各自的形象,這種改變一方面體現在“天祿”“辟邪”的“龍化”,一方面是“龍”增添羽翼,兩者很容易相混[12]。龍紋是中國藝術的典型主題,“天祿”“辟邪”雖源于中、西亞,但與中、西亞的獅首格里芬或帶翼獅子在造型上有所不同,況且其名稱被賦予了“中國化”的寓意,應當是經過改造的本土化產物。如此看來,“天祿”“辟邪”與同時期龍的造型相混應該是外來文明與漢文化融合之初出現的現象,故這幾例帶扣很可能就是這種文化交融下中原地區的產物。
況中原統治階層對域外珍品十分喜愛,畢竟“任何外來風格,一旦受到歡迎,馬上就會引起仿效,買方可以照單做,賣方可以投其所好。有仿造就有改造……漢代的諸侯王陵,特別喜歡異國情調,這在當時是一種風尚。比如南越王墓的銀豆和玉來通就是這種混合風格的典型”[13]。另外,有學者還指出戰國晚期至少趙、秦等國的工匠已經參與制造歐亞草原風格的動物牌飾,并在仿制過程中動物紋不斷出現變異[14]。這一方面反映了王公貴族好尚域外之物的獵奇心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在這種需求狀態下被激起的“仿制風”,并且這種“仿制風”早在戰國時期就已經出現了。
觀察這幾例帶扣可知其裝飾手法采用了錘揲、鑲嵌、金粟和掐絲焊接,其中掐絲分為圓絲和扁絲,扁絲用做鑲嵌外圍,而圓絲則做為單獨裝飾且決定著龍的形態和金粟的分布。同種裝飾手法也見于漢代其他墓葬中,如陜西西安的金灶、安徽合肥“宜子孫”金飾以及河北定縣金辟邪、金羊群、金龍等,這些金飾都具有中原本土化特征。有學者認為天山北麓博爾塔拉發現的一件帕提亞藝術風格的耳環制作工藝與新疆焉耆的帶扣相同,為烏禪幕工匠所制作。而同出烏禪幕工匠之手的還有哈薩克斯坦卡爾加里(the Kargaly burial)游牧貴族墓的金耳墜以及蒙古高勒毛都匈奴貴族墓的四瓣金花[15]。相較之下會發現,這些遺存制作難度遠不及帶扣的精湛,且兩者的裝飾手法也不盡相同。很顯然相當時期中原周邊地區出土的同類金飾中幾乎找不到同時具備幾種工藝的例子。此外這種鑲嵌“青碧、閔瑰飾”的裝飾特征,為漢代所習見,而西方當時在金器的鑲嵌筐內常填以琺瑯釉,漢代尚無此種做法[16]。綜合上述特點來看,幾例帶扣極有可能是中原的工匠應統治階層的要求制作的集幾種工藝為一體的特殊工藝品,屬“中原制造”。
3 總結
上文對漢晉時期掐絲、金粟帶扣的來源做了兩方面的分析,不管是“舶來品”說還是“中原制造”說,都具有一定的說服力。具體而言,筆者更傾向于“中原制造”說,但前提是兩種說法綜合起來講,即這類帶扣很可能是外來工匠或被傳授外來技法的中原工匠制作,且具有域外風格的“中原制造”品。
前文談到烏禪幕東遷,其在漢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2)投奔了匈奴日逐王,并成為匈奴統治西域的生力軍之一。而匈奴與漢的交往,從漢文帝時雙方就開始互通“關市”了,就算是漢匈之間發生軍事沖突,與匈奴一度終斷和親,但是互相間的物資交流始終沒有中斷過[17]。即便是推測這種工藝為烏禪幕傳入,也無法排除因漢匈之間長期的交流而將這種工藝傳入漢地,時間有可能在烏禪幕東遷之前。前面已提到早在公元前7世紀阿爾贊國王谷2號墓,以及近年國內發掘的甘肅馬家塬戰國墓、新疆哈密巴里坤戰國晚期到西漢早期墓中,都有過類似工藝使用的跡象。這一方面說明其傳布廣泛、流傳原因復雜,另一方面也說明從先秦時期這種工藝就有向中原滲透的趨勢。綜上,筆者以為這類帶扣很有可能屬于“中原制造”品。不過,還要考慮到其流傳原因復雜、出土數量有限、文獻記載缺失等原因,具體來源日后可能還有深入探討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