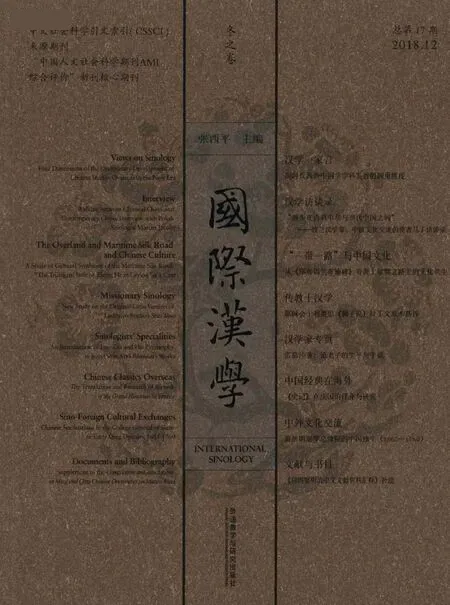《牛津中國古典文學手冊》:海外中國文學研究的新突破*
牛津手冊系列叢書以其權威性、時新性、通識性和原創性等特征,被視為學術研究和教育教學領域最重要的參考書目之一。其編寫過程科學嚴謹,一般由牛津大學出版社特邀某一學科領域中的頂尖專家學者組團參與編寫,覆蓋學科門類齊全,僅藝術人文類(Arts & Humanities)就涉及考古學、藝術學、語言學、文學、哲學、宗教學等15個分支。已出版的文學類手冊包含加拿大文學、兒童文學、文學認知研究、早期現代劇、莎士比亞、英國文學與神學、歐洲浪漫主義、中世紀拉丁文學、美國音樂劇、維多利亞時期文學文化等在內的十余種。牛津藝術人文類手冊雖仍以英語語系研究為主,但近些年也將目光投射到中國文化領域,已陸續出版《牛津中國心理學手冊》(Oxford Handbook of Chinese Psychology, 2010)、《牛津中國電影手冊》(The Oxford Handbook of Chinese Cinemas, 2013)、《牛津中國語言學手冊》(The Oxford Handbook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015)等作品,2016年《牛津中國現代文學手冊》(The Oxford Handbook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s)的出版,激起學界對《牛津中國古典文學手冊》出版的期待。2017年5月出版的《牛津中國古典文學手冊(上)》(The Oxford Handbook of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1000BCE-900CE,以下簡稱《手冊》)①Wiebke Denecke, Wai-yee Li, Xiaofei Tian,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1000BCE-900CE.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承襲了西方漢學研究的學養和思路,以西方文藝理論為主導,突破中國學者固有的中國文學史觀,既展現出中國古典文學更加多元的面向,也生動地勾勒出海外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動向與趨勢,對當下國內的古典文學研究及海外漢學研究具有重要的反思價值。
《手冊》既希望能夠在中國文學的域外研究中樹立“經典工具書”的地位,同時也希望能在專業領域之外尋求更多的閱讀受眾,包括諸如接受了西方教育的華人華裔及其族群,對中國文化感興趣但并不能(熟練)以中文閱讀與書寫的英語讀者群,甚至是以中譯本為中介的研究中國文學的漢語讀者群,因此它對編者的選擇格外謹慎嚴格:魏樸和(Wiebke Denecke)、李惠儀(Waiyee Li)及田曉菲(Xiaofei Tian)三位主編的研究范圍泛及東亞文學比較研究與上古文化文學研究、中古文學與文化、中國早期思想與敘事學研究、明清文學文化研究、手抄本文化研究、宮廷文化研究等領域;具有良好的跨語際學術素養的27位撰者中多見重量級的學者,像康達維(David R.Knechtges)、柯慕白(Paul W.Kroll)、伊維德(Wilt L.Idema)、宇文所安(Stephen Owen),他們都是相關研究領域的知名教授,也都分別參與過之前的《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01)和《劍橋中國文學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2010)的編纂工作。不過值得留意的是,絕大多數撰者來自美、英的主流名校(以哈佛系為主),壟斷式承擔絕大部分的編寫工作,非英語語系的學者僅三位,且撰文比重較低,大陸學者完全被排斥在話語之外(《中國現代文學手冊》則很好地避免了這一尷尬)。全書分為五個部分:第一部分,導論,分兩節討論“文學”的關鍵概念、分期和關節點。第二部分,讀寫能力基礎,分為兩小版塊,第一版塊,技術與媒介,分四節論述漢字書寫系統、書寫與口頭媒介、手抄本文化、書畫與文學的關系;第二版塊,文學文化體制,分五節分析教育和考試制度、文本與箋注的傳統(上古/中古)、文學習得:類書與文鈔、書閣書目與書佚現象。第三部分,文學創作,分為四個版塊,第一版塊,傳統文類視角,分經、史、子、集四節概括;第二版塊,現代視野下的文類,分三節細談,“中國詩”、士人文學與俗文學、敘事文體;第三版塊,整理、編輯與傳播,分四節分論,先唐選集和選輯、唐代選集、宋代對前期文學的接受、早期文學在元明清的文本流傳;第四版塊,文學與元文學,分四節討論文學/文學思想/詩學的辨析、作者身份的概念、漢代之前傳統的形成、六朝至唐中國文學文化的經典化。第四部分,以時間片段、地域場景(上/下)、人物形象四小節加以分敘。第五部分,早期中古中國與世界,分六節論析,包括殖民化/漢化與多文字體系的西域譯介、東亞漢字圈的共享文學遺產、漢字詞朝鮮文學、早期漢語日本文學、漢越詞越南文學。
盡管讀者仍須對編委組可能存在的東方主義想象和漢學主義學術意識保持警惕,但《手冊》在海外中國文學研究領域的突破還是非常引人注意的,主要表現為以下三點:
首先,《手冊》在成書體例上對之前出現的中國古典文學的主流工具書有所突破。大部分的文學手冊或辭典都偏向實用的工具書,提供條目供查詢,一般是作家作品(或涉理論、流派、文獻等)的條目,或者以單篇論文方式呈現學者、機構、文獻等概述。①前者如劉獻彪主編:《中國現代文學手冊》,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7年;后者如中國社會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主編:《俄蘇中國學手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與《手冊》較為相近的,國內如《北美中國學:研究概述與文獻資源》②張海惠等主編:《北美中國學:研究概述與文獻資源》,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在綜述文章方面介紹北美中國學各個領域的研究進展,在文獻參考方面提供專門的情報資源,但論證和介紹都似淺嘗輒止;國外如《印第安納中國古典文學手冊》(The Indiana Companion to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③William H.Nienhauser, eds., The Indiana Companion to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Vol.1 & 2.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6-1998.,先有簡介各個文類文體的專文,次有主體部分作家作品的英文條目,但還是更偏重于文學本體研究的實用目的。與之比較,《手冊》則完全摒棄了條目式的編排體例,既不依照文學史的敘事傳統,也不提供詳細的參考文獻書目,體系上呈現出對早期和中古中國文學、社會文化的全景式的整體關照。五大章節之間看似松散,卻存在著緊密的內部邏輯關系,導論梳理了基本概念之后緊接著介紹文學的物質載體和文化制度,以社會文化史的角度切入文學本體,調和中國傳統實際與西方文學觀念之間的沖突而使之并行不悖;既有了前期社會文化條件的充分討論,接下來論述文學生成也就順理成章了,再接之以傳播、消費與影響,復歸到文學性本體與經典化問題上;之后另辟之時空與人物,又是經典化問題的延續和認證;最后一部分把中國文學視為一個區域文學的中心來審視其輻射與影響,放在世界文學的全球化立場給予更為公允的評論,如此一來,前面四部分的本論又成了第五部分的基礎和背景。主編分工在各部分的導語中相互通氣,章節間也相互勾連,使得整體性得以鞏固,較好地避免了學界普遍焦慮的將“專著”變為“論文集”的問題。④隨著文學觀念的比較與深入,正如梅維恒指出:“然而到二十世紀六十至九十年代,以中國文學所有方面為主題的第二手研究開始如雨后春筍般出現,導致完全掌握參考書目都成了一個很大的問題。如何跟上新研究潮水般的步伐,就成為讓編寫參考書目、指南和百科全書的許多專家頭疼不已的問題。學術研究井噴式的進展,既是一種可喜的現象,也是一種噩夢。其可喜在于,有價值的見解和材料紛紛出爐;說它是噩夢,是因為人們不可能像二十世紀上半葉的學界那樣,掌握本領域的所有文獻。新研究成果的指數級增長,導致中國文學研究領域最出色的學者都宣布現在已經不可能再寫一部中國文學史了——即使是學界合作起來也不可能,以個人之力就更是妄談。相關內容如大海般浩繁,不可能壓縮成一卷甚至多卷。另外,隨著中國文學之復雜性日益為人所了解,撰寫一部言之鑿鑿的中國文學史也毫無意義。”(Victor H.Mair, eds., 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xvi-xii; 梅維恒主編,馬小悟譯:《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北京:新星出版社,2016年,引言,第1—2頁)正因如此,很多學者也嚴厲批判之前的一些合作式的中國文學史或研究手冊,如柯馬丁所斥“文章之間沒有關聯,也體現不出歷史的敘事性”(Martin Kern,Robert E.Hegel,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26(2004): 159-179)。
其次,《手冊》在研究理念上對大陸傳統中國文學的研究思路有所突破。《手冊》所代表的西方中國學研究突破了上一代以馬克思主義和階級斗爭為綱、以經典作家作品為脈的主流文學研究模式,力圖呈現和放大社會文化的物質決定性,不再局囿于“文學”本身,而更加著力于形成“文學”的外圍合力和內質輻射。19世紀,法國文藝批評家丹納(Hippolyte Taine, 1828—1893)的《英國文學史》(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1872)強調文學與社會史的聯系,提出社會歷史決定論的理念,而稍后朗松(Gustave Lanson, 1857—1934)的《法國文學史》(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aise, 1894)則提出“文學社會學”(sociology of literature)概念,主張綜合考慮社會因素對作家、讀者和文本的影響的復雜關系,舍勒(Wilhelm Scherer, 1841—1886)在《德國文學史》(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1883)中提出“3-E-s”模式(Ererbtes、Erlerntes、Erlebtes),倡導以傳承、學養、生活三種因素研究作家和藝術家的創作的實證主義文學觀。受此文學史觀的影響,《手冊》既維系了原本美學、文學、語言學范疇的文學內部研究維度,又增強了對文學的外部研究力度,將早期和中古中國文學的生成、傳播、保存、消費、影響的各個面向視為構成文學本體的必要層級,原本是背景、表現等的“次要”因素被凸顯成研究主體,打破普遍認為的文學本體至上的等級,也不再以時空為限劃分出朝代、文體、南北、性別、雅俗等斷裂二元對立式的中國古典文學的刻板樣貌,注意到不同文學影響因子和生成格局之間的內在聯系,力圖通過對時代風格、審美旨趣、哲學世界觀等方面的把握,揭示文學的社會規定性,全面勾勒出一個時代“文學生活”的不同側面。例如第二部分“讀寫能力基礎”涉及物質媒介和文化制度兩個維度,將書寫系統、正字法、讀寫能力、書寫與口頭傳播載體、口述與記憶等非文學層面的“外力”視為文學研究的有機構成來解釋中國文學的閱讀書寫與傳播層面,這些因素不再被視為研究的“催化劑”,而是“原材料”,打破了“文學是人學”“文學是摹仿”“文學是語言的藝術”等傳統文學觀的局囿。
第三,《手冊》對原本文學文本研究獨尊的話語體系有所突破,反經典,重實證,將文學研究提升到知識社會學(sociology of knowledge)的高度予以再度審視。20世紀80年代以來,北美以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所倡導的新歷史主義(New Historicism)、歐洲以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 1921—1988)為肇始的文化唯物主義(cultural materialism)推進了西方的文學研究的學術史觀念。新歷史主義強調透過文化語境去理解作品和通過文學文本去理解思想史應當同時進行,這意味著文化語境和文學文本不再是背景和前景、服務與被服務、決定與被決定的關系,重新考察文本在當時物質條件下的呈現和意義,不只停留在經典文本的研究,還要考慮次文本和非文本的存在,以及文學文本與歷史文本之間的互文;文化唯物主義的“反經典化”傾向則將目光較多地投向“經典”之外較為次要的作家作品和文學現象,以對其文學史地位進行重新反思。《手冊》貫徹此學術史觀念,例如在文學體制部分,古典文學研究素來重視教育和考試制度與文學的互動及文人知識獲取的主體途徑,而在主流之外,有一些為意識形態所輕視忽略、不太容易出現在一般的文學史脈絡之中的地方,《手冊》特別有所留心,像六朝時期宗教人士在寺院尼庵學習的不同層級決定其文化能力,以及不少文人在這些宗教場所接受早期世俗教育或從事研究的例子,此外還有這一時期女性接受教育的面向(第七章);再比如被認為原創性闕如、文學性不高的類書與書鈔,也有專節闡述其對特定讀者群(如帝王皇室)的文學影響力,從其體例對文學創作中的“對偶”習得的直接作用來界定它們對中古文學的價值和意義(第十章),這些都是從知識學的高度突破文學本位主義的體現。
突破之外,《手冊》在海外中國文學研究領域尚有三個方面值得留意:
首先,編撰《手冊》的學者為中國文學文本的重新闡釋帶入了西方文藝理論研究印跡,技巧嫻熟,解讀出彩。比如由陳威(Jack Chen)和田菱(Wendy Swartz)撰寫的“地域空間”兩章,借助了布迪厄(Pierre Bourdieu, 1930—2002)從空間維度展開論述的文學社會學思路,對宮廷、閨閣、都邑、邊塞、林苑、寺院、山水、路途等與中國古典文學相關的若干題材(subject)進行解讀。布迪厄所定義的“文學場域”(literary field)是一個有著自身職能規則和制約文學生產的社會語境,賀麥曉(Michel Hockx)就曾將此理論引入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手冊》此次將此理論系統引入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讓人眼前一亮,再次印證了非文本文學前景化、知識化、體系化的嘗試。再如第二十四章李惠儀所撰“作者身份的概念”,從詞匯學角度梳理“作”“述”“賦”“著”“撰”,進而討論作者身份概念的緣起,從紛繁的文學現象中探尋文本與作者之間的關系,認為署名歸屬或偽作系名是對文本意義的界定和控制,所舉孔子編五經、李陵蘇武詩、屈原《漁父》《懷沙》都是有力的例證。這明顯是受到了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 1915—1980)、 雅 克· 德里達(Jacques Derrida, 1930—2004)、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等理論家關于作者身份的理論的影響,而迥然有別于中國傳統文論中的“知人論世”“以意逆志”等作者觀。盡管這些解讀的視角和方法不免有現代主義反溯求證之嫌,甚至有陷入西方學術話語體系決定論的后殖民主義批評的危險,但平心而論,亦有助于跳出中國文論的刻板印象,有益于在差異化文藝思想的沖撞中激生新的研究成果,并借助比較文學的視閾,通過中西文化參照系的列舉,讓讀者更為清晰而直觀地掌握知識譜系。例如第一章對“文學”、第十六章對“詩”、第三十一章對“殖民化”、第三章拿中國文字跟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文字的比較(兼及從漢字語音體系發展而出的日語假名、湖南女書、臺灣注音符號等)等的討論,無不彰顯出《手冊》試圖避免將西方的文藝理念不加分辨地直接套用在中國傳統文論之上的努力。
其次,《手冊》非常重視知識的時新性及學術的前沿意識。撰文學者多是一線高校的學科帶頭人,關注學術前沿動態,所引的參考文獻多能看到近年來的最新成果,如高奕睿(Imre Galambos)的《漢語書寫系統》(“The Chinese Writing System”)所引38條文獻,2010年之后新出版的占了8條;羅吉偉(Paul Rouzer)所撰《中國詩》(“Chinese Poetry”)引用了兩本2015年出版的專著。即使在一些看似沒有爭議的傳統文學問題上,學者們也力圖推陳出新,例如田曉菲在《“集”部》(“Collections”)主論別集在文化語境中是如何編撰、傳閱、傳播、再輯的,收錄什么樣的文學類型,并如何理解中古時期的“文學”概念,這些問題都不單是在介紹別集的流變史,而更是對這一主題的挖掘和反思(第十五章),所舉材料很多都不見于一般的文學史,例如別集的結集命名原則提到了三國吳的薛綜,“凡所著詩賦難論數萬言,名曰《私載》”;南齊司徒左長史張融“《玉海集》十卷、《大澤集》十卷、《金波集》六十卷”等,這些在絕大多數文學史上的隱形角色,如今通過文獻爬梳而“浮現”“再發掘”出來,引導讀者另辟蹊徑地在文獻的指引下對許多隱形的文學文本再加審視而不限于固有話語模式中。倪健(Christopher M.B.Nugent)所寫第五章檢視手抄本文化的文本流動性,不僅借鑒了西方學界如陸威儀(Mark Edward Lewis)、柯馬丁(Martin Kern)、田曉菲、夏含夷(Edward L.Shaughnessy)、宇文所安等在這個問題上的主要論點,而且在生產、傳播、變異、影響四個方面都有豐富材料加以支撐,如提到文本的抄寫復制多是由作者本人或是其友人、家人、“好事者”所為,其中既有白居易與元稹、洛陽紙貴等熟悉的個案,也有杜牧之甥裴延翰、韋莊之弟韋藹、貫休之徒曇域基于寫本文字或記憶口述而代抄傳世之事。當然,國內學界也一度批判西方學者在選取論證材料的時候刻意標新立異,但客觀來說,就西方語系文化圈的學者而論,選擇哪些中國古代作家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凸顯他們的文學地位和價值,一則出于學者自身的學術興趣、價值判斷、文化取向等,一則出于學者所能接觸到的實際材料。但隨著學者自身教育背景的多元化和文化交流互動程度的提升,以及大數據時代文獻資源的共享力度,文學研究中的跨文化障礙正在不斷被消解,但或多或少還是會受到意識形態、研究方法和價值觀差異的影響。
第三,《手冊》中出現與中國傳統本位主義的意識形態的對立,在“世界文學的立場”里最可見一斑。第三十一章題目《殖民化、漢化與多文字體系的西域(中國西北)》(“Colonization,Sinicization, and the Polyscriptic Northwest”)中出現的“殖民化”和“漢化”與中國文化歷史敘事中的“向心力”“主流性”是兼容但異質的。敘事者試圖“客觀”地敘述歷史上中國一貫的“中華中心論”(Sinocentrism)的文化霸權主義,凸顯民族/種族多樣性的事實存在的意義和價值——在歐亞內陸區域版圖上,不僅僅是中華文化對周邊民族的同化(漢化)這一單一文化流向,還應呈現民族的遷徙、語言文字的多樣共存、游牧民族的文化侵入與互融等歷史圖景多樣性,彰顯異質文化的接觸和接受史(而非吞噬)。以“殖民化”為例,這一概念的表述是歷史詞匯“屯田”,跟現代詞匯“殖民”相去甚遠,雖有誤導之嫌,但確能在單一中心敘事之外對與此衍生出的中國傳統文學文類題材(如邊塞詩)進行更深層次的反思。對西域/內亞民族文字和文學的關注(包括第三章對周邊民族文字的論述),能將其放置在與漢文學幾乎等量齊觀的位置上而不是簡單定性為“受中華文化同化”的視角,嘗試在中華本土一元文化之外力避漢本位文化沙龍主義的弊端,也是難能可貴。此外,對漢字文化圈①漢字文化圈(Sinographic Sphere),有別于史書美(Shu-mei Shih)、石靜遠(Jing Tsu)、王德威(David Der-wei Wang)等所提的“Sinophone Writing/華語語系書寫”。的分析(第五部分)也在某種程度上反對中華文化中心論的偏執,在勾勒清晰的歷史軌跡中細數漢字文化作為共同的文化遺產對東亞其他國族文學的輻射和影響,分章論述漢字詞朝鮮文學、早期漢語日本文學、漢越詞越南文學的歷史文獻(之前也有零星涉及,如第十九章《文選》在日本和朝鮮);而這一東亞共享文化,在中古中國之后漸次分崩離析而漸行漸遠,這也是符合歷史事實的,不存在對中國文學傳統的顛覆,也不是別具用心的西方文藝批評對中國文學文化的武斷置喙。此外,《手冊》對宗教和信仰、民族和種群、地域和方言、人權和性別的關注也發人深省(某些議題在當代官方意識形態中不宜討論),呈現出多元關注聚焦而非局囿于文學、文本、文獻本身的單一線性模式。
總而言之,《牛津中國古典文學手冊》的出版是海外中國文學研究的又一里程碑,其意在厘清知識體系與歷史物質文化語境的互動關系,認為文學敘述的真實性來自于可信的文獻材料、文學思潮和傾向,同時也跟時代文化風尚和社會習俗密切相關,對文學文本的生產、傳播、消費、闡釋等環節之于文學本體的影響多有關注,且突出中古以前的中國在東亞區域文學上所扮演的角色和所處的地位。盡管難免有輕視本體研究、模糊主客體關系、學究炫才的論證氣等問題存在,但其在實現學術總結、累積、指導和展望上的多重意義卻值得學界重視。海外中國文學研究存在著西方學術話語的慣性思維,尤其是樂用后現代、后殖民的解構主義來審視文化和文學,不免會有主題先行和問題預設的風險,這種新歷史主義和漢學主義的傾向,很容易限于學者自己當前政治、歷史、視野和語境的偏見,投射到所研究的社會文化史的具體層面上而導致錯誤的結論。然而,我們大可不必對海外中國文學研究抱有敵意,它們的出現并非要改變格局,并非要對抗和顛覆,而是嘗試用不同的角度加以敘述,展現出一種不一樣的視角來豐富中國文學史的圖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