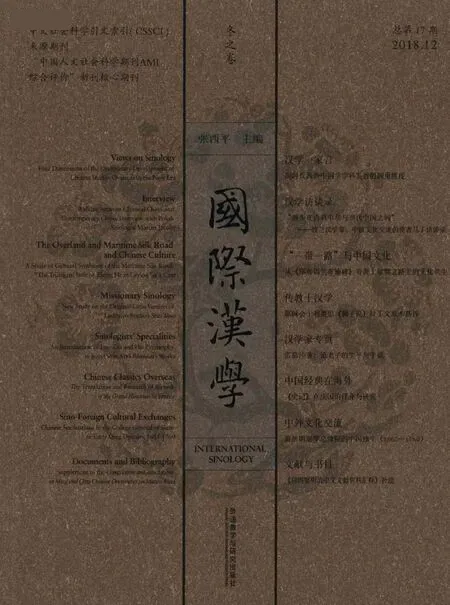絲綢之路上中伊文明交流的歷史敘事
伊朗位于亞洲西南部,北鄰亞美尼亞、阿塞拜疆、土庫曼斯坦,西與土耳其和伊拉克接壤,東面與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相連,南面瀕臨波斯灣和阿曼灣,素有“歐亞大陸橋”和“東西方空中走廊”之稱,是“一帶一路”的必經之地。在歷史上,伊朗是亞洲最古老文明的中心之一,它曾創造了光輝燦爛的波斯文化,在哲學、歷史、文學、藝術、醫學、天文學、農業、建筑、手工業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波斯文明連續幾個世紀,對世界各國的文化都產生了深遠影響,從信德河岸到尼羅河,從中國到歐洲都留下了波斯文明的足跡。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波斯古老的文明把亞洲、歐洲和非洲連接在一起,形成了古波斯文明圈。有著數千年歷史的絲綢之路,就是中伊兩國友誼的最好見證。
據史載,公元101年,安息王朝向中國派遣了使節,并為中國皇帝帶來了獅子、鴕鳥以及其他動物和禮品,獅子一詞的漢語發音正是源于波斯語“sheer”一詞,從此,伊朗與我國中原地區的交往連綿不斷。唐代高宗上元年間,唐州刺史達奚弘通,因出使撰有《西南海諸番行紀》,自稱經36國,經赤土(今蘇門答臘至馬來半島)至虔那,被后世疑為已經抵達阿拉伯半島南部。公元651年(唐永徽二年),大食國①大食是中國唐宋時期對阿拉伯帝國及伊朗地區的泛稱。第三任哈里發奧斯曼(Osman,574—656)派使臣抵達唐都長安,覲見唐高宗李治,向唐朝介紹了大食國的基本情況和伊斯蘭教的基本教義。在此后的148年中,進入長安的大食使節多達41批。唐天寶十一年(752)十二月,黑衣大食(阿拔斯王朝)在取代伍邁葉王朝后,遣使覲見,被唐玄宗特意授以左金吾員外大將軍的勛位。
1942年8月,伊朗與中華民國在羅馬簽訂了第一個友好條約。1945年9月,伊朗在重慶建立公使館,1946年2月該館被提升為大使館。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伊朗和中國于1971年8月16日正式建立外交關系。兩國建交以來,特別是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成立以來,中伊友誼翻開了新的篇章。絲綢之路上的中華文明與波斯文明的交流與交融從以下幾個方面可以窺見一斑。
一、絲綢之路上的波斯文化對中華文化的影響
波斯人是伊朗的主要民族。我們今天通常所說的波斯語即達里波斯語,又稱近代波斯語,目前仍是伊朗的通用語,也是阿富汗的兩種通用語之一。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達里波斯語流行的地域包括中亞地區和阿塞拜疆、兩河流域、小亞細亞、印度北部、阿富汗以及中國新疆西部某些地區。從歷史和現實的角度看,波斯語言文化對中國影響最大的應首推新疆地區。在中國信仰伊斯蘭教的10個少數民族中,塔吉克族是唯一信奉傳自伊朗的什葉派伊斯瑪儀勒派的民族,他們主要分布在新疆帕米爾高原以東地區,以及南疆的莎車、葉城、澤普和皮山等縣的農村,現有信眾4.1萬人,他們使用的色勒庫爾語屬于伊朗語族帕米爾語支。塔吉克族大約在公元10世紀信奉了伊斯蘭教,到16世紀末17世紀初,開始尊奉什葉派伊斯瑪儀勒派。塔吉克族伊斯瑪儀勒派把他們的宗教首領稱為“依禪”,可世襲相傳。在塔吉克族的節日、婚姻、飲食、喪葬、禮俗等各個方面,都受到伊斯瑪儀勒派教義的影響,如“拜拉特夜”在塔吉克族中就是贖罪節日。中國穆斯林傳統經堂教育采用的教材一般為13種,通稱為“十三本經”,其中波斯語和波斯人著作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經堂教育發展形成的學派中,以常志美、舍起靈等為代表的山東學派,尤以重視阿拉伯文、波斯文十三本經并注重蘇菲哲學見長。
我國《回回藥方》里的不少醫方原本來自波斯,展現了中古波斯人的醫術特色。它們分為以下三類:一類是從波斯薩珊王朝直接流傳下來的。比如,《回回藥方》卷三十的“馬竹尼虎八都里馬里其方”“古把的馬準方”等,它們的原型方劑乃是《醫典》(The Canon of Medicine)卷五里的“古把的國王的舔劑”;一類是波斯醫生自己制備的方劑。比如,《回回藥方》卷二十九目錄上的“大答而牙吉方”,此方即《醫典》卷五的“大的解毒劑方”,是伊本·西那(Ibn Sina,980—1037)自己配制的;還有一類是原本由拜占庭羅馬人、印度人創制的方劑,于伊斯蘭時期之前即已傳入波斯,并被波斯人加以利用、改變,后又流傳到了黑衣大食王朝。比如,《回回藥方》卷三十的“馬竹尼阿儺失答蘆方,此方是忻都人造的馬肫”,它就是《醫典》卷五里的印度人的方子——“救命丹”。
在伊朗成為伊斯蘭教國家之前,佛教大約在公元前1世紀初由中亞傳入我國新疆地區,隨后傳入中國內地。可以說中國早期的佛教并不是直接來自印度,而是經伊朗和中亞其他波斯語國家傳入中國的。瑣羅亞斯德教大約在中國的南北朝時期從伊朗傳入中國。摩尼教大約在公元4世紀從伊朗傳入中國,在中國西北地區流傳較廣,敦煌、吐魯番等地都發現有摩尼教寺院、繪畫和文獻。伊朗基督教聶斯脫利派是在唐朝初年傳入中國的,時稱景教,在中國流行二百余年。因此,在伊斯蘭教傳入中國以前,伊朗的其他宗教已在中華大地上留下了歷史的足跡,并且在不同歷史時期,對中國社會產生過不同程度的影響。
漢唐之際,伊朗的音樂、舞蹈、樂器、雜技等逐漸傳入我國中原地區,深受中國人民喜愛。伊朗的繪畫、雕塑、圖案設計技藝也在漢唐之際傳入我國中原地區,對我國工藝美術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中國一些地方保留下來的石雕獅子就是源于波斯古代的石雕藝術。唐朝是中伊交往最為密切的時期之一。當時,兩國的史學家還合編史書《史集》,被稱為“歷史百科全書”“中世紀最重要的文獻之一”。該書是研究中世紀亞歐各國的歷史,特別是蒙古史、元史和我國古代北方少數民族史,以及研究古代游牧民族社會制度、族源、民族學的重要文獻。波斯等國的西域樂舞也盛行于漢唐長安,從漢代起流行于中國的琵琶是從波斯傳入的。元代的蒙古人從中國內蒙古一直走到歐洲,最后在波斯——今天的伊朗一帶,發現了一種畫在瓷器上的原料“蘇麻離青”。中國自己土產的畫在瓷器上的藍色顏料比較灰暗,原因是中國原料里含錳比較多,而伊朗出土的原料含錳少,所以燒制之后顏色特別清亮。正是蒙古大軍帶去的中國瓷匠和伊朗的陶工相遇之后,采用了當地的原料,才終于燒制成如今流傳于世的美麗的青花瓷。
二、絲綢之路上中伊文明交流的歷史敘事
在中伊文明交流中有一些典型的材料可以說明中國文化與波斯文化的相互影響與交融。
1.怛羅斯之戰與杜環的《經行記》
中國人對阿拉伯—波斯文化的記載和了解首先集中在杜環的《經行記》中。751年(唐玄宗天寶十年),唐朝軍隊與大食軍隊在中亞的怛羅斯發生了一場軍事沖突。由于這次沖突是雙方睦鄰關系中的一次走火事件,并非雙方最高層有意策劃的戰爭,所以雙方很快修好。真所謂“不打不相識”,在四年以后的“安史之亂”中,唐王朝向大食國求援,得到實質性的軍事援助,幫助平定“安史之亂”。史書記載“至德初,(大食)遣使朝貢。代宗時為元帥,亦用其國兵以收兩都。”①《舊唐書》卷一九八,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大食援軍在平亂中立下戰功,獲得唐朝嘉獎。
怛羅斯之戰雖對雙方睦鄰關系的影響不大,但對中西文化的交流卻帶來了兩個人們始料不及的影響。怛羅斯之戰的一個直接后果是,推動了唐代高度發達文明的西傳。在這次戰役中,唐軍士兵大約萬人被俘,其中就有許多能工巧匠,如杜環在大食所見的“汗匠起作畫者,京兆人樊淑、劉泚,組織者,河東人樂澴、呂禮”。②《通典》卷一九三,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這些人把唐代高超的手工技藝教授給阿拉伯人,進而傳到歐洲,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特別值得提出的是中國造紙術的西傳,大食利用唐朝工匠藝人開設了造紙廠,生產的優質紙張很快通行大食各地并遠銷歐洲。后來這種造紙技術也傳到了歐洲,為東西文化的傳播提供了極為有利的條件。怛羅斯之戰的第二個結果是伊斯蘭—波斯文化開始有了系統的中文記載,這集中在杜環的《經行記》中。杜環是怛羅斯之戰中被俘的唐朝將士之一,在阿拉伯生活了十余年時間。這段生活使他不僅多方面了解到阿拉伯—波斯的物質文化,而且也深刻懂得了其精神文化。歸來后,他將自己所了解的阿拉伯—波斯的風土人情以及自己對伊斯蘭教的認識等寫進了《經行記》一書。
《經行記》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本系統記錄阿拉伯—波斯伊斯蘭文化的書,可惜原著早已亡佚,只有部分文字在他族叔杜佑撰寫《通典》時被引用,從而傳了下來,其中有不少地方談及大食國伊斯蘭文化。“不食豬、狗、驢、馬等肉,不拜國王、父母至尊,大信鬼神,祀天而已。”③《通典》卷一九三,大秦條。“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無問貴賤,一日五時禮天。食肉坐齋,以殺生為功德。系銀帶,佩銀刀。斷飲酒,禁音樂。人相爭者,不至毆擊。又有禮堂,容數萬人。每七日,王出禮拜,登高座為眾說法,曰:人生甚難,天道不易。奸非劫竊,細行謾言,安己危人,欺貧虐賤,有一于此,罪莫大焉。凡有征戰,為敵所戮,必得升天,殺其敵人,獲福無量。”④《通典》卷一九三,大食條。這些對學者研究早期伊斯蘭文化及其后來的演進具有非常高的價值。此外,在杜佑摘引的有限的文字中,杜環對伊斯蘭教法律、喪葬的寬儉,字里行間也流露出欣賞之情。但其內容還不僅僅在此,杜環懷著極大的熱情描寫了大食國的都市、鄉土風情及豐富的物品,使我們從中了解到當時中國和伊朗之間文化交流的信息。
杜環的族叔杜佑對后世伊斯蘭教文化研究的貢獻不僅僅在于他征引、保存了《經行記》有關伊斯蘭文化的片段,在他撰寫的《通史》第一九三卷中,還專門有波斯和大食的傳。杜佑對大食的地理位置、國家創建、軍事征服以及人民、出產、信仰等都做了概略的敘述。其《大食傳》全文如下:
大食,大唐永徽中遣使朝貢云。其國在波斯之西。或云:初有波斯胡人,若有神助,得刀殺人。因招附諸胡,有胡人十一來,據次第摩首受化為王。此后眾漸歸附,隨滅波斯,又破拂秣及婆羅門城,所當無敵。兵眾有四十二萬。有國以來三十四年矣。初王以死,次傳第一摩首者,今王即是第三,其王姓大食。其國男夫鼻大耳長,瘦黑多須鬢,似婆羅門,女人端麗。亦有文字,與波斯不同。出驢、馬、騾、毀羊等。土多砂石,不堪耕種,無五谷,惟食駝、馬等肉,破波斯、拂秣,始有米面。敬事天神。又云:其王常遣人乘船,將衣糧入海,經涉八年,未及西岸。于海中見一方石,石上有樹,枝赤葉青,樹上總生小兒,長六七寸,見人不語而皆能笑,動其手腳,頭著樹枝,人摘取,入手即干黑。其使得一支還,今在大食王處。①同上。
2.楊良瑤《神道碑》與出使黑衣大食
張廣達先生在《海舶來天方,絲路通大食——中國與阿拉伯世界的歷史聯系的回顧》中對唐朝與大食關系史做了扼要的闡述。他在文章中提到:“在唐代,確曾橫渡印度洋且有姓名可考的中國人有二人。一為達奚弘通,一為杜環。”②張廣達:《海舶來天方,絲路通大食——中國與阿拉伯世界的歷史聯系的回顧》,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其實還應補充一個重要的人,就是唐德宗貞元初年出使黑衣大食的宦官楊良瑤,其事跡載于《楊良瑤神道碑》中,相關記錄的文字雖然不長,但彌足珍貴。《楊良瑤神道碑》是1984年在陜西省涇陽縣云陽鎮小戶楊村附近發現的,后移存涇陽縣博物館。2005年,咸陽市地方志辦公室張世民先生發表《楊良瑤:中國最早航海下西洋的外交使節》一文,錄出全部碑文,并對其中豐富的內容一一做了考釋。③文載《咸陽師范學院學報》2005年第3期,第4—8頁。此前作者還撰有一篇介紹性文字《中國古代最早下西洋的外交使節楊良瑤》,載《唐史論叢》第7輯,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351—356頁。楊良瑤,傳世史傳中尚未見到記載,由于《楊良瑤神道碑》的發現,其被湮沒的名字才重現于世。據碑文,他出身弘農楊氏,曾祖為唐朝功臣,是幫助玄宗滅掉中宗皇后韋氏的禁軍將領。肅宗至德年間(756—757),人為內養,成為宦官。代宗永泰時(765),因為出使安撫叛亂的狼山部落首領塌實力繼章有功,授任行內侍省掖庭局監作。其后,代表皇帝四處出使,撫平亂局。這其中有不少重要的事跡,但最引人入勝的是出使黑衣大食一事。
關于楊良瑤出使黑衣大食之事,《神道碑》記載:
貞元初,既清寇難,天下乂安,四海無波,九譯入覲。昔使絕域,西漢難其選;今通區外,皇上思其人。比才類能,非公莫可。以貞元元年四月,賜緋魚袋,充聘國使于黑衣大食,備判官、內傔,受國信、詔書。奉命遂行,不畏厥遠。屆乎南海,舍陸登舟。邈爾無憚險之容,懔然有必濟之色。義激左右,忠感鬼神。公于是剪發祭波,指日誓眾。遂得陽侯斂浪,屏翳調風。掛帆凌汗漫之空,舉棹乘顥淼之氣。黑夜則神燈表路,白晝乃仙獸前驅。星霜再周,經過萬國。播皇風于異俗,被聲教于無垠。往返如期,成命不墜。斯又我公杖忠信之明効也。四年六月,轉中大夫。七月,封弘農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
據此碑文可知,唐朝于貞元元年四月,以宦官楊良瑤為聘國使,出使黑衣大食,楊良瑤一行帶著國信、詔書,先到南海(即廣州),從廣州登舟出發,經過漫長的海上旅行,到達黑衣大食。至少在貞元四年六月之前,使團回到長安。非常有意思的是,楊良瑤從廣州出發下西洋,不僅與他本人曾經出使廣州并熟悉那里的情形有關,可能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了解杜環在阿拉伯地區的見聞和他回程所經的海陸情況。當時杜環的族叔杜佑正擔任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杜佑所掌握的杜環《經行記》是楊良瑤出使大食的最好指南,不僅所去的目的地是杜環剛剛游歷過的地區,而且杜環所走的海陸也是楊良瑤選擇的路線。關于楊良瑤出使的成果,《神道碑》雖只有簡短的記載,但事實上楊良瑤出使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在8世紀60年代末加強唐朝和大食之間的聯系。從整個唐朝對外關系史來看,楊良瑤走海路出使黑衣大食,也大大促進了通過海路的東西文化交流,似乎從貞元初年開始,海上絲路日益繁榮興盛起來。王虔休《進嶺南館王市舶使院圖表》說:“(貞元年間),諸蕃君長,遠慕皇風,寶舶薦臻,倍于恒數”,“梯山航海,歲來中國”。到貞元末,“蕃國歲來互市,奇珠、瑇瑁、異香、文犀,皆浮海舶以來”。④載《全唐文》卷五一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大量物質文化產品源源運往東南沿海。
3.入華波斯人李素:波斯文化與中國文化在唐朝的相互影響與交融
近年來,隨著中國考古工作的進步和出版事業的發達,大量文物被挖掘出來,史料被刊布出來,為我們研究中古時期的外來文明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其中一個典型的材料是近年才真正為學界所知的波斯人李素(743—817)一家的事跡。1980年,《波斯人李素墓志》及其夫人《卑失氏墓志》被發現,展示了一個波斯家族入仕唐朝的完整畫面。據志文,李素出身貴裔,而且是波斯國王的外甥,家族“榮貴相承,寵光照灼”。他的祖父李益,天寶中(742—756)受君命而來通國好,作為質子,留在中國,宿衛京師,被授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的職銜,兼右武衛將軍,賜紫金魚袋,而且還特賜姓“李”,封隴西郡,與李唐皇家相同,以后子孫即以此為姓。李素的父親李志,出任朝散大夫,授廣州別駕、上柱國。李素早年隨父在廣州生活,大歷中(766—779)被召到京師長安,任職于司天臺,前后共五十余年,經歷了代、德、順、憲四朝皇帝,最終以“行司天監兼晉州長史翰林待詔”的身份,于元和十二年(817)去世。李素的六個兒子均先后在唐任職,并逐漸從中央或地方低級武官變成文職人員以及皇家禮儀中的配角。李素一族從波斯質子,最后成為太廟齋郎,甚至鄉貢明經,這說明來到中國的波斯人一旦進入這樣一個富有深厚文化傳統的社會當中,必然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逐漸脫離本來文化的束縛,最后變成面目雖異而心態相同的中國人。這一點也可以從波斯人采用李唐皇家的“李”姓作為自己的姓氏、作為融入中國社會的一條重要途徑中可見一斑。
然而,文化的交融不是這樣簡單的過程,入華波斯人在很長時間里都在力圖保持本民族的文化,并致力于把波斯文化傳入中國的各項事業。宗教是一個民族傳統文化中保持時間最久的文化因子之一。波斯人的正統宗教是瑣羅亞斯德教(Zoroastrianism,中國稱作祆教)。過去人們總是把波斯王卑路斯的正統祆教信仰與他要求建的寺院聯系起來,認為波斯王建的寺必定是祆祠。但是,作為政治人物,特別是來到他國的亡國君主,流亡長安的波斯王卑路斯完全有可能應長安的波斯景教教團的要求而新建一所寺院。據《長安志》卷十,景龍年間(707—710),因寵臣宗楚客筑宅侵入波斯胡寺,所以將此寺移至布政坊祆寺之西。這里同樣是把波斯寺(景寺)與祆祠處于同一坊中。景教屬基督教一個支派,于唐貞觀九年(635)傳入中國,長安的景教在波斯人的維護下綿延了兩百年。從對長安“景教碑”的考證中可以看出,李素和他的家族都是虔誠的景教徒,而且,李素把他六個兒子的名字與景教聯系起來,說明了他對維護景教繼續流傳的愿望。到李素兒子一輩,李素一家已經在華繁衍四輩,經過七十多年漫長歷程,已經成為唐朝中央或地方政府的官員,卻仍然在宗教信仰上保持不變。而這種景教的信仰,并沒有影響他們參與唐朝的政治運作,甚至禮儀活動。
兩千多年前,我們的先輩穿越草原沙漠,開辟出聯通亞歐非的陸上絲綢之路;揚帆遠航,闖蕩出連接東西方的海上絲綢之路,打開了各國友好交往的新窗口。在這條人類歷史的文明之途,中伊兩國之間的文明交流為人類發展進步書寫了新的篇章,開啟了許多新的文明智慧。
歷史是最好的老師,中伊文明交流的歷史表明,無論人類離人類命運共同體和人類共有精神家園的建成相隔還有多遠,只要我們像兩國的先輩們那樣勇敢地邁出第一步,堅持相向而行,就能走出一條相遇相知、共同發展之路,走向幸福安寧、和諧美好的遠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