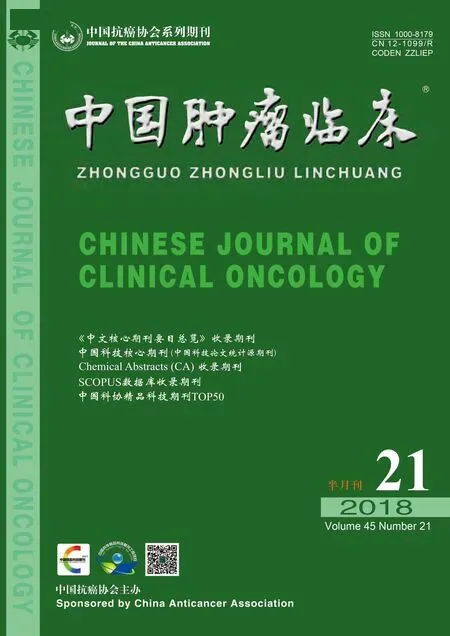癌癥相關性炎癥與腫瘤微環境相關研究進展*
綜述 焦順昌 審校
腫瘤相關性炎癥是癌癥的關鍵特征之一[1-2]。白細胞介素(interleukin,IL)、趨化因子和淋巴因子等細胞因子參與炎癥過程的介導與調控[3-4]。各類細胞因子間以及其膜受體與可溶性受體間存在相互協同、抑制、拮抗等復雜關系,形成細胞因子網絡。惡性腫瘤細胞因子網絡復雜,在影響腫瘤生物學的各種因素中扮演著重要角色[5]。腫瘤組織是由腫瘤細胞、間質細胞以及其他非細胞成分共同構成的復雜組織。腫瘤相關性炎癥可通過改變組織內穩態,在構建適宜腫瘤生長的環境中發揮重要作用。腫瘤微環境(tumor microenvironment,TME)是腫瘤演化的關鍵因素,而癌癥引起的炎癥是TME的重要組成部分[6-7]。本文就炎癥、細胞因子網絡與腫瘤微環境相關研究進展予以綜述。
1 癌癥相關性炎癥
炎癥是機體應對感染和組織損傷的適應性反應,以血管反應、免疫細胞的募集和分子介質的釋放為主要特征。炎癥反應的主要目的是對抗病原體或有害刺激、修復損壞的組織以及恢復體內平衡。若炎性刺激長期存在或炎癥調控機制失控將導致一系列的疾病,如自身免疫疾病、組織纖維化以及癌癥[8]。癌癥與炎癥的相關研究在早期主要著眼于炎癥的促癌作用[9],如在肝癌中炎癥可直接促進腫瘤細胞增殖與存活,并通過影響免疫調控使得腫瘤逃逸免疫系統的監視。此外,炎癥還可以誘導血管生成以及基因組不穩定性來促進腫瘤發展[10]。近年來惡性實體瘤繼發性炎癥則已成為研究熱點[11]。癌癥可影響炎癥級聯反應進而調節免疫系統并導致腫瘤進展或縮小。“腫瘤源性炎癥”的分子信號與致癌性突變和腫瘤誘導因素等致癌關鍵步驟相關[7]。多數腫瘤可誘導炎性微環境且與腫瘤的異質性無關。此外,缺氧是許多實體瘤共同的促腫瘤因素。腫瘤的高度增殖、血管缺陷、酸化及異常血管生存等因素,導致微環境缺氧進而激活缺氧誘導因子-1(hypoxia inducible factor,HIF-1),包括的HIF-1β和HIF-1α或HIF-2α等HIF-α亞型[12]。腫瘤釋放的生長因子和腫瘤微環境通過激活磷脂酰肌醇-3-羥激酶(phosphati?dylinositol 3-hydroxy kinase,PI3K)和絲裂原激活的蛋白激酶(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MAPK)信號通路,促進HIF-1α合成。腫瘤相關巨噬細胞(tumorassociated macrophages,TAMs)在腫瘤低氧區域激活HIF-1α后誘導腫瘤細胞表達程序性死亡配體-1(programmed death-ligand-1,PD-L1),抑制細胞毒性淋巴細胞(cytotoxic lymphocyte,CTL)活性[13]。因此,HIF-1是多數進展期腫瘤激活轉錄因子/信號通路和直接控制炎癥反應的良好例證。IL-1和IL-6等細胞因子促進癌變細胞的存活,克服癌基因誘導的衰老并促進TME的重塑、腫瘤進展和耐藥。抑癌基因p53的缺失可引起炎性細胞因子過表達,驅動腫瘤侵襲和轉移或協助克服致癌性轉化誘導的衰老[14-15]。
2 腫瘤微環境
TME即腫瘤細胞產生和生活的內環境,其中不僅包括了腫瘤細胞本身,還有其周圍的成纖維細胞、免疫和炎性細胞、膠質細胞等各種細胞,同時也包括附近區域內的細胞間質、微血管以及浸潤在其中的生物分子。低氧、低pH以及高壓是TME最明顯的特征。腫瘤通過TME減弱抗腫瘤免疫反應,維持增殖、逃避細胞凋亡以及保持炎性環境和血管生成等特征。將免疫監視功能從腫瘤清除轉向腫瘤誘發是一個涉及多個信號通路的復雜過程,受周圍組織中腫瘤細胞、免疫細胞和其他非腫瘤細胞如上皮細胞或腫瘤相關成纖維細胞(cancer associated fibroblasts,CAFs)表達的細胞因子的影響。癌癥免疫監視的促腫瘤性免疫抑制過程依賴于募集CAFs、腫瘤相關巨噬細胞(tumor-associated macrophages,TAMs)、腫瘤相關中性粒細胞(tumor-associated neu?trophils,TANs)、骨髓源性抑制細胞(myeloid-derived suppressor cells,MDSCs)、調節性T細胞(regulatory T cells,Tregs)和其他改變TME中免疫細胞數量平衡的其他細胞。最終結果是增加炎癥和血管生成,以及中性粒細胞表型從N1向N2的轉換、巨噬細胞從M1向M2的轉換和T細胞從Th1向Th2的轉換,以及CTLs與抗原提呈細胞(antigen-presenting cells,APCs)的數量與活性的降低[16]。成熟樹突狀細胞(dendritic cells,DCs)數量的大幅度減少使得有更多單核細胞前體可用以支持不斷增長的TAM2和MDSCs細胞群。隨后,這些免疫細胞間建立的細胞因子網絡相互增強,且有助于在促腫瘤為主的TME中保持免疫細胞的數量。此外,似乎轉化生長因子β(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TGF-β)、血管內皮生長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HIF-1α、趨化因子和炎性細胞因子(特別是Th2誘導的細胞因子)都與腫瘤誘導的血管生成、炎癥和免疫抑制相關聯。而這種關系似乎在CAFs和調節性B細胞(regulatory B cells,Bregs)支持下,通過IL-4、IL-6、IL-10和TGF-β由Th2、TAM2、TAN2、Tregs和MDSCs相互強化來維持[17-18]。
3 癌癥相關性炎癥與腫瘤微環境的相互作用
3.1 促炎性細胞因子網絡在腫瘤微環境中的作用
免疫細胞、癌細胞和基質細胞在TME中構成了復雜的調控網絡。在這個復雜的網絡中,通過彼此誘生、受體調節以及發揮生物效應等方式相互影響[19]。細胞因子由成纖維細胞和內皮細胞等合成,依賴于TME調節細胞增殖、存活、分化、活化、遷移和死亡。免疫細胞分泌的細胞因子也是腫瘤炎性反應的直接調節介質,不同因子互相作用誘導免疫細胞和腫瘤細胞發生功能變化,形成動態變化中的、復雜的TME,引發腫瘤惡性增殖及侵襲、轉移等生物學行為[20]。癌癥中常同時發生免疫刺激和免疫抑制,巨噬細胞移動抑制因子(macrophage migration inhibito?ry factor,MIF)、腫瘤壞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IL-6、IL-8、IL-10、IL-18、和TGF-β等細胞因子同時增加。趨化因子通過向癌細胞發出信號和重構局部微環境促進腫瘤生長和侵襲,增加轉移性病灶;另一些淋巴因子下調,則增強CTL活性并抑制腫瘤細胞生存,進而延緩腫瘤進展[21]。此外,腫瘤特異性以及非組織學依賴的細胞因子級聯反應還可能是潛在的副腫瘤性全身性疾病的表現之一。既往研究表明,IL-6、IL-8、IL-10、IL-18、和TGF-β等多種細胞因子上調炎癥反應為癌癥進展不可或缺的因素[22]。特別是部分細胞因子可以激活NF-κB和STAT家族轉錄因子,進而與腫瘤“分泌蛋白質組”的其他成分將炎性環境、腫瘤和免疫細胞聯系起來,并通過對生存因素的控制和調節TME直接促進腫瘤的形成與進展。以IL-6為例,其作用與生長因子相仿,對腫瘤細胞及TME均具有直接影響。目前已知的IL-6依賴性腫瘤包括肺癌、乳腺癌、胰腺癌、結腸癌、前列腺癌、胃癌,以及淋巴瘤、間皮瘤[23-26]。IL-6上調血管內皮生長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的表達,促進血管生成[2]。VEGF 通過促進Th17細胞的誘導和存活,調節Treg和Th17細胞之間的平衡[27];因此,IL-6對IL-17和IL-22等促炎性和促腫瘤性細胞因子分泌的影響超過TGF-β和IL-10等免疫調節細胞因子[28-29]。IL-6還能激活骨髓細胞,包括巨噬細胞和中性粒細胞,刺激其向抑制表型分化[30]。此外,子宮頸成纖維細胞上IL-6依賴性趨化因子(C-C 基序)配體 20[chemokine(C-C motif)li?gand 20,CCL20]的表達促進Th17的增殖以維持長期的促腫瘤性微環境[31]。STAT3的表達作用于IL-6家族所有細胞因子的下游,廣泛涉及腫瘤發生[32]。IL-6/STAT3通路激活基因表達抗凋亡蛋白和增殖蛋白,如上皮細胞和癌細胞中的Bcl-2、Bcl-xL、Mcl-1等,使得腫瘤抗凋亡能力增強。臨床上IL-6表達水平和腫瘤的分期、轉移以及預后息息相關。血漿中IL-6水平高的患者,往往預示著腫瘤偏晚期,并伴隨遠處轉移[33],而且預后比水平低的患者差[34,35]。由此可見,促炎性細胞因子是腫瘤微環境的關鍵調控因子,控制腫瘤細胞增殖,促進炎癥、血管生成和腫瘤轉移。此外,IL-1β、IL-11、IL-17、IL-18、TNF等的相關研究也表明,網絡化的促炎性細胞因子是腫瘤微環境的關鍵調控因子,可以控制腫瘤細胞增殖,促進炎癥、血管生成和腫瘤轉移[36]。
3.2 免疫編輯和免疫逃逸中的關鍵細胞因子網絡
在分子水平,TGF-β、Th2細胞因子(包括IL-4、IL-5、IL-6、IL-10、IL-12和IL-13)、趨化因子(尤其是血管生成趨化因子)、VEGF、炎性因子和粒細胞-巨噬細胞集落刺激因子(granulocyte-macrophage colony stimulating factor,GM-CSF)等均在腫瘤逃避免疫監視的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3.2.1 轉化生長因子(TGF-β) TGF-β信號在致癌過程中被稱為“雙刃劍”,因其在正常上皮細胞或者腫瘤發生早期可抑制腫瘤;但隨著腫瘤的發展,TGF-β信號也可促進晚期腫瘤進展以及轉移[37]。TGF-β直接抑制自然殺傷細胞(natural killer cell,NK)、巨噬細胞和CTL的殺傷活性,并能抑制NK細胞和CTL的克隆增殖[38]。Nam等[39]利用細胞因子抗體芯片技術揭示了CD8+T細胞(一種細胞毒性T細胞的前體)在TME中被破壞,進而促進乳腺癌和結直腸癌細胞存活的機制。TGF-β信號似乎通過影響B細胞群組成在腫瘤免疫編輯中扮演重要角色。雖然B細胞已知可表達TGF-β受體且分泌TGF-β,但TGF-β的作用在調節B細胞功能,特別是在腫瘤免疫編輯方面尚不清楚[38]。TGF-β通過抑制T-bet和GATA3的轉錄活性而促進T細胞群中Th2表型,影響Th1/Th2平衡并且在骨髓源性抑制細胞(myeloid-derived suppressor cells,MDSCs)的增殖中起著重要的作用,這也是其在癌癥免疫編輯中的主要作用之一。此外,TGF-β信號在血管生成中也起著重要的作用[40-42]。因此,作為對TGF-β信號的響應,多種促血管生成趨化因子為主要的MDSCs表達的細胞因子。Ⅱ型TGF-β受體基缺陷(Tgfbr2)乳腺癌小鼠模型的MDSCs分泌譜,為分析TGF-β信號增強抑癌而不是促癌提供了重要參考,并強調了髓樣Gr-1+CD11b+細胞(MDSCs)和趨化因子在腫瘤進展中的重要性[43-44]。Yang等[43]發現在Tgfbr2缺陷小鼠中的MDSCs被特別募集到TME,導致腫瘤細胞存活和轉移的增加;腫瘤大小與MDSCs的局部濃度成正比。同一個實驗室一項同期研究的RT-PCR分析顯示,來自Tgfbr2缺陷小鼠癌細胞GROα/Cxcl1、ENA-78/Cxcl5和COX2/Ptgs2的mRNA表達增加,抗體芯片技術確認Tgfbr2缺陷小鼠的腫瘤分泌的趨化因子顯著增加,包括GROα/CXCL1、ENA-78/CXCL5、CXCL16、MIP-1γ/CCL9、MIP-3α/CCL20和“調節激活-正常T細胞表達和分泌蛋白”(RAN?TES/CCL5)[44]。
3.2.2 Th2炎性細胞因子 由Th2分泌的細胞因子主要包括IL-4、IL-5、IL-6及IL-10等,主要功能為刺激B細胞增殖并產生IgG,IgE抗體,在體液免疫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機體正常時,Th1和Th2細胞功能處于動態平衡狀態,但當機體接觸抗原后,Th1和Th2細胞中某一亞群功能升高,另一亞群功能降低,該現象即為Th1/Th2漂移。由于Th1與Th2分泌的細胞因子不同,因此Th1/Th2漂移會引起體內細胞因子濃度的變化。一項基于DC-CIK的免疫治療臨床試驗發現,在非小細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患者中,已切除腫瘤的患者血漿中IL-4與IL-10濃度明顯低于未切除的患者,這表明晚期腫瘤患者Th表型更傾向于Th2,意味著IL-4與IL-10的濃度可能與腫瘤的進展有關[45]。Qiao等[46]針對SMAD4(TGF-β信號的中介體)的抑癌基因研究發現,Smad4缺陷小鼠的T細胞傾向于Th2表型,IL-4、IL-5、IL-6、IL-13在T細胞上清液中含量較高。Smad4缺陷小鼠腸道組織病理學顯示,免疫球蛋白A異常堆積,IgA+漿細胞浸潤且血清IgA水平大幅升高,與Smad4缺陷小鼠胃腸道中上皮癌進展有關。此外,MDSCs也有助于維持Th2細胞因子的表達。肺轉移癌異種移植模型中,肺溶解產物的廣譜細胞因子抗體芯片分析顯示:與正常的肺相比較,轉移癌肺組織的MMP-9、堿性成纖維細胞生長因子/FGF2、IGF-1、IL-1β、MCP-1/CCL2、SDF-1/CXCL12和Th2細胞因子(IL-4、IL-5、IL-9、IL-10)顯著增高[47]。
3.2.3 血管內皮生長因子(VEGF) 血管生成因子VEGF-A也具有抑制免疫的功能[44,48]。VEGF-A實際上是第一個被確認能抑制DCs成熟的細胞因子[44,49]。而VEGF信號更是一種與腫瘤促進炎癥及血管生成相關的關鍵因素[50]。該研究應用細胞因子抗體芯片技術對內皮細胞分泌蛋白質的檢測表明,VEGF通過VEGFR2有促炎性細胞因子的釋放的自分泌效應,可誘導內皮細胞(非白細胞)中的IL-6、IL-8/CXCL8和GRO-α/CXCL1分泌增加;相反TNF-α、IL-1β、IL-6和IL-8/CXCL8等炎性細胞因子可以誘導VEGF的表達。另外,在TME中缺氧不僅會誘發免疫抑制還能夠誘發血管生成和炎癥。炎癥和血管生成細胞因子表達之間的協調和相互強化可通過低氧誘導和NF-κB信號通路連接VEGF和COX2[50-51]。此外,IL-8/CXCL8和其他促血管生成和或促炎因子(包括TNF、IL-1、IL-6和IL-8/CXCL8)的表達,通過HIF信號、過氧化氫的產生并NF-κB信號,由低氧條件調節。VEGF作為巨噬細胞的化學引誘物還會導致炎癥和免疫抑制,而TAM則是VEGF、MMPs和炎癥因子的重要來源,特別是M-CSF/CSF1可增加VEGF的表達,因此可以在炎癥/血管生成和免疫抑制之間建立一個正反饋環路[52]。細胞外基質(extracellular matrixc,ECM)蛋白酶,尤其是MMPs可以通過對TME和周圍組織的ECM蛋白的重構促進血管生成和炎癥,同時也可在ECM中釋放VEGF及其他血管生成因子。CAFs是TGF-β、VEGF、COX2和MMPs的豐富來源,因此在TME中是血管生成和炎癥的主要因素[53-54]。
4 結論
慢性炎癥在癌癥的發生、發展、轉移以及耐藥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而癌癥的發生與惡化還和遺傳學改變的累積及調節過程失常相關。腫瘤相關性炎癥促進癌細胞的增殖與存活,并參與抑制抗腫瘤免疫。不同細胞因子互相作用誘導免疫細胞和腫瘤細胞發生功能變化,形成動態變化中的、復雜的腫瘤免疫微環境,可能引起腫瘤惡性增殖、侵襲以及轉移等生物學行為。腫瘤微環境中的炎癥與包括肺癌、乳腺癌在內多種癌癥的侵襲性和預后不良有關。盡管目前已取得了一些初步的研究成果,但仍需在細胞水平、動物模型以及臨床相關研究工作中深入推進,從而更好地完善理論框架,以明確其是否可用于評估TME和/或外周血中的免疫細胞的募集、分化、增殖和激活/極化。總之,為癌癥患者建立有效的抗腫瘤免疫反應是抗腫瘤治療成功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