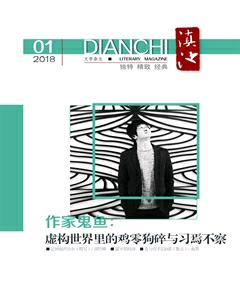與死神擦肩的七個小時(散文)
李國豪
向死而生的意義是:當你無限接近死亡,才能深切體會生的意義。
——馬丁·海德格爾
1、身體探索
那是幾年前的秋天了,我工作兩個年頭,參加單位的體檢。這是人生中的首次。按說,身體藏著秘密,該帶著某種好奇、敬畏,了解和親近。可我起初對體檢這回事是莫名輕視的,就像一頭倔強的公牛面對獸醫。
躺在 B超室的白色小床上,像躺在盲人按摩院的床上。任憑醫生用黏糊糊的棒子,在胸前和腹部滑來滑去。
“伙子,坐起來。”醫生突然叫。我很茫然地從床上彈起來。
“身體有點問題呀。”醫生說著,一揮手,叫助手拿來一瓶水,讓我一口氣喝下,又叫躺下,再次用那黏糊糊的棒子,滑去滑來。耗時許久,體檢醫生還是不太確定,他叮囑說,務必抽空到更好的醫院復查,確診之后及時手術。
手術?我對這個詞沒有概念,只在心中輕蔑地笑。想我平日里體壯如牛,能吃能喝能睡,身體又毫無癥狀,不可能需要手術。醫生說,我那是先天性膽總管囊腫,又叫擴張。人的膽像一個未脹的氣球,安靜地掛在總管上,而我居然有兩個,膽管擴張成鴨蛋那么大。
心想,既然是先天的,就說明并無什么大礙。我沒把醫生的話放在心里。甚至沒有把體檢簿交給總臺。體檢后的五年來,我與體內的鴨蛋君相安無事。
每年體檢,醫生多半會在膽囊部位止步不前。見到態度好的醫生,我會主動透露鴨蛋君的存在,并與之交流,想打探一些確切的信息。如果醫生粗聲粗氣:“躺那兒,衣服拉起來……”我就會安安靜靜地躺著,任憑鴨蛋君與醫生躲貓貓。
就真有那么一年,有個醫生告訴我:“沒事的,你這應該是個陰影。”我就照樣下床,心安理得回家,上班,運動,活著。
時間的指針進入 2014年,我已過而立。身體和思想好像都有了某種神秘的蘇醒,對待生與死的態度有了一絲變化。前三十年是上天賜予了健康和平安,三十年之后,似乎一切都變了,父母漸老,子女漸長,壯年男人肩挑重擔,一端家庭,一端江湖。天賜之福可樂享,卻不可恣意依持和浪費。
又得見身邊個別朋友,因對生活放肆,對身體和健康輕忽,讓一切本可挽回的,付諸東流,為時已晚時,卻有千般牽掛,萬般難舍,那些曾經喊著的“生死有命富貴在天”的宿命論和樂觀豪言,在病床上卻又變得幼稚可憐了。
我終于下定決心,再去探一探我身體力的隱疾。
2、生死幻想
我進了醫院。掛號,到肝膽外科問診,排隊做核磁共振。護士在我的左手腕射了一針,那針管,與獸醫給豬牛注射的針管相似,我兒時在鄉村見過,真是叫人顫栗,我看著它,像一柄明晃晃的寶劍,從我的手臂刺來。
繼而,我被棉花塞住兩耳,緩緩地往“棺材”里送,直到整個身子封閉在里頭。這時傳來一個聲音:“配合我,大口吸氣,呼氣……叫憋氣的時候,沒喊停不許呼吸。”
我在“棺材”里點點頭,那神秘的聲音,仿佛不是來自醫生,而分明是來自遙遠的異域,她是我人生的判官,我的好,或者壞,全都由她說了算。
“來,吸氣,呼氣,憋氣,呼吸。”一輪過去,再來,“吸氣,呼氣,憋氣……”這一輪,我憋著,一直憋著,卻不見呼吸的命令,我感覺快要休克了。
腦海里閃過許多怪異的畫面,那里有我趕著耕牛走過秋天的田埂,有我背著書包奔跑在雪地上,還有那些嘰嘰喳喳的麻雀,跳躍在陽光下曬著的谷粒堆上,土墻邊的月季花開得艷麗無邊,一朵一朵放大又縮小,像垂死的瞳孔。
讓我呼吸的命令還是沒有來。
我感覺自己正在喘粗氣,翻過一座高山,極目遠眺,看到遠方的城市亮著燈火,我飄起來了,飄起來了,那里有我的母親、愛人和孩子,我突然嗖的一下,身體正在下墜,嚇得張開嘴,大口大口地吸著氣。
終于等來了那個命令:“可以,結束了。”我出了“棺材”,腳板觸地,終于真切地回到了人間。
3、診室談判
拿著片子,找到門診醫生,他漫不經心地瞅了幾眼,也不對著我,恍如自言自語:“沒錯,膽總管囊腫,需要手術。”聲音輕飄飄地劃在空中,像一塊絲絨飄向窗外,與我無關,與天地無關,卻與生死相關。
沒有焦慮,沒有懸念和意外,仿佛是什么時候種下的因,早就知道的果,直到今天,我才去做了印證。
“小手術嗎?”
“大哦。”
“不做會怎樣?”
“癌變。”
“過幾年再做呢?”
“那你就等癌變了再來。”
我盯著醫生,兩相沉默,診室里氣氛凝滯,像是一個巨大的冰庫。那一瞬,診室不再是一個人為的空間,這里沒有人,甚至沒有生物,它是物理的,是化學的,是數字的,是歷史的,是分子,是原子,是離子,是塵埃,甚至都沒有語言,語言一定有溫度和情感,會讓人感到慰藉和溫暖,但我此時只感受到全身的冰寒。
十數秒后,醫生或許自覺言辭不妥,補充一句:“不明白你為什么還要等。”我們于是又展開了對話。
“我是想,身體向來很好,能吃能喝能動,平常感冒發燒都少,這么多年都沒事,卻要無端挨一刀,真是過不了那道坎。”
“你這個,也稱膽總管擴張,年齡越大癌變幾率越大。像你這樣的年齡還沒手術的,臨床上非常少見了。”
“那我現在,確定沒有癌變嗎?”
“沒有,如果癌變,你會反復發燒,黃疸發作,皮膚、眼睛發黃。”
我終于又感到了一絲溫暖,卻又看著眼前的醫生,獨自默默猜想,他像極了一個釣魚的高手。你看,他越是那樣漫不經心,我就越是這樣多疑,不上鉤,又怕死,就更加焦慮。這就是人了,人最難掌控的就是自己的無知。那些敢于搏命的人杰,心中必定清明,知道自己的想要和想得。而我的心和眼,全都是混沌。
人在當下的每個決定,都是拿著未知賭明天。歌里唱 :“跟著感覺走,緊抓夢的手,腳步越來越輕越來越快活……”那都是吹牛,大病來臨、生死攸關的時候,感覺從來不管用。endprint
我追問醫生:“手術后還會有癌變可能嗎?有哪些后遺癥?”
醫生終于認真地回答:“割除囊腫,就是永絕后患。”
我說:“那做吧!”
4、手術臺上
手術前夜,加班到很晚才進醫院。漂亮的護士拿著剃刀,命令我睡下,要剃除隱秘部位的毛發。我看著白色的天花板,那昏黃的燈罩里,跑進許多黑色的蟲子,像我此時腦海中的心猿意馬,某些部件不聽使喚地腫脹起來。
第二天清晨,我進了手術室。那兒一溜兒地擺著等待手術的患者,一排一排赤條條的,好他娘的像個屠宰場啊。我一直想象著,醫院應該是最有溫情的地方,它給生命第二次機會。
看了手術室的景象才知道,醫院是最接近地獄的地方,盡管你看不到,但有一個又一個死神,握著鋒利的刺刀,在你赤裸裸的身子旁徘徊。而醫生們剛好是拿著手術刀與死神搏斗的英雄。我表面沒有什么病。我自己爬上了手術臺。
護士來穿刺,一根 3厘米左右長、項鏈那么粗的管子,從鎖骨處進入,護士一邊穿一邊對身邊的實習生講解:“管子一定要緊挨著鎖骨進入,聽到沒,還有嚓嚓聲。”
醫生站在我旁邊,談論著電影,還有書,聽著聽著我就昏睡了過去,那是麻醉的魔力在起作用。
我在夢里,依然編著副刊,投稿的文章寫得真爛,丟掉一組,就罵一句,左一句右一句地罵,果真是罵了許多作者,卻硬是難見一組好稿,急呀,急得暴跳如雷……終于把我急醒了,這才發現冰冷的身子躺在手術臺上,我急促地喘著氣。周圍吵嚷不堪,醫生護士都在忙亂。腹部的刀疤隱隱作痛,有個護士跑過來給我戴上氧氣罩,將我推出手術室。
母親、妻子、姐姐一溜兒跟了過來。嘴里不停地喊著,出來了,終于出來了。那急迫和焦慮令人聽著心痛,我用眼角的余光掃了一眼母親,她那布滿皺紋的臉上,半是痛苦,半是祈求。
術前我問醫生,需要多長時間,一個半小時差不多了吧?手術醫生若有所思地笑笑說:“一個半小時恐怕不行哦,兩個多小時吧。”
對呀,不就是兩個多小時嗎,家人為何急成這樣?事先我也安慰過他們:“不要著急,醫生說了,最多兩個多小時就出來了!”一問才知,我手術了七個多小時,上午 8點進去,下午 3點才出來。家人以為,我肯定出什么問題了。
5、向死而生
在監護室里,不許喝水,不許進食。護工是兩位大姐,晝夜輪流值班。她們的長相分不清,都帶著口罩。每天,我與她們都是這樣展開交流:
“大姐,我好渴。”
“好,抹抹嘴皮吧。”
一個人走過來,拿起棉簽在杯子里沾點水,在我的嘴皮上抹幾下。我咂咂嘴,這一瞬間真是人生中最甜蜜的時刻,可是它太短暫了,最多兩次,大姐必然放下。于是我會央求:“大姐,多抹幾下。”
“不行的,醫生不讓哦。”大姐說完,留下一個堅決的背影,踩著碎步離開,鞋子在地板上擦出刷刷聲,病房里就更加安靜下來。扭頭看十五樓窗外的藍天,突然覺得這個世界滑稽起來。
手術前一晚,我要洗腸,必須在兩小時內,喝完 5杯 700毫升的水。那一刻,水跟我結下了深仇大恨。手術后那段日子,不能吃也不能喝,護工大姐用棉簽沾來的一滴水,都成了人間最寶貴的甘露。
躺在病床上的那些天,最讓我痛苦的是插在鼻腔里的那根胃管,十幾二十厘米長,筷子那么粗,就這樣傲然從鼻腔插進胃里,翻身、搖頭、呼吸……我做任何事,它都會引起一陣惡心,感覺就要天翻地覆。它勝過一尾毒蛇,尾巴甩在我的脖子邊,三角的頭在胃里搖晃不停。
我是一個意志極其薄弱的人,易馴服又膽怯。只要手上插著一根小小的針管,就動都不敢動,小心翼翼,怕疼怕癢。我左邊病床上的那個老人,卻兇猛得不得了。他都八十二歲了,手上插著針管輸著液,卻獨自爬起爬落,一下翻箱倒柜找衣服,一下翻身下床上廁所,動作敏捷,視手上那條管子若無物。
姐姐跟我說,那年我大哥在醫院做鼻息肉手術,醒來后發現插著一根尿管,感覺極不自在,伸手一拔,自個兒上廁所去了。而護士幫我拔尿管,尿道口有火燒的感覺,渾覺火山就要爆發,不禁全身起雞皮疙瘩。
我做事從來小心謹慎,對待自己的身體更是謹小慎微。大書法大家啟功先生躺在牽引床上還吟《西江月》,他寫自己做頸椎牽引術:
七節頸椎生刺,六斤鐵餅拴牢。
長繩牽系兩三條,頭上幾根活套。
雖不輕松愉快,略同鍛煉晨操。
洗冤錄里每篇瞧,不見這般上吊。
這般自嘲,這般愉快,全把痛苦拋身外,而我只想著毒蛇、針管,自嘆弗如。
6、佛光晚唱
湯匙稀飯,喝幾口排骨湯,吃三片蘋果,再不敢貪歡。養病期間,讀胡蘭成《今生今世》,那文字緩慢,心境漸漸平和。
到走廊上放風,腦海里全是大魚大肉。想起菜市場里煮熟的臘肉,油珠子在小店的燈光下,泛著耀眼的光芒;想起超市里那些火腿,切口渾如鮮艷的玫瑰;又想起云南正是吃菌的季節,一小籃一小籃新鮮的菌子,嬌嫩的朵兒上還滾著露珠,煎、炸、烹、煮、蒸都爽口。那些平日全是普通的菜式,如今都成了我的人間至味。
有一晚放風,終于讓我忘記了口腹之欲。前面走著個中年婦女,哼著一串聽不懂的旋律。她身穿長裙,外披黑衣,原來已是秋意襲人。她左手握著佛珠,右手微曲放于右懷。聲音發自她的胸腔,又像來自高原的風里,唱得動聽,溫婉如慈母的童謠,低沉如古剎的舊鐘,悠揚如急風里的經筒,柔美如細雨中的燕語,我瞬時如沐晨曦,全身好不舒暢。
聽了一會兒,我肯定她是念著藏經,于是輕輕地一路尾隨。我到過藏區,知道誦經的吉祥,就幻想著沐浴在一片佛光里,有些自在,有點忘懷。
這位樸實而高貴的女士,可能是某位病人的親人,也許她在為家人祈福,亦讓我同享,只是,她不知我,我亦不知她。現在又想起她來,我亦為她祈福。
7、病房諸友endprint
康復離開醫院很久,我依然會不斷想起那里的人事。
手術初愈,每餐不敢多吃。每晚吃幾有個做事風風火火的護士,長得極像
陳慧琳,話音脆如鈴響,生生打地上。有天晚上我頭痛欲裂,無法入睡,她火速回告醫生,回來給我打了一針,立馬泰然入夢。
病友 A,騎車與人相撞傷了脾。手術后,精力旺盛異常,從早到晚一直講電話,我就聽著。他先打給甲:“喂,我那照 CT的片子是你收著嗎?”“ ……”“好的,收著就好,明天交給醫生。”他又明知故問地打給乙:“喂,我那照 CT的片子是你收著嗎?”“……”“怎么,明明是你收著的,趕快幫我找。我的事你們這么不在心,你們的事以后我也不管了。”我聽著聽著就樂了,這是個孜孜不倦地尋找存在感的人。
病友 B,來自宣威,也許他不滿足護工的照顧,又或許是天性使然,他發起糖衣炮彈,對著護工大姐說:“大妹子,你與我們既不沾親,也不帶故,卻幫我們端屎端尿,服侍得像親人一樣,天底下哪有這般好人!”
護工大姐感動得話音顫抖:“大哥,你咋個這樣子會說話,這是我們該干的工作。”我聽著他們就這樣越聊越親切,這位病友自稱開著公司,可幫助護工大姐的老公找個工作。
“不知你家那位,會些哪樣技能?”“駕照倒是有。”“哦,可惜了,我們公司暫時倒是不要駕駛員。”一來二去,護工自然就把他老鄉照顧得服帖周到,搖床、倒水、拿尿壺……都像自家的人。
病友 C是位中年女性,前一分鐘還用手機聽著王強:“初秋的天冰冷的夜 /回憶慢慢襲來 /真心的愛就像落葉”,后一分鐘卻傷心地哭。聽說丈夫在她入院前一天出差北京,現在她都出了監護室,還不見人影,她傷心他“秋天不回來”。
病友 D是我的鄰床,叫李平安。次日要做手術,他一直等著麻醉醫生來簽字。等啊,等得焦急。他就對護工說:“我到外面抽根煙吧。”他剛走,麻醉醫生就來了,看病床上無人,二話不說轉身就出去了。
等啊,還是焦急。平安又對護工說:“我上個廁所。”他剛如廁,麻醉醫生就來了,看病床上無人就想轉身走,護工說:“他在廁所呢,應該快出來了。”左等右等,不見出來,原來他是出恭整大的,麻醉醫生只得說:“明早手術前再簽吧,來得及的。”
平安先生總是一遍遍地與機會擦肩而過。第二天手術完畢,平安先生都已經回到病房了,家人一個都沒有到,他急了就打電話,幾乎是吼著:“你們是來旅游的嗎?”聲音悲傷地擠在喉嚨處。
人這平凡一生,從生到死只有三地最重要,甲地是家庭,乙地是單位,丙地是醫院。我是幸運的。姐姐遠道來看我,家人常伴左右,痛了有藥,渴了給水,哪怕是一滴,也是滴水之恩。一切都在自然中,不濃不淡,不離不棄,是活在真實的人世。
道家說,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七個小時與死神擦肩而過,二十天后終于回到生活。一場手術真是一場修行,大道之行,在虧盈得當,在平衡,在中庸,在不多也不少,在不怨也不恨,在不貪也不
棄,在于珍惜。
責任編輯 馬成云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