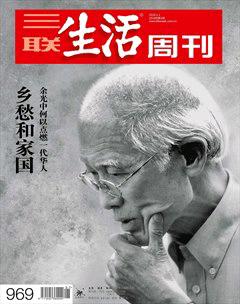在餐桌上走向滅絕的禾花雀
王海燕+黃子懿
禾花雀,一種上世紀80年代依然廣泛分布于亞歐大陸的雀形目候鳥,在短短不到30年里,已經與野外滅絕只有一線之隔。如今,在中國的遷徙路上,它依然面臨著天羅地網。
黃胸鹀的20年:從家常小鳥到瀕臨滅絕

黃胸鹀雄鳥(攝于江蘇張家港沿江)?;
作為一名觀鳥愛好者,陸建樹說,他真的不能接受,一個自己曾目擊過的物種,突然有一天被別人告訴,已經“滅絕”。12月23日下午2點,根據他的指點,我從天津西站地鐵口往西,果然看到提著鳥籠的大爺陸續出現,再往前,密密匝匝的人群聚在西青道輔路上,把兩車道的道路塞得水泄不通,間或有車輛通過,只能扭拐著從人群里擠出來。人群一團一團杵在路上,綿延了超過300米,包裹在他們中間的,是沿街鋪開的鳥販子。
這里是天津最新最大的鳥類交易露水市場,每周六下午固定開市。清一色的中老年男人,籠著袖子,在評論籠子小鳥的叫聲、羽毛,討價還價,談笑風生。小鳥大都被細棉線捆著翅膀或尾巴,撞籠、怕人、毛亂,在籠子里擠成一團,拼命往角落里縮。這樣的鳥通常都是剛剛從野外捕回來的,還沒喂熟。
問了一圈,沒有黃膽,鳥販子熱情地推銷,“黃巧(黃雀)也差不多,您看看這?”實際上,差得多了。黃膽就是禾花雀,學名黃胸鹀,2017年12月5日,在世界自然保護聯盟一年一度的瀕危物種紅色名錄更新里,黃胸鹀的受脅程度剛剛從瀕危升級成極危,離野外滅絕一步之遙。

2012年11月16日,在福建泉州境內發現的捕鳥網上密密麻麻地網住了許多候鳥
瀕危物種紅色名錄更新那天,動物保護圈子炸開了鍋。人們憤怒的原因很簡單:一是黃胸鹀的受脅等級上升太快了,2000年,這還是一種被認為“無危”的普通候鳥;二是黃胸鹀受脅等級上升的原因,根據世界自然保護聯盟的分析,“來自中國以供食品消費的非法捕捉是最大威脅”。而在中國的輿論場上,人們還有一個指向更加明確的尖銳概述:“黃胸鹀被廣東人吃絕種了。”
比起“黃膽”這個在北方籠養鳥交易市場上的名字,黃胸鹀在珠三角地區的俗名禾花雀更加廣為人知。作為一種典型候鳥,黃胸鹀可能是起源于澳洲和美洲新大陸的古鹀,穿過白令海峽進入亞洲,進化后擴展至歐洲的種群。在沒有國界的飛鳥世界,黃胸鹀的分布范圍曾經極其廣泛,光繁殖面積就多達1570萬平方公里,西至芬蘭,穿過俄羅斯,東到太平洋沿岸,日本北海道,南抵中國黑龍江和內蒙古,橫貫歐亞大陸,是中國領土面積的1.6倍。據估算,上世紀80年代,黃胸鹀在全世界的總數量超過1億。
繁殖季過后,黃胸鹀會從繁殖地往南遷徙,穿過中國,到達東南亞越冬,次年春天原路返回。雛鳥期的黃胸鹀吃蟲,在遷徙路上則吃高粱、水稻等各種谷物,尤其喜歡揚花后剛剛灌漿的青稻米,這是“禾花雀”一名的來源,也是黃胸鹀最早在中國引起注意的原因。1956年,中國開展“除四害”活動,一開始,麻雀因啄食谷物,與老鼠、蒼蠅、蚊子并列四害,與麻雀身形相似的黃胸鹀也被重點點名。1956年,一篇題為《麻雀與雀害》的文章稱“鹀類在我國境內最形繁多的,莫過乎黃胸鹀”。
畢業于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的生態學博士朱磊告訴本刊,在麻雀被“平反”之前的1960年前后數年間,是中國學術界對黃胸鹀研究最集中的時期,根據這一時期的資料顯示,即便除四害曾提倡捕捉雀鳥,但在其間和其后,黃胸鹀仍然數量極多。1958年夏秋和1959年夏,研究者者在武漢南湖地區統計到的遷徙黃胸鹀達數萬只;1959年,在廣東珠江三角洲的捕鳥網場,一張網一晚上就能捕到3000~4000只黃胸鹀。
到了80年代,1985年春,英國劍橋大學學生馬丁·威廉姆斯造訪北戴河,并從1986年連續5年秋天在這里觀察候鳥遷徙,在馬丁編寫的當地鳥類名錄中,對黃胸鹀的數量估計是常見且大量。另外,黃胸鹀在中國還有諸多別名,比如京津一帶的“黃膽”,內蒙古和東北的“黃肚囊”“黃肚皮”“黃豆瓣”“烙鐵背”,在湖北、湖南和江西等地的“麥雀”“麥黃雀”“蘆雀”,河北的“稻雀”、廣西的 “秧谷鳥”,也有地方直接將其與麻雀混雜。這些跡象都表明,黃胸鹀在中國曾經非常常見且分布廣泛,正因為如此,使得黃胸鹀曾經鮮少為人關注,直至今日,當我們采訪時,依然找不到對黃胸鹀有專門且深入研究的學者。
壞消息是從其繁殖地芬蘭、俄羅斯和日本陸續傳來的。芬蘭和俄羅斯從上世紀80年代早期開始,就對黃胸鹀有過持續的數量監測。俄羅斯的兩個站點在1979年和1990年環志過黃胸鹀,就是捕捉后套上腳環放歸,兩個年份的環志數量分別是10460和1346,呈斷崖式下降。日本北海道的黃胸鹀則是從1997年開始直線下降的,直至在部分區域完全消失。2004年,英國東方鳥類俱樂部通訊上的一篇短文首次指出,根據中國內地的新聞報道,黃胸鹀正面臨巨大的捕獵壓力。
坐實黃胸鹀在中國被捕獵至瀕危的研究,是2015年發表在美國重要學術期刊《保護生物學》上的一篇文章。這篇文章收集了全世界從1980年至2013年間跟黃胸鹀有關的所有數據,結果顯示,1980年到2013年間,黃胸鹀的數量下降了84.3%~94.7%,其在歐亞大陸北回歸線以北的繁殖范圍,從西北到東南逐步且極其快速地收縮了5000公里。到2012年,俄羅斯的歐洲區域,西伯利亞中西部、哈薩克斯坦,這種曾經遍地聚群而飛的小鳥已經完全絕跡,那些地方的人們再也沒見過它們靈動而鮮艷的身影。

被捕鳥網纏住小鳥拼命掙扎,精疲力盡后死去(攝于2014年10月江蘇鎮江市郊)?;
過去人們以為只有那些較小地理范圍內的稀有物種會面臨來自人類的危險,容易滅絕。分布如此廣泛、數量如此眾多的一個物種呈斷崖式崩潰,在生物學界既罕見且出人意料,幾乎是前所未見的。研究者們百思不得其解,設想了各種可能,比如棲息地收縮和環境污染導致死亡率上升,或者兩種情況兼有,但都不能解釋黃胸鹀種群的崩潰式下降。
另一種猜測是中國的捕獵導致了這一情形,研究者們設想了一個模型,以1980年的1億為基數,第一年捕獲總量2%,結合其繁殖特性,其后捕獲比例每年增加0.2%,得出的結果是,黃胸鹀種群下降的曲線與實際情況幾乎完美耦合。
為什么是禾花雀
研究者們的結論有其數據根據,不是來自學術界而是新聞報道。以廣東佛山三水曾舉辦過禾花雀美食節為例,根據公開報道,僅1996年,該節慶市場上黃胸鹀的交易數量就達數百萬只。
很難追溯黃胸鹀最早是如何被選中的,來自廣州的“70后”美食攝影師張張無忌告訴本刊,禾花雀在廣東算一種傳統食品,尤其是從他的上一輩,政府宣傳禾花雀為害稻谷,號召農民廣泛捕捉。人們很快發現,和其他同樣大小的雀鳥相比,禾花雀多且肥,采用焗、燜等做法,有大閘蟹的口感。國際鳥盟亞洲部主任研究員陳承彥是廣東人,他小時候也聽自己的父輩和祖父輩說,廣東人過去抓禾花雀吃非常常見,只是很少販賣。
真正讓禾花雀身涉險境的,是珠三角區域經濟發展后來自消費市場的需求。根據《三水縣志》,1992年10月5日至11月5日,三水縣人民政府舉辦首屆禾花雀美食節,“全縣酒家賓館名廚,各顯身手,做出菜式眾多的禾花雀宴席,以饗嘉賓”。三水縣(今佛山三水區)西接高丘,東臨廣州,同時三江匯流,曾經每年晚稻揚花的20天左右,禾花雀會從這個狹長的地理區間里集中過境。
實際上,佛山三水地處珠三角西北尾端,相對落后,當時三水政府為了發展當地經濟,舉辦了一系列各類營銷類節日,禾花雀節即是其中之一。根據《三水縣志》,最開始,當地人吃禾花雀只有“焗”一種做法,經過大力推廣,后來又發展出了數十種東南亞口味的新菜式,逐漸成為秋末冬初的時令進補食物。禾花雀個頭小,處理后上餐桌的成品,有的全只不足一湯匙,一桌宴席消耗百來只也稀疏平常。但直到1996年的一篇文章里,一位廣東的鳥類研究者在一篇名叫《天上人參禾花雀》的文章里,依然認為“它們明春返回北方繁殖出新的一代,不用擔心會造成禾花雀滅絕的危險”。
除了三水,廣東從化、四會、清遠等地,都是捕捉禾花雀的集中區域,每到遷徙季,這些地方捕捉的禾花雀會流入整個廣東地區的餐館酒樓。張張無忌甚至記得,他在1996年左右上大學時,街面上有小吃推車,小販們都樂于將乳鴿和其他鳥類標榜成禾花雀兜售。
在“天上人參”的美譽下,食客篤信禾花雀營養豐富,甚至補腎壯陽,消費市場對禾花雀的需求不減,隨著禾花雀數量減少,甚至漸漸從平民食物發展成高端宴請補品,價格也逐漸逐年翻番。根據1981年就簽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日本國政府保護候鳥及其棲息環境協定》,廣東省林業廳1997年5月17日就發函,取消了三水的禾花雀美食節。2000年,中國制定首批“三有保護動物”名錄,其中包括黃胸鹀;2001年,廣東省林業廳還將禾花雀列入廣東省重點保護野生動物。但明令禁止下,龐大的地下交易市場持續存在,捕捉甚至早就擴散到廣東省外。
根據民間環保組織“讓候鳥飛”項目組的不完全統計,2000年至2005年,新聞公開報道的禾花雀盜賣案件,屢屢出現倒賣數量過萬的大案。其中2001年8月廣州韶關的火車上一次甚至查獲了10萬只禾花雀。隨后,從2005年到2013年,交易環節上的禾花雀明顯減少,但每年各地依然屢屢曝出單案過千的禾花雀查獲數量,2013年11月,警方在安徽東至還查獲過兩萬余只禾花雀。這種鳥兒依然在被源源不斷地送上廣東的餐桌,根據“讓候鳥飛”志愿者的暗訪,除了一些梅州、潮汕偏遠地區之外,珠三角很多餐館依然在用“荷花”“荷葉”等暗號代替禾花雀以供售賣。
但一個疑問是,為什么黃胸鹀繁殖區域如此廣袤,還能被集中捕獵至極危?這跟黃胸鹀的遷徙路線有關。黃胸鹀雖然從西到東的繁殖區域跨度達數千公里,但從中東到中國新疆,從地圖上看,都是土黃的干旱區域,不適宜黃胸鹀生存,再往東還橫亙著高聳的青藏高原。迄今為止的觀測數據都顯示,體形小巧的黃胸鹀可能主要都是從西到東,飛越數千公里,入境中國,再抵達華南和東南亞的越冬地點。
在入境中國的關口,燕山山脈一直逼近海邊的秦皇島,留下環渤海灣成為遷徙鳥類集中南遷的咽喉地帶,黃胸鹀同樣會密集地從這里入境南遷。再往南,黃胸鹀的遷徙路線更加分散,因此在華北、華中和華南都廣有分布。但到達其越冬地點時,在云貴高原和太平洋的夾擊下,黃胸鹀的遷徙路線會再次向兩廣地區更狹窄的范圍收縮。
正是這樣的遷徙線路,為大量捕獵黃胸鹀提供了“天時地利”。根據《保護生物學》那篇文章的統計,黃胸鹀非法捕獵被查獲最集中的正是黃胸鹀每年春秋遷徙往返,入境和出境中國的“瓶頸”津唐地區和廣東地區。捕獵從這兩端向中間擴散。一名曾經的捕鳥人告訴本刊,北方最早捕鳥是從天津唐山一帶開始,隨后這種捕獵之風,隨著黃胸鹀的飛翔一路向南擴散。另一邊,2006年,《楚天都市報》登載過一則新聞,當時三名來自廣東、海南的商人到湖北荊門夢溪鎮,租用了三畝湖區,種植象草,聲稱造紙。后來當地村民卻發現,三名南方人是在等著禾花雀遷徙過境,張網捕獵,因為黃胸鹀晚上喜歡在濕地象草叢里集群歇息。當地村民報警后,警察在捕鳥人的絲網上發現950多只禾花雀。這則新聞的背景是,當時廣東本地的捕鳥人已經很難在春秋兩季捕捉到黃胸鹀了。
積少成多的貿易鏈條
如今,出現在廣東餐桌上的黃胸鹀幾乎全數來自北方,尤其是天津、唐山一帶。陸建樹就曾是一名天津的觀鳥愛好者,他終身難忘的一個場景是,2015年冬天,他隨一位買家去到一個鳥販子家里,那是一棟城中村的一七層小樓,大鐵門,門口拴著兩條大狼狗。進門后,陸建樹看到,每層樓除了樓梯共有三間房子,鳥販子一家住在7樓,而從1樓到6樓,每間房間都是柵欄門,鐵紗窗,門里是密集的各種各樣的鳥,在徒勞地撲騰,地上則堆滿了厚厚的鳥糞和鳥尸。陸建樹感覺自己到了一座“鳥類的奧斯維辛”。在那里,鳥販子驕傲地對他說:“只要天津有的鳥,我這里都有。”最終,陸建樹生平第一次在這里見到了成百上千的黃胸鹀。
陸建樹知道,這些黃胸鹀不是一次抓起來的。陸建樹從2012年開始觀鳥,2013年,黃胸鹀被世界自然保護聯盟提升為瀕危級別,他開始注意這種原本平淡無奇的鳥類。在文獻上,陸建樹看到很多關于黃胸鹀喜歡集群的描述,還曾看到過一網捕捉上千只的記錄,但在實際的觀鳥過程中,他從沒看到過30只以上的黃胸鹀鳥群,更無法想象僅僅20多年前,人們還可以見到的數百只巨大鳥群到底是什么樣子。
陸建樹說,在天津、唐山一代,捕鳥人分為三種:一種是無所事事的大爺,只要看到有塊荒地,就像釣魚一樣,早上騎個自行車把鳥網鳥夾往那一放,沒事過去看看,收到鳥兒了,有販子收就賣掉,沒人收就摔死或放掉。第二類是農民,冬天天地撂荒了,會有鳥販子專門過來給他們發放粘網和錄音機,粘網捕鳥,錄音機則是播放鳥叫誘鳥的,鳥網5元、錄音機20元,就算在捕到黃胸鹀后的價格里。這樣的生意,不需要任何成本,農民都樂意干,發展到后來,所有農民都在自家的地里張網“等收成”。而黃胸鹀面臨的情況,則是漫山遍野一層一層連接不斷的鳥網,飛往何處都沒有生路。第三種捕鳥人才是“專業”捕鳥人,會設計專門的機關捕捉猛禽。
黃胸鹀個小,無法專門捕捉,因此,市面上幾乎所有的黃胸鹀都來第一類和第二類捕鳥人。除了繁殖季節,黃胸鹀喜歡集群活動,夜晚也喜歡聚群棲息在有水的植物叢中,受驚嚇后容易竄落而非高飛,同時在一些遷徙時段,容易被同類叫聲吸引。這些特征都使得捕鳥人不斷開發出了更容易捕捉黃胸鹀的網捕手段。
如今在做反捕獵的志愿者劉偉就曾是這樣的捕獵者,他從2008年開始捕鳥,2013年后洗手不干。他告訴本刊,捕鳥的網一般都下在蘆葦溝子邊、稻田、玉米地和高粱地里,一塊地100張網的成本一般1500元,可以使用20天到一個月。而2008年,一個普通散戶一天都能抓100多只,不光是禾花雀,還有朱雀、金鐘(栗鹀)等,高峰時一天能掙1000~2000塊錢,最高正4000~5000塊的都有。“暴利,(賺回買網成本)不是一天就完事兒了?”他說那時候天津地區的養殖戶非常多,有的莊子幾乎家家戶戶都養,養到2萬~3萬只規模的也很多。
在廣東地區,一般野外捕捉的黃胸鹀就很肥厚,但天津、唐山一代秋天剛剛捕捉的黃胸鹀,一般都很瘦,因此養的意思就是催肥,用蘇子、芝麻、小米、葡萄糖、維C,還有一種叫“速達肥”的家禽添加劑飼料,養20天左右,到了達到6斤(100只)后悶死。催肥后的黃胸鹀胸前一吹毛看不到肉,全是黃色的油,行話叫“大油”,跟不催肥的個體價錢差一倍。采取悶死的辦法一是省事,二是方便運輸,三是為了帶血,因為食客認為這樣可以壯陽。悶死后的黃胸鹀連毛帶屎,一般以100只為一個食品兜的單位裝泡沫箱,一個泡沫箱能裝10~12袋,用膠帶封好,密閉保鮮,通過飛機運輸銷往廣東。一只黃胸鹀養20多天的成本在1元左右,而2008年養戶從捕鳥人手里收是15元一只,賣到天津25元一只,到廣東40~50元一只,依然暴利。
2000年左右,劉偉還在當兵,有個朋友是薊縣地區的,在蘆葦溝邊下網,晚上拿桿子在蘆葦溝里一轟,網上便全是禾花雀。劉偉的這個朋友一天曾逮過400多只,開車到天津賣,4元錢一只。但陸建樹2014年開始跑鳥市時,跟養戶聊天,說一個捕鳥人一次捕到的黃胸鹀,從來沒有超過三四只以上的,小養戶養到三五十只賣給大養戶,大養戶攢到成百上千只了再向廣東發貨。
天津向廣東供應黃胸鹀的地下鏈條最早起碼出現在2000年以前,天津曾有一名叫袁良的中學自然課老師,從上世紀就開始關注黃胸鹀,根據他還未出版的手稿,他曾在1997年到1999年秋季的收鳥站,看到用麻袋運往廣州的黃胸鹀,他還聽說當時廣州餐廳上,一餐禾花雀要四五百元。
在陸建樹看到的貿易鏈條里,黃胸鹀主要走公路運輸發貨。而且,從天津進入遠程運輸貿易鏈條里的鳥類里,只有黃胸鹀、栗鹀、黃眉鹀,還有少量普通朱雀四種。這四種鳥天津本地人不吃,是為南方的餐飲市場專門捕捉的。根據陸建樹的分析,最早貿易的可能只有黃胸鹀,隨著黃胸鹀減少,與黃胸鹀體態相近的栗鹀進入視野,黃眉鹀和朱雀可能也是同樣的原因。發貨時,幾種鳥價格分明,分裝清晰,這意味著無論捕鳥人還是鳥販子,針對性都非常強。因此,如果沒有針對性的保護和打擊措施,捕獵情況不僅不會有所好轉,相反,同樣的種群下降趨勢還會出現在其他鳥類身上。
拯救黃胸鹀?
志愿者們也組織過廣泛的拆網行動,“讓候鳥飛”的志愿者曹大宇已經連續三年拆網了,他在盤錦錦州交界地帶,拆過很多網,一排100米長,一天都能拆20多排。他說最開始捕鳥人還跟志愿者聊天,告訴他們一些行規,現在看見志愿者就跑,有時候還起沖突。
除了拆網,志愿者們幾乎沒有別的辦法直接挽救黃胸鹀。雖然在世界自然保護聯盟的瀕危物種紅色名錄里,黃胸鹀已經連續升級,中國2017年開始施行的《野生動物保護法》也將野生動物消費者列入犯罪,但在中國,黃胸鹀的級別依然停留在和麻雀相同的“三有保護動物”,捕鳥人即使被抓住,也不會受到有效的責罰。“讓候鳥飛”項目執行長劉慧莉告訴本刊,他們在暗訪中發現,根據法律,非法張網捕鳥達20只以上的,捕鳥者將受到刑事處罰,鳥販子就經常以19只的數量,分批運輸賣給餐館。
在陸建樹看來,拆網很直接,但也最無用。“今天拆,明天又張起來了,最便宜的普通鳥網一張兩元錢,拆10張20元,逮兩個黃胸鹀32元,還賺了。”他最常使用的辦法是報警,但主管捕鳥的是林業局森林公安,對黃胸鹀這種“普通”小鳥,森林公安只能當場放飛了事。而放飛的黃胸鹀遇到的依然是層層疊疊的鳥網,這是讓陸建樹覺得最恐怖的地方,“都是點點滴滴匯集起來的。”他曾和小伙伴討論過,覺得只有打擊取締大規模養戶,才能真正有效果。
但真正與捕鳥人、小養戶和大養戶長期接觸,試圖挽救這些被捕小鳥的,實際上是另外一個群體:放生人。陸建樹是2015年開始接觸這個群體的,放生人每到固定的日子,就會有領頭人號召大家捐款放生,然后同時去捕鳥人、小養戶和大養戶手里購買活鳥。因為黃胸鹀的珍稀,放生人同樣愿意購買黃胸鹀放生,光2015年,陸建樹就見識過三次放生人放生黃胸鹀的場面。
兩次在平津戰役紀念館前的空地上,一次就在鳥販子家院子里,最多的一次,放生數量達到2000只,那也是陸建樹真正見到黃胸鹀最多的時刻。陸建樹用“慘烈”來形容那個場面:到了固定的放生時間,鳥販子把鳥籠拉到放生人面前,放生人一手交錢,鳥販子一手將小鳥一只一只從籠子里捉出來,報數放飛。放生的人興致來了,也親自上手,有時候還撥弄幾下。放完生,放生人和鳥販子都滿足地離開。
但那些放飛的小鳥,能活下來多少?陸建樹估計一半都不到。一方面,這些鳥本來已經受了巨大的應激創傷;另一方面,同一種鳥類,突然密集地出現在一個區域內,不管食物、庇護、飲水還是人為擾動,都是致命的。陸建樹曾在放生第二天去過現場,看到地上一片鳥尸。陸建樹發現,很多放生人甚至沒有基本的生物學常識,他甚至見過給猛禽喂小米的,猛禽不吃,就硬往嘴里塞。他告訴過這些放生人,小鳥能從捕捉活到放生的可能只有1/10,而這1/10放生后同樣生死未卜。但放生人似乎無動于衷,他們更在意放生這個善念被實現的過程。
根據陸建樹的了解,天津的放生市場是從2011年到2012年左右開始興起的,算是橫插進原來食品消費鏈條中的一環。如今,這一環同樣在劇烈地影響捕鳥活動:一是放生交易周期更短,深受鳥販子歡迎,并且數量需求極大,在整個消費鏈條里的比重已經相當可觀;二是有鳥販子曾告訴陸建樹,如果沒有這些放生人,他們捕鳥只針對性地捕捉固定鳥種,其他鳥要么摔死,要么放掉,但有了放生需求,所有的鳥都可以換錢。陸建樹曾見過飯都吃不起也要放生的人,他理解這種心情,但實在無法認同,某種程度上,監管空缺下催生的放生市場正在讓黃胸鹀乃至所有的野生鳥類處境雪上加霜。
現在陸建樹在野外見到黃胸鹀時,心情特別復雜,他為自己感到幸運,“我竟然能夠看到它們”;也為被看到的黃胸鹀感到幸運,“還能活到現在”。他說那是一種看一眼少一眼的心情。熟悉生物保護的人都知道“美洲旅鴿”的故事,當歐洲人剛剛踏上北美大陸時,這里生活著50多億只旅鴿,隨著人們發現這種鴿子肉味鮮美,開始大規模地工業捕獵,隨后,在不到100年的時間里,1914年9月1日,最后一只人工飼養的雌性旅鴿在美國辛辛那提動物園中孤獨地死去,這個物種從此徹底在地球上銷聲匿跡。
沒人知道,黃胸鹀會不會成為下一個旅鴿。中國觀鳥記錄中心在過去一年里,只在34個地方記錄到了黃胸鹀的身影,而其中多達20個地方,觀鳥人在數小時的守候里,都只看到了一個孤零零的淡黃身影。這個身影還會沿著古老的,而今遍布殺機的遷徙路線,跨河跨湖,一年往返兩次,它無法述說它是否曾有同伴,它的同伴們都去了哪里。
(感謝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生態學博士朱磊,新西蘭奧塔哥大學自然影像科普博士朱雷,觀鳥愛好者漆青山提供的資料和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