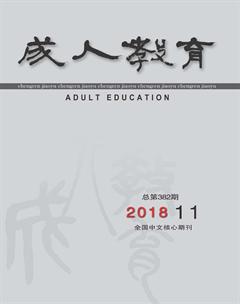農民工培訓政策研究述評
袁小平 王娜
【摘 要】培訓作為就業促進的重要方式,是一種重要的機會福利,只有從社會福利的角度分析才能更契合培訓的實質。當前的農民工培訓正面臨著“多而無效”難題,通過引入社會政策的新視角,分別從福利供給者和行動者角度討論國家、市場和社會三個主體在當前農民工培訓政策中的角色與責任,可以較好地找尋出農民工培訓政策失靈的結構性原因。對國內學界關于國家、市場與社會在農民工培訓領域內角色與功能的研究進行綜述,發現既有研究存在隔離式研究取向,僅側重關注三者的某一面向,而對三者的合作研究關注相對不足。下一階段的研究應更多從治理視角出發,從制度、行動兩方面加強農民工培訓主體間的關系研究,才能破解當前農民工培訓“多而無效”的難題。
【關鍵詞】農民工培訓;國家;市場;社會
【中圖分類號】G72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794(2018)11-0060-08
一、農民工培訓與社會政策的關系
培訓作為一種重要的機會福利,有助于促進機會平等,它是當前世界各國促進就業的重要手段。從社會福利的發展脈絡來看,隨著凱恩斯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在上世紀相繼遇到“社會危機”,安東尼·吉登斯提出的“第三條道路”這一社會框架逐漸被福利國家所接受。他主張建設積極的福利社會,強調“無責任即無權利”的福利觀,提倡對人力資本投資,實行發展性社會福利。在這一背景下,福利國家在促進就業方面紛紛加強了對培訓的投資。
當前,我國農民工培訓正處于“多而無效”的尷尬境地:一方面全社會投入的資本不斷加大;另一方面成效甚微,進展緩慢。雖然現在關于農民工培訓的研究可謂汗牛充棟,但既有的研究對這些問題缺乏很明顯的解釋力。通常只關注農民工培訓的具體過程,沒有看到多方力量在農民工培訓“場域”中的力量顯現與關系形態,更沒有看到“培訓即福利”這一實質性問題,導致“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看似針對性很強,其實是治標不治本。所以,本文認為應從社會政策視角出發,界定國家、市場和社會在農民工培訓這一社會福利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承擔的責任。具體而言,分別從國家、市場與社會三個側面來進行。
二、國家視角下的農民工培訓研究
國家在社會政策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羅斯在《相同的目標、不同的角色——國家對福利多元組合的貢獻》一文中對國家角色進行了界定,[1]其中最重要的兩種角色是福利制度供給者和行動者。供給者角色主要是將國家當成一種從宏觀制度來看待福利的來源,例如伊瓦斯的福利三角理論;行動者角色側重分析國家在福利供給中的自主性,例如斯考切波的“國家中心主義”。
1.作為福利制度供給者的國家
在農民工培訓政策的研究中,許多學者將國家看成一種制度來對待,他們分別研究了制度變遷、[2]制度效果、[3]制度匹配、[4]制度執行、[5]制度評估[6]以及制度設計理念、[7]制度調整[8]等方面。總體來看,學者們都認為作為福利制度的國家角色對于農民工培訓政策的支持是不可或缺,但同時由于激勵機制、評估體系、政策宣傳引導等方面的不足,導致政策實施效果大打折扣。為了更好地闡述國家的制度供給角色,本文從按照制度發生發展邏輯將制度供給研究細分為制度設計理念、制度內容、制度執行與項目落地以及制度匹配和評估四個部分。
首先,在制度設計理念方面,許多學者紛紛指出,政府應改變之前對農民工就業區別對待的理念,重視農民工就業。學者們討論的理念包括公平公正理念、合作理念和服務理念、[9]協同理念和責任理念[10]等。在以上理念的指導下,學者們針對之前在農民工就業治理中的政府缺位、越位和錯位等問題,提出當務之急是要實現政府責任的回歸,建設責任型政府。同時,根據“誰投資、誰受益”的原則,政府特別是流入地政府是培訓的主要受益者,為此,要積極推動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教育培訓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做好簡政放權,提升培訓中的多中心治理能力;[11]針對農民工返鄉的現實,田松青指出,應為農民工返鄉創業建立完善的政府支持體系,包括培訓體系、信用體系、行政服務體系和政策體系等。[12]其中,政策支持是最核心的支持,因此簡新華、黃錕提出應建立農民工人力資本投資的公共政策,它包括激勵企業和農民工增加人力資本投資的公共政策和政府直接增加農民工人力資本投資的公共政策,用于農民工遷移、就業、教育、培訓等方面的支出納入財政預算,完善轉移支付制度。[13]除財政支持外,學者們還認為政府還應從以下方面來做出變革,包括健全投入、完善監管和配套法規,[14]營造農民工技能培訓的良好社會氛圍、建立長效機制,提供全方位的服務,[15]改善政府工作機制等,盡快使轉移培訓主體法制化,加強政府規制建設,完善就業準入制度,[16]依法營造全民終身學習的環境。
其次,在制度內容方面,學者們針對國家已經提出的一系列關于促進農民工就業文件展開討論和分析。目前,關于農民工培訓的制度文本主要有:《2003—2010年全國農民工培訓計劃》、《就業促進法》、《國務院辦公廳關于支持農民工等人員返鄉創業的意見》、《關于實施農民工等人員返鄉創業培訓五年行動計劃(2016—2020年)》等。針對以上制度文本,學者主要從培訓主體、培訓資源、培訓的配套規劃、培訓的方針原則、[17]培訓的公益性和和合法性建設等[18]方面展開論述,總結了農民工培訓政策內容方面政府福利責任,確定了政府扶持、齊抓共管原則,保障了農民工培訓的合法性權利。同時,2010年,國家提出健全面向全體勞動者的職業培訓制度,真正將農民工作為勞動者的一員公平對待。2012年國家又提出構建勞動者終身職業培訓體系,將培訓時長延伸至整個生命周期。從國家這一系列的政策可見,國家對農民工的培訓已經從原來的控制、引導流動目的變成了一項發展型福利政策。通過國家的努力,培訓越來越被作為一種普惠型福利機會,使每位農民工都能獲益。
然后,在制度執行與項目落地方面,學者們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的政策執行不當(越位和錯位)等方面對農民工就業的影響上,項目落地不扎實。例如,紀韶發現農民工就業政策中存在著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之間、政府與企業之間博弈,嚴重影響了政策的執行效果。[19]顧微微認為,政府的角色失當是導致農民工就業困難的主要原因。[20]具體而言,國家對農民工就業促進(尤其是培訓)的投入有所加大,實施了一系列針對農民工培訓的項目。不少成果發現了政府培訓、職業教育等對農民工就業具有積極作用,但更多的成果則是指出政府在農民工就業促進中的各種不足。例如,郭亞非、鮑景認為政府定位對農民工培訓工作影響巨大,政府扮演實施者角色嚴重阻礙了農民工的培訓效果。[21]梁栩凌、王春稍指出了政府直接參加培訓和編寫教材等會造成越位。[22]高洪貴認為政府購買培訓服務中存在著績效評價機制不健全、制度保障缺乏、政府自身管理能力不足等諸多問題。[23]王飛指出了政府購買就業培訓券模式的不足。[24]
最后,在制度匹配和評估方面,學者們主要考查深層次的戶籍制度的社會排斥作用,以及農民工培訓政策評估體系和標準的建設。例如,劉傳江、程建林認為戶籍制度同就業制度、教育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等共同構成了“隱性戶籍墻”,[25]使農民工在求職、就業待遇、權益維護等方面處于不利境地。隱性戶籍墻使得城鄉就業始終存在壁壘效應,也就抑制了農民工參與培訓的需求。另一方面,農民工培訓評估體系不完整、標準不明確、主體單一化,[26]從而使得當前的制度評估處于空白。因此,學者們提議建立統一的城鄉戶籍制度,以及完善現有的農民工培訓評估體系,設置合理的評估標準,促進評估主體的多元化。
2.作為行動者的國家
國家在農民工培訓中不僅具有福利制度供給者的角色,還具有行動者的角色。從國家中心主義視角出發,國家不僅僅是社會、市場等利益相關者角逐的“場域”,還是一個具有自主性和能力的主體。聯系我國的農民工培訓政策,作為行動者的國家必然會有自己的利益考量與自主性偏好,同時對政策的實施也存在伸縮性。
在農民工培訓政策中的國家能力方面,斯考切波認為國家能力是國家自主性的基礎,所以考察農民工培訓政策中作為行動者的國家必須要首先研究國家能力。按照黃寶玖的說法,國家核心能力可以概括成十個方面,其中與農民工培訓息息相關的能力有:資源汲取與配置能力,公共產品供應能力,社會關系整合與規范能力。學者們重點從財政資金支持、[27]人員支持、[28]體系路徑[29]等方面考查農民工培訓政策中國家能力建設,并且注意到國家從“主體型行動者”到“主導型行動者”的角色轉化。從目前來看,國家處于福利體制的主導地位,不僅體現在安排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在農民工培訓中的具體責任,同時體現在對于企業、家庭、社會組織也設計了相應的福利合作網絡,[30]有利于整合多元力量參與農民工培訓。
在農民工培訓政策的國家自主性研究方面,目前學界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偏好,二是伸縮性。大量研究發現,國家在農民工培訓中具有考核偏好,[31]這種偏好一方面源于國家政策把農民工培訓作為一項官員考核的內容;另一方面在于各級政府的量化性效果導向。這種考核偏好造成了政府僅愿意承擔起對農民工培訓責任的有限責任,[32]從而不愿意與市場和家庭合作。同時,在國家中心主義者看來,國家是一個伸縮性的概念,可以以多種形式存在,因此國家自主性是一個變量而非常量。例如,何顯明注意到地方政府實際權限、職責及行為邊界的彈性化和模糊化。[33]張曦予、邵世志深入地分析了作為國家自主性制度基礎的政治體制的內在邏輯。[34]同時,在社會政策和公共政策領域,對于國家自主性的討論主要集中在地方參與和分權方面。例如,錢穎一和吉拉德·羅蘭主要從財政分權和貨幣分權角度討論國家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策略。因此,有不少學者認為,國家偏好的找尋除了需結合效用外,還需結合國家官僚機構和官僚集團進行。
三、市場視角下農民工培訓研究
福利多元主義興起之后,糾正了原來國家對福利的“壟斷式”責任,強調全社會各個主體參與到社會福利的供給之中。綜合來看,學界認為市場作為就業福利的提供者,一方面具有福利制度的供給者角色;另一方面又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行為主體,具有穩定的生產偏好。
1.作為福利制度供給者的市場
蒂特馬斯提出,福利政策可以劃分為三類,分別是社會福利、財稅福利和職業福利。職業福利作為福利制度的有效組成部分,主要是由市場部門提供。目前我國學界對于職業福利研究成果集中在對二元經濟結構、[35]非正規經濟、[36]多重分割的勞動力市場、[37]產業結構調整、[38]經濟波動[39]等對農民工就業的雙重影響上。不過,學者們更為強調以上因素對農民工就業的屏蔽與排斥作用,它們會造成農民工就業障礙,就業質量低。這些因子與農民工較低的人力資本相結合,進一步加大了農民工的就業困難。例如,李春玲認為三層制度分割會影響到農民工的市場進入機制,使流動人口勞動力被隔離在特定的社會和經濟空間之內。[40]還有學者認為勞動力市場分割還會造成對農民工勞動就業的歧視,[41]它是現階段我國經濟領域經常出現“用工荒”的根源。[42]此外,市場角度的職業福利研究還涉及經濟政策方面,學者們系統分析了現階段國家的產業結構政策、[43]財政政策、[44]稅收政策、[45]信貸政策、[46]最低工資政策[47]與城市化政策[48]等對農民工就業的支持效應,發現現有政策對農民工就業的促進效果有限。例如,杜劍、李家鴿、趙雪三人認為,惠及農民工群體就業的稅收政策不僅有利于緩解我國目前所面臨的巨大的就業壓力,也有利于推進我國的城市化和工業化進程,但是不能適應農民工就業總量加大、就業形勢嚴峻的特點,需要加以多方面的改進。[49]
其次,市場在社會政策中還可以提供間接的效率福利以及促進個人責任意識覺醒。在社會政策的范疇內,市場的作用在于為有需要的使用者提供可供選擇的資源,彌補家庭或政府的不足。市場一方面直接提供職業福利參與福利建設;另一方面通過提供間接的效率福利來影響福利建設。同時,由于合理的市場機制可以有效地配置資源,激發個人責任意識的覺醒,使福利體制中的客體從行為和心理兩個層面接受“福利社會”的建設思路,改變原有的“國家在福利建設中負有全部責任”這一思想。從歐美的發展來看,就業培訓領域,越來越傾向于政府購買服務來替代直接參與就業培訓,其根源就在于市場可以提供間接的效率福利,從而兼顧福利社會中公平和效率兩者之間的關系。另一方面,在當前的農民工培訓中,許多學者只關注到政府、市場、社會的主體作用。例如,章華麗認為農民工培訓可以分為三類主體,分別是作為供給主體的政府、作為實施主體的企業和職業學校、作為協作主體的非政府組織,[50]沒有看到培訓中農民工的主體作用。市場作為福利制度的供給者的潛在福利責任就是激發個人的責任意識,使其主動參與到福利體制建設中。
2.作為行動者的市場
由于市場中的企業天然帶有“生產偏好”,其對農民工培訓總是要考慮效率與投入產出比。例如,鄭光永就考查了人力資本外部性與企業農民工培訓效率不高的相關性。[51]一方面企業主認識到,為發展生產企業必須增強對員工的素質投入。在企業的成長階段,更要注重對員工的培訓。但是,企業的培訓實踐與其經濟能力有密切相關性,經濟效益的好壞直接決定培訓的實施好壞。[52]在生產偏好影響下,企業熱衷于保持對新生代農民工培訓的主導地位,只有這樣才能保證企業根據自己企業的情況來安排培訓。但是一旦和政府合作,政府就會對培訓的形式與培訓內容進行規定,而企業往往難以達到。另一方面,企業與農民工之間缺乏長期穩定的合約關系以及企業發展中存在短期行為,使企業對于農民工培訓往往缺乏足夠的動力。[53]許昆鵬、黃祖輝、賈馳等人認為,在當前的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中,培訓投資收益和實現利潤最大化的目的使企業均具有投資培訓的動力,但市場機制無法兼顧效率與公平,這種固有缺陷在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中得到了體現,為此需要政府的介入來克服市場機制的缺陷。[54]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職業能力建設司課題組認為,企業在農民工培訓的作用發揮不充分的原因在于對企業在農民工培訓中的責任缺乏明確法律和制度規范,對企業承擔農民工培訓缺乏有效的政策激勵。同時,企業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與學校、培訓機構和社會等其他力量開展培訓合作。[55]劉國永認為培訓具有“外溢性”,導致企業對培訓有所顧慮。為此,應鼓勵用人企業和農民工之間建立穩定的、持久的、長期化的雇傭關系。[56]
四、社會視角下農民工培訓研究
在福利多元主義的具體研究脈絡中,許多學者采用四分的方法把家庭和社會組織分別成為福利主體來進一步凸顯社會在社會政策中的重要性。當前,我國農民工培訓領域社會力量的介入只限于傳統的家庭幫助和一些非政府組織的介入,和西方國家社會力量參與就業促進的體制相比,還需要不斷改進。
1.作為福利制度供給者的社會
從社會的產生和發展視角來看,可以將社會劃分為家庭單位和家庭外單位(即社會組織等),從而更好地界定兩個單位作為福利制度供給者在農民工培訓中提供的福利內容以及承擔的福利責任。
農民工培訓中的家庭單位福利責任主要體現在供給“關系式”福利、親情照顧等配合式福利以及基礎教育的“投資式”福利。首先,家庭在供給“關系式”福利方面,目前學者主要圍繞在中國當前的社會、文化場域中,農民工的非正式關系網絡(如傳統的地緣關系和血緣關系)在農民工的求職與地位獲得中發揮的重要作用,涌現出了大量的成果。[57]這些成果共同指出農民工自身的關系網絡(規模、性質、層次性)是影響在城市中的求職與地位獲得的關鍵性變量。除此之外,學者們還發現,農民工對關系網絡的運用方式也會影響到就業效果。例如,李懷和李強發現農民工對關系網絡的策略性建構與運作有利于增加求職的成功性。[58]當然,還有一些研究發現農民工的非正式關系網絡對其就業具有負功能,容易導致權益受損。[59]其次,家庭可以供給親情照顧等配合式福利。如果從家庭的角度出發,農民工參與培訓是對家庭照顧、子女照顧時間的占用與擠壓,需要農民工家庭中的其他成員進行彌補,來承擔起因農民工外出而造成的家庭照顧空缺,從而使得做好各類保障工作,使他們能安心在外培訓。[60]最后,家庭可以供給基礎教育的“投資式”福利。我國傳統文化一直都有重視教育投資的偏好,認為教育投資對個人的長期發展具有幫助作用。因此,我國家庭對教育的投入經費占家庭支出的比重一直很高。文化偏好的特征也影響了家庭對新生代農民工培訓的偏好,使新生代農民工家庭對培訓非常重視。許多家庭認為,培訓具有生產性。這一偏好不僅會在新生代農民工從脫離學校后仍主動對其進行人力資本投資,還會在其就業后對培訓持正向評價態度,積極參與培訓。[61]
農民工培訓中家庭外單位的福利責任,主要體現在人力資本福利的提供。學者們普遍贊同社會組織的介入對農民工人力資本的提升有積極作用。這種作用可以從社會組織的培訓與政府的培訓相比所具有優勢來體現,其優勢包括師資隊伍、場地、課程設計優勢,與市場對接容易,便于整合社會資源,公益性明顯等。[62]例如,翁杰、郭天航發現職業教育對農民工就業的幫助超過政府組織的短期培訓,[63]戴國琴發現民工學校對建筑工的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提升具有顯著的正向作用。[64]
2.作為行動者的社會
經濟學的一個重要假設就是將行為主體假定為理性的“經濟人”,其經濟行為是在成本和效用之間進行最優組合。經濟學認為,國家、市場和社會的許多行為也都服從于這一自主性定律。因此,根據自主性的內涵,能力與偏好也適合對社會的分析。在偏好方面,持經濟學視角的學者早已對家庭等主體的偏好進行過深度研究。具體來說,家庭單位的短期培訓效用偏好影響農民工培訓的深度發展。雖然培訓相比于教育能更有效地增進農民工的人力資本,[65]但也具有短期效用和長期效用之分。短期效用主要體現在就業機會的供給和就業崗位的獲得,[66]長期效用則體現在職業流動上。[67]在一些企業,崗前培訓、安全培訓和崗位培訓是獲得就業崗位的前提。[68]因此,農民工的家庭對這三類培訓較為支持。而職業技能提升培訓則沒有這方面的限制,其短期效用不明顯。受農民工職業轉換頻繁影響,長期效用存在無法兌現風險,加上企業的短期培訓對家庭支持的要求更低,因此農民工家庭更重視培訓的短期效用而非長期效用。吳丹、顏懷坤、曾盼盼也發現,贍養老人和子女教育的負擔會阻礙農民工參與培訓和投資額度。[69]此外,還有少數學者研究了農民工家庭對培訓的投入問題。例如,朱占峰、張曉東發現農民工家庭存在著小富即安心理,大大制約了農民工創業,農民工家庭對培訓的投入斤斤計較,免費培訓尚能參與,對需要自己支出一部分時間和成本的培訓則不感興趣。[70]
家庭外單位的現實行動邏輯對于農民工培訓的考量,重點體現經濟能力不足以支撐培訓和慈善理念不足以支撐培訓。艾斯平·安德森在《福利資本主義的三個世界》中使用“非商品化”(是指個人福利相對獨立于其收入之外又不受其購買力影響的保障程度)概念概括出三種福利制度,來表明一個國家的福利制度發育水平。目前,市場中的企業提供培訓的“非商品化”程度很低,同時社會中的家庭外單位提供培訓的“非商品化”程度也很低,具體體現在喪失公益性、收費偏高、培訓學校的師資不足、培訓內容與培訓方法與市場脫節、技術手段低、對培訓的認識與投入不足等,[71]還包括承擔農民工培訓的意愿不強、[72]承接政府購買農民工服務的能力參差不齊等。
五、合作主義視角下的農民工培訓研究
上世紀70年代后,西方社會普遍走向“福利混合”,越來越強調社會各個部門之間的合作。發達國家還充分發展了公私伙伴關系,暢通國家、市場與社會之間的溝通渠道,增進多元主體之間的協調來促進勞動力的培訓。吉登斯曾指出伙伴關系是歐洲模式的重要特征之一。米什拉在《全球化與福利國家》中將世界上的福利體制模式分為“貨幣主義”和“新合作主義”,這代表了西方學界對于合作主義的認可與接受。聯系當前我國農民工培訓的就業促進問題,目前學界展開了對國家、市場與社會的合作關系和農民工就業之間的相關性研究,研究主要集中在影響因素和促進路徑兩個方面。
在影響因素方面,有一些研究發現人口結構、國家、市場、社會和個人對農民工就業的影響存在著相互關系,各因素之間共同起作用。例如,單正豐、季文、陳如東發現社會資本與人力資本分別對農民工就業和城市融合起到“兩級遴選”作用,其中人力資本起決定作用,社會資本起支持作用。[73]陳憲、黃健柏發現勞動力市場分割和農民工自身條件是影響農民工就業的第一主成分因素,政府服務水平和思想文化是第二主成分因素,信息靈敏性和就業崗位是第三主成分因素,家庭條件和農民工工資待遇是第四主成分因素。[74]此外,還有少數學者分別從政府、社會、家庭和農民工自身角度研究了農民工培訓的障礙問題。例如劉奉越認為,農民工培訓中的障礙包括意向障礙、素養障礙、情境障礙、機構障礙和信息障礙五個方面。[75]
在具體的促進對策方面,不少學者認為應將政府、企業、培訓機構、社會組織以及農民工自身力量綜合起來,共同促進農民工就業。例如,高靈芝倡導建立健全由政府部門、非營利性組織、營利性組織、用人單位、農民工等各責任主體共同參與的農民工就業促進組織網絡。[76]綜合性思路在農民工培訓中體現得最為明顯,許多學者主張建立多元主體在培訓中的協同關系。例如,趙澤洪、李傳香從政府、社會、個體三個層面構造了一個新生代農民工就業能力再造系統,政府主要做好基本公共服務,社會組織提供培訓和就業信息。[77]馮旭芳提出了一個政府、企業、學校三方聯動推進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框架,政府主要做好制度和經費供給,企業承擔培訓成本,學校為農民工提供培訓機會。[78]田書芹、王東強、牟芷提出了一個新生代農民工返鄉創業多中心治理模式,他們從政府、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機構培訓、社會組織等不同主體的關聯性入手,提出應從政策扶持機制、人力資本投入機制、立體化培訓機制、資源整合機制、制度設計角度系統地提出政策。[79]
總體來看,無論是政府主導模式,還是多元分擔的觀點,從權責角度來討論國家、市場、社會在農民工就業促進中的具體關系只是一種理想的合作狀態,并不會必然帶來幾者關系的融洽。例如,有研究揭示,不少培訓學校經常采取非法手段,騙取國家對農民工的培訓補貼。[80]另外,有些學者通過研究一些具體的成功培訓模式,總結出了一些可行的關系狀況,為就業促進中的國家、市場、社會的合作提供可能。例如,謝勇、黃承貴總結了五種農民工培訓模式,即委托模式、定點模式、訂單和聯合模式、企業培訓模式、商業培訓模式。[81]袁慶林、林新奇、洪姍姍提煉了六種模式,分別為農民工自發培訓模式、政府主導的公共職業培訓模式、職業院校主導的職業培訓模式、企業主導的職業培訓模式、民辦公助的“扶貧模式”以及多元化模式。[82]但模式研究也遇到一些問題,它并不能很好地結合特定政策框架和社會背景進行,因此會阻礙模式的適用空間。
六、結論與思考
本文基于社會政策視角對農民工培訓政策的研究,主要從國家、市場和社會三個層面進行具體剖析當前我國農民工培訓領域的政策。述評發現:培訓作為一種公共福利,對于促進農民工機會平等具有重要作用。同時,在涉及農民工培訓 “多而無效”的問題時,學界從國家、市場和社會之間的合作關系出發,試圖找到一條破解難題。
具體而言,國家視角下的農民工培訓政策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觀的制度演進邏輯和國家自主性的展開。在宏觀的制度演進邏輯方面,從制度的理念到制度的內容,從制度的執行到評估,形成了一條完整的供給鏈條。但是,學界針對這一鏈條中的執行不當和社會排斥展開論述,強調加強制度匹配和評估,以及重視戶籍制度等深層次阻礙農民工融入城市的因子。在國家自主性方面,主要集中在對于考核偏好和政策伸縮性的考查。這種考核偏好使得國家在農民工培訓中僅愿意承擔有限責任,并且消極對待和市場、社會的合作關系。
對于市場視角下的農民工培訓政策研究而言,一方面體現在對于職業福利、間接的效率福利提供和促進個人責任意識覺醒;另一方面又體現在市場中主要的企業部門的生產偏好對于農民工培訓的有限責任。進而考查了企業經濟能力以及勞動合同的不完善對于農民工培訓的消極影響。社會視角下的農民工培訓政策研究主要體現在家庭內單位和家庭外單位兩個主體:家庭內單位一方面為農民工參與培訓提供“關系式”福利、親情照顧“配合式”福利和教育“投資式”福利;另一方面又存在短期效用偏好。家庭外單位主要集中在人力資本的投資促進和現實經濟考量方面。
對于國家、市場和社會的合作研究,學者們發現影響農民工就業的因素是多元的,國家、市場與社會領域都存在阻礙農民工就業的因素。因此,要促進農民工就業而應采取多元方法,吸納多學科觀點,將國家、市場、社會和個人的力量綜合起來進行考量,進一步考察三者之間的關系與農民工培訓之間的相關性。但是,目前在農民工就業促進中,在如何將國家、市場、社會與個人的力量綜合起來方面,各個學科均留有不足。首先,在研究取向上重對策研究、輕理論分析。研究的應用取向使目前研究理論積淀分析少,非常缺乏好的理論框架去解釋國家、市場、社會和農民工個體在就業促進中的合作問題。其次,在研究內容上,各學科均未能將國家、市場、社會與農民工個人等多元主體不合作的原因作為研究的重點,只是從單一的角度(如市場、國家、社會)去解釋某一主體為什么不愿意合作。再次,在具體對策上,雖然有些研究提出過綜合性的合作框架,但這些框架大部分是按照國家、社會、市場的責任提出多元主體應扮演的角色,類似于多元培訓責任的分解,并沒有對多元主體間的深層合作機制展開深入討論。
自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央政府提出治理理念以來,決策層與學術界對于社會力量對社會問題的解決功能,注重在國家、市場與社會之間發展出合作的多元主體關系。在農民工培訓的研究中,當前的研究存在著隔離式研究視角,僅側重關注國家、市場和社會的某一面向,而對三者的合作研究關注不夠。因此,下一階段的研究,只有引入治理理念,從制度的供給者和行動者等多個維度對農民工培訓的主體關系進行研究,才能突破回答當前農民工培訓“多而無效”的難題。
【參考文獻】
[1]Rose R. Common Goals but Different Roles: The States Contribution[J].The welfare state East and West, 1986(13).
[2]張勝軍.我國農民工培訓政策的回顧與前瞻[J].職教論壇,2012(19).
[3]周秀平,李振剛.農民工培訓的集中化與政策瞄準效果分析[J].中國職業技術教育,2015(12).
[4]胡志平.從制度匹配檢視農村公共服務均等化[J].社會科學研究,2013(1).
[5]錢桃英,張勝軍.農民工培訓政策執行阻滯的利益分析[J].繼續教育研究,2013(9).
[6]羅金莉.就業培訓,政策評估與福利改善:理論與實證檢驗[J].繼續教育研究,2012(1).
[7]馮虹,葉迎.完善社會正義原則實現農民工就業待遇公平[J].管理世界,2009(8).
[8]姜長云.我國農民培訓的現狀及政策調整趨向[J].經濟研究參考,2005(35).
[9]張志勝.加強政府間合作 保障農民工權益[J].中國人力資源開發,2007(2);譚彥紅.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與農民工問題[J].財政監督,2009(15).
[10]譚彥紅.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與農民工問題[J].財政監督,2009(15).
[11]田書芹,王東強.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教育培訓主體博弈與政府治理能力提升[J].教育發展研究,2014(19).
[12]田松青.農民工返鄉創業的政府支持體系研究[J].中國行政管理,2010(11).
[13]簡新華,黃錕.中國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中的農民工問題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14]吳義太,鄧有蓮.試論我國農民工培訓的政府責任[J].成人教育,2012(3).
[15]許項發.基于公共管理的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J].成人教育,2007(2).
[16]朱占峰.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培訓實效研究[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4.
[17]馬貴萍.農民工培訓的制約因素及突破思路[J].高等農業教育,2004(11).
[18]戴峰,劉書岑.發展權視角下的農民工培訓政策[J].農業教育,2009(6).
[19]紀韶.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農民工就業政策社會效應評估研究[J].經濟與管理研究,2010(10).
[20]顧微微.論農民工就業扶持中的政府角色[J].科學·經濟·社會,2013(2).
[21]郭亞非,鮑景.入城農民工就業培訓中政府角色定位分析:以云南省調查為例[J].學術探索,2006(3).
[22]梁栩凌,王春稍.缺位或越位:農民工培訓中的政府角色研究[J].經濟問題,2014(9).
[23]高洪貴.農民工教育培訓的困境及其超越:以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理論為視角[J].現代遠距離教育,2014(2).
[24]王飛.淺析政府購買農民工就業培訓服務[J].創新,2012(6).
[25]劉傳江,程建林.雙重“戶籍墻”對農民工市民化的影響[J].經濟學家,2009(10).
[26]杜永紅,張艷.論農民工培訓質量監管機制建設[J].職教通訊,2016(4).
[27]潘寄青,沈洊.農民工培訓需求與資金支持機制建設[J].求索,2009(5).
[28]章華麗,陸素菊.農民工培訓政策中的政府角色變遷[J].職教論壇,2014(22).
[29]張三保,吳紹棠.農民工培訓體系建設與政府角色定位[J].當代經濟,2006(6).
[30]王飛.基于就業培訓券的農民工多元合作模式探討[J].西部論壇,2012(5).
[31]趙樹凱.農民工培訓的績效挑戰[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11(2).
[32]呂春燕,邵華.地方政府在農民工培訓中的責任[J].遼寧行政學院學報,2010(4).
[33]何顯明.市場化進程匯總地方政府角色及其行為邏輯:基于地方政府自主性的視角[J].浙江大學學報,2007(6).
[34]張曦予,邵世志.地方政府自主性的制度基礎[J].甘肅理論學刊,2011(1).
[35]肖衛,朱有志,肖琳子.元經濟結構,勞動力報酬差異與城鄉統籌發展:基于中國1978—2007年的實證分析[J].中國人口科學,2009(4).
[36]董克用.關于“非正規部門就業─分散性就業”問題的研究[J].中國勞動,2000(12).
[37]陳憲,黃健柏.勞動力市場分割對農民工就業影響的機理分析[J].開發研究,2009(10).
[38]王春超,吳佩勛.產業結構調整背景下農民工流動就業決策行為的雙重決定:珠江三角洲地區農民工流動就業調查研究[J].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1(5).
[39]黃瑞玲,安二中.經濟波動下返鄉農民工就業促進機制的創新:基于江蘇省13市1106名返鄉農民工的調研[J].現代經濟探討,2011(9).
[40]李春玲.流動人口地位獲得的非制度途徑:流動勞動力與非流動勞動力之比較[J].社會學研究,2006(5).
[41]劉傳江,程建林.第二代農民工市民化:現狀分析與進程測度[J].人口研究,2008(5).
[42]晉利珍,劉玥.新一輪“用工荒”現象的經濟學分析:基于勞動力市場雙重二元分割的視角[J].云南社會科學,2013(3).
[43]葉琪.農村勞動力轉移與產業結構調整互動[J].財經科學,2006(3).
[44]潘寄青,沈洊.財政轉移支付:支持農民工就業的政策研究[J].生產力研究,2009(8).
[45]馬列,石紅梅.促進“農民工”群體就業的稅收政策[J].稅務研究,2008(3).
[46]蘇文軍.金融服務支持返鄉農民工就業途徑探討[J].貴州社會科學,2009(4).
[47]羅小蘭.我國最低工資標準農民工就業效應分析:對全國、地區及行業的實證研究[J].財經研究,2011(11).
[48]楊宜勇,顧嚴,魏恒.我國城市化進程與就業增長相關分析[J].教學與研究,2005(4).
[49]杜劍,李家鴿,趙雪.促進就業的稅收政策:以農民工群體為研究視角[J].生產力研究,2009(21).
[50]章華麗.論農民工培訓三類承擔主體的責任分工[J].職教通訊,2014(22).
[51]鄭光永.基于人力資本理論的企業新生代農民工培訓分析[J].繼續教育,2011(2).
[52]姜紅,劉斌.企業社會責任與就業促進[J].中國就業,2014(1).
[53]“農民的培訓需求及培訓模式研究”課題組.農民的培訓需求及培訓模式研究(總報告)[J].經濟研究參考,2005(35).
[54]許昆鵬,黃祖輝,賈馳.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的市場機制分析及政策啟示[J].中國人口科學,2007(2).
[55]國務院農民工辦課題組.中國農民工發展研究[M].北京:中國勞動社會保障出版社,2013.
[56]劉國永.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實踐與政策思考[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2006(4).
[57]王春光.流動中的社會網絡:溫州人在巴黎和北京的行動方式[J].社會學研究,2000(3).
[58]李懷,李強.農民工求職關系網絡的再生產:基于對蘭州市江蘇籍裝修工的案例分析[J].西北師大學報,2008(6).
[59]甘滿堂.城市外來農民工街頭非正規就業現象淺析[J].中共福建省委黨校學報,2001(8).
[60]米娟.中國勞動力培訓的模式選擇與政策研究:基于發展型社會政策視角[D].杭州:浙江大學,2012.
[61]劉純陽.貧困地區農戶的人力資本投資:對湖南西部的研究[D].北京:中國農業大學,2005.
[62]王鵬,王秋芳.農民工職業培訓:高職院校的優勢體現與操作策略[J].繼續教育研究,2010(5).
[63]翁杰,郭天航.中國農村轉移勞動力需要什么樣的政府培訓:基于培訓效果的視角[J].中國軟科學,2014(4).
[64]戴國琴.民工學校在農民工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提升中的作用研究[J].浙江農業學報,2012(2).
[65]趙海.教育和培訓哪個更重要:對我國農民工人力資本回報率的實證分析[J].農業技術經濟,2013(1).
[66]范方志,李明橋,胡夢帆.勞動力優化配置與貧困地區勞動力剩余[J].當代經濟研究,2012(11).
[67]張錦華,沈亞芳.家庭人力資本對農村家庭職業流動的影響:對蘇中典型農村社區的考察[J].中國農村經濟,2012(4).
[68]蔣亞奇.論企業職業培訓和發展培訓的實施方略[J].中國人力資源開發,2004(8).
[69]吳丹,顏懷坤,曾盼盼.二代農民工培訓狀況及制度保障研究:基于四川省4個縣14個村的實證調查[J].全國商情,2010(17).
[70]朱占峰,張曉東,朱一青,趙靜.基層政府、企業家、農民三者的博弈:基于剩余勞動力轉移培訓的視角[J].農業經濟,2013(10).
[71]呂莉敏,馬建富.新生代農民工教育培訓需求及策略探究[J].中國職業技術教育,2010(33).
[72]張勝軍.農民工培訓的公益性及其保障[J].職業技術教育,2011(31).
[73]單正豐,季文,陳如東.農村勞動力遷移中的兩級遴選機制與群體分化:農村勞動力遷移過程中的公共政策選擇[J].農業經濟問題,2009(6).
[74]陳憲,黃健柏.農民工就業影響因素的主成分分析[J].生產力研究,2009(18).
[75]劉奉越.農民工培訓的障礙因素及對策分析[J].成人教育,2009(2).
[76]高靈芝.“治理理論”視角下的城市農民工就業促進的組織網絡:以濟南市為個案[J].東岳論叢,2006(6).
[77]趙澤洪,李傳香.就業能力貧困與再造:新生代農民工就業悖論及其破解[J].中國人力資源開發,2011(9).
[78]馮旭芳.政府、企業、學校三方聯動推進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J].中等職業教育,2010(35).
[79]田書芹,王東強,牟芷.新生代農民工返鄉創業能力的多中心治理模式研究[J].濟南大學學報,2014(4).
[80]李忠將,田苗.“民生工程”緣何成了腐敗溫床:貴州套取農民工就業培訓資金系列窩案透視[J].就業與保障,2009(1).
[81]謝勇,黃承貴.農民工參加職業培訓意愿的代際間差異分析[J].調研世界,2011(10).
[82]袁慶林,林新奇,洪姍姍.我國新生代農民工培訓主要模式及其比較研究[J].南方農村,20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