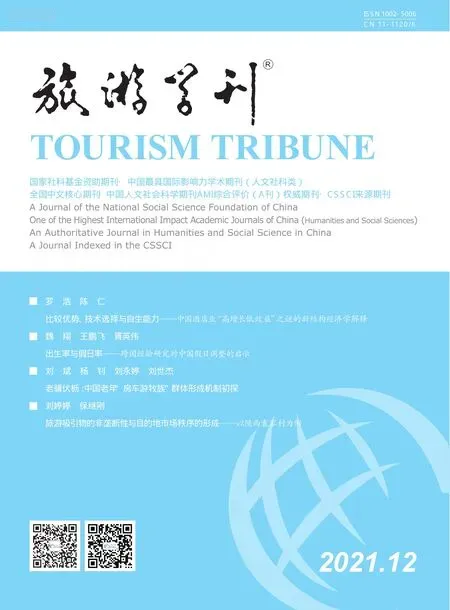《旅游者:休閑階層的新理論》與現(xiàn)代性的民族志者:Dean MacCannell訪談錄
Dean MacCannell 趙紅梅
[摘 要]《旅游者:休閑階層的新理論》(以下簡(jiǎn)稱《旅游者》)是對(duì)旅游研究影響深遠(yuǎn)的一部社會(huì)學(xué)著作。自1976年初版以來(lái),該書吸引了一批又一批評(píng)論者、運(yùn)用者與反思者,其中的“舞臺(tái)真實(shí)性”理論已成為“真實(shí)性”論域的一個(gè)元理論。《旅游者》的著者-Dean MacCannell教授是一位閱歷豐富、見解深邃的社會(huì)學(xué)家,他的研究路徑是通過(guò)旅游者反觀自身社會(huì),反觀無(wú)處不在的現(xiàn)代性。訪談圍繞Dean MacCannell教授的教育背景、智識(shí)淵源與該書的結(jié)構(gòu)、理論內(nèi)容來(lái)展開,以獲得對(duì)作者與經(jīng)典文本的雙重理解。
[關(guān)鍵詞]“舞臺(tái)真實(shí)性”;分化;社會(huì)結(jié)構(gòu);現(xiàn)代性;《旅游者:休閑階層的新理論》
[中圖分類號(hào)]F59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文章編號(hào)]1002-5006(2018)12-0015-11
Doi: 10.3 969/j.issn.1002-5 006.2018.12.009
引言
Dean MacCannell教授出生于20世紀(jì)40年代美國(guó)的西雅圖,是一位有深厚跨學(xué)科素養(yǎng)的社會(huì)學(xué)家,其學(xué)識(shí)涉及哲學(xué)、社會(huì)學(xué)、人類學(xué)、文化地理學(xué)、景觀設(shè)計(jì)與藝術(shù)學(xué)等領(lǐng)域。MacCannell本科就讀于美國(guó)加州大學(xué)伯克利分校人類學(xué)系,研究生轉(zhuǎn)向康奈爾大學(xué)的鄉(xiāng)村社會(huì)學(xué),博士后階段先后赴費(fèi)城和巴黎深造;在近十年的求學(xué)過(guò)程中接受到當(dāng)時(shí)一些大師級(jí)學(xué)者的影響與指點(diǎn),如歐文·戈夫曼( Erving Goffman)、克勞德·列維一斯特勞斯(ClaudeLevi- Strauss)、雅克·德里達(dá)(Jacques Derrida)等。目前,Dean MacCannell是美國(guó)加州大學(xué)戴維斯分校環(huán)境設(shè)計(jì)與景觀建筑系的榮休教授( EmeritusProfessor)、鄉(xiāng)村研究的社會(huì)學(xué)家與加州實(shí)驗(yàn)站景觀建筑部的研究員[1-2]。
Dean MacCannell對(duì)旅游者和旅游吸引物的興趣始于20世紀(jì)60年代,但其旅游思考的正式發(fā)布卻晚至20世紀(jì)70年代,即1973年發(fā)表的首篇旅游類論文——“舞臺(tái)真實(shí)性:旅游情境下的社會(huì)空間設(shè)置”(Staged authenticity: On arrangements ofsocial space in tourists settings)與1976出版的首部專著《旅游者:休閑階層的新理論》(The Tourists: ANew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以下簡(jiǎn)稱《旅游者》)。1989年,MacCannell在Annals of TourismResearch上組織了一期“符號(hào)學(xué)與旅游”專題的特刊,正式將符號(hào)學(xué)引入旅游研究,他強(qiáng)調(diào)在全球社會(huì)文化背景下符號(hào)學(xué)對(duì)“他者”(異文化)研究將大有可為[3]。由于《旅游者》名氣太大,反而使得MacCannell的后期研究難以彰顯,不過(guò),他自20世紀(jì)90年代以來(lái)的研究重心可從1992年的《聚會(huì)空?qǐng)觯郝糜握哐芯空撐募罚‥mpty Meeting Grounds:The Tourists Papers)和2011年的專著《觀光倫理學(xué)》(The Ethics of Sightseeing)中一窺究竟。
Dean MacCannell對(duì)旅游研究有卓越的原創(chuàng)性貢獻(xiàn)。《旅游者》是1976年以來(lái)唯一一部針對(duì)社會(huì)整體性的、英語(yǔ)語(yǔ)種的社會(huì)學(xué)論著,是旅游類專著里影響最廣泛綿長(zhǎng)的一部,“被書評(píng)”最多的一部,但同時(shí)也是被誤讀最為嚴(yán)重的一部。誤讀之一,MacCannell視《旅游者》為現(xiàn)代性的民族志,但讀者一眼讀出了“旅游者類型研究”。誤讀之二,MacCannell的“舞臺(tái)真實(shí)性”意在揭示旅游空間的結(jié)構(gòu)化與旅游動(dòng)機(jī),但讀者讀出了旅游展演與文化生產(chǎn)[4]。誤讀之三,過(guò)度關(guān)注“舞臺(tái)真實(shí)性”而嚴(yán)重忽略《旅游者》的另一個(gè)核心部分——“吸引力符號(hào)學(xué)”(the semiotics of attraction),使MacCannell關(guān)于“旅游是為社會(huì)分化所上演的一場(chǎng)儀式”[5]的觀點(diǎn)得不到普遍的理解。誤讀之四,《旅游者》是一部試圖在細(xì)致的經(jīng)驗(yàn)主義與中層理論之基礎(chǔ)上建構(gòu)社會(huì)系統(tǒng)之一般理論的社會(huì)學(xué)論著,但旅游人類學(xué)比旅游社會(huì)學(xué)更為熱烈地接納了它。簡(jiǎn)言之,上述誤解現(xiàn)象大都可歸因于“懶惰”的閱讀方式,《旅游者》是一部系統(tǒng)性的、有內(nèi)在邏輯的專著,但被割裂地閱讀了。
針對(duì)“舞臺(tái)真實(shí)性”的誤讀,MacCannell曾先后撰寫3篇文章予以糾正[2],但收效甚微,因?yàn)椴煌瑢W(xué)科背景的研究者已經(jīng)習(xí)慣對(duì)《旅游者》各取所需了。辯證地看,這樣的誤讀不無(wú)建設(shè)性,因?yàn)樽?973年以來(lái),從最初的真實(shí)性概念話語(yǔ)體系中逐漸分化出真實(shí)性研究的兩套新話語(yǔ):(1)真實(shí)化( authentication)過(guò)程,即真實(shí)性在不同文化中的多樣性表現(xiàn)及其影響效應(yīng);(2)對(duì)真實(shí)性的集體“再投資”,即在表演理論基礎(chǔ)上對(duì)真實(shí)性的跨學(xué)科研究[6]。這兩個(gè)方向?yàn)椤奥糜紊鐣?huì)學(xué)”與“旅游人類學(xué)”共同關(guān)注的論域——文化商品化與真實(shí)性研究奠定了相對(duì)堅(jiān)實(shí)的理論與實(shí)踐基礎(chǔ)。
筆者于2016年12月-2018年1月期間在加州大學(xué)伯克利分校人類學(xué)系訪學(xué),幾乎每周五都能在人類學(xué)系“旅游研究工作組”(Tourism StudiesWorking Group)的例會(huì)上與Dean MacCannell教授碰面,于是萌生了對(duì)這位令人尊敬的教授做一次訪談的念頭。基于對(duì)《旅游者》一書的粗淺閱讀以及對(duì)MacCannell教授學(xué)術(shù)生涯的大致了解,筆者草擬了8個(gè)問(wèn)題,由于場(chǎng)所不便,遂采用了電子郵件筆談的方式。訪談從2017年11月20日開始,一問(wèn)一答直到12月10日結(jié)束,此后是斷續(xù)的翻譯、商榷與確認(rèn)過(guò)程。訪談文本由引言、問(wèn)答、結(jié)語(yǔ)3部分構(gòu)成:引言由趙紅梅撰寫,隨后譯成英文供MacCannell教授確證授權(quán);主體是問(wèn)答部分,趙紅梅負(fù)責(zé)問(wèn)題,MacCannell教授負(fù)責(zé)回答;結(jié)束語(yǔ)由趙紅梅撰寫,并將大致內(nèi)容翻譯成英文供MacCannell教授參閱。訪談文本有中、英文兩個(gè)對(duì)照版本,由DeanMacCannell教授與趙紅梅共同收存。以下是中文版的訪談文本,意與國(guó)內(nèi)學(xué)界共享交流。《旅游者》的中譯本已于2008年面世,因此也期待這次訪談能激起對(duì)經(jīng)典文本的再閱讀、再反思與再發(fā)現(xiàn)。
1.趙紅梅(以下簡(jiǎn)稱趙):MacCannell教授,相對(duì)于你本人而言,中國(guó)的旅游學(xué)術(shù)圈更為熟悉您的“舞臺(tái)真實(shí)性”理論,不知您是否愿意分享您的教育經(jīng)歷以及一些相關(guān)的故事?中國(guó)讀者一定希望對(duì)“舞臺(tái)真實(shí)性”理論的提出者有一些基本的了解,我個(gè)人則對(duì)您在旅游研究尚未成氣候的年代選擇“旅游者”作為博士論文的最初選題比較好奇。
Dean MacCannell(以下簡(jiǎn)稱M):在西方智識(shí)傳統(tǒng)中,從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開始,一直有一股探索社會(huì)運(yùn)行機(jī)制的力量存在。我個(gè)人比較偏愛蒙田與盧梭的著作(尤其是盧梭的《社會(huì)契約論》和《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chǔ)》),以及涂爾干、馬克思與韋伯的社會(huì)學(xué)經(jīng)典論著。20世紀(jì)60年代,當(dāng)我還是美國(guó)兩所精英大學(xué)——加州大學(xué)伯克利分校與康奈爾大學(xué)的學(xué)生時(shí),就被要求深入閱讀這些相關(guān)著作,理解它們并加以延伸拓展。我本科就讀于伯克利分校人類學(xué)系,專業(yè)是文化人類學(xué),我喜歡經(jīng)典民族志,愛看《原始人類》那樣的書。但人類學(xué)引以為學(xué)科圭臬的研究對(duì)象,即所謂的“原始的孤島文化”(primitive isolate)正消逝于無(wú)形,所以我在康奈爾大學(xué)讀研時(shí)就轉(zhuǎn)向了鄉(xiāng)村社會(huì)學(xué)系。
就我對(duì)經(jīng)典著作的閱讀體驗(yàn)來(lái)說(shuō),印象最深刻的是這些書籍的涉獵范圍和探索勇氣。人類學(xué)家從不憚?dòng)谕渡砦幕w性的研究,他們總是想找到文化的這一部分與其他部分的共生關(guān)系;而像馬克思、韋伯和涂爾干這樣的社會(huì)學(xué)巨擘則毫不猶豫地緊盯社會(huì)整體性,探尋社會(huì)組織與社會(huì)變遷的重要機(jī)理。今天,社會(huì)學(xué)家和人類學(xué)家大都傾向于研究社會(huì)的一個(gè)小部分,比如一個(gè)特別的鄉(xiāng)村、制度、地理區(qū)域、階層,或是像少數(shù)民族或貧困人口這樣的特殊人群,沒有人愿意致力于社會(huì)整體形貌與總體發(fā)展趨向的研究。在研究生階段,我喜愛的論著有涂爾干的《社會(huì)分工論》和《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和“科層制”理論,馬克思的《資本論》和勞動(dòng)異化( alienatedlabor),莫斯的《禮物》,以及雷德菲爾德的城鄉(xiāng)連續(xù)體概念。歐文·戈夫曼是我在伯克利讀書時(shí)的老師,后來(lái)在費(fèi)城我們成了朋友。我讀過(guò)他的所有論著,有時(shí)他會(huì)在出版前把書稿拿給我看,征詢我的評(píng)論和意見。在20世紀(jì)60年代的社會(huì)學(xué)巨擘中,我認(rèn)為歐文·戈夫曼、克勞德·列維一斯特勞斯和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是最具洞察力的,也是最讓人受益匪淺的,此外還有羅蘭·巴特和雅克·拉康。在著手《旅游者》一書之前,我幸運(yùn)地踏入了費(fèi)城的歐文·戈夫曼和巴黎的列維一斯特勞斯的門庭,潛心做博士后研究。
馬克思、韋伯和涂爾干關(guān)于社會(huì)、社會(huì)關(guān)系的理論與他們所處的時(shí)代環(huán)境密切相關(guān),宏大的社會(huì)變遷是孕育其理論的源泉:作為其研究“實(shí)驗(yàn)場(chǎng)”的社會(huì)剛進(jìn)人工業(yè)革命不久,現(xiàn)代民族一國(guó)家的民主思想剛剛誕生,世俗民主制度初出茅廬。我曾試圖設(shè)想過(guò),對(duì)于20世紀(jì)中期的工業(yè)社會(huì),他們會(huì)作何反應(yīng)?他們?nèi)匀粫?huì)關(guān)注宗教的功能、無(wú)產(chǎn)階級(jí)和階級(jí)斗爭(zhēng)嗎?不然,我如是想。
伯克利和康奈爾的教授都灌輸給我一種責(zé)任感,即新生代學(xué)者應(yīng)該撿起社會(huì)整體性的接力棒,不要偏離宏大的社會(huì)問(wèn)題。我在康奈爾大學(xué)鄉(xiāng)村社會(huì)學(xué)系的研究生同學(xué)也義不容辭地肩負(fù)起探索不發(fā)達(dá)國(guó)家經(jīng)濟(jì)停滯原因的重任,他們來(lái)自不同的國(guó)家和地區(qū):印度、巴基斯坦(東部與西部)、澳大利亞、中國(guó)臺(tái)灣、巴西、肯尼亞、阿爾巴尼亞、阿富汗和伊朗。與他們同窗學(xué)習(xí),我收獲巨大,我們成為朋友,并與其中幾位一直保持密切聯(lián)系。
我想研究的是一種全球性現(xiàn)象,涉及所謂的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之間的互動(dòng)與交易、且潛在地揭示了一種新文化形式的現(xiàn)象。我讀研時(shí)到遙遠(yuǎn)的波多黎各做了平生第一次田野調(diào)查,研究那里農(nóng)村地區(qū)的傳統(tǒng)農(nóng)業(yè)活動(dòng)。在那兒的一個(gè)海濱小鎮(zhèn),我看到許多正在為外國(guó)旅游者而興建的酒店。哈哈,旅游!
我的第一個(gè)念頭是,有朝一日旅游可能作為嶄新而高效的農(nóng)業(yè)技術(shù)而對(duì)全球發(fā)展產(chǎn)生巨大影響;第二個(gè)念頭是旅游將成為一個(gè)有趣而持續(xù)的研究領(lǐng)域,因?yàn)樗婕耙匀祟悶檩d體的跨文化互動(dòng),而不僅僅是現(xiàn)代化理念、工序與科技等文化成果從文化源地進(jìn)入文化接受地的單向傳播模式。
當(dāng)我寫下《旅游者》的第一行字時(shí),對(duì)我而言,旅游者這個(gè)角色就充當(dāng)了一般人類的當(dāng)代替身或代表,接替了經(jīng)典社會(huì)學(xué)理論中產(chǎn)業(yè)無(wú)產(chǎn)階級(jí)的位置。我很快意識(shí)到常規(guī)研究方法不足以應(yīng)對(duì)《旅游者》所要完成的任務(wù),于是我追隨列維一斯特勞斯、歐文·戈夫曼與肯尼斯·伯克的腳步,轉(zhuǎn)而從結(jié)構(gòu)語(yǔ)言學(xué)、符號(hào)學(xué)以及文學(xué)批評(píng)的分支——解構(gòu)學(xué)派中尋找新的分析路徑,因此就有了《旅游者》中“吸引力符號(hào)學(xué)”那一章。所以,一開始我就沒有把《旅游者》看成一種旅游研究,我只是把旅游者和旅游當(dāng)作一把開啟當(dāng)代社會(huì)研究的鑰匙,跟隨旅游者,我進(jìn)入現(xiàn)代世界不為人所知的一些角落里,以全新的社會(huì)學(xué)眼光來(lái)審視這個(gè)世界。
2.趙:《旅游者》初版是在1976年,迄今,在社會(huì)學(xué)領(lǐng)域,該書仍是針對(duì)社會(huì)整體性研究的唯一一本英語(yǔ)類著作。鑒于這40年來(lái)現(xiàn)代人疏離感的日益強(qiáng)烈,您認(rèn)為《旅游者》的受歡迎是否與其所針對(duì)的社會(huì)分化現(xiàn)象(differentiations of society)有關(guān)系呢?分化這種現(xiàn)象對(duì)現(xiàn)代社會(huì)有什么影響?
M:涂爾干在論述“有機(jī)團(tuán)結(jié)”理論時(shí),他提到復(fù)雜社會(huì)(比如工業(yè)國(guó)家)得以凝聚的社會(huì)紐帶要比簡(jiǎn)單社會(huì)或農(nóng)村社會(huì)更牢固。這個(gè)邏輯令人疑惑,因?yàn)閺?fù)雜的、工業(yè)的、都市的社會(huì)人彼此間感受到的團(tuán)結(jié)感比小規(guī)模的、簡(jiǎn)單的鄉(xiāng)村社會(huì)要弱得多。一個(gè)擁有如此眾多疏離人口的社會(huì)怎么會(huì)比弱疏離的鄉(xiāng)民社會(huì)有更牢靠的社會(huì)紐帶呢?涂爾干說(shuō),“當(dāng)然我是正確的,以史為鑒,看看地球上曾存在過(guò)的社會(huì),無(wú)一不是大型的、復(fù)雜的、疏離的社會(huì)一直在統(tǒng)馭小型的、簡(jiǎn)單的熟人社會(huì)。”他還用“互惠依賴”理論(theory of reciprocal dependency)來(lái)解釋這個(gè)顯而易見的矛盾。
據(jù)涂爾干觀察,小規(guī)模的、簡(jiǎn)單的、原始的社會(huì)基本上是自給自足的社會(huì),每個(gè)人都自蓋房、自種糧、自狩獵,生病亦自主護(hù)理;但在大型的、復(fù)雜的社會(huì)里,無(wú)人能自給自足,我們雇用木匠來(lái)蓋房,從農(nóng)民那里購(gòu)買糧食,生病時(shí)找醫(yī)生,完全依賴于他人的專業(yè)化,正如他人亦依賴于我們?yōu)樯鐣?huì)整體性所貢獻(xiàn)的各種專業(yè)化一樣。這就是互惠依賴,涂爾干把這種互惠依賴稱為有機(jī)團(tuán)結(jié)。他解釋說(shuō),現(xiàn)代復(fù)雜社會(huì)好比一株有完整的根、莖、葉、花的植物,每一部分都對(duì)這株植物的生命狀態(tài)至關(guān)重要,如果一只害蟲損害了哪怕其中很小一個(gè)部分,整株植物都會(huì)因生命遭遇危機(jī)而做出連鎖反應(yīng)。另一方面,涂爾干將簡(jiǎn)單社會(huì)的團(tuán)結(jié)稱為機(jī)械的,簡(jiǎn)單社會(huì)的每個(gè)部分(每個(gè)家庭、每個(gè)村莊)都與其他部分類似,正如一面墻上的磚,每一塊都與其他任意一塊同等自足,如果其中一塊遭受戕害,整體不會(huì)有連鎖反應(yīng),整個(gè)社會(huì)將以較小的、依然自足的聚合體形式,像被戕害之前一樣繼續(xù)運(yùn)行。機(jī)械組織而成的社會(huì)可以被拆解,化整為零,剩下的任意部分都不會(huì)受影響,直至最后一部分消失。
涂爾干是個(gè)非常可愛的人,他假設(shè)現(xiàn)代復(fù)雜社會(huì)的人們能理解其自身相互依賴的關(guān)系,并且尊重差異性基礎(chǔ)上的功能性整合,因?yàn)檫@是集體生存的基礎(chǔ)。在撰寫《旅游者》一書時(shí),我卻看到現(xiàn)代人對(duì)彼此之間切實(shí)的依賴關(guān)系缺乏清醒的認(rèn)識(shí),這就是我為什么沒有借用涂爾干的勞動(dòng)分工和有機(jī)團(tuán)結(jié)這兩個(gè)概念的原因。這兩個(gè)概念意味著我們對(duì)相互依賴的情形有一種普遍的感覺深度,但我認(rèn)為這種感覺深度是普遍缺乏的,所以我改用“結(jié)構(gòu)性分化”(structural differentiation)這一中性詞,拋出“人們?cè)鯓討?yīng)對(duì)分化”這個(gè)問(wèn)題,我發(fā)現(xiàn)現(xiàn)代人對(duì)此作出的最普遍、最積極、最有趣的應(yīng)對(duì)方式就是觀光與旅游。在《聚會(huì)空?qǐng)觥返摹暗谌拢汉蟋F(xiàn)代社區(qū)規(guī)劃“里,我詳細(xì)解釋了自己與涂爾干在理論上的分歧。
那時(shí)寫《旅游者》,我還沒有認(rèn)真嚴(yán)肅地讀過(guò)弗洛伊德的書,但我見過(guò)青春期少女不無(wú)怨尤地聲稱憎恨自己含辛茹苦的母親;在加州,人們一邊依賴那些農(nóng)場(chǎng)移民工人提供的日常飲食,一邊又表現(xiàn)出對(duì)他們的憎惡與敵意。因此,就我的所見所聞,我認(rèn)為人類的相互依賴既能跨越差異產(chǎn)生尊重,亦能孕育出敵意。所以,分化對(duì)社會(huì)的影響取決于人們的反應(yīng),反應(yīng)主要包括兩種情形:一是面對(duì)與日俱增的復(fù)雜性與全球化,一些人自覺跟不上時(shí)代,主動(dòng)撤退到人為建構(gòu)的、相對(duì)簡(jiǎn)單的身份中去,以此彰顯其族類歸屬的純粹性;二是一些人會(huì)事先明智地理解并消化人類的差異性,再?gòu)牟町愋灾姓业截S富生活的辦法,這樣他們就有理由贊美社會(huì)的分化了,民族旅游走的就是這條路。
3.趙:在英文版《旅游者》的第13頁(yè),有一個(gè)很關(guān)鍵的句子:“觀光是為社會(huì)分化上演的一場(chǎng)儀式”(sightseeing is a ritual performed to the differentia-tions of society),應(yīng)該怎樣理解這個(gè)句子,尤其是分化( differentiation) 一詞的含義是什么?
M:你問(wèn)到最重要的問(wèn)題,我在《旅游者》里試圖解釋的不僅僅是旅游現(xiàn)象,我還對(duì)現(xiàn)代社會(huì)及社會(huì)生活是如何組織,它與工業(yè)社會(huì)、鄉(xiāng)民社會(huì)、原始社會(huì)有怎樣的區(qū)別很感興趣,因此我把《旅游者》稱作“一部現(xiàn)代性的民族志”。
現(xiàn)代生活最顯著的特征是其日益復(fù)雜的趨勢(shì),即“分化”,這是我能給出的主要答案。譬如人類以前只有一男一女的異性婚姻形式,但現(xiàn)在有“男女婚”“女同婚”與“男同婚”,一變?nèi)T诘厍蛏先我庖粋€(gè)角落,選擇層出不窮,現(xiàn)代生活所包羅的一切領(lǐng)域,都充斥著無(wú)數(shù)選項(xiàng),比如不同類型的金融合同、不同種族的人群、多重社會(huì)階層等,不再只有工人和雇主兩個(gè)對(duì)立階層,還有中產(chǎn)階級(jí),而中產(chǎn)階級(jí)內(nèi)部又有上、中、下之分。甚至連歷史也有分化,“過(guò)去”不再是一段均質(zhì)的時(shí)間類型,每10年就有個(gè)名號(hào),比如咆哮的20年代、最偉大的一代、60一代、X一代(迷惘的一代)等。
我認(rèn)為,一些研究者所宣稱的經(jīng)濟(jì)發(fā)展和現(xiàn)代化實(shí)際上也是制度、社會(huì)范疇不斷分化的結(jié)果。作為社會(huì)學(xué)家,我建議將經(jīng)濟(jì)發(fā)展看作社會(huì)分化的偶然性副產(chǎn)品;人類所能感受到的分化,似乎就是社會(huì)正在遠(yuǎn)離其日常生活實(shí)踐的一種體驗(yàn)。眾所周知,我們生活在社會(huì)復(fù)雜性之中,但我們無(wú)法理解或掌握它,現(xiàn)代社會(huì)的許多問(wèn)題都與失控的社會(huì)分化體驗(yàn)有關(guān),比如疏離、毒品泛濫、極端利己等。
讓我們回到旅游。我在旅游與現(xiàn)代性之間建立的是一種積極的聯(lián)系,我把每一個(gè)旅游吸引物都解釋成社會(huì)分化具象的象征對(duì)應(yīng)物,比如我者與他者如何發(fā)生聯(lián)系,現(xiàn)在與過(guò)去如何聯(lián)系等。如果社會(huì)變得不可思議的復(fù)雜,我們跟上它的唯一方式就是去觀摩那些象征其復(fù)雜性的事物或現(xiàn)象,并向它們致敬。于是,觀光就是為應(yīng)對(duì)社會(huì)分化所上演的一場(chǎng)儀式。
4.趙:我想知道在社會(huì)分化與文化碎片化現(xiàn)象之間是否有內(nèi)在聯(lián)系?我把《旅游者》的持續(xù)流行與社會(huì)分化聯(lián)系在一起的思路是對(duì)的嗎?我想這或許是因?yàn)樵缭?0世紀(jì)70年代您就預(yù)見到現(xiàn)代社會(huì)的發(fā)展趨勢(shì),它就是存在一股將人們推向其他時(shí)空的力量。
M:對(duì)你的問(wèn)題,我回答是的。的確是社會(huì)分化將人們推到異文化的時(shí)空中去,但它也能將眼界褊狹的人推進(jìn)所謂的庇護(hù)所與隔絕地,迫使他們?cè)谔摌?gòu)的、碎片的、傳統(tǒng)的“過(guò)去”里尋找安全感與慰藉。我最近就在研究這種兩種結(jié)果的區(qū)別所在,以及人們選擇逃開差異性和選擇面對(duì)并接納之的原因。
你關(guān)于文化碎片(fragmentation of cultures)的問(wèn)題很有趣,但我并不認(rèn)為一種文化可以碎片化,除非文化主體拒絕變化。在自然狀態(tài)下,文化是相當(dāng)混雜的,比如語(yǔ)言和音樂,當(dāng)它們存在或充滿活力時(shí),會(huì)拒斥過(guò)時(shí)的形式,嘗試并接納適宜的新形式。即便是所謂的傳統(tǒng)文化,也在發(fā)展變化。通過(guò)中國(guó)訪問(wèn)學(xué)者在伯克利“旅游研究工作組”所做的一系列演講,我看到中國(guó)的少數(shù)民族也處在不斷的變遷之中,他們將成為整個(gè)社會(huì)結(jié)構(gòu)性分化的能動(dòng)要素。多年前,我寫過(guò)一篇題為“傳統(tǒng)的前途”(Tradition's next step)的文章,討論藝術(shù)家與創(chuàng)意人才在文化變遷中所起到的作用,其實(shí)文化既能靈活地適應(yīng)變遷,同時(shí)亦能維系其認(rèn)同,而不是僵化和碎片化的,我想你在網(wǎng)上能找到這篇文章。
5.趙:在漢語(yǔ)類旅游文獻(xiàn)里,“舞臺(tái)真實(shí)性”理論被運(yùn)用的頻率比較高,與美國(guó)旅游學(xué)術(shù)圈的情形相似,對(duì)“舞臺(tái)真實(shí)性”概念的誤讀現(xiàn)象也普遍存在。我對(duì)您2008年那篇文章“為何真實(shí)性從未真實(shí)過(guò)”(why it never really was about authenticity)印象很深,為什么您會(huì)認(rèn)為愛德華·布魯納( EdwardBruner)的“真實(shí)性再生產(chǎn)”(authentic reproduction)與“舞臺(tái)真實(shí)性”沒有本質(zhì)區(qū)別?您認(rèn)為是什么使得“舞臺(tái)真實(shí)性”概念的運(yùn)用脫離了您的初衷?
M:為什么真實(shí)性概念出現(xiàn)如此之多的混淆用法,我認(rèn)為主要有兩個(gè)原因:
首先,在英語(yǔ)世界的社會(huì)科學(xué)傳統(tǒng)里,每門大學(xué)課程都在反復(fù)灌輸價(jià)值中立的研究取向,即研究者的心理、政治、宗教偏好不應(yīng)影響其解決問(wèn)題的方式,當(dāng)然亦不應(yīng)影響其發(fā)現(xiàn)與結(jié)論,比如人類學(xué)強(qiáng)調(diào)文化相對(duì)觀以確保民族志文本的客觀性不被人類學(xué)家身上的文化包袱所影響。“舞臺(tái)真實(shí)性”概念高度考驗(yàn)了我的社科同行們保持價(jià)值中立的能力。真實(shí)性,大概是美國(guó)白人世界里最根深蒂固的價(jià)值觀了。在個(gè)人層面,暗示某人或某物可能不真實(shí)的意思是他們或許是說(shuō)謊者、自欺的、不可靠的、膚淺的。我刻意與真實(shí)性的心理學(xué)意涵保持距離,轉(zhuǎn)而關(guān)注旅游者喜聞樂見的經(jīng)典吸引物,探究它們?cè)诒怀尸F(xiàn)和舞臺(tái)化的過(guò)程中采用了哪些顯得真實(shí)的手段和方式。我的本意在于真實(shí)性的社會(huì)建構(gòu),而非真實(shí)性本身,而且我有意漏掉了真實(shí)性體驗(yàn)或真實(shí)感這樣的論題。
現(xiàn)在我意識(shí)到,大多數(shù)讀者對(duì)我的真實(shí)性分析的反應(yīng)是防御性的,有點(diǎn)庸人自擾,以為我的分析是在質(zhì)疑他們辨別自我與他人真實(shí)性的能力,更糟的是,他們指出如果真實(shí)性可以舞臺(tái)化,那么可能真實(shí)性就不存在。所以,幾乎每個(gè)人都想繞開“舞臺(tái)真實(shí)性”的概念:“MacCannell錯(cuò)了,我們對(duì)真實(shí)性并不太感興趣;旅游者對(duì)真實(shí)性沒有訴求,他們只想尋歡作樂;我個(gè)人的真實(shí)感與MacCannell說(shuō)的截然不同”等。但這些評(píng)論都沒有觸及或駁倒《旅游者》所引用的那些實(shí)證材料:注射硝酸鹽的火腿和填塞硅膠的乳房;付費(fèi)拉人參加樂隊(duì)排練;搭建虛假的“后臺(tái)”以滿足旅游者;用魚網(wǎng)、軟木筏子和塑料金槍魚裝飾“漁夫餐館”;向食客開放飯店的廚房區(qū)域等。這類東道主行為在旅游場(chǎng)景里遍地開花,無(wú)非是為了提升想象中的旅游體驗(yàn)的真實(shí)性。
旅游者對(duì)“舞臺(tái)真實(shí)性”的態(tài)度與接納度因人而異,有人被吸引,有人看穿它,這一點(diǎn)我一直深知,并在真實(shí)性的那篇文章中予以了說(shuō)明(1973)。但旅游者的不同反應(yīng)并不能改變“舞臺(tái)真實(shí)性”是現(xiàn)代社會(huì)中一種無(wú)所不在的、浩大的文化建構(gòu)的事實(shí),詹妮·曹(Jenny Chio)在《旅行景觀》(ALandscape of Travel)一書中收錄了大量當(dāng)代中國(guó)社會(huì)的類似事實(shí),比如:給煤渣磚房的外墻貼上樹皮裝飾,顯得更有鄉(xiāng)村意味以吸引旅游者;千篇一律的民族節(jié)日的舞臺(tái)化;明明不再種田卻刻意保留稻田當(dāng)作標(biāo)志性風(fēng)景等。這一切都是不斷發(fā)展的、全球性的“舞臺(tái)真實(shí)性”建構(gòu)。在我的《觀光倫理學(xué)》一書里,專門有一章“今日舞臺(tái)真實(shí)”( StagedAuthenticity Today),闡述了在過(guò)去40年里建構(gòu)現(xiàn)象是如何變得如此廣泛而普遍的。
其次,我揣測(cè),旅游研究者誤讀“舞臺(tái)真實(shí)性”可能與另一個(gè)深層價(jià)值觀有密切關(guān)系,即原創(chuàng)性(originality)。西方教育重視學(xué)生發(fā)現(xiàn)新事物的能力,比如博士論文就應(yīng)該包含史無(wú)前例的新構(gòu)思或新發(fā)現(xiàn)。假設(shè)在你的論文答辯會(huì)上,一位教授指著一本期刊說(shuō):“很抱歉,你博士論文的發(fā)現(xiàn)與某某人十年前發(fā)表的這篇文章基本雷同。”那么,你的答辯就宣告失敗,必須另起爐灶了。這就是為何我那一代的學(xué)生比今天的學(xué)生閱讀量要大得多的原因。一位教授曾告誡我:“如果你打算就某個(gè)專題做研究,那沒有理由不讀完有關(guān)這個(gè)專題的所有文獻(xiàn)。”我們還被教導(dǎo)要引證完所有相關(guān)文獻(xiàn),表明是怎樣將這些文獻(xiàn)整合到自己的研究中的、自己的研究與前人有何不同、對(duì)這一專題領(lǐng)域的知識(shí)體系有何新貢獻(xiàn),如若不然,科學(xué)研究就將因此而萎縮并衰亡。我曾遇到過(guò)一位日本學(xué)者,他告訴我說(shuō),如果沒有把一本書的參考書目和腳注都統(tǒng)統(tǒng)找來(lái)讀完,他就不認(rèn)為自己是“讀”了這本書。他說(shuō)他用了好幾年才差點(diǎn)讀完《旅游者》,包括閱讀書中所引用的每一本書和每一篇文章,但最終仍未完成,他很沮喪,因?yàn)槲耶?dāng)時(shí)引用了露絲·揚(yáng)(RuthC.Young)的一篇未刊稿。我告訴他這篇文章業(yè)已發(fā)表,我可以給他一份,他很感激,說(shuō)自己終于能看完《旅游者》了。
最后,還是回到“舞臺(tái)真實(shí)性”。旅游研究者處于糾結(jié)困境,他們無(wú)法忽視“舞臺(tái)真實(shí)性”,因?yàn)樗锹糜螆?chǎng)域的一項(xiàng)龐大內(nèi)容;他們不能對(duì)1973年發(fā)表的“舞臺(tái)真實(shí)性”概念模型視而不見;他們也不能故意忘記自己應(yīng)該出一些新東西的學(xué)術(shù)職責(zé),即他們的研究應(yīng)該是原創(chuàng)的。許多人把自己打成一個(gè)結(jié),來(lái)一次性應(yīng)對(duì)這些要求,他們重復(fù)我的話,并打上新標(biāo)簽,這就是布魯納·愛德華所做的事,現(xiàn)在他承認(rèn)“真實(shí)性再生產(chǎn)”就是新瓶裝舊酒,不過(guò)是“舞臺(tái)真實(shí)性”的別稱罷了;或者,他們?cè)谧约旱难芯恐性拔枧_(tái)真實(shí)性”的觀點(diǎn),仿佛只要指出我的所說(shuō)與實(shí)際所指有出入,他們就成了原創(chuàng)者;或者,他們干脆繞過(guò)原作,直接撿拾那些草率學(xué)者的牙慧;或者,他們也可能生產(chǎn)出對(duì)于該論題而言完全原創(chuàng)的知識(shí)。
我同意你說(shuō)的,“舞臺(tái)真實(shí)性”的誤用興許是合理而富于創(chuàng)造性的,但若有人想從心理學(xué)路徑探尋旅游者體驗(yàn)的真實(shí)性,那就在我的概念框架之外了,不過(guò)我歡迎并鼓勵(lì)這樣的研究,這是一條有前途的研究路徑,基本上沒有引用或參考“舞臺(tái)真實(shí)性:旅游社會(huì)空間的規(guī)置”這篇文章的必要了。
6.趙:我注意到您高度認(rèn)可喬治·范登艾比力(George Van Den Abbeele)與蒂莫西·奧克斯( Timothy Oaks)關(guān)于《旅游者》的書評(píng),那是什么原因使您認(rèn)為這兩篇書評(píng)與眾不同呢?
M:?jiǎn)讨巍し兜前攘Φ摹白鳛槔碚摷业穆糜握摺保═he tourist as theorist)是我所讀過(guò)最長(zhǎng)且最有悟性的一篇關(guān)于《旅游者》的書評(píng),他寫這篇文章時(shí)還是康奈爾大學(xué)比較文學(xué)專業(yè)的一名研究生。后來(lái)他成為一位知名的、受人尊敬的學(xué)者,勒內(nèi)·笛卡爾(Rene Descartes)研究的專家(就是那位說(shuō)“我思故我在”的法國(guó)哲學(xué)家),旅行游記史的敏銳觀察者和一所大學(xué)的系主任。《旅游者》的書評(píng)是他發(fā)表的第一篇論文。
喬治的書評(píng)之所以與眾各別,是因?yàn)樗ㄓ[全書,從整體框架著眼。大多數(shù)評(píng)論人只針對(duì)像疏離、真實(shí)性、工作展演、現(xiàn)代化這樣的單一主題,他們把《旅游者》中的各章節(jié)當(dāng)作互不相干的文章來(lái)讀,但喬治就書讀書,認(rèn)真關(guān)注了統(tǒng)領(lǐng)全書每個(gè)部分的內(nèi)在邏輯(這正是20世紀(jì)60年代我們?cè)诳的螤柎髮W(xué)被教導(dǎo)的讀書方法)。《旅游者》首先是一部關(guān)于社會(huì)變遷的書,這個(gè)社會(huì)正處于一個(gè)特定時(shí)代的尾聲階段,工業(yè)化、現(xiàn)代民族國(guó)家、民主運(yùn)動(dòng)、全球混戰(zhàn)與全球市場(chǎng)仍余波未息,相形之下,旅游這個(gè)主題的重要性就退而居其次了。喬治成為徹底理解了這本書的極少數(shù)人之一,他洞悉到我是想用旅游者這個(gè)角色解開新出現(xiàn)的全球化社會(huì)與社會(huì)關(guān)系類型的謎題。
喬治還發(fā)現(xiàn),為捕捉正在出現(xiàn)的新社會(huì)形式和人類主體性的新類型,我不得不打破社會(huì)學(xué)和人類學(xué)的學(xué)科藩籬,選擇符號(hào)學(xué)作為主要方法,因?yàn)槲倚枰獮殡S時(shí)可能出現(xiàn)的新事物和事件搭建一個(gè)有效的框架,這個(gè)框架應(yīng)該適用于地表上任何一個(gè)地理、文化或社會(huì)場(chǎng)景。在我寫作《旅游者》的那個(gè)年代,多數(shù)社會(huì)科學(xué)的理論模型都有特定的針對(duì)性,要么是一個(gè)邊界明顯的文化區(qū),要么是英格蘭工業(yè)或歐洲資本主義國(guó)家階級(jí)關(guān)系的地方形成過(guò)程,要么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的關(guān)系問(wèn)題等,只有像《勞動(dòng)分工》《資本論》這樣偉大的社會(huì)學(xué)經(jīng)典才能超越其原來(lái)的概念王國(guó),成為相對(duì)普適的元概念。然而,社會(huì)已經(jīng)行進(jìn)到了一個(gè)甚至連偉大經(jīng)典都無(wú)法解釋的關(guān)鍵歷史節(jié)點(diǎn)上了。
在20世紀(jì)中期,旅游者已無(wú)處不在,我曾經(jīng)關(guān)注過(guò)這一時(shí)期的旅游者總?cè)藬?shù),包括剛剛興起的南極或北極包團(tuán)游。今天,我們說(shuō)起市場(chǎng)全球化及其衍生問(wèn)題來(lái),可能是云淡風(fēng)輕的口氣,但那時(shí)我的《旅游者》就是打算研究文化全球化及其衍生問(wèn)題,喬治看出了我的意圖,正是這一點(diǎn)使他刻意強(qiáng)調(diào)我的“吸引力符號(hào)學(xué)”模型。地球上到處都是旅游者,我想創(chuàng)建一個(gè)模式,切實(shí)弄清楚他們想看什么、做什么,其旅游動(dòng)機(jī)的基礎(chǔ)是什么?旅游吸引物何以成為吸引物?
喬治是唯一一個(gè)看出“吸引力符號(hào)學(xué)”是《旅游者》核心的人,因此他能對(duì)《旅游者》中被忽視的內(nèi)容作出一些解讀。針對(duì)《旅游者》的文化批評(píng)維度,他說(shuō),“旅游是現(xiàn)代人的鴉片。”他用一種新穎的方式延伸了書中的論點(diǎn),“觀光不僅是如MacCannell所說(shuō)的為社會(huì)分化而上演的儀式,事實(shí)上也是在生產(chǎn)分化。”喬治也抓到了《旅游者》的革命意涵,他意識(shí)到當(dāng)旅游者踏上歸途時(shí),就再無(wú)可能完全地重新整合到其母社會(huì)了,這樣,旅游行為自身就比任何現(xiàn)成的革命理論都更具革命性。他下結(jié)論說(shuō),我們必須停止對(duì)一些固定地方的理論思考與游歷。的確,思緒徜徉,我思故我旅行。
當(dāng)我們重新思考自己關(guān)于民族志主體、文化與文化接觸的一些觀念時(shí),毫無(wú)疑問(wèn),《旅游者》在影響我們的思考方式,所以我很高興《旅游者》找到回歸人類學(xué)的路,希望有朝一日,它也能找到回歸社會(huì)學(xué)的路,雖然這仍需要時(shí)間。
蒂莫西·奧克斯的書中有一章題為“旅游與現(xiàn)代主體”(Tourism and the Modern Subject)的內(nèi)容,寫得較晚,大概是在《旅游者》出版30年后。這一章與喬治的書評(píng)很不一樣,因?yàn)槿祟愔黧w性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正如我所預(yù)見的那樣,現(xiàn)代意識(shí)(modern consciousness)已經(jīng)出現(xiàn)。在他那篇發(fā)人深省的書評(píng)里,奧克斯描述了我在《旅游者》里只提了個(gè)大概的這類現(xiàn)代或后現(xiàn)代主體,我把它歸入真正拓展了我的理論的極少數(shù)應(yīng)用案例之列,不膚淺,有意義。
奧克斯大概是從《旅游者》第44頁(yè)開始仔細(xì)閱讀,他是唯一一個(gè)認(rèn)可在西方理論話語(yǔ)中該書是結(jié)構(gòu)主義向后結(jié)構(gòu)主義過(guò)渡的橋梁的人。由于《旅游者》在后結(jié)構(gòu)主義與解構(gòu)等術(shù)語(yǔ)出現(xiàn)之前就已出版,雖然膚淺的批評(píng)家想把它當(dāng)成過(guò)時(shí)的結(jié)構(gòu)理論,但問(wèn)題在于朱麗婭和我當(dāng)時(shí)就在“后結(jié)構(gòu)主義”的誕生地——雅克·德里達(dá)的研討班上,那時(shí)德里達(dá)還是巴黎城里的一名助教;我們還參加了康奈爾大學(xué)保羅·德曼的研討班,德曼是解構(gòu)主義的教父。因此,在后現(xiàn)代主義、后結(jié)構(gòu)主義和解構(gòu)主義變成英語(yǔ)學(xué)術(shù)界的時(shí)髦術(shù)語(yǔ)之前,我的《旅游者》寫作就搭乘了被雅克·德里達(dá)和保羅·德曼演繹到極致的符號(hào)學(xué)與列維一斯特勞斯的結(jié)構(gòu)主義的便車。我在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上曾有篇小文章回應(yīng)勞教授(Lau)對(duì)我的誤讀,在這篇文章里我也重溫了這段歷史。
尤其令我高興的是,在他那一章的末尾,奧克斯比我更好地闡釋了從《旅游者》到《聚會(huì)空?qǐng)觥防锏摹敖袢帐橙俗濉保?Cannibalism Today)章節(jié)中概念的演化過(guò)程。他支持我的觀點(diǎn),即現(xiàn)代主體/意識(shí)是從前原始和后現(xiàn)代性,或者說(shuō)是從旅游者與他者之間的互動(dòng)中產(chǎn)生的。
7.趙:您1989年在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上主持了一期“旅游與符號(hào)學(xué)”的特刊,特刊的主題亦是《旅游者》的核心內(nèi)容。在中國(guó)的旅游規(guī)劃與發(fā)展中,給旅游吸引物添加文化解釋的做法很盛行,這被認(rèn)為是一種吸引旅游者的快速而有效的策略。我想知道,在美國(guó)旅游學(xué)界,除了“舞臺(tái)真實(shí)”理論的蔭蔽效應(yīng)外,是什么原因使得大多數(shù)人都忽視了《旅游者》一書中的“吸引物符號(hào)學(xué)”理論?
M:要回答你的問(wèn)題,必須先了解與《旅游者》有關(guān)的三條閱讀路線:第一條,數(shù)量最多,是把《旅游者》看作一部研究旅游者和旅游現(xiàn)象的早期力作,書里所包含一些概念可以用來(lái)提升旅游產(chǎn)品,偶爾也可以用來(lái)批評(píng)旅游對(duì)旅游目的地及當(dāng)?shù)厝嗽斐傻呢?fù)面影響,這一條路線《旅游者》為旅游者研究的開山之作。第二條,我們還未涉及,即藝術(shù)家、社會(huì)活動(dòng)家、建筑家、城市規(guī)劃者與環(huán)境設(shè)計(jì)者對(duì)《旅游者》的接受,在這些領(lǐng)域,《旅游者》被用來(lái)解釋藝術(shù)、建筑、規(guī)劃、設(shè)計(jì)等的社會(huì)環(huán)境的變遷,這也是為何我職業(yè)生涯的最后15年是在環(huán)境設(shè)計(jì)與景觀建筑系的原因了。第三條,數(shù)量最少,包括喬治·范登艾比力與蒂莫西·奧克斯這樣的反思性述評(píng),但這批人看到了《旅游者》從社會(huì)科學(xué)與人性領(lǐng)域向一般理論發(fā)展的廣闊前景,以及足以解釋這個(gè)不斷變化世界的潛力。
在某種程度上,我是幸運(yùn)的,因?yàn)?9%的讀者沒有像喬治·范登艾比力與蒂莫西·奧克斯那樣理解《旅游者》的寬廣內(nèi)涵,他們把《旅游者》當(dāng)成一部研究旅游者與旅游現(xiàn)象的書,這反倒催生了大量的應(yīng)用實(shí)踐,并使這本書在應(yīng)用領(lǐng)域屹立不倒。
8.趙:最后一個(gè)問(wèn)題是關(guān)于旅游社會(huì)學(xué)與旅游人類學(xué)。事實(shí)上,在我涉入旅游研究之初,我對(duì)您和埃里克·科恩(Erik Cohen)的學(xué)科歸屬和學(xué)術(shù)身份的認(rèn)識(shí)是模糊的,當(dāng)然,現(xiàn)在我知道您們二人都曾有或多或少的人類學(xué)教育背景。那么,您能談?wù)劼糜紊鐣?huì)學(xué)和旅游人類學(xué)的研究有怎樣的區(qū)別嗎,或者說(shuō)探究這種區(qū)別本身是有意義的嗎?在中國(guó),一些年輕學(xué)者對(duì)旅游研究缺乏信心,您能就自己的學(xué)術(shù)生涯談?wù)勀鷱氖侣糜紊鐣?huì)學(xué)研究的動(dòng)力嗎?
M:我的研究是介于社會(huì)學(xué)和人類學(xué)之間,你的認(rèn)識(shí)是正確的。這是有充分理由的,讓我試著解釋一下。
我酷愛文化人類學(xué),本科時(shí)學(xué)得如饑似渴,課余時(shí)間還自己看民族志報(bào)告。但是20世紀(jì)60年代是人類學(xué)的危機(jī)時(shí)刻,其研究對(duì)象——原始文化——在地表上幾乎消失殆盡。然而,不像現(xiàn)在,當(dāng)時(shí)但凡有些名氣的人類學(xué)系都不會(huì)同意學(xué)生提交不針對(duì)“原始”文化的論文,盡管原始文化所剩無(wú)幾,幸存的那些也正走向消亡。研究生們?nèi)员桓嬲]說(shuō),即使文化接觸已經(jīng)發(fā)生,文化變遷已經(jīng)開始,也必須要捕捉到文化的純粹狀態(tài),哪怕為此只能去訪談最老的族群成員。我成不了這類工作的一員,我強(qiáng)烈感覺必須離開這個(gè)自己熱愛的領(lǐng)域,因?yàn)槲也辉敢鉃榱搜芯咳祟悓W(xué)王國(guó)碩果僅存的那點(diǎn)東西而去拼命爭(zhēng)取。我身體里那個(gè)科學(xué)家說(shuō),“如果文化接觸導(dǎo)致文化變遷,那么接觸與變遷是我們應(yīng)該研究的對(duì)象,而不是那些虛擬化的過(guò)去。”這也是為什么我對(duì)納爾什·格雷本(Nelson Graburn)的因紐特(Inuit)旅游雕刻品研究充滿敬佩的原因。1976年納爾什出發(fā)去研究當(dāng)時(shí)被認(rèn)為仍是純粹的、原始的、未被現(xiàn)代文明侵染的因紐特文化,但是他對(duì)還原因紐特文化曾有的形貌并不感興趣,他通過(guò)因紐特藝術(shù)文化的案例,告訴我們?cè)谶@個(gè)每一文化都與其他文化有潛在聯(lián)系的新世界里,因紐特人是怎樣調(diào)適其生活的。
但是,即使我知道我寫不出關(guān)于白人到來(lái)之前的原始生活的準(zhǔn)虛構(gòu)報(bào)道,我也不能任由人類學(xué)驅(qū)使自己去解讀一個(gè)人群的全部生活,去探究文化的每一部分是怎樣與其他部分相互適應(yīng)的。1963年,我在康奈爾的鄉(xiāng)村社會(huì)學(xué)系開始研究生學(xué)習(xí),當(dāng)時(shí)它是世界上排名很靠前的名系,其王牌專業(yè)是國(guó)際發(fā)展與現(xiàn)代化。我想我可以在原始人群曾經(jīng)生活過(guò)的附近區(qū)域做田野調(diào)查,觀察這些人群最終走向了何處。結(jié)果,我在田野調(diào)查中所體驗(yàn)到的一切悲哀都被列維一斯特勞斯那本關(guān)于南美探險(xiǎn)的游記的書名——《憂郁的熱帶》(Tristes Tropiques)給概括了,那本書最初譯成英文時(shí)名為《衰落的世界》(World on the Wane)。
今天的人類學(xué)轉(zhuǎn)過(guò)來(lái)又允許甚至是鼓勵(lì)用民族志方法來(lái)調(diào)查像旅游團(tuán)隊(duì)、運(yùn)用旅游營(yíng)銷或接受新技術(shù)使自己能(或不能)適應(yīng)現(xiàn)代世界的原始村莊這樣的對(duì)象,但在我本科時(shí)這是不可能發(fā)生的事情。我的一個(gè)人類學(xué)專業(yè)的同學(xué)提交了關(guān)于美國(guó)流行音樂的文化解釋的研究計(jì)劃,結(jié)果被勒令離開項(xiàng)目組,她是專業(yè)碩士里的優(yōu)等生,但就是因?yàn)樗氤鲞@么一個(gè)論題,就怎么也人不了人類學(xué)系的法眼。
我很快發(fā)現(xiàn)社會(huì)學(xué)對(duì)整體性研究不怎么感冒,我必須學(xué)習(xí)將對(duì)象拆解成階層、制度、官僚制、族群性、性別、地位與角色、消遣、城鎮(zhèn)與鄉(xiāng)村和支配性區(qū)域經(jīng)濟(jì)活動(dòng)等(像東北工業(yè)區(qū)、中西部農(nóng)業(yè)區(qū)等)概念,我還必須學(xué)習(xí)搜集能禁得起統(tǒng)計(jì)分析和假設(shè)檢驗(yàn)的數(shù)據(jù)類型。從20世紀(jì)50至70年代,一些社會(huì)學(xué)家(其中最出名的是歐文·戈夫曼)一直運(yùn)用整體觀的民族志方法,但研究對(duì)象主要是小群體的行為和面對(duì)面的互動(dòng)。我的人類學(xué)偏好使我將研究方向鎖定在社會(huì)整體性而非微觀層面的行為與互動(dòng),列維一斯特勞斯曾告誡我不要嘗試做現(xiàn)代性的民族志研究,他說(shuō)那是不可能的事,但最終我還是義無(wú)反顧了。
我為《旅游者》搜集了大量有關(guān)旅游場(chǎng)所和旅游吸引物的資料,因此我有足夠的數(shù)據(jù)來(lái)做編碼和統(tǒng)計(jì)分析,而且我確實(shí)從社會(huì)學(xué)那里借鑒了一些傳統(tǒng),比如要為自己的數(shù)據(jù)處理方式提供解釋,但在人類學(xué)領(lǐng)域,只要你能簡(jiǎn)單地描述資料的處理方法,就會(huì)得到贊許。我選擇用文字解釋我的數(shù)據(jù),而不是用統(tǒng)計(jì)方法來(lái)檢驗(yàn)假設(shè);但是,我也很樂于閱讀那些為《旅游者》的概念表述提供統(tǒng)計(jì)檢驗(yàn)的博士論文和期刊論文。最終,在《旅游者》里所涉及的社會(huì)學(xué)概念,像工作、消遣、官僚制、階層、村莊、制度等都顯得不像是概念范疇和理論建模,似乎統(tǒng)統(tǒng)被旅游吸引物這個(gè)概念象征性地置換了。你可以在《聚會(huì)空?qǐng)觥返摹昂蟋F(xiàn)代社區(qū)規(guī)劃”(Post- Modern Community Planning)那章里找到我對(duì)這種統(tǒng)計(jì)與象征之間關(guān)系的反思。
我是知道和理解這兩個(gè)領(lǐng)域的區(qū)別的,我很愿意承認(rèn)《旅游者》既是人類學(xué)的,也是社會(huì)學(xué)的,但就這本書被接受的現(xiàn)實(shí)過(guò)程來(lái)看,人類學(xué)家一直被它吸引,社會(huì)學(xué)家則不然。
結(jié)束語(yǔ)
在《休閑階層的理論》(The Theory of theLeisure Class)(1899) 一書中,索爾斯坦·凡勃倫(Thorstein Veblen)用“炫耀性消費(fèi)”和“去生產(chǎn)性勞動(dòng)”[7]兩個(gè)重要指標(biāo)識(shí)別出工業(yè)社會(huì)的一個(gè)新興群體——休閑階層,揭示了社會(huì)結(jié)構(gòu)的分化與變遷。這正是《旅游者:休閑階層的新理論》之書名的思想泉源,Dean MacCannell洞察到,社會(huì)結(jié)構(gòu)的分化催生了以旅游活動(dòng)為身份標(biāo)志的新休閑階層——旅游者,于是,旅游者作為一般現(xiàn)代人的典型代表,轉(zhuǎn)喻地成了MacCannell解析現(xiàn)代性的樣本。對(duì)20世紀(jì)70年代的西方社會(huì)而言,《旅游者》表達(dá)了關(guān)于旅游者、旅游吸引物的創(chuàng)造性觀點(diǎn),至少使對(duì)旅游有想當(dāng)然念頭的西方人獲得了關(guān)于前臺(tái)一后臺(tái)、虛假一真實(shí)、他者一我者、疏離一團(tuán)結(jié)[8]的二元反思意識(shí);同時(shí),在西方旅游研究共同體中,出版40余年的《旅游者》被視為真實(shí)性知識(shí)再生產(chǎn)的基地,罕見地免除了成為故紙堆的命運(yùn)。然而,MacCannell對(duì)現(xiàn)代性的解析過(guò)程,即《旅游者》一書的線索與結(jié)構(gòu)至今仍像個(gè)謎題,令人費(fèi)解,再加上作者戲謔的寫作風(fēng)格,都直接或間接導(dǎo)致《旅游者》“片斷可知,整體不可解”的閱讀現(xiàn)象。就西方旅游學(xué)界的閱讀經(jīng)驗(yàn)來(lái)看,《旅游者》是典型的“作者已死”的論著,成了被每一個(gè)接收它的人創(chuàng)造性閱讀、闡釋和賦予意義的文本。《旅游者》的文本貢獻(xiàn)與閱讀成就南轅北轍,使Dean MacCannell既獲得了學(xué)術(shù)聲望,也承受了一些污名。因此,要在《旅游者》的擁躉現(xiàn)象與閱讀現(xiàn)象的矛盾中探索其基于中國(guó)旅游經(jīng)驗(yàn)的理論貢獻(xiàn)與運(yùn)用價(jià)值,遠(yuǎn)非訪談的文本形式與篇幅所能勝任。但是,我們可以請(qǐng)作者復(fù)活,了解主位觀的寫作目的與方法論闡釋,并從《旅游者》的理論建構(gòu)與運(yùn)用研究?jī)蓚€(gè)維度做解讀與反思,提出反詰,從而推動(dòng)對(duì)《旅游者》作為旅游經(jīng)典論著的意義探索實(shí)踐,最終為國(guó)內(nèi)旅游研究尤其是真實(shí)性研究廓清方向,為創(chuàng)新研究提供可能。
從理論維度看,整部《旅游者》構(gòu)建了兩個(gè)重要理論:“舞臺(tái)真實(shí)性”與“吸引力符號(hào)學(xué)”。“舞臺(tái)真實(shí)性”的內(nèi)容與1973年“舞臺(tái)真實(shí)性:旅游情境下的社會(huì)空間設(shè)置”一文大同小異,其理論靈感來(lái)源于歐文·戈夫曼《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現(xiàn)》中的“前臺(tái)一后臺(tái)”理論,關(guān)于該理論的引介性論述可參見張曉萍、彭兆榮、楊慧的文章,不贅。一個(gè)重要的問(wèn)題是MacCannell是怎樣改造了“前臺(tái)一后臺(tái)”理論,用意何在?戈夫曼發(fā)現(xiàn)人們?cè)谌粘I钪谐3O乱庾R(shí)或無(wú)意識(shí)地運(yùn)用一種印象管理策略,即愿意展示一些事實(shí)而掩抑另一些事實(shí),展示部分放在人前一前臺(tái),掩抑部分藏到人后一后臺(tái)。通過(guò)對(duì)社會(huì)空間的“前臺(tái)一后臺(tái)”的二元?jiǎng)澐郑攴蚵赋銮芭_(tái)的表演性與后臺(tái)的真實(shí)性,從而得以解釋人性在多大程度上取決于前后與后臺(tái)的分界[9]。如果說(shuō)戈夫曼的“前臺(tái)一后臺(tái)”是基于個(gè)體或角色群體層面的、具象的社會(huì)空間區(qū)隔,那么MacCannell的“前臺(tái)一后臺(tái)”則是基于文化層面的抽象的旅游空間區(qū)隔;戈夫曼通過(guò)人們?nèi)粘I畹淖晕页尸F(xiàn)建構(gòu)了自我與他人的邊界,MacCannell借用旅游吸引物的“自我呈現(xiàn)”的多樣性建構(gòu)了東道主與游客之間的多重邊界,亦揭示了現(xiàn)代性的擴(kuò)散本質(zhì)。具體地,MacCannell建構(gòu)了“主一客”之間看與被看的相互關(guān)系,為提升被看的頻次與規(guī)模,東道主往往選擇表演一部分真實(shí)性而遺漏另一部分真實(shí)性,于是游客看到前臺(tái)表演的真實(shí)性而錯(cuò)過(guò)后臺(tái)自在的真實(shí)性。然而,MacCannell說(shuō)他的本意不在真實(shí)性本身,而在真實(shí)性的社會(huì)建構(gòu),即旅游吸引物在被呈現(xiàn)和舞臺(tái)化的過(guò)程中采用了哪些顯得真實(shí)的手段和方式。這是一個(gè)清晰的信號(hào),一位社會(huì)學(xué)家在細(xì)致剖析旅游吸引力的形成機(jī)制,他把真實(shí)性預(yù)設(shè)為西方旅游者所追求的核心價(jià)值觀,于是作為供應(yīng)一方的東道主動(dòng)用了真實(shí)化策略。
“吸引力符號(hào)學(xué)”的建構(gòu)邏輯與“舞臺(tái)真實(shí)性”類似,但有兩點(diǎn)必須予以強(qiáng)調(diào):一是《旅游者》第二章中的吸引力結(jié)構(gòu)與景觀神圣化,既提出了旅游吸引力的另一種形成機(jī)制——神圣化,又為第六章吸引力符號(hào)學(xué)研究打下認(rèn)識(shí)論基礎(chǔ);二是凸顯旅游者的“看”,進(jìn)一步剖析旅游吸引力的結(jié)構(gòu)關(guān)系:景觀一標(biāo)志一游客,從文化與旅游視覺體驗(yàn)的關(guān)系中提煉出旅游吸引力更為普遍的機(jī)制一符號(hào)化。但尚未結(jié)束,“舞臺(tái)真實(shí)性”與“吸引力符號(hào)學(xué)”不過(guò)是MacCannell的理論工具,他的目的在于現(xiàn)代性。MacCannell認(rèn)為,現(xiàn)代性的最大特征就是社會(huì)結(jié)構(gòu)的分化,但吊詭的是,社會(huì)分化并未帶來(lái)預(yù)想中的社會(huì)團(tuán)結(jié),反而引發(fā)對(duì)自我社會(huì)的疏離。于是,生活世界的社會(huì)是一個(gè)巨大的前臺(tái),它所缺失的后臺(tái)將仰仗旅游世界來(lái)彌補(bǔ),即異國(guó)他鄉(xiāng)、彼地、彼時(shí)、他者。當(dāng)然,在旅游世界,旅游者仍將迷失在旅游吸引物的結(jié)構(gòu)分化之中。這就是MacCannell關(guān)于現(xiàn)代性的民族志書寫:社會(huì)結(jié)構(gòu)的分化無(wú)所不在,旅游吸引物是分化的象征對(duì)應(yīng)物,至于旅游吸引力,無(wú)論是真實(shí)化、神圣化,還是符號(hào)化的機(jī)制,皆由現(xiàn)代社會(huì)集體收集與訂制。
基于上,我們可做如下理論思考:(1)為何“舞臺(tái)真實(shí)性”從一個(gè)從屬的工具性概念變成了范式研究?(2)《旅游者》以社會(huì)、旅游為核心的論證過(guò)程被發(fā)揚(yáng)光大,而論證目的——現(xiàn)代性與社會(huì)分化被普遍忽略,這是文本導(dǎo)向、讀者導(dǎo)向、學(xué)科導(dǎo)向還是現(xiàn)實(shí)導(dǎo)向的原因? (3)MacCannell的跨學(xué)科方法是否值得借鑒,如果可以借鑒,旅游研究者應(yīng)保持一個(gè)怎樣的學(xué)科立場(chǎng)?(4)從《旅游者》是否能總結(jié)出旅游社會(huì)科學(xué)研究最突出的文本特征體現(xiàn)在哪些方面?
《旅游者》對(duì)于國(guó)內(nèi)旅游社會(huì)科學(xué)研究的意義目前難以系統(tǒng)化,只能從個(gè)人層面做淺談。就真實(shí)性研究而言,“舞臺(tái)真實(shí)性”與真實(shí)性理論已成為旅游區(qū)域、旅游吸引物、旅游體驗(yàn)研究的理論工具,因此這一論域可嘗試本土化的基礎(chǔ)性研究,比如追溯真實(shí)性價(jià)值觀的中國(guó)文化之根,再調(diào)查中國(guó)文化背景的旅游者對(duì)旅游吸引物真實(shí)性的看法,或者更直白地自問(wèn):我們是追慕真實(shí)性研究,還是需要真實(shí)性研究?真實(shí)性理論在國(guó)內(nèi)生根的學(xué)理依據(jù)與文化傳統(tǒng)何在?這一工作既需要實(shí)證研究,亦隱含對(duì)方法論的探索。在研究者輕易對(duì)旅游吸引物做出“舞臺(tái)真實(shí)性”的價(jià)值判斷之前,不如先像MacCannell 一樣去觀察它們被真實(shí)化的手段和方式,這樣的研究功在知識(shí)生產(chǎn)的特殊性、地方性與累積性。簡(jiǎn)言之,“舞臺(tái)真實(shí)性”在國(guó)內(nèi)的概念移植需要檢驗(yàn)其適用性與有效性。就吸引力符號(hào)學(xué)而言,首先應(yīng)分析MacCannell的旅游吸引力機(jī)制在國(guó)內(nèi)是否有對(duì)應(yīng)的現(xiàn)象,再思考它在國(guó)內(nèi)旅游研究中作為認(rèn)知手段的理論意義與學(xué)科價(jià)值。
總之,《旅游者》是Dean MacCannell教授的標(biāo)志性研究成果,該書記載了他年輕時(shí)代的社會(huì)學(xué)抱負(fù),亦被證明是一部具有原創(chuàng)性與前瞻性的論著,《旅游者》在西方旅游研究學(xué)界的長(zhǎng)盛不衰是促成此次訪談的根本原因。作為率先起意的訪談人,筆者在訪談過(guò)程中受益匪淺,因此對(duì)上述反思有畫蛇添足之憂,倘若有吉光片羽的貢獻(xiàn),也應(yīng)歸功于Dean MacCannell教授的循循善誘及其激發(fā)他人閱讀欲望的能力。
參考文獻(xiàn)(References)
[1]MacCannell D. Anthropology for all the wrong reasons[A]//Nash D. The Study of Tourism: Anthropological and Sociolo-gicaI Beginnings[C]. Boston: Elsevier Science, 2007: 142-146.
[2]MacCannell D. The making ofthe tourist[J]. Unpublished.
[3]MacCannell D. Introduction[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1989, 16(1): 1-6.
[4] Van den Abbeely G. Review: Sightseers: The tourist as theorist [J]. Diacritics, 1980, 10(4): 2-14.
[5] MacCannell D. The Tourist: A New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M].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76:13.
[6] Cohen E, Cohen S. Current sociological theories and issues intourism[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12, 39(4): 2177-2202.
[7]Veblen T. 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M]. Cai Soubai,trans.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2009: 30-79.[索爾斯坦·凡勃倫.有閑階級(jí)論--關(guān)于制度的經(jīng)研究[M].蔡受百,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09: 30-79.]
[8]MacCannell D. Staged authenticity: Arrangements of socialspace in tourist settings[J].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73, 79(3):589-603.
[9]MacCannell D. The Ethics of Sightseeing[M].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