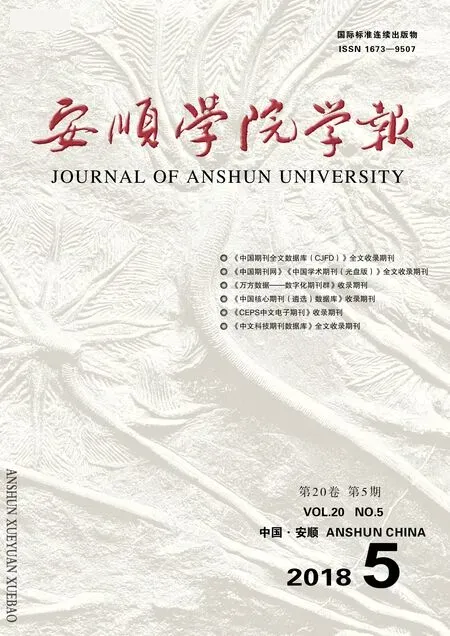論西南少數民族民間文學的社會治理思想
(1、2.貴州民族大學,貴州 貴陽550025)
現代主體論的思維使人類逐漸脫離自然界,自然成為人類改造世界的對象和物質資料的來源,由此而來的人類中心主義破壞了人對自然界的敬畏,成為引發現代性危機的一個重要因素。工具理性和經濟主義成為現代社會解讀一切現象的手段,形成對話語權的壟斷。所有非科學、非理性的事物成為了“未開化”的客體和他者。未接入世界體系的民族文化變成了所謂的“活化石”,民族生活空間和文化場域被“尊稱”為活著的“博物館”。這是文化帝國主義對非主流的“文化”一種不失身份的放逐和邊緣化。在這種視域下,我們無法客觀看待民族文化的價值,更無法發現民族文化的智慧與偉大。因此,必須對民族文化中蘊含的豐富智慧進行深入發掘,特別是對民族同胞以想象和愿景所構建出的民族民間文學進行深度理解,才可能客觀全面地認識民族文化。 西南地區少數民族民間文學的一大特征在于其具有多重的社會功能,不僅是一種民俗文化,還是民族地區社會治理的重要構成部分。社會治理(Social Governance)是政府、社會組織、企事業單位、社區以及個人等多種主體通過平等的合作、對話、協商、溝通等方式,依法對社會事務、社會組織和社會生活進行引導和規范,確保實現公共利益。社會治理的核心是多方參與的公共事務管理,涉及到社會公共生活的方方面面,用柔性手段調節社會關系,化解社會矛盾。治理的理想目標是善治,即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管理活動和管理過程,善治意味著官民對社會事務的合作共治,是國家與社會關系的最佳狀態。[1]15而西南地區少數民族民間文學則在社會治理中承載著大量群體成員義務觀念、行為規則、道德導向等社會治理中需要的原則和依據,并且伴隨著民族同胞的生產生活實踐參與到民族地區的基層社會治理活動中。因此,在民族民間文學中發掘這些寶貴的社會治理思想既能為當下中國社會治理帶來重要的啟發,又有助于拓展對西南地區少數民族文化的研究維度。
一、 西南少數民族民間文學研究的理論回顧
西南地區少數民族民間文學的研究成果豐碩,汗牛充棟。早在20世紀40年代,以西南聯大學者為主體的研究群體就對西南地區少數民族神話進行了較為系統的研究。再到20世紀80年代,在文化部、國家民宗委等部門支持下編撰的《民間文學三大集成》又對西南地區民族民間文學資料較為系統、全面的收集和整理。事實上,西南地區少數民族地區的民間文學一直以來都是學術界關注的熱點,各民族的歌謠、民間故事、神話等民間文學形式都得到多角度的分析和研究,不便一一贅述。在此主要考察針對西南地區少數民族民間文學解讀的相關研究。
鑒于民族民間文學資源的豐富多彩,很多學者嘗試對西南地區少數民族民間文學中的象征與意義進行研究。比如,支媛等人對水族神話中體現的多神信仰進行分析,嘗試解讀水族傳統信仰中的民族文化內涵。[2]142-144楊憲昭認為人類再生型的洪水神話表現了各民族間存在的文化共性。[3]141-146田光輝等人對苗族古歌進行了哲學視角的研究,認為古歌中記錄苗族先民們披荊斬棘的奮斗歷程展現民族同胞的民族性格。[4]172-180徐積明則認為苗族古歌中包含了樸素的唯物主義思想。[5]44-46陳漢杰等人認為苗族古歌體現了苗族同胞的審美意識,通過對其的研究,有助于了解中華民族美學思想的總體特征。[6]38-40屈永仙對云南傣族地區的英雄故事“布崗朗并”進行了研究,認為其故事情節幾乎與侗族的“吳勉傳說”和壯族的“莫一大王”十分相似,認為這體現了傣族與壯、侗民族共同分享著百越文化的底蘊。[7]33-37
總體來看,多數對于民族民間文學解讀的研究主要以文本分析為主,這與民族民間文學生長的現實社會環境還存在一定的距離。劉錫誠先生就對于民間文學的解讀態度就比較謹慎,比如在神話方面,他認為,神話產生于人類社會的早期階段,距離現在實在是太遙遠了,因此神話的真實含義是很難了解的。現在我們對神話的種種解釋,充滿著歧義,在某種程度上說,都是由于猜測和臆斷所造成的。[8]59-64他不贊成對民族神話作過度解讀。可見,盡管民族民間文學蘊含的豐富內涵讓眾多學者對其著迷不已,但是劉錫誠先生的擔心提醒了我們,單純的文本分析存在著一定的捕風捉影、過度解讀的風險。因而需要把少數民族民間文學放置于具體的民族生活環境中加以看待,才可能更加接近民族民間文學本真的面目。而從社會治理的角度來看,各種民族民間文學形式在民族同胞日常生活的作用發揮了調節社會關系的作用,是民族地區社會治理的重要參與要素。
故而立足于社會生活,發掘民族民間文學中關于社會治理的思想是一種較有意義的思考維度。在這一方面,目前多數關于民族地區社會治理的研究仍然采用的是比較傳統社會學、政治學、行政學等學科視角,除肖遠平、奉振對苗族民間故事善惡觀念與社會基層治理的關系進行了探討之外[9]48-52,關于民族民間文學與社會治理之間關系的研究尚不多見。因此,文章試從民族民間文學賴以生存的社會生活出發,探析民族民間文學中富含的社會治理思想對于當下社會治理的啟示,同時豐富對民族民間文學的研究視角。
二、 傳唱的法律
1.作為社會治理規則的歌謠
少數民族同胞熱愛生活、崇尚自然,傳統民族文學的發展與社會實踐活動交融在一起。以歌謠形式流傳的民間文學既是一種藝術形式,又是記錄民族傳統、歷史、倫理和社會規范的載體,集審美、教育、規范引導等社會功能于一身。可以說是具有社會治理功能的民族藝術,也可以說是一種富含藝術審美價值的社會治理手段。
自古以來,西南地區少數民族大多以習慣法調節社會關系、管理公共事務。清乾隆帝在處理“苗疆事宜”時指出:苗民風俗與內地百姓迥別,苗眾一切自相爭訟之事,俱照苗例,不必繩以官法[10]60。乾隆皇帝所指的苗例并非成文的法律典籍,而是蘊含在苗族古歌、理辭當中具有規范作用的內容。侗族、水、布依族就通過編成歌謠的形式保存訂立的款約或榔規,用歌唱的形式傳播這些社會規則。如,侗族以款約作為維系社會秩序的規范標準,款約制定或者修訂后,款首們就將制定款約的經過和款約的內容編成侗族民歌,通過傳唱的方式進行“政策宣傳”,讓款約深入人心。其中有這樣的內容:天管地,地生人,薩媽管天下,款約管侗村。衣輩先民制“款約”,子子孫孫應遵循,誰敢違反,款律治罪無情!……亂砍寨旁風水樹,處罰銅元五十吊。亂砍架橋木杉樹,處罰銅元三十吊,偷盜耕牛,處罰銅元三十至一百吊……。[11]56-58苗族理辭中還有處理家庭關系的內容:公公是公公,婆婆是婆婆,父親是父親,……各人是各人,倫理不能亂,……遠要笑,來近要問,弟弟問哥哥,小輩問長輩,子女問父母,兒懂事,孫明理。通過這種平直樸實的藝術形式將社會倫理規范記錄、傳達和運用于社會生活當中,有助于倫理價值成為社會共識,內化于人們的觀念之中。
不同于以抽象思維為基礎的現代成文法律體系,這種形式的規范是一種形象思維的產物,只有一些最基本的規則條單獨列出,更多的具體處理原則和方式則蘊含在具體的事件和案例中。如苗族理辭《希雄》敘述了希雄公誘奸漂亮的匹囊耐,又打死處理誘奸案件的“理老”乍雄勇和王降,最后被“理老”判罰以房屋、田土作賠償[12]90-93。這些記錄在理辭、古歌中的故事成為理老們進行社會仲裁的法律依據和參考案例。客觀來看,這是一種具有社會治理功能的藝術形式,具有獨特的生命力。膾炙人口、容易理解的歌謠在少數民族同胞手中變成一種多功能的手段,將社會教育、制度宣傳、糾紛調解、歷史記錄等集于一身,降低了一般民眾接觸、掌握本族文化的門檻,使之成為全民共有、全民共享、全民共創的精神財富。
2.少數民族歌謠對當下社會治理的啟示
中國在法治社會建設的探索過程中,面臨著法律知識普及面不足和法律精神傳播效果不佳的困難。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法治化和社會治理規范化是一個自上而下的過程。大多數社會民眾秉持的傳統社會道德價值體系和社會管理者所推行的現代法治文明之間不能完全兼容,法治精神傳播進展緩慢。相比于這種表里不一的社會運行情況,少數民族同胞將本民族的社會規則放置于民間歌謠之中,將藝術審美和法律意識的傳播融為一體,在客觀上促進了法律精神與法律實踐的統一。通過世代的傳習,榔規、款約等“法律規定”在古歌、理辭的演繹中逐漸成為民眾內心的規范和信仰。這些歌唱的法律不僅在實踐中成為伸張正義的標尺,也在審美和娛樂過程中樹立了民眾內心的律法觀念。
三、表達少數民族自然觀念的古歌
1.古歌中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觀念
主體論的思維模式是現代社會的一大重要特征,就其進步性而言,這種思維有力對抗了前工業社會宗教思想對人的桎梏和人在宗教世界觀下的自我異化,通過重視人的價值,解放了人類的思想和創造力。但是這種思維模式的局限性在于將人作為衡量世界萬物的尺度,以單向視角去審視多維度的世界,因而將自然視為“征服”的對象,將主流文明之外的文明形式視為“他者”。換言之,這種主體性的思維方式就是把主體作為世界上一切存在者的根據和尺度,除了主體——人之外,其他的一切存在者之所以存在的根據就在于主體,主體是他們存在的惟一理由,在這種主體性思維方式中,人挺立出來了,成為優于其他一切存在者的存在者[13]20-23。這樣,人成為了主體,而世界則淪為客體。在這種認知下,人類在改造自然和創造物質財富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也被主體性思維局限了視野,將人與自然的關系二元化,割裂了人與自然的天然聯系,作為人類社會載體和母體的自然被降格成了外在的改造對象,人對自然的認識變成了實現“與目的性相符合”的工具和途徑。
與之相對應的是,少數民族社會傳統上依賴自然條件和環境資源的供給,因此更加重視環境與人之間的關系和諧,在生產實踐中逐漸形成了和諧的自然觀和生態觀。西南地區少數民族往往將自身視為自然之子,并不把人的意志凌駕于自然之上,而是將自己看作自然的一個組成部分,人與自然界的其他生物處于平等地位。在侗族古歌《人類的起源》中,人類與動物是兄弟,在一起生活[14]38-42。白族、土家族同胞認為自己是白虎的后裔,彝族、納西族則將黑虎視為自己的祖先。根據苗族古歌《楓木歌·十二個蛋》的記載,苗族先民認為人、神、獸共祖,并把宇宙世界看成是一個整體的系統,強調萬物出自同一本源,把天地萬物都統一到云霧(水氣)那兒。貴州黔東南的苗族則有蝴蝶媽媽的說法,認為蝴蝶是人類的始祖。在這種觀念下,少數民族同胞對自然界是心懷敬畏的,與自然建立親密和諧的關系,并將這種觀念融合進了民族神話傳說與社會行為規范當中。彝族就忌諱砍伐龍樹,認為龍樹好壞關系到族人的興衰富貧,故嚴禁去龍樹林區伐木、放牧。更忌在出泉水的池塘洗手洗腳,認為這樣會污染水井,觸怒龍王,輕則病,重則死乃至降臨洪旱災害,殃及村莊糧食無收[15]269。可見,在西南地區少數民族的觀念中,人與自然的關系或者是親子關系,或者是平等關系。這就使得少數民族同胞在各種習俗中,特別注重對人的約束、對生靈的尊重和對自然的敬畏,并不完全將自然作為達成人類目的的客體。因而,人與自然的關系比較和諧。
2.少數民族古歌對于社會生態治理的啟示
從社會治理的角度來看,生態治理已經成為當代社會治理的重要環節。當前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仍然突出,多階段、多領域、多類型生態環境問題交織,生態環境與人民群眾需求和期待差距較大,提高環境質量,加強生態環境綜合治理,加快補齊生態環境短板,是當前核心任務[16]。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有賴于自然資源的恰當利用和自然環境的有效保護。長期以來,以生態環境破壞為代價的經濟增長模式得不到根本性改變的原因在于,人類依舊將自身看作世界的主體,將自然看作資源供給來源和被改造的客體少數。少數民族同胞在長期生活中形成了自然和諧的生態觀念,不將人類自身視為凌駕于自然之上的主體,不單純以人類需求為導向審視自然,而以平等的視角看待自然與人類之間關系,這種淳樸的自然觀念對于扭轉當下社會狹隘的發展觀念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四、樹立社會模范的神話傳說
1.作為社會模范的英雄人物
英雄模范人物有引導社會風尚和社會教化的作用,相比于抽象的教條和理性原則,英雄模范人物的事跡有具體性、生動性的特征,易于在普通百姓間傳播,是普及知識、樹立信念的重要手段。特別是在沒有文字記載和基礎教育不太發達的少數民族中,這種英雄模范事跡的傳播還具有記錄歷史、傳承文化的作用。符號化英雄和神話故事是構建民族文化場域的重要成分,也是連接民族同胞緊密關系的重要文化紐帶,更是少數民族社會的重要精神寄托和文化自信的依據。民族同胞熱愛自由、崇尚公平,在漫長歷史進程中,涌現了大量優秀人物,這些杰出分子長期被本民族所紀念,最后成為神話人物。在侗族信奉的神靈中,有一類神靈就是由族內的凡人升格而來的。這些道德品行優秀、做出過巨大貢獻、有優秀事跡的先賢被后人尊為神靈供奉起來,作為后世楷模。如,侗族同胞崇敬的神靈薩歲是以一名叫作婢奔的女英雄為原型的,作為歷史人物的婢奔帶領同胞反抗官府壓迫,英勇斗爭,最后不幸犧牲。侗族同胞為了紀念這位優秀人物的高貴品質,至今將其作為保護神崇拜。這樣,現實中的優秀人物、事跡通過神化和信仰化的方式進行傳播和傳承,產生了更為深遠和長久的教化作用。
如,彝族英雄史詩支嘎阿魯在千百年的民族文化傳承過程中,通過民間文學形式的流傳與塑造,從歷史人物成為逐造成為神話人物,作為彝族人民的英雄楷模流傳至今。肖遠平認為,支嘎阿魯是一個從歷史人物到有多重身份和功績的復合式英雄[17]133-141。在彝族史詩中記述了很多關于彝族人民面對邪惡入侵勢力的威脅奮勇抗擊的故事內容,既包括對戰爭過程的精彩描述,又包括戰爭破壞性后果的記載,蘊含著比較科學合理的歷史觀、戰爭觀、人生觀,并形成了關于“真、善、美”的價值標準,指引著彝族民眾正確地處理個人與社會的關系,為實現個人幸福和社會的發展而努力奮斗[18]39-45,體現出了彝族人民不畏強敵,但熱愛和平的道德風尚。再如,銅仁地區的苗族還流傳著老憨哥和桃花姑娘的傳說。在傳說中,貧窮本分的老憨哥和桃花姑娘自由戀愛,惡霸意圖霸占桃花姑娘,為了不連累本寨鄉親,兩人遠走他鄉,銷聲匿跡。當地人民為紀念二人,每年舉辦“花山節”。傳說中的桃花姑娘不嫌貧愛富,與貧窮但本分勇敢的老憨哥相愛,在惡霸的威逼利誘下仍對愛情忠貞不渝,體現了苗族人民真摯樸素的愛情觀;老憨哥勇敢對抗惡勢力,救回愛人后,為避免禍及鄉親父老而背井離鄉,成為代表勇敢和責任的英雄形象。在節日慶典的背后體現少數民族同胞對婚戀自由和幸福生活的追求和向往,通過故事中樹立的人物形象,抽象的道德品質獲得了擬人化的身份和形態,并使之成為永遠生活在村寨里的神靈和傳統價值的庇護者。
2.少數民族神話傳說對社會道德風尚導向的啟示
社會治理的多元主體中,公民參與是重要的環節。這就需要培養具有較高文化素養和較強公民意識的高素質公民群體。少數民族同胞在神話傳說中樹立起來的英雄形象不是具體的個人,而是在這些英雄人物中傾注了少數民族同胞對于完美社會成員形象的寄望,是對理想化人物的具象化。在神話傳說的傳頌過程中,這些英雄模范的言行和事跡就成為了少數民族同胞的行為規范的參考和標準。而各種對于理想化英雄的仿效則激發出群體成員對所屬社會的忠誠與認同,同時也塑造著個人作為群體成員的應有素養。因此,在當下社會治理中,也應當大力發掘傳統文化中的英雄人物作為代表性符號,引導社會道德風尚。
五、調解社會矛盾的傳說故事
1.以故事、傳說為依托調解社會矛盾
在社會生活中,道德教化和說理是比較常見的調節社會關系的手段。而民族文化中道德規范和價值標準很多是包含在民族民間故事、傳說之中的。在社會關系的調節,特別是矛盾化解中,調節者往往需要在大量的民族傳說和故事中旁征博引才能獲得說服性的效果,因而民族地區的社會關系的調節者往往都是資深的民族故事講述者。具體來看:
第一,少數民族基層社區中調節社會關系的重要人物往往都是本民族民間文學的精英。比如,在涼山彝族中,一個合格的“蘇易”“德古”必須熟悉家譜、習俗、諺語、民族神話、民間故事、過去的典型案例等。一般家支內部的糾紛爭議,由家支中的“蘇易”“德古”進行調解,如果是兩個不同的家支成員發生了爭議,則分別由各個家支的“蘇易”“德古”作為代表進行協商。一般由調解人和雙方當事人協商把時間、地點約定好,雙方當事人一般要分隔開,由“德古” “蘇易”穿梭于其間進行調解,并聽取雙方對相關問題的陳述與辯論,在整個案件情況事實清楚、責任大小劃定后,參與調解的“德古” “蘇易”就聚在一起進行合議,根據習慣法提出處理意見,然后引古論今,依據彝族習慣法中類似的事例說服雙方當事人接受調解意見,有時一天調解不成,可以連續調解幾天,直到雙方當事人都接受調解意見為止。在一種共同價值體系下,熟悉這種符號系統的“德古”“蘇易”們對蘊藏在古歌、民間故事、諺語中規范和意義進行重申,引發當事者的共鳴,進而達成一致或促使雙方接受調解結果。只有在具有意義共同性的社會中,才有可能通過協商作為解決社會紛爭的主要手段,否則就需要更多的依賴強制性手段和規范化手段。可以看出,這種社會關系的調節得益于“德古”和“蘇易”們對于民族民間文學的精通,他們往往熟記古歌、善講故事,在民間文學的知識庫中獲取說服他們的邏輯和援引為案例的典故。
第二,社會關系調節者以故事傳說作為社會仲裁的參考案例。西南地區少數民族地區的榔規、款約、理辭等一般都是比較寬泛的一般性原則,難以直接作為裁決爭議糾紛、調節利益關系的準繩。例如,很多地區的榔規、款約中有禁止子女對父母不孝的規定,貴州黎平、榕江地區的侗族款約中有“不許勾生吃熟”“不許不孝”等規定[19]141-144。但是對于認定“不孝”或“勾生吃熟”等條款的標準則沒有具體規定。因此,施用榔規的理老對于這些原則的理解和解釋就成為仲裁的關鍵。所以,理老需要熟悉古理、古規,處事公正無私,糾紛爭議的仲裁過程往往是一個說理的過程,其中的基本依據主要來自于理辭、古歌、故事傳說中的相關內容,對于這些基本規范原則的解讀和解釋必須依據所處的具體社會環境(村寨、鼓社)對于這些規范的普遍認知,否則就難以說服他人接受裁決,達成共識。值得注意的是,理老們并沒有因此壟斷對榔規、款約的解釋權。因為理老是不脫離生產活動的普遍勞動者,沒有任何超越群眾之上的特權,理老須具備的條件及其去留取決于公眾意志。不同于高度分化的現代社會,這種將調解、協商、仲裁集于一身的整體式治理路徑具有多重意義,既是治理過程、又是社會教育傳播過程。民族同胞通過故事傳說實現了用口頭傳統承載價值觀教育和規則教育的效果,讓一般民眾在故事的講述中成長為群體的一份子,幫助完成個體的社會化過程,促進社會的團結。
2.對于社會矛盾調解的啟示
少數民族同胞通過民間文學形式創造的智慧在很多方面與現代民主治理建設中的政治思維不謀而合。具體來看:第一,作為調解人的“德古”、“蘇易”等民族精英并沒有高于一般成員的特權,而是以德高望重的“資深人士”身份介入社會事務,避開了權威體制自上而下的體制壓力,在解決爭議糾紛的過程中不產生新的矛盾,不以威權和強制力壓制、掩蓋矛盾,有利于保持社會和諧。第二,每一次調解過程都是一次價值重申和道德教育的過程,所有的旁觀者作為見證人都置身于這種場域當中,在參與中得到教化和感染,并成為這一社會過程的組成部分。這種教育的效果是課堂教育無法比擬的,是一種在民主實踐中培養民主精神的方式。正如露絲·本尼迪克特所言,個體生活的歷史中,首要的就是對他所屬的那個社群傳統上手把手傳下來的那些模式和準則的適應。從嬰兒出生落地開始,社群的習俗便開始塑造他的經驗和行為。到咿呀學語時,他已是所屬文化的造物,而到他長大成人并能參加該文化的活動時,社群的習慣便已是他的習慣,社群的信仰便已是他的信仰,社群的戒律亦已是他的戒律[20]5。
因此,民族同胞依靠在長期生活中共同分享的價值信念和風俗習慣維系著社會秩序和人際關系,并以民間文學形式保存和傳播這些價值信念,讓民眾在喜聞樂見的民間文學審美中了解社會規則與倫理道德,有助于保持著一種相對和諧生活狀態和較低的社會管理成本。
結 語
不可否認,傳統的少數民族社會仍然是一種同質化較強的社會,在某種程度上是以犧牲個體的個性來獲得群體的一致性的。作為延綿了千百年的民族傳統和社會實踐,這些在險惡自然環境中艱難生活的先民們確實取得了讓人矚目的成就,文學、藝術、農業、建筑不一而足,每一個領域都透露著人類智慧的光芒。而在這些成就之中,最為重要就是包含了大量關于少數民族同胞們如何生活、如何共處的民族民間文學。在沒有文字的情況下,借助重申社會價值與行為規范的民間文學形式維持了像議榔、埋巖、合款這樣比較大的社會組織,并長時間保持了良好的組織傳承和規則的制訂、傳達、執行等功能,將社會的治理與民族文化的傳承很好結合起來,這不能不說是一種讓人驚嘆的創造,特別是對于正處于轉型期的中國社會而言,這一少數民族同胞在生活實踐中積攢的智慧寶庫是不可多得的精神財富。
我國社會正在經歷一個裂變過程,由于特殊的歷史原因,正經歷著工業化和后工業化同時進行的過程。過去社會所依賴的穩定性和確定性在這一環境中不再唾手可得,我們渴望在確保現代文明成果和多元價值的基礎上再次獲得一種傳統社會那樣的穩定性與確定性,但是我們不能回到過去,開歷史的倒車,像過去那樣用既有的、混合的、一元化的社會結構來實現這種穩定性與確定性。因此,當我們在現代社會與后現代社會的中轉站首鼠兩端時,望一眼與我們并肩前進了數千年的少數民族同胞們的民間文學寶庫,我們就會發現,少數民族同胞早已在千百年沉淀下來的故事、神話、歌謠中積累了大量關于社會規則、自然觀念、矛盾化解、風尚倡導等社會治理方面的智慧結晶,深入研究這些民族精神財富將十分有益于當代的社會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