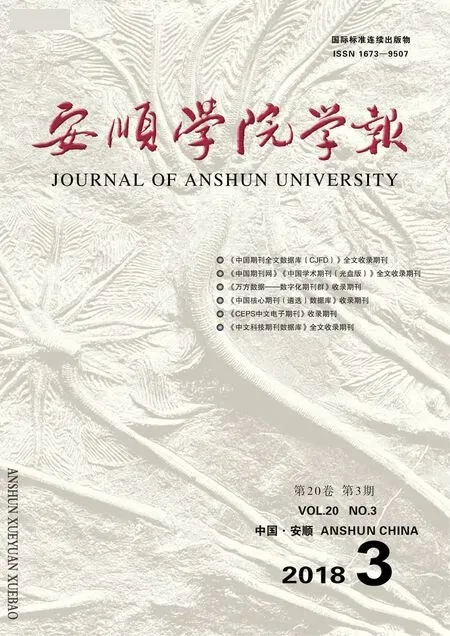儺儀中的面具表征與身份想象
——兼談舞劇《天蟬地儺》的面具之道
(貴州財(cái)經(jīng)大學(xué)文法學(xué)院,貴州 貴陽(yáng)550025)
儺文化在中國(guó)具有悠久的歷史,它在上古時(shí)代主要表現(xiàn)為一種具有巫術(shù)色彩的儀式。這就是所謂的儺儀。所以我們也可以說(shuō),儺儀是巫文化的一種特殊表現(xiàn)形式。按照學(xué)界通常的觀點(diǎn),儺儀首先是作為一種巫舞出現(xiàn)在原始狩獵活動(dòng)中。如果根據(jù)文獻(xiàn)的記載,儺舞在商周時(shí)期已經(jīng)發(fā)展成為一種儀式,這是沒(méi)有什么問(wèn)題的。郭凈說(shuō):“儺儀濫觴于史前,卻盛行于商周。”[1]這應(yīng)該是一種比較符合史實(shí)的觀點(diǎn)。儺儀作為巫文化的一種特殊形態(tài),其特點(diǎn)主要表現(xiàn)在面具的使用上,而儺儀中的面具使用則包涵了豐富的文化內(nèi)涵。國(guó)內(nèi)關(guān)于儺儀的研究著述,經(jīng)過(guò)幾十年的發(fā)展已成蔚然大觀,但是從文化研究的視角來(lái)進(jìn)行考察的卻還屈指可數(shù)。論文即從這一角度對(duì)儺儀面具的文化意蘊(yùn)進(jìn)行探討。
一、面具作為一種表征
在文化研究中,“表征”(representation)是一個(gè)重要的概念。對(duì)于表征的研究,著名的牙買加裔英國(guó)文化學(xué)者斯圖亞特·霍爾(Stuart Hall)算是一個(gè)重要的代表人物。霍爾在他主編的《表征》一書的導(dǎo)言中分析了他所提出的“文化的循環(huán)”這一觀念。所謂“文化的循環(huán)”,簡(jiǎn)單說(shuō)就是組成文化活動(dòng)的幾個(gè)要素中每?jī)蓚€(gè)要素之間都有一種相互影響的關(guān)系。這幾個(gè)要素是:生產(chǎn)、消費(fèi)、規(guī)則、表征、認(rèn)同,而表征則是這一循環(huán)過(guò)程中的一個(gè)重要環(huán)節(jié)。
何為表征?霍爾在其所撰《表征的運(yùn)作》一文中說(shuō):“簡(jiǎn)單地說(shuō),表征就是通過(guò)語(yǔ)言生產(chǎn)意義。”[2]16按照霍爾的觀點(diǎn),作為表征的事物,它的自身并不具有任何清晰的意義,它們只是承載意義的媒介。也就是說(shuō),起表征作用的事物只是相當(dāng)于一個(gè)能指。那么表征的意義從何而來(lái)?他認(rèn)為:“意義是由表征系統(tǒng)所建構(gòu)的。”[2]21他還說(shuō):“意義并不內(nèi)在于事物中,不內(nèi)在于世界中。它是被建構(gòu)的,被生產(chǎn)的。它是一種意指實(shí)踐的結(jié)果,這種實(shí)踐生產(chǎn)意義,使事物具有意義。”[2]24這種意指實(shí)踐是與特定的文化空間緊密相關(guān)的,是由文化成員在文化實(shí)踐中共同建構(gòu)起來(lái)的。
霍爾認(rèn)為,文化涉及的問(wèn)題主要是意義的共享,這種共享就是意義的生產(chǎn)與接受。這種意義的生產(chǎn)與接受就是通過(guò)表征的方式來(lái)完成和實(shí)現(xiàn)的,而這種表征就是語(yǔ)言的表征。這樣,我們只有進(jìn)入共同的語(yǔ)言才能實(shí)現(xiàn)意義的共享。盡管霍爾主要是分析語(yǔ)言的表征,但是其實(shí)表征又不僅表現(xiàn)為通常意義的語(yǔ)言。我們當(dāng)然也可以在非常廣泛的意義上理解這個(gè)語(yǔ)言。他也說(shuō):“在語(yǔ)言中我們使用各種記號(hào)與符號(hào)(不論它們是聲音、書寫文字、電子技術(shù)生產(chǎn)的形象、音符,甚至各種物品)來(lái)代表或向別人表征我們的概念、觀念和感情。”[3]2這就是說(shuō),凡能夠起到表征作用的文化事物都可以視為語(yǔ)言。
儺儀面具,就是一種獨(dú)特的文化語(yǔ)言。面具如同一般語(yǔ)言那樣,也是作為一種表征來(lái)運(yùn)作的,而這種表征的運(yùn)作就是一種特殊的實(shí)踐。霍爾說(shuō):“文化與其說(shuō)是一組事物,不如說(shuō)是一個(gè)過(guò)程,一組實(shí)踐。”[3]3這種實(shí)踐就是他所謂的那種“意指實(shí)踐”,這也就是意義的生產(chǎn)、接受與共享。作為表征的事物,其功能就是完成這樣的一種意指實(shí)踐。換句話說(shuō),這種意指實(shí)踐就是表征的核心方式。
表征,就是面具實(shí)現(xiàn)其功能的方式。面具作為一種表征,自然有其不同于其它表征方式的特殊性。霍爾非常強(qiáng)調(diào)文化的實(shí)踐意義,面具文化當(dāng)然也具有一種實(shí)踐性質(zhì)。但是,只有當(dāng)人戴上面具進(jìn)行舞蹈或表演時(shí),面具的意義才真正表現(xiàn)出來(lái)。這也就是說(shuō),面具只有在它的特殊語(yǔ)境中,才得以實(shí)現(xiàn)意義的建構(gòu)與共享。當(dāng)面具被懸掛起來(lái)或收藏起來(lái)的時(shí)候,它的意義便是一種隱匿的存在;即使它被“開光”過(guò),即使它在人們的心目中,具有了一種神性,但它的意義仍然是潛在的。只有當(dāng)它戴在人的面前,在戴面具者操演起來(lái)的時(shí)候,這種意義才顯現(xiàn)出來(lái),才算進(jìn)入了它的建構(gòu)過(guò)程。
當(dāng)儺表演者戴上面具時(shí),面具的語(yǔ)境也就發(fā)生了變化。不過(guò)這種語(yǔ)境是由一種現(xiàn)實(shí)的語(yǔ)境轉(zhuǎn)變?yōu)橐环N想象的語(yǔ)境。所以,面具的表征是具有想象性的,它并不保證新的語(yǔ)境的真實(shí)性。也就是說(shuō),儺儀中的這種意指實(shí)踐,未必就指向意義的真正實(shí)現(xiàn)。但是,在前現(xiàn)代的思維中,這種想象的語(yǔ)境卻被認(rèn)為是真實(shí)的。在這種語(yǔ)境中,表征與實(shí)在是同一的。
通常認(rèn)為,真名代表它所指的對(duì)象,假名是不代表這個(gè)對(duì)象的。但其實(shí),名字作為一種符號(hào)表征,真名與假名是沒(méi)有本質(zhì)區(qū)別的,它們都不等同于實(shí)在本身。不過(guò),在前現(xiàn)代的思維中,作為表征的符號(hào)與實(shí)在之間具有一種同一的關(guān)系。對(duì)于孫悟空,不管是他的真名還是假名,只要他答應(yīng),就都與他這個(gè)人本身保持同一。在這種思維下,表征符號(hào)與表征本體之間建立了一種同一性。在面具文化中,這種同一性是按照一種相似律來(lái)得到建構(gòu)的。這種相似律,在弗雷澤(J.G.Frazer)那里被表述為順勢(shì)巫術(shù)。他說(shuō):“‘順勢(shì)巫術(shù)’所犯的錯(cuò)誤是把彼此相似的東西看成是同一個(gè)東西。”[4]因?yàn)槊婢吲c其所代表的神具有相似性,所以戴面具的人也就被等同于神。
面具的表征意義是想象性的,但是這種想象性的意義又被面具所在的文化成員認(rèn)為是一種真實(shí)的存在,就導(dǎo)致了面具意義的神秘性。在儺儀中,與面具相關(guān)聯(lián)的是神性的東西,而神是不可見(jiàn)的。這同樣使得面具的表征意義具有了一種神秘性。這種神秘的表征,其功能表現(xiàn)為對(duì)人的行為的一種規(guī)范,而這種規(guī)范尤其在作為儀式的文化形式上得到體現(xiàn)。這樣,儺儀就能幫助一個(gè)群體建立一種道德規(guī)范。我們也可以說(shuō),儺儀面具表征著一種想象的事物與秩序。由此而來(lái),儺戲中的想象語(yǔ)境也多是引導(dǎo)一種現(xiàn)實(shí)秩序的建構(gòu)。郭凈認(rèn)為,儺儀與封禪、郊祀等祭典共同構(gòu)成維護(hù)中央集權(quán)體制的巫術(shù)禮儀制度。
關(guān)于表征,我們還可以將拉康的理論與霍爾的理論結(jié)合起來(lái)進(jìn)行理解。拉康提出了一個(gè)“想象-象征-實(shí)在”的理論,與霍爾的表征理論具有可以溝通的內(nèi)涵。何謂“想象-象征-實(shí)在”?拉康說(shuō):“即由能指代表的象征,由意義代表的想象,和在歷時(shí)層面上實(shí)際發(fā)生的話語(yǔ)的實(shí)在。”[5]語(yǔ)言的三個(gè)維度,在面具這種表征媒介上同樣得到體現(xiàn)。面具表征即是象征,它具有一種想象的維度,而文化的意指實(shí)踐就是一種實(shí)在的維度。拉康的實(shí)在界可以用霍爾這種“意指實(shí)踐”來(lái)理解。當(dāng)然,我們的語(yǔ)言是歷時(shí)性的,但是面具作為一種表征卻主要體現(xiàn)為共時(shí)性的。它的意指實(shí)踐也即一種話語(yǔ)的實(shí)在。
面具作為儺文化的一種表征方式,凝聚了儺文化群體的宗教意識(shí)、審美意識(shí)與道德意識(shí)等。首先,儺面具集中體現(xiàn)了儺文化群體的宗教意識(shí):儺儀驅(qū)鬼時(shí),人戴上面具本身就體現(xiàn)了文化群體的神鬼信仰;而在很多儺戲文化圈中,面具也逐漸形成了一個(gè)個(gè)相對(duì)穩(wěn)定的神靈譜系。此外,在儺儀與儺戲中,還有許多關(guān)于面具的禁忌,也同樣反映了儺文化群體的宗教意識(shí)。其次,面具的造型、著色以及風(fēng)格不僅與其表征意義具有緊密的關(guān)系,同時(shí)也體現(xiàn)了儺文化群體的審美風(fēng)尚。再次,面具所表征的這些宗教意識(shí)與審美意識(shí)也同樣表現(xiàn)著儺文化群體的愛(ài)憎與善惡觀念。
二、儺儀中的身份想象
儺儀中的面具表征還涉及到另一種意義,即身份的表達(dá)。當(dāng)然,這種表征也是在一種想象的語(yǔ)境中實(shí)現(xiàn)的,所以這種身份也是一種想象的完成,盡管對(duì)于前現(xiàn)代的思維來(lái)說(shuō)這種轉(zhuǎn)換可能是真實(shí)的。儺儀中的身份轉(zhuǎn)換是從人轉(zhuǎn)變?yōu)樯瘛畱蛑杏羞@樣的俗語(yǔ)“戴上臉殼就是神,放下臉殼就是人。”[6]82臉殼,在儺文化中就是面具。所以,儺儀中的面具并不單是起一種中介的作用,它更是讓儺師成為神的一種方式。
我們知道,儺文化是巫文化中的一種特殊表現(xiàn)形式。許慎在《說(shuō)文解字》中說(shuō):“巫,祝也。女能事無(wú)形,以舞降神者也。”[7]357許慎所說(shuō)的“無(wú)形”也就是神。神降下之后附于巫的身體,這時(shí)巫就成了神的代言人。在柏拉圖那里,抒情詩(shī)人就是這樣的一種存在。他說(shuō):“科里班特巫師們?cè)谖璧笗r(shí),心理都受一種迷狂支配;抒情詩(shī)人們?cè)谧髟?shī)時(shí)也是如此。”[8]按照柏拉圖的觀點(diǎn),這種迷狂就是神靈附體。如果說(shuō)儺是一種特殊的巫,那么這種特殊性主要體現(xiàn)在兩個(gè)方面。其一是功能的特殊:巫是降神,儺是驅(qū)疫。其二,儺與巫獲得神的身份的方式也是不同的。巫是以舞降神而通神,儺是戴著神的面具起舞。在這種舞蹈中,儺者就是神的化身。在儺儀中,面具使得儺師也達(dá)到一種神靈附體的迷狂狀態(tài)。
在古儺儀式中,方相是主神,進(jìn)入這種神靈附體的是方相氏。《周禮·夏官司馬》中說(shuō)方相氏之職:“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zhí)戈揚(yáng)盾,帥百隸而時(shí)難,以索室驅(qū)疫。大喪,先柩;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驅(qū)方良。”[9]826-827“難”即“儺”。段玉裁《說(shuō)文解字注》說(shuō):“‘儺,行有節(jié)度。’按,此字之本義也。其驅(qū)疫字,本作難。自假儺為驅(qū)疫字,而儺之本義廢矣。”[7]646“方良”即“罔兩”,也即“魍魎”。鄭玄在《周禮》注中說(shuō):“冒熊皮者,以驚驅(qū)疫癘之鬼,如今魌頭也。”[9]826所謂“魌頭”,也就是我們現(xiàn)在所說(shuō)的面具。
在儺儀中,面具不僅表征著一種性格,更是表征一種身份的變化。面具構(gòu)成了身份的轉(zhuǎn)變。郭凈說(shuō):“人們塑造面具,就是在塑造另一個(gè)自我,一個(gè)超脫于你我他之上的具有象征意義的自我。”[10]1“面具的功能在于掩蓋表演者的個(gè)性而顯示角色的神性。”[10]5當(dāng)然,并不是所有的面具都能具有這樣的功能。娛樂(lè)面具在這方面的功能就被大大弱化,但是在儀式中的面具卻主要為了實(shí)現(xiàn)這樣的一種功能。按照這種邏輯,在儺儀式中,神成為一種自我的鏡像。所以,這種身份的轉(zhuǎn)變是由一種自我達(dá)到一種超我。
儺儀式中的這種身份轉(zhuǎn)變,包涵了雙重的意蘊(yùn):首先,通過(guò)面具,這種身份獲得了他人的認(rèn)同。戴上面具,則意味著進(jìn)入了一種藝術(shù)程序或表演程序。對(duì)于表演的認(rèn)同,就是對(duì)表演者身份轉(zhuǎn)變的一種認(rèn)同。當(dāng)然,這種認(rèn)同其實(shí)是一種臨時(shí)的與想象的實(shí)現(xiàn)。儺戲中有所謂“開光”、“點(diǎn)像”、“藏魂”等儀式環(huán)節(jié),這是賦予面具以神性,面具就成為神祇的化身,這樣,戴上面具的人就完成了一種身份的轉(zhuǎn)換。
面具與戲劇臉譜是有區(qū)別的。臉譜只是通過(guò)化妝來(lái)表現(xiàn)人物的一種性格,有些面具也是這樣的一種功能,但儺文化中的面具卻不是這樣的。庹修明說(shuō):“面具并不是一種化妝術(shù),而是將人的靈魂輸送到另一個(gè)世界里去的運(yùn)載工具。”[6]34他還說(shuō):“在老藝人看來(lái),神靈本身存在于樹木之中,雕刻者只不過(guò)是把神靈復(fù)制出來(lái),請(qǐng)進(jìn)儺壇。”[6]42所以,在儺文化語(yǔ)境中,面具就是神的化身。
其次,儺儀表演還是群體成員身份認(rèn)同的一個(gè)過(guò)程。文化中的意指實(shí)踐本身就是一個(gè)身份認(rèn)同的過(guò)程。表征就是一種語(yǔ)言游戲,它的意義與其所在的生活世界是有緊密關(guān)系的。歸屬于一種文化,就是歸屬于一種表征系統(tǒng)。通過(guò)表征系統(tǒng)的意指實(shí)踐,隸屬于一種文化中的個(gè)體之間可以達(dá)到一種身份認(rèn)同。儺壇,是儺儀舉行的空間,儺壇就成為一個(gè)具有象征功能的神性空間。進(jìn)入了這樣的一個(gè)空間,就意味著進(jìn)入了一種文化身份的認(rèn)同期待。
在身份轉(zhuǎn)變的同時(shí),面具還實(shí)現(xiàn)了一種特殊的觀看機(jī)制。《周禮》中說(shuō)方相氏“黃金四目”,實(shí)際就是涉及了這樣的觀看機(jī)制。“四目”隱含著方相氏的觀看已然不同于常人的觀看,它成為神對(duì)人的觀看。如三星堆出土的青銅面具中有一具是眼睛凸出很長(zhǎng)的樣子,這表明戴面具者的觀看是要達(dá)到一種常規(guī)觀看所不具有的特殊維度。
從精神分析的角度說(shuō),戴上面具的觀看實(shí)際上滿足了人的一種窺視欲。在儺戲的面具中,眼睛的地方一般都有眼珠,而只是在眼珠周圍挖出一個(gè)小洞。這種雕刻方式更增加了觀看者眼睛的神秘性,這也在某種程度上增加了表演者的窺視感。
三、舞劇《天蟬地儺》的面具之道
在這種身份表征與觀看機(jī)制的理論背景下,我們嘗試分析一下由丁偉執(zhí)導(dǎo)的大型民族舞劇《天蟬地儺》中面具的使用所產(chǎn)生的藝術(shù)意蘊(yùn)。這臺(tái)舞劇將現(xiàn)代音樂(lè)與貴州的古儺文化和侗族音樂(lè)融為一體,是展現(xiàn)貴州少數(shù)民族藝術(shù)的一臺(tái)精致的作品。該劇自2009年在北京首演以來(lái),獲得了無(wú)數(shù)的好評(píng),并獲得多項(xiàng)國(guó)家級(jí)大獎(jiǎng)。
這出舞劇表現(xiàn)的是發(fā)生在年輕的土家族儺戲藝人“倉(cāng)”與美麗善良而深愛(ài)儺戲藝術(shù)的侗族姑娘“蟬”之間的一場(chǎng)愛(ài)情悲劇。年輕的儺戲藝人“倉(cāng)”,在儺戲上有著精湛的技藝;但是由于臉上的一塊傷疤,而不愿以真面目示人,在表演儺戲之余只與自己雕刻的面具在一起孤獨(dú)地生活。在他表演儺戲過(guò)程中,經(jīng)常觀看他的儺戲表演的侗族女孩“蟬”因?yàn)樗募妓嚩饾u深愛(ài)上了他。但同時(shí),另一個(gè)青年“卯”也愛(ài)上了“蟬”。于是,在三人之間發(fā)生了一場(chǎng)曲折而凄愴的愛(ài)情悲劇。這臺(tái)舞劇的故事線條雖說(shuō)曲折但也并不復(fù)雜,也并不是特別具有新意。但是它在融合少數(shù)民族文化方面,無(wú)疑獲得了巨大的成功。作品《天蟬地儺》巧妙地將儺戲穿插成故事的有機(jī)組成部分。不僅舞劇的敘事由儺戲來(lái)推動(dòng),而且儺戲面具在展現(xiàn)人物性格與情節(jié)沖突上有著重要的作用。
男主人公倉(cāng)的臉上有一個(gè)傷疤,這使得他變得內(nèi)向而怯懦;而面具就成了他的身體殘缺的掩飾,也成了他的內(nèi)心自卑的掩飾。這樣,戴上面具的倉(cāng)與不戴面目的倉(cāng)判若兩人:在人前表演時(shí)展現(xiàn)出來(lái)的是其自信與勇敢,在人后孤獨(dú)時(shí)展現(xiàn)出來(lái)的則是他的自卑與傷感。這種變化就是由于他的技藝與其身體缺陷的反差所造成的,而面具正好成了這兩種性格的中介,也正是面具使得故事變得更為曲折。當(dāng)然,在《天蟬地儺》這臺(tái)舞劇中,面具與身份的關(guān)系有了一個(gè)更加獨(dú)特的表現(xiàn)。倉(cāng)戴上面具不僅是身份的轉(zhuǎn)變,同時(shí)也是對(duì)現(xiàn)實(shí)身份的一種逃避,而這種逃避正好為演出的敘事造成了波瀾。這樣,在故事中,倉(cāng)的身份存在著一種分裂,而面具是這種身份分裂的界線。換句話說(shuō),面具之下隱藏著倉(cāng)在虛假身份與真實(shí)身份之間的掙扎。所以,在該劇中,儺戲面具不是拼合到作品中,而是與故事的敘事達(dá)到了一種深度的融合。
從儺儀到儺戲是儺文化從神圣化到世俗化的一個(gè)重要標(biāo)志。盡管如此,儺儀的信仰成分在儺戲中也仍然得到了部分的保留。正如李子和所說(shuō):“儺面具延展傳承于儺戲中,則存在著超越一般戲劇的所謂道具的性質(zhì),儺面具本身就是民間信仰的凝聚和外形化。”[11]不僅如此,儺儀中的面具表征與身份想象仍然在儺戲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xiàn)。
面具掩蓋了倉(cāng)因傷疤而產(chǎn)生的自卑。正由于儺面具的表征意義,戴上面具的倉(cāng)獲得了一個(gè)超我。不僅如此,他在戴上面具的時(shí)候,還能獲得他人的尊重。盡管在這種祛魅化的節(jié)日表演中,人們已經(jīng)知道這是一種娛樂(lè),但是神的面具還是在潛意識(shí)中讓觀眾改變了觀看的態(tài)度。所以,戴上面具之后的觀看是不平等的。
卡瓦拉羅(Dani Cavallaro)認(rèn)為,凝視(gaze)體現(xiàn)了一種與視覺(jué)有關(guān)的權(quán)力關(guān)系;我們凝視某人或某事時(shí),目的是要控制它們。[12]儀式是為了獲得凝視,表演也是為了獲得一種凝視。但是在儺戲表演中,由于儺表演者的身份轉(zhuǎn)變,觀眾對(duì)于儺戲的觀看與凝視體現(xiàn)出來(lái)的卻是卡瓦拉羅所說(shuō)的那種權(quán)力關(guān)系的顛倒。觀看儺戲的觀眾不是為了控制儺表演者,而是對(duì)儺表演者表現(xiàn)出一種敬畏的態(tài)度,因?yàn)閮硌菡咴谀撤N程度上已經(jīng)成為了神。這種權(quán)力關(guān)系在當(dāng)今的粉絲文化中達(dá)到一種極致的體現(xiàn)。所以,該舞劇雖說(shuō)是以“天蟬地儺”為名,但是從觀看這個(gè)層面來(lái)說(shuō),這種身份實(shí)際上卻被顛倒了。因?yàn)閭}(cāng)是神的化身,所以戴上面具的倉(cāng)是以神的目光對(duì)著觀眾,而蟬的觀看則是人的觀看。這樣,我們就可以說(shuō),倉(cāng)代表的是天,而蟬代表的卻是地。這就是面具的身份表征所產(chǎn)生的一種微妙的作用。
蟬正是因?yàn)閷?duì)儺戲藝術(shù)的熱愛(ài)與對(duì)倉(cāng)的真實(shí)身份的追尋而逐漸深深地愛(ài)上了他。但是,倉(cāng)為了不讓人看到他的本來(lái)面目,而在觀眾面前從不摘下他的面具。由于面具對(duì)人的身份增添了一種神秘性,這種神秘性倒更激起了蟬要了解他的身份的渴望,并且這種渴望因他的表演而成為一種愛(ài)戀。但是實(shí)際上,面具的掩蓋使得蟬的愛(ài)情是很危險(xiǎn)的,因?yàn)楸碚鞑⒉槐WC其與真實(shí)存在的必然聯(lián)系。幸而,倉(cāng)不僅有著精湛的技藝,也有著善良的品性;蟬也并沒(méi)有因其面貌的缺陷而放棄他,而是以其真誠(chéng)的愛(ài)使得倉(cāng)能夠勇敢地面對(duì)現(xiàn)實(shí)。但是二人的愛(ài)情因卯的介入而最終成為一幕悲劇。在這愛(ài)情的糾葛中,面具始終起到了推動(dòng)敘事的作用,這無(wú)疑是這臺(tái)舞劇的高明之處。
- 安順學(xué)院學(xué)報(bào)的其它文章
- 計(jì)算機(jī)硬件課程體系數(shù)字化實(shí)驗(yàn)教學(xué)平臺(tái)初探
- 典型巖溶區(qū)水土流失動(dòng)態(tài)監(jiān)測(cè)研究
- 農(nóng)業(yè)現(xiàn)代化、新型工業(yè)化、城鎮(zhèn)化協(xié)調(diào)發(fā)展探析
——基于貴州九個(gè)地州市的面板數(shù)據(jù) - 鋁硅酸鹽礦物復(fù)合材料吸附亞甲基藍(lán)性能研究
- 信息化對(duì)制造業(yè)產(chǎn)出增長(zhǎng)的貢獻(xiàn)度
——基于面板分位數(shù)回歸的分析 - 高職院校大學(xué)生人際關(guān)系現(xiàn)狀及對(duì)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