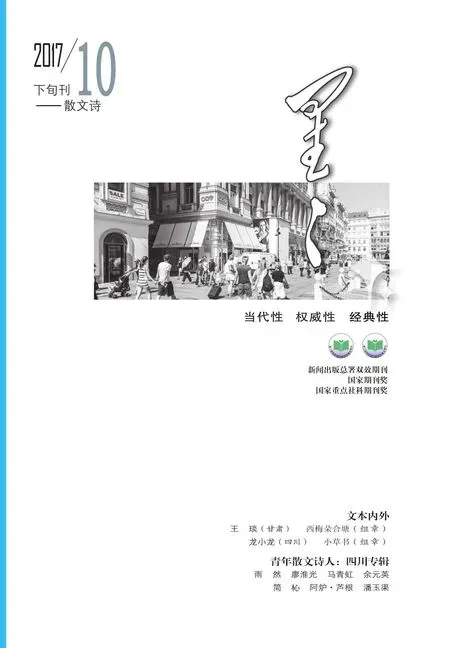寫在扉頁(組章)
陳旭明(湖南)
寫在扉頁(組章)
陳旭明(湖南)
沈從文
“選小地作基礎,用堅硬石頭堆砌它。精致,結實、對稱,形體雖小而不纖巧,是我理想的建筑,這廟供奉的是‘人’。”——沈從文(1902—1988)
一個老人。一卷黃昏。
胡同口的暮色,是不是比陪伴你的那把藤椅陳舊?
長河悠悠,心路亦悠悠。心靈,只為鄉音放縱。遠處的木葉、笙歌、儺舞,舟纜綰不住的漣漪、落花、鳥音,啟開靈魂的舞蹈。
有人能一步登天。有人至死難回鄉。連天風暴讓多少至情至性者鎩羽,歷史,有時不得不靠金雕玉綴的華衣遮掩瘢痕和創口。諦聽檐角雨聲嘀嗒,你心境靜水無波,俯身把目光投向歲月深處,讓美復活。
寂寞有時是幸福的。是另一種遠游。
人生如逆旅。從軍營到講臺,從傳世文章到故紙堆,完成這樣一種歷練,需要咀嚼多少破繭之疼?
野性,只在骨里鏗鏘。
愛讓人生真實,也讓人生疼痛。
曾經,多少燈火近黃昏。筆,墨,紙,硯,茶——花開給自己看,卻讓許多眼,找到了風景。
圭臬永遠。敬仰永恒。美,來自極致的蠱惑。
展館能讓什么價值連城?
那個人也許明天回來。吊腳樓老了,支柱依然插在水中苦苦支撐,靜靜守候。綠水青山,赤子情懷合而為一,是人之夢?還是山之幸?
“鄉下人”,三個字,讓無數名片上鍍金的身份暗淡無光。
帕 斯
“它每天創造自己,也將我創造。”——帕斯(1914—1998)
魔幻,才是真正的人生。
詩之魔。在陽光下站成一棵樹,風一來,所有的陰影全流成河,把景致一寸一寸推遠。
夢,在讖語的海拔之上。
教堂上的熹微是不可把握的;唱詩班的祈禱聲是虛幻縹緲的。所有的真實來自一夕性愛之后茫茫的空,圖騰,晃動在無形之中。
如何把陽光提煉成金?又如何把月色雕塑成銀?
黎明精致如一幀小品,你為何獨獨喜歡穿越狂草體的天空,在午夜無人的街道上等待閃電,以及一個陌生人的問答?
天堂鳥,把天空一點點啄空。
中午慢慢地彎曲,影子還在筆直地走,像一棵樹向春天跋涉。人,還是不是那個人?
一天即一瞬。風把時間的掌紋吹動。
白晝的月亮,在夜晚是唇。你的傾訴,讓一些不能提著耳朵飛離地面的欲望,在詩中完成。
詩人,僅僅是修補光陰的工匠。
時間輪回。宇宙再生。
人生魔幻。詩即產生。
策蘭
“死亡是花,只開放一次。/它就這樣綻開,開得不像自己。”——策蘭(1920—1970)
一個自溺的名字,浮出塞納河水面,被死亡的冷鍍亮。
出生即死亡的起步。
誰也無法選擇身世。
在朋友掩護下幸免于難的你,頓悟:真正的世外桃源,莫非是母親的子宮?
流亡,為生命尋找避難所。從德國到法國,有時候,詩意地棲居無異于癡人說夢。
《死亡賦格》——為生命的凋謝一詠三嘆。多好——多災多難的大地上,總有地方不經意地飄蕩出來自伊甸園的詩韻。
詩歌終生囚禁靈魂。多少漫漫長夜,孤獨的燈盞,被照亮。靜聽一瓣花開,你的手在撫摸屬于誰的秋天?
月光如水,難掩詩箋的蒼白。
在異鄉無處話凄涼。因此,你選擇瘋人院,無人干擾,直接與上帝通話。
人如謎,詩如謎;
生是謎。死是謎。
人生本來就是晦澀的,如詩。
濺起一聲巨響,讓生命把河流撞開一個永難愈合的傷口。一朵浪花搖曳里,生如花開,死亦如花,在深夜徐徐闔上歌唱的嘴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