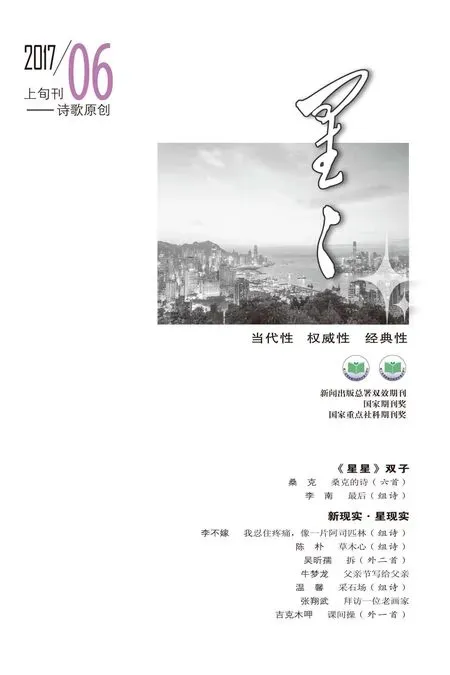真的“說出了它就戰(zhàn)勝了它”嗎
王建旗
真的“說出了它就戰(zhàn)勝了它”嗎
王建旗
按照語言哲學(xué)的觀點(diǎn),詩的詞語指稱在與它的指稱對(duì)象(存在)之間有著一道巨大的鴻溝,語言在穿越這道鴻溝之后所能企及的卻不是存在的本質(zhì),而只能是其表象。因此,存在是個(gè)歧義的詞匯,它“有時(shí)用來意味構(gòu)成現(xiàn)實(shí)世界的實(shí)在的事物,事件,事實(shí)和人,有時(shí)指終極的或形而上學(xué)的實(shí)在,它們是處于事物和人的世界之后和之上的某種東西”(《西方語言哲學(xué)》第3頁) 。這實(shí)質(zhì)上是指存在的理由,它們構(gòu)成了人類精神世界的基礎(chǔ)。數(shù)千年來,探求這種世界本原和形而上學(xué)的沖動(dòng)鼓舞又毀滅了無數(shù)(廣義上)詩人的雄心壯志……以致到二十世紀(jì)維特根斯坦一句極為“普通”的話——“對(duì)不能言說的東西要保持沉默”竟成為哲學(xué)界一再引證的至理名言。維特根斯坦邏輯實(shí)證主義的同仁們大肆非難形而上學(xué),他們強(qiáng)調(diào)“所有沒有關(guān)于數(shù)和量的抽象推理”和“沒有事實(shí)與實(shí)在的經(jīng)驗(yàn)推理”的書籍都應(yīng)當(dāng)付之一炬,認(rèn)為對(duì)于世界“這兩個(gè)命題已窮盡無遺”。整個(gè)二十世紀(jì)后半葉以來的詩歌寫作就籠罩在這樣的文化思潮當(dāng)中,使詩人們所從事的常常是一種憤懣的寫作,寫著寫著對(duì)精神世界無限性的自覺就遭到了限制……
但這樣也好,作為“談?wù)撝饕獑栴}”的人,在時(shí)代消解了形而上學(xué)的基原之后,我們正好可以借以“心安理得”地去“談?wù)?世界的表象、世俗的社會(huì),權(quán)且把這個(gè)世界的囂鬧當(dāng)做“主要問題”來談?wù)摚⑶胰σ愿啊P闹轮尽⒉挥?jì)后果地去談……我雖然在近年間自覺地加盟了這種趨向于“平面化”的“談?wù)摗保瑖L試一種包容、不潔、粗糙和“非純?cè)娀钡膶懽鳎嗄陙韨鹘y(tǒng)的詩歌精神綿延到主觀意識(shí)內(nèi)讓我殺不死的野心和虛妄還是讓我給這些詩歌起了一個(gè)具有理想主義色彩的名字:《說出了它就戰(zhàn)勝了它》。但問題是——你有什么勝利可言?你能戰(zhàn)勝什么?如果不能給代表了這些事物的存在的“表象”指出重返其“本原”的路線,那么世界就永將是它們的天下,在與這個(gè)世界的搏斗中我們就無法對(duì)這個(gè)世界施以由衷的同情。因此,我們就不能不與這個(gè)世俗的世界斗爭(zhēng)到底!這是一項(xiàng)無望的工作,但你沒有理由與這個(gè)同樣沒有理由與自己講和的世界講和。面對(duì)這個(gè)沒有理由的失去歸宿的世界,詩歌喪失了信仰。它惟一可以踐行的就是把它們“說出來”,以戰(zhàn)勝、顛覆并使它們轉(zhuǎn)化為與之不同的東西的信心把它們“說出來”;不可能在事實(shí)上,可必須在主觀里讓眾聲喧嘩的世界獲得一種可以稍稍信賴的平衡力量,從而使存在世界不是完全地一頭栽倒進(jìn)它們無休止囂鬧的表象里,而是盡力讓其在平衡中親近本原和精神,留下虛擬的回旋余地。
所以,我主張讓詩歌貼近世界的表象,但努力對(duì)世界的理由也即存在的形而上學(xué)潛在地留下缺口,以表達(dá)遺憾和可能的幻想(和幻象);進(jìn)而認(rèn)為在此語境內(nèi)產(chǎn)生的詩歌應(yīng)當(dāng)是與世界的世俗性同歸于盡的詩歌,它會(huì)在與世界的較量和搏斗中同時(shí)撲倒在地,以便為真正意義上的詩歌讓路。這或許就是我(我們)的意義所在,既是當(dāng)下被給定詩歌的特征,亦是宿命中這一代詩人的命運(yùn)。